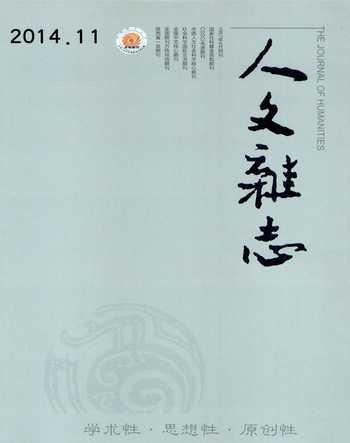中国与一战:中立国身份下的预筹与会
侯中军
内容提要 一战爆发后,为保全自身利益,北京政府因求中立而不可得,开始筹划加入战后和会。在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先派驻巴西公使刘式训赴欧调研,继之以外交部参事夏诒霆为特使探询欧洲各国状况。为达到参会目的,外交部分别分析了交战双方及中立国的态度,在中国屡求参战而不可得的状况下,为设想以中立国身份出席和会作了大量外交调研。外交部在中国参战前所做的这些调研,为中国做出正确的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战争的走向决定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方向,随着中国对德宣战,参会之议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关键词 参会外交 刘式训 夏诒霆 一战 巴黎和会
〔中图分类号〕K25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11-0082-09
中国走向一战的过程,基本上可以表述为从中立到参战。各种复杂形势下的国内政争及外交方针都是在这两种情势下展开的。学界现有研究认为:北京政府认识到,在中立的情形下,只有参加战后和会,才有可能维护中国利益,收回被日本侵夺的山东权益。虽然对参战之争已经有了相当精深的研究,并对争取参加战后和会一事时有涉及,但对中立时期北京政府为参会所做出的外交努力,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由于材料的缺乏,即使对于参会外交的一些史实亦缺乏必要的了解。 目前关于中立身份下的参会外交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王建朗:《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一文,此外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黄嘉谟:《中国对欧战的初步反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第1期)、徐国琦著:《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马建标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对中国而言,参战并非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参会,如果忽略了这一目的,可能无法充分认识参会外交的重要性。
事实上,我们所了解较多的是参战以后的事情,其中包括中国如何在巴黎和会上力争收回山东的外交活动,而在参战以前,民国外交部曾为如何加入大会作过细致而认真的努力,这部分外交活动,一直曾被遗忘。本文试图从外交决策过程出发,围绕参会决策的实施,主要梳理驻外使领与外交部之间的外交活动。如何寻求在不参战的情形下,而达到加入和会的目的,是本文所论述的主要内容,参考的主要是一线外交人员的建议。
一、参会之初议
欧战爆发后,为避免战火延及中国境内,袁世凯于1914年8月6日颁布大总统令,宣布“对于此次欧洲各国战事,决意严守中立”。 《大总统袁世凯关于严守中立令》,1914年8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83页。几乎同时,北京政府又提出限制战区的设想,并希望美、日政府出面“限制战区,保全东方。劝告交战各国,勿及远东”。 《外交部致陆宗舆电》,1914年8月6日,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三联书店1980年,第39页。但此举遭致日本反对,未能成功。 限制战区提议交涉经过,见黄嘉谟:《中国对欧战的初步反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第1期。日本很快参加战团,出兵山东。山东问题成为当时中国外交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其核心当是设法收回被日本侵占的青岛、胶济铁路及相应的权益。能达到此目的的最佳外交途径,莫过于参加战后和会,于会上伸张自身的权利及主张。为了获得参会资格,一是参加战团,成为交战国;二是出面调停,以调停国的身份得以参加和会。在参战之议屡被否决的情形下,出面调停,以调停者的身份获得参会资格成为现实选择。正是在此种背景之下,北京政府一方面另谋参战的可能,另一方面寻找一条可以参加和会的第二条道路。
目前所见到的材料,驻美公使夏偕复是较早提出中立参会的人。1914年8月5日,夏偕复建议外交部请大总统出面,致电德、奥、俄、法、英等国,做出调处姿态。夏认为,如此行为,中国可以获得三项利益:一是使中国在列强中占一位置;二是战事停止时,中国可以调解人的资格出席战后会议,以图保全中国无限权利;三是以调解为第一步办法,如调解无效,再以缩小战区为议。 参见黄嘉谟:《中国对欧战的初步反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第1期。梁士诒是另一个较早提出参加战后和会的人,但梁的办法是通过参战获得参会资格,这一点与夏偕复不同。1914年8月中旬,梁士诒与袁世凯有过一次彻夜长谈,在此次谈话中,梁提出“不妨明白对德绝交宣战,将来于和议中取得地位,于国家前途深有裨补”。 凤冈及门弟子编印:《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1946年,第196页。虽然参战问题因国内、国外各种因素的制约,难以实现,但参加和会的构想,一直未曾中断。1914年8、9月间,北京政府内部已经有了详细的研究报告,从理论上探讨中国参加战后和会的可能及利弊,该报告的名称为《媾和大会论》。由于报告所预设的前提是中国不参战、美国、日本亦不参战,藉此可以推定,该报告的出台的最晚时间应在1914年8月23日之前。 1914年8月23日,日本政府因德国未能在最后时限内答复其最后通牒,宣布加入协约国,对德作战。因此该报告的写作时间应在此之前。另外一条时间线索是,报告对美国调停亦不看好,而中国出面邀请美国调停当在1914年8、9月间。报告就欧洲一个世纪以来的历次议和大会展開探讨,认为此次战争结束后的会议,其种类当为万国公会,所讨论的议题都是关于某国灭亡、领土割让、二国合并等重大事项。 该报告收藏于张国淦档案,但没有时间和作者。据现有资料推测,该报告最可能的作者是北京政府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在1915年1月15日《收政事堂交夏诒霆条陈》中,有“日本有贺顾问,复援据一千八百十五年维也纳公会,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巴黎公会,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柏林公会,谓与战事间接关系诸国,亦得由战国介绍列席”之记载,与此报告的内容相吻合。(《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第664~666页)。报告认为,近代以来,仅有三次此类型的会议:即1815年维也纳会议、1856年巴黎会议及1878年柏林会议,这三次会议都是战争的结果。该报告将参会国分为直接关系国和间接关系国。虽然间接关系国可以参会,但其影响有限。中国是和会的间接关系国。报告总结三次万国公会后指出:“间接关系国欲行其志,不可不依赖直接关系诸国中之一国或数国,借其力以成事”。从战略而言,中国须与协约国接近,以便借力达成中国的目的,“为中国谋,应宜与三国协商亲善,借其联合之力,以行中国之意志”。⑧ 《媾和大会论》,日期不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特藏档案,甲350-203,张国淦档案,《外交宣战案件》卷。
与一般认识不同,报告并不看好中国所倚重的美国调停。虽然美国作为此次战争“未与战事惟一无二之强国,与柏林公会时德意志同”,但居间调停“亦未可必然,此事成功甚难”:一是美国向来奉行不干涉主义;二是美国没有调停的强制力,如同柏林会议时德国的身份;三是外交非美国强项,难以说服欧洲各国。报告显然对当时出现的联合美国调停一事并不看好。⑧
1914年12月12日,政事堂交给外交部一份关于参加和会问题的说帖,分析中国加入战后和会的必要性。说帖引用日俄战后故事,对于加入和会事有清醒认识,“虽然我之利,彼之不利也;我所欲,彼必多方阻挠,使我不能达到目的,故日俄战后开议和会于美境,我欲加入而未果”。由于中国未能加入议和,“日人先与战败之俄交涉,得所欲,乃再与势力悬殊之中国交涉,其得美满之效果也”。中国欲加入战后大会,目的在于“勿蹈南满之覆辙”。山东问题显然是关注的焦点,而解决山东问题,“最忌由中日两国单独交涉”,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由国际议和大会公共解决”,说帖强调,此解决思路已经送交钧座(当为袁世凯)参考。 《收政事堂交说帖》,1914年12月12日(除特别注明外,本文所引外交部信函、电文均以收到日期为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下同)《外交部档案》,03-37-001-01。
在外交部的参会筹划中,甚至出现了更为明确的执行计划。夏诒霆就对中国参会计划进行了更为明确的阶段划分,他将中国参会分为三个时期,“故为我国计:目前应设法加入,为筹备之第一时期。加入以后之各项提议,为第二时期。不能加入之后,最后之对付,为筹备之第三时期”。作为加入大会筹备的第一个时期,中国需要做三件事:一是联络中立国调停战事,以设法加入;二是离间联军各国,使其互相嫉妒,以设法加入;三是商允德国,倡议邀我列会,以设法加入。 《收政事堂交夏诒霆条陈》,1915年1月15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下册,第664~666页。
经过前期的初步讨论,北京政府已经决定采取主动外交应对措施,联络各国,为加入大会做初步准备。12月14日,外交部致电驻美公使夏偕复:“青岛胶济铁路及鲁省中立问题,非待欧战告终,加入议和大会解决,恐无公允结果。我为青岛地主,是有密切关系,理应加入大会”,为了防止别国从中阻拦,“已密函驻欧各使,先期密筹加入事宜”。 《发驻美夏公使电》,1914年12月14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1。此电已经将参会原因及困难明白讲出。该电表明,外交部在中国不能参战情形下,对如何实现参会意图,已经有了明确的思路。此时外交部的参会策略是:以调停身份出席会议,使反对者亦无所藉口,“倘我国能以和解调处资格入会,反对者当无所施其技”。 《收驻美夏公使函》,1914年12月25日,《中日关系史料 欧战与山东问题》下册,第599~600页。刘式训欧洲之行,即是在此种背景之下出现的。
二、外交部关于中立身份下参会的第一次赴欧调研
大约在1914年11月间,驻巴西公使刘式训被外交部选中,作为筹划参加战后和会的主要人选。 刘式训,字筝笙,号紫箴,1868年生,江苏南汇人。先后毕业于上海广方言馆和京师同文馆,是晚清培养出来的专门外交人才。1905年9月任出使法国、西班牙大臣,辛亥革命期间辞职。民国成立后,经陆征祥推荐,1913年1月29日出任外交次长,二人为广方言馆及京师同文馆同学。1913年12月29日,出任驻巴西兼驻秘鲁全权公使。11月18日,外交部致电刘式训:“政府拟派专使前往与会,届时拟派执事携陆专使与议,藉资挽救”,要其做好相关准备。与此同时,外交部将相关文件邮寄巴西,以便刘式训参阅。 《发驻巴西刘公使电》,1914年11月28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1。
刘式训于1914年12月24日自巴西启程,横渡大西洋。1915年1月9日抵达葡萄牙,由葡萄牙登陆欧洲,开始其筹议参会外交之旅。12日到西班牙,并预定于20日由西班牙赴法国巴黎,然后经瑞士前往柏林。由于未能购到20日赴法车票,改为21日动身,中途换车两次后,于1915年1月23日到达法国巴黎。由于赴德道路颇多周折,于是改变原定日程,于1月27日渡海到了英国,29日与施肇基会晤,30日离英回法。在法国短暂逗留后,进入瑞士。2月7日从瑞士动身赴德,最终于2月9日到达原定目的地荷兰。 参见《收驻巴西刘公使函》,1915年2月27日、3月3日、5月21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2。
在西班牙期间,刘式训曾致外交部咸、啸两电,将其与欧洲两使会商意见及自己的建议报予外交部。咸电系刘式训于12日抵达西班牙后发给外交部的电报,内容包括其与两使会商情形及西班牙政府的态度。为防止收发延误及电码出错,特别将两电内容以文函形式再行寄送。啸电主要是关于山东问题的处理建议,与中立参会提议其实无关。2月27日,外交部在所收刘式训函件中有“本日曾发啸电,略贡愚见,以备采择”之类的记载。 《收驻巴西刘公使函》,1915年2月27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2。而在另一份档案中则明确记载收到该函日期是1月19日,从刘式训行程推断,该日期应是发函(电)日期。刘提出“莫若就德人原占区域,仿上海公共租界办法,开为万国商场,归通商各国领事共同经理”,为了补偿德国,可以“声明将胶澳税款,尽数赠给德国若干年,以偿其历年经营之费”。对于处于实际掌控地位的英、日两国,“可以威海、旅大各口岸,租期若干年以酬之”。 《收驻巴西刘公使函》,1915年1月19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下册,第682页。
刘式训认为,法国对战后和会并无固定决策,“届时有无中立國参列和议,全视战局为何,现无从悬断”;法、俄之间关于是否要日军登陆欧洲参战一事,意见不一,“前外部毕盛主张用日本军队来欧助战,屡次著论鼓吹”;由于日本所提报酬包括占领库页岛及越南,“俄人大示反对,毕意遂寝”。 《刘式训致外部电》,1915年1月26日发;《收驻巴西刘公使函》,1915年3月3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2。经过在法国短暂停留后,刘式训渡海赴英。
在英期间,与驻英公使施肇基进行了广泛商谈,所涉内容不只包括加入大会事,还有与美国秘密商谈收回胶澳事。会谈之后,两人于1月29日联合致电外交部,就所商情形详细汇报。电文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英国的态度。两人分析认为,在战争形势未明朗之前 “英或资日”,目前则不免迁就;二是日人关于战后和会的理论。施肇基向刘式训出示了有贺长雄所撰写的有关媾和大会的文章,刘认为“其中辨析会议之性质及中国加入会议之准备,方法诸多可采”。但对有贺长雄在文章中指出的,中国若加入会议须依赖三协商国,则不以为然,“此仍是日本人议论,盖此时胜负未分,不能决定”。刘式训的建议是“只宜预定宗旨,待时而动。苟对于双方稍有抑扬偏倚之迹,不免招外来之疑问”。三是要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 《收驻巴西刘公使函》,1915年5月21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2;《驻英公使施肇基、驻巴西公使刘式训关于取消战区等事致外交部电》,1915年1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391页。
刘式训刚到欧洲时,驻德公使颜惠庆曾向国内汇报德国方面的态度,“谈及将来议和事,据云,德主张与各国单独议和,反对共同议和”,这与中国所持意见显然不同。北京政府外交部的设想是尽力避免单独与日本谈判,而是希望举行由各国参加的共同议和。当被问及如中国加入德日议和德国持何态度时,回答以 “德国方面当无异议”。德国甚至建议中国从日本方面做工作,“此事关系日本国较重,中国当从日本国下手”。 《收驻德颜公使电》,1915年1月10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2。奥匈帝国态度较为模糊,“据答,将来或开大会,或由战胜国开示条件,均难预定”, “惟中奥邦交素密,遇有中国提议之件,无不表示亲睦”。 《收驻奥沈公使电》,1915年1月15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2。
得悉德国方面的议和方式后,外交总长陆征祥会晤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探询俄方态度。库朋斯齐告诉陆征祥,在处置青岛问题上,俄、法、英三国意见相同,“将来贵国对于处分青岛一部分问题时,当然可以加入和会云”。当被问及德国欲与各国单独议和是否可能时,库朋斯齐的回答是“英、日、俄、法曾有一声明文件,不能单独议和,德之意或于彼有利益,联盟国必不答应也”。 《收总长十六日会晤俄库使问答一件》,1915年1月21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2。库朋斯齐所指文件即1914年9月5日的《伦敦盟约》,约文中声明“英法俄三国政府互相约定,于此次战役进行中,不单独议和。三国政府议定,于磋商和款时,若三协约国中之一国,不先以议和条件商诸他二国,则不得要求议和之条件”。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张国淦档案中有一份《伦敦盟约》抄件。在此之前,库朋斯齐已经向中国表达了赞成中国参加战后和会意见,认为除日本外,其它国家没有反对中国参会的理由,并强调如果不是直接交战国,中国只能参加与自己相关的会议事项。 《王秘书赴俄使馆问答》,《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下册,第660页。
因颜惠庆的劝阻,刘式训未能前往奥匈帝国。奥匈帝国方面的态度均由驻奥公使沈瑞麟提供。 “德奥胜利,于中国方面定多裨益,三协约胜,则与日人联络一气,中国后患之来,正难思议”,意在劝说中国。沈瑞麟则认为,胜负仍难分辨,“有无大会殊难悬断”。如大会果真召开,“自当坚请加入”;如出现中国不愿见到的局面,即“交战各国在战场定议”,不再召开大会,“亦须别筹抗议之法,以资补救”。 《收驻奥沈公使函》,1915年3月22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2。
1915年2月21日,外交部收到刘式训所报关于荷兰近况。刘式训认为,由于荷兰仍属中立,因此言辞谨慎。但荷兰方面对和会仍有自己的筹划。其中之一,就是希望海牙为战后议和地点。 《收驻巴西刘公使电》,1915年2月21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2。
刘式训欧洲之行,未涉足意大利。驻意大利公使高尔谦认为,意大利对于中国要求加入战后和会一事,“虽不能独力赞成,亦未必特加反对,此时即欲求彼赞助,自不外敷衍其词,究于事局实属无济”。高尔谦本望刘式训到意大利一叙,“乃昨接其来函,知先回国,方谓海行尚可于折奴鸦或那波里一见,迨电询和馆,始悉取道俄都,无从晤商,深为可惜”。 《收驻义高公使函》,1915年5月10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2。
丹麦的态度颇为含糊。事实上,民国政府外交部收到由德国使馆转来的关于丹麦态度的函件时,意大利已经宣布加入协約国对德作战。函件所讨论的以意大利为例子的中立国情形,已经不具实际意义。意大利加入协约国后,于1915年5月25日签署《伦敦盟约》,即遵守不单独与德议和的规定。同年10月19日,日本签署该约。至此,可以确定,协约国集团参战各国将不单独议和,而这与中国的战后议和期待是一致的,即不与日本单独交涉。 因十月革命的爆发,协约国集团未能严格遵守《伦敦盟约》,新成立的苏俄单独与德国缔结和约。从外交上而言,这也符合德国预先设定的单独议和的方针。德、奥虽然同意中国加入大会,但其单独议和的方式,不为中国所欢迎,因此中国主要的外交方向,将是协约诸国,及尚在中立地位的美国。
在欧洲各国经过将近2个月的调查后,刘式训准备由俄国回国,向外交部当面陈述参会事宜,“和一月二十日函件均到,咨询公法家事,十九日函详,和议尚游移 ,拟乘间由俄入京一行,面陈一切,候示”。 《收驻巴西刘公使电》,1915年2月28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2。3月2日,外交部致电刘式训,盼其回京接洽。 《发驻巴西刘公使电》,1915年3月2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2。
1915年6月1日,外交部就筹备战后和会问题致电各驻外使馆及机构:“驻巴刘使暂时留京,继续筹备,所有关于筹备事宜仍请查照部电及刘使函件,切按时势,悉心筹画,随时电部酌核”,此电可以作为刘式训欧洲外交之行的一个句号。虽然欧洲外交调查结束,但筹备和会任务远未完成,“将来和会关涉东亚,理应参预,且尚有应行提议之件,仍须以达到加入为目的”,如果出现有利于中国的时机,应即“向所驻国政府切实声明,将彼政府意见电本部,如系交战国,并向要求赞成”。 《发驻外各使馆电并各分馆筹备和会事》,1915年6月1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2。筹备和会一事继续为各驻外使领之首要外交任务之一。
三、教皇调停之传闻及第二次赴欧调研
经刘式训欧洲之行后,民国政府外交部初步了解到各国的态度,以及它们对战后和会的意向性构想,在此基础上需要完成的工作,就是寻找最佳的加入办法。作为中立国,任何筹划加入的方式,都充满变数,必将随形势的改变而进行相应的调整。随着战争的进行,各种消息不时出现,其他方案的调停计划亦在酝酿之中。在真假难辨的情形下,民国政府凡涉及和会事情都予以认真对待。
1915年6月28日,外交部致电驻意大利公使高尔谦:“闻将来议和当由教皇及瑞士居间调停,英和两国已在教皇处新设驻使,接洽一切等语。教皇是否有调和之意,希确切密查,并预筹加入大会与议”。 《发驻义高公使电》,1915年6月28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2。高尔谦不赞同在战局未分胜负之际,向各国探听有关议和大会的消息,认为此举“不但真情实际无从得窥,且鲜不遭其淡冷态度,故毋宁以郑重出之”。至于教皇调停,应属于其份内之事,并无特别安排,“教皇为风化主宰,各国皆有皈依之民,立志媾和,自其天职”,而之所以迄今未公开号召,“盖亦自知时机未至,空言无补,反损声望”。目前需要关注的是战争走向,“要在注视列国之趋势如何耳”,“将来如果一方面全胜,一方面败于极点,和议条款之权,自为战胜国所操”。 《收驻义使馆函》,1915年8月31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3。
沈瑞麟于8月25日致电外交部,“默窥欧战以来,各国对于教皇极为注重,英设驻使与前,法派专使于后,最近荷兰亦与教皇通使,至对瑞士方面,瑞典向无驻使,近亦添设,凡此举动,似有深意”,建议“从事联络,以达加入之目的,拟请列入筹备中,试商及之”。 《收驻奥沈公使函》,1915年8月27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3。外交部重视此种议和动向,将沈瑞麟电文转呈政事堂,政事堂于8月31日将批复后的电文转交外交部,要求外交部就教皇调停和会等事相机联络。 《收政事堂交电》,1915年8月13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3。
沈瑞麟认为虽然目前战局胜负未分,但中国宜乘此时选边站定,对外一视同仁只能是个表面的说辞,“倘若利用两联盟,则当力就联盟方面而倾向之,倘若利用三协约,则当就协约方面联络之,方针必须确定进行”。如果不能事先筹备,确定外交主攻方向,“即使加入酬和会,无一真挚可恃之友邦,发言盈庭,谁为赞助,临时而呼,将伯恐无及矣”。 《收驻奥沈公使函》,1915年8月23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3。
为了主动应对教皇调停战事的可能,外交部有意调整驻欧领使的职务范围,拟让沈瑞麟兼使瑞士,胡惟德兼使教廷,并于8月30日致电沈瑞麟、胡惟德,探询意见。 《发驻奥沈公使电》,1915年8月30日;《发驻法胡公使电》,1915年8月30日,《收驻奥沈公使函》,1915年8月27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3。驻法公使胡惟德认为由其兼使教廷并不适合,并举出两点理由:一是“法与教廷撤使绝交,感情极冷”,若以驻法公使兼任,可能“未收其效,先损法感情”;二是“在华各国天主教民,向由法保护,遣使教廷,定遭法忌,兼驻尤觉非宜”。胡惟德认为,奥匈帝国與教廷关系“方睦”,且相距不远;另一方面,法国、瑞士政体相同,“保护学生、侨民等事,向由法馆与瑞政府接洽”,希望外交部再行统筹兼驻事宜,其意在于希望兼使瑞士而不是教廷。 《收驻法胡公使电》,1915年9月6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3。沈瑞麟同意由其兼使瑞士,“麟驻地临近,遵当兼效驰驱”,认为此举在中瑞尚未订约的情形下,可以灵通消息,并建议“先与商订通好条约,彼此订定关乎通商事宜,随后续议是否恰当”。 《收驻奥沈公使电》,1915年9月7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3。获悉胡惟德建议的函电后,沈瑞麟同意由胡兼使瑞士,表示自己“自惭望浅,极愿让贤”,并于9月18日致电外交部,将自己的意见一一陈述。 由于瑞士可能为议和之地,或许因此促进了中瑞建立外交关系的进程。1918年6月13日,中瑞订立《通好条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沈瑞麟还愿以其个人关系,探询教廷方面的动静,“驻奥教使与麟甚熟,如有探询教廷之处,亦可托转”。 《收驻奥沈公使电》,1915年9月24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3。
外交部在寻求加入和会办法的同时,亦试图从欧洲历史上寻找借鉴。前文已经叙及,外交部曾有一份媾和大会的专门研究报告,认为维也纳会议、巴黎会议及柏林会议,系最为著名的三次议和大会。待刘式训欧洲之行结束后,在筹备具体加入方式的同时,外交部希望能有更多关于三次和会的材料,以供研究。1915年7月3日,外交部发出致驻英、法、德、俄、奥、义、美、荷公使函,告之国内关于三次媾和大会的材料“除一二条约历史外,苦无确切成例,足资考证”。函件并特别举希腊加入柏林大会一事为例,说明相关情形:以希腊为中立国,但因领土处分一节与其有直接关系,因此被特许入会,此种状况类似于中国于此次大战的境地,“不知关于当时希腊加入柏林大会,各国外交来往文件,此时能否设法搜觅”。函件强调,柏林大会之前“各国政府交换意见,必有多数文电之往还,我国似应详事搜求,或可作为筹备加入大会手续先例之一助”。鉴于会议所具有的上述重要借鉴意义,函件要求各使“务须将欧洲组织此三大会所有驻在国与他国预筹会议往来文件,及其他各国加入会议之历史,设法密为收集,或编列表册,或照录原件,迅速邮寄本部,以为筹备资料”。 《发驻英法德俄奥义美和各公使函》,1915年7月3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3。
各驻外使馆按外交部的要求调研三次和会时,为得到较为直接的经验,外交部再次派专人赴欧,从事联络及调查。此次担任者为外交部参事夏诒霆。1915年9月10日,外交部以“目前各国情形瞬息万变,将来究竟如何,不能不先为研究”为由,派遣夏诒霆前往欧洲各国。 《收驻和唐公使函》,1915年12月14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3。夏诒霆欧洲之行首站为何国,目前的材料尚不得知,目前可以得到的行程是大约在10月20日前后抵达法国,11月6日由法赴英,11月11日由英抵荷,14日离荷赴德, 11月18日离德赴奥,11月30日由奥赴俄,最后自俄返国。
夏诒霆到欧后,与各国政要及公法家接触,探询意见。1915年10月23日,外交部收到夏诒霆电,称“顷晤风登纳,诚恳密询。据云,战时结局总在明岁,大会如有中立国列席,中国亦可要求加入,惟此情形与维也纳、柏林等会议不同,恐交战国不愿别国与闻”。另外一点在于,现实处境不利于中国,“战后欧美列强于远东利益不肯漠视,但现在杀机已动”,可谓是“有强权,无公理”。风登纳 未能查明此人身份。在法国、德国会见的公法家及政要,由于缺乏相关材料,亦无法确认身份。建议中国,为了防范别国野心,可以做两方面准备:一是遍告国际友邦;二是“乘机赶修军备,整理财政,多派武员观战,造就将才,以备万一”。 《收本部夏参事电》,1915年10月23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3。
在法国期间,夏诒霆会晤法国政要。得到的意见是,如果战局胜负难分,由别国参与调停,则中立国可列席会议。法人的意见中均提及日本,认为日本可能会反对此举,因此“能预防日本国阻力最好”。 《收夏参事电》,1915年11月8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3。在德期间,晤见索尔息,探询其对东亚局势及各国影响的认识,尤其是如何牵制日本。索尔息认为东亚大局掌控于英国,“现英、日外虽亲睦,内实猜忌,战后盟约决难赓续,或竟先将解散”。美国与日本有利益冲突,但“挟制不足,牵制有余”。如果中国能联结英、美,“日患当可稍图补救”。不必担心日俄联盟之传言,日本果若联俄“不特关系中国。恐英美必从中阻挠”,即使日本“重审前议”,“恐未必能成事实”。 《收本部夏参事电》,1915年11月22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3。此后夏诒霆由德赴奥,后经俄国返回国内。
未能见到夏诒霆在俄国活动的资料,但透过俄国的档案,可以推断俄国对中国此时的外交动向十分清楚,认为中国的主要动机有二:一是“想参加将来应该解决青岛命运问题的和会”;二是“希望加入协约国,借此可保障自身安全,避免日本之阴谋”。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1915年11月7日;陈春华译:《沙俄等列强与中国参战——俄国外交文书选译》,《民国档案》2005年第1期。为推动中国对德绝交,俄国外交部曾周旋于英、法、日三国之间,力劝三国同意中国加入协约国,主要的阻力来自日本。
外交部对参会的外交调研,是基于中国中立这一前提的,因此其对中立国的研究也比较重视。此前对欧洲各中立国的调研,限于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等西欧国家,甚少注意到巴尔干半岛诸中立国。随着时间的推移,意大利加入战团,其中立国身份不复存在;荷兰为保和会所在地,对战后和会具有特殊地位,不是纯正意义上的中立国。因此研究上述中立国所能提供的借鉴意义,已经大打折扣。为解决此问题,1915年9月21日,外交部致函驻俄公使刘镜仁、驻奥公使沈瑞麟,要求密为探询希腊、罗马尼亚等中立国“对于战事、媾和公会,如何办法,有无筹备”,望随时电告。 《发驻俄刘、驻奥沈公使函》,1915年9月21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3。并于同日致函所有驻外使馆,要求切实调查中外报纸所载之“战事媾和渐有动机之说”,认为“此种论调未始非事实之先声,或作为我国筹备加入大会参考之一助”。 《发驻外各使馆函》,1915年9月21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3。
沈瑞麟于调查后回复外交部:“查巴尔干各国,除布加利亚已加入战局外,希、罗两国均系武装中立,将来遇有时机,难保不参与战事”。关于媾和问题,目前“尚无明了之筹备”。 《收驻奥沈公使函》,1915年12月25日,《外交部档案》,03-37-001-03。
至1915年底,外交部为筹备加入大会已准备一年有余,先后派刘式训、夏诒霆出使欧洲,探询意见,继之要求各使调查三次欧洲议和大会,希望从中得到借鉴。在联络各国公法家以为我用的同时,对传言中的教皇调停认真对待,一一做出外交因应。为防备瑞士可能作为议和之地点,特派专使兼驻瑞士,并探求订立通好条约的可能。外交部所作的这些准备都为中国将来以中立国身份加入和会打下基础。中国能否最终以中立国加入和会,加入之后能否达到预定的目的,均非这些准备工作所能准确预知,外交部只是在尽最大可能,为将来中国能参加和会并达预期目的做足外交方面的工作。此过程中,沈瑞麟要求外交部选择两集团中的一边为主要外交方向,唐在复则根据柏林和会经验,建议政府先与一强国接洽,以为后盾。这些建议,无疑对中国筹备加入和会,及加入和会后保护自身利益是有利的。
1916年春,德国已经有议和之意,此种动向引起外交部的注意。因美国所处中立地位,消息大多从美国而来。1916年3月25日,驻美公使顾维钧来电,“昨见各报纷载德首相与驻德美使晤谈,有议和意,拟请美国出为调停等语”,据以探询美国外交部,告以“所谈仅及美德交涉,惟据各处私密消息,双方均确有和意,不久议和亦意中事”。美国外交部人员提醒顾维钧,“和会与中国关系不小”,希望中国相应准备。虽然外交部一直在由刘式训等筹备加入和会的方法,但顾维钧此时竟然并不确定中国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战后和会,“我国拟否加入和会一节,如已决议,乞早日密示,俾有遵循”。 《收驻美顾公使电》,1916年3月25日,《外交部档案》,03-07-001-04。外交部肯定中国加入和会之愿望,但唯恐结果难如人愿,希望留出处理余地。除回电顾维钧表示“我国能加入大会,固所至盼”外,又引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个人意见,说明不加入和会的利益所在,“芮使以私意密告,以为中国宜宣言不欲加入,庶日本不至要求在会内代表我国利益,同时我国设法与各关系国另组专会,讨论东方问题”,外交部希望顾维钧对此发表看法。 《发驻美顾公使电》,1916年3月29日,《外交部档案》,03-07-001-04。
顾维钧不同意芮恩施的意见。顾指出,如果明确大会将处理有关中国问题,中国应该“坚请入会”。如中国宣言不加入大会,“他国或解释为我国愿将各项问题,一任和会处置,不复置词”,将导致“有损我国将来反抗和会决议之地位”。在中国要求入会的情形下,如果被拒绝加入,中国即可“不承认该会之议决,以为他日抗议之地步”。至于另开专会,顾维钧认为不可,“有损我国将来自由行动”,而且“日本殆必要求为专会主席,尤易实现其在亚洲霸权”。 《收驻美顾公使电》,1916年4月21日,《外交部档案》,03-07-001-04。顾维钧关于中国须加入和会的解释,从逻辑上讲有利于中国,而这与外交部确定加入和会总方针是一致的。外交部虽然早已为加入和会在进行各种筹备,但在核心筹备人员之外并未宣讲民国政府的底线,各种可能的预案也在一直进行。当德国议和之意酝酿出台时,外交部久已计划的参会之议,似乎将要有一个结果。
余论及结语
中立参会之议,最终随战争进行而出现转机。1916年12月,德国宣布将与协约国议和,条件是“大致系除波兰及律苏爱尼亚外,余俱恢复战时以前原状,所有德国已失非、亚二州属地,亦一律复归德有”。 《收驻美顾公使电》,1916年12月14日,《外交部档案》,03-07-001-04。该条件显然不利于中国,“德国协商收回属地为条件,若日本归还胶澳,势必另图取偿”。 《收驻和唐公使电》,1916年12月17日,《外交部档案》,03-07-001-04。12月19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将调停战争,强调其调停虽然出现在“欧洲中部各交战国现有媾和之意”后,但两者之间“根本上固毫无关系也”。中国驻美公使馆于12月23日收到美国调停照会,表示愿与美国合作出面调解。 《收美馆照会》,1916年12月23日,《外交部档案》,03-07-001-04。德国议和与美国的调停,均未见效。至此之后,战争形势陡转,因美国不满德国政府之无限制潜水艇战,于1917年2月3日对德绝交。中国很快步美国后尘,于2月9日对德提出抗议,并于3月14日宣布与德绝交。
美国对德绝交后,德国方面许诺,中国将来必能加入和平大会,无须与美国一起加入战争,并运动国内重要政治人物游说政府。但此时为时已晚。透过开战以来中国通过各种渠道所得信息,德国始终坚持单独议和,这是中国所要力主避免的情形。協约国自始就有不单独媾和的《伦敦盟约》,意大利、日本加入战团后,亦明确宣布遵守盟约,这无疑暗合了中国对战后议和方式的期许。事实上,自日本加入协约国后,透过简单的逻辑亦可推理出中国政府的外交选择。中国对战事的关心集中于山东问题,德、日是山东问题的直接关系国。如中国加入同盟国,与德国站在一起,德国战胜,德国能否放弃在山东权益不可知,中国获得的利益必将从协约诸国身上获取,中国能获多少,全无计划,德国所许,无非是加入和会,目的不明;如果战败,则从日本手中收回山东权益完全不可能,日、俄等在华已有重大利益的诸国,必将乘机扩大其利权,前车之鉴不远。加入协约国,如果战胜,则中国与日本站在同一战壕,收回山东问题有极大可能;如果战败,山东重回德国手中,中国无非恢复到一战爆发前的状态,没有失去什么。事实上,至中国对德绝交时,随着美国加入战团,德国败势已显,中国加入协约国只能促使山东问题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解决。
德国对中国参会的许诺,事实上存在极大的泡沫。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德国战胜的基础上的,如果失去了这个基础,德国自身都将难保。民国政府内部对战局的走势有着大体正确的预判,这种判断随着战争的进行而逐渐明晰。当然,从理论的角度讲,中国对德最终绝交与宣战,除去先前学界所认识到的原因外,德国对战后和会的处理方式与中国的预期并不相同,不利于中国,就外交而言,这也是中国绝德的原因之一。只是,我们不能把德国的许诺视为过重的因素,尤其是不能将其上升到影响中国外交选择的层面。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正式对德宣战。中国寻求参加和会的外交,以中国对德宣战为标志,划为一个段落。作为参战国,当然获得参会资格。如果梳理中国加入大战的原因,或许可以发现,战前所作的关于媾和大会的外交调研,为中国最终决定对德宣战,起到了指导性作用。从外交层面,防止中国走错方向,并尽可能藉战争之际,最大化自身利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自战争爆发到中国正式宣布对德绝交并参战,属于中国筹备加入和会的第一阶段。中国参战以后,与会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先前为此所做的种种准备,都有了一个结果。参战以后的与会筹备,与此前相比有重大改变。之前所做,是围绕着是否加入、如何加入而展开,此后,则是如何在会上最大程度实现中国利益。加入和会的筹划与民国政府的总体参战外交方针是一致的,不是说加入和会将与参战发生矛盾。其总体构想是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包括租借地、租界及胶济铁路,尽最大可能维护中国自身利益。其主要对手国,当属日本。参战外交的最终目的是参与大会,维护自身利益,不让日俄战争后的故事重演。当中国求中立以自保而不可得时,北京政府为达此目的而进行的外交交涉及国际活动,大体可分为两个线索:一是寻求参战,如果成功,结果当然是加入和会,在会上维护自身利益;二是不参战,但加入和会,并运用各种手段达到维护自身权利的目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