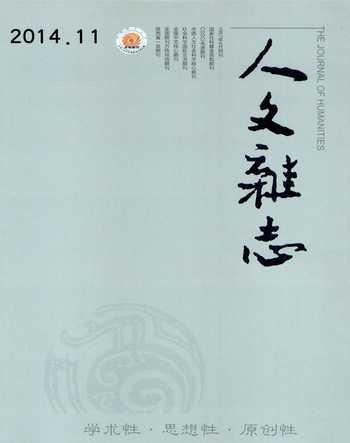奥哈拉城市诗歌中的“一人主义”诗学
汪小玲
内容提要 “一人主义”是美国纽约派代表诗人弗兰克·奥哈拉诗学理论和艺术风格的集中体现。“一人主义”诗学理念的确立,使得奥哈拉的诗歌作品极具个性色彩,饱含创造力。本文依托奥哈拉的城市诗歌创作活动,探讨“一人主义”诗学理念衍生的过程、“一人主义”的内涵及其对奥哈拉城市诗歌的意义,论证奥哈拉在这一诗学理念下所达到的诗歌艺术境界。
关键词 弗兰克·奥哈拉 “一人主义” 城市诗歌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11-0060-06
美国纽约派代表诗人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 1926-1966年)打破了20世纪50年代诗坛刻板教条、缺乏活力和创造力的正统诗风,走出了一条反文雅、反高贵、近民众、尚自由的诗歌创作之路。近年来国内外奥哈拉研究表明,他的诗作是人们了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纽约城市风貌和人文概况的指南,是他那个时代纽约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创造了“由城市生活中貌似不重要的细节组成的一幅拼贴画”,①奥哈拉也因此成为一位极具个性魅力的先锋诗人。奥哈拉曾用一个词——“一人主义”(personism)——来概括自己的诗学观和诗歌艺术:“‘一人主义是我最近确立的、他人丝毫不知的思想活动,对之我十分感兴趣……‘一人主义与哲学无关,纯粹是艺术。1959年8月27日,我与勒罗伊·琼斯共进午餐后确立了‘一人主义,那天我与人欢爱(顺便提一下,不是金发女郎勒罗伊,是另一个人)之后回去工作,为这个人写了一首诗。当我写这首诗时,我意识到我像是在用给对方打电话的方式在表达,于是‘一人主义写作法就产生了,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相信一定会有很多追随者。它使诗被平放在诗人和那个人之间,这样的诗令人满意,它最终处于两人之间,而非纸上。”②
奥哈拉在其艺术活动和创作过程中逐渐清晰地阐释了他的“一人主义”的诗歌理论:许多诗都有特定的写作对象,或是亲密无间的朋友,或是一面之缘的邂逅者,似乎与局外人无关,而局外人对这些诗的独特含义也难以把握。“一人主义”突破了诗歌创作的种种藩篱,成为奥哈拉城市诗歌理论的一个关键词。本文将从“一人主义”诗学理论的确立、人与人之间的诗话、以及“一人主义”诗学下的城市诗歌创作三个层面,解读奥哈拉所展示的“城市拼贴画”,论证其“一人主义”诗学的独特张力,以及诗人由此达到的诗歌境界和艺术成就。
一、“一人主义”诗学理论
奥哈拉“一人主义”诗学理论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诗人汲取现代诗学精髓的结果。虽然在奥哈拉的有生之年,人们出于对他才华的仰慕以及对他在文学艺术界名望的尊重,称赞他为反传统的“文化英雄”(cultural hero),并把他看成是20世纪美国尤其是纽约诗坛的改革家、前卫诗人,认定他从骨子里就鄙视传统,乐于将自己视为异类,但从本质上而言,奥哈拉却是一个把传统的艺术理念与创作技法都看做是自己写作指南的人。他曾经如饥似渴地钻研传统,不愿意以懈怠的态度简单复制,而是寻求突破,以使传统焕发生机,并进而改变传统。在写作过程中,他十分注重自身的理论修养,在看似随意自适、信手拈来的诗行里实际承载着他的苦思冥想以及玄思状态下意识的自由流动。对前人诗学理论与创作风格的研究、借鉴与拓展促成了他那如同万花筒般令人眼花缭乱的精彩诗行之下自成一体的诗学观,其核心就是“一人主义”。
“一人主义”的衍生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亚瑟·兰波(Arthur Rimbaud, 1854-1891年)。大学时代的奥哈拉酷爱读书,所涉猎的范围很广,从他那一连串的书单中可以看出兰波是他的最爱,对他的影响根深蒂固。兰波在诗歌理论与实践上对法国诗歌的两点贡献对奥哈拉触动最大,其一是兰波的名言:“我是另一个人。(I am somebody else.)” 葛雷:《现代法国诗歌美学描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5页。即我要用另一个人看我时的目光冷峻地注视自我,把“我”看作诗歌创作中首要也是唯一的对象。兰波极力倡导要在诗歌中表现自我,创造自我,这种自我意识的增强真正揭开了现代诗歌的序幕,并在后续的超现实主义诗歌和存在主义哲学中得到了发展。兰波的自我意识论给了奥哈拉很大的启发,他开始思考自我、他人与诗歌创作的联系。在奥哈拉重要的诗作里,即便是最不经意的读者也会发现,第一人称无所不在,如在他的名篇《音乐》(Music)中,代词“I”(我)和它的同根词在21行的空间中就出现过十次。然而,《音乐》并没有去探求说话人的过去以断定是什么造就了现在的“这个人”;并非因此而“自白”或“揭示”它(即“I”)内在的精神生活。“I”(我)的作用是对事物做出反响,是要去观察事物,去注视事物,去创作出与音乐主题相关的诗作:“我的门向着隆冬之夜敞开着/雪轻轻地落在报纸上。/把我像一颗泪滴用你的手帕包起 /那是午后的喇叭声!/曾响起在云霧缭绕的秋季。/当他们在帕克大道竖起圣诞树时,/我将看到我的白日梦伴随裹着毯子的狗漫步经过,/ 在华灯溢彩之前还挺管用!/可是再无喷泉,再无雨水,/商店的门一直开着直至夜色锁重楼。” Donald Allen, The Selected Poems of Frank OHar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 p.210.诗中出现的午后的喇叭声使全诗笼罩在“音乐化”浓厚的氛围里,一切仿佛都跟着音乐的节律展开并赋予诗歌内容与意象浓郁的象征色彩。法国诗人瓦莱里(Paul Valery, 1871-1945年)认为,象征主义诗歌的本质在于诗歌的“音乐化”。 [法]瓦莱里:《纯诗:现代西方文论选》,陈力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7页。 “音乐化是指诗的词语关系在读者欣赏时引起的一种和谐的整体感觉效果。”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而《音乐》这首诗正是“音乐化”精彩的呈现。诗人通过乐器——喇叭的渲染,把人们习以为常的雪景写得美丽、空灵,富有旋律,也将个人对雪的怜惜表露得生动感人,引发读者情感的共鸣。然而这首诗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是奥哈拉“一人主义”诗学观在诗歌实践中生动的演绎。它不像典型的自传体诗,不去探究诗中“说话人”的过去以说明是什么成就了现在的“他”,也不去揭示他的内在精神生活,因此诗行里反复出现的角色“我”与其说是在自我表白,还不如说是在观察、关注着外部事物并对之做出反应。
奥哈拉是个怀疑论者,他积极思考并凭借自己的判断与领悟力来透析文学、艺术、社会和形形色色的纽约市民,他把诗歌创作看成是自己与某个人之间的对话——“真实的”对白,看似纯粹个人的,却刻意避免“令人生厌的自哀自怜” Marjorie Perloff, Frank OHara: Poet Among Painter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26.而向他人、外界开放。诚如奥哈拉在《一人主义:宣言》(Personism: A Manifesto)中所宣称的那样:“一人主义针对的是某个人而非诗人自己。” Donald Allen, The Selected Poems of Frank OHar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 p.499.因为自我是无法脱离它所感知的那些物质对象的,相反,它会融化其间成为外部风景中的一部分。《音乐》中,“我”借助各种手段与“本我”拉开距离,如把自我贬低成同行的狗所制造的幽默;以“广角”拍摄帕克大道的全景;以“白日梦”揭示奇思异想以及那个不知有何来头的“把我像一颗泪滴用你的手帕包起”的第二人称“你”,所有种种都把我们拉进了诗人的魔圈里,如同身临其境。诗中人称的变换独具匠心,当奥哈拉将诗中的“我”、“你”富有技巧性地调换成“某个人”(one)时,这首“一人主义”的诗歌使读者已然成为与诗人亲密平等的人。据此,奥哈拉在创造读者的同时扩展了诗歌的视野和范畴,使得看似很个人的情势(如“我将看到我的白日梦伴随裹着毯子的狗漫步经过”)变成虚实相间、戏剧性十足的意境,从而大大增强了这首诗的张力、活力与创造力,这不能不说是“一人主义”创作理念所带来的显著效应。
兰波对奥哈拉“一人主义”诗学观的确立之另一触动是其“诗格在于人格” 葛雷:《现代法国诗歌美学描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5页。的创作理念。诗人要写出非凡出众的诗句,就应具备超凡脱俗的生活,用种种探索与历险来摆脱自我生存的平庸状态。对于诗人而言,生活、友情、爱情等有待于重新创造,因此,诗人的首要任务不是在诗艺上下功夫,而是要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人生。对此奥哈拉深受启迪,他不仅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是纽约诗派最忙碌的诗人,是现代艺术博物馆著名的艺术品鉴赏家,是评论界极富盛名的评论家,是派对上炙手可热的常客,是许多画家、音乐家、电影、戏剧表演家和其他诗人、作家亲密的朋友,是诗坛领袖和“文化英雄”,是被某些人看做另類的“同性恋者”。他短短40个春秋所积累的丰富生活阅历可以说是许多人穷其漫长人生也望尘莫及的。所有这一切成就了奥哈拉城市诗歌丰富的内涵,使之成为纽约都市生活的万花筒。纽约派另一位重要诗人肯尼思·柯克(Kenneth Koch, 1925年-)就将奥哈拉的《诗集》(Collected Poems)称作“创作瞬间的聚集,照亮了诗人光辉的一生。” Marjorie Perloff, Frank OHara: Poet Among Painter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136.很多读者也都认为该诗集“实际上就是一首冗长的诗,一旦人们开始阅读奥哈拉的作品,他们就爱不释手。” David Shapiro, “All the Imagination Can Hold,” New Public, January 1 & 8, 1972, p.24.这就是“一人主义”的诗学魅力之所在,它的确立在奥哈拉的诗歌创作过程中饱含特别的意义。一个人读奥哈拉的诗越多,就越想知道诗人对某一特定的事件、一件风流韵事甚至是交通堵塞会做出怎样的反响。这样的关注在无意间的潜移默化中最终使得诗人的自我经历成了读者自己经验的一部分,诗人也因为成为他们的知交。
因此,尽管奥哈拉一直被视作为先锋派的前卫诗人、一个随性而为的即兴诗人,他却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严肃的诗人,他的严肃性集中体现在他自成一体的诗学理论——“一人主义”。它的确立离不开法国现代诗歌美学尤其是兰波创作理念的直接影响,更离不开奥哈拉诗歌实践中对之创造性地运用与拓展,并终使自己的诗歌在这一理论体系的建构下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二、人与人之间的诗话
奥哈拉认为,诗是置放在诗人与某个人之间的文字表述,是一种互动,而非两页纸之间写满诗人的独白和没完没了的感叹。由此,他暗示我们:“戏剧独白已成为过时的传统,诗人渗透小说叙事者的经历实际上正是使自己疏远了这种经历。” Charles Altieri, “The Significance of Frank OHara,” Iowa Review, 4 (Winter), 1973, p.99. 因此诗人的创作如同自身(I)所从事的生动谈话,通过促膝谈心去告知对方“我”的所思所想——亲密、熟悉、富于表现力,于是“一人主义”就成了亲密交流的“魔术手法”,介于“我”和“你”,抑或“我们”、“他”、“他们”,或者就是“某个人”(one)之间,给予我们一种“错觉”(illusion),我们是在无意间听到某个正在进行中的对话,而我们正好在现场。于是,平放在人与人之间的诗话便应运而生。
奥哈拉强调诗应该“最终处于两人之间,而非两页纸之间”,旨在阐述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如果是两页纸之间的事就意味着修改、润色、甚至于推翻、重写也皆有可能,而若是两人之间,那么最直接的交流方式就是对话(conversation),一经口出,就再无更改的可能。由此,奥哈拉为他以口语体写诗找到了理论依据,以此而创作的大量诗行自由流畅、幽默机智、插科打诨,透着一股浓郁的都市生活气息。这样的“一人主义”是对奥哈拉时代的诗坛所盛行的以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年)为首的“新象征主义”唯美诗风的颠覆。当时的艾略特俨然是“诗圣”般的人物,所写诗句严谨、高雅,如圣经般被奉若神明,就连出版商也不敢轻易更改只言片语,但奥哈拉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的诗歌格调实际上已是成规陋习,严重制约了诗歌多元化发展的格局和蓬勃的创造力,也脱离了普通民众。因此,他有意将诗意写成两人间的交流,将口语融入诗歌实践中,以拉近诗歌与纽约大众的距离,还产生了随意自适、凡事皆可入诗的新的诗歌理念,令人耳目一新。如他的诗作《里厄比斯里德》(Liebeslied)的前两个诗节:“我猥琐地/走近你/我们所做的事/就是我将你吞噬/你看见我/独自站立在那里/我是骨头/你是骨髓。” Donald Allen, The Selected Poems of Frank OHar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 p. 380.显而易见,这是置放在诗人与某个人之间的诗行——我和你。诗人与他的关系我们不得而知,这也是诗人不屑于告诉读者的。但字里行间的用心,我们能够探究到一二:首先,这两节诗从诗意上颠覆了当时美国诗坛高贵、文雅的诗风,因为它是赤裸裸性爱的描述,这在所谓高雅、严肃的诗人那里绝无可能,也是极不以为然的;其次,诗歌读起来如同日常交谈,语汇彰显简单直接的特质,简明扼要,毫不雕琢,这又与“新象征主义为求一句诗,拧断数根须”的创作理念背道而驰;最后,诗节中不见一个标点,也没有特定的韵脚、韵律,这在强调传统诗歌格律的名家眼里更是大逆不道。由此可见,奥哈拉刻意用“耸人听闻”的方式讥讽与挑战当时浮华、雕琢、业已失去活力的纽约诗坛。但奥哈拉绝非一味强调前卫,也远不是位把写诗当作“雕虫小技”来把玩的“艺术界的人物”。
尽管一生中常受质疑与误解,但他始终将自己视为严肃的诗人并终生致力于诗歌创作,而他的影响力正是他创作理念结出的硕果。他的“一人主义”诗学所彰显的“平放在人与人之间的诗话”理念,在杰作《致约翰·阿希伯雷》(To John Ashbery)中得到了更深层次的解读。约翰·阿希伯雷(John Ashbery, 1927年-)是纽约派第二位重要诗人,也是奥哈拉的好朋友,作为读者,你只有了解约翰与奥哈拉那亲密的关系,方能充分领会诗中“我”与“你”交流中所流露的兄弟般的情谊。如同生活中的彼此,诗中的弗兰克与约翰一起切磋诗艺,一起在山顶的风口里欣赏白雪飘落枝桠的美景,一起回忆往昔记忆温馨的青草地。言语间,我们依稀可见诗人内心的那份柔软和凄惶,月明时分的空虚以及“何事长向别时圆?”的惆怅都是他不想看到的,更惧怕友人的生命如花卉般凄美地零落,所以诗人开口即言:“我不相信没有另一个世界”,也就是说,今生我与你亲如兄弟,来生我们依然会手足相待。短短的诗句所营造的氛围清新迷人、浓淡相间、深情款款,所用语汇简单明了,口语化十足。尽管因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奥哈拉将杜甫与白居易而非李白与杜甫并置在一起,又把月中长袖飘舞的嫦娥误当作孙猴子女士,但诗中的描写还是令人不禁想起伯牙与钟子期那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美妙境界。所以,全诗的内容完全铺陈在两个有血有肉的活人面前,而非堆积在苍白的两页纸之上,它所流露的情真与凄美既触动人心又令人称道。这首堪称是奥哈拉效仿中国古典诗歌创作风格最为成功的短诗是奥哈拉“一人主义”理念极富特色的呈现,它赋予诗作朴实清新的格调、美妙空灵的意境,又不乏古朴典雅的风貌,再现了作品蓬勃的创造力和生动的艺术性。它的成功还昭示着一个不争的事实:用对话体及口头语言的形式创作诗歌不仅可行,而且同样光彩夺目。
由此可见,奥哈拉在诗作中所采取的日常语言态势,犹如他在打电话时向对方滔滔不绝地讲话,不事雕琢,自然洒脱。这样的创造方式一经推出,其他纽约派诗人竞相模仿,在纽约诗坛一度造成不小的震动。纽约派诗歌是以一种先锋文学的姿态出现在美国诗坛的。在奥哈拉看来,先锋派诗人的优势在于他们可以在一块白板上任意挥写,拒绝接受固有诗歌传统的模式,打破固有诗歌的秩序,从而解放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追求诗歌的更高境界。为了这一目标,种种方式与途径都值得一试。因此,“一人主义”所极力提倡的诗人与某个人之间的诗话不仅是一种诗歌理念,更是对传统诗歌理念的挑战和创新。
三、“一人主义”诗学下的城市诗歌
奥哈拉“一人主义”诗学下的诗歌犹如城市生活的“拼贴画”,折射出纽约大都会的人生百态,成为人们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尤其是纽约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依据。这一切都与“一人主义”诗学理念密不可分,虽然奥哈拉的“一人主义”衍生于兰波的“我是另一个人”的思想观点,但两者之间却有着不同的深层含义。我们在读兰波的诗集时,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几乎所有的诗歌都是对自我的专注、解剖和自白。” 葛雷:《现代法国诗歌美学描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8页。 其字里行间充斥着的自哀自怜之情,我们很少能从奥哈拉的诗作里感受到。与兰波不同,奥哈拉在叙述的过程中始终给人一种轻松愉悦、幽默风趣、真实动人的体验。这就意味着,奥哈拉的诗在强调自我意识的同时,更多关注的是本我与他人外在的联系,它不只是随意精彩的谈话,而是对纽约大都会生活场景和市井民众真实生活的写照,更以“一人主义”的诗学理念折射出诗人对爱情的渴望、对友谊的珍惜、对艺术的追求。
《晨恋》(Morning)是奥哈拉早期所创作的爱情诗之一,共有12个诗节:“我要告诉你/我始终深爱着你/在一个个灰色的黎明/我想着这份爱至死不渝/口中的茶/我觉不出热气/香烟也干巴巴的/紫红色的睡袍/令我发冷/我需要你/我朝窗外张望/雪花默默地飘飞/在夜晚的码头/一辆辆巴士/像云彩夺目/我孤独地想着悠扬的长笛/当我去海滩时/我总是思念着你/沙子因泪水而潮湿/好似我的眼泪。” Donald Allen, The Selected Poems of Frank OHar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 pp.30~31.所选前五个诗节宛如诗人与情侣之间的对话,虽然我们只听到一方的倾诉,但也深切感受到诗人的浓情蜜意以及因得不到对方情感的回馈而由衷流露的孤独、忧伤与悲凉心境。诗行的内容简单流畅,新颖的分行、句法以及无标点使得诗意犹如声声诉说,使读者情不自禁地一直往下读直至休止符的出现。诗中的意象(如“海滩”、“沙子”、“泪水”)可谓简单之极,然而,将沙滩的潮湿比拟成泪水从而折射出诗人的伤心,显得别出心裁。草木无情,如此的推理谬误看似荒诞,却强化了个人情感的真实。毫无疑问,《晨恋》的主题虽是爱情,却从多个视角折射出纽约大都会的风貌——雪花飘飞中的浪漫都市。这座名副其实的不夜城即使在夜间也忙碌不已,碼头的沙滩是情侣约会的好去处,扎堆的巴士、悠扬的乐声使这座年轻的城市散发出青春的活力。因此,“一人主义”诗学的这种口语体的妙用大大渲染了诗歌的内在意蕴和可读性。
秉承“一人主义”重塑人生的主张,1954年,已近而立之年的奥哈拉在随后七年的岁月里写出了一生最好的作品以及最有影响力的艺术评论,从而进入创作的黄金时期。和兰波一样,他歇斯底里地改变生活、重新创造生活,并成为纽约派最具有魅力和冲击力的诗人。到了50年代末,奥哈拉已成为艺术家圈子里的中心人物。尽管他已是现代博物馆的副馆长,要组织重要的展览,但他那繁忙的工作并没有妨碍他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看电影,听音乐会和歌剧,观看芭蕾舞,深夜欣赏雪松,在城镇里到处参加派对,周末去英格兰汉普郡的一个城市——南安普敦寻欢作乐,他的生活始终没有离开过诗歌、绘画以及音乐,也结交了数不清的朋友。《向肯尼思·柯克致敬》(Homage to Kenneth Koch)是一首荒诞不经但却颇具魅力的小诗,表面写的是情侣在在酷热难耐的车库里约会,实质是在表述奥哈拉与其好友柯克亲密无间的友谊和善意的调侃。一次鸡尾酒会后,柯克与一个漂亮却长着一双大脚的女孩幽会,被奥哈拉知道后,写下了下列幽默可笑但却相称的诗句:“我站立在/你家的窗户外/我太幸运了/你刚将它清洗过/后来我想到了你/在车库里/我戴着头罩/感到酷热难耐/你也如此吗?” Marjorie Perloff, Frank OHara: Poet Among Painter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107.显然,诗歌的内容涉及的是奥哈拉和柯克之间的“对话”,诗中对他的调侃溢于言表。他先是去柯克家找他,柯克不在家,后来才知道,后者跟新交的女朋友躲在车库里欢爱,于是诗人挑逗对方:“我带个头罩都热得不行,你在车库干那事岂能不酷热难耐?”诗歌虽短,但依旧反映出纽约当时的社会现象:美国已然成为“车轮子上的国家”;年轻人对爱情已持有自由开放的态度,他们在创造人生的同时也创造了爱与友谊。
奥哈拉的“一人主义”还充分彰显出诗人的艺术观:诗歌与哲学、政治、宗教等统统无关,它纯粹是艺术,因此,它与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与有调无调的音乐、与电影和戏剧、与达达派艺术等有着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奥哈拉的名篇《收音机》(Radio)也充分凸显了“一人主义”诗学观对诗歌艺术理念的改革与创新:“你为什么要播出如此单调的音乐/在周六的午后/我疲惫得要死/渴望记忆能带给与我一点力气。/工作圈禁了我/一周的劳碌后/我就不该听听普罗科菲耶夫的乐章?/还好,我有美丽的德·库宁去追求 / 我想那张橘红色的床/魅力胜过听觉的盛宴。” Donald Allen, The Selected Poems of Frank OHar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 p.234.该诗画龙点睛之笔无疑在最后三行,表面在说有了美丽的画家比尔·德·库宁就可以抛开音乐,实际上呈现的是诗意的倒置。深谙绘画之道又精通音乐的奥哈拉在插科打诨的同时,也并未忘记继续秉持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繁忙的工作的确把他“圈禁”在博物馆里,但却无法阻拦他享受音乐的快感,并教会他“聆听”绘画内在的旋律。 在奥哈拉看来,“一切的艺术——视觉的、听觉的、文字的——均相互依赖。”③ Marjorie Perloff, Frank OHara: Poet Among Painter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81, Preface xxxi.诗中看似随意提起的流行音乐和古典乐章反映了当时纽约乐坛的现状。奥哈拉时代,世界艺术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纽约,多种流派的诗作、绘画、雕塑、无调性的音乐和当代电影融合在一起。奥哈拉坚持认为诗、画、音乐都是同谱艺术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因为艺术不能容忍分割,它们相映成辉,相辅相成,相互融合,就像诗人要走近你、他、他们,走进任何一个读者的心扉一样。艺术与艺术之间、人与人之间实际都存在着某种通感与默契,这就是“一人主义”诗学的精髓。因此,读奥哈拉的诗有时好似在观看“现代派画家在画布上任意泼洒颜料的油画一样,光怪陆离,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③
总之,奥哈拉“一人主义”诗学映照下的诗歌作品充分折射出纽约大都会的生活现状与纽约市民的精神风貌,体现了诗人对爱情的渴望、对友谊的珍惜、对艺术的追求,由“一人主义”在写作过程中的运用所产生的丰富内涵已超越诗歌本身所能涵盖的实质内容而走向了创作的更高境界。
四、结语
奥哈拉一生都将诗歌艺术看作自己的最高追求,但却在其有生之年遭遇种种非议,被认为是“艺术界的名人而非严肃的诗人。” 张子清:《二十世纪美国诗歌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51页。但这丝毫也不妨碍奥哈拉成为当今美国最重要的诗人、美国纽约城市诗人最杰出的代表。写作的激情促使奥哈拉尝试过多种体裁的诗,包括十四行诗、颂诗、民谣、牧歌和挽歌。正是在勤奋的写作实践中,奥哈拉逐渐确立了“一人主义”的诗学理念与创作技法,并在这一理论的观照下形成了自成一体、极具个性的诗歌风格。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诗话,奥哈拉展示了一幅多姿多彩、光怪陆离的“城市拼贴画”,令读者常常在不经意间步入诗人所营造的纽约大都会的场景中。他敢于挑战权威,赋予诗歌创作浓郁的个性色彩,给了整整一代新的诗人写诗的自由:文字的、口头的、一切的一切皆可以成为诗歌的内容,而且可以在灵感闪现时随意写就。正如奥哈拉自己所宣称的那样,“一人主义”诗学有着众多的追随者,如“纽约派”第二代代表诗人特德·贝里根(Ted Berrigan, 1934-1983年)。随着奥哈拉声望的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诗人与读者体会到这一创作手法的重要性,因为“奥哈拉击中了一根新的琴弦——一种崭新的诗歌应运而生。” Marjorie Perloff, Frank OHara: Poet Among Painters,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183.它擺脱了诗歌主题、格律、标点、体裁等种种限制,走向了诗歌创作的自由与不羁;它不仅革新与丰富了美国诗坛,而且对全球后现代诗歌的多元化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
责任编辑:魏策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