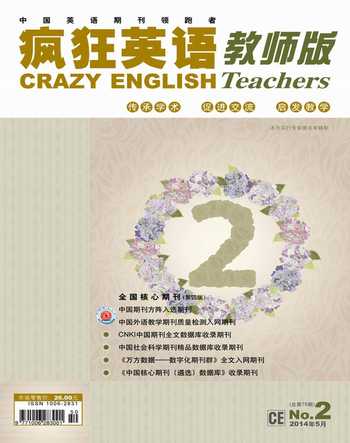《法国中尉的女人》的福柯式解读
李洪青
摘 要: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从考古学的角度将西方社会对疯癫的态度分为三个阶段,认为疯癫不仅仅是生理病变的产物,而且还是文明或文化的产物。《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莎拉的经历可谓是对西方几百年来疯人境遇的较好诠释。本文拟运用福柯的理论来对英国当代作家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进行主题分析,以期解读出作品的历史和社会内涵。
关键词: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福柯;疯癫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4)05-0195-3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4.02.047
约翰·福尔斯是当代英国文坛享有盛名的作家,他的《法国中尉的女人》自1969年问世以来就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大部分评论主要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对其主题进行研究,有些文章对莎拉的形象加以评论,讨论她对自由的追求和大胆选择。本文旨在通过运用密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话语与权力理论,特别是他在《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1961)中对疯癫史的理解,对小说文本进行主题分析,以期解读出作品的历史和社会内涵。法国哲学家福柯一直孜孜不倦于对社会的边缘人群,诸如疯子、犯人、同性恋等的研究,因为他认为这些边缘人群相对于那些“理性”的人而言,在话语特点上更为接近人的本性。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从考古学角度记述了西方社会癫狂的历史,将西方社会对疯癫的态度分为了三个阶段:(1)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在这段时间,疯癫者尽管受到排斥和驱逐,他们仍然乘着德国诗人布兰特笔下的“愚人船”过着极富浪漫色彩的流放生活。(2)古典时代。这个时代也就是“大监禁时代”。疯癫在这个阶段被作为理性的对立面开始遭到迫害,疯癫者被关进了监闭所。(3)现代社会。实证精神病学的创设一改过去对病人的肉体監禁,转而使用现代精神病学原理对他们进行治疗,福柯认为这是对疯癫者的更为残忍的精神摧残。
《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莎拉的经历可谓是对西方几百年来疯人境遇的较好诠释。我们如果将莎拉的经历与上述疯癫的三个历史阶段进行比照,就会深切感受到疯人们的话语权被不断剥夺,以及莎拉作为个人所作的反抗。
1 . 莎拉短暂的“愚人船之旅”
莎拉本是一位农民的女儿,但是她的父亲一心希望她能“光宗耀祖”,所以送她去寄宿学校读书,然而事与愿违,读书使得她有点“高不成低不就”,她的婚事反而被耽误了,于是在莎拉18岁毕业回家后,父亲受到打击发了疯,被送进疯人院一年后就断气了。莎拉此后去塔尔博特船长家当家庭教师,期间爱上了在船长家养伤的一名法国中尉,但后来遭到遗弃,此后每天她都会在莱姆镇海边的防波堤附近独自徘徊。因为传言,她成了莱姆镇上人们所不齿的“淫妇”和神经错乱的疯子。
尽管莎拉被当作疯子在镇上受到排斥和疏远,但她就像加缪笔下的莫尔雷一样,不在乎他人的看法,反而期望在对孤独的体验中享受自由。她在向查尔斯讲述自己的经历时说过这段话:“我有时候甚至可怜别的女人,觉得我很自由,而这种自由她们无法理解。侮辱也好,指桑骂槐也好,都不能动我一根毫毛,因为我已把侮辱和指责置之度外了,我毫无存在价值,我几乎不再是人了,我只是法国中尉的淫妇。”莎拉选择用坏名声来糟蹋自己的同时,似乎享受着孤独。疯狂本身就是一种自由的获得,因此莎拉故意成为人们眼中的“疯女人”,这样她就可以游离于父权制的统治,过着自己想过的日子。疯狂本质上是一种颠覆性的反抗语言。虽然疯狂作为一种反抗略显得有些被动,但比起继续使用父权话语来扼杀自我未尝不是种进步。莎拉“凭着‘自我放逐获取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张中载,2001: 358)。这段经历似乎可以被看作中世纪“愚人船”故事的现代版,然而当莎拉同意在波尔蒂尼夫人家任职的时候,她这段相对自由而又短暂的“黄金时代”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大监禁时代”,开始受到理性进一步的折磨和压迫。
2 . 大监禁时代
由于生活所迫,莎拉不得不受雇于波尔蒂尼夫人,一位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传统道德准则的捍卫者。波尔蒂尼夫人专横霸道,道貌岸然,一心想要通过做慈善事业来获取进入天堂的资格。她捐资修建教堂,但又自认为那笔钱财远远不足以确保她死后进入天堂,因而在遗嘱中保证将所缺的数额待她死后全部补上。可是她又担心在读遗嘱时上帝恰巧不在场没有听到,因此为了求得安心,她收留了“堕落的法国中尉的女人”。通过这一细节描写,波尔蒂尼夫人自私、可笑而又愚蠢的形象跃然纸上。自从莎拉来到波尔蒂尼夫人家任职后,她的漫漫黑夜已然来临。
波尔蒂尼夫人对仆人们的物质生活毫不关心,然而对他们的精神生活却无比关注,整天担心他们的灵魂会在没有她的监管下堕落。因此,“他们星期日必须去教堂两次。另外,每天还要进行早祷要唱圣歌,做日课进行祷告……早祷固然很好,但是还有一次崇拜上帝的仪式。仆人们要在厨房里举行晚祷”。莎拉的工作是为波尔蒂尼夫人读《圣经》,这也是后者精心计划的,她期望莎拉这只“迷途的羔羊”能幡然悔悟,迷途知返。在莎拉的灵魂得到拯救的同时,她的灵魂也得到了拯救,从而为自己进入天堂增加筹码。然而,这位特立独行的莎拉却压根儿不相信上帝,她对维多利亚时期虚伪的宗教道德嗤之以鼻,“她看透了尘世,也看透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教堂,看透了教堂中那些污浊不堪的玻璃,那种种蠢事,还有那些对《圣经》狭隘,拘泥的解释”。因此,在波尔蒂尼夫人家中任职对她来说不啻为一种精神上的折磨。此外,莎拉的每次外出都受到了管家弗尔利太太的监视。这种压抑与束缚是无处不在的。在福柯看来,高度理性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它的公共设施和福利形式)凭着对社会各个领域的监督和干预,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的监闭所。波尔蒂尼夫人的府邸就是这样一个披着慈善外衣的监闭所,波尔蒂尼夫人看上去就像“一个女修道院院长”,弗尔利太太是修道院的看守,“这两个女人堪称是现代虐待狂的老祖宗”。福柯认为,权利总是与知识携手并进,利用知识来扩张社会控制。在这样微型的社会权力机构中,处于主体地位的“院长”波尔蒂尼夫人和“看守”弗尔利太太就是利用虚伪的社会道德来对莎拉进行控制,利用她们在话语体系中的霸权,蛮横残酷地对待莎拉,以体现自己的权威。
3 . 精神炼狱
当莎拉最后难以忍受波尔蒂尼夫人对她的监禁和控制后,她巧用计谋让自己摆脱了波尔蒂尼夫人的魔掌。她故意在与查尔斯会面后,让一直监视她的弗尔利太太发现,从而成功地让波尔蒂尼夫人解雇了她。读者读到这里本该可以松一口气了——莎拉终于重获自由,然而查尔斯却将莎拉和他吐露的心事全盘告诉了格罗根医生。和传统的心理医生一样,格罗根“身上仍带着魔鬼的气味”,对病人的性情非常了解,“他可以根据病情的需要,要么给予熟练的治疗,要么加以巧妙的安慰,要么干脆不理不睬”。当莎拉还在波尔蒂尼夫人家任职时,格罗根医生就诊断她患了“抑郁症”,然后给她开出的药方是让她每天都有半天的自由。在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观念的作怪下,格罗根医生一直对莎拉的事情很感兴趣,并将她作为一个特殊的病例来看待。在小说第19章,格罗根医生和查尔斯探讨了莎拉的病情。医生提到他曾建议莎拉离开莱姆镇,去埃克斯特的一位朋友家去做家庭教师。这在常人看来是个不错的选择,然而,“智力高于常人”的莎拉却拒绝了他的“好意”,因为别人称之为“善良的虔诚的基督教徒”在莎拉眼中却是“比最残酷的异教徒还残酷,比最愚蠢的动物还愚蠢”。那善良人的家不过就是个“监闭所”。这位代表理性的医生在与莎拉的第一次交锋中遭到了失败。在第27章中,莎拉被波尔蒂尼夫人解雇后不知去向,查尔斯猜到了她会在他们见面的老地方,然而他预感到如果再去与莎拉见面,他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地步。在犹豫和彷徨中,他向医生讲述了他和莎拉相识的全部经过。格罗根医生曾经受過妓女的欺骗,尽管书中对此没有进行详细论述,但格罗根医生说他自己“被她们毁了”,并疯狂地想要“报仇雪恨”。我们可以想到事实上他把莎拉也看成是他报复的对象之一,因此他要求查尔斯把他们以前相会的地点告诉他,并打算在找到她后将她送到疯人院,甚至还向查尔斯承诺“在那里她的精神创伤可以得到治疗,她将得到斯宾塞医生的治疗和悉心照顾”。这看似是给莎拉开出了较好的药方,实则是打着人道的幌子对莎拉进行残忍的精神摧残。莎拉作为疯癫者势必在接受医生心理和精神治疗的同时沦为维多利亚时代的牺牲品,彻底地失去话语权。格罗根医生的药方事实上是维多利亚社会给疯癫者套上的层层枷锁。在《疯癫与文明》第6章“医生与病人”以及第9章“精神病院的诞生”中,福柯认为医生所代表的理性世界对疯癫有着绝对的权威。精神病院中的精神治疗并不意味着疯癫者的身体解放,相反却意味着精神被完全制服了。“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使疯子认识到自己处于一个天网恢恢的审判世界”(米歇尔,1999: 247)。幸运的是,莎拉最终逃出了他的视线。
福尔斯颠覆了传统文学作品中“疯女人”的被动形象,赋予了莎拉敢于追求自由的无上的勇气,让莎拉凭借自己的智慧,一次次成功地化解了困境。莎拉在被冠名为“法国中尉的娼妇”后却仍然我行我素,泰然处之。她主动结识了贵族青年查尔斯,并且一直在二人交往的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她不断制造机会接近查尔斯,把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原原本本地倾诉给他。查尔斯一开始同情她的遭遇,希望能够将她从不幸中拯救出来,但慢慢地爱上了这个神秘的女子,并且一步步沦陷,在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最终竟然决定和欧内斯蒂娜解除婚姻,向莎拉求婚。然而在查尔斯和莎拉的关系达到高潮后,莎拉却神秘地失踪了。在作者提供的三个截然不同的结局中,其中一个就是查尔斯千辛万苦找到莎拉后向她求婚,却遭到了拒绝。莎拉此时已是一个独立成熟的新女性,她为一群前期拉斐尔画派的画家工作,不愿意让婚姻剥夺了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对她而言,婚姻会让她失去自我,因此选择孤独是她对自我存在的最终认定。在整个故事中,莎拉一直是自己命运的主宰,福尔斯借莎拉这个具有反叛精神的“女疯子”形象控诉了西方正统文化中的“理性”对“非理性”的压迫。
莎拉的疯癫映射了一个长期遭受西方父权制和理性主义压迫的女性企图追求自由和反抗压迫的心路历程。莎拉这样的疯癫者其实表达了一种对自由的渴望,对男女平等关系的一种期盼,然而这些正常的人的需求却在当代西方社会不得不以一种非正常的疯癫方式表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疯癫与其说是自然的产物,不如说是文化和社会的产物”的论断恐怕更容易得到我们的认同了。
参考文献
程丽.《法国中尉的女人》浅析[ J ] .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0 6 ( 2 ) .
宁梅. 论约翰·福尔斯对“疯女人”形象和心理医生形象塑造的延续与创新[ J ] . 当代外国文学,2 0 0 8 ( 1 ) .
米歇尔·福柯. 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 M ]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 9 9 9 .
约翰·福尔斯. 法国中尉的女人[ M ]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 0 0 2 .
张中载. 二十世纪英国文学—小说研究[ M ] .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 0 0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