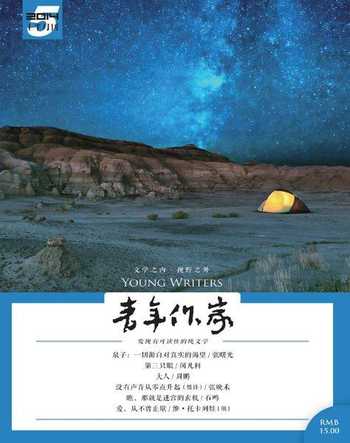狗 命
栗辉龙
或许你不曾到过流沙镇,或许你也未曾听说过流沙镇,如果真的没有,那么请允许我向你描述一下:那是一个藏在旮旯里的小镇,它没有沈从文笔下的边城那么恬静、柔美,也没有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里的香格里拉那么神秘,有的仅是一条弯弯的山路像蛇一般延伸入流沙镇,末了便能看到许多白色整齐的房子,这些房子更多时候像一些野生的菌类。许多黑烟集体从烟囱里钻出。不要以为你大可以一眼把流沙镇看透,其实不然。
流沙镇就好比是一页没有修订在历史上的历史,经常让生活在这方土地的人去揣摩审读它:譬如这里什么时候开始养狗?为什么很少有老人?……流沙镇里的人视养狗为传统,几乎每户都养狗。依流沙镇的格局,沿公路边养狗的都是“大户”人家,是一些比较凶恶但擅长经营生意的人——经营汤锅,而住在离公路较远地方的人就仅仅是养狗罢了。这里的年轻人很多,唯独老人出奇的少。在流沙镇里你很难见到陈旧而有生命的东西,所以流沙镇里的人都有一种非凡的本领:能以声音辨别他们是否年老。许多时候,我一个人踏着人字拖鞋走在橘黄色的街灯下,我见到的流浪狗比这里的人还要多。
关于流沙镇养狗的习俗,我那早已死去的父亲曾经对我说,养狗如同女人养小孩一样平常。年幼无知的我对他这话百思不得其解。只是流沙镇上的人都不约而同继承着祖辈遗下的习俗。
我所居住的房子是沿公路边的,也就是说我家是开汤锅的,但我的样子并不凶恶。每年春天,我们镇里的人都在忙着粉刷自己的房子,他们在墙上涂抹上浓厚的石灰,干了的时候像一层层快脱了的皮。临近冬天的时候,流沙镇的汤锅就像野生植物一样多了起来。前排的白色房子撑起了红蓝白三色相同的塑料棚,棚子上方歪歪斜斜地写着“xx狗肉汤锅”。
很明显这块土地上的人都喜欢吃狗肉。他们趁着冬日的光景,用狗肉消去一年来的疲劳,到店后,威风地把车子停在店门前像泊船一样。这些喜欢吃狗肉的几乎是清一色的中年男人。他们有的红光满面,有的衣衫褴褛,他们只管手里攥着票子就往店里挤去。
我们这里的狗肉要数李根的最为出名,李根是我的父亲。那年代,李根是流沙镇上最风光的男人,尽管相貌凶恶,眉宇间长着一大颗黑痣,讲话就像放鞭炮,可他却是流沙镇上最懂得经营生意的人。他能弄出最地道的狗肉。那个阴冷的下午,我半蹲在房间前的石头上看着我的父亲宰狗:他一棒子就让老狗倒地,然后麻利地把着刀,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屠宰着狗的尸体。我的父亲曾告诉我养狗就好比养人,怎么他却如此对待这些残弱的生命,我不得而知。
一直以来,我的父亲所经营的生意就如田地里开花的芝麻,一节赛过一节,火红得让人羡慕。走在路上同行们都会拍他的马屁。他忙乎得连自己的头发掉色都浑然不觉。我告诉父亲:爹,你的头发白了。他这才把生意交给我打理。
我接管汤锅店后,生意就像王二小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一直苟延残喘着,原因很简单:一是我害怕杀狗;二是我压根没有我父亲那凶狠的胸襟。我的父亲曾经指着我的鼻子骂,你他妈的要是做生意的料,我他妈的就不会活这么久。他骂这话时我一直很纳闷,是的,我的父亲老得连牙都掉光了,他是流沙镇上唯一一个活过70岁的老人。
我的生意衰败景况直到我把生意交给我儿子打理时才有些好转。在我经营的时候,即使是最寒冷的冬天,我的狗肉汤锅店里也只有一两名顾客。有好几回我想把家迁移到里边不做生意,但结果没搬成。我店里的狗肉都是我儿子弄好的,狗也是我儿子一个人屠宰的。有的客人说,我儿子的手艺比他爷爷还要好,有的说我儿子仿佛就同他爷爷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们说我儿子比我强,我总是很窝囊地站在一边听着。
在一个清晨,我仍然如往常一样,拿着旱烟筒,抽着那些便宜劣质的烟草,烟头的红点在我的吸气下忽明忽暗。这时我半蹲在门前那块光滑得可以照脸的鹅卵石上。呆呆地望着来往的路人和狗。
一条老母狗摇晃着下垂的乳房在我眼前走着,它一直低着头,仿佛与这个世界隔绝起来。我朝它“嘘”了几声招它过来,老母狗抬起头望了望我,灰淡无光的眼神在这个冬日里显得特别孤独无助。
它一瘸一拐地向着我走来,这是一条受伤的狗,一条我养了8年的老母狗。他蹲在我面前不断滑动着喉结似乎要我检阅它的饥饿,我抚摸它,笑了。我脸上的皱纹如浪,此时即便是没有阳光的冬日,我也能感到骨头里的水分一点点地被蒸发掉。
我在流沙镇整整活过了无数春秋,目睹过我的父母在冬日里安详地死去,为他们做了无数次哀悼。我也目睹一些与我年纪相仿的老人在这样寒冷的冬天像花一样地凋败。陈树和我年纪相仿,那年冬天之后我再也没有在春天看到陈树拉着他的那条黄色的老狗在路上徘徊的身影。陈树逝世之前,我还看到陈树的儿子把他养的狗拉到汤锅店给屠宰了。此刻流沙镇里和我年纪相仿的人在这样的冬天里彼此之间感到深深的不安。
就在前一天,我抱着我的老母狗坐在火炉旁边,我希望有足够的热量打发走我内心的寒冷。火炉上边烤着几个干扁的馒头,一碟几天前的菜放在炉旁的木凳上,屋里的光线很是暗淡。老母狗看着炉子里的火,我看见火在它瞳孔里燃烧,但我仍然感到它被寒冷侵犯着——它不住地哆嗦。寒冷的风直往墙的裂缝里钻,此时我把老母狗抱得更紧了,这么冷的冬天又一次不动声色地来到我家里。早前我把怕冻的东西一一搬进屋子里,钉好窗户,用碎棉屑填着裂缝,但寒冷还是进来了,它比我更熟悉这里的每一处裂缝。
我抽到第八口烟的时候,我的儿子从他沿公路的白房子来到靠林子的破瓦屋找我。之前我儿子打伤了老母狗的脚,他对我说,要把我的狗宰了。他还甩了我一巴掌。现在我那凶悍的儿子就站在我面前,我和我的狗望着我那麻子脸的儿子。他对我说,他今天一定要带走我的狗。他的话像火药一样散播在空气中,但我坚决不让他带走老母狗。他拿出绳圈往狗的脖子上套,好几回都让我给弄开。这次他缚好了圈,走近我身旁时猛地用绳圈套住狗,奋力地一扯,把狗从我身边拉了出去,我也摔倒在地上。我的头“砰”的一声像鸡蛋般撞在石头上,我的儿子拖走我的老母狗,末了还踹了我一脚。“老不死的,老了连屁用都没有,狗还能让人宰来下酒,你却终日靠我养。”他丢下这句话就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此时我头上的血顺着我的皱纹模糊了双眼,我身上涂满了像植物汁液一样的血。
在此后的几天里,我经过我儿子的狗肉汤锅店时都没有见到老母狗。春天的时候我儿子圈狗的笼子空了,沿公路边的汤锅店,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忙着拆掉塑料棚,然后开始粉刷房子。
事实上每年一到冬天,我就感到无比地害怕,我总是怕走不过冬天。譬如现在,冬天刚过我就担心下一个冬天的到来。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这里的老狗就像这里的老人一样,等到岁月带走它们的青春年华,等待它们的不是同情,不是怜悯,更不是关爱,而是无尽的孤独和死亡。我的老母狗在冬天死掉了,我只剩下一条孤单的命。
我穿着冬天穿的那件破旧的黑色袄子,茫然地走在流沙镇的路上,虽然是春天,但我依然觉得寒气逼人……
[作者简介] 粟辉龙,生于1987年,四川南充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在《星星》《青年文学》《散文诗》《美文》《时代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现居四川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