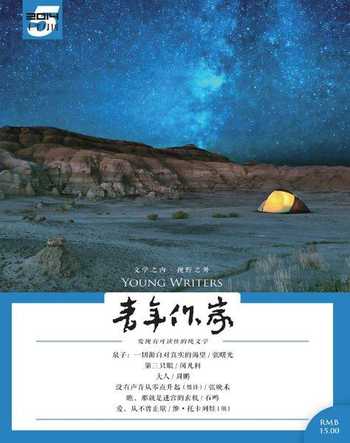小路都一样
17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和生前很疼我的姨夫走在去煤矿山的路上。月亮在记忆里仿佛处于树梢的位置,远远的地方,可以听见欢悦的叫得像乌鸦的雀。
我长得很矮,到不了他的肚脐。我喜欢看他锃亮的皮鞋,仿佛一点都不带时间的痕迹。他的昏黑呢子大衣里面渗透出古龙水和洗衣粉混合的味道,说不上让我喜欢还是不喜欢。他的脸色在黑暗中仿佛黑面包里夹着的香肠,配合着我看不清,但在想象里可以勾勒的痤疮和小眼睛,总是若隐若现。
忘记了我们走了多少步。我的小胶皮鞋和他的大头皮鞋共同作响,在老旧的大路小街留下声音。多年后,我仿佛还能在这条路上听见我们当初的痕迹。当时觉得煤山是个好玩的东西,路一边是堆得高高的煤堆,仿佛是山上滚下来的雪堆。姨夫告诉我不要瞎喊,煤堆轰然堆下,凭我母亲挖几天也挖不到我们。路另一边是孤独的坟墓们,里面住着和我玩得最好的伙伴的奶奶,我的伙伴总是吓唬我,他奶奶生前总是心情不好,不好的原因就是我总欺负我的伙伴,或是给他喜欢的女孩的帽子里放绿豆虫,或是把他推到吴梅子的身边。吴梅子是我们童年时代里镇子上的傻女人,没人知道她为什么疯了,她仿佛活了几百年,自这个小镇第一天诞生就存在,用她特别忧伤的傻笑来带给小镇的孩子们快乐。因此,他奶奶的灵魂总是要变成一只动作有点迟钝的老猫。我注意听着猫声,记着姨夫给我的承诺,走到了矿里就一定有好东西。
后来的我失望透顶,矿里我是没有进去,只在外面的看门屋子里看见了一个总也睡不醒的大妈,口水的味道满屋子都是,至今我也记不清那晚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就是记得我和姨夫的脚步声,以及我们走过的煤山旁的小路。后来我的姨夫去世了,由于癌症。我忽然发现我原来和姨夫之间的话很少,没啥特别的记忆,直到我发现我和姨夫共同拥有的东西无非就是那一条小路。
十年前,我告别故乡后第一次回去,夜晚的光亮里,我看见远远的房子上面有个人在走来走去。房子对面的小楼就是我曾经的家。我不敢往回走,往前走也是无期。这条小路太长了,我心里装着别的事,小路载着我往前走。房子上的人形状模糊,面容可怖。我想起了所有鬼片的集合,那人也是个集合体。当年我还在学着几何,觉得那人所属的圆必定在鬼神圆之内。那人跑得飞快,瞬间不见。
小路太长,幼年我从舅家回来的时候还分明很短。小路的尽头是食品店,天色太晚,已经关了。食品店旁边就是容得两个人并排打滚儿的胡同,进去就是家所在的小楼了。我拼命跑去,却害怕任何一个拐角。但就是这个小路的拐角里,我看见了穿着紫色外套的女人,头发特别蓬乱,我当然觉得她有百分之五十可能是鬼。但是借着记忆里的月光,我还是看见了蓬乱背后的脸,明显的板牙,猫一样的眼睛,只不过尽是可怕的鱼尾纹,仿佛再过一阵子,鱼尾纹就会把她的眼睛统统吃掉。这不是吴梅子么?
吴梅子,是吴梅子。虽然我离开故乡几年了,但是我还是能认出吴梅子。我身上一颤,立即想到最好的同伴那天说我的话。那天,我把他推到吴梅子的身边,吴梅子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儿子一样,立即想把他扑倒在怀里面。脸上的笑却不再是傻笑。我看见她当年还不深的鱼尾纹里面藏着污垢还有新鲜的眼泪儿。她再不笑了,确切地说是微笑,慈祥得可怕。同伴儿跑开,诅咒我:“你不是要离开这么?你别回来,吴梅子就在这等着你!就是这。”后来,他又对我说,那个吴梅子怀里有奇特的尿骚味儿。
可不就是这,当年我最好的伙伴指着的地方。这个小路的路口,站在面前的吴梅子。
我又想起来,前几年的时候,她仿佛被人说成消失了。后来听说她在厕所里被喝醉的人玷污了。后来,吴梅子不见了。人们说她死了。她活了那么久,却没有和小镇一起湮灭。她仿佛先走了。
现在,我见到的不就是她,或许,她早就不在了。但是在这条小路上,我几年后第一次探乡,却看见了小镇的吴梅子。她曾经在我们玩耍的小路上不只一次经过。吊着膀子,傻笑着。有小朋友被推到她身边,她就不笑了,然后微笑,然后慈祥得可怕。
现在呢?我不知道前进还是后退了,吴梅子见了我却也停下来,她还是笑了,夜里,傻傻的笑。我却觉得她不傻了,她仿佛认得我,认得我皮囊里装着童年。然后她的表情像是熟了后再不能变形的饼干,老旧的花纹里流着的是新鲜的眼泪。她的表情动了的,慈祥地笑,仿佛好久好久不曾见我的童年。在她的世界里,童年的我们似乎都是属于她的小镇里的一部分。
她认得我的,浅浅地笑了,有点慈祥,这次不可怕。一年后,吴梅子被正式宣告去世了,政府的人草草处理了她。据说她是在某一年冬天冻死或是在某一年夏天溺死在小镇的河流里,我们的记忆中渐渐没有了她和她的小镇。她没有和小镇一起湮灭。
四年前的一天,我沿着小镇的河流去找童年最好的伙伴儿,我们没有彼此的电话,十几年不曾联系。我们曾经吵架打架不见彼此,分别的时候不在一起。但是我们还是最好的伙伴儿。他给我的老家写信,却从没问我的新地址。记忆里的月光铺洒在不太轻灵的水面上,水面承载了过去十几年逐渐老去的洗衣泡沫。流走又流来,流来又流走。河流的旁边没有坟。这条路离煤山的路很远,离着回家的小路不近,但是拐来拐去总要相通的。我从舅妈那里听见了关于我的伙伴的一个版本,他童年以后不曾长大过,还是一米多一点。小镇在湮灭,但是我不要说我的记忆在湮灭,虽然我在回忆里时常抹杀它。我只能说小镇在湮灭,河水在湮灭,小动物们在湮灭,熟悉的昆虫也不见了。小路上的草被行人踩在脚下,一年一年曾很少抬头过。夜晚,我一路走过去,月光始终跟随我,我却没有看见熟悉的房子。没有听见熟悉的吵架声。那里一半是我,一半是他。如果舅妈讲的是一个童话就好了。一个人不再长大,永远稚嫩地笑傲不断出现鱼尾纹的小镇。
听见舅妈的话后的几年的生日里,我都会梦见最好的伙伴在我的梦里出现,却都是幼年的样子。我没回故乡,没机会见到他,或者也不敢找他。或者一直希望他是我想象中的样子,童颜未衰。
我没有找到他,没有找到我们曾经嬉笑怒骂的小路。我找到了标志性的百年大松树,那棵树下曾经有很多孩子转着圈子许愿。但是就是没有他家的房子。午饭的时候,舅妈告诉我另一个童话,我的伙伴的一辈子都没长大过,一米多一点点。他的生命终止在2004年冬天的一个傍晚,营养不良。还有,听说他生前不喜欢剃自个儿的胡子。这是我听见的关于他最甜蜜的习惯。
离去的时候,小路上有只动作不大灵活的猫。原来它不在煤山,却在这。
[作者简介] 黑山坡,曾任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记者,为社会新闻、人物特稿、讣闻栏目供稿,现旅居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