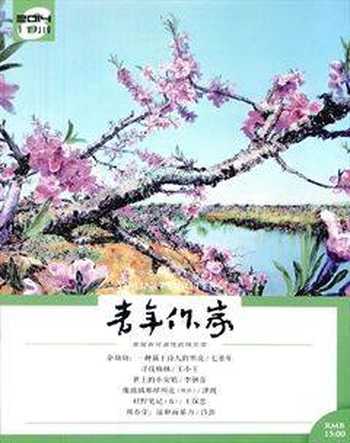克拉科夫
扎加耶夫斯基[波兰]
过于美丽的城市往往会失去个性。一些南部城镇,为游客们修葺一新,让人想起那些光鲜的广告图片,而不是生机盎然的人类居所。丑陋创造个性。克拉科夫并不抱怨自己缺失了不幸、凝重且忧郁的场所。
紧邻着亮丽的文艺复兴时期街道的,是阴暗的几乎是黑色的峡谷溪流,从19世纪的城镇中穿过。蓝色的有轨电车、卡车,身着冬天外套的昏昏欲睡的路人,以及穿着厚重长袍的村民们,在这些峡谷间穿梭。在咫尺之外,便是明亮而优雅的街道,都通向市集广场。
相同的情形是,神经细胞服务于脑神经中枢,它是我们肌体的主角;同样,中世纪的修道院里,那些熟读亚里士多德著述的僧侣们,在艰难而实际的日常生活中,受到那些精神饱满、拥有巨大而强劲双手的僧侣的帮助。
几条凝重而丑陋的街道的名称:德鲁加(Dluga),克拉科夫斯卡(Krakowska),斯塔罗维斯日纳(Starowislna),兹维齐涅茨基(Zwierzyniecki)(更不用提右岸的帕德格勒泽
我作为一名来自格利维策(Gliwice)刚被录取的大学生,来到克拉科夫时刚满十八岁。格利维策是一个西里西亚城市,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我的家庭被从利沃夫(Lvov)——传说中的东方城市驱逐。在对失落的利沃夫的渴望中,我度过了整个童年,尽管离开那里的时候,我只是四个月大的婴儿。当我来到克拉科夫,就像一名朝圣者来到一个圣地进行朝拜。克拉科夫是一个真实的城市。
我在十月抵达克拉科夫。冰凉的雨倾泻而下,空气中透着凉爽。大学里还没有开课,我有大把的时间。我整日穿行于城市的大街小巷,漫无目的地闲逛。我是一名害羞的学生,不敢进入商店、书店或是博物馆。我只是暂时从外面打量着一切。大门紧闭,温暖的灯泡在窗内散发出黄色的光芒。
我既不嫉妒,也不觉得疏离,并不厌恶这一切。我的内心满是惊奇。仅仅瞥见书架的一角,就足以让我对自己说:一位哲学家、智慧之人或者声名卓著的作家极有可能居住在这里。
我沿着德鲁加路走到普兰蒂环城绿化带(Planty),我会沿着绿化带散步,尽管小径上经常覆盖着一层秋天的湿气,以及随风跌落在地的残败落叶。
普兰蒂绿化带隔开了两类街道,阴暗的和明亮的,它也是一道堤坝,将郊区的浑水和市中心澄澈的溪流一分为二。到了夏天,茂密的树——梣树、栗子树、榆树、椴木,甚至波兰非常稀有的悬铃木,绿荫如盖,聪明的鸟儿则在里面安家筑巢。而在十月,这些树木的树冠则变得稀疏。
我充满敬意地望着那些修道院的外墙,这些庭院占据着大量城区面积。慢慢地,我发现,有两个高地是观测教堂的绝佳位置:位于帕德格勒泽地区的科希丘什科(Kosciuszko)和克拉库斯(Krakus)。克拉科夫的教堂会让人联想到一艘又一艘紧挨着的航行中的轮船,从科希丘什科高地望过去,船头正对着观测者,(当然,因为它们都是沿着东西走向修建的)。从克拉库斯高地望过去,看到的则是一排长长的砖砌的殿堂——教堂圣殿巨大的躯体。而且,这样看过去,圣玛丽安(Marian)教堂反而并不是最大的,圣凯瑟琳(St. Catherine)大教堂和圣体(Corpus Christi)教堂显得更大一些。
它们一艘紧挨着另一艘航行着,拥挤,却身形巨大。它们所置身的大海是城镇房屋的屋顶。大雨过后,太阳从紫罗兰色的乌云背后跃出,那些分散在各处的尖塔和圆形穹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从克拉库斯高地看过去,城市则仿佛区分出了丑陋和可爱,虽然界限模糊。突然,一切都显得必要,那些阴暗和凝重的街道变成了波浪的褶皱,而教堂本身却显得笨重。我们并不是在意大利,船只从远方驶来。
我花了很多时间,驻足在书店的橱窗前。记得有一次,我在一家书店前面停了下来,那是格贝特纳(Gebethner)书店的前身(我当时对这家书店的名字一无所知),书和唱片摆放在那里。一对外省来的夫妇——一个长着一张乡绅脸的老人和妻子,停在我的旁边。乡绅模样的老人指着一张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唱片。他对妻子说,这是非常艰涩的音乐。
我立刻兴奋起来。我的漫游并不孤独。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瞬间将我们联系在一起,虽然,我马上把自己从橱窗前拉走了,沿着朝向漆黑一片的瓦维尔城堡(Wawel)方向行进,继续我的游走。我忙于瞻仰这座城市。我的行程越来越长,但我总是回到中央广场。
我的一条路线通向维斯瓦河高高的堤岸,我的左边,是被秋天所侵蚀的园林;而右边,维斯瓦河静静地在那里流淌着。我可以看到河对岸的泊船码头,即便是现在,在天气晴朗的下午,身穿运动服的学生也会坐在那边的船里,就像是一些巨大的棕色昆虫在准备它们的赛周会。终于抵达了这座城市,在这里,我可以如此近距离地观察着意大利風格的诺伯丁(Norbertine)女修道院。
我也漫步于巨大而宽阔的布洛涅公园(Blonie)。有时,浓雾将克拉科夫的中心笼罩其中,而那时候我自己就仿佛置身于乡间,置身于一个宽阔的牧场,独自一人。
从布沃涅公园穿过亚尔登(Jarden)公园,就来到了一月十八号街(January 18 Street)周围的街区。这里曾经是,现在也是充满人文气息、严肃而安静的居住区。这一次也是如此,这里的每一位路人,看上去都像是画家或者演员。
我在平日里不时地出入教堂,那些时候教堂里几乎没有人,除了两个老太太跪在神坛前,低声与耶稣交谈着。
有人告诉我一家便宜的餐厅,很多知识分子都在那里吃饭。还有人告诉了我主教宫的位置。我自己找到了大剧院的确切地点,也找到了文学杂志编辑部,还自己琢磨出了交响乐团的所在地,这幢仍旧被交响乐团使用着的建筑,已经丑陋不堪,也丝毫不能发挥应有的功用,被电车车轮的摩擦声破坏的柔版不计其数,即便如此,交响乐依旧让我激动不已。
之后,我一直居住在克拉科夫,在那里呆了将近十七年之久,我的激情逐渐溶解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之中。渐渐地,我认识了一些当地的名人、艺术家、学者以及编辑。不能说我对所有的人都不再心存幻想,却没几个能和我当初对他们的期待是一样的。艺术家们总是酩酊大醉;我无法理解这一点,我觉得想象力所带来的刺激早已绰绰有余;而学者们都很谨慎,编辑则显得很多疑。在开始谈论政治事务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压低声音。城市的上空悬挂着一道幕布。我觉得自己像一名旅行者,偶然闯入了一个被恶魔所胁迫着的地方,一个被弥诺陶洛斯 所胁迫着的城市。
没人能够谈论弥诺陶洛斯,我自然也并非是从不知名的地方闯入的无辜漫游者。我同样沾染了极权主义的病根,除了来自外省和我微不足道的童年,而正是这些,让我能够处在这样的位置,能够留意到这里奇怪的氛围,危险、不确定以及妥协。
我们都知道,这一切都已经改变了,但我并不想说这些。我想要说的,是在离开这里七年之后,1989年6月,我重新返回克拉科夫。在这七年之间,我造访过那些伟大而天赋荣光的西方城市——巴黎、纽约、斯德哥尔摩。我曾见过波士顿、旧金山、阿姆斯特丹、伦敦、里斯本、慕尼黑。我并不是在炫耀这些,这也没有什么好炫耀的(如果你不是城市的建设者)。我提到这些只是为了说,我作为一个在外面游玩厌倦的旅行者回到了克拉科夫。
是的,克拉科夫的很多东西如今看上去很矮小,也很乡土气、贫穷、疏于管理。老剧院的大礼堂,也变小了很多,我曾经在那里体验到了最强烈的戏剧的震撼。在我的记忆中,它是如此恢宏,可事实上,它没有那么高大。
如今,走在克拉科夫街道上,我很确定这个城市变得多么小了。但一段时间之后,出乎意料地,我之前对这座圣城的景仰之情又一次回来了。我漫步在克拉科夫,同时感受着它的渺小与伟大、粗鄙和壮丽、贫穷和富足、平凡无奇和非同寻常。只有一件事我确定无疑,普兰蒂绿化带的树木长大了。我对这座城市的仰慕因为怀疑而消减,但树木却更加伟岸,也更为真实。
·译者手记·
2013年9月,克拉科夫机场,下着细雨,通往市区的班车即将驶入站台,我手忙脚乱地捣鼓着售票机,在一位波兰小伙的帮助下,终于在最后时刻买到了车票。公交车上非常拥挤,连椅子也显得狭窄,两个人坐在三个人的座位上已经满满当当,随着车子行进,游客们、更多的是当地人不停上上下下,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感觉自己又回到了中国,坐在上海某辆公交车上,在雨天去赶赴某一场重要的约会。我和丈夫在中央广场与《世界文学》副主编高兴先生碰面。接下来的几天,拿着地图,按图索骥,我们一起穿梭于城区各处,在那些传说中的、古老而令人景仰的地方游走、停顿和遐想,尤其是诗人米沃什和辛波丝卡的故居和墓地,以及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克拉科夫国立博物馆中,我们还碰巧遇上了名为“辛波斯卡的抽屉”的展览。克拉科夫是美丽的,那些伟岸的建筑剪影,就如同它们在几百前就定格的那样,印刻在每一位到访者的脑海。但除此之外,留在我的记忆深处的还有:细雨中在教堂前面吟唱的那位中年女子的歌声和眼泪;为了带我们找景点陪着我们走过好几个街区,一路上手舞足蹈为我们讲解的波兰中年人,以及那一对随着音乐情不自禁在城门口起舞的老人……这些生活在这里的人,用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与爱,装点着克拉科夫,正是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饱含着历史创伤与生命张力的城市,正是他们,让我彻底爱上了这座城市,让我想要更多地了解它,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它。后来在扎加耶夫斯基的随笔集《两座城市》中的这篇《克拉科夫》时,我就开始了翻译。
克拉科夫是一座中世纪古城,文艺复兴时期,这里曾是欧洲文化和科学的中心。克拉科夫也是一座文学之城,两位诺贝尔奖诗人得主——米沃什和辛波斯卡都在这里度过了大量的时光。这里也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雅盖隆大学的所在地,这是哥白尼的母校,也是诗人辛波斯卡、赫伯特、赫魯伯的母校,当然也包括健在的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大学的学习生涯让扎加耶夫斯基开始了在这里长达十七年的生活,而在离开七年之后,他又回到了这座城市。如今,他往返于美国和波兰之间。
维斯瓦河从克拉科夫城区缓缓流过,两岸总是有散步和骑车的市民。瓦维尔城堡则占据着城市的西南角,俯瞰着整个城区,诗人米沃什一生最后十年就在城堡北边的一处老宅中度过。中央广场是欧洲最大的中世纪广场,永远充满着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等待着整点的时候圣玛丽安教堂的号角响起。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曾在《两生花》中拍摄过这个广场,电影中来自法国的维罗妮卡在电车上拍下了波兰的维罗妮卡……而城市的西北角,是“知识分子”所偏爱的区域,这里不再有中古时期的印迹。如今,走在这些这个区域的某些街道上,社会主义时期的遗留物仍旧会不时地从某个角落冒出来,面目依旧清晰可辨,提醒人们记起曾经的那段特殊历史。为此,扎加耶夫斯基还写过一篇《知识分子的克拉科夫》,集中描绘了城市的西北角,诗人辛波斯卡曾住在这一片街区,还有许多波兰著名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当然还要包括扎加耶夫斯基自己。这里是游客的相机不会去捕猎的地方,却遗留着真切的当代波兰历史记忆,也铭刻着扎加耶夫斯基诗歌中所凝聚的独特历史经验。
诗人及评论家罗伯特?品斯基曾这样评论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关于过去在普通生活中的存在:历史并不是死去的编年史,或者由某些主义启发而成;历史是一种无处不在有时却很微妙的力量,它源自人们在每一天的所见和感知——用我们所见和所感知的方式”。而在《克拉科夫》一文中,扎加耶夫斯基正是透过一种最为日常的视线和感知为我们勾勒出1960年代的克拉科夫。如果说作为一名新世纪的观光客,我们的目光更多会被这座城市曾经的荣光、被市集广场古老而宏大的建筑所吸引,那么,1960年代的扎加耶夫斯基眼中的克拉科夫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外来者,他带着兴奋与羞涩漫游在克拉科夫,恢弘的历史以及初到者的仰慕之情,都渗入到真实的目光和感知中而显得更加鲜活。而这,恐怕也是作为一名游客所无法感受到的最为真实的克拉科夫。
[译者简介]独孤晶,上海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2007-2008年任教于泰国宋卡王子大学普吉岛分校,2013年旅居德国,现居上海。译著有《红魔的假面舞会》(爱伦?坡),《无法触碰的爱》(纳撒尼尔?拉胥梅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