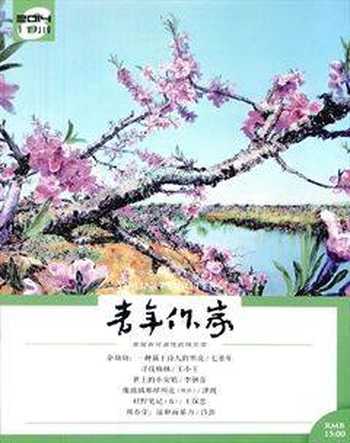余幼幼 一种属于诗人的明亮
在众多的年轻诗人当中,余幼幼无疑是特立独行的。在《星星》《诗刊》《天涯》等一系列纯文学刊物上,她的名字已然不陌生,然而直到去年赴北京参加全国青创会的时候才见到她本人。个子小小的,实在有点难以想象那些辨识度极强的诗是怎样从这个娇小的姑娘身上绽放出来的。我难以忘记那一次随意的聊天,她对我说起她去贵州乡下见到的种种趣闻轶事,她说着,眼睛明亮,语言也很明亮,那是属于诗人的明亮。
——采访手记
七堇年: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
余幼幼:我从2004年开始写诗,那会儿上初二,成绩还可以,上课也不怎么听讲,经常听着听着思想就走远了、跑偏了。我一般都是桌上放当堂课的教科书,下面放着另外的书,一边要假装自己很认真听课,一边又在看其他的东西,经常搞得自己神经紧绷,有点小刺激。其实这种精神高度紧张的情况下特能激发灵感,有时候突然被某个点刺激了,就赶紧在教科书上写下来,扮成在做笔记的样子,我也被老师逮过很多次,反正死性不改,他们也拿我没办法。回家以后整理那些碎片,忽然感觉,咦,怎么特像诗歌。估计我的语感就是那个时候慢慢训练出来的。那会儿我才十四岁,什么也不懂,不知道怎么写是好怎么写是差,我就凭着直觉去写,直到现在都觉得写诗我的直觉大于其他。也许是由于年龄小,我的好奇心和对世界的探索欲望很重,喜欢涉足和尝试未知,喜欢陌生化、反传统的表达方式,虽然是个标准的魔蝎女,但特别反感俗套和旧式的抒写形式,于是我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写,爱咋咋爱谁谁,反正也没人看。但是我从来不硬写,硬写不但写不出好诗,而且还是一种自损。写诗还是自然而然的好,就像遇见一个喜欢的人,诗歌也是一样,讲求缘分,是你的就是你的,强求不来。
七堇年:就文学类型来说,为什么你最倾向于用诗歌,而不是以小说、散文等形式来进行表达?
余幼幼:其实我最早写的就是散文,小说一直写得少,因为思维跳跃得有时候连我自己都驾驭不了,很难去布局写个故事什么的,写过好多次小说,中途都放弃了,反正写小说我有几个字形容就是:憋屈、痛苦、难受。不过最近我写了个《即兴表演》那种瞎扯淡的,没什么结构的小故事,把自己给写嗨了,好多人读了也觉得挺嗨。通过这事儿我也自我总结了一下,结论是:还是写诗吧!目前,小说注定是写不出能称之为“作品”的东西出来了,不过话也不能说死了,将来人老迟钝,思维跳不起来了,没准就能写了,诗人写小说可有天生的语言优势。散文虽然写得没有诗歌多,但也一直没丢,大三到大四的时候写了个《迷失在九州大道》的四万多字的随笔,想的是给马上结束的大学生活留下一点东西,算是把我精、氣、神都掏空了,没想到反响还不错。不过我最钟爱的表达还是诗,就像电路串联似的,线路搭对了,灯才能亮,我觉得我写诗就是属于文字和交感神经搭对了吧,脑子和心里都特亮堂、特通透,说白了就是爽歪歪。那种感觉就好像诗歌跟我通了灵,触电一样,再拿刚刚喜欢一个人来比喻,就是看对眼儿了,怎么着都觉得舒服。
七堇年:写作对于你现在来说意味着什么?
余幼幼:写作真的是一个“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但我还是想让它伴随我越长越好。如果我有能力让我的作品留在这个世上,并且可以超越时空,那最好不过。我以前一直觉得能写就写,写不了就拉倒,看得挺开的。但现在越来越觉得,我真的是“拿得起,放不下”,如果哪天让我不写了,我还真的会不知所措。如果没有写作,我想我还是我,只是不是现在的我,也许是另一个我,我觉得现在的我挺好,没什么贪念,也不崇拜金钱和物质,这些都是写作让我慢慢养成的秉性,喜欢自然澄澈的东西,喜欢自由简单的生活,不会被世俗的一些浮夸的欲望和肤浅追求所拖累。写作让我保持了自己的风格,不容易被外界所侵蚀,我独成一个世界,我有我自己的主张和观点,我看透或者看不透都无关乎其他对我的影响,人其实想保持纯粹是很难的,我一直在努力做到这一点,写作帮了我很大的忙。
七堇年:听说你之前也有过一段上班族的生活,对于这种生活,你有什么感想?
余幼幼:嗯,我刚好上了一年班。感想是,如果当成一种生存手段的话简直不是用悲催二字就可以形容的。工资付了房租几乎所剩无几,还要吃饭坐车买书,养活自己真的不太容易,有段时间特别自弃,感觉自个儿特没出息,这种状况维持了半年,然后找单位把住宿解决了,情况要好一点,不过依旧穷得掉渣。我朋友开我玩笑说:“你当个穷人还不够,还要当个喜欢思考的穷人,你觉得这两个哪个听起来更搞笑?”好在我自嘲已经养成习惯,别人怎么讲我都当给自嘲添加素材,无所谓了。如果是当成一种经历的话那还是挺值得回味一下的,甭管好坏,对你的人生都是一种充盈和丰富。只要饿不死,一切都还有余地。不过上班确实很磨损人,一天打三次卡,就如同一天杀三次头,感觉是对于人身自由的无形监控,有点受不了。值得欣慰的是,我的工作单位环境还是比较单纯,不用花费精力处理人际关系。由于工作原因还完成了我一份小小心愿,创办了“52赫兹诗歌网”,专门针对大学生诗人开设的网络诗歌平台,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有更多热爱诗歌的青年人能够发表自己的作品和文学创作言论。由于诸多客观因素,网站建成后的运营比想象中艰难,为了诗歌我坚持了一年,有点疲倦和无奈。接下来对于自己的未来我会重新考虑,但我还是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我不喜欢上班——也许这就是一个决定。
七堇年:也许难免会被贴上“90后诗人”这样带有前缀的标签,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么?
余幼幼:这个标签其实一直存在,不是偶然,也并非难免。说实在的,我觉得这种划分除了方便历史向度的研究外,好像年龄越小越受益。写得好别人评价你天赋异禀,写得不好也没关系,反正还小嘛。其实这是带有功利性的,我不敢说我没有从中受益,但我尽量避免标签大过了我的诗歌本身,首先我是诗人,哪一年出生是自己没法决定的,是诗人就写诗,把诗写好就行了。对待标签我的态度是你们随意我自嗨,我的目的不是要去获得某个标签上的认可和成立,而是写出自己想写的东西。对于那些大张旗鼓宣称反对被划分或者被归类的人其实挺没意思的,标签会妨碍你写作吗?会让你变质吗?既然不能,那管它干嘛。好好写自己的东西不就完了,耗费精力去反对,其实不就是想获得另一方面的认同吗?写作的人就是拿作品说话,拿不出作品的人才需要搞些别人看得见的东西来撑门面。
七堇年:有最喜欢的诗人吗?
余幼幼:加个“最”字让我有点为难,不同的创作阶段喜欢读的东西不太一样,不过我更喜欢读诗以外的东西。好像是因为缺啥补啥吧,我比较喜欢看小说和一些内心深处的独白,自言自语的那种。要说几个比较喜欢的诗人的话,最早很喜欢保罗?策兰,喜欢他那种忧伤自抑而又充满爆发的语言,主要是喜欢他诗中那些象征意味浓重的修饰。前阵子很喜欢贝恩,一个怪诞的医生兼诗人,他写了很多关于诊所、病人这样意象的诗歌,读来十分受震撼。墨西哥的诗人帕斯,一直很吸引我,他关于诗歌理的论也非常精辟。辛波斯卡、阿多尼斯、海子、普拉斯、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都还很值得一读。不过我现在更喜欢表达简练、精准、一针见血的东西,不太喜欢打磨得过于光滑的诗歌,粗糙一点读来更有味道。有时候我还会看一些民谣和摇滚的歌词,好的歌词都是诗,这个要说到诗人兼歌手科恩,简直太有魅力了。
七堇年:写诗之余喜欢做什么?
余幼幼:不写诗的时候喜欢发呆,别人看来有点儿浪费时间,但我觉得挺好,让自己静下来,用心来呼吸,啥也不想,把脑子放空,有时候我坐着发呆不知不觉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然后就是旅行,旅行也是换个地方发呆,不过那种发呆的感觉是新鲜的。喜欢大自然,喜欢脱离人群的味道的地方,去看看山水,随意地走,让人轻松愉悦。
七堇年:你喜欢和同为写作者的朋友圈子交往吗?
余幼幼:随着写作时间的增加,好像认识的人也多了起来,除了几个习气相投的人偶尔联系一下,其他人几乎都不怎么来往。经常在一起的朋友几乎都不写作,在一起弹吉他唱歌,聊聊有趣的事儿,感觉都比几个人凑在一起聊文学要放松自由得多,毕竟写作是很自我和私人的事儿,聊也聊不出个所以然。
七堇年:推荐一些你喜欢的书?
余幼幼:帕斯《诗与思的激情对话》、伍迪艾伦《门萨的娼妓》、曹乃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索甲仁波切《西藏生死书》、三岛由纪夫《潮骚》、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七堇年:最后问一个很老套的问题:你为什么写诗?
余幼幼:我為什么写诗跟我为什么吃饭睡觉其实是一样的。多做一些不为什么的事儿其实并不坏,这样更从容更心无旁骛。写诗已经成为我的一种本能,本能的东西也就是你没办法克制也没办法改变的。我无法回答我为什么写诗这个问题,只能回答我为什么不写诗,那大概就是因为我的生命终结了吧。我对诗歌的热爱也许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如若这是一种偏执,那我宁愿为此疯狂。
[作者简介]七堇年,本名赵勤,女,1986年出生于四川泸州;2006年,她在二十岁的时候写下第一部长篇小说《大地之灯》;曾获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