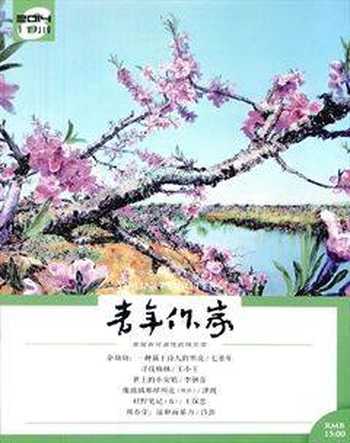世上的小安娘

[一]
这世上千千万万的人里面,小安娘是倒霉的那一个。
哏——,她终于在长途车的座位上安顿好自己,粗重地喘一口气。客车夹在车流里,忽畅忽堵地出了城。穿过棋谱一样的外环线,驶上高速路。
小安娘又吁一口气。她用脚跟磕一下塞进凳底的鼓胀的包裹,两手放在腹前。
“打货啊?”身边胡子拉碴的男人问她。他见她大包小包地拖上车来,脸红涨着,汗湿的头发粘在两鬓。
她抬起眼皮睃他一下,不搭腔。她的心事重着呢,谁也打捞不起来。
她的男人,跟别的女人跑了。跑远一些也好,偏偏只从河边跑到山脚,出门冷不丁就遇上,这就让她在村里抬不起头。年轻时,她还是有一番挑选的,她的标准有两条,一是牙齿要白,说笑时不能露出黑黄,一辈子在眼前晃,惹人窝心;二是要有文化,能把道理说出子丑寅卯来,跟他过日子不吃亏。这两点他都有。虽说他家在山顶的那个村,比她家境况差,她还是嫁了他,接连生下三个孩子,像一头牛一样干活。黑亮的头发毛了,丰润的脸腮陷了,灵巧的手指粗了,说话的声音嘎了,原等着再过几年就当婆婆,他倒给别人的两个孩子当爹去了。
她的妈呢,这一生就不像个女人,就好那两口酒。牙缝里抠出一点钱来,立马换了黄汤灌下去。她把几十年本该平顺的日子都灌进肚子,剩下那么多争吵、厌恨和苦痛给她们姊妹。小安娘和姐姐,从小就包揽了家务和农活。夜晚,她们躺在黑黢黢的屋檐下,听猪在圈里拱槽,一遍遍恨恨地想,只要一长大,就离开这个家,头也不回。
爹先走了,走的时候眉头锁成一个深深的川字,刀刻斧凿一般。小安娘看着请来的端公给他擦身,想伸手去把那个川字抚平,但她不敢。姐姐终于先长大,嫁得远远的,轻易不回来。这几年见田土值钱,生了懊悔,觉得小安娘守着老母亲是占了便宜。只要小安娘出门打工,姐的电话就阴魂一样追来,翻来覆去说,你倒好,妈的田土一份钱,外面一份钱,把妈丢在家里。妈年纪一大把,磕着碰着咋办?好似她最有孝道。
大儿子照照,答应了要读到高中的,可是初中才毕业,就跑到城里找她。小安娘正在人家做保姆,照照来了,眉头也有一个川字,细长的眼里两个褐色的恹恹的眼珠,像他外公,日子还没开始就活够了一般。他在人家客厅的沙发上睡了两天,小安娘觉得屋子里的空气拧扭着,要绞出水来,忍心将他支走了。照照还算有运气,在一家发廊做了学徒。过一阵二儿子耀耀也来,打啊捶的也不走,跟他哥都进了发廊。有一天耀耀的电话打来,说照照把他的头打破了。小安娘急忙穿过半个城,赶到他们租下的房子里。那不是房子,是一个批发市场的楼梯脚搭成的小窝,用预制板围着,月租50元,开门就是床。两兄弟挤一张床,挤着挤着便开打。耀耀的头真破了,缠着纱布依旧渗出血来。
一棵秧苗一滴露水,照照来到这世上,自有他的运道。他在城里的发廊学了不到一年,向小安娘要了钱,带上耀耀回到县城,租下铺面开发廊。第一个月净挣五百多,第二个月一结账,小安娘听了也唬一跳,居然有四千多。两兄弟又打了一架,这次是为了分钱,照照一个大拇指的指甲,被耀耀劈了。他们哥俩,像庄稼拔节,每长一程都用打架来总结,又才有个新開始。
是庄稼倒好了,不声不响地在地里发芽、开花、结果、收割,走完它在世上的途程。照照不过19岁,在县城里和湖南来做批发的小美相好,小美很快怀上了孩子。小美的电话又打到小安娘新换的阿姨家里。阿姨一家在看电视,是星光大道,正守着一人憋出常人不及的高音来,电话一响,一家人都皱眉头。小安娘赶紧躲进厨房,听小美在那头泼水一样地哭:你管不管你家儿子?你不管,我去喊公安局来管!小美豁出去时,像乡野里几个孩子的娘。小安娘急忙拨通照照的电话,压低嗓门骂他:你爹只管生不管养,才出了你们这样没有素质的兄弟。你也去东生一个、西生一个,将来都没有素质,你做人有什么想头?
孩子生了下来,照照和小美也结婚了。小美的哭诉电话,依旧打来,总是那句话:你管不管你家儿子?小美的日子浅,心也小,装不下那么多怨愤,积一点就要往外倒。照照从早到晚在发廊,好不容易回家,坐在电脑跟前就不挪屁股,娃娃哭哑了嗓子也不管。小美自己呢,自从有了这个娃娃,就被捆在家里了,没有烫过一次头发,没有出去旅游过一次,没有唱过一次卡拉OK。小安娘说:小美,你是个女人,这就是女人的命嘛。小美道:这是你的命哈,不是我的命!小安娘也火了:那咋办,你跟他离婚,又去找一个?再找一个,你给不给人家生娃娃?给不给人家养娃娃?
高速路把沿途的风物和城镇都掠开,把原先悠悠的日升月落也掠开,在单调的车轮和路面的摩擦声中,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地向前。日月和风景,人都是可以不顾的,可是,人在这世上,是个远行客,一路上能挑拣的、无法挑拣的,背了重重的一个包裹,却是丢不掉了。
[二]
小安娘的眼皮重了,犯了困,但她不敢睡着,担心错过了站。阿姨家淘汰的东西,她足足收捡了两天,每一样搬回她那空落落的屋里,都能排上用场。里面还有两只玩具熊,洗衣机里转过了,毛茸茸的,小美的女儿也用得上。小安娘昏沉的脑子里闪过了这些,并没有高兴起来。
车窗外壁立的大山变成了丘陵,深深浅浅的山包,铺展在天宇下,像粗心的天神丢弃的一屉馒头,荆棘和杂树是它们长出的毛。它们亿万年地伫立,春绿秋黄,注视又承载了一切。但小安娘是这世上一个倒霉的人啊,她的苦处,也亿万年都诉不完了。
这是快到她的凤池村了。小安娘脸上经年的焦愁,也愈加深了,嘴角撇下去,眼色沉沉的,额头眉角的细纹里,埋着擦不净的怨艾。阿姨的女儿不过三十出头,在家里做全职太太,她那个当经理的丈夫说,现在这个世界,中年女人就不要出去混了。小安娘40多岁,照样在外面打工。这个世界,可以不要她,她的那些烦难和伤心,却紧紧地抓住她,一天也是甩不掉的。
终于,小安娘背着扛着提着,摇摇晃晃地走在了通往村子的水泥路上。她早把斜挎的小皮包塞进了背囊里,若给人瞧见了,会说:哎哟,以为挣了好大一包钱回来哟,还不是去给人家当保姆?
小路和一条小河随行,穿过大片的稻田。有的人家已经收完了谷子,土地像被剃了头,她家的谷子还站着,等着她回来收。
他还没裹上那女人的时候, 在家里也是悠哉游哉地十几年,动不动便丢下一句,猫场的蒋家要打官司,叫我去写状纸,一去就是好几天。那时候,遇上大小事情,打过了吵过了,她好歹还有个人来断后。现在呢,她退无可退、靠无可靠,终归要硬着头皮自己迎上去。这一次回家,除了收谷子,房子也漏水了,需找人来修。妈喝醉了跌一跤,手腕断了。小美在电话那头威胁了几次,说再不回来帮着带孙女,哪天她就丢下孩子跑得远远的,反正都是照照的种。三女儿阳阳的班主任打来电话,说要开家长会。阳阳的成绩好,学校准备培养她考县里的重点高中,已经替她联系好了,插班到一个好学校的初三去,也等小安娘回来商量。小安娘在电话里气冲冲地对阳阳道:你那个爹呢?法律上说的,他也要出一半的钱!阳阳说: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没有钱。小安娘气得泪花都要溅出来:他没有钱,他就有一根骚鞭子,胡子一大把了还要跑人家屋里去!这么说着,她心底的积怨并没有分毫减轻,又添了懊悔,不该对14岁的阳阳说这些话。可是,她实在不懂,村里的人也说,他们也不懂,他丢下她和照照兄妹去那个女人家,那个女人是个闷葫芦,并不比小安娘年轻漂亮,丈夫死了,还拖着两个娃娃,不知他到底图什么。
风夹着稻香,轻轻挠人的脸。一只鹭鸶低贴着河面飞过,收了白色的翅膀,亭亭地单脚立在石上。远山从葱绿到青黛,间杂着花朵一样的金黄或酡红。这片山间的田野,忽一看,是偏远而落寞的,只有二十来栋高矮新旧的房屋,倚在河边山前,面对着世代耕作的田畴。其实,它四季里都是充盈的,有数不清的生命活动。
但是人的心,常常走在自己的一个甬道里,甬道黑咕隆咚的,看不见这些山色水波。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小安娘的心,就总是阴云密布着,难得放晴。她的肩疼了、手酸了,包带深深地勒进手掌。又坚持了几步,腿弯微颤起来,她就把包袱堆叠在路边,直起腰来,稍稍歇一下。
去年春节她回来,妈坐在火炉边,老眼迷迷瞪瞪的,身子像钟摆摇晃。小安娘发现烟管的一处缝隙漏烟油,一滴一滴的,妈的后背也染花了。这烟油洗不净,一件衣服就糟蹋了。小安娘正忙着拆烟管,呛得眼泪鼻涕的,姐来看妈。她袖着两手在门边嘀咕说,妈眼见老糊涂了,这回是烟油滴在背上,下回只怕烟管砸在头上,也无人照管。小安娘知道姐后面的话,她火了,将烟管“咚”一下擂地,嘎着声音说,对妈,各尽各的孝道,你平时只会蹲在窝里孵蛋,还知道烟管在哪?这个家就剩一老一小,就没有你一点事?姐的前半辈子,只想着离家远走,后半辈子,只想着自己没有分到田土吃亏了,她的眉心也有一个川字。
姐长得像爹。人说女儿像爹有福,但至今看不出她的福气在哪里。她的男人好赌,一个家几十年中打得鸡飞狗跳。一双儿女都在外面打工,留下三个孙子给她带着,大孙子整天泡在网吧里,听说有一回昏死在电脑前了。姐的日子不好,脸上堆着积怨,眼睛看人的时候,带一种不耐烦和挑衅,仿佛有什么永远在后面追赶她,她跑到绝路了,倏一下转过身来,防御而反击的表情。
她们姐妹一人一句,有来有往地斗嘴。妈坐在一边张着嘴看她们,摇啊摇的,她那是酒精中毒了。
一辆摩托从小路那头开过来,突突声撞开了清冽的空气。近了,小安娘认出是张家老二。一年多不见,他染了黄头发,刺猬般立着,夹克上印着骷髅头,脚下的运动鞋一片银光。
张家老二潇洒地一腿支地,停下车道:“小安娘,回来了?这么多东西,发财了哈。要不要我帮你驮回家?”
“不要不要,拿得动。老二,你这是去哪里?”
小安娘本来是不愿见人的。离婚以后,她看谁的眼睛,都能看出别人在笑她。从那些眼睛里,她也看到了自己,一个被男人甩掉的四十几岁的女人,像鲜菜叶在坛子里腌过,连她的无辜都可以忽略。她好强,装作毫不在乎,但再怎样撑持,别人还是同情地看她。
张家老二的眼睛却很清亮,像河水,被奇怪的黄头发映衬着,有小安娘陌生的东西。他向山边一努嘴道:“去镇上买个耳麦。那我走了!”
小安娘没听清他去买什么,也不及问,见他的摩托又突突地开走。他总是满世界地跑,今年去上海,明年去深圳,人没法把那个小时候吊两条鼻涕虫的娃娃跟现在关联。他们是这村里的新人了,像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吹到天南海北去,若不是秋收农忙,影子都找不到。
小安娘收回眼光,呆呆地看河边的一蓬芦苇,觉得身上的汗落下了一些。其实,她什么都没有看见,只看见自己的苦命,它像一块糍粑粘着她的心,蒙着她的眼。
[三]
阳阳继续读书,小安娘倒是愿意的。虽然是个姑娘,一家人只有阳阳是读书种子。学费呢,小安娘再省一点,也可以拿出来,反正交了养老保险,吃穿都在别人家里,阿姨和她女儿淘汰的衣服,自己一辈子也穿不完。阿姨还说过,城市里难找她这样又诚实又有道德的人。若是小安娘愿意给他们养老送终,除了每月的工资,待他们老夫妻百年以后,房子卖了,可以给她一半的钱,现在就能签下合同。阿姨家那点活,洗衣服有洗衣机,买菜做饭有电磁炉、煤气灶和冰箱,每年陪他们去住医院,如同疗养,龙头一拧就有热水,卫生间就在病床边,虽然把人的腿脚给捆住了,难得的是清闲。
但是,小安娘终归就是个不甘心。
当年,他算是倒插门的女婿。他家山上的那个家,穷得叮当响,跟她谈恋爱的时候,一条咔叽裤子都是跟别人借的。到了她家十幾年,田土里的活,想不做就不做,反正老婆抵得上一个壮劳力。一日三餐的饭菜,哪一餐不是端到他眼皮底下?他只管床上的事情,娃娃生下来了,他就是那一句:找你们的妈去。别人说,小安娘会嫁哦,嫁了个白面书生,像白娘子嫁许仙。她总是苦笑作答:我不是嫁了个许仙,我是家里多了个幺儿,你要把他抬着哄着!
她就是愿意把他抬举着,这世上有钱难买愿意。她见人就埋怨他,说他是家里的老四,其实她心底是认命的。她和这四邻八乡的大多数女人一样,趁开花开朵的时候嫁了人,也就是嫁了一个命,往后,就守着这命过日子。她的肚子鼓起来,又瘪了,从早到晚被孩子和活计填满,上床就起了鼾声,常常记不住是哪年哪月哪日。
但是,她的男人,还是跟别人的男人不一样的。他的牙齿白,身条清瘦。她卖掉一头猪,送他去县里参加过法律培训班,回来就能替人写状纸,有了些声名。她跟别的女人一道骂男人,笑过骂过了,心里还是有安慰,她想,她们都不懂他有一样好,脾气好,从来不打她。被她说急了,要么扭头走开,要么倚在门上,低头垂脑地听她一边干活一边数落,将东西摔摔打打。有时候,话戳到了他心里,他抬起头来,急急地辩白,长长的眼睛上面两道凹影。他在外面也算能说会道,一板一眼的,什么合同啊、条款啊、股份啊、上诉啊、程序啊,听他说这些,她就很满足。这是她找的男人,自有一堆落落大套的说辞,把这世上混乱不清的来龙去脉讲明白。
但是在家里,他不是她的对手,因为他不占理。田土是她家的,里里外外的活是她做的,就凭这两点,他的理,就大不到哪里去。
发现他跟那个女人好,小安娘的天都要塌了。她哭啊、喊啊、闹啊,到那女人家砸东西。两个男人一左一右地架住她,她还是勾腰低头,像一头斗牛俯冲过去,把那女人撞个仰八叉。她还要寻死,举头向墙上撞。那两个男人领教了她的力气,脸红筋涨地死命拽她。她那是心碎了啊,碎了的心像碎了的玻璃,扎得她从里到外、脚趾发梢都在痛。
她痛得四肢没有了力气,滚在地上,呕吐一样地嚎哭。
他站在那里,冰冷地说,你们等她闹,要闹就闹个够。
她听进耳朵里,受了激,反跳起来,又向他身上扑:“你狼心狗肺!知法犯法,你罪加一等,我要去告你!”
他倒伶牙俐齿起来:“好笑,我有什么罪?第一,从今天开始,我就起诉跟你离婚。第二,你说我和她好,你有什么证据?既没有白纸黑字,也没有捉奸在床。第三,我没有违反婚姻法,不是重婚罪,你说我罪加一等,你是法官啊?既然不是,你说的这些就等于屁话。”
她有些发呆地听他朗朗说着,四肢又痛得发软。原来他的那些词像刀子,是可以要人的命。
这个她在人前把他叫做老四的男人,她把命给他,他也不要了。她的命,被他丢在这个村子里,丢在田土、灶台、猪圈边,就连她的妈和三个孩子,也变成了他丢给她的。她去城里当保姆,原本是想躲开这个被他丢掉不要的命,只要还在村里,这命就像她的影子,太阳下月亮下都悄悄跟着。
到城里,她什么都做,在商场里收纸箱,在新修的楼房外守着装修材料和家具上电梯,在菜场帮人家背菜送货。现在,她在阿姨家安顿了。她脚下这双皮鞋,是阿姨的女儿给的,还是一种世界名牌,鞋跟太高,她找鞋匠给锯掉一半。阿姨说女儿是购物狂,阿姨自己也爱买,还说购物是女人的天生特权。人家的天生特权是购物,小安娘的天生特权是拖着这个破碎了的家。不管怎样,小安娘在阿姨家住一段时间,就能带回几个鼓鼓囊囊的包裹,阳阳再长一两年,春夏秋冬的衣服都不缺了。
她在阿姨家的日子,是这一生最轻松的日子。晚上,洗好了碗筷,她打着毛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剧。开始的时候她爱哭,电视里的人流眼泪,她就用袖子擦眼睛。后来她不哭了,还跟着阿姨他们议论几句。阿姨说,小安娘是聪明人,如果读了书,就更不得了。
阿姨还给她介绍过男人,是从乡下去广州给工厂看大门的,老婆死了两年。那个男人倒好笑,第一次打电话到阿姨家,张口就道:“哦,你是小潘啊,你愿不愿意和我结婚啊?”电话里除了他的声音,还有一辆货车驶过去,隆隆的。连她姓潘姓安都没弄清楚,就要结婚。阿姨一家笑得喷饭。小安娘说,她不找男人,找来一个,不知对她的三个娃娃好不好。她是笑着说的,心口却划拉一下地疼。
村庄总是这样安静。房屋原本像河滩的石头,日子像水流,终日有哗哗的水响,但是现在,这日子变了。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成年的都出外打工去了,即便回来,也忙慌慌的,走路和见面的招呼都像城里人。小安娘进村的一路,再也没有遇上谁,她这样倒霉的女人,谁也不见的好。
终于,她拖着大小包裹,进了她大山里的凤池村。
[四]
巷道的上方是一溜天空,一只鹰缓缓地滑过去。它不知从哪里来,如果它低头一看,看见的,一定是这群山里的村庄。屋舍排在青绿的山边,面对着铺展在阳光下的大片稻黄。
走在巷道里的小安娘,被身上的包裹压得有些趔趄,皮鞋崴着。她心里叹着气,真是这世上万千的人里面一个倒霉的女人,她的苦,即便说得出来,即便有人听了,也是乱风中的一缕,消散在这千沟万壑的大地上。
多亏是午后,村里见不到人。小安娘进了屋,喊妈和阳阳,没有人应她。
她推门到西屋,见妈侧身冲墙躺着,呼吸又粗又重。妈的一只手腕上了石膏,用纱布吊在脖子上,纱布上黄斑点点,想是有一阵了。小安娘返身出来,四处转一圈。灶台上的锅碗没有洗。鸡笼上压着石板,粪便斑驳。墙角和门框上都积了蛛网,蜘蛛养得硬币那么大。晒好的辣椒就堆在院里的簸箕上,沾了灰。她在条凳上坐了片刻,喘匀了气,又去水缸里舀一勺水喝了,恢复了力气,这就脚不沾地忙开来。
太阳光柔暖了下来,妈醒了。小安娘给她穿上衣服,扶她到院里晒太阳,一边从各屋抱出铺笼帐被来,埋下头洗。妈摇啊摇的,问她十句话,九句用摇晃来回答。阳阳和她一老一小在家,两人也不会有话。
洗到天黑,估计阳阳快回来了,小安娘便去做饭。菜是现成的,都是早晨临走时阿姨塞进包里的东西,还有几个八宝饭罐头,说保质期还有一阵,放心吃。灶台边油、盐都有,墙角斜靠着一袋剪开的味精,比起阿姨家的厨房,很萧条了。阿姨家的调味酱是满满的一冰箱,沙拉、番茄酱、黑白胡椒、咖喱,她至今也不会用。这么一想,她这一天的心思才落到了阳阳身上。陽阳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她不过14岁,天不亮,一村的人都睡着,她就去打猪草。回来喂了猪,把外婆和自己的早饭中饭都做了,才去上学。镇中学离村子有八里地,她带着午饭每天走一个来回,披星戴月的。回到家,放下书包就做晚饭,收好了碗筷,又赶紧做作业,成绩还是班上的一二名。小安娘对阿姨说起阳阳,阿姨扬着眉、张着嘴,只说简直不相信。阿姨的孙女15岁,一家人说她是青春期,今天和她爸爸吵架,明天喜欢同桌的男生,道理一套一套的,没人能说过她。但她不会洗自己的袜子和内衣。她妈念叨她,她就说,我每天除了这么多功课,还要思考人类和宇宙的问题、思考到底是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不会洗袜子有什么关系,将来结了婚,不就会洗了?
阳阳是自己的女儿,她的成绩好,小安娘是高兴的。其他的,她倒没有余闲多想。这山间的姑娘,大多是这样长大的。假如阳阳成绩不好,小安娘更难得想她了。自己这份日子,就有多少的心烦意乱。
比如阳阳去县里上学,就有一道关,是去找她的校长签字盖章。镇中学的校长陈炳德,二十年前还是一个民办教师,剪一个瓦片头,穿一双反毛皮鞋,裤管翘在脚踝处。小安娘和村里的姐妹去他那个村子走亲戚,认识了他。他把她们请到他的宿舍里,给她们用普通话读诗。他的普通话让她们想笑,嘴角抿得发酸,脸憋得通红。但是,诗是一种让人不敢笑的东西,她们就生生地忍着。她发现,陈炳德看自己的时候,眼睛深处一闪一闪地亮,但她不喜欢他。他的牙齿是黄的,肩膀肉肉的,削下去,不像个男子。
后来有一天,她去镇里赶集,遇见了他。他找各种话跟她说,又随着她在田垄里走了很久。那天正是油菜花铺天盖地的时候,酽稠的花香熏得人昏昏欲睡。陈炳德从挎包里掏出一个本子,说他写了一首诗,请她提意见。那诗说,你是一朵阴云,我是一朵阳云,我们在天空相遇,洒下爱的甘霖。她分不清“霖”字读“雨”还是“林”,藏了拙,只笑不说话。她肩头的扁担挑了两只箩筐,他靠不近她,只得忽前忽后地围着她走。后来,他们在岔道上分手。他有点不舍的样子,咬了嘴,几分委屈地看着她走远了。
这些年,她很少想到陈炳德。偶尔有人提起他,她记得的只是他的那双反毛皮鞋,粘着泥土,走路时鞋带在脚面上一搭一搭的,在她的前后左右迈动。但是去年,她忽然接了一个电话,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叫她的名字,安启菊。她疑惑了,又警觉着,硬邦邦地问他是谁。他竟然说:“你猜。”她没好气道:“我没有闲心猜。你不说,我就挂电话了。”他连忙说:“我是陈炳德嘛。连我都记不得了,你不是贵人多忘事吧?”她是聪明人,知道他二十年后又冒头来联系,是想让她安启菊知道,他陈炳德当了校长。当初她看不上他,那是做了一件无法追悔的蠢事。总之,他找她不是叙旧或调情。这世上有的女人,一辈子想讨男人喜欢,她小安娘不是那样的人。她也像庄稼,开了花结了果,懂得自己的凋零,只想更深地把根须扎在土里,然后听天由命。所以,她心里倒是爽利的,跟他有板有眼、一本正经地说话,明知他是阳阳的校长,也没有一句半句的讨好。但现在,她不得不为了阳阳去找他了,她要小心地笑着,为自己当初看不上他显出一点懊悔……唉,也不知会是怎样的情形。
这世上的感情,也像天空里的阴晴,太阳照过了,雷雨下过了,终将过去吧。她这样一个女人,还期待什么感情呢?只要一份安稳都是难的。
天黑透了,阳阳也回来了。
[五]
阳阳在她身后,叫一声“妈”。声音平静得好像母女天天相见,倒让小安娘奇怪。
阳阳因为赶长路,青白的脸上起了两团绯红,眼光灼灼的,鼻头渗出了汗。她似乎长高了一点,又似乎没有。
见小安娘回身看她。阳阳笑一笑,取下书包放好。端起灶上的菜,又去找碗筷,问道:“今天的车好坐不?”小安娘说:“再好坐,还不是抹黑就起床?我就是这个命,忙完了这头忙那头,哪天两脚一蹬,就不忙了。”
阳阳怔一下,无话了,进到堂屋里摆晚饭。
夜凉从敞开的门外渗进来,带着无边无涯的昼夜轮转的气息,还有草木褪掉燥热后的清凉。她们老少三代女人,隔了很久,终于又坐在堂屋的一盏吊灯下吃饭。这个家的男人们都跑了,但是跑出了门,跑不出她们的心。
小安娘问:“你大哥他们现在也挣钱了,就没有回来给你半分一毛的?
阳阳摇摇头,只顾专心吃饭。
小安娘又着恼:“这两个白眼狼啊!自己的亲妹妹,又要读书,又要管外婆,还要守家。他们就在镇上,也这样不管不顾,我白养他们一场。我这个命,咋这样苦!”她罩在灯影下,额头的皱纹分明地现出来。话声像爆竹的余响,干裂得充斥了一个屋子,可她不知道。
阳阳低着头,头顶的发缕被乱风揉过了。在这个家里,她一直没有长到可以说话的时候,但是今天,她坐在灯下,脸上不再是木木的,有了一种新鲜的生气。她抬起眼睛,平直地看着小安娘,开口说:“他们没有义务要给我钱。再说,他们才刚刚好起来,也不容易。”
她的神情,像她的爸爸。小安娘心底那一层层掩藏的痛,又泛了上来,她几乎没去想阳阳的话,自顧恨声道:“你那个爹!这次你的事情,他咋说的?”
阳阳等了一会,好像要等小安娘话里的烟火散尽,才说:“他的确没有钱。那家的老二,听说查出来是心脏病,要花一大笔钱,他们也没有。”
“他们!”小安娘把手里的碗在膝头一顿:“他们也是人?报应啊,这是报应!”
阳阳不吱声了。妈在一边摇啊摇,像钟摆,直摇到更深漏尽。
“妈。”阳阳仍是平直地看她:“你们已经这样了。你再恨,伤的还不是你自己?有人研究出来,人生气的时候,会排出一种毒气,这种毒气连小白鼠都会毒死。你每天都在生气,对你很不好的。”
小安娘听了,有些惊诧,又有些震动,终于认真地看向阳阳。她撇一下嘴,又气又笑起来:“照你这样说,那些伤天害理的人,倒活得好好的,我们被人家欺负了,还要放毒气把自己毒死?这世上也太没有王法了嘛!”
阳阳竟是胸有成竹,她把外婆手上的空碗放在桌上,抚去她掉在襟前的饭粒,说:“其实,说来说去,别人不是都错,你也不是都对,因为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有原因的。你天天觉得自己被欺负了,天天一肚子的气,唉声叹气地过日子,那你就是傻子。”
小安娘愣了。这是阳阳第一次跟她这样说话。她瞪眼看着她,她还是长高了一点。上次回来,她的这件运动衣的下摆是在腿上的,这次向上挪了。“你这是小鸡教训老母鸡啊,唵?你在这周围看一看,还有哪一个比你妈更苦,更受人欺负的?你那个爹,当年一条好裤子都没有,就到我们家来了。不说他这些年吃的用的,都靠我这双手辛辛苦苦从地里刨出来,就说你们兄妹,他是抱过呢还是管过呢?上次照照租门面,还是我拿的钱。我,他可以不管,拍屁股就走人,照照好歹还跟他姓,是他家的种……”
“妈。”阳阳打断她。她不过刚长大,不知哪里学来的心平气和的样子:“你这些话,我从小就听到大。人活在世界上,谁会没有苦,没有委屈呢?都像你这样恨一辈子、气一辈子,那人生出来就是专门受苦了?又何必生出来呢?”
她看向小安娘,眼睛里有一种询问,安静地等她回答。
小安娘被她的话牵着,脑子里一团迷茫,不知该怎么想、怎么说了。顿一下,她又习惯地恢复了经年的忿忿:“人又不是自己想生出来就生出来的!再说,比我们过得好的人满世界都是。我当年要是不嫁你那个爹,未必是这样的命。”
阳阳垂下眼皮,思虑了一下,才抬眼看她:“妈,当年嫁给他,也是你自己愿意的,又没有人逼你。你嫁他,是嫁错了,他娶你呢,就娶对了?如果娶对了,他为什么要走呢?
小安娘“啪”的一下拍响桌子,一根指头指向阳阳的鼻子:“我看你还翻天了?读了几天书,教训起老娘来了。你向着你那个爹,有本事去找他要钱给你读书啊!”
她声色俱厉,心里却有些发呆。阳阳的说法,她倒是第一次听见。这么多年,她让他过得不比村里的哪个男人差,他娶她,还会错了?如果他娶的不是她,他还能有另一番日子?这么一想,她有些动摇了。原来这日子,也可以不依据她的想法和说法,也可以有另外的样子。
阳阳的脸红了。很奇怪的,她想到了什么,眼里竟有了笑意。她扭头看看门外的院子,灯光探出去,又被连接了山野的宽广的夜堵了回来。她回过头说:“妈,我不是说你和爸谁对谁错,你们的事情,我也说不清楚。我想给你说的是,人活在世上,大家都是辛苦的。如果你一边辛辛苦苦地活,一边自己的心里还很苦,那有的苦,就是你自己找来的。”
她郑重的脸色,一句一句慢吞吞说出来的话,让小安娘忽然觉得,她瘦瘦的身板里,那件穿得起了绒球的运动衣后面,有一颗小小的心。这个丫头,在自己身边长了14年,她从来没有感到她也会有一颗小小的心。
“好笑!”她毕竟是妈,不能服了气。人生九十九座桥,她才过了几座?“一个人命苦,心还能不苦?给你一碗苦药喝,你还脸上笑嘻嘻的,人家不会说你是神经病?”
阳阳的脸又红了,那不是因为争执。她心里有许多话,从她的脸上泛出来了。她还是一句一句地说:“你的命苦,比你命苦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我们的历史书上说,这世上曾经打过很多的仗,死过很多的人,他们都比我们命苦。如果跟别人比命好,那你的心就会苦,跟别人比命苦呢,你就会觉得,自己再苦也不苦了。”
“你不要给我背书本,先把剩菜赶在这个碗里。你那点道理,是书上背来的,我这些苦,是一天天熬过来的!”
阳阳手上忙着,话却停不下来:“妈,原来我也觉得自己命苦。特别是放学回来的时候,走着走着天就黑了,我的心就会苦,也找不到人说。有一段时间,我就恨你们,一个一个地恨,恨爹,恨你,恨大哥和二哥,你们都走了,把我和外婆丢在家里。还有一段时间呢,我就哭,反正也没有人看见,我觉得苦了,就痛快地哭一次。后来有一天,我发现,只要自己不觉得苦了,那些苦就不算一回事了。路上黑了,我就唱歌、背书。累得不行了,我就想,睡上一觉,什么都会好了。我们老师和同学都说,我变了。我一变,学习也好了,自己也高兴了。”
一只飞蛾呆头呆脑地撞上了灯泡,掉下翅膀上的几粒粉,又飞走了。小安娘把她的话听进了心里,一阵悲,一阵喜,却渐渐地有了一种陌生的踏实。她叹一口气,缓和一下声音说:“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过来的,觉得前面有更好的东西在等你,所有的苦吃完了,就会没有了。过到后来,苦,还是一个接一个,你呢,慢慢老了,没有心气了,那苦就更苦了……”
“妈——!”阳阳从厨房里转出来,站在门栏边,眼睛亮亮地看着她:“就是你说的这样,没有心气才是最可怕的。没有心气的人,先被自己打败了、打垮了,那就谁也扶不起来了。像我们这样的,在这世上,谁也靠不了,只有靠自己的心气。只要心气在,总能找出一条路来。”
阳阳依旧青涩的嗓门,在这个被夜色包裹的静静的屋子里,竟有掷地有声的分量。小安娘心里一颤,有什么地方湿润了,漫开来。她的心,很久以来总是愤懑的、尖厉的、防备的,后来也就麻木了。而现在,好像垒起的墙塌了一块,露出一线光,柔软地照着她,她也是很久不懂得柔软的。
“是喽是喽,就你会说。”她有些喃喃地,抓过门后的扫帚低头扫地,掩住了自己的脸。
[六]
天还没亮,山巅上飘浮着几道殷红,四下稻田里的黄,是沉沉的。凤池村通向鎮里的山道上,小安娘走在前面,阳阳跟在后面,她们母女从未并排走过,现在仍是这样。
“那个陈炳德,年轻的时候倒是个老实人。现在人家是校长,这四乡八寨,外加一个镇,哪家没有读书的?哪个不求他?人心隔肚皮,我们这样空着手去,晓得他怎样想?”
小安娘说着,声音是惯常的抱怨,但是奇怪,她的心却并不往下落。昨天夜里,她翻来覆去地把所有的事情想了一遍,把自己的命想了一遍。最后她想,还是要往下活,要拿出心气来,活出个不一样来。这是她这几十年从来没有过的决定,这个决定一有了,今早出门,她发现自己不再害怕遇见人了。遇见了又怎样,大大方方地笑一笑,打个招呼,让人家知道,她小安娘虽然倒霉,却是个有心气的人。
阳阳在身后,小姑娘的脚步是轻巧的。她说:“你先不要把人家往坏处想嘛。你把他想坏了,你自己就不知道怎么说话了。再说,你家三姑娘,很争气,成绩是最好的。你去我们学校,老师和同学看你,都会佩服你、羡慕你呢。”
小安娘笑起来,她很久没有这样笑,竟隐然有年轻时的样子。她转过身,佯作垮脸道:“我家三姑娘,那是谁?”
阳阳站住了,笑道:“就是我嘛。”
小安娘一时不知是伸手摸她一下,还是打她一下。她返身继续走,长长地吸一口气,黎明前的空气,清凉得有些刺鼻。小安娘看看山下的稻田和渐远的凤池村,她想,这世上有千千万万的人,人家能过下去,她也能。
[作者简介]李钢音,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文学创作。曾任记者、编辑、艺术研究员等。出版长篇小说《远天远地》、中短篇小说《惊慌》,发表小说、散文、文学评论、艺术评论等数百万字。撰写舞剧剧本、舞台剧本等多部。现为贵州财经大学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