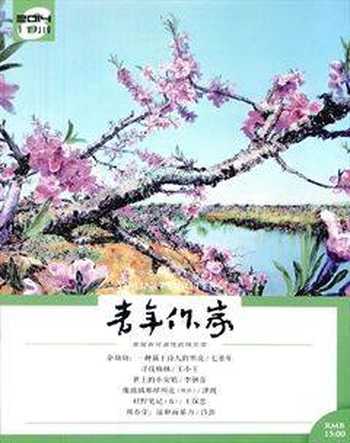周春芽:温和而暴力
“桃花”系列是与画家绘制“绿狗”乃至“人体”的同时进行的,在新的世纪里,周春芽的“桃花”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在观念的借用与绘画性的保持之间形成了呼应。
西方人是否真能理解中国古人的“溃烂之处艳若桃李”文字的含义,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们肯定理解画家作品中的“艳若桃李”的景象来自何处。
从心理学意义上讲,任何行为都潜藏着动机,即便我们不了解画家每天的经历和特殊遭遇,也能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语言的特殊性仍然是绘画的生命。焦虑、感伤、恐惧以及伤害感从来不是莫名其妙地生发出来的,而画家只能用最后的图像来证明自己内心变化的特殊性。因此,消除“意义”和拒绝“阐释”只有在眼睛能够判断的新图像产生后才可能被认为不是一种欺骗。哲学观念只能启开画家的编程,而图像本身才是我们对观念进行判断的最后依据。到九十年代末,从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开始的个人图像非常壮观,人们逐渐很容易对画家的符号保持记忆。这样的现象促使人们开始理解“商标”或者“品牌”的重要性。独特的和重复的就是艺术的。尤其是当照片和电视影像成为一种有效的工具时,绘画性被降低到消除笔触的最低水平。在这样的形势下,人们有可能会再次关注画面的趣味,而不是观念的新颖。的确,当商业的力量阻止着画家的创造力和敏感性时,我们同样能够发现开放的绘画性的产生。
事实上,观念的自由与绘画的趣味助长着“新绘画”的展开,在世纪的转折时期,周春芽的艺术成为我们归纳新绘画的案例。周春芽的绘画经历了凡高、莫迪格里阿尼、契里柯以及前述德国画家精神上的洗礼,这样的精神史是与中国现代艺术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转变历程相吻合的,他接受时代的气息,他渴望了解西方文化的历史,可是,他知道自己这个“中国石头”有它不可分割的自然环境,他必须将自己摆放在所有有教养的人都深深眷念的土壤中,也就是说,他不认为有一个世界主义的当代标准,即便是有,那正好是表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时体现出来的个性。所以,他用更多的时间与实践去理解文明与传统的含义,与仅仅使用传统工具和材料的新文人画家不同的是,周春芽只承认有一个必须通过新工具和新观念重新理解、阐释、体会和追忆的文明和传统。同时,画家也非常明白,不存在什么一成不变的个性,个性总是在变化中生發出来的。所有的概念——革命与改良、传统与现代、当代性与全球化等等——也许遮蔽着文明本身的演变,而直觉却可以告诉自己什么是今天应有的艺术态度。
我相信,历史是一个充满个性的演进过程,真正有魅力的往往不是那些事后总结出来的“必然规律”,而是那些看似偶然的东西——那些偶然的东西比必然的规律带给我们更多的感动,在我们的生活中变得更为重要——如果你要去追问那些看似偶然的东西何以变得重要,你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地迷恋上历史。也只有在这样的追问中,传统才变得有魅力,也只有这样的传统才是具有艺术品质的传统。(《花间记》——周春芽访谈)
周春芽所表达的这种悟性存在于很多杰出的艺术家的大脑中,他们对艺术的历史与未来的理解构成了二十世纪艺术观念的宝贵遗产。(此文节选吕澎《新绘画的“桃月”》——周春芽的艺术历程,题目为编者按。)
[作者简介]吕澎,1956年出生于四川重庆。1982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1982—1985年任《戏剧与电影》杂志社编辑;1986—1991年任四川省戏剧家协会副秘书长;1990年—1993年任《艺术·市场》杂志执行主编;2004年,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成都当代美术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