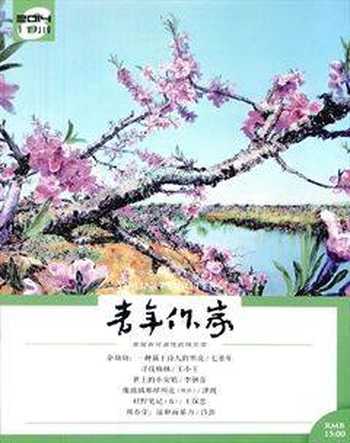烟火岛屿
[两年前]
那天晚上他喝醉了,喝得非常醉。在酒吧里,匆匆赶来的余乔将他接回了家,无微不至地照顾,将他吐在地上的呕吐物拖了一遍又一遍。彼时时值深秋,满街萧索颓唐,四处是落了一地的叶子,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到了暮年,却又不忍要卖弄一把,自己也曾辉煌过。这时距他从前的爱人谢梓嫚离开又一年了。
简陋昏暗的出租房里,余乔用一只电热水壶煮开水,给他冲葡萄糖水喝。电壶水开后“咕噜—咕噜—”的蜂鸣声响彻了整个房间,不多时他便醒了,头重脚轻地走去门外撒了一泡尿回来,看到余乔一动不动地坐在床边,他看了一下墙上老式的摇摆挂钟,已经两点了。不过直觉告诉他,她心里有事。
这个季节里的夜晚是一年当中最静的,连街上刮的风都是阴森阴森的,有种让人绝望的念头。
他开始在房间里来回地踱步,也没有其他可以走的地方,这已经是第几支烟了,但看他的样子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余乔也抬头看了一眼挂钟旁边挂着的日历,问他:
“明天几号了?”
他狠狠吸了一口烟,头也不回地说:
“又一年了吧。”像是在答非所问。
“嗯。”
房间里的气氛就跟她此时脸上的表情一样平淡。她突然说:
“对不起。”
“没什么。”终于,他按灭了烟头。
谁都没有提起谢梓嫚,这个无数次被打碎又缝合起来的名字,但又彼此心照不宣,谁都知道这是迈不过去的一道坎。
她想起自己三年前才来这里的时候。那会儿他们的店里正好缺一个人手,她看到铺面上张贴的招聘启事,就这样留下来了,一切像是顺理成章那样。也没什么面试,她去的时候,他们夫妻俩吵架正在势头上,等吵完了,老板娘气喘喘地从屋里出来,没什么好气地问她,会干什么。于是她就耐着性子说,自己是哪所学校毕业的、学什么专业、以前都干过些什么,诸如此类。当然对方没有这么好的耐性,再说就他们卖这么个百货,管她哪所学校,又是什么专业,只要人勤劳,怎么都行。所以,在她说到一半的时候,老板娘打断她:
“行了,要愿意,不怕苦,做得下来,就留下来。”
其他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一直以来,他们之间都很少说话,一说话就是吵架。天下夫妻,家家都是柴米油盐,他就不知道她哪里来那么大火气。他们躺在床上看电视,他要看体育频道,她不肯,执意让他换台,奈何她任何事都是三十分钟热度,这会儿她又嫌肥皂剧里的女主角长得太丑看不下去,索性关了电视,也不准他再打开。夜里睡觉,也是同床异梦,确切点说,都是她一个人在做梦,将所有的梦都做完了,包括他的那一部分一起。有时半夜,她把手伸向他的身體,顺势整个身子附上来。但他哪里去找那份心思。于是她又开始撒泼,弄出的声响一次比一次大,到后来街坊邻居都来投诉。他们跟他说,你娶了一个什么样的老婆。被她听到,骂街那声音堪比车祸现场,他却无能为力。
“你哪时候怎么想的?”她说。
“我有时候真想杀了她,一了百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明显带着很深很深的感慨。
每逢他们一吵架她就往家里跑,他匆忙赶去,她家里的姐妹不听任何理由将他从头到脚数落一番,在娘家小住几天,气消了,打电话叫他来接她回去,回他们的出租房。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后来回忆起来,谢梓嫚在的那几年,他们生活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差不多都是依着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的固定模式过来的,对此他早已烦不胜烦。所以到不久之后的后来,哪怕那些闲来无事的街坊邻居当中的老婆婆来找到他说:小陆啊,你看那个,我有好几次一大早上街出去买菜,看到你们小谢也走在街上……他想,其实这有什么呢,他当然不会不知道,她姓谢的是去找其他男人去了,她一连好几天都没回来,衣服也带走了两件。他又不是傻子,撇开他们感情不和不说,从她那么久没碰过报刊,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地拿起搁在床头柜上那本已经很久没有翻过、蒙了一层灰的《知音》杂志来看,他就告诉自己,她不是个天真的女人。虽然明知这样,但还是不甘心,他潜意识里会想,她是怎么和别的男人上床、他们又是如何在那层没有他的空气里开始怎样的新生活。他越想头脑越大,当下脑子里联想到的情况使他抓狂。
于是,和余乔交往,在他看来,更像是一件生活中必不可少且又顺理成章的事情。这甚至让他觉得,他的这一行为,丝毫没有和谢梓嫚赌气的意味在里面。而且,他当真也是怀着憧憬般的心情,小心翼翼地如他的初恋一般去经营。他告诉自己,一点都不是因为寂寞。
余乔是个十分懂事的女孩子,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非常轻柔,像生怕做错了事一样,有时候还搞得他很不好意思,他们上床的时候他很紧张,好几次他都试图让自己停下来,但那种被欢快笼络的感觉让他无法思考。
他上大学的时候认识的谢梓嫚,期末大考前,图书馆人满为患,像是将所有人关在密不透风的笼子里。图书管理员不停地在块头高大的书架上整理书籍,待到谢梓嫚去取书,因为一本古旧稀有的英语考级书和管理员发生争执,原本异常安静的四周只听到尖锐的争吵声划过来,掠过所有人的头顶,她被很多双不同的目光注视着,觉得羞愧。那时是五月,窗外的杜鹃花开满了树枝,有几枝从开着的窗户伸了进来,这从南方调过来的娇艳花种,竟也带了一丝北方的豪放,就像她的性格。
那天他一直坐在窗边,不知为何就被这不尚友好的声音吸引过去,整个人都被她吸引。她十分美,长着一双会发光的眼睛,小圆樱桃一样的鼻子像是漫画里走出来的人物,一切都让他沉迷,情不自禁地走了进去。他坐在原地走了一上午的神,从不同的角度看她,面前的书一直停留在第一页,直到她走到他的对面坐下,他才恍过神来。
现在的谢梓嫚让他觉得她是个不可理喻的女人,他难以将她和记忆里的她相比。那时候他们在北京,刚毕业的时候,他一无所有,她义无反顾地跟着他来到他的家乡,租了一家小店。生活虽不易,但老天也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恩赐,渐渐地,谢梓嫚也学着开始频繁地进出茶楼,和一些被称作“太太”的妇女打牌,一进去,半天过了,等出来,半天又过了。他们之间的生活越来越乏味,谢梓嫚看他的眼神,让他知道他们之间应该不会持续太久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经常半夜里睡不着,思来想去,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像是提早进入了冬天。
[五个月前]
早上,那个警察开着车在巡街的时候,又经过这里两次。
这会儿,他又坐在这间奶茶店里消闲时间了,一边从包里取出一包烟,抽出一支点上,老板娘从吧台上给他端来一杯冰水,也在桌旁坐下来。
然后他们开始交谈。
他们的对话,几乎每次都是这样开始,像两个老朋友一般地拉拉家常,虽说以他们的年龄感觉上好像不太合时宜。
警察一开始是因为两年前那起案件认识他们小夫妻的,那时候他们还不是夫妻。只记得原来那个叫谢梓嫚的女人,有段时间,差不多整条街上的人们都在传说她脑子有问题的事。譬如在茶楼里打牌,服务员端来一杯茶水,她责怪并坚信其端上的是一杯咖啡;譬如,毫无征兆的她跑去向房东拿出租房子的钥匙,将别人家的小孩子牵去马路上逛街,吓得别人打电话报警。
出事的那天晚上,她坐在吧台上调一杯奶茶,暗黄色的灯光打在脸上,使她的表情看上去神乎其神。天色暗下来之前,她早早地就关了奶茶店的门。
吃过饭后,男人齐冬就一直呆在房间里,电视里正在播放《焦点访谈》,讲一对夫妻闹离婚,男的不愿意,女人一哭二闹三上吊,不依不饶地撒泼。也就在那个当口,谢梓嫚走进来,将手里端着的奶茶往男人面前的桌子上使劲一放,奶茶从杯子边上淌出来,溅了男人一手都是。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顺手扯了一张纸来擦掉,大概是早已经习惯于她神经质的性格。
“我们离婚吧。”她说。
男人不理她,继续抽着手上的烟,像是没听见一样。
“我要和你离婚。”她又说了一次,这次聲音明显提高了两个度。
男人从来没告诉她的是,她撒泼的时候看起来就像个魔鬼,比更年期的妇女还厉害,她脸上的表情实在称得上是狰狞,没有一点女人柔美的气质。“妈的,跟个魔鬼一样。”他在心里暗骂了两声。
那天到后来的时候,谢梓嫚从狭仄房间的旮旯里面翻出一条内裤,上面带着女人干掉的血渍,可想而知,那是怎样的一种歇斯底里般的情绪发泄,事后屋内和醉鬼闹场没什么区别。
第二天起床,他发现谢梓嫚吞了安眠药,不多不少,刚好五十颗,混着酒吃了下去。哭天抢地地送到医院,还是没能抢救过来。
之后,她和齐冬被带回去做笔录。大概从没有遇到过像他一样如此唐突提问的警察。
他说:
“她之前知不知道你们的关系?”
他们两人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的话,倒也不是因为羞赧。复而他又说:
“你们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很严重吗?”“一点都没有考虑过吗?”
男人艰难地摇摇头。
“你爱她吗?”警察问他。
“当然。”男人回答得斩钉截铁。
“你的老婆?”他提醒他。
“也爱。” “爱过。”他补充道。
差不多两分钟,三个人谁都没有说话。
他很怅惘。在他和谢梓嫚的这段感情里面,他慢慢变得一点都不像当年那个在学校里抱着吉他站在女生宿舍楼下向她求爱的大男生,自然她也不是那个他为了她跟傲慢的图书管理员在大堂里大吵起来甚至差点打上一架而感动的女生,谁也没有兴趣再去细读谁的人生,住在一个屋檐下,不像是夫妻,倒更像是两个关系交恶的房客。
再之后也就跟众人想象的一样,在谢梓嫚离开后的一年,齐冬和余乔结婚。他们举办喜宴的时候警察也来了,齐冬和他喝了很多,还借着酒劲胡言乱语地说了些称兄道弟的话,他告诉警察,他现在轻松了许多,自在坦然,余乔的到来使他的生活变得不再枯燥无味。
下午没什么人,除了偶尔路过进店来买两杯奶茶的路人,在仅有的一张小圆桌面前,只有余乔和警察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他好奇像余乔这么年轻的女孩子,在北京那样的大城市念完正经的大学,为何跑到南方这样偏远的小县城里来。
“毕业那年和朋友来这边玩,感觉生活悠闲安逸,就不想走了。”她说得轻描淡写,仿佛事情注定就是这样,没什么可奇怪的。
他笑笑,也不由得从心里佩服一个柔弱女子竟有这样随性的胆识。
她说:
“我爸爸也是警察。”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多年来她都很自立,上中学开始就在寄宿学校里度过。
警察深深地呷了一口烟,没有说话。后来她听人说警察的老婆两年前死于一场癌症。她不知道,好像心里面一直有块无比坚硬的东西,不知何时正在一点一点地融化掉。
很快就到了黄昏,警察面前桌子上杯子里面的水已经倒了第三杯,待他接完一个电话后起身,准备回家去,余乔留他吃饭,他推托着说下次。
那时距谢梓嫚离开已有差不多两年半的时间,而齐冬一来醉酒的状况并没有得到缓解,时不时伙同他的几个酒肉朋友跑出去痛饮,等到夜里回来,发完酒疯之后,偶尔还煞有介事地跑到门外的马路牙子上去哭,有时遇到几个夜归的路人,看到的话,就像躲人瘟一样厌恶般地快速走过,大概在他们眼里,那可能是一整天里最让人感到晦暗的声音。
[一个月前]
奶茶店的生意越发的不好,街上经常也没什么人,冷清得像个坟场,小地方的人都到外面大城市打工去了。其间还有好几对情侣跑来打听,问老板娘余乔店面能否转让给他们。她想那些情侣也可能和当初的她一样,抱着一份文艺情结的心来这里。而今她却觉得,那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由于各种各样不由分说的原因选择以逃避的方式来前进,实在是对生命的损耗。并且用不了很久的时间就会发现这种逃避毫无意义,一点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像心里一直横着一条梗,不仅没有拿掉,到后来反而越磨越细,顶在原地让人苦闷到极致。
比如现在,她感觉脑子里一片混乱,觉得所有事情都搅到了一起,让人头皮发麻。齐冬和谢梓嫚,齐冬日复一日的醉酒,一喝多了就发酒疯控制不住。直到有天晚上,两人睡到半夜,他一直醒着,终于忍无可忍地翻身到她上面,哭着对她说,叫她打他,用力打。
“我是罪人。”他哭着说。
她不说话,诧异地看着从未那样失态过的他。
他几乎是一双哀怨的眼睛,眼泪和鼻涕流了一脸,低声说:
“你打我吧,狠狠地打,狠狠地打。”
她不可置信地看着他,觉得像在看一个精神病人。
随后他又跳下床,从床脚边上的小柜子里翻出一瓶安定片,她看到他一张诞着诡异表情的脸,说不出话来,感觉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一周前]
最近那个警察来店里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了,很意外的是,他居然也提到了谢梓嫚。他一直都是个好警察。在他问到余乔“你知道些什么吗?”的时候,那一瞬间她感到从没有那样无助过,她不断告诉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她想象的那樣,不是真的。可同时又有另一个声音跳出来反驳道:你为什么要拒绝承认,他是为了你好。难道是因为害怕吗,害怕知道一些事实,害怕打碎她一直以来平静生活的美梦。那个声音在说,不然的话你自己去问问,问齐冬,问他两年前谢梓嫚的死,到底和他有没有关系。难道你忘记了齐冬这么久以来上了瘾一般的醉酒吗?还不是因为他心里过意不去……
够了,她打断那个声音。她觉得自己像是在和它进行一场艰难的博弈,此刻她精疲力竭,断然想阻止这一切,却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样的感觉就像是茫茫大海中的一座孤岛,放眼四周,全是无边无际的大海和蓝天,孤援无助。
警察看出她脸色很难看,轻轻抚着她肩膀,感慨着说:
“别怕,有我在。”
她思考良久,最后还是无奈地摇了摇头,拒绝了他。
很明显看得出来警察有些失望,神情忧伤地看着她。
“别忘了你父亲是警察。”“我也是。”他强调。
“你要主动些,不能这样。”警察说完就离开了。
晚上齐冬回来,一场百无聊赖的争吵之后两个人各自窝在那张狭窄又脏乱的沙发的一头,不发一语。不一会儿他的身边又放了好几个空啤酒罐,一边从电视柜里面翻出碟片来看,她终于忍无可忍,起身去厕所对着水龙头狠狠冲了个冷水脸回来。他这会儿像是清醒了些,为刚才无理取闹的行为向她道歉。
她没有说话,径直走到床边,从床下拖出那个小柜子,那一刻,他好似终于明白了一点什么事情,问她:
“你在找什么?”
她毫不耐烦地看了他一眼,深吸一口气,用手捋了捋额头边垂下来的一丝头发,问他:
“你那瓶安定片呢,还在里面吗?”
差不多同时,她的手机屏幕一闪一闪地亮了起来,是那个警察打给她的。
不过没什么吧,她想,反正她已经想好了。
[作者简介]陈燃,1989年末生于四川;作品多散见于片刻网、ONE?一个等网络媒体,曾入围香港青年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