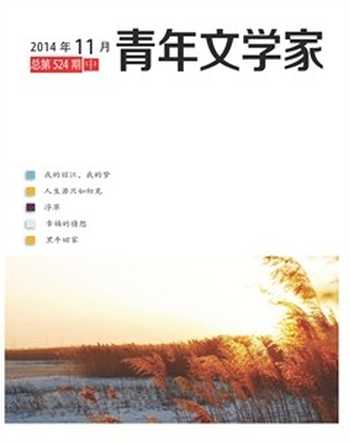试论北魏造像碑的汉代渊源
张优群
摘 要:北魏时期,在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下,我国佛教造像大肆兴起。这种佛教造像艺术是外来佛教文化与中华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北魏时期的造像碑既受了外来文化艺术的熏染,也有着对汉代艺术样式的传承。本文拟从形制、图像、结构和构图以及艺术手法等方面分析北魏造像碑造型的汉代渊源。
关键词:造像碑;造型
[中图分类号]:J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32--02
一、引言
早在造像碑兴起之前的远古时代,中国人就有用树石来表达对土地神崇拜的习俗。现今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玉璋、玉圭 ,证实了先民对“美石”的偏好。据文献记载,商周时期人们就已经模仿玉圭发明了石碑,用于重大的礼仪活动。《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了秦始皇泰山刻石的情况,可惜原碑已残,仅存十字,无法考证原石的形制。但这些都是石碑的原型。到了汉代后期,用铭文记述建碑原由、出资者姓名的功德碑,祭天、祭孔的石碑,以及用于丧葬目的石碑广泛流行。这些碑大部分建于公元一世纪至公元二世纪。到了北魏时期,由于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我国佛教造像之风大肆兴起。这种外来艺术一开始就和我本土文化交相融合,进而产生了一种具有诸多文化因素的中国特有的艺术样式:造像碑。
造像碑按所属宗教性质可分为佛教造像碑和道教造像碑,还有一种佛道混合形造像碑。北魏造像碑在形制、图像、结构和艺术手法等方面承袭了汉代造型艺术样式,既吸收了外来文化艺术特征,也是汉代艺术样式的传承。
二、北魏造像碑基本形制的汉代渊源
汉代早期石碑通常高一至三米,最初多为圭形和简易方形,但很快又出现了以螭装饰的弧形碑首。这些石碑大部分产生于公元一至二世纪,基本上由碑首、碑身和碑座三部分组成。碑身的正面谓“阳”,刻碑名;反面谓“阴”,刻题文;左右两面谓“侧”,亦用以刻题名。碑首内通常有用于题刻“标题”的篆首,碑阳刻造碑缘由,碑阴刻出资者姓名。汉代保存下来的这类石碑多为丧葬碑,其次为功德碑。这种构造的石碑在后世广为延用。
北魏造像碑在最初建造时并没有被称之为“造像碑”,而是被称为“石像”、“四面好铭”等。据罗宏才先生在《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以关中地区为考察中心》一书中对“扁体碑形造像碑各时期称谓示例统计”一表中显示,迟至北周保定三年(公563元),造像碑发愿文中始见“碑”的称谓。笔者按罗先生的统计将发愿文中的称谓进行分类,有如下几种:1.以其形体指称,如“四面好铭”“四面真容”;2.模糊称其为“像”、 “石像”;3.以主龛造像尊号指称,如“阿弥陀佛”、“弥勒”,4.称“碑”者;5.其他。这些称谓交错繁复,通过分类,笔者认为冠以“四面”指出其形体的,应该和石窟造像中“中心柱式”石碑有着某种关联。而以主尊尊号指称应该是强调具体的信仰。泛指为像者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应该是在强调其“图像”的视觉性。这些构想缺乏依据,还有待进一步考证。而称谓“碑”者,我们通过分析现藏临潼博物馆的北魏正光年间(公元523年)的师录生造像碑,了解到其在建造之初就和碑的视觉特征及其纪念功能相关联,使之具有碑的特征。这是一尊佛道混合造像碑,高215cm,宽77cm,厚27cm。碑阴碑阳在视觉形式上和汉代石碑相似,同时也具有汉代石碑所具有的螭形碑首、篆额、碑身铭文等基本要素。这些要素佛教造像碑也有采用,如甘肃省博物馆藏北周保定三年(公元563年)权道奴造像碑,碑高82cm,宽33cm,螭首,长方形碑额,内有“伏福寺”三字,碑阳有发愿文和供养人提名,这些符合我们今天碑的定义的视觉特征和基本构造。又如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的北周吕建从造像碑,碑高111厘米,宽50厘米,螭首圆顶,篆首内刻“建崇寺”三字,碑阳有长篇发愿铭文。
受佛教造像艺术影响,虽有图画因素融入了传统石碑,但北魏造像碑还是保留了汉代碑的一般形制,并沿袭了汉代以来石碑的纪念功能。
三、北魏造像碑一般图像的汉代渊源
北魏造像碑的基本图像有龙纹,庑殿式龛楣和博山炉,这些图像和它象征在汉代已经形成。
龛楣交龙纹图样是造像碑常见的样式之一。中国已知最早的龙的形象是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村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碧玉龙,是不同图腾崇拜的部落融合的产物。进而发展成商周时期刻在青铜器上的夔龙纹。秦汉之际这种龙纹成为皇权的象征及民间祥瑞动物,并使用在碑上。其汉代墓室的壁画和画像石中也多有表现。汉代人相信灵魂不死,龙引领是灵魂升仙的交通工具。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铭旌里,墓主人的灵魂正是乘着双龙飞升天国的。北朝造像碑沿袭了汉代信仰及以龙为装饰的圆形碑首的样式。
龛楣廡殿式图样是佛教造像和道教造像主要区分的标志之一,显示了道教造像一开始力图区别于佛教造像的花瓣形的背光造型。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样式来源于墓室建筑阙。阙在汉代标志着天宫的入口,是灵魂升仙的场所,和北魏造像碑就有相同的“升仙”功能。汉代人们认为灵魂不死,在另一个世界应该享有更好的物资条件,因此汉代画像石经常刻有这一建筑形象—“天宫”。
汉代博山炉昌装饰在主龛造像的下方,两侧常有“邑师”、“邑正”和“道士”等神职人员,作礼仪状。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就有燃香的习俗。博山炉在汉代是非常流行的样式,主要源于汉代对于神仙居住之所-仙山非常向往。博山炉炉体峰峦叠嶂,中空用于燃香,有孔与外相通,燃香时烟雾从孔洞中冒出,顿时群山间烟雾缭绕,有如神仙仙境,因此而得名。这种博山炉在汉墓中多有出土,其中最为精美者有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汉代无名墓出土的鎏金银铜竹节熏炉和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错金银博山炉。北魏期道教造像碑所刻博山炉与汉代博山炉形式相仿或直接挪用了汉代博山炉的样式,这些样式在一些佛教造像碑也有采用,并成为礼佛的象征。
这些在汉代就形成的具有特定象征的图像,在北魏道教造像碑上大量出现,同时也被佛教造像碑所采用,显现出造像碑对汉代艺术的继承。
四、北魏造像碑画面的结构和构图的汉代渊源
北魏造像碑碑身从一面造像到四面造像的多种样式,各个面在构图上自成整体,尤以碑阳和碑阴最为精美。造像碑多为“天”、“连接天人的中间结构”和“人”三段式结构,采用不留空白的“满画幅式”构图。上部碑额通常用龙纹、双凤鸟、屋顶、日月纹来装饰,竭力营造一个奇异的天上空间。中间间以“道士”、“邑师”、“邑正”等神职人员来沟通天和人,碑身下部为供养人、出行图等,表现出人间生活。各部分虽属不同空间,但并不以界格将其完全分开,而是各不凡间相互穿插交织,空白处饰以瑞兽、植物等纹样,这样在构图上主龛造像突出,形式饱满,浑然天成。如耀县博物馆藏北魏始光元年(公元424年)魏文朗造像碑,这是一尊佛道混合式造像碑,高131cm,宽60-72cm,厚29-31cm。该碑碑阳主龛刻双尊坐像,一佛一道。上部龛楣刻双交龙纹,双龙身和龙舌分碑交绕在碑身中线上,左右各饰一飞天羽人,双龙尾各由左右两侧垂至龛楣中部,上卷的尾部巧妙的围合了上部空间,而使像龛下部成开放状态。主尊造像坐在胡床上,两侧床腿稍下延,右侧外部刻一道女,左侧刻一汉式建筑。胡床下方两床腿中央刻一博山炉,博山炉上部与胡床底部相接,两侧各刻一人作跪拜状。博山炉下方刻一行车马出行图,两侧都到碑的边沿。其中以女子持伞,伞顶部升至博山炉底座左侧跪拜状人居于下方。碑的底部刻一排供养人,成平列式展开。该碑碑阴和碑阳相仿,局部内容稍有不同。两碑侧稍简。北朝年间道教造像碑多采用这种结构方式和构图。如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北魏延昌元年(公元512年)朱奇兄弟造像碑。其中有些碑由于下方所刻供养人过多而影响视觉,但就其结构而言并未改变。
这些造像碑的结构和构图样式我们在汉代帛画,画像石,画像砖里能找到其原型。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铭旌最为典型。一号墓铭旌也分“天”、“中间结构”和“人”。上段天宫中央画有一人首蛇身女娲,两角分别饰象征日月的金乌和蟾蜍,女娲和日月图形间以仙鹤填补。天宫下部画两条蜿蜒飞舞的巨龙,两龙头上仰至女娲交绕的蛇身两侧。天宫下部双龙中央有天阙,两司阍守门。上方两只瑞鸟相对而立,下饰一蝙蝠的菱形纹样镶入天阙之中,两条飞龙载着墓主人从两侧飞向天阙。下段错综交绕的两龙尾中画一厅堂,厅堂内設案列鼎,有人跪坐向死者致祭。这样的原型还有马王堆三号墓铭旌和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墓铭旌。
通过分析比较北魏造像碑和汉代帛画的结构与构图,我们发现其有很大的相似性。
五、北魏造像碑艺术手法的汉代渊源
北魏造像碑除基本形制、图像、结构和构图等方面沿袭了汉代艺术之外,还在艺术手法方面承袭汉代画像石阴线刻、平面减地辅以刻线和浅浮雕等造型方式。阴线刻是不直接拉开物体到底层次,仅通过向下刻出深深的线条来区分物体和背景以及物象的各个部件,结构类似于白描的一种方式。平面减地辅以刻线的造型手法是在平整的石块上将主体物象以外的背景薄薄的减去一层,以区分物象和背景,但各物象间和物象各部分并不以高低层次表现物体的空间,而是通过边缘轮廓线和机构线表现物象形体和空间的一种艺术造型手法。汉代画像石浅浮雕手法和平面减地手法类似,通常也薄薄地减去一层背景,但物象各部分的空间层次通过减低交界处在后面的部分来实现,而物像高点部位处在同一平面。这两种手法具有很强的平面绘画性。这类画像石在陕北,苏北和山东与四川等地都有出土,北魏造像碑艺术继承了这一手法,显现出与外来佛教石窟造像所用的圆雕或高浮雕的明显差异。
北魏造像碑通常在主尊造像处先造出一个弧形的深坑,主尊造像采用高浮雕手法表现主尊造像的形体,而龛楣装饰图样和供养人采用画像石平面减地或浅浮雕手法,既保证了碑体的整体性,同时主龛造像突出,光影下也显得异常神圣。如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田良宽造像碑。该碑除采用高浮雕形式刻出主尊造像形体,并刻曹衣出水般密集的线条表现外,龛楣、飞天 、供养人等采用刻线的手法。又如邑子六十人造像碑,除主龛造像外,龛楣交龙纹、道士、邑师等神职人员与各供养人均采用平面减地辅以刻线的手法,这和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艺术手法一致。两者均采用平面减地的艺术手法,刻去图像以外的背景,使之与图像相比低一个层次,图像整体在一个平面上,图像结构和装饰均采用刻线。由此可见北魏造像碑在艺术手法上对汉代画像石造型手法的借用。
六、结论
汉代民间流行 “升仙”信仰,事死如事生,盛行厚葬。为实现“升仙”的愿望,在地下建造起富丽堂皇的墓室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在地上树立了高耸的石碑、石阙,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汉代丧葬艺术样式。这些艺术样式后世不断沿用和发展。北魏造像碑在形制上基本承袭了汉代石碑石阙的基本样式和构件,图像沿袭了汉代帛画和画像石的图样及象征,结构和构图样采用了汉代帛画、墓室壁画和画像石、画像砖的结构和构图,艺术手法方面直接承袭了汉代画像石平面减地辅以刻线的艺术手法,是外来佛教艺术的外衣影响下的中国特色的艺术样式,对后期佛教造像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罗宏才.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以关中地区为考察中心[M]. 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
[2]王静芬.中国石碑一种象征形式在佛教传入之前或之后的运用[M].商务印书馆,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