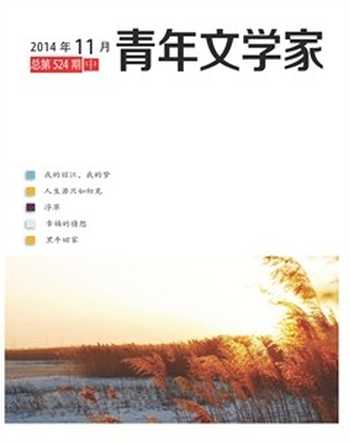批《边城》的“世外桃源”论调
马晓月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32-0-01
沈从文笔下一派清新明媚,质朴明朗,勾勒出一个干净清澈的边城。
一般观点来看,边城似陶公笔下的桃花源,因而引起了人们相当大的争议。有的人说边城太干净太美好,将现实生活理想化。特别是在动荡纷乱的1934,沈从文并没有于乱世担起社会的责任来。很多人将响应寥寥也振臂高呼的鲁迅与其相比,不满沈从文明哲保身的态度,并引用鲁迅的话“时代所要求的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而不是‘供雅人摩挲的小摆设。”加以批判。
在我眼里,这是相当错误的论调。
一、《边城》反映的年代
首先在年代的判断上,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边城》发表于1934年,但其反映的年代并不是当时,因而不具有那时动荡不安的时代特色。《〈边城〉题记》里,沈从文曾预告似地说:“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这表明,关于“二十年来的内战”他会在“另一个作品里”进行描写,而这“另一个作品”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长河》。《长河<题记>》也有云:“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这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边城》是“过去”而《长河》是“当前”。他看出二十年的内战对当下湘西农民产生的深层次的影响,淳朴的乡民被时代的纷乱所害,失去了原来美好朴实与正直热情,“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
但这种变化前推二十年则是没有的,因而不会在“过去”的《边城》中得到明确体现。1914年,也就是民国3年,民国刚刚成立,其影响还没有到达西南乡村。此时,湖南省废“府”、“州”、“厅”,保留道,州厅改名为县。改辰沅永靖道为辰沅道,治凤凰,世道较为和平,是一个相对沉寂的时代。因而表现那时风土的《边城》较多的表达的是原始的朴素澄明。
二、《边城》的悲剧色彩
《边城》常为人诟病的是它的理想化,然而,这同样也是一个错误。之所以人们觉得《边城》理想,是因为其悲剧色彩被沈从文有意识的冲淡了。爷爷去世了还有老马兵,翠翠摆渡时有人群的关怀,爷爷的葬礼并不太沉重等,就算在结尾也透着殷切期望:“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但看看边城里的人物,爷爷和天保去世,傩送出走,留下翠翠一人孤苦无依守着渡船,这怎么不是悲剧呢?黑格尔将悲剧分为三等,最高一等是“悲剧的根源来自两种伦理力量的冲突,冲突双方所代表的伦理力量都是合理的,但又都有片面性。由于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片面性而损害对方的合理性,从而产生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冲突。”而《边城》正是这种架构在合理性冲突之间的悲剧。里面所有的人都没有错,都在做自己地位下合理的事。只因为缺乏交流,不能真正理解对方,所以在各种误会中走向惨淡。纵使亲密如爷爷翠翠,也各怀心事,不能完全敞开心扉,因而翠翠直到爷爷死去,才从别人口中知道这一切因由,哭了一夜。
这是更高层次的悲剧,没有激烈的冲突场面,也没有罪魁祸首,人们也无法找出元凶和过错。这种悲剧隐没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很难被发现,但却贯穿于整个故事始末,平淡琐碎几乎无事,却在无形中扼杀生命。
三、边城与现实的联系
《边城》题记有云:“我将把这个民族位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些作品或许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动荡的1934,他还是注意到了国家的现状,在整个社会经历大变动之时,他写的是小人物在大环境的变化。
真实条件下,《边城》不可能与社会完全割裂。比如,水手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傩送会要碾坊不要渡船。故事中渡船和碾坊具有象征意义,象征着爷爷和翠翠的无私奉献,而碾坊则是现代工业经济的产物 ,是物质金钱的代表。人们对碾坊的趋向性正体现出物质财富对小城乡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同化。又比如,翠翠的母亲引来很多恋歌,而翠翠这代,就只有傩送一个人唱了。就连这一个人,也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唱,专挑了深夜,让翠翠疑心是在梦里。原始的纯洁和浪漫情调如同恋歌一样,已经渐渐淡出小城,取而代之的则是金钱与物质欲望,河街吊脚楼里的妓女通宵达旦陪客唱歌,世俗的淫调取代了恋歌成为夜晚的主旋律。尽管这些妓女有别于城市中媚俗的妓女们,她们还保留一点乡土的纯净,但这已经与传统的乡民性格相去甚远了。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说:“自由主义作家不可能完全无视民族国家的呼唤,他们也是以自己的不同于革命作家的方式,通过也许是更为曲折的道路,与自己的民族,人民以及社会现实生活保持着或一程度的联系。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社会人生,探求民族复兴的道路”。社会动荡之时,虽然不明显,但沈从文还是挑起了作家的责任,毕竟他属于社会,此等环境,不能与时代完全拉开距离。
参考文献:
[1]沈从文《边城》[M]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7月
[2]刘一友《评一曲谈了五十年的论调》[M]《沈从文研究》1988年8月26-28
[3]匿名《湘西沿革》[Z]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区政府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