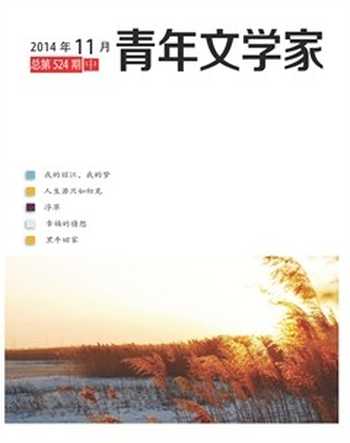从文学视域中透视沈从文如何看鲁迅
吴丹
摘 要:考察沈从文论及鲁迅的文字,其对鲁迅的评价主要在两个向度上进行,而且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形态:其对鲁迅的小说与散文创作,包括其早期诗歌创作则大体持肯定态度,而对鲁迅的杂文创作和人格气度却持否定态度。因而,可以从中检索出两位文学大家在文学观念上的歧异和冲撞。
关键词:沈从文;鲁迅;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32-0-02
沈从文是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原名沈岳焕,生于荒僻神秘的湘西凤凰县。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于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直至三十年代起勾勒出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了一系列诸如《边城》、《长河》之类的代表作。从作品到理论的“湘西系列”,以乡村生命形态的美丽对照物城市生命形态,这种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独有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因而,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
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了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时逐步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也正因为这样,奠定了沈从文对于同时代的作家鲁迅抱有一种复杂的态度。我们可以从文学层面来考证,沈从文与鲁迅的关系是复杂的,其视阈下呈现的鲁迅也是复杂的。沈从文是以双重角色来评价鲁迅的:当他作为批评家时,其对鲁迅的评价不失公允;而站在社会和现实层面,其对思想家和战士的鲁迅并不以为然,甚至较为刻薄。这种复杂的态度,既源自于沈从文与鲁迅文学观念层面的差异,同时也彰显了二者文学创作态度方面的分歧。
一、对于作品的复杂态度源于隔膜或认同
沈从文对鲁迅的态度是复杂的,首先体现在其与鲁迅在社会、人生层面的或隔膜或认同。在沈从文的社会辞海与人生辞典里,“鲁迅”一词似乎总是自然地带有不认同甚至是讽刺的色调,但有时其中言辞所潜隐的意味,似乎又显现出游离的复杂。沈从文在1929年所写的《一个天才的通信》中,有对鲁迅刻薄的讽刺。而在1930年2月发表的小说《血》中曾提到认为鲁迅这个人,“也不过是呆子之一” 。在小说中还提到“从血管里出来的才是血”, 也不过是“呆话”。在沈从文的惯用词汇中,“官”是贬义词,而“呆子”、“呆话”则是褒义词,因此,笔者认为此处沈从文的笔调中戏谑的意味更浓重一些,揶揄的同时又不无认同感,进而呈现出的则是其对鲁迅的一种复杂态度。而这也正是较长一段时间里,沈从文对鲁迅评价的一种定位和基调。
沈从文对文坛纷争和人事纠结一向非常厌恶,这成为他一贯的态度,因此,在人事纠结事务中神经较为敏感的鲁迅以及鲁迅的一些个性化的行为和反映则是沈从文所不能认同的。沈从文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一文中曾经谈到左翼作家的内部论争,并非常反感。在1933年发生于鲁迅和施蛰存之间的“《庄子》与《文选》”之争中,沈从文同样表现出这种反感情绪。在致信中,沈从文劝慰施蛰存:“关于与鲁迅先生争辩事,弟以为兄不必再在作文道及。……何必使主张在无味争辩中获胜。”之后,在致施蛰存的另一封信中也曾说道: “中国似乎还需要一群能埋头苦干写小说的人,目前同政治离稍远一点,有主张也把主张放在作品里,不放在作品以外的东西上,这种作品所主张的所解释的,一定比杂论影响来得大来得远。”「1」由此可以看到沈从文的文学主张。而这,也就可以理解沈从文为何会在《文学者的态度》等文章中指责海派的“白相文学态度”。鲁迅曾把那种采用欺诈哄骗等不诚实手段谋生称作“吃白相饭”。而沈从文则将文学商业化、文学政治化的文学状况及创作态度称为“白相文学态度”。与此同时,在指责海派作家时,沈从文凸显了自己的观点,即认为鲁迅并不会被人误认为海派,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沈从文还是比较认同鲁迅的文学态度的。
而从鲁迅逝世后沈从文的反应中,我们也可以洞悉出,沈从文对于鲁迅的伟大心存异议。1936年10月,鲁迅的逝世在中国文化界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文学界出现了万千纪念文章。而沈从文直到1937年7月发表《再谈差不多》一文,才提到此事:“最好的回答倒是鲁迅先生的死,被许多人称为‘中国最伟大人物。伟大何在?都说他性格、思想、文章比一切作家都深刻。‘比一切作家都深刻,这是从万千纪念文章中抽出的结论!倘若话是可靠的,那鲁迅先生却是个从各方面表现度越流俗最切实的一位。倘若话是不可靠的,那一切纪念文章都说错了,把魯迅先生的伟大估错了。”而在这之前的1936年10月,其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中,直指文学创作界的“差不多”现象,进而引起强烈反响,形成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反差不多运动”。尽管沈从文提倡作家“走鲁迅那么一条比一切深刻的路”,但他显然对“万千纪念文章”持保留态度,因为在他看来,鲁迅并不属于中国最伟大的人物。
二、文学研究存在独到性和主观性的交织并存
沈从文对鲁迅的文学作品进行的文学批评式的研究性评价则是具有独到性和主观性相交织的复杂特点的。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沈从文对鲁迅的文学评价是到武汉大学任教以后开始的。由于教学工作的关系,沈从文写过大量评论文章,并于1934年结集为《沫沫集》。在这其中多有涉及鲁迅之处,比如在《论施蛰存与罗黑芷》一文中,沈从文认为,“以被都市物质文明毁灭的中国中部城镇乡村人物作模范,用略带嘲弄的悲悯的画笔,涂上鲜明准确的颜色,调子美丽悦目,而显出的人物姿态又不免使人发笑,是鲁迅先生的作品独造处。”应该说,此处的评价是带有鲜明个性化特征的印象式批评,其中也的确窥探到了鲁迅部分小说的深邃处,即鲁迅小说中复杂的矛盾冲突状态。而且于其中,沈从文高度评价鲁迅的乡土小说,认为它“于江南风物,农村静穆和平,作抒情的幻想”和“表现的亲切”,然而,却也许因其对鲁迅的复杂态度而导致他放弃去解析和透视鲁迅笔下那深沉的民族生存忧虑感和强烈的批判意识。
此外,沈从文一直把鲁迅的乡土小说视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源头,其曾多次公开承认其“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对自身的启蒙和启迪,并也坦陈自己受到鲁迅的影响。《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是一篇回顾新文学运动进程中小说创作情况的文章,在这当中,沈从文再次肯定了鲁迅对于现代乡土小说的贡献,且从四个层面上对鲁迅进行了个人性评价和猜想。而另一方面,沈从文大肆强调鲁迅小说的颓废厌世与伤感悲观色彩,而对鲁迅小说“忠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与肉来” 「2」的现实主义精神置若罔视,却把这现实战斗精神看作是“辱骂一切,嘲笑一切”和 “陷到无以自拔的沉闷里去”的虚无主义心态。在文章最后,沈从文几乎一笔抹杀讽刺诙谐手法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可以说,沈从文此时对讽刺诙谐手法具有偏见性的否定。然而当其在进行《绅士的太太》、《八骏图》、《某夫妇》、《大小阮》等城市知识阶层题材的小说创作时,对于城市知识社会道德沦丧、人性堕落的揭露,其中或夹杂或饱蘸的讽刺的笔墨又不自觉地靠近了鲁迅,走向了“讽刺”。
沈从文对于鲁迅小说的评价体现出一种复杂的状态,有称赞有隔膜,而对于鲁迅的杂文却多半是持否定态度的。如在《鲁迅的战斗》一文中。文章从三个方面于嘲讽中消解着鲁迅杂文的现实战斗意义:其一,他赋予“战士”、“战斗”等词语以强烈的讽刺意味,并据此概括鲁迅的战斗是“辱骂”,“是毫无危险的袭击,是很方便的法术。”「3」其二,他分析了鲁迅杂文创作的动因,并把它归结为是对衰老与死亡的恐惧,对寂寞的无可忍耐造成了鲁迅异常强烈的复仇感和愤懑情绪,从而获得心灵上的快慰与解脱。其三,全盘否定鲁迅杂文的价值和现实意义,认为鲁迅的杂文创作都只关乎“意气”和“趣味”。
之所以沈从文对于鲁迅杂文及其战斗风格持全盘否定态度,笔者以为或许与其当时对待杂文的态度相关联。因为在沈从文看来,“写杂论自然一时节可以热闹些,但毫无用处”「4」。而讽刺手法则是“使许多作品用小丑神气存在”「5」,“除非是个病人,就不会成天在非常讽刺人中讨生活的。”「6」此外,他还非常梵高所谓的“战士”,认为只有“与抄抄撮撮的杂感离远,与装模作样的战士离远”,才能“与那个‘艺术接近” 「7」。但即便如此看待杂文,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沈从文也逐步认识到杂文对于“国家重造”的功用,因此在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也写过不少的杂文。
除此之外,沈从文也曾关注到鲁迅在诗歌层面的影响。在1935年11月发表的《新诗的旧帐》中,把鲁迅列入了新文学运动时新诗运动先驱者的行列,认为正是周作人、鲁迅、钱玄同、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被称为文化先驱的新人,在五四前后常常写新诗,才使“新诗能引起特别注意”,“可算做是奠定中国新诗基础的功臣,值得我们记忆”。
沈从文以自己独特的文学观为起点,秉持文学独立与纯正的审美意趣,因而使得其在评价鲁迅的时候,一方面能较为精准地把握鲁迅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又视而不见鲁迅气质上的现实战斗精神和思想锋芒。同时,这种矛盾的评价呈现也只有從评价者个体维度寻求原因才是最合理的,也是最有说服力的。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新废邮存底》,《沈从文文集》,第12卷,第17页,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2]鲁迅:《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241页。
[3]沈从文:《沈从文批评文集》第180页,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4]沈从文:《新废邮存底》,《沈从文文集》,第12卷,第25页,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5]沈从文:《新废邮存底》,《沈从文文集》第12卷,第17页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6]沈从文:《职业与事业》,《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358页,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7]沈从文:《短篇小说》,《沈从文文集》第12卷,第119页,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