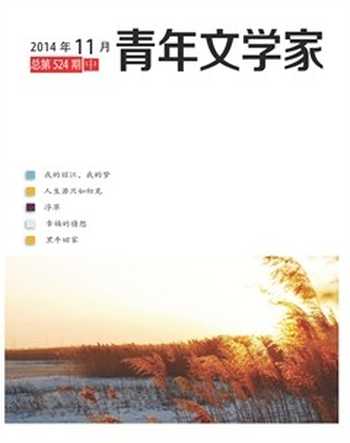近代小说“新闻化”的内在动因
摘 要:关于近代小说“新闻化”现象的研究,已有不少学人做出贡献,而近代小说“新闻化”的成因分析也多有建树,但多侧重在时代风潮、技术革命等方面。本文将从中国传统小说自身的特质,来探讨近代小说“新闻化”的内在动因。小说从古代社会发展至近代,具有“新闻化”特征的“实录”与“教化功用”,并不是仅仅来源于近代社会风云突变的各个方面的影响,而是传统小说中早已孕育着的因素。
关键词:近代小说;新闻化;内在动因
作者简介:龙桥波,1987年生,女,漢族,籍贯:成都,毕业于四川大学,就职于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32-0-02
1992年出版的《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一书中,作者袁进指出近代“新小说”作品有“文章化”和“新闻化”的倾向。“新闻化”是近代小说不同于中国古代传统小说,也区别于现代小说的一种特点,此前已有不少学人对这一特殊文学现象进行了研究,关于近代小说“新闻化”的成因分析也多有建树,但多侧重在时代风潮、技术革命等方面。本文将从中国传统小说自身的特质,来探讨近代小说“新闻化”的内在动因。小说从古代社会发展至近代,具有“新闻化”特征的“实录”与“教化功用”,并不是仅仅来源于近代社会风云突变的各个方面的影响,而是传统小说中早已孕育着的因素。
一、基于事实的创作,古已有之
《世说新语》中记载:庾道季诧谢公曰:“裴郎云:‘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裴郎又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儁逸。”谢公云:“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庾意甚不以为好,因陈东亭经酒垆下赋。读毕,都不下赏裁,直云:‘君乃复作裴氏学。于此,《语林》遂废。”
南朝梁刘孝标注这段故事,引《续晋阳秋》云:“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时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后说太傅事不实……自是众咸鄙其事矣”。
东晋裴启的《语林》,是一部品评当时知名人物语录的书,由于《语林》的标新立异,为时人追捧,甚至形成风靡一时的“裴氏学”。但这部书却因为所记的谢太傅谢安的语录,遭到谢安本人的否认,被认为“太傅事不实”,而“众咸鄙其事”,可见当时对小说 “实录” 的追求。
无论作品是否全为事实,小说家至少都会强调自己的作品有根有据。东晋干宝撰《搜神记》,本多记民间神话传说中的鬼神之事,但作者却在序言中说:“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可见,干宝是以史学家“实证”的态度,将“鬼神之事”作为真实来记述的。
小说发展至唐代,始开白话小说先河,而以搜奇记逸闻名的唐传奇,也有实录之作。如唐传奇代表作品《李娃传》,文末作者白行简就道出了自己做这个故事的渊源:“予伯祖尝牧晋州,转户部,为水陆运使。三任皆与生为代,故谙群其事。贞元中,予与陇西李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附掌竦听,命予为传。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引文中所说的“生”即是《李娃传》中的男主人公,“三任皆与生为代,故谙群其事”,可知小说故事来源于发生在作者身边的真实故事,基本为事实。
明代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的序言中说:“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作者抨击时人多爱鬼怪小说,认为小说应把注意力放到日常生活中来,刻画普通琐碎的真实生活,也大有可为。
“睡乡居士”为又一拟话本短篇小说集《二刻拍案惊奇》作序说:“今之小说之行世者,无虑百种。然而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奇之为奇,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舍目前可纪之事,而驰骛于不论不议之乡,如画家之不图犬马而图鬼魅者,曰:‘吾以骇听而止耳。……即如《西游》一记,怪诞不经,读者皆知其谬;然据其所载,师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动止,试摘取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摸索,亦知其出自何人,则正以幻中有真,乃为传神阿堵。”
这一段话,认为小说“失真”是“病”,而大赞《西游记》的“幻中有真”。接着,“睡乡居士”还指出,凌蒙初的《二刻拍案惊奇》“其所捃摭,大多真切可据”,强调、宣扬作品中的“实录”成分。
《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史》一书提及:“中国古代小说早期创作十分注重语出有凭、事出有据。小说家一般不敢凭自己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虚构结撰作品,而更多是借前朝或前辈的事件创作,于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可见,“实录”在传统小说的创作观念中早就存在,近代小说求实求真,反映当时当世的社会现实,也不过是继承了这种传统观念。
二、舆论教化的功用,古已有之
文学发展至明清,传统的文学主流——诗文——走向衰落,小说作品开始大量产生,并在民间以传阅、传抄或演绎、说唱的形式,得到大众的青睐。《金瓶梅》、《红楼梦》等作品的诞生,更在宣誓着小说更多的可能性,定位着小说全新的高度。而近代小说则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由“大众之爱”,走上了“精英之旗”的发展道路,不少仁人志士、学者文人开始关注小说、肯定小说,并致力于小说创作,甚至创办专刊小说的杂志。自然而然地,小说的地位被抬升至了空前的高度,走出“小道”的低等定位,开始继承传统诗文“经世致用”的严肃使命。
而事实上,小说这种针砭时弊、引导风气的功用,古已有之,历代批评家都在强调小说的“功能性”:
对于“稗官”,颜师古引如淳之话,注为“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者,使称说之。”可见,最初搜集这种街谈巷语的目的,亦是为君王知晓民情来服务的,相当于君王治理国家的资料依据及舆论参考。虽然班固引述孔子的话,认为小说是“小道”,“刍荛狂夫之议”,甚至还将其放在低于其他九家的地位:“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小说家的存在,是带有功利目的性的,是为政治服务的。虽然《汉书·艺文志》的“小说”概念与后世小说大有不同,然而这种强调政治舆论功能的思维方式,影响深远,也是孕育出白话小说的文化土壤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者十分明确,自己是为“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迎合“春秋之义”,才创作这篇小说的。强调的是小说的舆论教化功能。
再如白行简《李娃传》开篇便说:“汧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倡女也。节行瑰奇,有足称者。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传述。”
近代小说发端之前,明清小说已然蔚为大观,佳作频出。而这个时期的小说,仍然没有摆脱《汉书·艺文志》中的思维方式,还是力图在寻求小说的功用。
与金圣叹认为《水浒传》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的娱乐之作的看法不同,明代李贽撰评点《水浒传》的《读<忠义水浒全传>序》,指出“《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将《水浒传》的创作动机,与古代先贤韩非子进行类比,还进一步指出读《水浒传》的政治社会功用:“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日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日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否则,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腹心。乌乎在?在水浒。此传之所为发愤矣。”
终上所述,这种自小说发端就已根植的特征,已经渐渐深植于小说之中,成为中国小说倡导的特质。而中国小说这样一种特质,刚好迎合了时代需要,也与新闻的特征不谋而合,于是小说在近代一变,更全面、更典型、更深刻地呈现出了成熟的“新闻化”特征。这是近代小说会发生“新闻化”的内在性的、根本性的渊源及动力。没有中国小说自身的特质,就没有近代小说“新闻化”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6月版;
[2]刘义庆《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1月版;
[3]干宝《搜神记》,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年9月版;
[4]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第十第四百八十四》,中华书局,1961年9月新1版;
[5]凌濛初编著《初刻拍案惊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版;
[6]凌濛初编著《二刻拍案惊奇》,陈迩东、郭隽杰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