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给不出答案
田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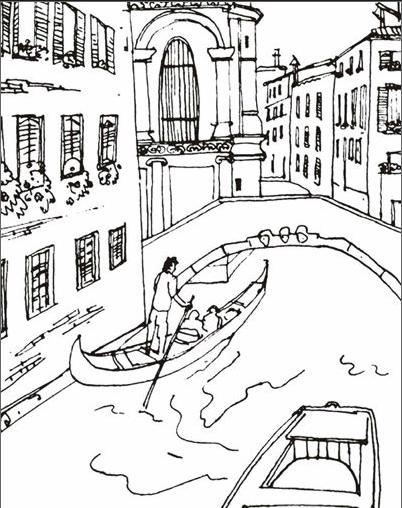
谁都猜不透一条河有着怎样的秘密?
这么多年,它一直在村庄里。最初的时候,我并没想过一条河会有什么样的秘密。至于为什么会突然想去打探一条河的秘密,我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总觉得有些事情必须弄清楚。我准备向河流开口。
走到河边的时候,我却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在河流的入口,一小股河水慢悠悠地流淌着,像一些少不更事的孩子,它们连奔跑都没有学会,能说出什么有价值的秘密?河流的中间位置又太宽广,我的一只手放在水里,就像一粒沙子扔到了大海,我问它们一句,连个回音都没有,更别说得到秘密。
我守在河流的底部,打算把秘密堵在出口。但是,水流出来的时候,我慌了神,不知道哪一滴或者哪一股水里有秘密。其实,对于河流本身来说,我连它的长相都没搞清楚,想要得到秘密,难度可想而知。
于是,我想到岸,或许它能给我答案。从一开始,岸就一直陪着河流,常年和河流在一起,岸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就是河流的管理者。既然如此,河流有什么样的秘密,岸应该最清楚。
但是河流从形成那一天,就有自己宏大的理想:冲破一切阻碍,奔向大海。在它们朝着理想前进的过程中,它一直将岸视作桎梏。也就是说,河流并没有将它看作领导者。
为了打败岸,河流使出浑身解数。它们东突西破,将岸冲出一道道的豁口,不过河流每进一步,岸都会如影随形。河流受够了岸的束缚,便派使者水汽与雨水合谋,决心与岸决一死战。
在一个秋天的午后,雨水如期而至,看到援兵,河流早已按捺不住自己,开始膨胀、上升。没有多久,它便冲破河的岸堤,越过村庄,把房屋连根拔起,把人逼到村庄的高处……
一切都被打乱,河与岸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岸上的东西变成了河里的,生活在岸边的人,变成了生活在山上的人。他们与水为伴,但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邻居会突然来这么一出。
现在,整个村庄都成了河流的河床,树只剩下顶部,农具和庄稼以及来不及逃跑的牲畜们,漂在水上。它们是河流逆袭的牺牲品,但绝不会是战利品,河流从来就没有真正胜利过。
河流回头一看,身后全是水的子民,它自以为胜利了,准备宣布主权时,抬头却发现岸还在眼前。其实,河流曾经很多次悄无声息地浸没岸,并且占领了一个又一个村庄,但是最后,总会有新的岸等着它们。即使汇集到了大海,河流也始终没有脱逃过岸的手掌心。
和岸斗了一路,又败了一路,河流不死心,但是又无能为力,它整天郁郁寡欢,心思越来越难以捉摸。从山谷里出来的时候,它像女王一样傲慢,一路有众多的水的子民追随,但是当它集荣华与大气于一身的时候,却还是得不到岸的宠幸,别说河流,给谁心里也不会舒服。
河流开始与岸势不两立。后来,它试图用绕指柔瓦解岸的钢铁之心,便主动靠近岸,并提出要握手言和。岸既往不咎,对河流保持了一个管理者的大度和姿态。即便如此,过往的纠葛,也不可能让河流对岸亲密到连秘密都没有。
其实,做惯了统治者的岸,对河流的所谓秘密一直很不屑,它甚至对河流也视而不见,不管河流忧伤还是高兴,岸只对水面之上以及自身之上的东西保持兴趣。因此,想从岸那里得到河流的秘密,要比从河流本身得到还难。
岸对河流的冷漠,被豁口看在眼里。处于河流与岸之间的过渡地带,豁口对自己的身份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但是很明显,它的出生与水有关,它们是河床的一部分。这些被河流冲刷出来的豁口,知道河流的坚持和沮丧,但是对于河流的秘密却一无所知。
但是,趁岸不注意,河流有时候会悄悄地和豁口、河床联合起来搞一次策反。如果成功,此前压制河流的岸就变成了河床,被河流压在身下;如果计谋被识破,河流便会知趣地一走了之,于是,此前参与策反的河床和豁口,被岸遗弃,它们既不靠岸又不靠河,裸露在阳光下,时间一长就变成了路。
有了前车之鉴,豁口和河床明显乖巧了很多。经过认真反思,它们决定跟随河流,河流到哪里,哪里就有它们的容身之处。而为了考验河床,河流用尽手段,冲刷、泥沙堆积、漩涡……于是,河床变得千疮百孔,被恩宠的地方,宽阔笔直;被嫌弃的地方,坑坑洼洼,身上带着一条条的划痕。而豁口,最终被泥沙填满,成了河床的一部分。
河床经受住了考验,哪怕是被遗弃,它们也一直等在原地。后来,河流接纳了河床,让它们扶持自己完成理想。与河流待在一起,它们多多少少知道点什么,但是为了证明忠诚,河床一直替河流保守着秘密。它们每天扶持着河水,河流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虽然有时候也暗流涌动,但是从来没有出过格。现在,它们是河流彻彻底底的追随者,你会指望一群没有骨气的奴隶泄露什么样的秘密?
河流处理好与岸以及河床的关系之后,开始经营自己的内部。它召集到一众的水草、鱼和蛙类。像一个母亲一样,用氧气和阳光喂养它们,水草、鱼和蛙类长大后,又开始喂养自己的子民,一代代繁衍生息,让河流的内部变得生动起来。
兴许,河流内部的这些物种能提供一点关于秘密的蛛丝马迹。于是,我便开始琢磨着和水草、鱼以及蛙类对话。遗憾的是,浸润在河流里时间太久,水草已经熟悉地掌握了河流的内心,它熟悉自己主人的脾气,因此对我的打探圆滑而巧妙地予以了拒绝。青蛙由于带着祖先给的性格,一直游走在河流与岸之间,它没办法确定自己到底是河流的忠诚者还是叛徒,因此,对我的提问避而不谈,呱呱地卖弄着自己的嗓音。
如果说河床掌握着水的半斤八两,那么鱼就熟知河水的深浅。我很早就羡慕一条鱼,能时时刻刻待在水里,永远属于河流。而河流又把那么多的秘密都告诉了鱼,有时候我在想,那一串串的泡泡里,会不会有河流的秘密?
但是,要命的是,为了让鱼保持对自己的忠心,河流给了鱼一个离开水就必须死的信条。为了活命,鱼学会了守口如瓶。别看它每天都吐出无数的泡泡,没有一个是和秘密有关的。我理解鱼的处境,决定不为难它们。
树想打探河流的秘密,就把根伸进了水里。结果,树的半个身子枯萎,叶子还不到落的时候就全部落到了水里。刚开始,树以为是叶子背叛了它,最后才发现,是水用自己的方式,将树的阴谋揭穿,并予以回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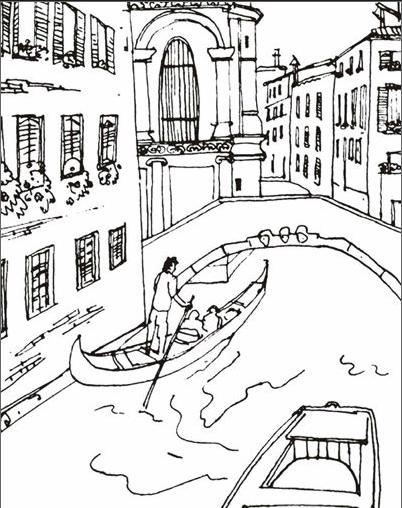
为了保全自己,树全身而退,守在河边。但是,树再也不敢琢磨河流的秘密了,它不想以生命为代价了解一条河虚无缥缈的秘密。从水里回来之后,树对水敬而远之,因为心里有一份敬畏,久而久之树还成了水的追随者。你看,现在树连自己的模样都改变了,一条条树枝就像一条条细小的河流一样,脉络清晰。
芦苇本来生长在山上,因为好奇,它也想知道一些关于河流的秘密。于是,它们结伴来到河边,准备打探消息,但是刚一入水,就被河流收买。它们发现,河流有深厚的泥土和足够的水分供它们吃喝玩乐。它们有去无回,也因此给生活在山上的芦苇留下了把柄。为此,水里的芦苇一直抬不起头,甚至连头发都愁白了,一到秋天,就早早地枯萎扬花,然后躲在冰面上暗自伤神。最后,它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借助水让自己长高长粗,以示和山上的芦苇有别。从它们长大的那天起,旱地芦苇便与水生芦苇老死不相往来。
这样一个连自己的祖宗都能背弃的物种,怎么会得到河流的宠信从而知道其秘密呢?你看它们,像竹子又没有节;中空,又底气不足。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它们是河流专门安排在某个地方以监视地面上的一切,一有风吹草动,它们便会摇摆起来,把情报传递给河流。我要是向它打探消息,不是自我暴露吗?
有一天,一只水鸟引起了我的注意。眼看着它从天空中掉了下来,但是快到水面上的时候,它迅疾地翻了个身,同时将喙伸进了水里。它叼起什么东西之后,又很快消失不见了。水鸟应该能帮我找到答案,它不依附于河流,并且能迅速地从水里带走东西,让它找秘密,是最合适不过。不过,遗憾的是,一个上午,我都没看清这只鸟长什么样子,更别说跟它谈合作的事情。
为了寻找河流的秘密,我整天琢磨岸、河床和水生植物,就这么错过了童年。有一天当我面对河流的时候,被眼前的那个人吓了一跳。鼻子之下竟然有一些乱糟糟的不明植被,黑,掺杂着黄。我开始恐慌起来,它们是从哪来的?叫什么?到我的嘴上要干什么?难道是河流知道了我的行踪要报复我?
是镜子启发了我,当我站在一面镜子面前时,才确认那些不明植被是从我的内部长出来的,并不是河流在作祟。后来,大人们告诉我,不明植被叫胡须,是长大的表现,我才放下对河流的警惕,开始重新寻找河流的秘密。
河流不也是一面镜子吗?它能照出我的样子,就能照出树的样子,芦苇的样子,时间一长,它熟练地掌握了应付一切的本领。水鸟飞过,河面上便有一只一模一样的鸟,这时候,我看到的秘密或许就是一只鸟的秘密;白云飘过,河面变成了另一片天空,我看到的秘密就是白云野鹤蓝天的秘密。我即便是通过水中或水上的东西找到河流的秘密,不一定就是河流自己的秘密,我决定转移视线。
人被河流折腾过几次之后,开始意识到水的重要性。其实,最初的时候,河流是在没有人的地方前进的,它们遇到山会拐弯,遇到人也一样,它们不想与用两条腿丈量世界的人为伍,河流喜欢全身心扑在大地上的物种。是人将自己的居住地定在河边的,也就是说,河水没有选择余地,只能被人所依靠,所利用。
有了人便有了村庄,而水就自然地被人当作村庄的一部分。河流为此做出过努力,但是不管它怎样改道,居民们就是喜欢沿河而居。在河流的眼里,人和岸一样难以对付,并且人和岸要是联合在一起,河流就没有好日子了。于是,河流开始习惯居民。
村庄里有人学会了打鱼,他们用绳子结网,用木头做成船,划着船到他们以为有鱼的地方。下网,然后是漫长的等待,网被打上来的时候,运气好点,会有几条小鱼,一只破鞋什么的,运气不好的话,连水都捞不上来。
我突然有了用渔网打捞秘密的想法。如果河流有秘密的话,一定是漂浮在水中的,一网下去,是不是能多多少少捞上来一些?于是,我划着小船,将网撒到河的中央,等待的过程中,我设计了几套与秘密见面时的表情。比如:惊讶。如果真的捞上秘密,这个表情应该是恰当的,并且能准确描述我当时的心情;比如:平静,面对我苦苦寻觅多时的河流的秘密,我是不是应该矜持一些,至少不能让它看出我的急切,即便是秘密,它也是平常之物,谁还没有个秘密呢?比如:微笑。水知道答案,我要了解它,是不是应该给它一个微笑呢?
在所有的表情里,我单单没有准备沮丧,但事实是,它不期而遇。当网被捞上来时,我悬着的心一下子就掉进了水里,网里除了水,空空如也。几次三番,情况照旧。
在村庄里待久了,河流就有了人的脾气。深沉、隐忍、圆滑、狡诈……人有的性格特征河流都有,但是河流有的,人不一定有。比如,它会很快干枯消失,又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原状。人不行,人一但干枯了,就只能成为一抔土。
有一年夏天,村庄像是要被烤熟了,村庄里的井抛弃了所有的绳子和桶,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开始搬运河水,很快,河流也露出丑陋的底部,变成一汪浅浅的池塘。
池塘水面混浊,像一个绝望的女人流干了泪的眼睛。这时候,石轱辘露了出来、半个菜坛子露了出来、一只旧鞋露了出来……人们发现,已经消失好多年的东西,躲过众人的目光,竟然一直藏在河流里。不过,它们终究躲不过时间,你看,它们身上的臃肿一点都没有遮挡住沧桑。
就在大家争相认领走失已久的旧物件时,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这些老物件一直和水在一起,它们有没有发现河流的秘密?我的一厢情愿没有得到任何回应,那些在阳光下暴晒了几天的老物件,还来不及被带走,就皴裂、风化,然后和干涸的淤泥一起,变成尘土。
为了不让自己暴露,河流最终选择牺牲自己。于是,那一汪池塘也消失了,河流把所有追随者都抛弃了,带着它的秘密不知所终。我站在干裂的河床上,两眼空空,为自己没有抓住机会而沮丧。
秋天来了。几场雨,就让河流变得丰腴起来。居民们也从干涸里回过神来,开始享受一年中最美好的时节。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庆祝丰收,并在墒情不错的土地上播种。
人们只关心粮食和土地,几乎忘记了河流的存在,但是河流一直惦记着他们。它悄悄地恢复到此前的样子,并且甚至比此前要宽阔,要深邃。它神秘地消失之后,像是获得了无限的能量,再一次成为众多追随者的女王。每隔几年,它都会用干涸和丰腴告诫居民,既然选择河流,就必须重视它。但是,人们真的把河流遗忘了,直到有人被河流带走。
一个早晨,有人发现,河面上有一株黑色的植物,蓬松但似乎无根。起初,这株植物并没引起人的注意,最后是一阵哭声,将人们的视线转移到了河流之上。最后被证实,一个可怜的男人被人扔进了河里,河流对此来者不拒带走了他。
河流或许是被漠视太久了,才带走了这个可怜的男人,但是,用如此方式引起人关注,这代价未免太大。人们开始恐慌,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抵抗。神秘的摇铃人对着河面嘴里说着只有自己能听懂的话语,牲畜们再次出现在河面上,不过它们不是被淹死的,是居民们专门宰杀之后,披红挂彩送来的。
大人们用牲畜抵消内心恐惧的空当,我有了大胆的猜想:这个可怜的男人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是否与河水交换过秘密?他是不是第一个知道河流秘密的人?但是,想从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嘴里得到答案,远比从河流自身拿到标准答案要难得多。
带走这个可怜的男人之后,河流没有一点愧疚,它领受了居民们的馈赠,但是对摇铃人以及他嘴里的话语置之不理。接下来的时间里,还会不断有人出现在河流里,他们有的是自愿的,有些是毫不知情就被带走的。他们可能是为数不多的知道河流秘密的人,但是他们永远都不会开口。
河流时而干枯,时而丰腴;时而平静,又时而暴戾恣睢;时而与人为善,又时而向人下手。它越是变化多端,我就越想知道关于它的秘密和真相。既然岸、河床、水、芦苇以及鱼都不给出答案,那我就亲自到河流中看看。
这是我做了很久的一个决定,在下水前,我观察了好几天,排除了会被河流带走等种种可能之后,一个下午,我把自己脱光,一头扎进了平静的河面。
河流把我紧紧地抱住。河水温度适中,浸泡在水中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子宫,那个我已经无法再回去的地方,有着河流一般的温度。它的味道和河流的味道相似。我就像个婴儿,躲在温暖的子宫里,小心翼翼地,用手和脚划拉着。
涟漪一圈一圈向岸边荡去,我把自己彻底没在了水中。睁开双眼,我已经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了。我不确定这里和子宫内部有什么相似或者区别,但是总感觉似曾相识,却又说不上在哪见过。河流的内部清澈宁静,光打到水里时,漶漫而又有规则。我不认识的水草,随着水波摇曳,一听到动静,鱼迅速地钻进草丛中。
我有点不知所措。进入河流的内部却不知道从何下手去打探它的秘密。我开始恍惚,开始有幻觉。我像一条鱼一样,不停地冒着泡泡。还来不及开口,水已经进入我的腹腔,整个身体也开始下沉。我踩在河床上,猛一下子钻出水面。河流像个阴谋得逞的人,用波纹将笑声传到很远。
我落荒而逃,从此离开村庄。但是,对于河流的秘密,一直保持着兴趣。多年以后,当我带着理论和帮手回到村庄准备对河流再次下手的时候,我被眼前的场景怔住了:河流呆滞无光,河面上堆积着大量的破鞋,塑料纸袋,河床发黑,散发着阵阵恶臭……
岸和河床已经分不清彼此,黑乎乎一片;鱼剩下了骨头,再也吐不出气泡,来不及说出口的秘密就这么被带走;蛙类把自己藏进了土里,毕竟跟随河流这么多年,它选择用这种方式悼念河流;芦苇和树去向不明,只留着一些叶子,漂在水面上,毫无生机。
我不知道我走后的几年,河流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是它太过于寂寞,最终自甘堕落,还是与岸与居民搏斗,最后遍体鳞伤。我不愿意再多想了,眼前的这条河,还有必要兴师动众去了解它的秘密吗?看来,一条河就要带着自己的秘密终老一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