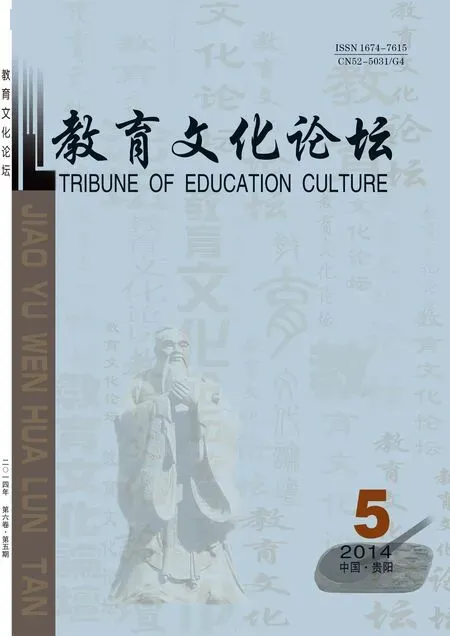甘南牧区藏族生态移民社会融入问题解析
王玉强 冯雪红
(北方民族大学,宁夏 银川 750021)
甘南牧区雄踞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甘南高原,地处长江、黄河上游,是青藏高原“中华水塔”的重要涵养地,包括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碌曲、玛曲、夏河、合作4个纯牧区县和卓尼、迭部2个半牧区县,属于典型的高寒牧区。2010 年甘南藏族自治州总人口 72.35 万人,包括藏族、汉族、回族、土族、撒拉族、满族等 24 个民族,其中藏族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54.0%,是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居住区[1]。然而,随着牧区人口急剧增加以及对畜产品需求的不断扩大,草地生态系统遭到掠夺性破坏,草地大面积退化,草场生产能力下降,水源涵养功能锐减。甘南牧区贫困人口占到牧民人口的84.7%,环境恶化和贫困是甘南牧区亟待解决的问题。2007 年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了《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对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实施全面的生态保护与建设, 其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实施生态移民、游牧民定居工程。甘南牧区53万农牧人口中以牧业为主的人口有28.7万,占农牧业总人口的一半还多。《规划》确定将安置游牧民14 524户、73 708人[2]。截止2009年生态移民规模达到4 171户21 274人,生态移民工程总投资达到2亿元。2012年底,甘南牧区尚有3 000多户、1.9万名牧民未实现定居[3]。经济发展还是主要依托资源禀赋,但生态环境的脆弱和出现的恶化趋势,使得民生问题、生态问题与民族问题交织叠加。[4]
近几年来,由于国家的大力支持,甘南牧区生态移民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使移民的数量增多,且迁出地生态的恢复、移民的就业、生态移民定居建设等方面都有了良好的发展。但在强调经济改善、基础设施完善的同时,从牧区迁出的生态移民在面对定居及城镇化过程中表现出的不适应也日渐显现。一些伴随着生态移民工程产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方面的变化使生态移民融入迁入地生活的节奏缓慢。尤其是生态移民作为相对弱势群体,在与当地已有群体相处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一、生态移民社会融入之困境
1.生产方式转变中出现的问题。甘南牧区的生态移民是以禁牧育草为前提的,按照生态移民工程建设内容的要求,项目实施区的牧民变卖了牲畜,离开了世代居住的草场,来到政府为他们修建的新居点,过上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这就意味着他们脱离了世代相传的高原畜牧业生产,原来的生产方式在生态移民迁入地己不复存在,成为历史。从牧业到农业的转变的是较为艰难的。一些生态移民变卖了自己的牛羊,拿起以前从来没用过的农具进行农事劳动。过去牧民家庭中劳动的分工是:男人掌管放牧、剪羊毛、宰牲畜、建围栏;女人负责挤奶、拾牛粪、做酸奶,所有的工作都围绕牛羊展开。如今,以放牧牛羊为主的牧业变成了以种植农作物为主且兼及商业的生计方式,一切生产技能都要从头学起,这对早已习惯牧业生产方式的牧民而言无疑是困难重重。一方面必然会带来资源的浪费和不合理使用,另一方面一些生态移民会产生文化震荡、文化断裂,在生计方式的选择上出现偏差。根据张家骝在玛曲县的调查,当问及“您当前家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96%的牧民认为是“经济困难”,4%的牧民认为“生活不适应”[5]。可见,由生产方式转变带来的无法就业的现象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困难仍是生态移民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些现实问题无疑会拉大生态移民与迁入地原有居民生产效率、生产效果以及生活水平的差距,不利于生态移民自身的生存和长远发展,而且给生态移民与迁入地原有居民的交往带来障碍,更不利于甘南牧区生态移民工程目标的实现和移民工程整体的顺利实施。
2.生活方式转变中出现的问题。生活方式是指在一定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生活价值观念等各种主客观条件制约下形成的人们创造和享用物质、精神财富及处理一切生活关系的活动形式与行为习惯的总和。生活方式是一个内涵十分广泛的复杂综合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指人们衣、食、住、行、休息、娱乐等日常生活方式。广义,除上述日常生活方式外,还包括劳动生活方式、精神文化生活方式等[6] (369)。在此,主要从狭义上讨论、了解藏族生态移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及遭遇的问题。首先,生态移民迁居城镇后,饮食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搬迁之前牧民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日常的饮食主要是牛羊肉、酥油茶、酸奶;搬迁之后,自家的牛羊卖了,却需要花费比卖出价格更多的钱去买肉吃,酸奶、酥油茶也被茶水和白开水取代。许多藏族家庭仍会坚持每餐食用肉类的习惯,那么日常开支就会增加,如果收入得不到相应的提高,家庭负担势必与日俱增,生活水平不升反降。其次,搬迁到城镇后,受城市生活的影响,过去穿藏袍、藏靴的藏民尤其是较年轻的藏民,纷纷改穿西装、运动鞋。住所从过去自家制作的可随时搬运的牛毛帐篷变成了砖混、固定的定居院落。这些生态移民似乎以一种情愿的或不情愿的方式成为了“现代人”。最后,藏族是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崇拜神山圣湖的宗教观念和重视藏族寺院的思想已深深注入到每一个藏族民众心中。生态移民工程大多是把生态移民迁移到较搬迁之前距离寺院更远的地区,这对于藏族教民来说无疑是生活方式的一大改变。与自己“精神家园”空间距离的拉大使一些生态移民去寺院和转山、转湖的成本增加,也导致一部分年龄稍大的藏民无法进行这些宗教活动。另外,年轻人尤其是第二代移民更多地接受了现代的生活方式,又因为这种距离感的增加,他们的生活已不单单是围绕世代相传的宗教而展开。这就使得年老的生态移民对于他们的这种“不重视传统”产生不满情绪,代际间的传承和交流出现问题。
3.思想观念转变中出现的问题。人们的生产活动以及居住环境与生产、生活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生产、生活观念。甘南牧区生态移民工程不仅改变了生态移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还进一步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观念。作为人类的一种重要思维定势的观念,由个人在判断分析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生存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伦理观念、功利观念等都是观念的具体形态[7] (120)。甘南牧区藏族生态移民,从自给自足的牧业生活转变到截然不同的市场经济生活,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转变与现代各种新型的思想观念共同深刻改变并影响着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态移民迁居城镇后,一时找不到好的就业方式,较多的空闲时间和微薄的收入,致使部分藏族移民抛却了原本优秀的传统观念,在利益的驱使下,发生偷盗、抢劫等不良行为,给社会带来危害。现在一些投机、不靠劳动也能致富的思想影响了淳朴的藏族移民,少数移民参与了赌博等违法活动。在一项对甘南牧区65户藏族牧民定居意愿的调查中显示,58.5%的牧民把“享受政府补贴”作为其集中定居的好处,而83.1%的牧民认为“缺乏文化技术”是其集中定居的障碍,78.5%的牧民觉得“缺乏就业门路”是他们定居中的问题[8]。当地政府实施的生态移民补贴和低保等政策,本来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民众就业和个人发展的举措,但是无法就业和较低的文化水平带来的生活困境却使一些生态移民产生消极的生活态度,过度依赖政府的补贴,削减了藏族人原本勤劳质朴的性格特点,“等、靠、要”的观念开始滋生。此外,文化传承与保护问题、学龄儿童入学入托问题、同当地他民族文化的调适与互动等问题,都或多或少对搬迁后移民的思想观念产生着冲击和影响。
二、生态移民社会融入问题之解析
在生态移民工程如火如荼进行的过程中,生态移民各方面发生的转变和由此带来的问题也不同程度地暴露出来,上述问题的出现,一方面为生态移民工程的后续实施提供了现实参考和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也印证了民族社会学范畴内社会融合理论等相关理论的科学性。社会融合理论为解释和分析生态移民在群体和个人两个层面试图融入当地社会时出现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且为此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和可供选择的有效解决途径。
1.从社会融合理论看生态移民社会融入出现的问题。社会融合是指具有不同性质的人、集团或民族接触以后合成新的文化单位的过程,是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进行的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目前较通行的解说是:“所谓社会融合,是指新移民在居住、就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进展程度可以用新移民与城市居民的同质化水平来衡量,城市居民和新移民将在共变中趋向接近并最终融为一体。”[9](197)作为一个社会政策概念,社会融合起源于欧洲学者对社会排斥的研究。由于被社会排斥的群体通常是脆弱群体,又往往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而且社会排斥常常表现为不同阶层之间的排斥与疏离,以及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因此,脆弱群体理论、社会分层理论、社会距离理论和社会排斥理论分别从不同角度为社会融合提供理论依据[10]。社会融合主要关注的是由原来的生存环境搬迁到另一个生存环境后,移民群体由于自身障碍或适应能力跟不上环境的变化节奏而出现的在现有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缺少应对变化的能力和群体的竞争能力。他们在新的环境下属于弱势的一方,在其自身发展以及与其他群体交往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脆弱性,但这种脆弱不是要被淘汰和排斥的,相反人们应当尊重和保护脆弱群体。社会融入于此,更强调缩小移民差距,为移民增权和鼓励移民和弱势群体的社会参与。[11]
从群体层面看,藏族生态移民作为当地人眼中的外来人口,难免会受到迁入地原有居民一定程度的排斥。在经济方面,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生态移民大多滞后于迁入地原有居民,加之民族身份、生活方式、文化差异的影响,使得迁入地原有居民面对生态移民时对自我群体认同感与日俱增,一些受功利思想影响的迁入地原有居民对生态移民产生了疏离,认为他们“没文化”,是“穷人”,抑或“暴发户”。从个体层面看,生态移民的交往也大多限于移民群体内部。根据桑才让关于“你亲密的朋友中迁入区和迁出区所占比例”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是100%的迁入城市的生态移民、90%迁入州县府所在地城镇的生态移民、80%迁入乡镇所在地的生态移民其回答是“原住地和本社区内的本民族”,在问及“你是否经常参加其他族群成员组织的私人聚会时”,100%迁入城市的生态移民、90%迁入州县府所在地城镇的生态移民、80%迁入乡镇所在地的生态移民,他们的回答是:“不经常参加”[12]。可见,作为脆弱群体的生态移民一旦得不到迁入地原有居民群体的理解和接纳,那么藏族同胞不但会被排除出城镇的日常活动和公共事务,作为个体的藏族和汉族之间的交往也会出现不和谐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解释生态移民闲暇时间用打麻将、玩电脑、打台球等来消磨时间,而不能很好地参与当地公共活动的现象。从社会融合理论看,笔者认为,脆弱群体社会融入的困境一部分是来自迁入地原有居民群体的区别对待,这种情况下社会融合理论强调对脆弱群体的保护和支持,在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上给予生态移民大量便利和帮助,不仅要从物质上支持生态移民,更要让生态移民享受到社会各方面的精神关怀。另外,脆弱群体是社会为了平稳运行而作出的社会安排,社会融合理论则强调脆弱群体本身在困境之下需要发挥自主能力,在一定的引导下完成自身潜力的挖掘,在自我发展的同时带动身边包括迁入地原有居民在内的社区居民共同完成致富的目标。藏族在畜牧养殖和培育方面有着优秀的传统和丰富的经验,生态移民应当发挥这一优势参与到当地养殖场的生产管理之中,这样不仅可实现自我价值而且也会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2.从社会距离理论看生态移民社会融入出现的问题。社会融合理论的另一理论基础是社会距离理论。目前学界普遍使用的“社会距离”概念主要来源于加布里尔·塔德。塔德在《模仿的规律》一书中首创了社会距离概念,并将其用于表征阶级差异。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帕克则发展了这一概念。帕克认为: “社会距离描述的是一种思想状态,是人们准备与他人在他们的关系中建立亲密关系的程度,是存在于个人与集团之间的亲近程度。”[13](257)“社会距离量表”是用来测量、比较不同的被试者对同一群体的社会距离的大小,也可以比较同一被试者对不同群体的社会距离的大小。社会距离的大小反应了两个群体间或两个个人间以及群体和个人间的亲疏程度。社会距离理论在应用中往往是和社会分层的理论相结合来进行分析的:处于不同社会阶层间的群体,社会距离都会比较大,群体间会比较疏远。处于相同社会阶层间的群体,社会距离比较小,群体间往往比较亲密。作为迁入者的生态移民在迁入城镇后由于职业、财富、声望方面与迁入地原有居民的差距,使得两者处于不同的层级,社会距离较大。加之,一方面生态移民群体与迁入地原有居民群体在交往中出现文化震荡和文化差异从而产生一定的自卑、孤独心理,多数生态移民不敢、不愿与当地人交流、合作;另一方面迁入地原有居民群体对生态移民群体不认同和排斥。这样,群体间的社会距离被不知不觉地拉大,如果是汉藏混居的生态移民社区,本来就缺乏了解的双方愈发疏远,藏族人和汉族人之间的交往也少之又少,汉族人不愿帮助藏族人在本地落脚,藏族人不愿在遇到困难时向汉族人求助,致使本来就很难适应当地生产、生活方式的生态移民在生存和发展方面遇到更大的难题。在举目无亲和孤立无援的困境下,一些生态移民产生“返回牧区”的想法,个别生态移民借助赌博、偷盗等投机行为勉强立足城镇,而另一些生态移民则消极心理严重,等待政府的补助成了他们维持生计的手段。
值得重视的是,社会距离过大的直接后果是分属各群体的个人相互的不理解乃至群体间的歧视甚至冲突。20世纪美国社会对黑人的歧视成为整个美国国家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就是最好的例证。社会距离理论的意义在于出现社会距离被拉大的情况下,及时制止社会距离的进一步扩大,并采取措施从两个群体间经济、心理等方面缩小这一差距。在笔者看来,社会距离理论在分析群体间关系方面能给予生态移民工程很好的理论借鉴,对于迁入地原有居民群体和生态移民群体间社会距离的扩大,应当从政府、社会团体等各个方面为这两个群体搭建缩短距离的“桥梁”。首先,政府应在群众间宣传互帮互助的邻里观念,积极推动社区间和社区内部的公共事务和公共活动,一定程度上淡化由民族身份产生的群体意识,增进生态移民群体与迁入地原有居民群体的相互理解,拉近他们的心理距离。其次,在生态移民定居安置上应更倾向于把生态移民定居在迁入地原有居民社区中,或在迁入地原有居民社区周围设立生态移民社区。这样一种空间距离的拉近会带来迁入地原有居民群体和生态移民群体间更多的互动和交流,由此社会距离也会相应地缩短。但是由于测量手段、问卷调查、操作化方面的原因,对于社会距离的测量在现今仍具有很大的难度和挑战性,国内对于社会距离测量的研究也不完全成熟,相信今后对于生态移民与迁入地原有居民间社会距离的研究会有更多的发展。
三、结 语
关于生态移民社会融入问题的解决,在经济生活方面政府需要占据主导地位,积极引导生态移民培养个人的职业技能,竭力帮助生态移民完成就业,大力扶持生态移民集体和个人的创业项目。还要加大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创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改善居民生活环境。使生态移民在生产、生活方式上更好地融入当地新的生活环境。在社会生活方面要以社会民间团体为主、政府机构为辅,大力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发动社会工作者对包括藏族居民在内的所有困难群众给予帮助,最重要的是给予精神和心理关怀,深入居民家中进行心理疏导的同时传播积极的生活态度,让汉族和藏族居民一起参加社区活动,促进汉藏群众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除此之外,政府应给予生态移民宗教文化事业大力支持,作为政府工作人员要通过学习认识到藏传佛教宣扬的“慈悲”“放生”“平等”的思想能与生态移民工程中的“生态观”“环境保护”等思想很好地契合,且发扬这种思想是有利于指导社会整体的生态改造和环保事业的发展。转变过去不主动接触宗教,对宗教敬而远之的态度。在这种思想的转变下,宗教文化事业就能得到全面的支持和推动。对此,提出几点具体措施。首先,在生态移民过重大民族节日时,可以在政府公告栏公告这一节日,让当地各族群众都了解藏族的这一节日;也可以把慰问生态移民困难群众的工作放在节日进行,一方面体现政府的关怀和对宗教节日的重视,另一方面在节日的良好气氛中促进政府和群众关系更加融洽。其次,对藏传佛教寺院的修缮和兴建,政府也应在资金和建造技术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一方面,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兴建的藏传佛教寺院传播了宗教思想,能够增强其他民族对于藏族同胞和其宗教信仰的进一步了解。另一方面,能解决一些生态移民搬迁后宗教生活上的不适应,守护了藏族同胞世代相传的“精神家园”。
[1] 王生,荣李巍.制度创新视角下的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城镇化问题研究——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J].生态经济,2014(3).
[2] 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网站:[EB/OL].http://www.gn.gansu.gov.cn/.
[3] 王文浩.甘肃省甘南州:保护修复生态系统稳步推进牧民定居[J].城乡建设,2009(6).
[4] 徐宁,赵金锁.西部民族地区限制开发区经济、发展方式形成机理分析[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35.
[5] 张家骝.甘南藏族牧民定居问题调查研究[D].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6]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编写组.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
[7] 马伟华.生态移民与文化调适:西北回族地区吊庄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8] 高永久,邓艾.藏族游牧民定居与新牧区建设-甘南藏族自治州调查报告[J].民族研究,2007(5).
[9] 童星.交往、适应与融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0] 黄匡时,嘎日达.社会融合理论研究综述[J].新视野,2010(6).
[11] 李吉和,常岚.穆斯林人口城市融入研究文献综述[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1).
[12] 桑才让.对三江源生态移民文化适应性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攀登,2011(6).
[13] Robert E.Park.Race and Culture[M].New York:The FreeP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