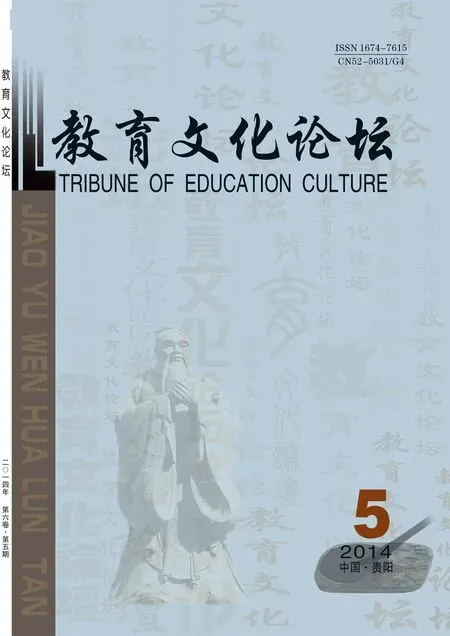款词文化变迁:兼论传统力量与侗族地区治理问题
梁宏信 张琪亚
(1.贵州民族大学 研究生院,贵州 贵阳 550025;2.贵州民族大学 科研处,贵州 贵阳 550025)
款规约的制定、宣传与实践依赖作为其语言载体的款词来完成,因此款词的传承与演变过程既反映着款规约的变迁史,同时也具体地反映着侗族社会款的变迁。在传统的侗族社会里,受汉文化和国家政治的直接影响,款词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可根据款词表达与保存形式,将其分为口头规约和文字规约两个阶段,由此来描述款词的传承与演变过程,以展示款词文化的各时代特征及其对侗族社会传统治理的直接影响。
一、款词文化的生成与实践
(一)款的形成与实践
聚居湘、黔、桂交界地带的侗人,由古代百越的骆越、西瓯支系发展而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没有发展形成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是处于一种氏族到国家的过渡阶段。正因侗民族的这种过渡性,在自然秩序与国家政治之间孕育了具有原始民主性质的地方性组织“款”,通过它邀集各村寨头人及族众共同议定“社区秩序”以推进和维系侗族社会的良性运行及协调发展。
款以村寨为基本单位,结构上分为大、中、小三个层次,是侗族社会特有社会组织形式。朱辅《溪蛮丛笑》中载:“当地蛮夷,彼此相结,歃血为盟,援急相救,名曰门款。”[1]和周去非《岭外代答》记:“款者誓也,今人谓中心之事为款,御事以情实为款。蛮夷效顺。以其中心实情,发其誓词,故曰款也。”[2]二者即是对侗族“门款”或“款”的详实介绍与解释,可以看出侗族的款是一种“歃血为盟”的地方联合性组织。
款滥觞于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或称军事联盟)时期[3],存在于侗族社会除其民族自身的“过渡性”因素外,还受惠于侗族地区长期地处在传统力量和国家政治的双重统治之下的这一外部条件:“一部分侗族地区已经纳入封建社会的统治轨道,而另外一部分侗族地区则仍然处在前阶级社会阶段,这是侗族款组织存在的基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才有所改变。”[4]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内,侗族社会受封建政治影响极少,因此在管理上更多依赖民间组织的“款”来完成。
清代末期、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后的这段时期,国家政治在侗族地区逐步被强化,款这种传统力量在社会管理中日渐“失意”。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配合、补充国家政治对侗族地区的管理,在这一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民间规约形式——村规民约或乡规民约,其承继了款制度的精髓,继续发挥传统力量对侗族社会的治理作用。
(二)款词:款规约的语言载体
在侗族社会里,款是建立在款规约基础之上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具有自治、自卫性质的民间组织”[5],款规约对款组织活动及款众行为具有直接的约束和规范作用;而具体的款规约又是款活动的产物:款众根据侗族社会生产及生活需要,共同协商、议定出相应的规范性条款且当众立石盟誓实施。所有参与盟誓的款众需严格按照款规约行事,任何人触犯都要被依款惩处。[6]其公布实施后,由款首在款坪或鼓楼内讲诵这类款规款约,为便于讲诵、记忆和产生互动效应,在其讲诵过程中添加了一些富有寓意且雅俗相间的词语,使之逐渐变成了一种口头文学样式,即称之为“款词”(Leix Kuant)。
因受早期社会生产力及侗族无文字等客观条件限制,原始款词是一种栽岩为誓的口头式盟约,无文字记录。参与立誓各方积极遵照盟约条款行事,款众彼此监督,促进社会秩序的有序性。而地方精英的款首们为了方便款众记忆以及款师讲诵和宣传,“借用人们喜闻乐见的诗歌形式来表达和保存款约内容”[7]形成侗族社会中寓意深远、生动形象、富有节奏感的款词。款词的传承和保存一直以极为传统的口耳相传形式进行,因此聚众讲款成为侗族社会传统的款规约宣传方式。随汉文化进入后(明清时期),在制立款规款约时,侗人中的“知识分子”们通过汉字记音、汉字记意、土字记音的方法将这些具有约法性的款词分条逐款地刻在石碑上,使其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
然而,在上世纪80、90年代前后,款词及款引领了侗学研究的一股“热潮”。这股热潮中,学者们对于款词源流的各种探究及论证众说纷纭,直接导致了款词内涵与外延的模糊性,直至现今,这一论题仍为“各家之言”,难以统一。而正是由于这些探源及论证的“繁乱性”与不确定性,使款词在进一步论述上遭遇难题。因此,本文首先要厘清这样一个问题:款词与款活动紧密相关,最初的形态即是语言粗糙的款规约;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款词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丰富,不仅从内容单一(款约)的形式向内容更为丰富(款史款、约法款、迁徙款、英雄款等)的形式发展,而且更具韵律感及节奏感;在表达方式上,它也从一种单一口头传诵形式向文本记录、口头传诵等形式发展。
二、款词文化的传承及演变
(一)款石:一种口头规约的见证
侗款制度的产生源于侗族社会的失序。“当初村无款规,寨无约法的时候,好事得不到赞扬,坏事没有受到惩处;内忧无法解除,外患无力抵御。有人手脚不干净,园内偷菜偷瓜,笼里偷鸡摸鸭。有的心中起歹意、白天执刀行凶,黑夜偷牛盗马。还有肇事争闹、逞蛮相打。杀死好人、造成祸事、闹得村寨不安宁,打得地方不太平。村村期待制止乱事,寨寨要求惩办坏人。”[8]在这种失序的情况下,侗族各村寨头人彼此相邀、召集族众及地方长老进行集体议事,共同商定维持社区秩序的“款规”和“约法”,“大众合意同心;就这样约定、这样讲成”[9]。而于此时,经由大家“讲成”后的款规约仅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来表达、传达与保存。因此,“口耳相传”可以说是早期款词的突出特征,其表现为一种无文字的口头规约形式。
尽管早期款词没有文字记录,但这种口头规约仍具有其自身独特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通过其自身的合法性及神圣性实现:侗族社会极力追求“平权”,他们更认同“协商”是处理问题的最有效方式,[10]款规约的合法性无疑得益于这种集体性“协商”——款规约在民众议事中使其得以达成,并获得民众的集体性通过,这就意味着由此形成的款词在侗族社会里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再加之款约的发布需以“栽岩为誓”的方式来实现最终的确定,那么使其固有的合法性在传统民间仪式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一经实施它不但受款众之间彼此的监督,还受规约本身“神圣性”的束缚,这双重压力使它更具稳定性的同时,也更有约束力、规范力和说服力。可见,集体性协商与“栽岩为誓”在款规约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栽岩为誓”是侗族社会一种传统的、严肃的“决议”或“决定”形式。栽岩仪式庄重且具宗教性,多在一些正式的场合与必要事件上进行,可涉及侗族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在侗族社会里影响深远,“据调查,这种情况在明清时期的大部分侗族地区都仍流行,有的地方甚至比较盛行。”[11]甚至现今贵州苗侗地区处理一些事务时仍会使用。《侗款》中载“我们一齐好商量,商量好了,在九岭十洞立块石碑、开个款场。”[12]其中“立块石碑”即是这种形式的具体体现,称“勒石定规”或“勒石盟约”,是通过一项新规约的必经环节。“栽岩为誓”、“勒石定规”、“勒石盟约”又简称“栽岩”或“埋岩”,“‘栽岩’时,要举行‘栽岩’大会,然后在集会地点将一块长形的条石竖立栽入土中,半截露出地面,作为会议决议和决定的见证。”[13]
侗族款规约的制定一般称作“栽大岩”或“做大岩”,是一种范围较大的活动,所立之“岩”通称“款石”。款石上无文字,多为质地坚硬的石块,竖立于款坪的“款坛”之上,款词获得通过时“立石为证,以示威严。”[14]即一是表明参加誓盟者的决心有如石坚;二是表明款规约有如石头一样坚硬;三是表明条规一经议定有如石头一样永世长存。[15]而罗马尼亚宗教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在关于“显圣物”(hierophany)的讨论中,给出这样的解释:早期人类注视一块石头时,他们看到的并非是一块毫无生气的石头,他们在石头上看到了坚固、永恒和力,是另一种绝对的生命式样象征。由于石头成为“显圣物”,所显现出某种隐形力量(一种超自然的存在)的存在而受到敬拜。[16]相似地,立款时的“栽岩”同样具有这样的寓意存在,侗人通过此仪式赋予“款石”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突出石头的象征意义——“它总是通过拥有的恒久性和绝对性来提醒人们,并在这种提醒的过程中,通过类比的方法向人们展示了自己恒久性和绝对性”[17]。因此自然地,作为显圣物的“款石”在此即会具有一种属于神圣、属于完全另类的某种精神存在。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款石’上没有文字,是一种‘象征法’,但参加聚会的款众心里对此次‘勒石’的目的和要调整的内容很清楚,如果村寨中以后出现了款石中所指向的行为,就会把违反者拉到款坪上,在款石前进行处理,这就是‘聚款’,所以在侗族原始的话语中都把‘犯罪’叫做‘犯岩’。”[18]以此类推,研究者称侗款为“石头法”在情理之中。
由此可见,“款石”不仅见证款词形成的整个过程,更是早期款规约的物质载体,对栽岩范围内的款众都产生相应的作用力。
(二)草结:款词的另一种符号存在
款是侗族社会联系的纽带,它对内自治、对外防御,不起款时人们无法看见它,只有在其活动时才能清楚地知道它的存在,是侗族社会极为特殊的社会运行机制。款的活动通称“起款”,围绕着款词进行,因此可将“起款”的原因归纳为款词的制定、宣传或执行三种,其中“制定”和“执行”视具体情况来定,而“宣传”则是侗款最为频繁的活动。款词的宣传活动通常在春秋两季举行,有“三月约青、九月约黄”的说法,主要原因是春秋两季为下种和秋收的重要时节,作为南方的稻作民族,侗族对此自然特别重视,他们在春三月时起款宣诵款词以祈求和保护禾苗不受破坏、健康成长;而“九月约黄”则是为了祈祷粮食饱满和维护秋收的顺利进行,确保稻谷完整归仓,即反映了款词文化在侗族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实际意义所在,也是该民族的生存智慧体现。
款词的宣传被称作“说款”或“讲款”,讲款仪式十分庄重、严肃,说款者通常先在款石前三拜三叩,祭祀先祖后才能开始宣诵款词。这项“活动一般以村寨或鼓楼为单位进行,全寨或全族人都参加,由有威望的寨老、款首或款师当众背诵《约法款》或其它方面的款词,并使讲款活动一直处于一种庄重而神秘的气氛中。讲款者一般都站在高高的石台上或板凳上,手中拿一大把用禾杆草或芭茅草挽成的草结。每讲完一条,听众就齐声高呼‘是呀’、‘对呀’,然后讲款者就将一根草结放在神台上,以示此条已经讲完。接着再讲一条,直至将各条讲完,由此而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19]讲完后,数数草结即可知道讲过多少个条款。
打草结是侗族地区一种普遍的民间习俗,又称“打草标”,以用禾杆草或芭茅草挽成草结多见。在侗族社会里,人们常常用打草结的方式来宣示自己对于某一事物的占有权,而社区成员也都会默认这种占有权的合法性,约定俗成、神圣不可侵犯。因此打草结成为一种侗族民间普遍承认的不成文契约,草结则是这种契约被默认的标识性符号,在日常劳作中一旦遇见这种“标识符号”,大家都会彼此遵守俗规,敬而远之,即便再喜欢也不能强行占有。否则,即会遭致世俗人言与神圣力量的共同“谴责”。在讲款过程中,讲款者以打草结的方式将每一条经宣示、并获得听款者承认的款词做草结的标识,正是让款众牢记彼此达成契约的具体条款,并以这种方式使规约分条逐款地物化为具体的草结,进一步增加其合法性和神圣性“筹码”。
(三)立碑:文字契约的建立
随着时代的变迁,汉文化的进入使款词文化体系日渐成熟。不仅各种规约在制定上更规范,从其表现形式上看,变化更加明显:出现了文字形式的款词,即款碑。款碑以汉文书写,明显表现为汉文化进入侗族地区后的产物;从时间上看,现存可考的款碑主要集中在清朝中后期,民国时期存有少量。[20]。究其原因,明朝以前汉文化对侗族地区的影响极为有限,而进入明清后,随着政府加强对侗族地区的管理及大量汉学书院的设立,汉文化随之全面深入这一地区,对侗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产生了直接性的影响,也包括款的活动。汉文字进入后,侗族人民在制立或修改款规约时通过汉字记音、汉字记意、土字记音的方法将这些具有约法性的款词分条逐款地刻抄在石碑上,以简洁明了的文字形式以呈现出来。
文字的出现使得款规约的新时代特征表现更为明显。在制定程序上,尽管延续了传统款首、长老、民众参与议事的民主原则,但发布时“栽岩”仪式的内容发生了变化,所栽之岩是一种细致地记录了议事达成的具体内容的“款碑”。它的出现使得款规约有了更具体的保障:以明确的文字形式记录下来。这样对参与立约款众的约束除了依靠口头承诺、集体监督、习俗维护外,还以“明文”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规约的运作更加有理有据。不仅如此,在款碑的行文格式中还清晰地记录了立款的原因、具体内容、参与者(村寨)和时间:“第一部分是立碑的意义和原因,第二部分是立碑所要订立的具体条款,也就是碑刻中的具体内容。第三部分是立碑的人员。第四部分是立碑的时间等。”[21]由此,盟约各方在处理款碑所指事件时即能“有法可依”,依据碑文进行论事的处理方式更显理性和公正,也更有说服力(据明文条款惩处)。
现存款碑主要以地名、规约内容、立碑时间或立碑目的来命名,如“三龙大款款碑”、“乡例碑”、“禁款碑”等。这些款碑除其碑文以文字记录外,还表现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在句式结构特征上的明显变化,从口头盟约时期相对工整的、讲究节奏感和韵律感的行文转为平铺直叙的叙事型句式结构,念诵起来相对平稳、直白,且简单易懂易记;二是款词内容上发生了变化,因受汉文化和国家政治的直接影响,它既继承了传统的族规、寨规和地方规约,同时也融入了与国家法典相关的内容,彰显国家政治的存在。与此同时,新时代的款词也更加偏重于对违约者的严重惩处姿态,显现了“法”的理性存在。总之,这些变化凸显出在汉文化进入后新时代的款词特征。
款词在侗族社会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文字的出现使得款词走进了“文字时代”,文字规约形式使款规约有了更明确的保障,也更加理性、更具说服力,亦是款词在新时代的新表达和保存形式。
(四)纸、音、像:款词的新载体
新时代的新表达和保存形式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汉文字传入后,侗族地区一些“文化人”以手抄的形式将款词集成文本形式,世代相传;到了20世纪50年代,文化工作者陆续进入侗族地区进行研究,在侗文化历史调查的过程中搜集、整理了一大批的款词,并着手刊印;80年代,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程启动与实施,侗族款词以民族民间文化的姿态进入民间文学领域,获得了较为全面的搜集、整理、编册、刊印等,如当时搜集编成的《侗族款词·耶歌·酒歌》。
而随着党及国家对民族文化的重视及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发与发展,侗族各村寨庆典活动时刊印相关的民族文化宣传册,刊印和宣传村规民约条例,或族谱、家谱规约等将款词记录下来。[22]特别近几年,一些地区还以录像影音的形式将款词及诵款者唱诵的现场拍录下来制成影音文件,以DVD、VCD碟片或电脑文件的形式进行播放与传播;部分在场者甚至用智能手机进行拍录,进行数字化处理后再以蓝牙或网络方式分享与他人等。这些都是新时代文化语境中款词的新的表达与保存方式,各类文本即呈现了一种新的款词存在方式。
三、结 语
款词是款规约的语言载体。在汉文化和国家政治大量进入侗族地区之前,它主要依靠口头传诵的方式来进行表达和保存,并在周而复始的“讲款”活动中警示、约束、规范和教化款众,推进和维系侗族社会的良性运行、有序发展;进入明清时期后,国家政治在这一地区的用强和汉学书院的大量设立,款词也以汉文字形式呈现出来。但无论是口头规约时代还是文字规约时期,款词都需要通过集体性“协商”(集体议事)与当众发布的方式使其本身合法化,并在传统“栽岩”、打草结、立碑活动中使这种合法性得以增强且神圣化,成为侗族社会治理无可代替的传统力量。这种力量的获得既是传统民族民主制度的赋予,也是民俗自身力量的自我推力。无论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民俗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的展示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民俗努力将人们的言行和思想观念纳入规范的维度之中;另一方面,是以传统的力量捍卫传统。”[23]侗人款词的历史变迁即展示着这种力量的存在。
[1][14] 冼光位.侗族通览[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2] [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 粟定先.论侗款流源[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4).
[4] 石开忠.侗族款组织的文化人类学阐释[D].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4.
[5] 刘琳,张中华.广西三江侗族侗款的传承及其现实影响[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2(4).
[6] 丁桂芳.仪式、契约与秩序——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群体盟誓制度探析[J].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6).
[7] 张美圣.略论侗族款词及其文学价值[J].贵州民族研究,1985(4).
[8][9][12] 杨锡光,杨锡,吴治忠.侗款[M].长沙:长沙:岳麓书社,1988:84,13,229.
[10] 林淑蓉.“平权”社会的阶序与权力:以中国侗族的人群关系为例[J].台湾人类学刊,2006(1).
[11][20][21] 石开忠.侗族款组织及其变迁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13,118-120,141.
[13] 龙耀宏.“栽岩”及《栽岩规例》研究[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
[15] 杨玉琪.款制文化探析[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6).
[16][17] (罗)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M].王建光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88,89.
[18] 陈迪,徐晓光.款词与讲款—兼论黔湘桂边区侗族社会的口头“普法”形式[J].贵州社会科学,2010(3).
[19] 徐晓光.“石头法”的嬗变—黔湘桂侗族地区从“款石”、“法岩”到“石碑法”的立法活动[J].贵州社会科学,2009.
[22] 吴鹏毅.自然法则与生态生产观:款词款约法的文化调查模式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23] 万建中.民俗的力量与政府权力[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