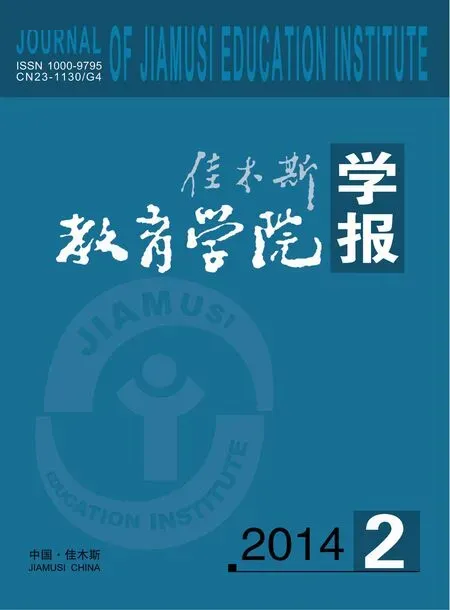《无名的裘德》中的时间和意识
郑超群
(福州大学阳光学院外语系 福建福州 350015)
《无名的裘德》中的时间和意识
郑超群
(福州大学阳光学院外语系 福建福州 350015)
相对哈代同时代的作家而言,哈代的作品中有着较强烈的现代主义意识。在《无名的裘德》中,时间作为客观社会环境的象征,对人物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人作为个体,在这个荒谬世界中的异化。然而在哈代笔下,主人公身处在人类存在的困境中,却仍保有对真我的执著追求,这种个体的意识对时间的反抗体现了哈代对人类存在的关注和人的主体性。
哈代;《无名的裘德》;时间;意识
一直以来对哈代悲观主义和宿命论的过分强调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一再被研究者回避的问题,即作者是否在肯定环境巨大影响的同时消解了人的主体性?而事实上,哈代在对时间持悲观主义态度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他的笔下,主人公身虽然处在人类存在的困境中,却仍奋力保有对真我的执著追求,从主人公的心路历程、与外在世界的交锋对抗、到最后被社会所遗弃的过程中这种个体的意识与时间的对立体现了哈代对人类存在的关注。
吴笛指出“哈代诗中的时间有着多种不同的时间意识,既有单向的、按年月日次序流动的时间,也有稳固不动的记忆之中的时间,甚至还有弹跳到未来的超前的时间。正是这些时间意识使作者感受到悲剧的痛苦,产生出悲剧的意识。”而《无名的裘德》是哈代从小说创作转向诗歌创作的关键转折点。它被认为是哈代最具争议性地一部小说,表现了强烈的现代意识,时间主题和表现形式尤为突出。时间作为外在社会环境的象征对人物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人作为个体,在这个荒谬世界中的异化。
小说描述了平凡的小人物在英国由传统农业经济向新兴工业经济转型的新旧交替的世界中奋力却又绝望地挣扎。裘德和淑正是在这种不可避免的夹缝中承受着思想和制度、个体和社会的冲突。作为自我意识的载体,他们痛苦得徘徊在超越时代的思想与陈腐的社会习俗之间,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的心路历程无一不说明了个体在宇宙中的渺小和无能为力。然而,这种挣扎本身也正体现了哈代对人类存在的关注,强调了人的主体性。
赛缪尔·海纳斯认为“在哈代的世界里,时间是单向的永无逆转的运功过程……哈代的时间是毁灭性地、永不可治、也不可超越的力量。”这里的时间代表了英国正处于转型社会阶段的传统体制。小说通过空间和一些反复出现的意象为凝聚点,如路、基督寺、生命力脆弱的动物等来表现时间的冷酷和无情,其中为基督寺最为明显。时间背后所代表的社会道德准则、婚姻制度、神学信仰等对个体存在的约束和压制往往引发了人物内在的思想变化。
亨利·柏格森在他的著作《时间和自由意识》中讨论了时间和意识的关系。他认为时间可以影响并规范着人的思想,而意识的“心理时间”能从内在视野感受外部世界,并具有独特的弹性,可以能动地更改时间状态,从而创造出一个虚幻的意识空间。
哈代十分注重对人物意识和情感的描述。人物的意识在小说中或是游荡在记忆当中或是弹跳到未来,通过改变了时间的长度和顺序,来表达个体存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现实的极度失望。如在描述小时候的裘德时,哈代说到“由于集中精力思考,男孩走得比较慢——当他思索的时候,有时成熟得像一位老人,而有时又比较幼稚得好像比自己的实际年龄小许多。”而裘德身上这种与直线性发展的时间相矛盾的性格也一直贯穿着小说始终。
与此同时,人物意识也通过幻想、内省、自责或梦境等建构一个想象的空间。正是时间启发了裘德在基督寺前的梦境之旅:“这时,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铿锵的钟声。他侧耳听了一阵……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街上地行人越来越少,他仍旧在墙阴门影中蹩来蹩去……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无所寓寄德幽灵一样,在这座城市中游荡。人们既看不到他的形体,又听不到他的声音”。在随后的梦境中裘德的意识获得了暂时的自由,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时间的局限,他与想象中那些崇高身份的人物对话,沉浸在自我的肯定和认同当中。在意识所创造的这个心理时间中,他不再是一个无名的“他者”。意识跨过传统时间的界限,时间被停滞,甚至被忽略。
这场意识与时间的较量体现了哈代对人类命运的关注。裘德原本是一个充满理想抱负的青年。他渴求知识和爱。他对一切美好的精神追求,使得他焕发着活力,具有强烈的生命力意识,然而却在充满肉欲和无道德意识的阿拉贝拉的引诱下堕落,迷失了自我。而裘德对淑的追求,本质上则是精神上的柏拉图式恋爱,是对传统的婚姻制度的挑战,是自我意识的逐渐觉醒,对个体存在的肯定。然而裘德的自我意识始终在徘徊,这由他一而再地被阿拉贝拉引诱,最后和阿拉贝拉复婚中可窥一斑。
站在十字路口,裘德的自我意识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仿佛向前一步即可触碰到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而退后一步则又会马上坠入充满诱惑和自我谴责的深渊。在这场与时间的较量中,裘德的自我意识成长之路是艰辛的、然而却又让人欣喜的。看似内心懦弱、优柔寡断的裘德成长为一个拥有独立意识、能够对世俗体制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的自由人。
然而小说中最具讽刺性和戏剧性的是,个人的意识在庞大的社会机器面前苦苦挣扎的渺小和无力感一直贯穿小说始终。裘德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意味着悲剧命运的降临。裘德和淑一直竭力试图在社会中证明自我的存在,结果却意识到在无情的时间之手的恣意摆弄下,一切竟如黄粱一梦般虚幻、可笑。在这个高度物质化的世界中,残酷的时间让个体意识感受到的只有令人窒息的压抑。淑最终对社会教化的妥协与她先前作为一个有着叛逆思想的进步女性形象来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戏剧性效果突出了个体在这场时间和自我意识的殊死搏斗中的悲剧结局。淑的个体意识最终屈服于时间的压迫、与之同化。她的自由意识开始缺失,被物质化的时间所吞噬、侵占。
哈代创造性地将这场时间与意识的较量融合在“小时间老人”这个荒诞的人物形象身上——他的存在令人感觉处处与社会格格不入。“他就像一个由老年人装扮成的儿童,……有时,在这个年龄如同初升旭日的孩子的心头,仿佛压上了从远古以来所有的人类愁苦,所以每当他回首过去的一切,那沉浮于心中的汹涌波涛就会不断地拍打着他的记忆,所以,他才会对眼前的事物,显得毫不在意。”
小时间老人的早熟形象与小时候的裘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重合和再现。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心理成长颠覆了传统的成长模式。小说是这样描述小时候的裘德:“这个已经经历过生活心酸的孩子,满腹心事地站在井边,脸上毫无表情地注视着眼前的这口老井的深处”。这种过于早熟、历经沧桑的形象颠倒了传统的时间认知模式,让人耳目一新的同时也让人触目惊心。哈代通过塑造小时间老人的人物形象,将与时代脱钩的意识具体形象化。小时光老人从一开始就对社会抱有完全敌对的态度,他对社会的质问和对自身的否定,诉说着个人意识在社会群体当中的危机感。
在哈代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哈代是高度赞颂和推崇爱,然而在小时间老人的世界中缺乏爱和其他情感,他是终极意义上的自我异化。他的存在是裘德的自我意识屈服于物质化的阿拉贝拉的情欲引诱。这种意识向时间的屈服带有毁灭性的力量。小时间老人的到来暗示了“最终审判日”的到来:—切时间的终结。小时光老人杀死了自己的兄弟并自杀,这一死亡事件将故事中时间和意识的矛盾冲突激化。淑离开裘德,回到与费劳孙的婚姻当中。淑的离开,在裘德看来违背了一直以来两人之间共同的意志追求,导致了他独自孤立无援的面对困难。他对于淑后来的转变,悲痛地感叹道:
“她的智慧就枯萎了,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走向了黑暗……我和淑的生活本来是非常幸福的,我们头脑清晰,我们大胆追求真理。但是我们的行为却大大地超越了时代,时代还没有成熟到我们这种程度。我们的思想提前了五十年,所以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没有好处的。当这些思想遇到阻碍的时候,她就退却了;而我,则要不顾一切地毁灭自己!”
死亡是个体生命时间的终止。而在小说中的死亡和自杀却往往引人联想到自由和解脱。裘德和小时光老人常常在质疑自己生命的意义,自杀的念头时时萦绕在他们心中。他们渴望为自身找到存在理由和自由,逃离这囚禁着他们思想的社会体制。自杀成了裘德“从世俗的苦苦挣扎中解脱的最后一根稻草”。和对生存的困惑、对死亡的思索和最终抉择体现了他们的意识反叛时间的无奈之举。
时间和意识之间的巨大反差成为了小说人物生活悲剧的根源。然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假如没有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懈的追求,裘德也仅是芸芸众生中对时间麻木的一员,缺失自身存在的意义。在贫穷的命运和周遭的嘲笑声中,裘德对知识的渴望和信仰显得弥足珍贵。同阿拉贝拉推崇的肉欲横流的物质社会相比较,裘德和淑对爱情真谛的追求是这个污浊、混乱的社会中的一股清流。哈代在小说中所描绘的“理想主义和社会现实之间的斗争”⑩给他的时代和读者带来了震撼人心的体验。
虽然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时代局限下,哈代笔下的人物似乎都笼罩在一层凝重、令人窒息的悲观阴影下,但哈代在小说中更多的是用了大量的笔墨塑造了超越时代的渴望独立人格和追求自由意识的人物形象。他对人物的同情和关注使得这些人物形象在沉默、冷酷的社会制度背景衬托下从而显得格外生动、真实、美好。小说的标题《无名的裘德》本身也正说明了人物在小说中的主体性。
小说中人物意识与时间的这场拉锯之争体现了哈代的人文关怀和他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同情。哈代的性格和环境小说主要探索人的内在意识活动。虽然由于时代的限制,他的小说中对个人和社会冲突的根源的分析并没有现代主义派作家那么深刻,但是我们不应仅仅停留在对哈代的社会局限性的分析上,而是要从哲学的角度把它看作是时代的产物的同时,也要看到它超越时代的一面。
[1]吴笛.论哈代诗歌中的悲观主义时间意识[J].国外文学,2004,3:54-58.
[2]赛缪尔·海纳斯.哈代诗歌模式[M].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61:50.
[3]亨利·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识[M].吴士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托马斯·哈代.无名的裘德[M].都兴东,译,南方出版社,2003:20.
[5]同上,80-81.
[6]同上,305.
[7]同上,3.
[8]同上,443.
[9]Ford, Tracy A. Thomas Hardy: Timely Exits [D]. Ph.D.Diss. The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ProQuest LLC, 2009: 137.
[10]Ihaddadene, Boussaad. The Confict between the Ideal and the Social in Thomas Hardy’s Jude the Obscure [D]. Mentouri University, Constantine,2010: 45
The time and consciousness in "Jude the obscure"
Zheng Chao-qun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Fuzhou University Yangguang College, Fuzhou Fujian,350015, China)
Compared to contemporary writers of Hardy, it has a strong modern consciousness in Hardy's works. In "Jude the obscure", time as a symbol of the objective social environment, has a great influence not to be ignored on the characters, mainly in the people as individuals, alienation in the absurd world. However, under Hardy's pen, the heroine in the predicament of human existence, but still have pursuit of real m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individual subject to human existence embodies Hardy's attention and the time of rebellion.
Hardy; "Jude the obscure"; time; consciousness
I106.4
A
1000-9795(2014)02-0129-02
[责任编辑:董 维]
2013-12-29
郑超群(1984-),女,福建莆田人,讲师,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方向的研究。
跨学科文化批评视阈下的哈代作品研究,项目编号: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课题2011B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