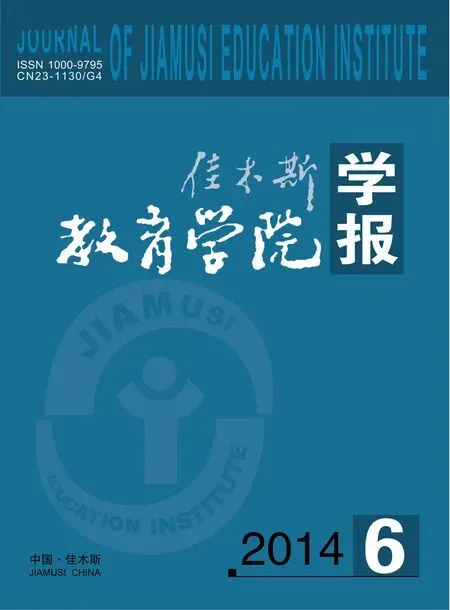《呼兰河传》中的视点反讽的三重表达
张宇男
(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5800)
《呼兰河传》中的视点反讽的三重表达
张宇男
(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5800)
本文以《呼兰河传》为个案,并通过双重视点、视角干预等方面分析未能引起研究者重视的萧红的反讽性叙事。
视点反讽;儿童视角;视点干预
当代学者在关于萧红《呼兰河传》的研究上一直是围绕着茅盾的序言“这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做诠释,将注意力更多的放在她的身世与创作关系,例如:自传体、童年回忆录、寂寞说,还有散文化的小说结构、儿童视角等方面上,并认为这是萧红在即将离世时对遥远故乡的温情回想,是她理想中家园景观的一种寄托。
然而,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初读《呼兰河传》体会的是作者对风俗画的描写,是对故乡的眷恋;再度体会到作者求而不得、思而不往的无奈与寂寞;三度体会到了通过反讽叙事而表达的作者理性批判的态度。1940年创作完成的《呼兰河传》正是因为它叙事的反讽性而常读常新,也正是因为它的耐读,才成为了萧红(1911—1942)个人最重要的代表作,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一部经典。
理性的批判与情感的怀恋之间的交织,批判不是最终的目的,对读者灵魂的诗意触动才是萧红的反讽修辞的旨归。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是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身份,对病态的民族文化心理和丑陋的灵魂做了文化批判。
一、关于反讽的界定
反讽是小说中最常见的微观修辞技巧,具有意婉旨微而又深刻有力、耐人寻味的特点。但因为至今还是一种发展中的技巧和方法,因而很难对它做精准的界定和理论把握。
综合赵毅衡、李建军等学者的界定,以及对于文本的反复体味,对于“反讽”我也做了自己的判定,认为:反讽是在旨意上较嘲讽柔和,又比嘲讽更趋于暗示、婉转的一种间接性讽刺手法。它是让作者的态度不做直面抒发但通过某些线索又能使读者朦胧的体悟到作者批判态度,并通过潜在的反讽消解显在的主题意向并形成一种张力性修辞、叙事手法。它包括回避直接陈述、言意悖反、需要读者参与等特点。
于是,下文就将继续阐述叙述者是怎样在表层结构的下面流露深层内涵的。
二、成人、儿童的双视角叙事
视点反讽在于视点的特异性,即“叙事通过异常、独特的视角展开,从而具有了勘测普通视角无法观照的殊异风景的能力。视点反讽依靠的就是异叙述者的异常叙述。”例如:一个小孩子看到的事情完全不同于成人,一个疯子、傻子、甚至动物的特殊视点展开的叙述肯定偏离正常的叙事,这就会形成反讽。简单地说,叙述者就是作者在文本中的心灵投影。
成人视角比较好理解,比如文章中第一章第三节中,描写了众多人的死亡,人们看见这样的人,既有恻隐之心但又觉得这样的人太多可怜不过来,于是又冷漠了。人们的生老病死就像四季的春生秋落一样,默默的交替着,惹不起半点涟漪。读者的阅读期待是本以为在这样的死亡面前,叙述者的态度应该是悲悯、同情、愤慨的,然而《呼兰河传》中的成人视角叙述却是类似零度叙事一样不动声色的、平静的、可观的,于是在读者的阅读期待和实际叙述中产生了错位,生成离间效果,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
而儿童视角的运用,在《呼兰河传》中则是一个亮点。所谓“儿童视角”,简而言之,就是用童眼观看世界,用童言言说世界,用童心感受世界。
萧红通过儿童视角,在天真和疑惑的发问中,完成了对成人世界的拷问。他们为什么轻生重死,对别人的死能够有看热闹那样轻松的态度,却又对给死人扎纸人那么热衷?走出文本,身为读者的我们会感到,这种情境恰如《皇帝的新衣》中说出皇帝什么衣服也没有穿的小孩。“我”是如此直白地说出了我的困惑,我不明白为什么如此明了的事实在大人那里却很是不清楚,甚至在“瘟猪问题”、“小团圆媳妇生病”问题上,他们也不愿意让一个孩童帮他们找出真相。
例如,第五章的描述中,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凑热闹去看小团圆媳妇,儿童视角的“我”自然也央求祖父带我去。在小团圆媳妇的故事里,女童是惟一与众不同的观众,“与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样,没有什么好看的,团圆媳妇在那儿?我也看不见,经人家指指点点的,我才看见了。不是什么媳妇,而是一个小姑娘。”可见,在儿童视角对于“小团圆媳妇”这一身份的消解,“我”认为她是小姑娘不是什么媳妇。
在《呼兰河传》中,作者萧红将自己裂变成成人叙述者和儿童叙述者两个叙事人,也就用儿童视角和成人视角的双重叙述方式,使文本呈现出一种复调的诗学意蕴。儿童视角因其立场的边缘性、情感经历的原始性,她所感受的世界与所做的情感评价都将与小说呈现出来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又为了避免读者将作品当作非反讽故事来阅读,作者在再现童年生活的过程中又适时地介入了成年人的身份来干预儿童视角的叙述。
三、叙述视角的干预
作者的反讽性的叙述还体现在叙述视角干预、越界上。文中在塑造小团圆媳妇的婆婆这一人物形象时,就有明显的视角越界。
例如,来个云游真人要给小团圆媳妇抽帖,婆婆想“这倒也简单、容易,想赶快抽一帖出来看看,命定是死是活,多半也可以看出来个大概。”当听到每帖十吊钱的时候,她的心理经过了用十吊钱买豆腐、养口猪、买鸡等等的“发财梦”的如意算盘。
但是,前文已经阐述过,小说从第三章开始,叙述视角就由全知视角转换为童年的“我”,即儿童视角。按常规来说,抽帖时婆婆的心理活动,作为局外人、作为看客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是无法知道的,更无从知晓她从前养鸡的艰辛。那么显而易见,此时的叙事策略,就有从第一人称的限制视角向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侵入,因为只有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才有这种洞察别人心理活动的权力和能力,通过这样的视角干预,有利于作者更为深入地剖析人物的内在心理。
反讽以委婉隐幽为主要叙事风格,通过巧妙的暗示,把事实的真相或自已的态度暗含在似是而非的假象以及含混的陈述之中,让读者透过表象去领会其中的深层含义。
四、反讽性评述
虽说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是由作者虚构的叙述者,阐述的一个虚构的真实。然而,在《呼兰河传》中,我们随处可见作者的声音。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只言片语暴露了作者的踪迹、泄露了作者的态度倾向。例如:
第一章第二节,先有一个哲理性总论:“一年四季,春暖花开、秋雨、冬雪,也不过是随着季节穿起棉衣来,脱下单衣去地过着。生老病死也都是一声不响地默默地办理。”(P104)作者萧红以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轮换,来对应人的生老病死的生命轮回,以一种最为简单、粗砺的形式传达出乡村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生死场”,没有变化,没有希望,有的只是人的生存的悲哀和生命的荒凉,进而直指人性的荒芜和灵魂的死寂。
“荒凉”这个词在第二章中频繁出现,并且是从该章第二节到结尾第五节的每一节的开头,可想而知,“荒凉”这个词所要传达的深意是必须引起读者重视的。那么试问,一个整天在后花园中玩耍,黏在祖父身后的小女孩,如何能够感受到当时的家是荒凉、是空虚的?那么文中的这些声音又是由谁发出的呢?显然这是出自作者之口,是作者时不时的跳出虚构的叙述人身份而发表作者自己的评论。出现作者声音的原因,究竟是一种叙事策略还是作者的缱绻之情难以自掩的一种体现?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就这种现象本身而言还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钱理群说:“这样的批判性的审视,显然不属于前述儿童的眼光;这是成年人的叙述对儿童视角的一种干预,让读者身入其中,又出于其外,这‘进(入)’、‘出’,‘内’、‘外’之间的就形成了一种张力。”
其实,作者运用反讽并非要掩盖自己真正的意思,相反,它是以一种更隐蔽更高明的方法来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带领我们积极追寻自己的真实意旨,以享受更多的阅读乐趣。在议论中所流露出的作者情绪,并非是要控制故事的发展或走向,而是一种介入的方式,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叙事态度,是隐含作者对所叙之事的反讽。
[1]陈振华.小说反讽叙事:基于中国新时期的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
Shallow discussion the hulan river "the irony of the triple expression of viewpoint
Zhang Yu-nan
(Graduate School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155800, China)
This paper takes the hulan river as a case, and through the double point of view, the respect such as Angle of intervention analysis failed to sexual narrative irony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researchers of xiao hong.
Viewpoint of irony; Children's perspective; A viewpoint intervention
I207.4
A
1000-9795(2014)06-0105-02
[责任编辑:董 维]
2014-03-11
张宇男(1989-),女,河南洛阳人,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