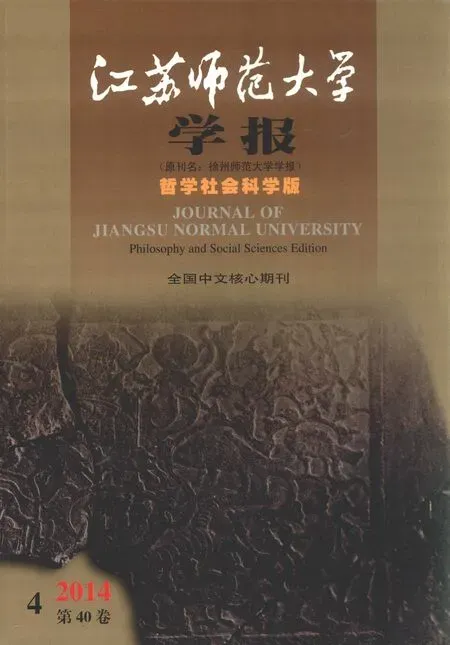从侨易学的角度审视徐志摩人生志向的转变
熊 辉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从侨易学的角度审视徐志摩人生志向的转变
熊 辉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侨易学;徐志摩;人生志向;侨易事件;侨易行为
徐志摩的一生经历了几次侨易行动:从硖石到杭州的区域侨易导致他从私塾学童,转化为胸怀天下的有志青年;从杭州到北京的都市位移导致他从意气风发的理想主义者,转化为洞察世事且立意走出国门的实业救国者;从中国到美国的双边侨易,导致其人生志向从经济转向政治;从美国到英国的双边侨易导致其人生志向从政治转向文学。复杂的侨易行动改变了徐志摩的人生观念和价值观念,其英伦绅士般的生活方式,必然会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遭遇尴尬和矛盾。
学界对于徐志摩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本文特从侨易学的角度,通过对其数次侨易行为的考察,希望对徐志摩的人生目标和生活志趣的转变找到更多合理的解释,也从中探求其作为一代学人代表的成长史和心灵史。
一、从硖石到杭州的区域侨易
作为一种学科概念,侨易学“主要关注事物二元取象之后的流力因素,以及间性关系的研究”,其基本原则之重心便是“物质位移导致精神质变”,且此时所谓的物质位移“是由多个因素构成的重要的文化区结构差之间的位移过程,如此导致个体精神产生重大变化”[1]。这为我们打量个体或群体精神思想的流变提供了重要思路,即侨易主体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生活空间的转变是其精神转变的关键因素,由此检索便会注意到物质位移之后,主体遭遇的各种异质文化因素带来的正负影响。
一般来讲,区域性侨易主要是指侨易主体从边陲地区向中心文化城市的迁变过程。徐志摩的第一次侨易行为是从家乡硖石到杭州求学,他从相对闭塞的小镇来到江南经济文化中心杭州,所见所闻和所学所思都与之前大相径庭。正是杭州与硖石这两个文化区结构的差异,导致徐志摩的人生理念发生了巨大变化。
徐志摩在硖石的学堂生活枯燥无味。1900年,年仅5岁的志摩被送进了自家设立的私塾,开始启蒙学习,其漫漫求学路自此展开。这对天性喜爱自由的志摩来讲,无疑像穿鼻的牛犊,只能跟着别人的牵引生活,而不能在青青的草地上恣意奔跑。徐志摩的第一位老师叫孙荫轩,系海宁庆云镇秀才,教他读书认字。孙先生常常在课堂上一边呵斥学生,一边抽大烟;或者在学生练习书法时,独自哼唱清平乐府。私塾的生活异常沉闷,幼小的“读书官”要临帖写字,要大声诵读不甚了了的四字句,要面对先生冷不防举起的戒尺。除传统节日外,徐志摩和表兄沈叔薇只能呆坐课堂,枯燥的日子看不到尽头。他讨厌私塾生活,于是将先生的戒尺投入井中,以发泄内心的叛逆。或者坐在教室里,看着窗外的白云,心思飞到广阔无边的蓝天上,让约束的心灵获得暂时的解脱。打雷下雨更是让他兴奋不已,炎热乏味的下午变得热闹起来。人们忙着关窗,教室楼上的女仆忙着收衣,小燕子到教室避雨等等,到处都是响声,先生哪有心思教学,学生哪有心思诵读,于是大家作鸟兽散。枯燥的学习得以暂时终止,徐志摩由是得以自由。
1901年,徐志摩迎来了第二位老师査桐轸,系海宁县袁花镇贡生。査先生与志摩缘分不浅。首先是师徒二人对洗澡都心怀芥蒂。志摩在文章中曾说,查先生出生时,父母怕孩子洗澡受凉,几年里没给他洗澡。如此一来,养成了查先生不洗澡的习惯,直到去世前仍然如此。此外,查先生平时不刷牙,不洗头,几乎不洗脸,身体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查先生行为如此怪异,却深得志摩父亲徐申如的赏识。这当与其深厚的古文功底有关,有知识的人向来受人尊重。从1901年到1907年,志摩跟着查先生念了六年有余的诗文,私塾生活在让他感到乏味的同时,也让他的古文功底日见深厚。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清廷废除科举,推广新式学堂,传播实学。1906年,清廷诏准停止所有乡试会试,令学务大臣即刻颁发新教科书,于乡城各处设立启蒙学堂。科举制虽在1906年废止,但新式学堂的建立只能循序渐进。因此,徐志摩在新旧学制叠加的时期,接受旧式教育至1907年,直到硖石开办新式小学开智学堂后,他才转入该校继续学习至1909年冬。
1910年春,徐志摩来到有人间天堂美称的杭州上学。杭州府中学是浙江最好的中学,新学制肇始,还没有形成完备的人才选拔制度,能进入该校,徐家动用了社会关系。徐志摩的姑丈蒋谨旃与时任浙江省咨议局副议长的沈钧儒交好,拜托沈钧儒给杭州府中学监督写推荐信,才使徐志摩和表兄沈叔薇获得上学的机会。杭州府中开设有国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地理等课程。徐志摩的国文老师有张献之、刘子庚。到了新环境,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徐志摩成绩依然高居榜首。按照校方规定,每个年级由第一名担任年级长,徐志摩自然成为年级长的不二人选。杭州府中时期的志摩,没有改掉调皮好动的习惯。15岁,身材瘦小,头大脸长,戴一副金边近视镜,在教室里跳来跳去。他平时爱看闲书,功课上用力不多,但考试总能领先,很多同学对他佩服不已。志摩的文章依然让人称道,常被作为范文在班上念读,他是杭州府中绝对的明星。
杭州府中汇聚了浙江文化界名流,也吸纳了全省最优秀的学生。郁达夫是志摩的同学,与徐志摩如鱼得水的生活不同,郁达夫初到杭州,无论是课堂上,还是宿舍里,都如同蜗牛似的蜷伏着,不敢抬头正眼看人。二人性格相差很远,但恰同学少年,能彼此惺惺相惜,实在是难得的同窗。二人文章都做得好,是班级里出类拔萃的才子,几经交流,便加深了友谊。郁达夫的《志摩在回忆里》一文,翔实地记录了志摩在杭州府中的形象:“尤其使我惊异的,是那个头大尾巴小,戴着金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他平时拿在手里的总是一卷有光纸上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考起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分数得最多的一个。”[2]
走出硖石,徐志摩在广阔的天地里奋力翱翔,他那自由的灵魂,在书海里求得了最好的释放。中学时期,除读文学书籍外,志摩还阅读社会学、历史学方面的书,了解中国和世界的现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徐志摩受到了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通过阅读,他开始思考很多社会问题,并被维新派人士梁启超的行文和思想所折服。1913年,杭州府中改名杭州一中。是年,徐志摩在校刊《友声》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题目和内容均有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影响印记。虽是一篇效仿之作,却可看出徐志摩思想观念的变化。青少年有旺盛的求知欲,除功课之外,徐志摩积极了解社会思想的变化,吸纳新知。同时,他对自然科学也发生了兴趣,从化学课上知道了镭元素,这种银白色晶体能放射大量热能,穿透一切物体。于是,徐志摩从镭入手,习得了很多关于地球的知识,写出了自然科学论文《镭锭与地球之历史》,发表在校刊第二期上。这种文理兼得的兴趣,似乎是五四前后学者的共性,比如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曾研究过采矿,在《河南》月刊上既发表过《摩罗诗力说》,又发表过《科学史教篇》,反映出一代学人健全的知识结构,以及通达自然和人伦的洞察力。
青少年时期是求知欲和可塑性最强的阶段,徐志摩有幸从硖石来到杭州府中学求学五年,接触到了外文和自然科学,通过自身的阅读了解了很多社会文化,且当时杭州府中学汇聚了浙江省文化名流和新派人士,他们讲授的知识让徐志摩茅塞顿开。徐志摩沉浸在全新的知识世界和繁华的大城市里,他的精神世界和世界观念发生了近乎质的飞跃,他从昔日只会念书习文的私塾弟子转而成为胸怀天下的有志青年,这为他日后走向更为高远的人生目标奠定了基础。
二、从杭州到北京的都市侨易
徐志摩的都市侨易较为复杂,不仅仅是从区域性的文化中心杭州向全国性的文化中心北京的侨易,而且也涉及到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天津以及从天津再到北京的侨易过程。都市侨易行为带给徐志摩丰富的生活体验,自然也增富甚或改变了徐志摩的精神世界。
从硖石到杭州,徐志摩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他是天空的一片云,要到更辽阔的大海去投射自己的影子,他要走出江浙,到文化氛围更浓厚的北京求学。1915年秋天,徐志摩与父亲共赴北京,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他对北上途中的所见所闻颇觉新鲜,倒是父亲途中感冒,胃寒腹泻。志摩初到北方,觉得“空气甚燥,肢体热,不免唇焦等现象,住惯当亦无妨”[3]。在京求学期间,他住在蒋百里家,作为一代军事家和政治家,蒋百里给他讲解了很多社会道理,让他能在混乱的时局中看清社会的本质。蒋家位于锡拉胡同,是北京东城的西式建筑。中国政局风云变幻,不久袁世凯叛国,蒋百里南下,徐志摩就搬到腊库居住。在寄居蒋家的日子里,徐志摩对政治有了直接而深刻的认识。在北大预科读书期间,他对戏剧产生了浓厚兴趣。朋友毛子水有时候去居所看望他,“远远便听见他唱戏的声音了(大约是学杨小楼)”。在梅兰芳和杨小楼之间,徐志摩更偏爱后者。1915年10月,在北大预科学习刚两个月,徐志摩就被父亲一纸电文催回硖石,目的是希望他早日完婚。农历10月29日,徐志摩与张幼仪在硖石完婚,后张幼仪退学,徐志摩则短时间内呆在家里。
1916年春,徐志摩告别家人和妻子,转入上海浸会学院学习。浸会学院即沪江大学前身,志摩在此学习中英文学、历史、圣经、物理、化学等课程,成绩优异。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但他在此还是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文化氛围。5月,转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预科,1917年6月,以优异的成绩升入本科。恰好这一年北洋大学撤销法科,并入北京大学法科,这样徐志摩又回到了北京大学。由于考虑出国留学,徐志摩升入北大法科之后,并未正式上课,从1917年秋到1918年夏,他只作为旁听生选修了政治学、法文和日文等课程。徐志摩在国内的求学历程,游学的意味儿更浓。从北京到上海,再到北京,他经历的虽不是完整的大学教育,但在辗转中,他遇见了很多人、很多事,增长了见识,所学也许并不次于学堂知识。后来出国留学,徐志摩也先后在美国的克拉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等学府学习或旁听,领受了不同风格、不同层次的西方大学教育,自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熏陶。
在此应当提及徐志摩经历的重要侨易事件,那就是1918年夏天,在离开北大准备赴美留学之前,徐志摩成功拜师梁启超,这对他后来的人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拜师梁启超实属不易,毕竟彼时梁任公在文化界是大人物,社会影响巨大。但有妻兄张君劢的引荐,有父亲徐申如的重金酬谢,徐志摩如愿成为梁门子弟。人们都说徐申如的一千大洋花在了刀刃上,这为徐志摩日后进入中国文坛开辟了路径。后人往往怀着实用或功利的眼光打量历史,这固然有其合理性。万事万物一旦成为客观事实,就不能单以主观臆断观其价值。作为父亲,徐申如在志摩的人生道路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其所作所为,不能简单地站在“势利”的立场上加以评判。没有哪个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在没有强大外力的胁迫下,也没有哪个父母愿意牺牲孩子的幸福去换取浮华的功名。从联姻张家到拜师梁启超,再到远涉重洋求学,徐申如为志摩预设的人生之路,也是一条曲折的侨易之路,可谓用心良苦!
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终于挣脱束缚的缰绳,迎向太平洋汹涌的波涛,到美利坚新大陆去寻求自己的梦想,开始了一段双边侨易的行动。
三、从中国到美国的双边侨易
从中国到美国的双边侨易,让徐志摩有了更高的人生追求,美国的生活体验不但使他有了浓厚的爱国热情,而且还使他改变了创办实业的理想,转而对政治和社会学发生了兴趣。值得注意的是,徐志摩侨居美国之后,也有都市侨易的行为,那就是从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城到纽约州的曼哈顿,这种侨居时期的都市侨易,同样对徐志摩的精神世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从大陆到海上的物质位移,让徐志摩接触了很多有志之士并产生了不少新鲜的认识。轮船要在海上航行二十余日,船舱和甲板俨然构筑起新生活空间。当年钱钟书在《围城》中所写方鸿渐在船上的所作所为,足以演绎“同舟共济”的传奇。轮船驶出吴淞口,便是无边的大海,滚滚的波涛扑面而来,彼岸的新大陆指日可待。志摩手扶栏杆,任海风吹乱头发,看远处海鸥的飞翔,无限的秋思涌上心头。每一次远足,都有未知的风景等着;每一次远足,都会让情怀得到涤荡。心潮澎湃之时,自当豪情万丈。在有限而无趣的空间里,志摩时常在甲板上散步、与人寒暄,打发海上只见太阳升起又落下的无聊时光。和志摩同赴美国的有清华留美预科的62名庚子赔款留学生,57名自费留学生。与志摩时常聚在一处的有杭州一中同学董任坚、海宁的查良钊、湖州的朱家骅,此三人算是浙江同乡,还有刘叔和、李济元、汪精卫等人。这群人正值青春年少,风华正茂,民族理想远大。他们的言谈自然也深深地触动了志摩。所乘轮船“南京号”途径日本横滨、美国夏威夷,沿途的所见所闻,让志摩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他挥笔疾书,在轮船上写下了气势恢宏的家书:“今弃祖国五万里,违父母之养,入异俗之域,舍安乐而耽劳苦,固未尝不痛心欲泣,而卒不得已者,将以忍小剧而克大绪也。”[4]这封家书“是现在所知道的、最早使用‘志摩’这一名字的文书。此前均用谱名徐章垿,就是到美国后入学所用的名字,仍是徐章垿”[5]。徐志摩胸怀天下的气度,青年人的远大抱负以及民族的忧思等跃然纸上。
徐志摩抵达美国后所选学的专业,对他以后的人生发生了关键性影响。1918年9月4日,徐志摩终于踏上了新大陆,他的梦想也即将开启。他在给老师梁启超的信中说,他到达旧金山后,“横决大陆,历经芝加哥纽约诸城,今所止者,麦斯省之晤斯忒也”[6]。徐志摩到达的是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城,入读克拉克大学。他在克拉克大学选读的是历史系,选学的科目有《欧洲现代史》、《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商业管理》、《劳工问题》、《社会学》、《心理学》、法文和西班牙文等。徐志摩没有选学经济专业,只有一门《商业管理》课与其要做中国汉密尔顿的理想有关。他的选择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原因不得而知。但正是他在美国的求学经历,改变了他打算日后回国作金融界精英的目标,其引发的精神质变非同小可。
徐志摩在美国学到的远不止几门课程知识,美国人的爱国热情对他触动很深。美国是世界强国,是国际大事的风向标。美国虽远离欧洲,但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给这块大陆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徐志摩发现这里的人关心战争,与自己的国家站在同一立场,支持美国军队。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民众获悉此讯,欣喜若狂。克拉克大学旁的街道上游行的人群鱼贯而行,他们脸上的表情折射出身为美利坚合众民族而自豪的心态。作为远道而来的异邦人,徐志摩以旁观者的身份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睹物思情,太平洋对岸的祖国又是什么境况呢?一战后,中国的处境和待遇在此不必赘述。志摩被强大的美国震动,被美国人强大的爱国热情震动。他希望祖国能够强大,希望同胞能够觉悟。
1918年12月,徐志摩参加哈佛大学留美学生组织的国防会。据当时在哈佛大学的吴宓介绍,国防会在国难深重的关头成立,目的是唤醒国人,“共事抵抗外国之侵略与凌逼,以救亡图存而已。”入会者,“皆留美学生中之优秀分子,确实热心爱国者”[7]。志摩加入此会,足以表明他有真挚的爱国情怀。关于志摩入会的情形,吴宓有清晰的记载:“一日,有克拉克大学的两位中国学生,来加入国防会;其中一位李济(济之),另一位便是徐章垿,字志摩。照例签名注册之后,大家便畅谈国事和外交政治等,以后还会见过几次,所谈仍不出此范围。”[8]12月22日,徐志摩在哈佛大学与吴宓第一次会面,后来他又造访过几次,均是为着谈论国事的目的。徐志摩爱国热情至此,与他的留美经历密不可分。当初太平洋上的宏愿,抵美后的所见所闻,都让他这个弱国子民有了强国的梦想,爱国之情由是与日俱增。志摩和室友商订了日常生活章程:早上六时起身;七时朝会;日间刻苦学习、阅读报刊、锻炼身体;傍晚面对祖国方向,高唱国歌;晚上十点半就寝。这是一份简单而充实的作息表,朝会即与同屋的李济、董任坚、张道宏等商讨国事,交流鼓励,以确保明志之态。唱国歌表露出他们的爱国心,以不被强大的异域文化所同化。白天所为,也都是积极向上的学习和锻炼。
徐志摩虽出身富家,但到美国之后,有了自食其力的想法。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他曾到乔治湖附近的餐厅作服务生。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把盘碟、刀叉收到小推车上,运到厨房后的水槽清洗干净。从小养尊处优的志摩,洗刷餐具的工作自然是一大挑战,几个来回就累得腰酸背疼。有个周末,由于餐厅生意特别好,工作量加大,导致志摩体力透支,推车倾斜,器皿倒在地上,这令他尴尬不已。为磨练意志,他参加了克拉克大学的陆军训练团队,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志摩从行动上改变了自己,不再是枕睡在安乐窝里的富家公子。他的英文进步很快,加上学习努力,他于1919年6月获得克拉克大学的一等荣誉学位,成功申请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1919年9月中旬,徐志摩来到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政治学。如果说徐志摩在克拉克大学懂得了奋斗和爱国,那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则完成了人生目标的转向,他对政治思想、哲学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实业。徐志摩的父亲与实业家张謇是至交,受“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希望徐志摩将来投身金融界,把徐家的实业管理妥当。但是,来到美国后,新知识和新思想改变了徐志摩的初衷。他在克拉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所学均与金融和实业相去甚远。在哥大期间,徐志摩对社会主义思想发生了兴趣,被中国学生称为“鲍尔雪维克”。社会主义思想改变了徐志摩,他主动摒弃实业救国的理想,站在劳工阶级的立场上,看到工厂的烟囱、铁轨等就会想到工人的艰辛。徐志摩思想的转变更多来自美国工业文明的压迫。且先不说徐志摩,就拿后来的新月同人闻一多来讲,他曾这样描述芝加哥:“抬头往窗口一望,那如像波涛的屋顶上,只见林立的烟囱开遍了‘黑牡丹’,楼下是火车,电车,汽车,货车,永远奏着惊心动魄的交响乐。”[9]在闻一多留美的同学中,有两位遭遇车祸身亡,这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引发的恶果。1923年3月30日,闻一多给四位即将赴美的友人写信说:“这封信是恭祝四友横渡太平洋之喜,或是预吊四友闯入十八层地狱之哀的。”[10]将美国形容为“十八层地狱”,足以见出闻一多对工业社会的厌恶。有学者对中国留学生的心态作了这样的分析:“西方社会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机械文明,注重实利的人际关系和紧张激烈的生存竞争,对于来自东方农业文明古国、诗书传家的中国学子来说,是一种更实际的压迫。”[11]虽然徐志摩在西方社会生活游刃有余,但最初两年所遭遇的文化冲突,想必也是让他痛恨工业文明的源头。
留学美国两载,徐志摩经历了多次蜕变。他放弃实业救国的理想后,开始关注社会问题;他决定放弃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到英国寻求新的人生理想。1920年9月24日,徐志摩离开美国,穿越大西洋,开始了新的寻梦之旅。
四、从美国到英国的双边侨易
从中国到美国的双边侨易让徐志摩的兴趣从经济转变为政治,而从美国到英国的双边侨易又使他从社会现实主义者转变为浪漫的抒情诗人。徐志摩侨居英国的最初目的不是为了文学创作,而是为着探求政治和思想的真髓。
以往学者都说志摩奔赴伦敦的原因是为拜师大哲学家罗素,但也有人认为此说经不起推敲。那他为何漂洋过海来英国呢?据赵毅衡先生在《现代留学史笔记》中所讲,志摩到英国实际上是为了投奔政治学家拉斯基:“金岳霖是另一个传奇式换专业人物。1914年到费城学商业,得学士;1917年去哥大研究院学政治学,得到博士学位;与徐志摩、张奚若听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拉斯基教授演讲,大感兴趣,一起转学到英国学政治思想史。”[12]志摩在美国求学期间,开始对政治发生兴趣,因在纽约听政治学家拉斯基的演讲,被其广博的知识和敏锐的洞察所折服,决定跟随拉斯基学习政治学。拉斯基是英国人,当时在哈佛大学任教,1920年回到英国,受聘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也就是在他离开那年,徐志摩也随其到了英国。为什么徐志摩不提及这段往事呢?刚开始的时候,志摩学习态度端正,希望早日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第一学期选了六门课程。但不久,他开始逃课,校方很难见到这个东方学生,无奈之余只好求助于导师。弟子逃学被校方知道,并找上门来,这自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因此,“拉斯基后来对徐志摩是不满意的,师生之间想必还发生过龃龉。徐志摩追忆这段经历时,有意回避扯到拉斯基,也在情理之中。”[13]不管是为了罗素,还是为了拉斯基,徐志摩选择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都是合理的结果。一则罗素去了中国,志摩不可能折返回美国,只好留下来继续学习,必然会选择一所学校;二则拉斯基在此,入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正符此行的意图。志摩在此意欲攻读博士学位,但他醉心于英国社会的各种新奇事儿,很难静下心来学习。这一时期徐志摩给梁启超和蒋百里创办的《改造》杂志写了几篇文章,比如《安斯坦相对主义(物理界大革命)》、《罗素游俄记书后》、《评韦尔斯之游俄记》等,均是政治新见或科学新知。其中,1921年8月发表的《安斯坦相对主义(物理界大革命)》一文,是当时国内言说爱因斯坦相对论最清楚的文章,据说大学者梁启超在看了志摩的文章后,才懂得了相对论的道理[14]。
拉斯基曾经将徐志摩从经济拉向政治,而罗素则将他从政治拉向深邃的哲学。徐志摩在旅居英国期间,频繁地和罗素接触交流,罗素对徐志摩的思想行为的影响是深刻的。一是在政治主张上,罗素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徐志摩1926年在主编《晨报·副刊》时,发动了反共的论辩,不能不推及罗素的影响。也正是这次论辩,让徐志摩在后来的文学史上,长时间处于沉默的地位。二是在家庭婚姻上,罗素一生对两性关系问题始终抱有一种自由主义的态度,他认为爱情是自由的,不应该受任何外在因素的约束。只要双方的感情有了裂痕,婚姻就不应再勉强维持下去。徐志摩在处理他和张幼仪关系时、在辛苦地追求林徽因时、在痴心地追求陆小曼时,不能不说是受了罗素的影响。
徐志摩广结英伦名士则又让他的兴趣从哲学转向了文学。赵毅衡先生在《徐志摩:最适应西方的中国文人》中这样写道:“徐志摩结交名人的本领,可能盖世无双:1921年徐到英国时,是个二十四岁的青年学生,尚未想到写作,只是个文学爱好者,政治、经济,哪一门都念得半不拉儿。结交的却是大作家威尔士、康拉德,著名批评家墨雷,桂冠诗人布城基斯,英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家拉斯基,最重要的美学家弗赖,而当时知识界的领袖狄金森竟成了徐的保护人。”[15]作为旅居英伦数十载的学者,赵先生语出有据,徐志摩在英国的交友令人惊叹。1920年11月26日,在家书中,徐志摩饶有兴味地说起在英国的交友情况:“儿尤喜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益倍蓰,真所谓学不完的聪明。儿过一年始觉一年之过法不妥,以前初到美国,回首从前教育如腐朽,到纽约后,回首第一年如虚度,今复悔去年之未算用,大概下半年又是一种进步之表现,要可喜也。”[16]徐志摩通过陈西滢和章士钊,结识了威尔斯,通过威尔斯结识了魏雷,通过魏雷结识了卞因等人。通过林长民,又结识了剑桥王家学院的狄更生,通过狄更生认识了傅来,通过傅来认识了嘉本特,而且还通过狄更生的介绍信,求得了哈代的接见。
与英国名人的交往,让徐志摩学到很多知识,其对待生活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将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由社会现实关怀转向了生命情感关怀,他的兴趣也由政治转向了“艺术”和“美”——文学。这是徐志摩在英国的最大转变,也是他人生的第二次转变——从政治转向文学,从此他在文学和诗歌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就卓著的诗人和学者。
五、徐志摩侨易的结局
徐志摩一生经历了多次异文化结构区间的物质位移,其精神世界也在一次次侨易中发生着质的变化,以至于他在回国之初已经养成了自由文化人的心态,并且习惯了英伦绅士般的生活。这与徐志摩最初的人生理想相去甚远,其精神气质和性情也不可同日而语。
徐志摩从不以偏激的心态处事,人前总是风度翩翩,绅士作风。对志摩的这种个性,魏雷曾在文章《我的朋友徐志摩》中说:“徐志摩虽然崇拜拜伦,但为人并没有多少拜伦作风,比如缺少拜伦之愤世嫉俗。”志摩在国内文坛从不主动树敌,总是友好宽容地待人。比如鲁迅当年曾作诗《我的失恋》来讽刺志摩的恋爱状态,尽管有笔墨相讥之芥蒂,但志摩还是较为客观地评价鲁迅的文章。他曾在给魏雷的一封信中极力推荐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我们一个朋友新出一本《小说史略》颇好,我也买一本送给你。”[17]能在别人的挖苦面前,如此淡然处之,除了志摩,恐怕难寻第二人。
徐志摩回国后,虽然在新文学园地里收获了丰硕的果实,而且在爱情路上得到了京城名媛陆小曼的爱情,但他最终却生活在苦闷与彷徨之中。1928年6月,徐志摩为躲避家庭的残缺现状,为躲避无法正视的婚姻,他决定再次出国。这次出游,是徐志摩此生最后一次出国。也许心里隐隐觉得时日不多,他要将之前走过的地方,重新再温故一遍。照例是乘船,照例经由日本,横渡太平洋到达美国;照例穿越大西洋达到欧洲,照例去了剑桥,照例拜访昔日的朋友,甚至绕道去印度,见到了思念已久的泰戈尔。旧地重游,物是人非,徐志摩感慨良多。期间,徐志摩写下了名诗《再别康桥》。这不是单纯的怀旧和道别之词,而是诗人对曾经生活的道别,对曾经生活的记忆与珍藏。英国绅士风度的生活、政治理想、爱情信念等,当年那个满是英伦风情的徐志摩,已不复存在。他往后的生活去向何方?徐志摩自己心里没有方向。
作为特殊的侨易个体,徐志摩的侨易行动和所经历的侨易事件无疑是成功的,但其变创后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却在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遭遇了尴尬。这当然也符合侨易学的思维模式,那就是过快的变化会破坏固有的秩序,因此,“就人的思想观念发展而言,渐变与渐常这两者居于常态,而变创则是异态,必须蓄积到一定程度以后才发生质性变化的;个体如此,文化体的变化则更是一种长时段的积累过程”[18]。徐志摩侨易行动之后获得巨大的精神质变,必然与渐变的中国社会形成反差,其矛盾冲突自然就不可避免了。
[1][18]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1、228页。
[2]郁达夫:《志摩在回忆里》,《新月》(志摩纪念号),1931年第1期。
[3]徐志摩:《致徐蓉初》(1915年8月23日),载于韩石山编《徐志摩书信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305页。(注:韩石山先生在书信集中,将此信的时间确定为1914年8月23日,而徐志摩中学毕业去北京求学的时间,应该在1915年。)
[4]徐志摩:《民国七年八月十四日启行赴美分致亲友文》,《徐志摩全集》(第六辑),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99-102页。
[5]韩石山:《徐志摩传》,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6]徐志摩:《致梁启超》(1918年秋),《徐志摩书信集》,载于韩石山编《徐志摩书信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7页。
[7]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82页。
[8]吴宓:《徐志摩与雪莱》,《宇宙风》(第十二期),1936年3月1日。
[9]刘烜:《闻一多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0页。
[10]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11]李兆忠:《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页。
[12][15]赵毅衡:《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人物》,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11页。
[13]刘洪涛:《徐志摩与剑桥大学》,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2页。
[14]林徽因:《悼志摩》,《林徽因文集》,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版,第84页。
[16]徐志摩:《致双亲》(1920年11月26日),载于韩石山编《徐志摩书信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17]徐志摩:《致魏雷》(1924年2月21日),《徐志摩书信集》,韩石山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5页。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Xu Zhimo's Life Ambition from the Viewpoint of Kiao-Iology
XIONG Hui
(Modern Chinese Poetry Research Institut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Kiao-Iology;Xu Zhimo;life ambition;the action of Kiao-Iology;the event of Kiao-Iology
Xu Zhimo had the following actions of Kiao-Iology:the regional Kiao-Iology from Xiashi to Hangzhou changed Xu Zhimo from a schoolchild in private school to an ambitious young man with the thought of the world,the urban Kiao-Iology from Hangzhou to Beijing changed Xu Zhimo from an idealist to an industrialist who wanted to go abroad to study,the bilateral Kiao-Iology from China to America changed Xu Zhimo's ambition from economical field to political field,the bilateral Kiao-Iology from America to England changed Xu Zhimo's ambition from the political field to literary field.The complex actions of Kiao-Iology changed Xu Zhimo's conception about life and values,and his living style of English gentleman must meet with the contradiction and embarrassment in the realistic context of China.
I206.6
A
2095-5170(2014)04-0016-07
[责任编辑:周 棉]
2014-03-11
熊辉,男,四川邻水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