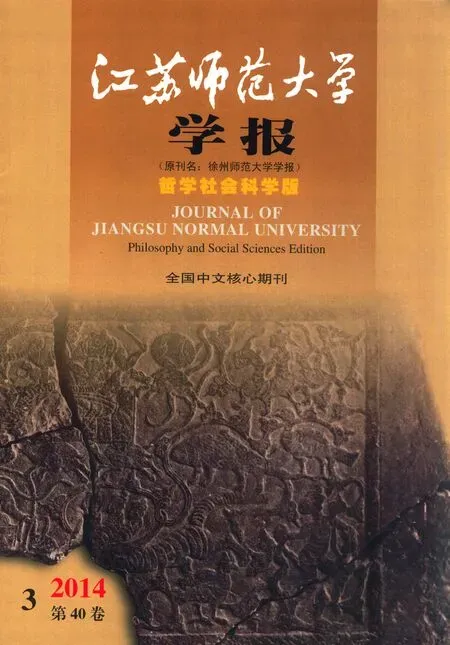从二战后美国公民权利运动看政府角色嬗变
吕庆广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无锡 214122)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战后美国所呈现出的和谐一致局面逐渐为一浪高过一浪并日趋激烈的社会运动所打破,无论是作为先行军的黑人民权运动,还是更加声势浩大的学生反战运动、嬉皮士反主流文化运动、激进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其核心目标或宗旨大多不外于促进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正、建构真正的社会和谐。因此,所有这些运动可以称之为公民权利运动。这些运动的发展与美国从联邦到州及各大中城市的各级政府的态度密切相关,运动目标的实现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和运动组织间的互动制约。因此,对互动关系中政府角色进行探讨,对于认识美国社会战后和谐化进程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由于社会运动的高潮是在1960年代,故本文主要以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作为研究对象。
一、战前美国社会运动中的政府形象
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美国是社会运动向来比较发达的国家。早在殖民地时代,以宗教和政治理想主义为动力的社会实验运动就已成为北美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后至19世纪末,废奴运动、农民运动、工人运动高潮迭起;进入20世纪,进步主义改革运动、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妇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更是构成一幅幅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在这些运动中,美国各级政府所采取的立场和对策是什么呢?
自启蒙时代以来,自由主义政治话语在西方政治哲学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反映在政府与社会关系中即为政府不干预经济与社会活动的自由放任思想被奉为金科玉律。政府管得越少就越好的格言在美国长期被视为评判政府行为的当然准绳,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但这主要体现在经济与社会生活领域,在政治领域则不然。面对形形色色的突发的或有组织的公民社会政治运动,国家通常的反应是“压制或者是尽力维护国家权威”[1]。在战前的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1890年前,社会运动大多对政府持敌视态度,而政府同样把社会抗议运动视为异己力量而选择站在其对立面,在法律设定的范围内,充分发挥政府的镇压职能。无论是早期对威士忌酒抗议的弹压,19世纪前期对南方种植园主立场的支持,对西进运动中土著印第安人权利的漠视,还是工业化时代在城市中对激烈劳资冲突中资方利益的维护,对要求改变黑白种族关系和男女性别关系中不公正现象呼声的充耳不闻,甚至不惜出动坦克等暴力工具对付大萧条中饥肠辘辘的退伍老兵和其他和平求助者[2],都是这种镇压职能充分发挥的经典表现。至于对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信仰者进行迫害的帕尔默袭击(1919年)、冷战初期对美共成员的逮捕和在政府部门与高校强迫忠诚宣誓(1950年代)等则更充分体现了政府的这种倾向性。虽然美国是世界近代史上较早实行共和政治的国家,更是最早实现普遍民主的国家,但所有这些事实却足以证明美国民选政府在对待社会不满及其抗议的历史表现上与许多保守主义政府比较,并没有太大区别。
具体而言,在20世纪中叶以前,美国政府针对社会运动的态度和立场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以法律为依据坚决维护自身的权威地位。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统治工具被充分而有效应用,即使是在中央权力极其软弱的邦联时期,当谢斯领导数百农民暴力抗议重税苛政时,在援引法律条例派遣军队镇压过程中,政府的反应堪称快捷;成立联邦后,面对参与威士忌酒抗议的民众,政府的反应同样铁腕无情;19世纪40年代,当梭罗以个人方式发起非暴力不合作斗争以抗议政府的非正义政策时,政治合法性受到挑战的权力部门立即以判决入狱的方式作出回应;20世纪中叶,知识界一些人士以维护自我基本人权为由拒绝忠诚宣誓,权力部门则以剥夺其工作机会进行惩戒,如加州伯克利分校就有不少教师因此失去饭碗。在这当中,权力部门不时存在强制和暴力选择上的偏好。如19世纪80年代以武力对付芝加哥大罢工工人,20世纪初期对参与“返回非洲运动”的骨干分子加维等人强制驱逐出境,冷战之初把大批美国共产党人投入牢房等,事例不胜枚举。其二,在进步力量与保守势力的较量中,往往站在后者一边。内战前,废奴运动引领着美国社会正义的方向,反奴隶制人士面对的不仅是监狱之灾,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内战后的重建结果是,吉米·克劳法在南方盛行开来,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ressy v.Fugerson)中“隔离但平等”的荒谬判决使被解放的黑奴的人权受到“合法的”践踏;在激烈的劳资冲突中,政治权力每每与财富结盟。其三,总是从道德的角度评价运动的参加者和运动本身。认为参加社会运动的人不是阴谋家,就是人品低贱者。例如,对参与劳工运动或左翼政治组织的积极分子和领袖人物,往往用有色眼镜视之:不是外国利益的代理人就是里通外国的叛国者。20世纪30~40年代,美国共产党被看作是苏联利益或斯大林的代理人,是潜伏的第五纵队。其四,对社会运动与反社会运动的组织和成员采用双重标准。这在司法和执法领域尤为突出。比如左翼组织的领袖和骨干往往被从重量刑,而右翼组织成员则多从轻处罚。
简单地说,在20世纪中叶前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就像社会大众厌恶政府一样,美国政府对社会运动持有一种恐惧心理,基本上不是站在社会运动的对立面,就是作为对立面的支持者出现的。
然而,以上情形在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时代开始发生变化,而真正的转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际政治和国内社会环境的变化,美国政府在针对公民权利运动的政策选择上,不再是简单地走压制与权威维护单行道,政府与社会运动间的关系显得复杂而微妙。
二、战后美国公民权利运动的勃兴与政府的对策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重要后果的非殖民化浪潮在战后高潮迭起,使世界殖民主义统治体系土崩瓦解,在有力地促进国际社会民主进程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刺激了西方社会内部民主化进程的新发展。在美国,在权利、社会地位和机会方面长期处于不公平境地的少数族裔、妇女、同性恋者等群体,从亚非拉一个个挣脱枷锁的民族那里领悟到奋起抗争的必要性。与此同时,自20世纪初进步运动和30年代“新政”以来社会经济改革的持续推进也使他们增强了行动的信心,因为政府在弱势群体和个体权利保障问题上无法再无动于衷。例如,战后初期杜鲁门政府的“公平施政”纲领已经涉及到黑白种族关系的公正问题。1950年代美国南方的抵制公共汽车运动的发生,则是新政改革和二次世界大战共同培育的社会变革精神的直接产物。它有力地传达出一个强烈信号:长期作为美国社会二等公民的黑人群体再也不能对施加于自身的种种不公忍气吞声了,黑人要争取宪法规定拥有的基本公民权利。由此开始的黑人民权运动在教育、就业、住房、福利待遇等领域向现行制度发起挑战,在1960年代演变为无数城市暴乱,使美国社会陷入分裂为白人和黑人两个社会的险境[3]。与此同时,因种族、性别、经济不公和越南战争引起的学生运动也从温和的改革走向激进的文化革命。运动的社会理想主义诉求对中产阶级传统价值观和社会结构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波。由学生运动派生而来的女权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真正使公民权利成为人的基本自由权利的基石。
面对战后公民权利运动的蓬勃发展,以维护社会法律和道德秩序为职责的美国联邦和州等各级政府是如何回应的呢?我们可以从政府对待社会运动和逆向社会运动的态度与措施两个层面的分析中寻找答案。
在应对战后公民权运动方面,美国联邦和州政府的对策大致有以下几种:
1.镇压或压制。一般来说,权力部门在对付社会运动中的激进组织时每每采用强硬手段。例如,1960年代针对新左派和激进黑人民权运动,约翰逊政府动用一切公开和秘密的力量进行打压。尼克松则一上台就警告:“挑战一项具体政策是一回事,挑战政府权利则是另一回事。”“我们有权力进行回击。”[4]因此,当街头政治规模迅速扩大并伴以大量城市暴乱,对政府的内外政策产生冲击时,政府手中的警察暴力不断增加,从高压水枪到真枪实弹几乎无所不用,1970年5月发生在俄亥俄肯特州立大学校园警察枪杀学生事件看似偶然,实为必然。武力镇压对扼止运动暴力化趋势是十分有效的,如暴烈的“气象员”(Weatherman)组织在经过几次武装斗争的挫折后,终于意识到“枪并非都是革命的”,把使用炸弹和枪视为唯一革命行动是“军事错误”[5]。
2.内部分化。1957年,为对付美国共产党人,联邦调查局搞了一个秘密反谍计划:COINTELPRO,1960年代该计划转而用于对付公民权利运动中的激进组织及其成员。联邦调查局局长E.胡佛亲自部署,动用大量人力物力,采用反宣传、窃听电话、制造并散布谣言、鼓励告密以及派人打入组织等手段从内部分化瓦解运动组织。而中央情报局也有MERRIMAC和RESISTANCE两个计划[6]。“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等激进团体在1960年代末走向瓦解,个中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3.支持、合作与利用。1960年代初,肯尼迪的“新边疆”点燃了年轻一代变革社会的激情,反贫困和反种族歧视斗争把大批高校学生推向社会,肯尼迪特别是约翰逊政府支持并充分利用学生的激情,不仅帮助自己在大选中获胜,也不仅借用学生运动的政治压力促成一系列改革法案的通过,更重要的是在实施改革措施上与社会运动组织开展合作,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肯尼迪和约翰逊面对风起云涌的公民权运动,在多个场合明确表示同情与支持,并把公民权运动提出的种族平等、经济公正等诉求变成施政纲领中的重要内容,从而在执政党和社会运动之间建立起共同话语,进而推动双方走向合作。比如,约翰逊经常到一些高校发表演说,对其政策进行解释,争取公民权运动团体的理解与支持。在城市反贫困运动中,以SDS为代表的许多高校学生组织在华盛顿设立联络处,接受政府资助,积极与政府开展合作,在芝加哥、巴尔的摩、克利夫兰、费城、纽瓦克、波士顿等城市破败街区致力于社区扶贫与经济复兴活动。虽然学生组织是抱着发动社会底层的社会实验目的参与的,但客观上却成为政府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抬轿人。
4.容纳政纲等。在1960年代,激进运动中最著名的政治口号是“参与民主”(participation democracy),寻求最大限度的平等,美国民主党在其政纲中很快吸收了这一口号,使之吸引了无以计数的年轻人。尼克松上台后,共和党政府则对环境保护运动作出回应,政府一方面全面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另一方面则把联邦环保局实际上交给了环保运动人士。与此同时,两大党特别是民主党甚至还向社会运动中的激进党派与团体开放,把它们吸纳进来。例如,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政治目标的美国社会民主党(SDUSA)自1972年成立以来就一直在民主党内活动,稍晚成立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党(DSA)也同样名列民主党内[7],民主党把自身变成了左翼政治团体的政治平台。
政府对逆向社会运动的支持、鼓励与抑制。所谓逆向社会运动,是指反社会运动的势力及其行为,如19世纪前期南方种植园主和政治保守派发起的反废奴运动的主张与行动;镀金时代企业主针对有组织工会组织并实施的反对扩大工会和工人权利的种种政治性活动;内战后反对黑人民权的极端组织三K党及其活动;高校中因应左翼力量而产生的多少具有教会背景的保守组织如“基督教青年学生会”的活动,等等,都属典型的逆向社会运动。在美国政治史上,逆向社会运动每每扮演了政府工具的角色。
如前所述,美国政府在战前的岁月里,其立场与态度明显倾向于保守,对待逆向社会运动不是公开支持就是暗中为之撑腰,对许多极端或过火的行径不是一路绿灯就是熟视无睹。战后这种情况虽然仍在持续,如密西西比州政府到1960年代中期仍在财政上大力扶持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白人公民委员会,1960-1964年间,州主权委员会向白人公民委员会论坛捐赠的转帐款近20万美元[8]。然而,从整体上看,变化还是不容置疑地发生了。首先,政府全面强化对极端反社会运动团体行为的控制与压制。1960年代初,随着民权运动的高涨,三K党和白人公民委员会等南方白人至上组织的行为日益走向极端化。针对民权组织机构和个人以及黑人群体的暴力时有发生,如对民权运动积极分子进行侮辱、恐吓甚至谋杀,对黑人教堂投掷石块、燃烧瓶甚至炸弹,纵火焚烧黑人房屋等事件有增无减。1954-1965年间,《纽约时报》报道的发生在南方的反公民权运动事件达1500多起,导致29人遇害,1000多人受伤。对此,以北卡罗来纳为代表的南方许多州相关权力部门采取较为强硬的手段进行压制。在联邦政府层面,早在1950年代艾森豪威尔时期,政府就曾运用国民自卫队干预阿肯色州小石城事件,以确保教育领域种族平等判决的法律权威不受蔑视。肯尼迪政府则在对小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非暴力民权运动明确表示支持的同时,对反种族平等团体的极端言行进行谴责。在州政府层面,虽然有路易斯安那、阿拉巴马、密西西比等州政府仍顽固地站在逆向组织一边,但以北、南卡罗来纳州为代表的一些南方州政府则逐渐顺应时势,与种族隔离政策告别。1958年,北卡州长霍奇斯公开抨击三K党,其继任者T.桑福德则不仅警告三K党不要进行暴力活动,还让州调查局(SBI)对三K党和白人公民委员会进行秘密渗透与打压。在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霍林斯向反公民权个人和团体发出明确信号:白人反公民权运动的暴力在南卡罗来纳州没有容身之处。当自由乘车运动分子路过南卡罗来纳受到当地白人极端分子袭击时,州警察毫不迟疑地将袭击者逮捕,警察亲自护送,让自由乘车者顺利离境。在权力部门的打压下,南北卡罗来纳州的三K党等极端白人组织规模不断萎缩,影响力明显下降。
其次,巧妙利用逆向运动力量来平衡公民权运动力量的影响。在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虽然对白人至上主义者及其团体进行打压,但他同时也指责公民权运动关于种族平等的主张,以此表明政府只是在维护法律与秩序。当自由乘车运动人士到达时,为防止白人至上分子出来捣乱引起冲突,州长下令对自由乘车者进行调查,并暗示他们可能受共产主义者教唆。这种巧妙的手法既控制住了前者,又限制了后者影响的扩大。
再次,推动逆向运动团体或组织革故鼎新。各州政府通过多种手段推动逆向团体向合法化和非暴力化方向转变。政府的强大压力迫使许多极端组织如三K党逐步改弦更张,转向和平轨道。自1960年代开始,三K党人虽然仍不时犯案,但明火执仗的滥施暴力情形已不多见。
最后,联邦政府自上而下地给顽固站在逆向运动一边的州施加压力,使它们转向。除来自总统、司法部长等人的行政指令和口头指责外,主要通过联邦法院司法案例解释扩展司法部门起诉反公民权暴力的范围,使密西西比、阿拉巴马等州默许支持逆向组织无视法律行为的做法难以为继。1960年代中期,密西西比等州开始启动司法程序,打击三K党等极端组织。
概括来说,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对策逻辑很清晰:通过公开的政治纲领亮明其自由主义改革立场,以宣示其进步主义抱负;以维护法律与秩序的理由对正向和反向运动中的激进和极端势力进行镇压与打击,以彰显其权威并标示其政治容忍的底线;以与温和公民权运动组织的合作化解来自公民权运动本身和共和党政治对手的双重挑战,并为改革创设出一个同盟者和群众基础。
三、政府行为转变的原因
战后美国政府应对公民权运动的政策和策略与以往相比,有了明显变化。如果说过去侧重于国家机器镇压职能的充分发挥,那么,现在则倾向于吸收、引导、利用甚至于合作。简言之,过去重视刚性手段的威力,现在则强调柔性手段的实效。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这样的行为模式发生转变?
第一,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福利国家的发展是导致转变的首要原因。1929-1933年的大萧条及随之而来的罗斯福“新政”是美国社会发展史的重要转折点,之前的一个多世纪是美国由一个农业社会向工业和城市社会转型的时期,其特点是经济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政府不干涉主义。结果是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动荡、紊乱无序、劳资关系紧张、政治生活中的腐败以及社会经济生活中严重的不公。“新政”改革使政府从经济社会的局外人变成了参与者或监管人。政府不仅要维护市场的有序运转,更要为社会成员的福祉负起责任,促进社会公正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种福利国家体制的基本要求使得政府职能空前扩大和强化。与此同时,福利国家道路的开辟客观上使政府与社会抗议运动间传统的对立关系因双方在价值、目标和话语上的重叠和共鸣而改变,进而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了政治基础。
第二,新政开始的传统政党、改革左翼与社会运动间的结盟缔造的政治合作传统的内在机制使然。国家权力仅靠一己之力很难顺利推进其职能目标的实现,与社会进步或改革力量进行合作或结盟成为必然的和最为重要的战略性选择。事实上,罗斯福改革的成功就是与左派、自由派等进步力量结成改革同盟的结果[9]。这一同盟持续了30多年,在20世纪30至60年代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浪潮,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社会的基本面貌。
第三,社会变迁与政党社会基础变化的影响。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开始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或后现代社会转向,在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向服务性经济;在职业结构上,白领或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处于主导地位;从中轴原理上看,如果说工业社会是以资本为中心运转的资产阶级社会,后工业社会则是“围绕知识组织起来的”[10]知识阶级社会;在政治上,工业社会实行有限民主,如在相当长时期内,只有部分男性拥有政治投票权,后工业社会则是普遍民主,因为社会结构的基石是占人口最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政治投票面的公民化,必然对政党行为模式产生根本性影响。作为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两大党,深知民意不可违,为了生存与发展,尽可能在不同利益群体中扩大社会基础,这已成为其必然选择。
第四,政治代沟和价值嬗变的影响。社会学中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世界是人的行动建构起来的,故对人的行动的理解是理解社会现实的前提。人的行动则与人所遵奉的价值和理念直接相关。因此,在政治领域,代际差异是现实的客观存在。战后时期的政治家,如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等,大多出生于20世纪,没有经历镀金时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喧嚣,却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大萧条的困苦、罗斯福大刀阔斧改革的灰宏气势以及其中折射出的进步主义和合作精神,这种榜样力量塑造出战后自由主义政治家的新理想主义情怀和寻求合作的心理惯性。肯尼迪和约翰逊是典型代表。1960年代以前,两人就是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改革的追随者和忠实参与者。他们与艾森豪威尔所代表的前一代政治家秉持19世纪弱政府的保守政府治理理念完全不同,他们的主张是:自我完善、乐观向上、积极进取、创新与超越,代表穷人、少数民族、弱势群体,“挽起袖子,改造美国”[11]。这种理想主义与战后婴儿潮一代在社会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形成了共振。
值得一提的是,战后美国西部和南方阳光地带在经济上的崛起带来了政治版图重绘和权势转移,来自西部的政治家越来越多地进入权力中心,约翰逊是其代表。而西部在美国文化版图中与东部明显存在差异,与东部的高雅而保守相比,西部自由而开放,充满活力,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J·特纳所说,西部“是一眼神奇的青春之泉,美国始终沐浴于其中,并不断恢复活力”[12]。事实上,西部文化更接近清教传统:超强的自由理念,凝重的个人主义,深厚的乌托邦意识,久远的无政府反权威精神[13]。至于公平、正义、合作,更是清教的基本价值和西部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约翰逊政府致力于社会改革并与公民权运动开展合作的内生动力即在于此。
四、公共权力与社会力量互动的结果
公共权力部门利用社会运动的力量有力地促进一系列社会改革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在约翰逊执政的五年多时间里,美国国会通过的改革法案数量之多,堪称空前绝后,仅环境保护立法就超过100个,如果没有社会运动力量的支持与配合是难以想象的。
社会运动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公共权力资源向目标迈进。1960年代的公民权运动,其具体目标是在政治、经济、就业、教育和社会生活多个领域消除以肤色、性别差异等为理由存在的偏见和制度性不公,以及因此导致的族群对立与冲突,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不同种族和利益群体间和谐相处的梦想。对于公民权利运动参与者,正是这一目标的神圣唤起他们内心巨大的热情,但他们很清楚,这一目标最终要由拥有巨大资源的国家或政府来实现。通过对致力于改革的政府及其政策的支持与合作,推动政府把社会运动的政治诉求转变为政府或执政党的政策内容,一直是公民权运动与政府合作的出发点。在与政府合作中,一个基本的要求是承认并维护政府权威,帮助政府应对挑战,渡过危机。最好的例子是1964年大选期间,国内的种族骚乱给共和党候选人提供了攻击约翰逊政府的机会,民权领袖迅速行动,让各地的黑人骚乱团体停止活动,减轻约翰逊的压力,并在大选中踊跃投票给民主党,使约翰逊获得了61%以上的选民票,取得了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选举史上空前性胜利。
拥有权力的政党通过吸收社会运动群体的诉求融合了对立面,并使自身获得了活力。民主党由于1960年代与公民权运动的合作关系而吸收了较多的运动诉求,许多运动参加者顺理成章地加入了民主党,成为新生力量和之后年代里民主党内坚持社会改革的中坚。共和党虽然以保守著称,但尼克松政府面对内外困局,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社会运动的一些目标作为政府目标,如从越南撤军就是例子。美国政府能主动从越南撤退,这是出乎很多运动参与者所料的,这引起他们思考,并从激进立场逐渐后退。
社会冲突在互动中得以缓和,孕育了新的社会和谐局面。1970年代以来的美国虽然问题依然层出不穷,但与1960年代及之前相比,其和谐度明显上升,这得益于1960年代国家权力与公民权运动之间的互动,互动的结果是:社会运动从制度化政治的对立面或边缘区进入体制内,成为制度的一部分。把抗议政治力量从敌手化解为伙伴,这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强大的自我修复机制的一部分,成为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阀。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塞认为,社会的不满需要有排泄渠道,单纯压制只能使不满累积,对社会会形成系统性风险。是否拥有制度化的排泄不满的安全阀机制,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民主和健全的尺度。1960年代美国政府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和政府积极主动的作为已经构成一种其后历届政府萧规曹随的成熟模式,至于这一模式在应对现今的反华尔街社会抗议等新社会运动中会有何新发展,我们仍需拭目以待。
[1][8]杰克·戈德斯通:《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年版,第27、13 页。
[2]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9年版,第6-13页。
[3]Report of 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New York:New York Times Company.1968.pp.407-408.
[4]Kirkpatrick Sale.SDS.New York:Random House,1973.p.542.
[5]Roger G. Betsworth, the Radical Movement of the 1960s.Metuchen,New Jersey:The Scarecrow Press,1980,pp.302-303.
[6]Peter H.Buckingham.America Sees Red:Anticommunism in A-merica 1870s ~ 1980s. Clarement, California:Regina Books,1988.pp.128-130.
[7]"Leftist Parties of the USA",http://www.broadleft.org/us.htm.
[9]Rossinow,Visions of Progress:the left-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8.pp.103-142.
[10][美]D.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6页。
[11]王庆安:《“伟大社会”改革——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改革及其启示》,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12]Henry Nash Smith:《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页。
[13]吕庆广:《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