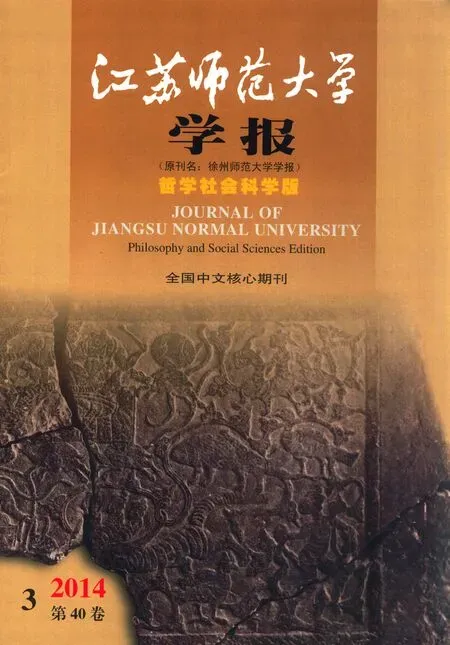边缘生存的讲述
——日本女作家大庭美奈子旅美三部曲解读
田 鸣
(外交学院外语系,北京 100000)
边缘生存的讲述
——日本女作家大庭美奈子旅美三部曲解读
田 鸣
(外交学院外语系,北京 100000)
大庭美奈子;《绿色落叶》三部曲;边缘人;后殖民主义
大庭美奈子的小说创作,主人公多为女性,且被置于两性关系中表现。其作品在从女性经验的视角观照女性日常活动的同时,与社会历史语境紧密关联的叙事亦颇引人注目。旅美三部曲《绿色落叶》便凸显出女主人公在性别、种族等多重身份覆盖下边缘“他者”的生存状态。作品一方面从性别、种族“他者”的视角,将置身异域主流群体中女主人公的生存艰难而无从认同的焦虑、困惑等边缘叙事的话语揭示出来,同时,还将女主人公在与白人主流群体之间彼此认同的艰难过程中所凸显的文化冲突及文化“他者”的这一语境表述于文本,彰显出作家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视野。
《绿色落叶》三部曲[1]是日本现代女作家大庭美奈子20世纪60年代旅美期间的作品,由上篇《无构图的画》、中篇《彩虹与浮桥》和下篇《跳蚤市场》组成。三部曲讲述了旅居美国的日裔女主人公左喜在异国的生存际遇,通过对左喜恋爱、婚姻及至孕育、流产等一系列女性经验的叙写,将其挣扎于灵与肉之间的人生故事以及在对自我主体的追求中边缘生存的焦虑话语呈现出来。三部曲的故事空间为偏远的美国阿拉斯加小镇,而主人公为亚裔有色人种,且是女性,更使其生存状态增添了几重边缘性。
一、性别、种族的“他者”
综观大庭美奈子的小说创作,主人公多为女性,且被置于两性关系中表现。其作品在从女性经验的视角观照女性日常生活的同时,与社会历史语境紧密关联的叙事亦颇引人注目。在作家早期的小说中,涉及种族、性别、文化身份的文本语境尤为显著。旅美三部曲便凸显了女主人公在性别、种族等多重身份覆盖下边缘“他者”的生存际遇。
在三部曲中,左喜经历了一个由未婚女性到为人之妻的人生过程。在文本的故事层面,主人公婚前是一个自由开放、率性而为和富有魅力的女性。婚后因不甘于现实的生存状态,只身离家并与其他异性交往。然而,细读文本不难发现,尽管作品在故事层面讲述了一个置身异域自由国度,我行我素、无视制度规约的女主人公的生存追求,但透过其文本的叙事话语则可以看出,在那个看似轻佻的人物表象下,当她欲以女性主体自我示人,置身主流群体异性中时,处境却非常艰难,处于无从认同的焦虑和边缘生存的困惑之中。
在上篇中,左喜的身份是日籍未婚留学生,开篇的叙事便是周围人对她与工艺课讲师鲍曼暧昧关系心照不宣的渲染,以及左喜与白人女性对立意识的表现。法国籍女孩西嫫奴是左喜的同学,亦是鲍曼的女助手,她因“来自欧洲富裕国家,而不受移民配额限制很早就取得了永居权”。此人时常刁难左喜。左喜对这个盛气凌人的女人满心不快,而鲍曼夫人、西西里岛女人索菲亚的趾高气扬及对左喜英语的嘲笑和鄙视,更是令她愤懑。比左喜高一年级的黑人艾德颇具才华,因为其毕业创作获得权威奖而被看好留校任教,但学校最终人选却是一名白人学生。左喜一方面赞赏艾德的画技,同时亦为他受到的偏见而鸣不平。艾德却反过来劝慰左喜:“毕竟你们女人还有和白人结婚这一招。比如说你和鲍曼。”由此可以看出,作品透过故事的表层文本,将女主人公被边缘化的生存处境巧妙、隐晦地揭示出来。左喜除了是性别的‘他者’外,还有因肤色及少数族裔所显示出的种族及文化‘他者’的身份。
在后殖民主义理论话语中,“他者(the other)”与“本土(native)”相对。“本土”作为主体、自我、民族、种族、普遍性、成规、同化、整体性等,具有自己的范畴体系;“他者”作为客体、异己、国外、特殊性、片段、差异等显示外在于本土的身份和角色[2]。在作品中,作家以大段笔墨叙述了左喜与黑人同窗间的沟通及交往,不仅勾勒出他们对彼此境遇的同情和理解,而且揭示出女性“与殖民地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相似性,他们都处在边缘、从属的位置,都被白人视为异己的‘另类’和‘他者’”[3]这一地位。自上个世纪50年代末起,旅居美国十数年的大庭,作为少数族裔的女性作家,对此问题早有关注和思考。在与日本女诗人山本道子座谈时,大庭就谈到:“女作家究竟如何找到自己的语言表达?我这里所说的语言,是因为觉得女性与黑人有极其相似的地方,所以又想到了黑人……”[4]。因为西方白人女性主义者只关注“性别”,却“忽略了妇女问题的其他维度——种族、阶级、国家……”[5]。
在三部曲中,左喜的认同焦虑首先表现在她与白人同性的关系中。尽管她对白人女性的强势及刁难愤懑不已,也常伺机报复她们的羞辱和蔑视,但充其量也只能是些隐晦的、满足一下自我的小把戏,而更多的时候,则只能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发泄。在三部曲中篇,左喜已与在美国大学做讲师的日本人岳浜明结婚7年,因对生存状态的焦虑而决意回国。经丈夫说服和建议,她选择了先去美国S大学参加艺术讲座,而后再行决定。在S大学,左喜与家境优越、自诩有良好教养的B市图书馆白人女馆长黛比同居一室。但这位金发碧眼的室友动辄便对左喜讥讽挑剔。一次,左喜在公共浴室洗完澡欲出来时,听到黛比在外面与另一白人女性议论她:“哎,那个左喜、就是和我同寝室的那个日本女人真让人讨厌……哎?不知你看到过没有,我已经两次看到她和一个男孩儿、像是个墨西哥人在一起……那小子看上去还乳臭未干呐……这些东方女人……年轻的也好,上年纪的也罢,全都妖里怪气的,真搞不懂。”
这些羞辱让左喜既愤慨又难堪。平日对于黛比的说教,左喜虽常显出难以从命,但也多是无言以对。而在被困浴室受其羞辱的这一刻,她却只能“像被塞进箱子里的偷渡客一样,一动不动地忍耐着”。此刻她的反抗只能是内心独白:“啊!这地方太可怕了!要在日本这些议论至少不会夹带‘那个日本女的’的字眼。”左喜担心无辜的自己因为这些欲加之罪而遭人唾弃,从而无比的恐惧和不安,最终令她“患上了黛比恐惧症”,只要呆在宿舍,就会让她“莫名地心神不宁”。显而易见,看似我行我素的左喜,其实内心充满了恐惧与焦虑。
在下篇中,主人公的“他者”特征及其边缘感和无助的焦虑被进一步诠释出来。白人女护士萨莉与左喜的丈夫及多名异性有染。左喜离家数月后回到家中时,一进门就看见萨莉遗忘在屋里的物品,这令她神经紧绷,情绪焦虑。而在左喜流产住院期间,每当丈夫前来探视时,她总是担心他会遇到来查房的萨莉而不快。但她与萨莉间的正面冲突最终未能幸免:
那当然了!左喜,卡拉就是我的公主!难道不是吗?!……我实话告诉你吧,左喜,为要这孩子我选了7个自己倾慕的男性……
萨莉、你太过分了!我讨厌你!我可是流产的人,你竟然说这些话刺伤我……你就是这么欺负人的?!
对于被“他者”化早已无奈的左喜来说,此时其反抗的声音较之以前显得有力了许多。尽管如此,她的抗议也不过是一个手势而已。而对于萨莉嘲讽的眼神和傲慢无礼的态度,左喜也只能是情绪上的“忍无可忍”。循着作家对女主人公生存境遇的描述,读者不难发现,她的身份完全是由其生存处境中主流群体的认知构成的,在西方白人的注视下,被“他者”化的女主人公形象也在与各色异性的关系中被刻画得愈加深刻。
在三部曲上篇中,白人讲师鲍曼与左喜的交往,起因于他发现妻子索菲亚有婚外恋情。于是,极善审时度势、左右逢源,生活态度很现实的他,便开始约会左喜。即便如此,他的原则也依旧是只要索菲亚不先挑事、自己也就佯装不知,这样一来,他“便得以愉悦于两座山谷间”。当妻子向他公开恋情并决意离婚时,他则越发现自己和左喜间的交往富于异国情调,正好可就此顺理成章步入婚姻了。为了掩人耳目,他常狡黠地以一个教师对外国学生的关心,半公开地接近左喜,并常趁外出为人设计饰品之时暗地约会左喜。但是,左喜常被丢在他途中的旅馆,一人孤寂地等待数小时。这令她“极感可悲”。她不断地质疑自己与鲍曼之间的关系,不止一次地慨叹:“啊!再也不想一个人在这种地方傻呆呆地等待他的出现了!”这每每让她感到不安,也更令她痛苦。很明显,在他们两人的关系中,鲍曼对左喜除了含有霸权征服意味之欲望外,并没有更多的认同,而左喜面对强势的鲍曼及索菲亚的阴影,则明显处于弱势、被动的地位。
关于女性的性别身份,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6]透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白人男子鲍曼的眼中,连妻子也是一只“可以一直饲养的动物”的“他者”,相比之下,左喜无疑更是附属于他的“他者”。
白人讲师鲍曼的强势及其东方主义式的征服令左喜生厌,而左喜与白人同窗达尼埃尔之间的碰撞,则将两性关系及两种文化间的冲突表现得更为激烈和直接。在他们的交往中,就因为左喜没能装出被征服的姿态而使他不快,从而发生龃龉,尼埃尔强烈的自我意识令左喜心生不安与恐惧。在下篇中,对于左喜与拉美留学生奇蔻间关系的讲述,则一方面呈现出主流群体对他们的蔑视,同时也把他们对彼此边缘化身份的认同反映出来。奇蔻一出生便遭遗弃后被人收养的身世,以及约会左喜时的温存等,既令左喜动情,又让她有似曾相识感。但另一方面,奇蔻的强势、狂妄及放荡不羁的言行,亦让左喜再次醒悟到自己性别他者的身份。而在与日本丈夫岳的婚姻中,岳的男性优越感及其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亦与左喜的意识相左,这更为她的边缘生存徒添了焦虑与孤独。
由此可见,置身异域的女主人公左喜,当她欲以其女性主体意识释放自我的生命本能时,其少数族裔女性的身份,却令其难以被主流群体所接受和认同,从而成为边缘生存的“他者”;与此同时,在同为少数族裔、有色人种的异性目光中,她又是性别的“他者”。
二、文化的“他者”
关于现代社会中人的“边缘性”特征,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在他的《人类的迁徙与边缘人》一文中指出:“边缘人是一种新的人格类型,是文化的混血儿,边缘人亲密地生活在两种不同的人群中,并亲密地分享他们的文化生活和传统。他们不愿和过去以及传统彻底决裂,但由于种族偏见,又不被他们所陌生的主流社会所认同。他们站在两种文化、两种社会的边缘,这两种文化从未完全互相渗透或紧密交融。”[7]在三部曲中,作家通过左喜与白人异性鲍曼、达尼埃尔之间关系的讲述,将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边缘人左喜的性别、种族及其文化“他者”的身份充分地凸显出来。达尼埃尔以其精湛的学院派画技深得好评,左喜赞赏他的画技并经常向其讨教,但两人间又常因审美差异而对峙。每当左喜把自己的画拿给达尼埃尔看并期待其肯定时,得到的往往是令她难堪的贬损甚至“奚落”。左喜在看了达尼埃尔的个人画展后,在夸赞其画技的同时,也指出其多数作品:“……感觉不到你的情感流露。可你再看艾德的画,尽管构图不够匀称、但却与你的截然不同。那是一种喷薄欲出的挥洒!有股扑面而来的热烈,富于激情!”这番话招致达尼埃尔回敬:“知道你们是在嘲笑我!……艾德虽画技好,可留校的人却是我。这是妒忌最好的说辞!”此后,只要左喜有赞美艾德的言语,必定遭到达尼埃尔愤愤的回击,并且“那个黑鬼!”的字眼也不止一次地几乎脱口而出,与此同时,“你这个黄种女人!”的诅咒也常在他的喉咙里打转。
尽管达尼埃尔没有想过结婚,可却一直欲把左喜“据为己有”,而这个“性情古怪”的白人男孩身上“特有的倔强也吸引着左喜”。然而,当他们亲密接触时,左喜又感到愕然,仿佛“碰到了一堵黑岩石般的‘他人’,而且是一堵没有抓手的黑色巨岩,一堵无法攀缘的岩石”。显然,呈现于这一意象中的隐喻话语是无所适从的冷漠与拒斥。从这一刻起,左喜意识到两个均不甘示弱的人已很难融洽,故也不再理会对方的诱惑。但这却令自尊受挫的达尼埃尔于心不甘,他不停地纠缠左喜:“别以为(咱俩)这事就此为止了!……像你这样的女人就该把你头朝下倒栽葱扔进湖里,看着你大口地呛水直到淹死……”“哼!你天生就是个淫荡的女人!”对此,左喜虽然嘴上的回敬只有:“那你别来招惹我呀!”而潜藏于她意识里的真正心声则仍不能说出口。她深知达尼埃尔之所以大为光火,是因为自己的主动示强没能够满足他的男性自尊。她想,其实装样子给他看也很容易,然而左喜再没有像迎合鲍曼那样去佯装。“我森田左喜为了能活下去忍耐了太多的东西!我装样子已经装够了!”尽管这声音尚显微弱且大多仍是内心独白,但也正是在那些内心独白中,曾囿于传统以及被给定的规约中的、隐蔽的女性经验及本体欲望,才得以空前地表现出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左喜在主流文化中的“他者”身份亦被呈现出来,左喜最终决意拒绝并离开鲍曼,也是源于他那带有霸权意味的东方主义式的想象。左喜曾不止一次地发现,“鲍曼因与东方女人睡觉而体味到带有征服感的异国情调,且沉醉其中。”尤其鲍曼经常流露出的带有侮辱色彩的东方想象,更是令左喜忍无可忍。于是,当鲍曼向她提出结婚的要求时,左喜终于断然地回绝道:“你对我的各种期待,任何一样我都不具备,而你对妻子提出的那些条件我也都不符合。我更不是那种能身着绯色和服,端庄地跪在有日本提灯的起居间中、缎子蒲团上的女人。”一直以沉默面对鲍曼的左喜,不仅以自我的主体话语回绝了这个白人男性带有霸权征服意味的要求,而且还表明她对这个主流群体的异性欲加诸于自己的文化“他者”身份的拒斥。
在三部曲中,与强势并带有霸权征服意味的主流群体的异性相比,左喜和日本同乡岳之间,因共同的边缘从属地位及对故乡的归属意识而彼此认同并理解。在两人初识时,岳正面临留下来还是回国的选择,亲切的家乡话即刻拉近了他们的距离:“你打算回日本吗?”(左喜),“无家可归!”(岳)。“是啊,我也是无家可归!”(左喜)。共同的归属意识,让二人开始彼此寻找认同。左喜告知自己在日本失恋身心受创的经历以及来美后所面临的困惑,岳则对有回国意愿的左喜表述自己对故国的失望,并以自己来美六年的困惑及体会说服左喜。作品以大段笔墨讲述了他们彼此对故土家园的认同,以及对在美生存的感受和对两性关系的思考。尽管共同的文化背景让他们彼此有诸多的理解和认同并结为夫妻,但在对文化的认同上,岳与左喜之间也显现出差异。
在三部曲中篇及下篇中,作家对这对少数族裔夫妻间的情感困惑、挣扎与分歧予以关注,突出了婚后为人之妻的左喜与丈夫岳对婚姻、家庭、两性关系和生育等问题的困惑与思考。对婚前已经被性别、少数族裔等多重身份边缘化的左喜来说,婚姻无疑又为之添加了新的身份困惑,而岳与左喜的困惑与挣扎亦有不同。在美国社会,作为少数族裔东方男性的岳,其生存处境同样艰难。岳因在美国读博士学位而未能如期回国,从而丢掉了国内大学教师的职业。虽然他在美国大学也做了讲师,受聘讲授日本文学,但他也深知,以其少数族裔的身份,即便有博士学位,在大学教书顶多只能升到副教授。尽管如此,这至少表明:他已跻身那个主流群体并被部分地接纳,其社会及文化身份亦得到了部分的认同。然而,为了博得这份来自主流群体的“部分认同”,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异域边缘生存中经年累月的磨砺令他低调、冷漠甚至麻木;令他学会不外露情感,蹑手蹑脚走路,轻声细语说话。有些时候,即便察觉了什么,也要佯装不知,甚而故作谦卑渺小。因此,岳的自我主体意识已经被抹消。
在这种被边缘化的夫妻关系中,丈夫虽看似无为却相对逍遥,而妻子左喜则始终居于不能完全表达主体意识以及被动的“他者”位置上。尽管左喜婚后也曾继续无视世俗,大胆体验认识世界,探索两性关系,但同时,置身主流群体目光之下的她,又处处招致世俗的责难。尤其在下篇的故事中,作家通过书写女性自身独有的身体经验——孕育、生产,将经历了怀孕与流产的左喜的心理及对夫妻关系的思考与困惑予以呈现。因此,与岳相比,左喜一方面充满了对文化认同的困惑,且常有“在这个国家不是在生活,而是在漂泊”的感触;另一方面,对于白人主流群体加诸于她的文化“他者”的身份则予以抗拒。
大庭在谈及当年的移民时曾感同身受地说:“很无奈。就算回国了,国内也没有其容身之地。”[8]从作家的这番慨叹中,她对游走于两种文化夹缝中的边缘人的困惑亦可见一斑。而作家的此番思绪呈现于其笔端的是:一方面,以接受被边缘化的他者身份为代价而获取主流群体部分认同的岳的形象,另一方面,欲拒绝被加诸多重身份而致边缘化、却又欲罢不能的左喜的生存困惑与焦虑。不仅如此,作家还通过这对日本夫妇对于故国文化的疏离与陌生的直接描述,进一步诠释了游走于两种文化夹缝中的、文化“他者”的困境。
在来美三年时,岳因为思乡而回国探亲,但却处处遭到冷遇,对此他难以释怀:“在他们迎接我的眼神里,仿佛我是一个变节者”。而且,那些被奉为传统美德的礼节,也让他无所适从:“本来可以一分钟解决的事情,却要花十倍的时间,在不必要的枝节末叶上繁文缛节。还有那些没完没了的寒暄及迟缓的节奏。其实,结果却是不近人情的交易支配着所有人。”而当岳在美取得博士学位,做了大学教师后,却在为人处世方面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他在两种文化圈之间小心地保持着平衡,就像杂技演员那样,一边走钢丝一边耍着手中的球”,而“在那张假面具的后面,隐藏着内心的悲凉”[9]。夫妻二人在异国他乡是无家可归的漂泊者,回到故国的家园,他们也被视为“局外人”,挣扎在身份认同的困境之中。
三、结语
在旅美三部曲中,主人公左喜无论有着如何强烈的主体自我意识,以及怎样追求并展示其女性的生命本能,都始终无法摆脱其作为性别、种族“他者”的边缘人处境。而这种生存处境的窘迫必然导致其作为第二性的以及边缘对中心的生存焦虑。在作品中,作家对主人公与主流群体间关系的书写,采用了大量的内心独白化叙事,在揭示女主人公孤独无助的生存状态的同时,也对其内心深切的“边缘感”及其压抑、不安和焦虑做了诠释。不仅如此,作家还对左喜与岳这对少数族裔夫妇在异域环境下作为文化“他者”的艰难境遇,以及他们为博得些许的认同而付出的代价和牺牲予以深刻揭示。与此同时,作品对左喜夫妇对于故国文化的疏离与陌生的叙写,呈示出游走于两种文化夹缝中边缘人的窘境,从而进一步深化了文化“他者”的意味,充分展现出作家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视野。
[1]旅美三部曲指大庭美奈子20世纪60年代末相继发表的三篇作品。即『虹と浮橋』、『群像』1968年7月号、『構図のない絵』、『群像』1968年10月号、『蚤の市』、『文芸』1970年10月号。1972年日本講談社以『三匹の蟹·青い落ち葉』为题,将上述三篇合辑为《绿色落叶》三部曲。本文引用皆出自其中,不再加注。
[2]刘晓文:《多元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女性文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3][5]黄华:《权利,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236页。
[4]详见大庭みな子·山本道子座談「なぜ小説を書くか-異国で覚えた文学的衝動-」、『文学界』、1973年4月号,第202页。
[6]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7]Park,R.E."H u man Migration and the M arginal M an."A 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28(33)P881.
[8]大庭みな子·山本道子座談「なぜ小説を書くか-異国で覚えた文学的衝動-」、第194-195页。
[9]刘易斯·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7页。
A Narrative of a Marginalized Existence:Interpreting Oba Minako's Trilogy
TIAN Mi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Beijing 100000,China)
Oba Minako;The Trilogy of The Green Falling Leaves;marginalized person;post colonialism
Most protagonists shaped in Oba Minako's novels are women whose life and fate are usually depicted in the context of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men.A female empirical perspective is always adopted in the narrative of those protagonists 'daily life.However,what is most impressive is that the narrative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socio-historic context. Oba Minako's Trilogy,likewise,manages to highlight the female protagonist's marginalized survival of"The Other"which is covered by layers of identities concerning gender,race etc.In terms of gender and race-the perspective of"The Other",the trilogy employs some text of marginal narrative intended to reveal the female protagonist's worries and anxieties caused by their failure to identify with the mainstream in a foreign country.Meanwhile,the trilogy has also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the narrative texts that unveil the culture of"The Other"and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which take place during the female protagonist's hard pursuit of her mutual identity with white male and white female.Oba Minako's trilogy successfully depicted the marginalized life and fate of the female protagonist of ethnic minorities,whose identity is covered by several labels,which,however,shows her view of colonial feminism.
I561.06
A
2095-5170(2014)03-0036-05
[责任编辑:林晓雯]
2014-01-25
田鸣,女,天津人,外交学院外语系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