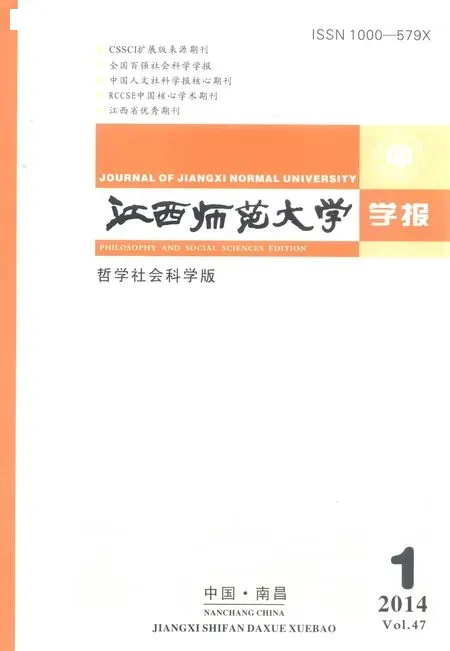叙事视角与性别意识建构
李勇忠
(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词语中存在着性别歧视,这似乎是所有语言的共相。为了争取跟男性平等的地位,女权主义者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对语言的改革便是重要的内容之一。不过,更多吸引女权主义目光的是显性存在的歧视性词语。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对词语的改良或者改革一直是女权运动的重要奋斗目标。然而,从语言学角度来看,歧视性词语的数量和携带歧视意识的语法结构毕竟是有限的,而语言应用的无限灵活性给了性别歧视更加高明更加隐蔽的生存空间。与话语中隐藏的性别歧视相比,显性词语歧视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语言背后所隐藏的意识一直是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热点,本文尝试运用叙事视角理论阐释话语中性别意识的生成机制。
一、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
批评话语分析(CDA)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英国,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系统功能语言学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理论支撑。随着该学科研究的深入,语言生成和理解过程中的认知因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CDA与认知语言学的跨学科性质日见凸显。
Fairclough&Wodak认为CDA研究要区分两种话语,一类是常规意义上的文本话语,另一类是福柯式话语。[1](P258-284)前一种话语的研究,通常关注连贯和衔接机制,受话者如何综合运用背景知识、情景语境等等对文本意义进行解读等问题;后者则专指福柯倡导的权力话语,其核心观点是:话语并非是权力的外化,话语本身构成权力,话语的生成过程实则就是实施权势的过程,知识在不同的机制之下通过话语进行组织、讲述,并对社会施加影响。
文本话语主要与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有关,而福柯式话语则是与社会文化实践(sociocultural practice)相联。前者依赖阅读语境,后者则依赖社会文化语境。后者比前者更显宽泛。
批评话语分析更多的是针对福柯式话语。在此,我们不妨重温一下Wodak对CDA的学科特点的精辟总结:[2](P17-20)
1.CDA旨在解决社会问题。CDA的兴趣不在于语言本身,而在于社会、文化建构过程的语言特点;
2.权力关系是话语式的。话语实践就是发话者通过话语实施权力的方式;
3.话语自身构成社会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4.话语体现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表征和建构社会的特殊方式,意识形态通过话语制造不平等的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5.话语是历史性质的。话语必须在特定的语境下进行研究,当下语境总是与过往的语境产生互文效应;
6.对话语的理解和生成,需要采取“社会-认知”的方法去解释文本和社会的关系;
7.话语分析是阐释性的;
8.CDA采用科学的范式积极地干预和改变正在特定语境下发生的事件。
从以上八条原则,我们不难看出CDA研究的主要目的:通过话语提供的线索,在历史、文化、政治和社会的维度中,揭示语言背后所隐藏的语言意识,继而达到解决社会问题、改变社会不平等的权势关系的目的。
二、惯性思维下的性别歧视
惯性思维,是指人们在日常语言运用中,往往有意无意地坚持既成的习惯,自觉不自觉地坚守既定话语。
根据百度百科的释义,性别歧视(sex discrimination,或sexism)指一种性别成员对另一种性别成员的不平等对待。尤其是男性对女性的不平等对待。两性之间的不平等,造成社会的性别歧视。也可用来指称任何因为性别所造成的差别待遇。
本文要讨论的性别歧视,专指男性对女性的歧视。
从文化语义的视角来看,在男性话语霸权的语境中,“性别歧视”一词往往凸显其固有的“对女性歧视”的缺省义。女性贬抑是性别歧视中最极端又是最常见的形式,倡导和实践这种歧视的人常被称为男性沙文主义者。
从历时语言学的角度来看,除去短暂的母系氏族外,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可谓是一部男权主宰的宏大叙事史。直至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仍然承袭了几千年来“男性中心、女性边缘”的男权思想,这种思想渐次固化成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影响着日常的观念、行为意识和价值取向。
众所周知,语言总是与思维共现,而思维习惯总与文化模式并存。在男权思想盛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男性视角是审视世界的主导,人们往往以此来表征世界。
语言的性别歧视,有显性和隐性之分。显性歧视多半表现在语词上,而隐性歧视则更多表现在语词之外的句法之中。
通过语词来表现的显性性别歧视,存在于几乎所有的语言中。以汉语为例,男性视角是通行的标准,女性总是处于被把玩被观赏的地位,语言中有贬义的女性用词要比男性用词多得多,如:奴、妖精、狐狸精、骚货、荡妇、小娘们、母老虎、悍妇、红颜祸水、淫妇等,不胜枚举。[3]以女性作为观赏品的词有:好、娇、媚、婷、妍、妩、妙、嫣、嫩等等。无论是贬损还是赞赏,均是站在男性的立场,要么把女人当成批驳的对象,要么视为掌中玩物。
在父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女性常被视为“较软弱的群体”,是男性的附属。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权运动的开展,一种矫枉过正式的性别平等观念悄然进入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软弱”的女性需要过度保护。“女士优先”便是这种意识在语言和行动中的最典型体现。女性优先,不仅是男士在社交场合表现其教养的最好名片,而且也渐渐成了女性在男性面前获得特权的最便捷的修辞武器。孰不知,这种无意识的话语实践,却在宣扬着另类的性别不平等,负载着更加隐性的语言性别歧视。
惯性思维在语言中表现为惯用法,在词汇、句法乃至语篇均有表现。这种由于经过人们反复使用而得以形成的语用知识,可被称为意识语法。[4]下文要谈到的女性性侵的新闻报道中被动式的大量运用,便是意识语法的体现。
三、隐喻与语言意识
作为我们赖以生存的思维模式,隐喻总是以隐蔽且修辞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隐喻修辞观向隐喻认知观的迈进,印证了Lakoff和Johnson(1980)的理论假说,即:隐喻不仅仅是美化语言的修辞工具,更是人们认识世界表达世界的一种基本思维模式。他们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解构了自亚里斯多德以降的传统隐喻修辞观,建构了人们对隐喻的全新认知。
概念隐喻其实就是语言习惯,是自动或下意识的认知操作。概念隐喻与语言意识紧密相关。它根植于个体经验,情感体验就是概念隐喻的典型例证。尽管概念隐喻本质上是无意识的过程,但它们却能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有目的地表达着语言意识,引导着语言使用者进行隐喻式推理。
一般而论,语言意识是以隐含的方式出现于文本的命题中,它可能是以预设出现,作为文本的前构建成分。男性中心主义的文本常常预设女人不如男人聪明。
Fairclough注意到了把人隐喻为动物的现象,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隐喻背后的歧视性语言意识:[5]
[例1]Everywhere in the Third World life in rural areas gets harder,and poor people flock to the city.The urban poor get poorer…
从语义激活理论来看,flock激活sheep,因为在flock构成的语义网络中,最原型成员便是sheep,flock与sheep之间构成了缺省逻辑关系。作为隐喻表达式flock,它是由概念隐喻“穷人是动物”派生而来。把人动物化,隐喻与歧视性意识的关系不言自明。
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隐喻给我们透视世界提供了一个极具主观性的视角。把物人格化,把人动物化或工具化,无不体现了人类喻性思维的独特性,从而给我们看待和表达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四、叙事视角与话语建构
叙事视角,又称为认知视点,是发话者透视事件的角度或立场。在一定的时空中观察和描述世界,语言受制于外部客观条件和个体自身的条件,我们总是难以达到全景式的客观描述标准。立场或角度的必然,决定了语言表达视角化的必然。视角不同,话语也不同。从词语到句子到语篇,莫不如此。
(一)词语选择的叙事视角。
语言表达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发话者在众多的符号备选项中作出恰当的选择。语境和发话者的不同,自然会产生不同的视角,生成的话语也不尽相同。形容女人,可以用“花”,可以用“月亮”,可以用“祸水”,用“老虎”,用“家”,用“港湾”,也可以用“半边天”。对概念隐喻的选择,即是对认知视角的选择,是产生不同隐喻表达式的前提。
就视角而论,Langacker关于词的连续性和离散性的区分,可以看作是最好的例证。[6]他认为,认知视角不同,影响观察距离的远近,直接改变同一事物的离散性和连续性。如从山顶远距离看牛到逐渐缩小距离直至贴近牛身观看,依次会出现下列情形:
herd[count]> cows[plural]> cow[count]> cowhide[mass]> hairs[plural]> hair[count]> keratin[mass]> cells[plural]> cell[count]……
同一对象,只因认知距离不同,便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可数与不可数、单数与复数等特性聚集在同一物体中,连续性与离散性如万花筒般渐次展开。
(二)句式选择的叙事视角
语篇中句法形式特征被看作是从语法系统中作出的有意义的选择。句式与词语构成有意义的连续统,句式本身有独立于词语的意义,句子的整体意义是句式义与词汇义要么冲突要么协调要么压制的函数,这早已成了句式语法的核心内容,广为学界认可。
选择什么样的句式,取决于发话者的叙事视角。批评话语分析把重点放在句式背后隐藏的语言意识上,认为最隐性的语言权势和歧视是通过句式来传递的。请看:[7]
[例2]a.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
b.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
两条法律条文,尽管只有一字之别,然而,包含的语言意识却有天壤之别。例2a是198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六条,第二例减去“也”字却是2001年的修订。第一例的言外之义是:子女随父亲姓是常态,而随母亲姓是非常态。因为句式“可以V1,也可以V2”固有的句式意义便是:首选V1,不能V1则选V2,暗含的语言意识是不情愿、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意思。该条文带着严重性别歧视,子女首选随父姓,不得已亦可随母姓。男性是家庭的主角,而女人只不过是配角。而例2b,减了一个标记词“也”,句式发生了变化,话语的客观性明显增强,背后体现的语言意识明显指向男女在家庭中更加平等的地位。
再如,若要写一篇关于“第三世界”的评论报道,假如作者始终把第三世界国家的穷人放在及物动词后面作宾语,那么文本便会传递一种信息:穷人是被动的受害者,不是积极地参与抗争的主动者,由此可见,对语法结构的选择是作者有意而为的结果,语法结构体现了意识倾向。[1](P263)
句法结构的选择,实则就是语言意识的选择和表达。如被动式的选择,往往体现了发话者凸显受事、隐藏施事的意识。在女性受侵的新闻事件中,被动式的大量使用,是极为常见的语言现象。在第五节中,我们将用语料来说明。
(三)语篇建构的叙事视角
大凡作文,都得讲究谋篇布局,谋篇即计划整体语篇,布局即结构的安排。作文时,必先有主题,成竹在胸,方能建构成文。有了主题,便须考虑如何布局。布局不外乎是句式和词语的选择,然后考虑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的衔接与连贯。
语篇主旨的确定,词、句和衔接连贯的选择,都脱离不了叙事视角。要说叙事视角决定了语篇的性质以及意义的生成机制,此话一点也不为过。请看下例:
[例3]……我想象到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我就会蹲在地上,用力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嘴巴里发出疯狗一样的叫声。等到她高傲的身影在风雪中渐渐模糊时,我就会趴在雪地上,让肮脏的脸贴在圣洁的雪上,让飘摇而下的雪花把我埋葬。我还想象到,等她从温泉宾馆卖完了回来时,大雪已经把我彻底覆盖,就着我的身形在大街上出现了一道小小的丘陵,宛如一座修长的坟墓。她站在我的墓前,脸色惨白,犹如一尊大理石的雕像……就在我被自己的想象出来的情景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时候,她已经来到了医院的门口。
——莫言《冰雪美人》
这是莫言的短篇小说《冰雪美人》的片断。小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了一个偏远小镇个性独立的漂亮女孩“孟喜喜”的悲剧人生。作为同学的“我”,满含同情和爱情,与叔叔和婶婶代表的传统世俗意识相抗争。在叙述者的眼里,孟喜喜是一位纯洁如冰雪一样的美人,而“我”则如同周围的其他人一样,既肮脏又丑陋。正因为有了这样独特的认知视点,于是便有了上面这段蒙太奇式的描写。
(四)实例分析:基于CDA视角
批评语言学的主要观点就是坚信语言产生意识。[8](P6)作为社会行为不可分离的组成形式,语言不可避免地与政治、文化、社会语境紧密相联。语言不会在零语境的真空中产生,它总是与特定的语境相联,反映并且建构社会意识。
标榜中立、客观、不受某种价值观左右的话语是不存在的。从理论上说,语言批评适应于任何文体,然而这种泛语境研究(pan-contextual search)受到了指责,被认为是过于泛化。[8](P7)学科成立伊始,批评语言学便把重点放在新闻和政治语篇的研究上,因为新闻和政治语篇最能体现权势关系和意识形态。下面我们通过一些实例来说明语言背后的性别歧视。
[例4]A man who suffered head injuries when attacked by two men who broke into his home in Beckenham,Kent,early yesterday,was pinned down on the bed by intruders who took it in turns to rape his wife.
在这则语篇中,作者极力渲染丈夫受到的伤害,用了三个下位层次范畴的动词suffered,attacked,pinned down进行细致的描述,并且采用复合句式,把丈夫作为语篇的主题,位于句法的凸显位置。根据“凸显则易受关注”的认知规律,很显然,作者是有意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至丈夫身上。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复合句式的刻意使用。复合句式是复杂的句子结构,根据语言象似性原则,复杂的句子结构表达的内容要比简单句表达的内容丰富翔实。丈夫所受的伤害,通过复合句式的描述,信息量大大增强。与之相反的是,同样受到伤害的妻子被置于句尾,只是作为附带性的描述,信息量明显减弱。称谓时也是作为男人的妻子(wife),缺乏个性化的标签,独立性几乎不复存在。
英国学者Kate Clark专门对英国《太阳报》关于强奸案的新闻报道进行了研究,发现文本大量采用模糊语用策略,对凶手的罪行模糊化,有意或无意地把责任推给受害者本人或第三方。[9](p119-143)这种女性受到强奸的新闻报道惯常采用的句式是被动式。被动句的构式意义是把施事置于隐藏或遮蔽的句法位置,而把受事置于句法凸显位置。有意把读者的注意焦点牵引到受事。例如:
[例5]Two of Steed’s rape victims——aged 20 and 19——had a screwdriver held at their throats as they were forced to submit.
此话语采用的是典型的被动句式,两名受害者受到的伤害真实的再现出来,然而作为凶手的施事却只字未提。
报道者甚至会对受害者进行别样的描述,以开脱罪责,找到对施暴者原谅的理由,诸如“单亲家庭”、“童年的悲惨记忆”等等。例如:
[例6]Sex killer John Steed was set on the path to evil by seeing his mother raped when he was a little boy.
Clark认为,报纸之所以会如此处理这类报道,就是为了掩盖当下社会众多男性对女性进行性侵的社会本质。[9]
针对性别意识在句法选择上的体现,女性主义学者苏珊·埃尔利希在《再现强奸》一书中用了四个例句来说明:[10]
[例7]a.一男子昨日在一旅馆杀了一女子。
b.一女子昨日在一旅馆被一男子所杀。
c.一女子昨日在一旅馆被杀。
d.昨日,在一旅馆发生了一起女子凶杀案。
例7a是主动句式,例7b和例7c都是被动句,例7c句完全把施事隐藏起来,例7d采用了名物化形式,用名词“凶杀案”把凶杀从动态变为了静态,把事件的原因、过程连同施暴者完全地排除在视野之外。通过对不同句式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同一个新闻事件,采用不一样的叙事视角,选择的句法不同,生成的话语不同,语言意识也迥异。
五、结语
意识隐藏在话语中,语用者常常通过词汇、句法和语篇的不同视角选择,把语言意识悄然地布置在字里行间。性别意识是典型的例子。
意识受制于语言的内容和形式,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着语言内容的产生和形式的选择。正如熊学亮所言,意识对话语内容和形式的影响是微妙的,话语内容既可能受到意识的制约(如话不能乱说),又可能被一些语用固化了的套话所掩盖。[4]掩盖施事的被动句式,便是一种经过潜移默化的语用意识逻辑,最终变为了语用者的意识语法知识。
我们认为,话语的内容和形式离不开语用者的叙事视角,叙事视角决定着语言意识。惟有把握了话语的叙事视角,才能更有效地揭示语言背后的意识。
[1]Fairclough,Norman & Ruth Wodak.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A].In:Teun A.van Dijk.T.A(ed.).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C].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4.
[2]Wodak,Ruth.Disorders of Discourse[M].London:Longman,1996.
[3]叶匡政.语言的性别歧视[J].百花洲,2010,(2).
[4]熊学亮.话语意识逻辑刍议[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1).
[5]李勇忠.隐喻修辞策略背后的语言意识[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6]Langacker,R.W.On the Continuous Debate about Discreteness[J].Cognitive Linguistics,2006,(1).
[7]姚双云,“主观视点”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J].汉语学报,2012,(2).
[8]Simpson,Paul.Language,Ideology,and Point of View[M].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3.
[9]West,C.,Lazar,Michelle M.and Cheris Kramarae.Gender in Discourse[A].In:Teun A.van Dijk.T.A(ed.).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C].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4.
[10]何金梅.修辞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J].修辞学习,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