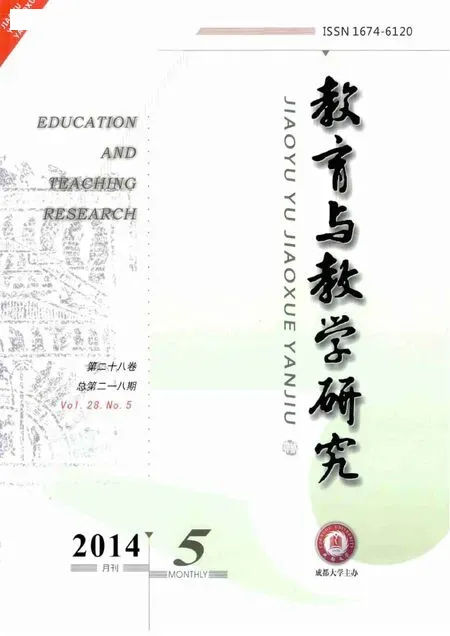基于生命本性沉思的生命教育刍议*
——高校生命道德教育的思考
熊小青
(赣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赣州 341000)
基于生命本性沉思的生命教育刍议*
——高校生命道德教育的思考
熊小青
(赣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赣州 341000)
重视并实践生命教育是现阶段高等教育的重要特征。然而,高校生命教育却被更多地误读和理解为口号式、情感式甚至应对性教育。高校生命教育不能缺乏对生命及其生命教育的反思,这是大学生认知、思维特征所决定的。要使生命教育真正取得实效,应该理性地深刻体悟和认知生命本身,即对生命及其生命教育“沉思”,才能真正使大学生在生命教育中体悟生命真谛,确立生命之自觉。
生命与生命教育;生命沉思;生命自觉
2000年以来开始的“生命教育”活动,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行为。生命就其本质而言应该构成教育的终极目标与价值追求,教育的本质就是要遵循生命发展规律,促进生命的健康发展,提升生命的价值。因此,生命教育就是“帮助学生认识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促进学生主动积极、健康地发展生命,提升生命的质量,实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1]。正是在人们普遍重视生命、善待生命并由此引发教育理念的生命取向的这一大背景下,2010年7月公布和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要学会生存生活”,要“重视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国防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等一系列旨在促进生命教育的措施,“生命教育”成为了国家教育发展的战略决策。这时,生命教育就不仅是一种教育理念、教育价值和教育目的的选择,而且更是教育事业的有机组成,是社会主义人才培养的基本内涵,是受教育者健康成长的基本素养,从而成为必须开展的教育。此时,生命教育获得了高校教育工作者重视并得到普遍推行,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生命教育也构成目前教育显著特点之一。然而,在这当中同样存在对生命教育的片面化或狭义性认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生命教育仅作表象化、感性化理解,而未能从更具本源性、本体性的视角去引导学生对生命进行深刻认知和沉思,其结果必然使生命教育难以成为大学生生命实践及其人生活动的生命自觉。
一、生命教育不应出现对“生命沉思”的遗忘
“沉思”无疑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它表征着主体对事物根源性、本体性思考的思维进程及其程度,体现着主体不满足于事物所呈现的表象和当下人们的习惯、认知、观点,而对事物进行着更深层次的本质追问,也表征着主体始终保持着主体所独有的质疑、反省和深思。“沉思”体现着对事物客观本质的主体性诠释,是对事物的更加全面和深刻的理解和彻悟,是在对事物更深层次认识理解当中的一种对主体的启示和启迪。
生命沉思是对生命本质的追问,包括了对生命的价值、生命意识、生命智慧、生命目的、生命关系等问题的追问。显然,这涉及到了生命哲学、生命伦理、宗教学、政治学、教育学等诸多学科。生命对于任何生命体而言都是唯一的,并且就其物质性存在方式而言都是有限的,这就意味着生命沉思必定是对生命的死和活的现象及其进程做出反思、反省,也正是生命的必死使得生命必定蕴含着更深刻的生命真谛,即一种有限之存在如何以其“活”展示其生命的存在及其进程,一种生命的本然存在究竟是什么,或者也可以表达为生命的本质或何以为生命,这些无疑构成了人类对生命沉思的永恒主题。当然人们也由此就有了对生命的更多追问,比如:人的生命与非人生命是什么关系?人的生命必然高于非人生命吗?人的生命呈现过程何以为有价值的?自然生命与社会生命的关系是什么?人应该如何生存?人的生命自身就是目的吗?等等。生命沉思无疑提升着主体对生命的理解,而这一切将使得主体能从繁杂的、或然的生命现象中认识到生命的本质,从生命体的关联实在性、客观性中感悟生命共同体之间的依存性和互赢互利性。当然,也能使生命个体在向死而生并最终归于死亡的生命历程中,体验出生之快乐、幸福和意义,从其中去重新审视生命的生活样式及其生命追求的根之所在。从生命的生死必然更深刻地理解到个体生命死亡对于整个生命世界的必要性及其意义;更加深切感悟没有生命个体之间的新陈代谢,显然就没有生命世界的实现,等等。生命沉思将使主体的生命建构图景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也将影响着主体的生命实践和生命体验。因此,没有对生命的沉思,我们对生命的理解更多的是表象的、个我的,或者说感性的、直观的,与此所进行的生命实践和生命教育必定是诉诸于情感或情绪性的、感官的或经验的。我们可以说,“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为了人类的未来,我们应该爱护动物”。我们也可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有意义的人生就在于给予,就是让别人获得幸福”,“生命是宝贵的,珍惜生命”,“关爱生命,敬畏生命”。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学生激情之后的许多困惑,或者说过之后就似乎完全没有发生此事一般。喊过“保护环境”的口号过后,照样奢侈消费,照样把以GDP增长作为追求目标而任意粗放式地耗费着资源,照样以吃稀有动物为荣。也就是说口号式、宣传式的生命说教在面对生命存在状况、生命实践的乱象时显然难以自圆其说。保护动物生命是出自人类的未来,那是否表明动物的存在价值就在于为人服务、动物的价值需要人来体现?既然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是否意味着我们都应该成为素食主义者?等等。生命是宝贵的,那为什么会有人提出安乐死,甚至世界上有的国家通过立法去承认?有意义的人生就是让别人快乐,那是不是自己的生命就无关紧要,自己的生命价值需要通过别人的生命来获得确认?放弃自己的生命追求和生命满足,是不是对生命的一种漠视、践踏?等等。这些问题正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情感的渗透、功利式的认知在整个生命教育中固然必要,但是情感、功利的背后是理性,理性对于生命实践及生命教育而言是基础和动力,脱离理性思考及其认知的普遍常识、情感渲染和功利诱导,只能使生命教育失去其应有作用。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于大学生的生命教育需要生命沉思,没有对生命本质的追问,就无法真正理解生命,当然也无法真正实现生命教育。
二、生命沉思的合理指向
生命教育,其实质就是使每一个人能够珍爱生命的教育。教育就其本意而言就意味着传递、传授一种生命的正能量,而并非去挖掘、研究和探求这种正能量;就是说教育本身更多的是传道解惑,而并非去探究研讨生命自身的内涵。尽管这二者存在着联系,甚至无法分开,但是它们各自的侧重点还是不一样的。因此,生命教育视野中的生命沉思,应该有着教育的内在规定和确定指向,从而使之有着特定的内涵,它主要表现在:
(一)追问生命何以为生命,生命何以成为伦理关注的对象
在生命教育中,显然必须交待生命是什么、生命特征是什么、生命的表现是什么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显然什么是什么是一种知识论思维,这也是一种科学思维,理应从科学视角来理解生命。“生命有秉承天意之生长,化生万物之义”,这显然是生命的广义理解,把一切具有生殖、生长,即具有“活”的事物理解为生命。“生命始终与‘活着’‘生气’‘活力’等联系在一起的。”[2](P2)然而,生命的现实存在总是以人的单个生命体的生命实践及其体验来理解人的生命,或许是生命的同类性或者人对自身类的更为关注而言,这就成为了生命的狭义理解即“人的生命”。人的生命,就其物质实质而言,与其他生命尤其是与人类接近的动物而言没有什么区别,在其基本的生理机能,维持一种生命存在过程中所体现的新陈代谢方面,本质上是一样的。生命教育当然不是从这一意义上进行理解。生命之所以被人关注并施以极大的情感,就是任何生命体存在的唯一性及有限性给予人的精神震撼,从而给予生命以人性的伦理去诠释生命。人是所有生命中唯一具有意识的生命存在物,决定了只有人的生命才能承载道德地对待生命包括其他物种生命之责。马克思说:“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正是这一意义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直接区分开来。”[3](P162)当人生命活动体现着主体性,并把这种主体性表现为对其他生命体的一种感同身受之时,人的生命存在就已经超载于自己的生命而变成类生命和“大生命”。因此,“广义生命就其实质仍然是人对人的生命超越之理解,是人以自身‘生之’、‘活之’的把握推广至所存一切生命体的‘生之’‘活之’的理解。”[2](P6)也就是说,生命教育的生命是人的生命,“通过自己的意识并通过文化的形式表现出了对生命和非人生命物质的一种理解并按这一理解去践行之”。“正因为如此,生命的属人化理解、呈现和诉求,而并非是生命的自在化呈现和诉求。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处于西方工业文明之中的现代人,在对生命理解当中已经有了某种为人的先在性、预设性。即人已经成为理解一切生命的起点,当然也成为理解生命意义的终点。”[2](P6)归纳起来,生命教育的生命主体就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实践的感知和体悟的对象是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非人生命。人的生命无疑是人对生命理解的核心,也是人对其他生命理解的基础,生命教育的生命并非仅指生命的物质构成实质,更多的是对生命体呈现出来的生命现象尤其是生死现象的情感、道义的关注。
(二)追问生命的关系存在
生命是个体的,但更是群体的和类性的。无数生命个体之间的关联,使生命成为有机整体也成就了生命世界。任何个我生命实践必将对其他生命体生存产生影响。因此,生命教育中如何使学生理解生命世界中生命体间的彼此关联、相互作用与影响,并由此成为生命有机整体,构成了生命教育中的生命关系问题。个体人的生命实践都是个我的,并以独立甚至排外方式呈现着,比如现实生命实践中的竞争现象、控制与反控制现象,这由此造成了生命理解的个体化存在表象。突破这一问题的表象困惑,关键是让生命教育的受教育者理解到生命世界的整体性、依存性及其诸生命体间的关联性,而不仅仅从生命间的功利性,或者从人的生命道德性去诠释这一问题,否则是很难达到从内心深处建构起对生命的敬畏和关爱。功利意味着当人的生命一旦没有了对它的需求,那人类的生命实践就可以对之冷漠和无视,也就是说,我们关爱生命,不应该仅仅是出于这一生命现象及其生命体对人生命的功利价值。这无疑玷污了人之为人之品格。同样,人的任何道德从根本而言,就是更好地体现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性,但道德性表现着主体自觉自愿,是一种觉醒性表现,是超越生存意义的“更好”而言。尽管生存意义的生存行为形式上可以设置道德规范,但是生存行为在内容上是不能进行评判的,它是本能、是生存的基本。道德评判是基于生活于社会的人的一种“更好”更高觉醒的评判并非生存的基本评判,意味着生命行为的基本生存领域所形成的生命关系是不能发挥作用的,比如大象将把人的生命置于死地时,人必须制裁大象,乃至把它杀死;不杀动物,人就不能活下去时,人必须杀死动物。这些就其内容上不应该是道德问题,而是任何生命的本能问题。
因此,个我生命实践何以关联其他生命和生命体,体现着本体论质疑和诘问。它需要更加根源、本质上的追问。这就需要一种世界观、宇宙观的认知。宇宙世界的整体统一及其内部诸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相互影响、共生共荣,使得宇宙世界成为一个有机体。如果没有宇宙世界的认知、体悟,就人的生命实践而言,就无法真正理解并接受任何生命个体是整个生命世界无数生命个体的一个,是整个宇宙物质世界纵横交错的织锦中的重要的线,当然也无法理解生命关联之本质。缺乏对宇宙万物相互联系与作用、彼此影响之一体性的本质认知和体悟,并成为对宇宙世界的基本理念,个我生命永远无法超越个我生命局限而予以一切生命之爱,生命教育中的生命宝贵、敬畏生命等理念,只能是一种空洞说教口号或成为生命实践中的某种托词、教条。
(三)追问生命之爱的本质
“爱”成为生命教育的核心词,爱生命也成为生命教育的主题。何谓爱,爱什么,如何体现生命之爱等等,这些问题无疑是生命教育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爱生命、爱生活、爱他人,也由此引出敬畏生命、保全生命、关爱生命等等。我们习惯于如此表达并标榜生命之爱,但却忽视了对生命之爱的追问,即生命之爱的实质是什么。生命之爱是人之生命实践的一种情怀,还是价值必然?是功利还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尽管爱是情感,但也是一种理性,作为充满理性的生命教育必须思考这一问题。
爱,体现宽容、包涵和无私含义,是一种善念和善行。当你将你的生命之爱给予其他生命体,意味着你海纳其他生命体并将给予其人的类意义之情感,这一生命之爱无疑是高尚的、无私的和崇高的。然而,当我们面对着“如果我爱他人,原谅他人,他人却不如此对待我,那又如何?”“为什么总是要头脑清楚的人让步,认真的人就要吃苦?”的诘问之时,或者遭遇农夫和蛇的寓言故事所述蛇之忘恩之窘境时,爱又何以继续,生命之爱何以可能?
事实上,当爱被理解为一种伦理之爱而非本能之爱之时,生命之爱只能是人之生命行为,本能之爱是所有生命特别是高等动物生命所具有的。“虎毒不食子”、“象群对小象的保护”、“鸟对同类死亡的哀鸣”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正如达尔文所说,它们是基于同类的一种天然的本能行为。只有超越了同类而给予了所有生命体以生命之爱时才是道德的,而这显然只能是人的生命才能承受的。“爱”表征着一种单方地给予,并非是一种功利性利用之果,而是人的生命基于自身生命体体现而给予其他生命体的一种慰藉、关爱。生命之爱应该出于一种人之为人的本性所付出的一种情感、善意。因此,爱的本质就在于利他而非自利,是一种无私欲地付出给予,任何带有诉求或者回报意愿为出发点的“爱”,只能是功利而非爱。
人的生命个体对其他人或者其他生命体的爱,如对大灾中百姓苦难,对死亡或生活困苦之不幸,对弱小动物暴毙或陷入困境所表现出来感同身受的同情、生命呵护、关爱等,无疑是人的生命实践中爱的体现。因此,生命之爱总是出于爱的对象或爱之承载体的生命不幸,是人对生命体所遭遇的不测而表现出来的人的情感、善待和给予。更为规范地说,是生命体遭受了生命体自然生存以外之压力以至生命体存在已遭遇困境甚至死亡境地之时,人们所表现出来的生命感慨和善意。生命自然之不自然是承载生命之爱的前提,也只有生命自然当中的不自然,即一种外力对生命生存的改变并导致生命之不幸,才能成为生命的爱,这种爱才符合生命之爱的本旨。一切有悖于这一情境和事实的爱,都无法被理解为生命之爱。冬天来了,给小动物穿上厚厚的衣服,给动物提供丰富的食物,使之饭来张口,这是许多人对动物爱之表现,人们认为唯有这样才能表现出人类对动物之爱。希望工程中,好心人士资助贫困地区小孩上学,希望所赞助的小孩依他所愿的上高中、读大学,或者如他所规划的路径成长而非小孩自身发展轨迹成长。捐资助学是善举,是基于生命的一种爱的表现;而当你的意愿完全左右小孩而忽视小孩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存在,这时善就变成了某种伪善。捐资者的失落、不解、困惑甚至夹杂着某些后悔,恨铁不成钢的无奈的哀怨,等等,表现的是捐资者对生命之爱的误读。这二者共同之处,就是以主体个体的生命感悟去塑造爱的承载者的生命存在与实践,爱对于被爱的生命体成为一种外在的限制、规定,成为一种不自由。一种对自由无情的限制、约束的爱,对于任何一个生命体而言,显然都是难以承受的。爱对于被爱者将成为一种累赘、负担甚至压力,一种无法负载之重。这恰恰违背了爱的本意,是爱的本质的异化。
三、“生命沉思”的实现:生命教育的深化
生命教育是关于“生存、生活、生命以及生死的教育,其目标在于使人们学会如何积极地应对人生进程及生死的挑战,学会尊重生命并理解生命的意义,进而培养人们对待自己、他人乃至一切生命体的责任感,以让人们从小就知晓生命的可贵”[1]。生命教育离不开“生命沉思”即一种对生命本质的思考。对生命本质思考的目的,在于提高人们对生命的认知和感悟,及其尊重生命、珍惜生命的自觉性,以更好实现人们自我生命教育和生命理解的提升。生命沉思必须贯穿于生命实践和教育实践中,伴随着人的生命存在过程之中。生命沉思总是根植于生命实践与教育,并自始至终是生命实践与教育的组成部分。然而,生命沉思作为一种认识之思,尽管是在实践之思基础上实现的,但认识之思的根源性、本质性、抽象性追问以达到对认识对象本质的认识,决定了生命沉思更多地体现为理性自觉。当它应用于现实生命教育实践或者结合于现实生命教育活动时,必然遭遇到许多的困惑以及诸多现实问题,从而也使这一生命沉思在其现实生命教育实践中有着特定的表现和特点,这也构成生命沉思在现实生命教育中如何可能、如何实现的问题。如何使我们的生命教育不只是停留于某种空洞说教或情感性的宣传口号,而是使受教育者真正从内心认同生命价值及其积极性,在情感、价值等维度领悟生命真谛并践行。这就构成了“生命沉思”的现实化问题,它主要是通过以下方面实现:
(一)注重生命知识的系统传授
生命就其存在方式是物质的,然而生命之“活”又表征着生命之“活”所具有的心理、行为。因此,就生命自身而言,“活”的物质基础及其机能即生命存在的结构特征及其构成要素成为人们理解生命的前提。人类在长期的生命认知和生命感情中形成了认知成果,对人们了解生命提供了知识基础。强调生命知识的系统性,就在于从更加完整准确的视角去认识生命、把握生命,进而把握生命的本质。在这当中,生命教育涉及的生命,包括了生理、心理、生活,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在知识学看来,它涉及到生态学、生物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生态学揭示了生命体之间及其与非生命体之间的关联,生物学揭示的是生命体的演化及其实质。社会学揭示了人类不同族群、民族在生命问题上的认知及生命价值取向等,当然还有宗教学等其他学科。这些学科知识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生命之为生命的要素、结构等特质及其生命的基本特征,也由此揭示了生命在类意义和个体意义的显现及其价值。通过这些知识的传授学习,受教育者能够从知识上对生命有着更加全面的认知,对生命世界的关联性、系统性有着更加直接的理解,从而对于生命的珍爱、保护,以及人的生命在生命世界的影响更能理性把握。
(二)重视生命的体验和感悟
生命教育显然是针对人的生命教育,包括生命价值教育、生命意识培养、生命智慧开启、生命理性建立等诸多内容。这些内容要真正内化为每一个生命主体的生命内涵并呈现生命自觉,除了科学的认知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强调生命体验。体验通过生命主体对生命、生活的亲身感受,在对生命的生与死、感与观、得与失的情境中完善主体的生命认识,达到一种知、情和行的生命教育。
缺乏一种对生命的体验,显然难以从内心唤起人的生命激情,就会把这种教育视为一种外在约束。人的生命就其本质是一种关系生命,即在一种生命体与生命体、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交互作用中实现生命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4](P486)而“人的活着在现实上是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活着。因此,活着的原有的生物性意义就自然打上了社会关系烙印并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来"[2](P260)。关系生命就在于人的对象性得以实现,即在一种体验感悟中确立生命存在。正是生命呈现中体验到生与死、挫败与成功、享乐与节制、快乐幸福与痛苦灾难,使得人的生命得到锤炼,使得人在生死一体中提升生命质量。因此,生命过程“必定是一种对生命本质的悟并由此出来的一种为人之‘活’的状态”[2](P260)的呈现、体验过程,也成为生命自觉的感性基础。生命行为之规范成为人的生命行为内在之自觉的前提就是人的生命之感同身受,是出于己之遭遇的感受而推至他人的恻隐之心的人类的良知。因此,体验是真正理解生命的开始。
(三)积极吸收生命及其生命教育的最新成果
近二十多年来,人类对生命的认识有了许多拓展和深入,比如人类基因组工程。当然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如生命体克隆问题、转基因问题、各种人工辅助生育技术问题,等等。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人类在解决这些问题中获得了许多对生命的更加深入的认识,也由此形成许多新观点、新的生命现象阐释的通道。忽视了这些新的观点、解释,在生命教育中就必然会遇到许多困惑,甚至面对学生追问,你都无法回答。比如转基因食物安全、动物为何拥有道德关爱资格等问题。作为生存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受教育者,他们总是从现实生存和生命实践中提出问题。因此,生命教育需要不断吸收在生命领域及所有社会领域中的新思路、新理论。
同时,教育本质就在于塑造并完善人格。而人格本身是历史的、发展的,即人格总是“超我”和“本我”在当下的表现。一种新的生命理论、生命观点,就意味着对生命的一种新阐释。在当今全球遭遇气候异常、水资源严重缺乏、生物多样性危机等等情况下,生命体尤其是人类生命陷入危机之中。许多基于这种环境生态危机的观点、理论被提出,科学的事实数据让我们对生命存在的脆弱性、生命体存在的人化及人的生命体生存的物化状况,有更深刻也更直观的认识。这些正是以往生命教育之缺失。因此,生命教育需要这些理论、观点,这也是生命教育对时代需求的一种回应。
总之,生命教育究其根源的反思追问,使得生命教育不仅仅是诉求于情感或者口号,而有了理性认识基础上的坚守和执著。只有这样开展生命教育,尊重、敬畏生命才是真正人的生命之自觉。
[1]郑晓江.生命教育事业的回顾与前瞻[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5-8.
[2]熊小青.生命自然与自觉——现代生命哲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责任编辑:彭文彬)
On Life Education Based on Life Nature Meditation—Thinking on life mor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Xiong Xiao-qing
(Institute of Marxism,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Ganzhou, Jiangxi, 341000, China)
Valuing and practicing life education is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present higher education.Lif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however,has been misunderstood as a slogan and a kind of emotional and coping education.Reflections on life and life education are indispensabl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which is determined by college students' cognitive and thinking pattern.To achieve actual effect life educ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nd rational cognition of life itself,that is,the “meditation" on life and life education,so as to help college students' truly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raise their awareness of life in life education.
life and life education;life meditation;life consciousness
2013-12-01
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现阶段大学生生命成长的新情况与高校生命教育创新”(编号:11YB189)。
熊小青(1964—),男,赣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生命哲学。
G410
A
1674-6120(2014)05-005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