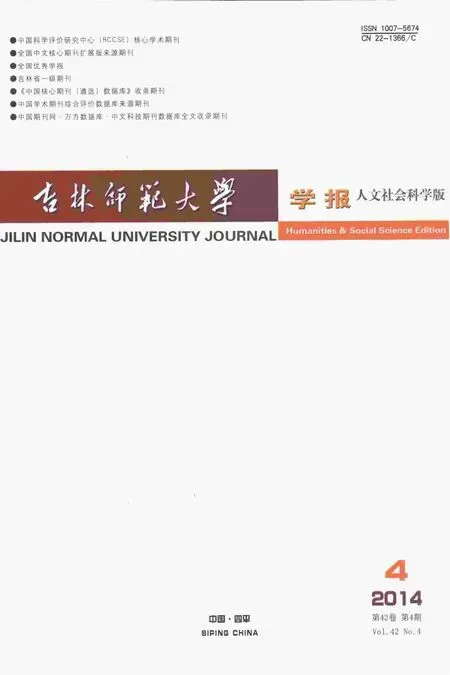中国现代散文诗的语词建构及语体特质
张 翼,陈 芳
(1.福建警察学院 基础部,福建 福州 350007;2.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中国现代散文诗的语词建构及语体特质
张 翼1,陈 芳2
(1.福建警察学院 基础部,福建 福州 350007;2.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散文诗的语言融合散文语言的舒展自然与诗歌语言的精密凝练,放弃对语言高低抑扬、错落有致的外在形式美的追求,专注于对情感内在韵律的捕捉。作品在娓娓道来中隐含着寓意、哲理,自由不拘地把流动多变的现代生活的瞬时意绪抒发出来,将繁复深潜的内在意识予以暗示。在对细节、物象、事件形象叙述基础上,以整体语境呈现复杂的周遭关系,涵容现代性的生活经验与思想冲突,进而把握存在的意义。中国散文诗的语言更兼文、白、中、西之长,追求物象与事象关系中的多重可能与生成,以独有的语词建构容纳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新的审美情感体验与精神困境,既涵盖文体的文类共性,也体现文体的民族个性魅力。
散文诗;语词;建构;语体;特质
语言是作家内心活动的媒介,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即在“使用”,语体的选择反映着作家与社会及自我所要建立的个性结构与言说形式。同时,语体是文体的肌质,须与文体特性相谐,勒内·韦勒克认为可做这样的文体分析:就是对作品的语言做系统的分析,从一件作品的审美角度出发,把它的特征解释为“全部的意义”,这样,文体就好像是一件或一组作品的具有个性的语言系统。[1]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作为散文诗的开山之作,其语言独具特色及混杂性,本雅明认为:“它们不受诗的氛围的约束,以其独创的光彩震慑了人们。”[2]散文诗的语言仿佛诗落入散文中,给予诗意更多的延展空间。其语体特质适宜对物象、事件作细节或形象叙述基础上,表现瞬时变幻的潜意识、幻觉等非理性的超验世界,涵容复杂的现代性生活体验,适合现代人对生存况味的“重新澄明”。中国散文诗的语言更兼文、白、中、西之长,包涵了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新的审美趣味和情感体验,涵盖了文体的普遍共性,也体现了文体本土性魅力。从语言诗学的角度对文本加以细致解读,可以避免意识形态粗暴的意义附加影响对文体的诗学研究;语言又与思想、经验、思维纠结在一起,也不宜采取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分析,割裂能指和所指、语言与言语,落入纯形式主义研究的窠臼。
一、不拘外在形式的内在韵美
散文诗的语言放弃了高低抑扬、错落有致的外在形式美追求,执着于情感流露的自然旋律,富有内在的韵美。泰戈尔认为散文诗的韵律单凭外在的语言形式则不显著,但靠感觉仍能体味到韵律的存在。郭沫若称散文诗的语言是具有内在音乐精神的“裸体的美人”[3]。散文诗可以没有外在韵律或音律的外形式,但其语词建构必须忠于内心情绪的起伏。穆木天认为散文诗的语言放弃宫商徵羽、双声叠韵等外在纯音上的节奏追求,专注于内在情思旋律与语言流动的配合。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伯认为,语言的“声音应是意义的回声”[4],强调语音对意义的忠实追随。散文诗的语词建构更多考虑的是语音对思想内容的呼应与回响,而不仅为了单纯的语言节奏之美。
沈尹默创作于1918年的《三弦》是最早出现的散文诗代表作之一,体现了散文诗语言追随主体情思而不拘格律的特色。作品以短句为主,形成更多停顿,增加了节奏,让语言顺应内在情感的韵律节奏:夏日正午烦闷,孤寂的情绪与弦乐较为短促的韵律相契合。作品中还用了14个声母为d、t的字,如“挡”、“动”、“大”、“低”、“挡”、“弹”、“断”、“荡”,用以模写三弦的声音,让弹拨乐器抑扬顿挫之声与抒情主人公沉重的内心齐鸣共振,让语音成为内容的呼应与回响。同时,“悄悄”、“闪闪”等五组叠字的穿插应用,使语言沉郁顿挫之中又不失音节的和谐与旋律的流畅,借此表现一种世道没落的情怀。《三弦》虽不分行,也没押韵,但凭借语言节奏对内心情感旋律的忠实追随,形成散文诗语言特有的张力和韵味,正如茅盾所指出的,“比我们常见的分行写成长短一样的几行而且句末一字押韵的诗更‘诗些’”。[5]
初期的散文诗和新诗创作同处于摸索阶段,虽也借鉴西方诗歌的创作方法,但更多的写作背景是中国传统诗歌体式,白话文很难迅速创造出超越古典诗文的文学体式。在沈尹默的《三弦》中还有古诗韵律痕迹的留存,到了朱自清1923年创作《匆匆》时,则看到其语言融汇文、白及中、西之长,以独有的语词建构展现时代变迁中新的审美情感体验。作者任凭内心情感的波动,以舒展自在的语言,贴切再现了内宇宙的波澜起伏。作品完全由着情绪的内在节律抒写而成,虽没有外在纯音美的节奏追求,却能感受到内心音乐旋律在字面上的灵动舞蹈。朱自清以顺乎内在情感的律动组织语言,放弃了外在获得音乐性的手段,不依靠格律、押韵等人为形式以获取语音上的旋律美,而是让语言的情韵之美从心灵对题材的精微感觉中去自然流淌,使情感在无拘无束的语言中获得自在和谐的表达。《匆匆》打破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的界限,将熟悉的生活场景描写与个性化的情感抒发行云流水般融合在一起,让内在情感在语言中自然流淌。
文言诗语得益于“竹节式”的语言结构,注重“字”的推敲,讲求形音义的巧妙配合,倚重字本身的弹性,通过字自身而炼铸语言的“爆破力”。“春风又绿江南岸”,单一个“绿”字便盘活了全诗;“红杏枝头春意闹”,一个“闹”字有点石成金的功效。竹节式的语言结构不仅获得视觉上的均齐感,还带来听觉上的音韵感。均齐之美是古诗的必备要素,它既指语言排列上的“均齐”,也包含诗句字词上的均齐。新诗在五四时期对古诗“竹节式”语言结构进行破坏与颠覆后,迅速回归,开始在“被拉长的竹节式结构中探索生成诗性的特质”[6],以“音尺”、“顿”或“音组”的新竹节替换古诗讲求平仄押韵的“字”竹节。散文诗的语言放弃竹节式的语言结构,追求词语与词语之间的自然链接,通过句子间广泛的联络网结,实现句群或语篇的整体效果,注重作品全篇语境的生成。散文诗中的情感旋律不会像新诗那样由于考虑分行而被强行打断,其语言讲究情韵上的舒展流畅,让语言配合内部情思节奏的起伏消长表现出随波逐流式的自然律动。散文诗不仅靠语词的独特建构传达内部情感的节奏,还借助句法的复沓、排比、对称等修辞手法,呈现内在情思的迤逦流转。冰心的《往事二·之三》接连使用四个“今夜的林中……不宜于……”的否定句式为下文“今夜的青山只宜于这些女孩子,这些病中倚枕看月的女孩子”做铺垫。使用排比兼对比手法,将四种热闹的情景与夜下林间的清澈静冷作比照,句子间通过广泛的意义联结,转达少女细腻温柔又微带忧愁的情怀。情感内在节奏在笔下自然溢出,引领着或长、或短、或偶、或奇的字句,虽使用排比、反复、反问等修辞手法,但不以诗行为单位,而以情绪为单位。作品里不乏有精致的文言的情韵之美,但更多涌动的是幽微、复杂的现代意识流、情绪流,必须以内在节奏的秩序为主导的“内在律”才能应对裕如。散文诗的语言是自觉的艺术加工,但这种“自觉”是在内在律的引领下与情境相谐,不以诗行为单位,而以情绪为单位。自然舒放的语词建构使情绪的节奏从语言的形式节奏中解放出来,虽语言外形上不讲究整饬对称等形式美,但语词、语调、语速以及修辞都在句式中默契配合着情思的婉转流变,抒发着对生命的无比眷念。心灵对客观事物的微妙反应和瞬间领悟,在不拘格律、不拘成法的字里行间流畅自如地传达,意到笔随,情感真挚、动人。
散文诗语言的内在韵美主要靠“情绪取胜”,没有固定节奏和音律规范的束缚,也没有分行排列的显豁形式,不拘格律、不重外在形式的特点使节奏韵律在表征上不明显。语言节奏的缓急轻重依据作者自身状物抒怀的需要,其蕴含的内在节律需通过语言的整体氛围和主体情思的自然流淌来体会,仅抽取片段则难以感受其内在旋律的完整性。鲁迅写于1925年的《希望》并没有什么和谐顺畅的节奏和韵脚,甚至出现不少转折性的虚词——八个“然而”和五个“但”,委婉地写出了自己思想经历了无数次希望与幻灭交替的心理流程。和谐的语言节奏须尽量减少转折、粘结的介词、连词,但散文诗的语言建构放弃外形式的和谐,转折性虚词的插入,更能传达鲁迅在各种战斗中内心前进变化的复杂感受与百般滋味。全诗“迂缓结鴂”[7]的节奏与作者思想矛盾斗争的曲折激荡完美地融合,形成语言内在的韵律,收获情感与思想的“性格”力量。
二、诗文交融的精巧自然
散文诗的语言诗文交融,不仅可以对物象、事象作周致生动的描叙,还便于自如地再现内宇宙朦胧晦涩的地带,捕捉现代人瞬间变化的复杂意绪,把作者的内心体验与外部世界深蕴的生命意味悄然融合。
何其芳的《画梦录》集中体现了散文诗诗文交融的语言个性。何其芳在谈其写作时说:“比如《墓》,那写得最早的一篇……写的时候就不曾想到过散文这个名字。又比如《独语》和《梦后》,虽说没有分行排列,显然是我的诗歌写作的继续,因为它们过于紧凑而又缺乏散文中应有的联系。”[8]这番创作谈表明其在创作过程文体意识的游移不定,虽自身认为是诗歌写作的延续,但又深知其不具备诗的最基本也是显著的语言形式——分行排列;虽具有散文的外在形式,但其内在表述的跳跃性和心灵化又跨越了散文的写作范式。尽管语体意识不明,尚存文体困惑,但何其芳还是采用这种全新的语言形式进行创作,这是因为散文诗语言极其适应作者内在情感的召唤。《黄昏》描摹的不是纯粹的街景,而是富有心灵意味的生活图景。“孤独又忧郁地自远而近”的“马蹄声”、“白色的小花朵”、“曼长的立着一列整饬的宫墙”、“暝色天空下小山颠的亭子”,这些如诗般密集出现的意象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再加上对细节场景的形象生动再现,共同描绘出作者青春的感伤和梦幻,给内心世界的诗意表达以更延展的空间。《黄昏》开头的比喻让人耳目一新,将马蹄声比作洒落在街上的白色小花朵,“在普通人以为不同的事物中间看出同来”,“发现事物间的新关系并且用最经济的方法将这关系组织成诗”,[9]这种“远取譬”与黑格尔在诠释隐喻时说的“为着避免平凡,尽量在貌似不伦不类的事物之中找出相关联的特征,从而把相隔最远的东西出人意料地结合在一起”[10]是相同的艺术路径。作品中不乏这样意象性的语言,但其更注重词语与句子间,句子与句群间的广泛的意义网结和整体联络效果,比文言诗句靠有限字词的“单打独斗”以寻找事物间的联接来得容易。对物象“马蹄”细节的形象描写让读者在动态的“马蹄声”与静态的“白色小花”之间亦有迹可循,既享受了诗歌语言“陌生化的”效果又不会如诗那样,因变形的跨度过大而导致多数读者解读的困难。作家董鼎山回忆《画梦录》出版之后,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掀起一阵不小的波澜,那时的文学青年几乎人手一册,由此可见一斑。通感也是散文诗中常见的修辞手法,新奇的意象传达出心灵刹那间的微妙感受:在马蹄声中竟然可以“看”到颜色和图案;不断流转的黄昏时光如物品一般可以载在车上沿途播撒,让人驻足观赏;“慵倦”的主观感受,被转化为可视的东西,似乎只是无端地由外物生出,与“我”无关;暮色仿佛是可以触摸的柔软物体,“如从银灰的归翅间坠落一些慵倦于我心上”。这样的语言自然精巧,既富有诗歌语言的凝练、含蓄,又具备画卷写生的细致、形象,便于抒情主体将客体景象的个性化感觉淋漓尽致地予以展现。后半部分,何其芳返回内心,以冷艳的笔调诉说心底的幽微情思。用“曾有”、“又曾有”的递进式回忆,把过往与现时的情思贯通起来,前述的追怀与后面精巧的喻义连成一片,结尾作者点明伤感的缘由。《黄昏》以精巧自然的文字再现了现实与梦幻不断流转切换的场景,自由流畅的文字赋予抽象情绪和情感经验以具体可感的形象与韵律。
《画梦录》的语言有的真实细致,如同纤毫毕现的工笔画,但在精雕细镂的“工笔”之中又有灵动抒情的诗意笔致,兼具诗文之长,将散文的形象描述与诗的朦胧多义浑然无间地交融在一起,把青春的迷茫、孤独以及现实与梦想冲突的苦闷、忧伤予以细致而诗意地描画出来。于赓虞认为:“散文诗乃以美的近于诗辞的散文,表现人类更深邃的情思”,“诗与散文诗最大的区别,就在作散文诗者,在文字上有充分运用的自由,在思想上有更深刻表现的机会。”[11]于赓虞的散文诗很好地诠释了他的文体自觉。1925年11月22日,他与好友到京郊的公主坟游玩,写过自由诗《公主墓畔》和散文诗《伴某君游公主墓》,两篇作品创作的时间相隔了四年,但都源于同一次郊游经历。《公主墓畔》写于郊游当晚,《伴某君游公主墓》写于1929年。时隔四年,作者为何还重温旧梦,另创新体?“我已不如四年前今日之心情,会将此死了的少女之青春,渗入我的神秘的歌喉,而今,我只看见了丑恶的骷髅!”这番夫子自道透露了四年后创作《伴某君游公主墓》时的复杂感怀与当年浪漫感伤的《公主墓畔》哀歌大为异样:不是当年的余兴生发,而是别抒怀抱,另辟境界。“病残的灵魂”、“于混醉之后”,“做了许多怪梦”……这些繁杂的意绪冲破了诗行的拘束,需藉以舒展自在的语言形式方可表现出来。散文诗的语言随意生发,长短不拘,比诗句韵语容纳更多的意象和细节。《伴某君游公主墓》的每小段像一句诗,任凭跌宕变幻的情感随性流动,其繁复流转的情思是《公主墓畔》中诗句难以表达承载的。《伴某君游公主墓》中对现实的解构,对世人的嘲讽任由一连串的排比和警句决堤而出,既强化了诗情,又深化了理致,时空场景、情感节奏和言语因素有机结合,使理性思辨和心灵感觉的流程更为清晰可见。
鲁迅的《野草》展示了散文诗语言的修辞追求:凝练精美且自然畅达,文情并茂且含蕴深厚。如开篇《秋夜》对夜空、花草和枣树的拟人化抒写,含蓄传达出作者对夜空的独特感觉与讥讽态度。接着写粉红花还做着弱者的美梦,令人同情。随后出场的是“简直落尽了叶子”的枣树,并多次重复枣树“简直落尽了叶子”。既写实又写意,道出枣树与粉红花等其他植物一样饱受高高在上夜空的残害,为下文枣树的奇崛雄姿做铺垫与渲染。紧接着详细描写了枣树的姿态和行为,调动句式、辞格和语调共同强化枣树的不屈形象。这时的枣树已“变形”,不单纯是自然界中的植物,而成为鲁迅想像的投射物,它不仅清醒地洞察万物,还脱卸负担,在自我保护的同时向恶势力发起进攻。这显然与作者提倡的韧性战斗的精神异质同构,或者说,鲁迅把枣树人格化、心灵化,对物象的细节描写升华为象征的境界。诗的语言因极尽俭省,不易对细节展开描写,难以对事物周遭的关系作出复杂覆盖,而散文诗的语言多以叙述为主干,现场感更强,追求物象与事象关系中的多重可能与生成。它可以对“枣树”周遭各种关系展开细节性交代,“奇怪而高的天空”、“冷眼的星星”,“瑟缩地做梦的粉红花”、“夜游的恶鸟”、“灯火中献身、喘息的小青虫”,这些关系中蕴藏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是鲁迅对生活的智性审度,传达自身对社会的独特认知:希望青年既不要像“小粉红花”一样,以美丽的梦来喂养自己的天真和幼稚,也不要如“小青虫”那样为追求光明而作出不必要的牺牲,应该如“枣树”那般,与强大的黑暗势力做长久的韧性的“壕堑战”。
散文诗的语言不讲求固定的节奏与和谐的音韵,但“韵在骨子里”;语言清楚明白,却不作平面叙述,比散文的语言更倾向于心灵化,娓娓道来中隐含着各种意蕴、哲理,抒发现实生活里瞬时产生的意绪,把细腻繁复的意识流、幻象暗示出来。在对细节、物象、事件形象叙述基础上,用整体语境呈现社会变迁中复杂纠结的关系,涵容现代生活里认知性体验与情绪性体验。中国散文诗的语词建构融合文、白、中、西之长,通过语言的刷新,复活汉语的生机,让人们理解和返观世界,以“诗意地栖居”实现审美的主体间性。
[1]韦勒克,沃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203.
[2]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张旭东,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120.
[3]郭沫若.论诗三札[M]//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十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337-338.
[4]聂珍钊.英语诗歌形式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39.
[5]公木.新诗鉴赏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12.
[6]刘剑,周帆.新诗“竹节式”结构的诗路探寻[J].西南大学学报,2011(5):55-60.
[7]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尹慧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60.
[8]易明善,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何其芳研究专集[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591.
[9]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3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3.
[10]黑格尔.美学:第2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32.
[11]解志熙,王文金.于赓虞诗文辑存:上[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309-310.
[责任编辑 王金茹]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 Form and Lexicon Construction in Modern Prose Poetry
ZHANG Yi1,CHEN Fang2
(1.Foundational Course Deparment,Fujian Police College,Fuzhou 350007,China,2.College of Literature,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Fujian 350108,China)
Prose Poem language combines the natural stretch of prose and poetry of precision concise lan⁃guage,gave up on the language level circumflex,patchwork pursuit of formal beauty,focusing on capturing the emo⁃tions inherent rhythm.Hidden in plain narrative meaning and philosophy.It is appropriate to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modern life instantaneous thread expresses them and puts out the complicated inner consciousness implies,pres⁃ents the overall context surround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ssimilative modern life experience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Chinese Prose Poem fusion of classical and modern languages,Chinese and Western lan⁃guages strengths accommodate social change in new aesthetic emotional experience,covering the stylistic similari⁃ties,reflecting the national character style charm.
The Modern Prose Poem;phraseology;construction;language form;characteristics
I01
A
1007-5674(2014)04-0067-04
10.3969/j.issn.1007-5674.2014.04.012
2014-05-06
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现代散文诗的诗学研究”(编号:JA13349S)
张翼(1975—),女,福建福州人,福建警察学院基础部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陈芳(1977—),女,福建福清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编审,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