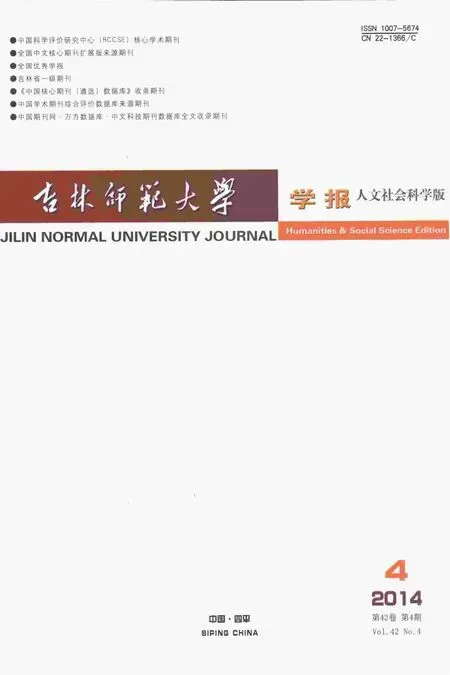市民文学与平民文学之争
董国炎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市民文学与平民文学之争
董国炎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关于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社会基础,长期存在两种理解:一种认为通俗文学的社会基础是市民阶层,甚至直接称之为市民文学;另一种认为通俗文学的社会基础是平民阶层。这两种理解长期存在,市民文学提法占据上风。然而市民文学理论体系来自欧洲,在中国运用有生硬牵强之处,平民文学观念体系更适合中国国情。实际上平民与市民两种体系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相支持互相依存的互补关系。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与平民阶层的发展壮大,也是同步互补的关系。
通俗文学;社会基础;市民;平民
围绕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古人的评论大多从文白雅俗角度展开,其社会基础问题基本无人重视和研究。然而随着西学东渐,特别是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传播发展,通俗文学的社会基础问题,就成为重要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通俗文学的发展,依赖生产力发展和城市繁荣,那么通俗文学的社会基础,肯定是市民阶层,甚至把社会基础上升为文学属性,直接称之为市民文学,这已经成为广泛使用的概念。
但在市民文学概念的运用中,人们的实际理解有很大差别,其运用中经常有各种歧义现象。比如:市民文学的时间范围,一种观点认为,晚明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城市繁荣,市民阶层壮大,随之产生市民文学。“三言二拍”中很多作品,像《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郎独占花魁》、《施润泽滩阙遇友》之类,就可以作为市民文学的代表。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在近代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背景下,才可能产生市民阶层及相应的文学。而中国近代化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市民文学只能在鸦片战争之后,在此之前谈不到市民文学。但还有另一种观点,与部分日本韩国学者主张的“中国近世史始于宋代”的说法相呼应,认为中国城市经济之发达、中国市民之产生、中国市民文学之产生,都应该从宋代开始算起。在以上这些讨论中经常运用政治经济学和阶级分析方法,城市中哪些人的创作属于市民文学,实际上成为核心问题。
在此举出两例笔者的“自己人”的观点,以便看出,如何划分市民群体,实际是个分歧很大的问题。一例是我敬重的谢桃坊先生,1997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市民文学史》。一例是扬州大学毕业的优秀博士方志远先生,2004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两位先生都是首先对市民进行定义,规定哪些城市居民可以算作市民,哪些城市居民不能算作市民。谢桃坊先生的《中国市民文学史》首先在城市居民中划分市民:“市民阶层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代表新的商品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手工业者、商人和工匠。坊郭户中的地主、没落官僚贵族、士人、低级军官、吏员以及城市的统治阶级附庸,都不应属于市民阶层的;只有手工业者、商贩、租赁主、工匠、苦力、自由职业者、贫民等构成坊郭户中的大多数,他们组成了一个庞杂的市民阶层。”[1]
方志远先生的《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以很大篇幅定义和划分市民,他把市民划分为三类:一是城市知识分子;二是工商业者;三是妓女、游民及其他身份的市民。方志远还进一步分析:明代后期全国的三五十万生员“绝大多数都在各地城市为市民”[2]。认为再加上各种私塾、族学、社学,当时的知识分子型市民应不下100万人。
谢先生的书出版时间早,写作时间更早,这应该是第一部中国市民文学史,观点方面难免有些较早的痕迹。方先生的书毕竟到了21世纪了,也体现了新的眼光和魄力。因此两位先生的观点常有明显不同之处。例如,围绕知识分子如何划分,双方观点已经形成对峙。谢先生的市民范围中,没有士人的一席之地。他用新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来作内在性质判断,用“只有”作出明确划分:知识分子明确不属于市民。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谢桃坊先生这种分析判断很正常,知识分子需要“再教育”,属于被改造对象。这曾经是一种普遍常识,更具有一种严肃的方针政策意义。这个群体自然不可能成为先进的市民。直到特别重要的新政策颁发,而且需要明确提出: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一部分。局面才根本改观,长期被教育被改造的知识分子才重新打量各种问题。
方志远先生划分市民群体,没有以往的教条桎梏,给人痛快之感。但是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仍然可能让人们产生新的困惑。中国士人的身份地位很复杂,自古以来就有高门、寒门、门阀、世族、庶民、平民等种种称呼。而士人、文人、知识分子这类称呼其实笼统、空泛甚至苍白,决定人们的贵贱地位、婚嫁选择、青眼白眼种种,往往是人们所处的具体条件背景。方先生把不入仕的文人都看作市民,从社会统计学角度说,似乎只能这样划分。但是有没有其他标准与方法呢?知识分子当中既有穿着长衫却混迹城市下层讨生活的贫困潦倒的孔乙己们,又有华贵的文人绅士,尽管不做官,但是他们交接官府,仆役婢妾成群,豪奢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远超过一般财主。看来在市民群体中排斥所有文人,或者单纯以入仕不入仕来划分文人,都可能有简单化的弊端。
商人的划分办法,同样存在矛盾。商人中既有普通商贾,也有奢华惊人的富商大贾。很多富商紧密依赖官府、交结官府,给人的感觉仿佛官家人。豪华富贵如《红楼梦》中贾府,府中也不过只养一个昆曲班子,后来还把芳官龄官一班小戏子分给公子小姐们做了丫鬟。然而扬州大盐商江春却家养花部与雅部两个戏班子。很多大盐商拥有官衔,甚至有赏穿黄马褂者。商人之间,地位高下悬殊判若云泥,他们若整体归类很不容易。谢桃坊先生采用“商贩”一词,看来不但排斥豪商巨贾,可能也排斥很多店铺老板。城市中各种衙役差人、男女仆役这个阶层,涉及的行当很多很杂,总人数也不少。在谢桃坊先生的划分中,他们可能属于“统治阶级附庸”,不在市民之列。方先生的划分中,他们好像属于其他身份的市民。诸如此类的问题林林总总,都显得庞杂。实际上,与市民文学研究领域常见的评判标准相比,这两位先生的观点已经属于宽泛宏通。可惜的是在他们的体系中,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若干矛盾。笔者以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市民文学这种理论体系不适合中国国情,把产生于西方的市民文学观念拿到中国环境来使用,难免出现生硬甚至混乱之处。
市民文学观念来自欧洲,但是中国城市的特点与欧洲城市有很大不同,城市居民的状况有更多不同。在中世纪欧洲大陆,原有的城市,不过是贵族领主控制的封建城堡,此外并没有别的城市。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状态下,工商业很不发达,这些城市的功能也主要是政治中心及军事中心。由工商业者居住并控制的城市,是后起的,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漫长,并充满坎坷艰辛。这种城市最初不过是一些商贩和工匠的聚居地。在传统农耕社会背景下,这些商贩工匠等于是社会边缘闲散人员,其成员大多是各种灾难中失去土地的农夫、大家庭中没有继承到土地的次子、幼子等。这些没有土地的人们为了谋生,选择各种边缘性服务工作,在各城堡、各采邑乃至各公国之间贩运贸易农副产品,或者自己加工生产若干物品。他们聚集居住的地方,经常在领主城堡之外,或在不同城堡、不同采邑的中间地带。领主的城堡经常在地势险要之处,有些位于山岗上,用巨大石料修建的城堡异常坚固雄壮,而工商业者聚集居住的地方,经常在平原在水陆交通要道上,无险可守,杂乱凡俗。随着生产和生活的发展,商业和手工业也不断发展,工商业者居住的地方逐渐发展为一种新型城市。在罗马帝国崩溃的局面下,欧洲大陆充斥诸多封建领主,各种国王、主教、公爵、伯爵和男爵之间,形成一种“契约式封建”的特殊状况。这种特殊状况造成一些漏洞夹缝甚至三不管现象,这有利于新兴工商城市在夹缝中壮大发展。
新兴工商业城市与封建领主的城堡,存在着经济制度、生活方式、政治主张、文化思想的严重分歧。市民主张自由贸易与合理的关税制度,追求“市民权”和“城市宪章”,本质上是合法地进行工商业生产、合法管理城市、合法成为自由民。封建领主对新型工商业从开始不重视,到后来坚决要控制要管辖,双方分歧不断加剧,甚至酿成激烈冲突和对抗。工商业城市代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代表近代工人阶级的发展,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在商业手工业城市背景下产生的市民文学,反映市民思想情绪,抵制批判嘲讽封建领主封闭割据倾向,从追求自由贸易经济制度发展到追求民主政治制度,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这种市民文学与19世纪欧洲文学一脉相承。欧风东渐以后,市民文学概念开始出现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市民文学概念,不仅与西方文学发展史呼应,更符合建国以来盛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因而受到重视和广泛采纳。
但是欧洲市民文学理论体系,包括其发展历史和各种具体主张,中国人经常觉得陌生。比如,欧洲市民追求的市政厅和议政制度,对中国城市居民来说,就是陌生和不甚理解的。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类型,先秦两汉南北朝以来,长期处于世族豪门政治之下,所谓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之类官员选拔制度与社会政治类型紧密依托,二者的联系息息相关,最为敏感。隋唐科举制度对豪门世族政治形成冲击,但当时的科举制度还很不完善,豪门世族还有很大威力。唐代文人的人生理想普遍有二:一是科举中进士。二是娶五大姓之女,这后一点正反映了豪门世族的牢固的社会地位。史学界有一个重要观点,安史之乱不但是唐代社会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转折点。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武人得志。凭借武装力量,藩镇割据,或改朝换代成为常见现象。由黄巢之乱历经整个五代时期,政权更替如同走马灯,帝王权贵经常被杀戮、被取代、被嘲弄。宋代以下,传统的豪门世族政治难以为继。宋初有人想编定新的世族谱,但是“赵钱孙李”云云,只不过是《百家姓》开头而已,不能代表尊卑高低排列顺序。
中国城市发展历史悠久,城市发达繁荣也早有记载,战国时期齐国临淄城车水马龙、行人摩肩接踵之繁盛,受到得意炫耀。汉代和魏晋时期的《二京赋》、《三都赋》之类,都反映中国城市很早就追求繁华追求规模的风气。汉唐时代长安城、宋金时代汴梁城、元代大都城,曾经是当时世界最繁华城市,人口规模可能都超过百万。这些繁盛情况都有文献可索,这些城市多是京城,或是地区中心城市,既是政治军事中心也是经济文化中心。这些中国的城市,自古以来首先是政治都邑,是帝王诸侯和官府的统治中心,是富豪权贵、巨商大贾、社会上层人物的居住中心,是思想文化中心也是经济财政中心。中国城市居民构成复杂,贫富差异和地位差异很大。汉唐城市盛行里坊制度,闾左豪右,截然有别。豪门贵族,甲第连云,贫民百姓,蛰居里坊之中。
宋代以后,里坊制度崩溃,但是直到明清乃至更晚,城市也好农村也好,官本位体制和贫富差异根深蒂固,居民贵贱有别,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判若云泥。中国并没有欧洲那种工商业城市。与欧洲工商业城市居民有极大差别,运用欧洲的市民文学理论,等于硬行套入一个外来理论,其实很不适应。中国的城市居民,实际可以分为很多阶层,各阶层生存状态大不相同。所以凡主张市民文学观念者,首先要对中国城市居民进行划分,规定哪些城市居民可以算作市民,哪些不能算作市民。这类划分认定办法,有时候显得逻辑矛盾、体系混乱。如果分析人们划分市民的依据,可以看出在中国市民的划分办法中,实际需要符合两个简单标准∶既要求生活在城市中,又要求社会地位低下。换言之,只有城市下层民众才能算作市民,实际上这完全可以称之为平民标准。所谓平民,不是按照居住城市还是居住农村的地域特征来划分,而是按照社会地位高低来划分,不管城市还是农村,权贵富豪之外的普通人,即属于平民大众。从中国社会数千年历史看,城乡差别不是造成思想文化差别的主要原因,贵贱差别才是主要原因。中国社会有一个特点,贵族与平民的差别好像并不稳定,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平民百姓草莽人物发迹成为新贵的例子也常见。然而政治机制和社会文化心理,却维持高低贵贱之别。人们说中国文化特征是官本位文化,就因为高低贵贱之别被持久延续。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平民文学才是切实适合国情的。
平民文学概念,在“五四”时期曾经得到提倡和运用。“五四”运动提倡科学民主,陈独秀、胡适等人提倡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八病说,反对贵族的、古雅的文言文学,倡导平民大众的通俗白话文学,正是在精神层面上提高平民大众的地位,张扬平民大众的精神文化。鲁迅把平民文学概念具体运用到文学史研究中,《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就明确提出:“是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3]这番话很简要,但明确提出平民文学的概念,指出宋人话本小说是平民文学初兴、清代武侠小说是平民文学再兴。鲁迅这个重要观点自上世纪20年代初提出,至今大约90年,但论其反响,却基本是长期沉寂的现象,这本身就显得意味深长。
鲁迅的观点素来影响很大,一方面,很多观点被人们详细解释,甚至过度阐释,唯独平民文学观点,好像没有多少人支持。但另一方面,好像也没有人明确反对过鲁迅的观点,即使在上世纪50—60年代侠义公案小说受到批判的时期,也无人对鲁迅此说提出异议。鲁迅这个重要观点问世90年,处于“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特殊状态中,可谓中国学术活动中的有趣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可能因为鲁迅说得简略,他有关平民文学的系统观点没有展开论述,长期不为人了解。原因之二,可能在于观点本身的挑战性和风险性,既联系平民文学这一概念如何把握,还联系我们对古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看法。有些问题是以往未曾研究过的,有些问题存在明显分歧。鲁迅的观点与流行观点明显不同,导致人们不愿陷入这些风险争议中。
鲁迅有关平民文学的观点至少涉及三个难题。第一,以具体评价而言,鲁迅作为平民文学再兴标志的清代武侠小说在几十年间曾经一直是被批判对象,认定这些武侠小说是平民文学重要代表,这需要突破很多认识藩篱,需要上升到理论高度来评价平民文学。第二,从文学史观念来看,鲁迅勾勒出一条历时七八百年的平民文学兴起、再次兴起的发展脉络。这条脉络实际还有延续,这与我们对封建时代文学演变的总体把握能否相容?第三,从文学史分期和文学阶段性质的界定而言,我们久已从“五四”作了一个根本的截断,在此终结了封建时代的文学。“五四”之后就是新的白话革命文学。但是清代中后期兴起的武侠小说不断延续发展,并没有终止于“五四”之前。如果承认这条平民文学发展脉络,可能会搅乱原有的文学史蓝图,这又造成接受心理的障碍。因为以上种种原因,鲁迅提出的平民文学观念及其发展脉络的评述都被长期搁置。也许正因为提出这一观念的人物是鲁迅,在特殊环境中,无人对鲁迅进行驳斥。于是不议不论,置之不理,形成一种奇怪的沉默。“五四”之后数十年间,学术领域盛行的主流观念是来自欧洲的政治经济学和市民文学理论,平民文学提法长期湮没。但是来自欧洲的理论与中国国情不符,实际运用中经常格格不入。
有些著述比较随意地运用市民文学、平民文学等提法,对概念的把握相当宽泛自由,好像市民文学、平民文学都是古已有之。这种宽泛有可能泛而无当,虽然平民百姓自古就有,城市居民也很早就有,但上古时代实际上谈不到平民文学、市民文学。如果简单引证先秦文献,容易说明当时城市娱乐文艺比较发达,但这种引证并不能反映当时文学发展状况。只有社会稳定经济发达,城市比较繁华,居民人数达到一定规模,娱乐消遣行业才可能形成市场。大众文化娱乐消费市场形成之后,才可能出现平民文艺和平民文学。具体说,民众寻求消遣娱乐,首先要有基本固定的场所。从事娱乐服务的人员,在经济方面需要获得报酬,需要形成经营体制。宋代出现的瓦市勾栏,正是这种性质的大众文化娱乐消费市场,而宋代出现的通俗读物的刊刻销售,又是最早的平民文学读物。汉代至隋唐还没有瓦市勾栏,百戏等演艺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广场,甚至寺院空地,演出的时间最多在节庆日。这种活动经常被称为“献艺”,“献艺”的首要对象是官员公侯甚至君王,演出得到的赏赐也主要来自他们。君王权贵们“与民同乐”,平民百姓人数虽多,却是观赏和赏赐的陪衬群体。
从《隋书·音乐志》和《炀帝本纪》来看,隋炀帝酷爱百戏散乐演出,征集各地艺人进京,演出规模和演出时间在历史上都可谓空前。隋炀帝在午门外辟出空地,由朝廷出资建起乐棚,并动员公侯达官们各自出资兴建乐棚,官员权贵们纷纷建起乐棚,形成了绵延数里的“演戏一条街”。当时百戏的内容,包括大小各种类型的杂技、魔术、歌舞,等等,千变万化。演出人员数万人,火树银花不夜天,炫人耳目。隋炀帝曾数次亲临现场,达官贵人、外国宾客、少数民族酋长都来观赏,全城百姓男女老幼倾城而出。官府组织的类似演出,通常只是元宵节几天,而隋朝这次演出的时间,几乎贯穿整个正月。这大概是历史上“献艺”活动的典范了。
然而尽管当时隋朝国力强盛,隋炀帝组织“献艺”活动魄力很大,官府组织的“献艺”仍然不能与后代的大众文化消费市场相比。大众文化消费市场包括文艺产品的生产创作、修改加工再创作、欣赏批评接受过程、传播传承过程,能够长期延续,有很强生命力。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说话人的讲史表演,能够长期吸引大批观众,不受“风雨寒暑”之影响,书棚中日日拥挤。这种生命力形成一种自然循环态势,因而生命力顽强。宋代非常敏锐的重要学者李覯《直讲李先生文集》中,曾经注意到文化娱乐行业从业人员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这个群体人数众多,居住里巷之中,歌啸自得,往来自恣,不在古四民之列。超越了传统的士农工商,正反映文化娱乐行业当时是一种新兴产业。大众娱乐和通俗文学生命力强,更体现在受众社会基础之广泛。不单以城市普通民众为基础,更以广大乡村普通民众为基础。平民文艺和平民文学对应的正是城乡广大受众群体。
宋代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水平,使平民文化消费市场形成。平民文艺能够形成稳定的类型,占领相应的文艺舞台。宋代说话从相关作品的创作、表演、传播、继承,文艺产品的消费接受,包括刊本的修订、刊刻、刊本销售和购买,都处在说话艺人、勾栏主人、书坊主人把握中。东京和临安都有专门说书的书棚,平民大众听众人数众多,甚至不受风雨寒暑之影响。如果书台上坐着说话人,台下听众主要是各类平民,包括商贩、工匠、衙役、军卒、游民闲人等三教九流人物,在紧张聆听中,在哄笑叫好或者责问声、唾骂声中,形成了创作和接受相交融的过程。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就是说话人和听众,在这种交融中都比较充分地展现了自己的主体性。应当说这是一种平民文艺比较成熟的状态,确实反映平民文艺之繁荣和平民文学之兴起。
这里需要特别分析平民文学与市民文学的关系。显然只有社会经济和城市都比较发达,有了比较稳定的市民群体之后,相应的文学艺术活动才能发展起来。既然如此,就叫做市民文学不是更好吗?对此需要分析二者的差别,分析哪种更适合中国国情。平民文学与市民文学并无根本矛盾,但平民文学侧重社会地位,广大下层民众都是平民。城市平民因为集中,因为城市娱乐业更发达,所以城市成为平民文学最主要的创作和消费地点。市民文学是平民文学的核心,但平民文学绝不限于城市,农村平民也是平民文学的基础。考察平民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城市固然是重点,但广大乡村也是平民文学发生发展的地方。中国长期是自然经济占绝对地位的农业大国,小农生产像汪洋大海一样,而商业和手工业、娱乐业发达的城市,像大海中的岛屿,显然市民在人口总数中只占少数。市民文学的传播,需要通过流动的艺人、商贩和工匠,通过三教九流的游民,通过城市郊区的农民,传播到其他市镇和广大农村。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四首》中写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反映的正是说唱艺人在乡村流动演出的情况。
元代以下,通俗文艺发展迅速,城市勾栏之外,艺人在城乡各地流动表演规模扩大。各类艺人唱戏说书,冲州撞府打野呵,规模大小不一,数量数不胜数。还有非专业性的地方文艺表演,春社秋社演出,节庆演出,敬神赛会演出。此外,还有宝卷、善书之类,长期在乡村发展,加工底本者、演唱者和听众,人数不少而且相当稳定。有些宝卷书目的继承和表演,由同一家族几代人长期延续。郑板桥曾有诗写到清代扬州郊区农村,人们从事的多半是为城市服务的职业——“十里栽花算种田”。郊区农民的经济活动围绕服务城市展开,城市生活及审美风气也对郊区农村产生重要影响,郊区居民对城市文化的发展,也有积极的直接贡献。清人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乾隆时期扬州戏曲演出情况,扬州周围四乡八镇之人,组织花部戏班到城中演出,而且成为扬州最活跃的戏班,因为很受欢迎,盛暑季节也不停演,因而被称为“火社”。这些戏班中人,家庭基本还在农村,他们在城市和乡村可能都有演出,农忙季节参加生产劳动也是可能的,说他们是市民或者农民都未必准确,称之为平民符合实际情况。花部戏本来是各地乡土戏,经过多方面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京戏。京戏的形成,意义重大,但并不能说它仅仅是市民文艺发展所成。京戏的形成与四大徽班进京有直接联系。四大徽班首推三庆班,班主高朗亭后来还担任北京梨园行会会首。高朗亭是扬州府宝应县人,四大徽班中有不少扬州籍名伶。后来京剧名伶梅兰芳就是籍贯扬州府泰州。很多梨园世家、说唱艺术世家和通俗文学作家,出自某州府某乡村,这在中国是很正常的。城市和农村都不是孤立静止的,各阶层各类型人口的流动、影响、交融,也从未停息。如果综合把握农村文艺与城市文艺相结合的过程,很多文艺品种称为平民文艺更准确,更符合它们的动态状况。
中国通俗文学不断扩展延续,生命力很强。这与中国通俗文学社会基础广泛,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这可能涉及到中国文学发展动力和发展规律等重要问题。实际上,平民文学兴起推动文学发展,也是中国文学史重要发展规律。这条规律的表现是:很多新兴文学艺术种类,首先从民间从下层兴起。这个民间下层地域范围很广,包括城市,包括乡村,还包括少数民族地区。
新起的文艺形式通常是以往未曾有过的形式。在初起时候,这种形式可能初具特征但还不够固定,可能粗陋简单,缺少足够规范,但是独具感染力表现力。其内容形式均可能比较新鲜大胆,与传统文艺规范有一定距离,但是受下层民众欢迎,得到传播。这种新兴的文艺种类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一种平民文学样式,这时会有一些文人接受新兴文学,帮助修改加工与传播,还会模仿这种新兴文学,用新的形式创作出具有文人特征的作品。文人普遍接受这种文学艺术之后,可能逐渐创作出不少经典作品,使这种文学成为文学史上稳定范式。在新的文学形式固定化的同时,也有部分文人过分讲求形式,对形式规范严格要求,可能导致这种文学走向典雅化甚至僵化,与普通民众审美口味的距离越来越远。
当原有文学形式经典化也逐步僵化之后,民间又会产生新的文艺形式,受到民众欢迎,得到传播发展。直到文人又接受新的文学形式。从四言诗的起源来讲,“十五国风”本来就是各地民歌。当四言诗逐渐僵化以后,五言诗又从民间产生。“汉乐府”收集的大量民间歌诗,就是以五言居多。七言诗体最初也是民歌的一部分,文人成为五七言诗写作的主力以后,经过长期探索实验,在六朝后期初步完成近体诗形式,至唐代达到鼎盛,成为中国诗歌史的顶峰。词的起源说法不一,不论起于妓女乐工的歌唱,还是起于民间的清商乐府,乃至起于少数民族的歌唱,最初都是下层的平民的文艺。唐宋以来讲唱文学不断发展,宋元话本兴起,是一种重要的平民文学种类。明清时代文人拟话本有不小成绩,也产生很多问题,这正是文人接手后的常见表现。评话评书的发展,弹词鼓词的发展,相应的小说唱本以至整个通俗文学的发展,都联系着平民文学不断创新这样一个发展规律。这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规律、基本规律,通俗文学的社会基础深厚广阔,保证了这条规律有强劲持久的生命活力。
[1]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13.
[2]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4:92.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济南:齐鲁书社,1997:225.
[责任编辑 王金茹]
On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Civil Literature and Civilian-Literature
DONG Guo-yan
(Humanities School,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Jiangsu 225002,China)
About the social basis of ancient popular literature in China,there are two kinds of understand⁃ing for a long time,some people think the popular literature is based on citizen stratum,even which directly was called citizen literature.Another think that is based on civilian estate.These understandings exist for a long time,the ideas of citizen literature have the upper hand.Compared with citizen literary theory,civilian literature concept system is more suitable for Chinese national conditions.In fact,civilians or the citizens is not antagonistic,but sup⁃port each other.Th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popular literature;the social basis;citizens;civilians.
I02
A
1007-5674(2014)04-0054-06
10.3969/j.issn.1007-5674.2014.04.010
2014-05-30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说唱文学史“(编号:13BZW084)
董国炎(1948—),男,辽宁营口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通俗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