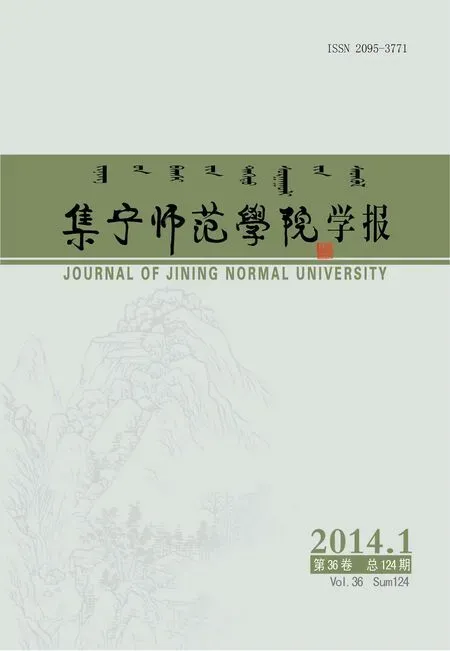草原文化与现代性
——以中国蒙古族文学为例
张无为
(赤峰学院文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草原文化与现代性
——以中国蒙古族文学为例
张无为
(赤峰学院文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文章围绕中国蒙古族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展开,阐发了蒙古文学中古代即有潜在的现代性元素,当代则有更多自觉或不自觉的现代性理念的事实,揭示出与汉文化不同的个性及其对中华民族的独特贡献;同时对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民族性、草原文化、蒙古族文学等概念及其界定均有新的思考,以期为蒙古族文学、民族文学研究提供见仁见智的思考向度;由此也为当下中国文学的深入研究、混乱认识的澄清提供一些参照。
蒙古文学;草原文化;现代性;民族性
从内蒙古文艺界入手,打造草原文化的举措是智慧、及时而富有远见的。因为,提升或者矫正一个民族的精神品格与生活质量,以文学艺术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是最具长效与实效的选择。虽然,唤起华夏民族精神,重铸民族文化品格,是以全国五十六个民族为公分母或公约数的,但蒙古族文化毕竟是草原文化及少数民族文化最为典型的代表之一,故草原文化工程的建设,不仅能推动本地域文明前行,而且对整个国民素质的跟进提高,必将产生不可替代的影响力。
不过,多年来,每当提起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与汉文化之间的关系,大多都以为,后者是中心,是主流,是强势文化;前者只是边缘,是补充,是弱势文化。这在报刊文字中亦不鲜见,如此评价显然有问题。甚至,有的少数民族文化人,在提起自己的身份时,自惭形秽之感或有流露,更是大不应该。
因为我在考察文化现代性时发现,少数民族文化不仅各有其特长,而且其中一些民族文化中的根本性元素乃至文化精神,在汉语文化的时代转型中,是非常值得借鉴与汲取的。例如:蒙古族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元素与现代性就有天然的相通之处,有些原生态特征都不必“摇身一变”,继承和发扬即可水到渠成。这是其它一些民族,尤其是汉文化中恰恰被断裂的。关注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必须注意到这些。下面仅以考察中国蒙古族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为重心,兼对民族性、草原文化、民族文学等相关概念等进行一些反思。
一 几个相关概念的清理与界定
至今,有关“现代性”、“民族文化”、“民族文学”等术语,在见仁见智中虽有相当的共识,但在内涵、外延的界定上依然莫衷一是,而这些都关涉到文化立场与文化发展,笔者以为,对此有必要进一步确认。
(一)现代性、文学现代性再确认
1918 年《新青年》第 4卷第1号,登载过周作人翻译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中,即有“现代性”一词。原文是:“陀氏著作,近来忽然复活。其复活的缘故,就因为有非常明显的现代性(现代性是艺术最好的试验物,因真理永远现在故)。”1948年《文学杂志》第3卷第6期登载过袁可嘉的汉译论文,标题就是《释现代诗中底现代性》。但在当时,这个术语并未引起学术界注意,真正运用“现代性”理论研究中国问题是从海外学者开始的。
上世纪70年代末,李欧梵等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①,将1895—1927年的中国文学思潮定性为“追求现代性”,已经有意识地将现代性理论系统应用于中国文学研究,但在中国并没有波澜。直到20世纪90年代,“文学现代性”才开始在学术界讨论得风风火火。1996年,杨春时、宋剑华发表《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②,引发了论争,文章结论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完成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转型,它属于世界近代文学的范围,所以,它只具有近代性,而不具备现代性。”由此,文学现代性成为大陆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如杨春时就相继发表 《试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性》和《文学的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他指出,现代性“包括工具理性(科学)和人文理性(自我价值)”,“理性精神成为现代性的核心”,而文学现代性不是对社会现代性的认同,而是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因此,现代文学才突出了非理性精神。他还阐释了文学现代性的一些特征:文学独立,反传统,世界文学,雅俗文学分流等。
就讨论情形而言,应该说,学术界已经意识到,对现代性这一概念不能作简单化理解,必须注意其内在张力,并大体有澄清的共识。不过,至今依然有人将现代性概念与人文主义、现实主义等19世纪以前的思潮属性混为一谈,可见现代性界定依然有争议。不解决这个问题,许多事情都难以说清楚。
那么,现代性究竟指什么?首先它是与传统性相对而言的;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界限又是什么呢?对此,中国与西方区别明显,即在中国有“偏斜”特点。
在西方,现代性是指伴随西方工业化而产生的,与西方现代派社会思潮、现代派哲学、文学等流派特质相一致的某种属性,其核心理念是从新层面去反思人类,包括重新审视人的智慧、能力、价值意义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可见,现代性与既定的人文主义思潮有别,甚至有抵触。笔者以为,它是对人文主义思潮的某种纠偏与超越,正如后现代性是与后现代主义并驾齐驱。可见,从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到现代派思潮前后承上启下关系非常明显而有层次。
然而在中国,现代性从五四运动前后已经产生。当时,人文主义思潮、现代派思潮以及马列主义传播相互并存,此起彼伏。但是在中国大陆,从上个世纪40年代末一直到70年代末的三十年间,现代性则完全变成了另一种样子。人文主义思潮、现代派思潮都被排挤到圈外,甚至在边缘之外。你可以说这是独特的文化景观,不过,其中的现代性元素究竟如何判断这难免成问题。所以,中国的现代性并没有完全与西方接轨。正因此,当深入触及到一些关节就会发现,中国现代性、中国文学现代性兼有独特性与局限性。以下三点必须引起学术界注意:
第一,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固然是被动遭遇的,但其理论价值逼使我们必须真正改变单一化研究视角,抛开以“特色”为由的自以为是,而应该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反思与批判,否则,势必还会像建国后的中国现代作家一样,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最终却皈依了传统而不自知。其立场的如此转换,不仅导致了创作的全面滑坡,而且是十分可怕的。只有以极具内在张力的“现代性”视角审视现当代文学活动,才能推进这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才能在更大程度上弥补以往过于偏重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层面所带来的某些缺憾,才能在整体观照 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促进多样化,进而实现世纪转型。
第二,在西方文学中,“启蒙”与“审美”是对立的,而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很少有人自觉、有意识地表现“审美”与“启蒙”的截然对立。中国作家在追求现代性审美层面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启蒙”的诉求。长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界所关注、挖掘的也是现代文学作品中启蒙层面的现代性,这使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解读一直徘徊在改造国民性、个性解放、革命等领域。新时期初,这种相互杂糅在一起的特征再一次出现,有学者把它概括为前现代性,是不无道理的。其实,“现代性”的审美层面有助于弥补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这一缺憾,它对人、人类的生命、感性、终极的关注,将过去与现在有机地融为一体,揭示了作品何以经久不衰的奥秘。
第三,由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点,是在“追求社会进步”和“表现人的生存体验”之间偏重于前者,那些追求现代性的先驱们看重的是现代化技术,而非内在的精神,“中体西用”曾几度成为多数人所认同的选择。因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追求更集中地表现在对国家富强的渴求方面(如四个现代化),这一点与西方更看重个人自由的现代性追求有明显差异。故1980年代以前的现代文学史,无论是阶段划分、作家评价还是具体文本分析,都仅将文学看作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注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长期以来过于重视文学与政治、革命、进步等层面的关系问题,而从根本上忽略了当代读者的个体生命感受。
既然是在全球视野下考察“现代性”,就不能因为各国特点而忽略概念的一致。
(二)民族性、草原文化、蒙古族文学再思考
1.民族、民族性梳理
“民族”于19世纪从日语传入中国,与中国古代的“族、族类”等含义相同或相近。民族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指人们在历史上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的、处于不同时间阶段的各种共同体(如原始民族、古代民族、现代民族),或作为某个区域内所有民族的统称(如美洲民族、非洲民族、阿拉伯民族),或作为多民族国家内所有民族的总称(如中华民族)。狭义上流行较广的是斯大林1913年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③中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据此,世界目前约有大小民族2千多,其中中国有56个,包括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本文中所关注的民族在狭义范畴。
不过,各个民族在实际上都不可能泾渭分明。在战争与掠夺、通婚与交流、迁徙与往来等复杂的融合中,原初的各个民族之间不断同化或异化,在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以及文化、心理素质等无不发生新的组合,百代千年,盘根错节,而所谓各原初民族基本上已经不存在。所以,所有民族只能是相对而言。
民族性即各个民族,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在发展中形成并具有的属性及特质。张俊才在《正确理解和把握文学的民族性》④中所说的,对“民族性”这一概念的理解和诠释,是因时、因势、因人而异的。可见,民族性也都是相对的,各个民族性之间的差异,只能在比照中大体厘定。如:本文将考察的对象即以中国蒙古族为主体,依托草原环境生息发展过来的庞大、复杂的群体,及其生成的文化特征与精神属性。中国北方的各个民族,在千百年来盘根错节般的纷争与融合中,无论在血缘关系及其遗传基因还是在文化习俗与心理上均同样呈现为既有稳固独立性亦相互交织渗透的事实,这是在考察民族性时所不能忽略的。
2.草原文化及其特征
中华文明有三大主源,即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草原文化。潘照东先生认为,草原文化以草原民族的游牧文化为主体,在北方草原,即以主要发源于蒙古高原西部(如:匈奴、突厥、回纥、维吾尔等)的族系,发源于蒙古高原东部的东胡、乌桓、鲜卑、契丹、蒙古族系,及主要发源于大兴安岭以东的肃慎、女真、满族族系等三大族系的草原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生产、生活、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的总体,它包括:北方草原的原生文化,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西域民族、藏族及南亚、中亚、西亚、欧洲等民族交往中,特别是北方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建立中央王朝后创造的次生文化,还包括自古以来生活在北方草原却并非游牧民族的人们创造的共生文化。
该作者认为,草原文化的特质包括: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的统一,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统一。当然,这样从整体上作鸟瞰式的概括很有必要,也为下一步细致研究既确定了基调,留出了空间。如:草原文化在保持传统中,也“积极吸纳现代文化的一切有益因素,从内涵到外在形式不断增强其现代性,与时代同步发展”,那么,有没有例外?现代文化在生活方式与精神心理上的作用有没有差异?传统文化中有没有现代元素?等等,都可以继续深入。还有,吴团英在《略论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⑦中认为,草原文化的基本特质是否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崇尚自然。二是践行自由。三是英雄崇拜。这些同样都值得参考、借鉴。蒙古族文化在草原文化中是核心,也是最为突出、壮观的,在其文化深处,永远有不断深入挖掘的可能性。
3.蒙古族文学新界定
蒙古族文学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之一。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划分标准一般来说,作者的民族成分、民族题材和民族语言是三个主要标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学者特别严格,把民族语言这一标准也纳入进来,如刘宾在其《对界定“民族文学”范围问题之管见》一文中指出,民族文学应具备以下条件:“作家是少数民族,作品所反映的内容是少数民族的生活,作品的语言是民族语言。一些学者的划分标准略有放松,对民族语言这一标准不再严格要求,如《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三卷本主编毛星提出:“所谓‘民族文学’,我们的理解是:第一,作者是这个民族的;第二,作品具有这个民族的民族特点,或反映的是这个民族的生活。”有些学者的划分标准比较宽泛,只强调创作者的民族归属这点,认为凡是属于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文学都应该属于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如何其芳在 《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判断作品所属民族一般只能以作者的民族成分为依据。”⑧
我以为,在划分的标准比较宽泛的基础上还可以再宽泛些,即在一定范围内,凡是民族生活题材的作品均应被纳入其所在的民族文学范畴。“一定范围”可以包括区域内长期生活的非本民族居民,或包括国内公民等。前者是因为其生活习惯、心理、语言都会“融合”,甚至民族中途也改变;后者理由是研究范畴所需,如:蒙古国作家作品属于蒙古族文学,却不属于中华民族,斯诺及《西行漫记》、好莱坞电影《末代皇帝》也同样。而中国作家,无论他是什么民族,既然生活或倾心于观照某民族,并创作出了相关文本,产生了社会作用,就应该考虑纳入某民族文学,其中的民族元素、文化心理等也肯定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对考察这个民族肯定会有益处。而且,自我表达是主要的依据,但也不能忽略旁观者清。所以,民族文化身份应该强调的是文化身份,而不是“血缘身份”。
二 蒙古族文学中草原文化的现代性
在本部分,蒙古族文学中草原文化的现代性就是基于笔者在前面对相关概念的界定之上思考的,这决定了本文中的观点与其他专家学者的见解势必有较大的区别。欢迎批评。
(一)文学中潜在的现代性体现。
普通高中财务会计核算工作的质量会影响到高中资金活动的使用,所以需要提升会计核算的质量和效率。就目前的具体分析来看,如何在会计实务中,会计核算的项目确定清楚,具体核算的内容明确,有效的避免核算的纰漏,在会计核算中明确内容十分的必要。基于此,从高中具体工作实践入手对会计核算的具体内容做清楚的分析,然后基于内容讨论研究会计核算质量提升的策略和方法,这于实践工作而言价值十分突出。
在考察与研究中我发现,我们今天认为的现代性元素潜藏在少数民族文化中。
据《让草原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⑨报道,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敖敦其木格说:“草原文化博大精深、底蕴深厚,也包含很多现代元素,是一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事实的确如此,而且现代性元素不仅现代有,古代也有。
我想,从原因上来看,汉民族传统文化中,却很少有现代性元素,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结果。当然,在少数民族文化中,现代性与原始性也混杂在一起,对此需要我们认真清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认真地有所发现,整理出来。还需要把他提升到自觉的高度。通过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现代性元素来重新确认中国文化的新格局,个中意义重大。所以,少数民族面对自身文化应该挺起胸脯,因为这种贡献是独特的也是无可替代的,汉民族也应为之肃然起敬。
那么,在蒙古族文学中,潜在现代性都有哪些突出的表现与特点呢?在此不妨主要以蒙古族文学历史中的诗歌等文本为例,作基础性分析。
1.蒙古族古代文学中的现代性元素
笔者在阅读蒙古族古代文学中感受到了这种可贵品质。如诗歌:13世纪的《成吉思汗训辞》⑩中有这样的诗句,“视战斗之日为新婚之夜∕把枪刺当作美女的亲吻”,“狮子般的诺颜(大臣)们∕则由老虎般的群臣相伴∕……豹子似的诺颜们∕则由狐狸似的群臣相伴——因而民众必遭苦难”。这些诗句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思想与汉族文化有明显的区别。他对于人的生命价值,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有现代性的感悟。
14世纪诗人却吉奥塞尔的 《万物难以永存》:“苍生性命短促∕如长空之闪电滚雷∕倏忽一泻而下的江水”;19世纪诗人桑德格的 《雪的自白》:“暖风吹起∕大地露出黑斑浑身支离破碎∕才生出几多忧愁滋味……∕终于化净流干∕不留丝毫形骸”等诗歌也包含了现代性元素。而依希桑布的《黄羊孤羔之言》中,与母亲的告别大有现代人的孤独感。沙格德尔的诗多批判现实,揭露统治者,但如《“赞颂”王爷》:“为了让奴隶们走进天堂,∕您把他们吊在背架上;∕为了让奴隶们的头顶发亮,∕……您把他们的头发全部拔光”;还有20世纪初诗人达那楚克道尔吉的《爱情》里:“所谓爱情,可也脆弱,磕磕碰碰,裂成碎片。”……
从以上诗人的一些诗中可见,在表达对生命与自然的关系时,明显留有现代气息。我以为,这种现代性元素是与生俱来的,而且没有像汉族文化及文学中那样,从根本上受到了儒家等思想的传统影响,相反,这些诗中所表现出的,确实是蒙古族同胞生命深处本色感悟,这些元素现在看来都是十分可贵的。
2.古代蒙古族民歌中也有潜在的现代性元素
民歌《黑骏马》(蒙语“钢嘎·哈拉”)是流传于锡林郭勒盟北部及外蒙古苏赫巴托一带的一首长调,全诗写在“我”骑着黑骏马去寻找嫁到了远方的心爱的妹妹,到过哈莱井、“艾勒”帐篷都不见她的踪影;向牧羊人打听,说她运羊粪去了;向牧牛的询问说她拾牛粪去了。我举目眺望那茫茫的四野,突然发现山梁上有她的影子,就骑马飞奔上山梁,结果那熟识的身影却不是她!
人们大多以为,此诗以黑骏马为名,讲述的却是一个悲怆的爱情故事。其实,透过爱情的表层,我们还能发现更深层的价值,那就是人类命运的独特关系,即使追求的理想似乎就在眼前,也常常感到触手可及,但它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即使你真的获得了,他已经彻底改变性质。这应该是现代人才感受到的一种困惑与无奈,说到底这是由于人本身的原因造成的。一首古歌能够感悟到这样的层次是难能可贵的。当然,民歌中的主体一般都是咏唱爱情,蒙古族的民歌也不例外,但就这首诗所感悟到的现代性元素而言,在汉族文化中近乎为零。
(二)中国当代更多的诗人、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出现代性理念
在许多现代蒙古族诗人、作家笔下,大面积呈现出现代性理念与手法。如:牛汉《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邓一光《我是父亲》、《我是太阳》、《想念草原》,郭雪波的《大漠魂》、《大漠狼孩》、《银狐》、《苍鹰》等生态小说,宁才的《天上草原》、《季风中的马》,塞夫、麦丽斯的《悲情布鲁克》等电影,鲍尔吉·原野的散文,席慕容、查干、娜仁琪琪格、白涛的诗歌等,很多很多。而且,“草原风景”已然成为了深入他们内心与叙事本质的一种民族精神,就此毋庸赘言。
在非蒙古族作家队伍里,以蒙古族生活为重要或主要创作资源的作家,伴随再次以其新近性、开放性、动态性和时效性蓬勃起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或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成为杰出作家和文学复兴的中坚;或自90年代后登上文坛,产生反响。 如张承志的《黑骏马》、《春天》,老鬼的《血色黄昏》、邓九刚《走西口》、冯苓植的《忽必烈大帝和察苾皇后》等小说,冯小宁的《嘎达梅林》、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等电影,敕勒川等许多诗人诗作。
如对张承志、老鬼等,学术界主要将其归入“知青”作家,其中对张承志的研究最多,也主要考察其理想主义、昂扬的激情、穆斯林理念等艺术品格,认为他在寻觅一代知青失落的青春记,表达汉人与牧民的深厚友情,甚至认为他是用现代手法表现的却是传统文化精神等等。对老鬼,都将其作品归入新“伤痕文学”。对郭雪波的评论集中在从生态关系、环境保护方面。事实上,他们写蒙古族生活的作品,对深入研究草原与蒙古族文化有重要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有作者从旁观者的角度对所书写生活的独特体验与感悟,仅仅将其纳入比较研究视野是不够的。
张承志是回族作家,著有长篇小说 《金牧场》,中篇小说《黑骏马》、《北方的河》等。他1983获北京文学奖的《春天》,通过展现东乌珠穆沁青年马倌乔玛在暴风雪之夜为保护马群而殉职的故事,以极其抒情的笔调,刻画了乔玛勇于献身的形象,并通过象征化的手法诗意地揭示了春天、爱情、青春和生命的意义:它既美丽迷人,而又意味着庄严的责任和严酷的考验,同时也揭示了生命的价值。作品揭示出生命的奔腾与跃动体现在人、马、自然等方方面面,生命各有自身的本性,而各种奔放的生命,在错落纠缠中的对峙、较量博弈中,无不闪现灿烂光辉,正是这些光辉构成了绚丽多姿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本篇不仅是一曲具有现代性品格的生命赞歌。作品在多种层面上运用象征手法,春天、暴风雪、白色的儿马、驼背老人的话等都具有深刻、丰富的蕴含。
三 不算结论
总之,本文之所以考察草原文化、蒙古族文学及其与现代性的关系等问题,首要目的是确认蒙古族文化的丰富多彩,无论在它自身的发展积淀中,还是在与其它文化的交汇影响中,既有草原游牧文化的传统特点,也有在文化整合中的变化规律。特别是,即便在传统蒙古文化中,也有一些现代性元素,这是人类共同性的应有一隅。有此,才意味着该文化有常态性;知此,才能把握某种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才能把握民族文化的独特符号并找到民族文化进入世界的通道。
同时,也是出于一种使命感,即思考中国既定文化的现代转型。因为现代性是新科技、新视野下人类智慧,对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进行更深刻的观照;是基于传统人文主义,纠正包括人文主义思潮在内的片面性,及其在人类发展中对人类造成的危害,例如环保。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性能够使人们正视自身,避免在对人类及其命运相关问题的处理方面自以为是。也特别有利于对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以及汉民族文化深处的根性,进行真诚、深刻的反思。
这不仅有助于对相关作家的深入考察,更有助于作家在感悟和体验蒙古族生活与文化中增加一些新向度,为蒙古族文学研究特别是文化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启示。这至少能引发人们对相关问题进行再思考,进一步扩大自治区文学在国内外的影响。当然,最终要使中华民族真正站在人类的前沿,还有较长的路。
注释:
①费正清、费维恺编,刘敬坤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
②《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后面两篇分别载于《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与《学术月刊》1998年第5期。
③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1页。
④⑥《光明日报》,2004年1月21日。
⑤参见《内蒙古草原文化的“根”到底在哪里》,《内蒙古晨报》,2006年1月23日。
⑦《鄂尔多斯文化》,2006年第2期。
⑧杨春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辨析》,《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1期。
⑨刘昕、李国萍,《北方新报》,2011年7月11日。
⑩那顺德力格尔主编,《历代蒙古族文学作品选I》,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本节中的作家作品均出自此书。
Prairie Culture and Modernity——A Case Study of Mongolian Literature in China
ZHANG Wu-wei
(College of Arts of Chifeng Unviersity,Chifeng 024000,Inner Mongolia)
In the paper,centering up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golian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modernity,the author expounds upon the fact that there was the potentiality of some modern elements in the Mongolian literature in the Medieval ancient and medieval eras and now there is an emergence of more conceptions of modernity-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and the author also reveals the uniqueness of the Mongolian culture,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 one,and uncovers its unique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 nation by pondering freshly over the definitions of the following conceptions like“modernity”,“literary modernity”,“nationality”,“prairie culture”and“Mongolian literature”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for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Mongolian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literature and hence offering some reference for clarifying the confusions in the further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Mongolia literature;prairie culture;modernity;nationality
I29;G127
A
2095-3771(2014)01-0023-07
2013-10-15
张无为(1960—),男,汉族,河北省承德市人,赤峰学院文学院教授,赤峰学院诗词学会会长,赤峰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