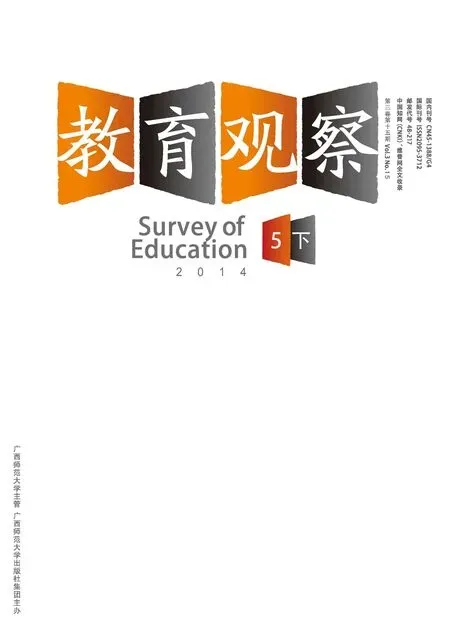汉英“主语”使用差异背后映射的民族思维方式
瞿笑丹
(西南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四川成都,610074)
一、汉语的“主语”特征
汉语作为汉藏语系(Sino-Tibetan family)中极具代表性的语言,有着鲜明的特征。总体来讲,汉语是分析型的语言,其语法呈隐含性,句子重意合。具体体现在汉语无曲折变化,词素粘着构成词组,句子多为单句、短句,句间无需严格逻辑连词进行粘连,且句子以“主题”为中心,而非“主语”。
(一)“无主句”的广泛使用
“无主句”是指句子的直接成分中无主语的句子。通俗来说,无主句并非是没有逻辑意义上的主语,只是一种无需主语或主语省略的语言现象。而这一语言现象在汉语中尤为突出。
例1: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司马迁《太史公自序》)
例2:“怎么啦?”老程问:“辞了工?”
“没有,”祥子依然坐在铺盖上,“出了乱子!曹先生一家全跑了,我也不敢独自看家!”(老舍《骆驼祥子》)
例3:希望今后能够加强合作。
从以上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汉语省略主语的现象从古到今都是存在的,并且在书面文本和口语中皆有体现。在汉语的一定语境中,在不至于误解的情况下,说话时往往会省略一些不言自明的成分。
(二)汉语中主语多为“人”
汉语句子习惯以“人”作为主语。在许多中学老师的语法课上,“主语”多被定义为句子中动作的发出者和执行者。很多时候看来,这是符合我们的逻辑与思维方式的,学生往往也容易接受这样的定义。在中文句子中,我们很少去调整语序,将一个“主动句”变为“被动句”,多数时候中文的被动句总是显得十分别扭和拗口。
二、英文中的“主语”特征
英文属于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family),总体来讲,是一门分析加综合型的语言,其语法特征呈外显性,句法重形合,具体表现在曲折变化,句子多为复杂句、从句,句间强调严密的逻辑关联、意义完整。英语的句子是构建在形式(或主谓)主轴上的,强调句子结构的严密和完整。
(一)“主语”地位突出
英语句子构建在主谓主轴上,主语在句子中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主语的变化决定了句子其他成分的变化,可以说英语是一门“主语突出”的语言。大多数英语句子的主语都是不可缺失的,我们在分析一个长难句的时候,往往首先要做的是找到该句子的主语。由此可见,“主语”的地位在英语中是极为显著的。
例 4:My thanks goes to everyone.(感谢各位。)
(二)“无灵主语”在英语中的广泛使用
所谓“无灵主语”,意指英语句子中常常会使用无生命的物或抽象的概念作为主语,“灵”即指“生命”。这种现象在汉语中是很少见的。我们在翻译时不难发现,一个以“人”作主语的汉语句子译作英语后,句子的主语往往发生了变化,原句中的宾语甚至状语都可能替代“人”而成为译文中的主语。教师往往会反映,一些中学生写的英语作文中,通篇都是“I”或者“we”在统领句子。这从根本上来说,是学生用汉语的思维写英语作文的结果。
例 5:I don’t agree with this.(我不赞同这一点。)
改写:This idea can’t acquire my acceptance.(这一点无法得到我的认同。)
例6:we achieved a great success in 2009.(我们在2009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改写(1):A great success was achieved by us in 2009.(一项辉煌的成就在2009年被我们取得。)
改写(2):2009 saw our great success.(2009 年见证了我们辉煌的成就。)
三、“主语”差异背后
英汉双语仅从“主语”这个微观的语言现象来看,大体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显著差异:1.汉语突出主题,不突出主语,主语经常省略;英语突出主语,主语地位显著,不可随意减省。2.汉语惯用“人”做主语,英语惯用“无灵主语”。导致这差异,不是单纯的语法习惯,而应当与之相应的社会文化、民族思维有着紧密联系。
(一)汉语成长的社会土壤与民族的“主体思维”
从历史和社会的因素来看,汉语民族,其祖先世世代代是靠土地和农耕来维生的。土地和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若不是天灾人祸、兵荒马乱,靠土地吃饭的人是不会轻易迁移的。他们祖祖辈辈定居在一个靠土地划定的区域里,人与人之间以土地为纽带联系起来,形成了“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谈到,中国社会的根基是一个“乡土社会”。由于人口较少地流动和迁移,人们长期居住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成长起来的人,对周围的人和事物都十分熟悉。这样一来,中国社会便形成了“熟人的社会”。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对人、对事的观念都是通过口口相传形成的,都是通过熟悉的经验获得的。他们往往不需要一种适用范围广、普遍的抽象的原则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同样地,他们交际所用的语言也只需满足熟人之间的交际即可。熟人之间的交际,面对面的交际,很多时候一个手势、一个表情便能达到传情达意的效果,自然不必每个字都说出来。因此,在这样的社会里,语言扮演的角色并不那么突出。很多东西不用说出来,大家心里都明明白白,只要语句的主题明确了,“主语”要不要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由于自然经济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数千年,直到近代,汉语也就在这样的社会中发展。依附在土地上的人靠天吃饭,总是祈求风调雨顺。他们面对自然时多了一份敬畏,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又由于受到土地的限制,这样的人世代定局,不愿迁徙,不愿走出自己所处的相对闭塞的区域,这也导致新的思维、新的观念难以产生。这样的人既不会想着去征服自然,也不会想求新求变,他们能做的便是“关注自己”。中国古典哲学最根本的观念之一便是“天人合一”。《易经》讲“三才之道”,“天、地、人”三者并立,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之道在于“成万物”。由此“人”被摆在了中心的地位;中国人历来讲究“内向自求”“修身养性”,追求“修齐治平”的境界。中国人的民族思维讲求“推己及人”,也由此构建出以“己”为中心,像水波一样层层推出的社会关系。具有这种“主体思维”特性的民族思维也由民族语言体现出来。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汉语多以“人”做主语的原因了。
(二)英语成长的社会土壤和民族思维的体现
英语属于印欧语系中日耳曼语族下的西日耳曼语支,由古代从欧洲大陆移民大不列颠岛的盎格鲁、撒克逊和朱特部落的日耳曼人所说的语言演变而来。与汉语生存的农耕社会不同,英语产生于很多支部落和民族的长期迁徙及变化之中。这些部落和民族,多数逐水草而居,飘忽不定,长期处于迁移和流动的状态。因此人们会不断地遇到陌生人、陌生的居住环境,这样一来,英语便在这种“陌生人的社会”中逐渐发展而来。陌生人之间若想有效交流,必然需要一套适用性广、具有普遍性的语言规则。并且,由于是同陌生人交流,很多信息是不可省略的,语言定要做到意思表达完整,无论是意念上还是形式上,这种完整和严密是必要的。否则彼此不熟悉、不了解的陌生人将会难以有效沟通。王力先生曾这样形象地论述过英语主语的地位:“就句子结构而言,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法治的不管主语用得着用不着,重要的是呆板地求句子形式一律;人治的用得着就用,用不着就不用,只要能使对话人听懂说话人的意思,就算了。”可见,陌生人社会的交际传统,让英语保留了主语突出的地位。
正是由于长期的迁移,英语民族总体而言没有可供其紧紧依附的土地,而迁徙本身,也需要克服自然的艰难险阻。所以,我们可以推测,英语民族同自然的关系便不那么和谐,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人们只有不断克服自然界的艰险,才能生存,由此,“征服自然”的观念便深深植根于这个民族。天、地、人不是一体的,主体和客体有了十分明确的界限。同时,随着西方文化发源地希腊半岛及其附近沿海地区的手工业、商业、航海业的发展,人们对天文、气象、几何、物理等自然科学的兴趣逐渐浓厚起来,整个西方都逐渐形成了注重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传统。受到这种传统影响的英语民族,便日渐形成了重实验、重逻辑,追求客观求证而非主观臆测的“客体思维”。因此,当人们在用言语表达的时候,这样的思维同样起到了作用。我们可以想象,一篇通篇都以“人”做主语的论述,在这个民族的人看来,岂不是毫无依据的主观判断吗?因此,或许“无灵主语”正是为了避免“主观不可靠印象”而频繁使用的。
交际者只有具备了交际语言所承载的思维方式,才能有效地理解和传达交际内容。通过不断探究语言背后折射的社会文化,对从事语言转换工作、跨文化沟通将有所助益。
[1]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陈宏薇.汉英翻译基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3]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5]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