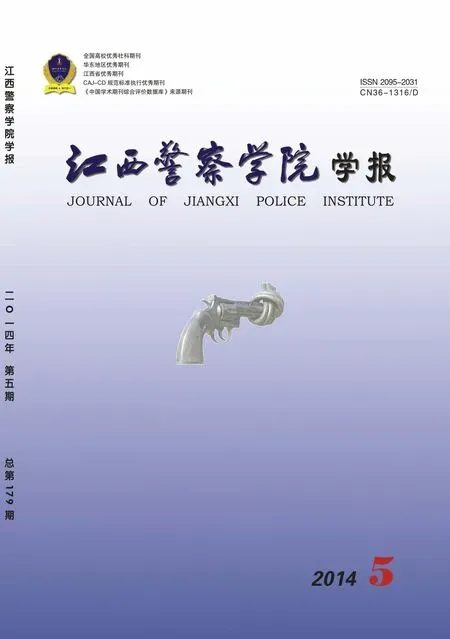被害人特殊体质因素的刑法规制
——以城管故意伤害致死案判决为例
黄 茹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
城管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市民稳定生活的城市管理者,然而近几年来,媒体报道的各种有关城管执法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伴随着一起又一起冲突乃至伤亡的案件, 公众对城管的执法活动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尤其对殴打过程中致人死亡案件的处理结果,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争议。 在城管殴打行为致被害人死亡的情形中, 被害人自身具有特殊体质这一因素成为了城管规避罪责的救命草, 只要尸检报告中将死因指向被害人自身存在疾病的情况,城管队员的刑事责任就会得到相应的减轻, 更有甚者被免予刑事处罚。 社会群众对这一系列的处理结果存在着广泛的争议,其合理性受到各方的质疑。
一、城管故意伤害致死案件的判例现状
根据《南方周末》对近几年来媒体报道的关于城管队员在执法过程中致人死亡案件的判决数据统计,有5 起被追究刑事责任,5 起未被追究刑事责任,还有个别情况刑罚尚未明确。[1]在没有追究城管刑事责任的5 起案件情形中, 尸检报告大部分将死因归咎于被害人自身具有疾病,存在特殊体质的情形。 例如贵州安顺小贩邓启国于2011 年7 月26 日与西城区城管队员冲突后倒地死亡,负责人王胜被刑拘。 由贵州省公安厅、贵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中心等单位的专家组成的法医专家组排除了邓启国因 “机械性损伤致死”的可能性,[2]即死亡原因并非暴力作用所致,而是被害人自身体质的原因导致死亡。 王胜最终因为这个鉴定报告而免予刑事处罚。同样,49 岁的四川宜宾小贩梁云贵为了护一袋花生与城管队员发生争执,城管将其扭送至派出所训诫后死亡。 警方宣称当时并无民警在场, 城管在询问室对梁云贵进行教育,梁云贵情绪激动拍桌后倒地身亡。 官方随后正式公布的死亡原因也是梁云贵因为 “情绪异常激动从而导致心脏病突发而亡”,最终并未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只做了相应的行政补偿而不是行政赔偿。[3]
在5 起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中, 只要存在被害人特殊体质的情形, 城管承担的刑事责任往往较轻,比较典型的案件如湖北的天门事件:41 岁的魏文华用手机拍摄了天门城管与村民发生纠纷的场面,后被城管队员发现殴打致死。 而在官方出具的尸检报告中却指出魏文华是 “因为外伤诱发冠心病急性发作而死亡”。 在侦查终结报告中,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罪给其中四名城管队员定罪, 并称定罪的主要依据就是尸检报告, 最后四人被追究了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 分别获得了3 至6 年的有期徒刑,[4]并没有对致死结果负责。 在本案中,城管殴打行为本身便具有故意伤害的心态, 最终也因为伤害行为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完全应该适用《刑法》第234 条故意伤害罪第2 款关于致人死亡情形的规定, 但根据本案的量刑可以看出, 法院并未严格适用该款的规定, 其原因正是考虑了被害人是由于冠心病的发作而导致死亡这一特殊体质因素, 城管的伤害行为只是死亡的诱因, 从而对城管的行为进行了责任和量刑上的减轻。
考察多个关于城管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发现多以故意伤害罪认定, 而且只要查明被害人自身体质“有病”,即使故意伤害行为最终致使被害人死亡,在现有的案例中均未对死亡结果重判。 在城管执法人员外力伤害的前提下,被害人是否“有病”成为量刑轻重的关键, 然而这种做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外界的争议, 从而引发对被害人特殊体质这一介入因素的刑法学思考。
二、 故意伤害罪中被害人特殊体质介入的刑法分析
(一)被害人特殊体质介入的因果关系认定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构成要件的必备要素之一, 即行为与构成要件的结果之间必须具有因果关系。 只有在能够肯定两者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场合,才能说行为引起了构成要件的结果(实质地来说,使法益受到了侵害或者危险化)。[5]缺乏因果关系就缺乏构成要件的符合性、违法性,当然也不能构成犯罪。因此在被害人特殊体质因素介入的案件中, 因果关系的认定是确定刑事责任前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6]刑法中对于因果关系的判定, 理论界存在多种不同的学说,其中主要有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等理论。 条件说认为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着前因后果的关系,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7]相关因果关系说主要是指在通常情况下, 根据一般人普通的社会生活经验, 某种行为产生了某种被视为是相当的结果, 就可以认定该行为与该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8]客观归责理论是指在结果与行为存在条件关系的前提下,行为制造了法所不允许的危险,而且该行为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并实现了相应的结果时,才能将该结果归属于行为人, 因此客观归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行为人制造了法所不允许的危险;二是行为人实施了该危险; 三是该结果未超出构成要件所保护的范围。[9]166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现有的判例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大都坚持条件说的立场, 肯定了行为人的危害行为与具有特殊体质的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着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即使最终没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的案件,也没有否定因果关系的存在。 主要原因在于因果关系是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较强客观性的概念,因此有学者指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只是犯罪行为客观方面的因素,仅是刑事责任的客观归责基础,如果因果关系不存在就不能让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而若客观上虽然存在因果关系,但也不一定让行为人对结果承担刑事责任, 还要看行为人是否具有主观上的过错。 ”[10]张明楷教授也主张采取条件说来认定因果关系, 但采取条件说的同时主张禁止溯及理论,以防止因果关系认定范围的恣意扩大。他还进一步指出:条件关系是一种客观上的联系,行为人是否意识到会发生危害的结果, 以及事态的发展过程是否与其料想的过程相吻合都不影响条件关系的存在与否,同样,行为人是否认识到特定条件的存在,也并不影响对因果关系的认定。[9]176
在城管故意伤害小贩的过程中, 对小贩自身特殊体质的认识与否, 并不否定其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同样的结论在日本的判决书中也得到了证实, 日本最高法院1971 年6 月17 日的判决书中写道:作为致死原因的暴行,并不要求是死亡的唯一原因或直接原因, 即便因为被害人碰巧具有高度的病变, 并且该病变与行为人的行为共同作用导致了被害人死亡的场合, 也并不妨碍暴力行为成立致人死亡的犯罪。[11]而在城管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多起处理结果中,即使承认了存在因果关系,也并未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追究刑事责任, 更有甚者将被害人存在特殊体质的情形作为一个介入因素从而中断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笔者认为,在公共场所领域, 存在年老体弱的人是经常存在的事实,符合一般人的认识判断,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事情。 基于经验法则,在殴打一个陌生人时,由于对其情况不了解, 在以故意的心理态度伤害他人时理应具有注意义务以及对危害结果的风险防范义务。 即使被害人不存在特殊体质, 由于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同,对于打击的承受能力也不同,城管本身就应该预见具有危害结果发生的不确定因素, 因此在故意伤害案中,被害人存在特殊体质并不异常,不应成为中断因果关系的因素。 根据条件说,城管故意伤害致特殊体质者死亡,伤害行为本身是实行行为,与被害人疾病发作最终致死的结果存在着紧密的引起与被引起的逻辑关系,因而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二)死亡结果的预见可能性对刑事归责的影响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规定是故意伤害罪的结果加重情节,属于结果加重犯。 所谓的结果加重犯则是指在法律所规定的基本犯罪行为的基础上发生了更为严重的结果而加重行为人的法定刑的情形, 并且基本的犯罪行为与所发生的加重结果之间必须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9]156城管伤害小贩致死的行为中,是否应该适用故意伤害罪结果加重犯的规定, 还依附于对结果加重犯本质的探讨, 即除了肯定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的因果关系外, 还要考虑结果加重犯的适用是否要求行为人对加重结果的预见可能性。
有学者认为, 结果加重犯是一种故意的犯罪行为,并且处在特殊的更高层次的刑罚幅度内,这种犯罪的实施产生了更为严重的结果, 而且造成严重结果的主观心理至少是过失。[12]笔者认为,若以结果加重犯需要“过失”为成立条件来探讨,城管伤害致死的行为主观上不可能没有过失。 刑法关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法定刑, 本来就是为那些在一般情况下伤害行为引起他人死亡的情形而设立的。 城管人员基于伤害的故意实施基本犯罪时, 其主观上是希望并积极追求的心理态度,即使没有积极追求,也存在放任的态度,由于行为本身就具有伤害的故意,对加重结果不可能不能预见, 只能说是应当预见却没有预见。 被害人存在特殊体质,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刑法不可能期待每一个被害人都是身体健壮无任何疾病缺陷的人。 在故意伤害他人时,被害人自身存在疾病的因素理应当在行为人注意义务的范围之内,而不应当作为特殊的介入因素,即使被害人的特殊体质在客观上增加了死亡结果发生的盖然性,也不能否定行为人应具备的最基本的谨慎注意义务。
立法者之所以将某些犯罪进行行为类型化的规定而设置特殊的加重刑罚幅度, 是因为这些犯罪行为本身就存在能够引起更为严重的结果发生的高度盖然性。[13]148由于故意伤害罪是以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为定罪标准, 行为本身就具有造成严重结果的潜在危险, 此时行为人就应该对加重结果承担比普通过失更大的注意义务, 而且故意伤害罪结果加重犯中的过失不同于普通的过失犯罪, 它是基于故意伤害罪这一基本的犯罪而引发了伤害故意, 继而过失的造成了加重结果, 并不是单纯的只具有过失的心理状态,因而具有更大的可责难性。 笔者认为,如果结果加重犯的认定需要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失,那么被害人特殊体质这一因素应该纳入行为人注意义务的范围之内,是可以预见并且应当预见的。 城管在殴打他人时,应该履行注意义务,该注意义务属于结果预见义务, 应该预见却没有预见, 主观上存在过失, 加上其殴打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应当以故意伤害致死罪的法定刑进行定罪处罚, 并且被害人特殊体质这一因素没有理由作为减轻处罚的事由。
关于行为人是否对加重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的探讨,判例和学界有着不同的立场,在日本的众多判例中均不要求行为人的主观因素, 如日本的最高裁判所在判决书中明确表明“成立伤害致死罪,只要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可, 并不以对致死这一结果存在预见为必要。 ”[14]故意伤害行为本身就具有致人死亡的高度盖然性, 城管故意殴打他人的行为, 其必然后果是对他人造成轻伤以上的伤害,至于是轻伤,重伤还是死亡的结果,本身就内在的包含偶然的因素, 而被害人特殊体质这一因素正是这偶然因素的一种。 如果城管不对被害人进行伤害行为,就不会诱发被害人心脏病、冠心病等疾病的发生,最终也不可能产生死亡的结果。 基于这样的观点, 即使不考虑行为人是否对加重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也应该对致死的结果负责,理应对城管的行为以故意伤害致死罪定罪量刑。
三、被害人特殊体质因素的限缩性适用
在实践中殴打特殊体质者致人死亡具有多种情形,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况进行区别处理:
(一)日常生活中的交往行为,比如开玩笑似的互相推搡,或者表示友好的两者之间的相互击掌、互碰等适度行为,在遇到类似于“蛋壳脑袋”之类的特殊体质而致人死亡的情况下, 笔者认为行为人的先前行为属于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往方式, 在行为人不知道被害人有特殊体质的情况下, 按照一般人的经验根本无法预见这些极个别的罕见体质, 即使对于常见的疾病,行为人主观上也没有任何恶意,无法进行刑法意义上的规制。 另外在被害人对自身体质较为清楚的情况下, 应该尽更多的注意义务以减少损害后果的发生,对于行为人而言,在普通的交往过程中如果苛刻的要求其在履行最基本的谨慎注意义务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的加重其注意的义务,那么将有悖于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比例原则。 由于行为人的正常交往行为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并没有为被害人创设一般人所不能承受的危险,因而对死亡结果没有过失,主观上不存在过错,完全可以定性为意外事件。
(二)行为人虽然有击打被害人的行为,但是若主观上仅仅是为了某事教训一下被害人, 或者与被害人发生争执, 发泄或表达愤怒不满的情绪而相互扭打致被害人轻微伤的情况下, 被害人由于自身疾病的因素,比如血友病、心脏病等导致死亡的结果,笔者认为,行为人虽然主观上有一定的伤害故意,但这种故意还未达到刑法所评价和规制的程度, 行为充其量只会使一般健康人具有暂时性的疼痛, 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非难性, 所造成的伤害也仅限于轻微伤,因此不可能评价为故意伤害罪,行为人仅需对最终的结果负责。 而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完全超出其实施的行为所能涉及的范围, 即该结果是行为人实施行为的超出结果, 并不是在击打行为的基础上直接发生的,而是远远超出了击打行为的射程范围。 但是这并不代表行为人对死亡结果不负责任, 因为先前的争执击打行为虽然作用力没有达到故意伤害的程度, 但是本身给被害人创设了一般人所能感受到的风险,只不过这个风险较小罢了。 这便赋予了行为人一定的注意义务, 即对自己的殴打行为可能会对被害人造成伤害的结果存在预见的可能性, 行为人由于疏忽大意没有预见从而导致结果的发生, 主观上存在过失, 因此应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追究刑事责任。
(三) 行为人本身知道被害人具有特殊体质,故意利用这个特殊体质对被害人实施加害行为导致死亡结果,那么毫无疑问应该定故意杀人罪。 但如果行为人不知道被害人具有特殊体质而进行的故意伤害行为导致被害人疾病突发而死亡的, 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本身就具有伤害的故意, 具有刑法上的可责难性。 行为人的故意伤害行为增加了被害人现存身体状态的危险性, 具有使特殊体质者死亡结果发生的现实可能性, 其对加重结果的心理态度离不开对基本犯罪行为所持的故意的心理, 以及基本犯罪行为本身具有的引起加重结果发生的危险性,[13]151对死亡的结果存在的主观态度是故意伤害心理的延续。被害人具有特殊体质这一因素是行为人在实施伤害行为时所应当承担的风险,换句话说,行为人故意伤害的行为不仅在客观上给被害人的人身造成了死亡的风险, 而且也给自己承担更重的法律责任带来了风险,是一种双重风险行为。 基于这样的观点,被害人具有特殊体质这一因素对故意伤害的行为人而言并不能作为责任阻却或者违法阻却事由, 在故意伤害罪中,应该对这一因素进行限缩适用,行为人理应对死亡的结果承担加重的刑事责任, 并不因此而减轻行为人的罪责。
四、结语
被害人患有常见疾病的体质已经不再属于 “特殊体质”,不能再对其进行“特殊化”了。 在基于伤害故意的前提下,本身就具有主观恶性,对伤害结果是在其预料范围之内的, 因而被害人的特殊体质作为一个偶然因素并不中断其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可以预见并且应当预见,应该纳入故意伤害罪注意义务的范畴, 避免出现故意伤害行为引发他人死亡的结果却无需承担责任的荒谬情况。 暴城市的确需要管理,城管也不可或缺,但是现代化的城市更需要的是法治, 任何管理权力都必须受到法律制度的约束。 因此对被害人特殊体质的介入因素进行限缩适用,可以更好的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同时对相关人员的暴力行为进行刑法上的威慑, 从而维护司法的公平与正义,也更有利于保障被害人的人权。
[1] 刘俊.“因公” 犯罪的刑罚尺度——城管致人死亡案怎么判[N].南方周末,2013-10-17.
[2] 邓启国——小贩之死[EB/OL].(2011-07-31).[2014-04-10].http://dz.xdkb.net/html/2011 -07/31/content_111766.htm
[3] 杨继斌. 四川小贩梁云贵之死[EB/OL].(2007-11-20).[2014 -04 -10].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07 -11/20/content_115773.htm.
[4] 李俊杰. 天门城管殴人致死事件追踪[EB/OL].(2008-01-11).[2014-04-10].http://www.efaw.cn/html/fzzb/20081 11/AJ7710963_2.html.
[5] [日]山口厚.刑法总论(第2 版)[M].付立庆,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8-49.
[6] 武良军. 轻伤害案件中特异体质介入的刑法分析——以中日立法·判例·学说比较为视点[J].湖南警察学院学报,
2011,(3):72.
[7] 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75.
[8]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23.
[9] 张明楷.刑法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0] 许任刚,黄伯青.殴打特异体质者致死型案件的刑法解读[J].犯罪研究,2010,(3):69.
[11] [日]大谷实. 刑法总论(第2 版)[M].黎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07-208.
[12] [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 卷)[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18.
[13] 李文军.故意伤害致特异体质者死亡案件处断争议之辨析[J].法学,2010,(8):148.
[14] [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M].刘明祥,王昭武,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6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