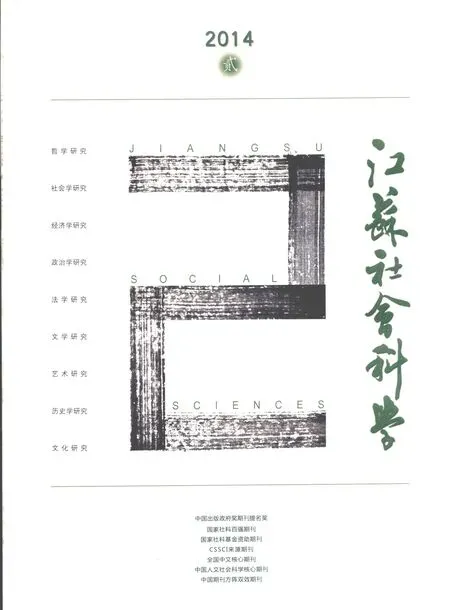中国艺术感悟方式:神遇—物化
姜耕玉
中国艺术感悟方式:神遇—物化
姜耕玉
神遇、物化,是中国古代艺术家感悟或体验的独特方式。神遇,是心与物交会中一拍即合的原初默契,体现了“物”的亲在性、纯粹性与创造主体的本真性,是艺术创生的契机,可称为艺术直觉体验的初级阶段;物化,则是进入物我同一的高级直觉阶段,是在对形下的物的超越中进入形上的精神境界的实现。“庄周梦蝶”式的体验,是实现精神超越的大境界。王国维所说“无我之境”的写作难度,正表现在诗人对物化体验深度把握之不易。物化的体验方式,是中国独有的静观境界。
艺术感悟 神遇 物化 凝神 静寂
中国艺术理论将心物之间的互动视为艺术创生的缘由。走向大自然,在自我与景物的亲近融通中,获得感悟与深层体验。艺术生命与创造之心感于物而律动,物,又是心的对应物,随时能够触发艺术家的悟性与灵感,并成为生命精神的艺术载体。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农耕社会的自然生态,荡漾着一种家园感与一触即发的诗意。“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1]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93页。,“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2]钟嵘:《诗品》,见王大鹏主编《中国历代诗话选》(一),〔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2页。,即是对景物与心意之间发生感应和交融的生动描述。陆机所说“精鹜八极,心游万仞”[3]陆机:《文赋》,见郭绍虞等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70页。,则是从更广阔的视野里获取内心体验及其独特境界。心与物之间互动的关系,是层层深入的拓进,也是从“感物”或“物感”到“超物”的体验过程。“神遇”、“物化”,是艺术体验与感悟中两个重要环节,凸显着中国艺术创造理论的亮点。
西方后现代主义提出:“后现代主义世界中将拥有一种家园感,他们把其他物种看成是具有其自身的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并能感受到他们同这些物种之间的亲情关系。”[4]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中国古代诗人、画家的山水体验理论,为现代艺术体验提供了重要资源,他们创造的一大批古代经典作品,仍显现出不朽的魅力。
神遇:心物交会中一拍即合的原初默契
庄子“庖丁解牛”中最早出现“神遇”这个概念,“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1]庄子:《养生主》,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6页。。是说技艺纯熟的境界,也是顺应自然之理的一种“道”的境界,其强调用心神领会而不用眼睛去看,得力于心物交会之天成。应该说,后代诗人、艺术家所说的“神遇”,无疑带有庄子“顺应自然”、“万物与我为一”的哲学底蕴。
“感物”或“物感”,是最初的体验与感悟;“神遇”,是这种心物感应的过程中交会契合的特有现象。苏轼曾有“神与万物交”之说:“或曰:龙眠居士作《山庄图》,使后来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见所梦,如悟前世,见山中泉石草木,不问而知其名,遇山中渔樵隐逸,不名而识其人。此岂强记不忘者乎?曰:非也。画日者常疑饼,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饮,梦中不以趾捉,天机之所合,不强而自记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2]苏轼:《书李伯时山庄图后》,《苏东坡集》前集卷二三。“后来入山者”因受龙眠居士李公麟的《山庄图》的感染,而获得奇妙的“山庄”体验。“神与万物交”,揭示了心物感应的普遍现象,提供了“神遇”的可能性。苏轼这段文字描写,是“后来入山者”与龙眠居士《山庄图》的“神遇”,其根由还在于原创者龙眠居士在山的体验中进入了“神遇”之境。“不留于一物”至关重要,否则不会发生“如见所梦,如悟前世”的令人痴迷的奇迹。苏轼把它视为“神与万物交”的重要条件,无疑切入带有想象性的艺术体验的特点。艺术感悟中的“神遇”,属于艺术理论的范畴。“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苏轼从“艺”的方面,阐释心物关系,单凭“道”而不具备艺术创造者的心灵,就不可能产生好作品。
“神遇”,得之于“感物”或“物感”,而又“不留于一物”,即不受物的滞碍,正显示和发挥艺术创造性想象的心理因素的作用。“诗人感物,联类不穷”[3]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93页。,“神与物游”[4]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93-494页。,“神遇”,作为艺术家“感物”所悟得的灵境,不能说不含有“神思”之意,即艺术的想象的因素。艺术体验既是知觉与情感的活动,又带有想象的审美心理因素,表现为探索性与选择性的特点,最终是要获得引起心灵震动的艺术发现,即神遇的境界。马斯洛在谈到“高峰体验”时认为,“这些美好的瞬间”,最容易在艺术与审美领域里发生,“伟大的灵感,来自意义重大的领悟和发现。”[5]转引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
郑板桥《题画》曰:“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6]郑板桥:《题画》,《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0页。虽然“眼中之竹”已在艺术家“聚精会神地观赏”中,但仅仅是引起艺术家的兴趣和情思,而在没有发生“神遇”之悟,还只是“眼中之竹”。只有受到深刻的感动,并触发内心深处的东西,才有发生“神遇”的瞬间的可能。所谓“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即意味着“神遇”的状态与创作冲动的来临。“胸中之竹”,可以理解为“神遇”之境。没有引起“心”的感应与震撼,而仅仅停留在对“物”的形、色、质的一般认识上,称不上直觉意义上的初级体验。初级体验也是原初的纯真的体验。“神遇”,这一心物交感的特有现象,是指艺术体验中特有的艺术心理反应。它是心与物交会中的一拍即合,是心与物之间达成的原初默契,可称为艺术直觉体验的初级阶段。可以说,惟有“神遇”,才能进入艺术创造之门。
清代画家石涛致力于“搜尽奇峰打草稿”,旨在获取“神遇”的契机。他说:“且山水之大,广土千里,结云万重,罗峰列嶂,以一管窥之,即飞仙恐不能周旋也。以一画测之,即可参天地之化育也……我有是一画,能贯山川之形神。此予五十年前未脱胎于山川也,亦非糟粕其山川而使山川自私也。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之于大涤也。”[1]石涛:《苦瓜和尚话语录》,沈子承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369页。石涛的“神遇”说,不仅道出了中国诗人、艺术家进入艺术体验与感悟的独特方式,以“山川与予神遇”而创造出作品,而且,“神遇”与石涛著名的“一画”论有机联系在一起,它不仅赋有“意义重大的领悟和发现”,同时以充盈的庄禅意蕴,显现着对大地山川的虔诚与胸襟,因而有了“代山川而言”的可能,“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如此“神遇”,即是物我同一的体验之大境界、大惊喜。“神遇”,作为艺术体验中的心物感应的现象,既触发于那些新鲜奇异的、可亲近的事物,又生成于艺术家的大心大智。石涛主张“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是认为自然山水可居、可游、可望,足以令人亲近,是艺术家的心灵寄所,艺术家应该潜入自然山水体验中,获取心物交会的契机。二是强调艺术家的自我意识,批评了“道眼未明”[2]石涛在长卷画《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卷末长题中曰:“江南江北,水陆平川,新沙古岸,是可居者。浅则赤壁苍横,湖桥断岸,深则林峦翠滴,瀑水悬争,是可游者。峰峰入云,飞岩堕日,山无凡土,石长无根,木不妄有,是可望者。今之游于笔墨者,总是名山大川,未览幽岩,独屋何居?出郭何曾百里,入室容半年,交泛滥之酒杯,货簇新之古董。道眼未明,纵横习气安可辩焉。自之曰:此某家笔墨,此某家法派,犹盲人之示盲人,丑妇之评丑妇尔,鉴赏云乎哉!”的浅薄平庸之风。没有大心慧眼与对“物”的虔诚,没有对心物感应的艺术把握,就不会有“山川与予神遇”的可能。
艺术感悟或体验,是从外物界寻回自我,是对我的内心及梦境的发现,但首先是创造主体与外物之间的交会。诗人“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3]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93-494页。,这种对自然景物“情”和“意”的投射,立普司曾作过移情解释。他说:“……在对美的对象进行审美的观照之中,我感到精力旺盛,活泼,轻松自由或自豪。但是我感到这些,并不是面对着对象或对象的对立,而是自己就在对象里面。”[4]立普司:《论移情作用,内摹仿和器官感觉》,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09页。正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中国诗人、艺术家徜徉于山水之中,是心灵的徜徉、灵魂的徜徉,是山川之灵秀、日月之精华、大自然之亘古,对心灵与灵魂的滋润和哺育。从这一角度看,艺术家主体更多地表现为受动性。“山川与予神遇”,是指自然山川对心和灵魂的亲近,对生命的亲近,诗人、艺术家只是怀着对自然山川的虔诚,把一木一石视为纯洁的“物”,由此“物”成了心灵寓所,即神遇。这种神遇即是“物感”,“物”对我的震撼,对“我”的精神的激发、对我的生命灵性的触动。
艺术家胸中须有丘壑,眼底须有性情。王夫之认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强调“阅物多,得景大,取精宏,寄意远”[5]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二。。这也是说人生阅历、记忆与经验在艺术体验中的作用。譬如郑板桥画竹。“眼中之竹”,一经“神遇”而成为“胸中之竹”,就成了“我”的生命情感与精神的载体。其竹图,或立于山崖,或立于水边,都是瘦硬秀拔,傲然挺立,突出了孤傲独立的人格境界,这显然是郑板桥人生经验的深度显现。这种指向认识层面的经验,固然提供了对体验物的凝练升华的可能,但也可能会造成对悟性与想象力的束缚。
神遇,是妙不可言的瞬间体验。每一次“神遇”,可以理解为一次感性经验的发现。这并不指一般的生活经验,而是直接出自内心和生命情感的感悟。它虽然会受到人生经历与情感记忆的影响,但没有受到理性认识的束缚。正如杜威所说,“那些具有理智结论的经验的材料是一些记号和符号,它们没有自身的内在性质”。“这一个经验是一个整体,其中带有它自身的个性化的性质以及自我满足。”[6]杜威:《艺术即经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5页。杜威把个体直觉经验与理智结论的经验的材料之间的界限,说的很清楚。那种一味渴求认识论层面上的真理,而尚未看到感性经验自身所蕴含真理的可能性,或者说割裂了经验与感觉之间的联系。中国古代艺术家深入直觉体验与感悟的“神遇”现象,以其个性化的性质及自我满足,与现代经验理论相通。
神遇,也可理解为灵感的最初闪现。艺术家对心物感应的瞬间体验,如电光石火。或触动寂寞的内在情感,或唤起某种陌生的经验,或敲开沉睡之中的生命之门,一种豁然的敞亮,“物象走进他的心灵”,以至“吸进了一种充满神物的音乐”[1]塞尚:《真实的世界》,《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3页。。所谓偶遇枯槎顽石,勺水疏林,都能以深情冷眼,求其幽意所在,即是传递出一种无声之声的冷音乐。据《宣和画谱》卷十一记载:(范宽)“卜居于终南、太华岩隈林麓之间,而览其云烟惨淡、风月阴霁难状之景,默与神遇,一寄于笔端之间。”画家深居“岩隈林麓之间”,痴迷于“云烟惨淡、风月阴霁难状之景”,“默与神遇”,默然中足见其心灵震撼的力度,直接跃入艺术灵境。神遇——物化,是中国艺术发生过程中物我交会的奇观,如果说神遇是艺术创生的契机,那么,物化则显现着东方的艺术灵境。
物化:从形下的物到形上精神体验的实现
艺术家从“神遇”中获得一种创造的冲动与契机,但在通常情况下,“神遇”这一初级的直觉体验,还有待于开拓、上升到体验的高级阶段。“物化”,即是创造主体深入体验的标识,它意味着物我交感在向更高层次突入中而达到物我同一,使艺术形象的产生有了瓜熟蒂落的可能。“物化”这一概念,最早见于《庄周梦蝶》: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2]《齐物论》,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2页。
庄周变为“栩栩然胡蝶”的优美形象,似与《逍遥游》中的“大鹏”一样,都是“自喻适志”的鸟类形象,实质上并不一样。这里“物化”,是指一种特有的物我同一的状态或境界。如此物我一体,才可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的存在。这种物我一体的物化现象,在艺术体验与审美体验中是存在的,对于艺术创造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苏东坡有“竹化”之说:“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3]苏轼:《书晁补之所藏文与可画竹三首》,《苏东坡集》前集卷十六。文与可画竹,并没有达到苏东坡所言境地,但所言“竹化”理论,可以说是庄子的“物化”思想的反映。如果说“见竹不见人”,是对文与可画竹的初步印象,那么,“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更多的则是苏东坡在审美体验中发挥,抑或是对庄周梦蝶的物化理论的饶有兴趣的理论阐释。“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从“凝神”理解“物化”,把“物化”引入了艺术的审美体验领域。“嗒然遗其身”,这般神不知、鬼不觉的“竹化”,只会发生在凝神的瞬间,即物我融一的物化现象。这是竹子由形而下的物,质变为形而上的精神形象的艺术实现。可见,“物化”的艺术体验与创造的境界,是自觉而又不自觉的浑化之境。以心物之间天衣无缝的交合而显示自生自足的怡然状态,以无言之美,催动生命精神形象的诞生。凝神、浑化,是艺术体验中物化之艺术实现的关键词。
物化,作为艺术体验与形象创造的方式,属于审美范畴。宋代邵雍说:“以我观物,物我皆遁,以物观物,便可臻大道。”[4]邵雍:《伊川击壤集序》。邵雍虽是从义理的方面立论,却也涉及物化这一美学命题。“以物观物”,并非没有“我”,而是摆脱世俗的“我”、囿于个人利害关系的“我”。正如王国维所说,“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苟一物焉,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吾人之观之也,不观其关系,而但观其物。”[5]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见《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艺术家包括观赏者,都有一个实现物我关系之超越的问题。物化体验心理,即意味着在实现“我”的转换与超越中进入心物交感的艺术过程。古代诗人、艺术家因为具有处世的淡泊心境,不与邪恶同流合污而归隐的人格精神,从而坚守真我,保持诗意存在的状态,以物我融一的全身心的投入,而创造了经典作品。
艺术创造中的物化体验心理,不是没有我,而是去弃了假我、非我,存有真我、本我。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物化即人化。法国新印象派画家塞尚说:“在我内心里,风景反射着自己,人化着自己,思维着自己。我把它客体化,固定在我的画布上。”[1]塞尚:《真实的世界》,《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3页。“物化”具有塞尚的“人化”的意思,不同的是,艺术物象的张力朝着两个维度。苏东坡所说“竹化”,“其身”化为“竹”,未留“人化”之痕,亦是“竹”化为“其身”。如此“心手两相忘”、“见竹不见人”,正显示了“物化”的特点。人们在鉴赏中自然感受到“臻于化境”,“见竹如见人”,“竹”中有“其身”,真正达到了“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艺术境地。西方艺术的“人化”,根于移情经验,把我的知觉和情感移注或外射到物的身上去。不是“物”成为“我”,而是“我”变成了“物”。正如波德莱尔说的,“把你的情感欲望和哀愁一齐假借给树”,“你觉得它表现‘超凡脱俗’一个终古不磨的希望”,那么你变成了“树”或“飞鸟”[2]见《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页。的体验。这种人化或拟人的形象,显然更带有艺术的主体性。
庄子所说“物化”与立普斯的移情经验有相通之处,如庄子有“自喻适志与”之说,即获得愉悦的美感境界,但二者还是有很大差别。立普斯倾向主观,称为“内在移置”,“这种向我们周围的现实灌注生命的一切活动之所以发生,而且能以独特的方式发生,都因为我们把亲身经历的东西,我们的力量感觉,我们的努力,起意志,主动或被动的感觉,移置到外在于我们的事物里去,移置到在这种事物身上发生的或和它一起发生的事件里去。这种向内移置的活动使事物更接近我们,更亲切,因而显得更易理解。”[3]立普司:《空间美学》,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06页。而庄子倾向客观,或者说无“主”无“客”,追求失去物我界限的无拘无束的自由。庄子那种精神愉悦,是失去自己的愉悦,失去人也失去物的乌托邦精神,是庄子的“物化”思想的灵魂。然而,庄周梦蝶式乌托邦,却是实现精神超越的大境界,庄子所说“物化”,作为艺术体验的方式而言,提供了显现内心与形上的精神层面的可能。
王国维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尔。”[4]王国维:《人间词话》,郭绍虞等主编《蕙风词话人间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1页。王国维推崇的“无我之境”,可以理解为艺术创造中的物化体验方式。“无我之境”写作的难度,正表现在诗人对物化体验的深度把握。物化与人化,都要进入心物交汇与融一的过程中而显现倾向。王昌龄在阐释“心物交会”的过程中,认为“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5]王昌龄:《诗格》,见王大鹏主编《中国历代诗话选》,〔长沙〕岳麓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艺术创造中的物化体验,显然也有一个“神会于物,因心而得”的过程。当然,王昌龄强调“以心击之”,使“心入于物”,则可从“以我观物”的“有我之境”方面去理解。
“无我之境”并非没有“我”,只是冷却了情感,淡化了“我”,“我”隐没于物中,消失于物中。石涛所说“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这种物化,可以称之为“忘我”、“物我两忘”的体验境界,所谓“忘我”、“物我两忘”,只是通过对“我”与“物”的双重超越,把创造主体提升到一个自由充实的境界。它是以“真我”、“观赏的自我”与“非自我”的物象相同一,达到由形而下的物向形而上的精神形象的艺术实现。这种物化体验的最高境界,达到主客体融一的全新的境界,即是康德所说的那种“我在世界中,世界在我中”,主客体的硬性边缘为意义所浸蚀,而逐渐双向渗透,最终成为一个意义的重赋[6]王岳川:《艺术本体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63页。。
“物”的意蕴及形上的特征,取决于物化体验的深度。诗人、艺术家的灵感与冲动,一旦受到陌生的外物的激发,有可能发生心物对应与同构的意象定型,神遇即物化。但这种偶得的成功形象,抑或有一次经验的奇迹,也离不开创造主体的充盈与天才的艺术悟性。在一般情况下,形象创造中的物化体验,是一个深入与开拓的过程,进入“物我两忘”的体验境界,即是一种审美期待,只有具备对宇宙人生感悟深刻与独特的想象力的艺术家,方能抵达艺术的彼岸。诗人、艺术家没有对宇宙人生的深刻体验,没有对形而下的物的尊重与体恤,没有对非我、假我的痛恨,就没有超越物我的理由。所谓超越社会现实的最高体验境界,是由爱、痛苦或对恶的痛恨而引起的人生境界的升华。古代不少才华卓绝的诗人、艺术家表现为超然于世的姿态,并不意味着他们脱离宇宙社会,而在于他们以“出乎其外”的观察方式,独得对宇宙人生的深刻看法。王国维说:“吾人之胸中洞然无物,而后其观物也深,而其体物也切。”[1][2]王国维《文学小言》(四),见《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洞然无物”,首先是相对于胸中有物而言,即是王国维所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出乎其外,故有高致”[2],“洞然无物”是“出乎其外”的标识,它以对胸中之物的彻底超越,从对物的远离与扬弃中去重新认识物、亲近物,故“观物也深”、“体物也切”。这一看法,十分精到深刻。宋代魏了翁所言,“以物观物,而不牵于物,吟咏情性,而不累于情”[3]魏了翁:《费元甫注陶靖节诗序》,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81页。,不光是说观物须彻底摆脱物,还提出对情的超脱,可以理解为对物化体验心理特点的描述。
邵雍强调“因闲观时,因静观物”。他在“万物静观皆自得”的境界中,获得“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之佳句。“静观”,是物化体验的第一要素。“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王国维从“静中静”与“动之静”的区别,揭示了“无我之境”中“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物化体验心理的深度。譬如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诗中空山、惊鸟,虽是表现极静(“静中静”)之物,却不是物牵制于人,而是呈现物的本性、灵性、真趣、真意,惊山鸟是春山月夜的灵物,春山空是花落夜静的深度显现。它们虽出自诗人的悟性,却不带丝毫的情感色彩,是这种空灵之物逼近人的精神境界。王维受禅宗思想影响,在诗画创作中,潜入物化体验甚深。“摩诘用渲淡,开后世法门”[4]唐岱:《绘事发微》,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404页。,“渲淡”,可以理解为王维进入物化体验的深度标识。王维在《荐福寺光师房花药诗序》中称,是把山水景物当作通向“色空有无之际”来表现。“色空有无之际”,是显现灵魂的物化体验形式,色空,反映了物我同一的强度。它见诸画面构图中水墨的“淡”与“远”。王维、董其昌的水墨山水画中的“淡”与“远”,给人以视觉心理的静与空,显示禅悟的精神形式的独特美感。
如果说“物化”体验是“静中静”的体验境界,那么庄禅哲学境界提供了这种“静中静”之体验的可能。“庄周梦蝶”中“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是消失了物我界限、获得物我同一的大浑的境界,然而,首先意味着是一种静寂的生命状态。梅特林克在《寂静》中说:“真正的寂静……从各个方面包围我们,成为我们生命潜流的源泉;我们当中任何一人试用战颤的手指去弹深渊之门,那么这门也会在同样寂静的殷切关注之下,被打开了。因为寂静没有任何疆域,是无限度的,在它面前,人人平等。”[5]梅特林克:《寂静》,转引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480页。从“寂静”是“生命潜流的源泉”的观点看,庄禅境界通向神秘的生命之门。诗人、艺术家借助庄禅境界潜入或获得寂静的天空,倾听自身内部,倾听生命与灵魂的声音。从现代生命体验的意义上,庄禅境界之静寂,从远古延绵而来,包围着我们,亲近着我们。王维的《雪溪图》与他的“空山不见人”、“夜静春山空”之类的诗一样,表现了那种空寂无人之境(静),其“溪雪”之白,“春山”之“空”,给人造成灵魂的颤动与空寂之美。当然,中国艺术独有的静观境界,旨趣在于进入凝神或畅神的审美观照,表现了与西方现代艺术体验心理之差异。
〔责任编辑:平啸〕
姜耕玉,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21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