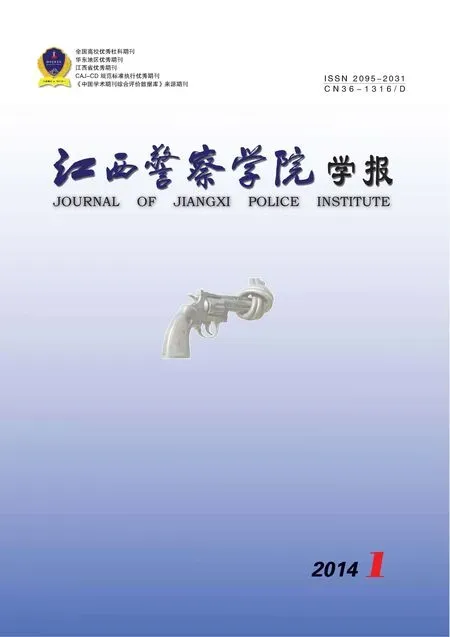刑事推定与应当知道
白冰
(北京大学,北京 102206)
刑事推定与应当知道
白冰
(北京大学,北京 102206)
刑事推定作为一个横跨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理论范畴,近年来颇受关注。司法解释中的“应当知道”也常常被视为推定的适用。刑事推定是在证明困难和特定的形势政策下,基于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的常态联系所设置的,其效力在于证明责任的转移,而非证明责任的倒置。司法解释中的“应当知道”并非全部属于推定的适用,对待刑事推定应当谨慎。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常态联系和证明责任的转移,是判断某一规则是否设置推定的重要标准。对于推定的判断和认识,必须回到推定的本元,厘清推定的基础的效力。
推定;应当知道;证明责任转移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刑事推定作为一个横跨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理论范畴,受到了理论界的高度关注,并产生了很多成果。然而,正如德国法学家罗森贝克在其经典著作《证明责任论》中所言,“没有哪个学说会像推定学说这样,对推定的概念十分混乱。可以肯定地说,迄今为止人们还不能成功地阐明推定的概念”。[1]在迄今为止的刑事推定研究中,可谓分歧多于共识。而自1992年起,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开始出现“应当知道”的用语。很多论者将“应当知道”与刑事推定的设置联系起来,认为“应当知道”的用语是运用推定方法的一种表现。面对纷扰的刑事推定理论,本文仅在推定的基础与效力的范围内,结合目前的共识与争议进行整理,并依此为出发点对司法解释的“应当知道”进行定位。
二、刑事推定的基础与效力
近些年来,关于刑事推定的研究逐渐增多,也出现了广泛的理论争鸣。笔者认为,阐明刑事推定的基础与效力十分必要,刑事推定的基础是其赖以产生、存在的根据,决定了推定“与生俱来”的一些特质。刑事推定的效力问题既是理论上的争议问题,又是认识推定在诉讼中作用的必需。
(一)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的常态联系是刑事推定的基础
尽管关于推定的理论争议较多,但理论界对于推定的基本结构则有普遍共识。一般而言,推定的结构中具有两个关键要素,即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教授将推定定义为:“推定是指从A事实(前提事实)推认B事实(推定事实)”。[2]这一说法简明地勾勒出了推定的基本结构。在推定的适用中,基础事实的成立,是认定推定事实成立的前提;而推定事实的成立,并不是根据基础事实所直接推导出来的结论,而是法官运用推定规则所作的法律认定;在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并没有建立必然的因果关系,而可能存在一种逻辑推理上的跳跃。[3]265因此,“推定不是诉讼证明,而是诉讼证明的替代方法”。[4]28
众所周知,在诉讼证明活动中,对于某一待证事实的证明,需要控方运用证据,在证明活动中达到了证明标准。而适用推定时,则并不遵循上述逻辑。推定事实的成立并非由于运用证据对其的证明,而是由于基础事实的成立。详言之,根据经验法则、逻辑法则,一般而言基础事实的成立,往往意味着推定事实的成立,由此推定规则才得以构建。美国学者华尔兹认为,“推定产生于下面这种思维过程,即根据一个已知的基础事实的证明来推断出一个未知的事实,因为常识和经验表明该已知的经验事实通常会与该未知事实并存”。[5]因此,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的常态联系是刑事推定的基础。
我国刑法第39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一般认为,该条确立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属于我国刑法中适用推定的典型。具体而言,基础事实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推定事实是“差额部分为非法所得”,根据社会的一般常识与经验,国家工作人员明显超出其合法收入的财产、支出系非法所得的可能性较大,换言之,二者之间存在常态联系,因此,才有设置这种推定的前提。
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的常态联系是推定的基础,因此需要注意两方面的考量。第一,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常态联系需要审慎考察和抉择。“在司法推定的适用中,为保证推定结论的正确性,关键是应当科学地确定推定的基础事实。只要基础事实与推定结论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推定结论就具有可靠性”。[6]84第二,所谓“常态联系”,而不是必然联系,也就意味着存在例外的情况。例如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国家工作人员虽然有明显超出其合法收入的财产、支出,但却并非必然是非法所得,也可能是通过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等合法来源所得。例外的存在决定了允许被告人反驳的必要性,被告人没有反驳或者反驳不成立的,推定事实方可被正式认定,这也是适用推定的重要特点。
(二)证明困难和特定的政策是刑事推定的现实基础与政策基础
在刑事诉讼中,基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控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而诉讼活动受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往往存在证据稀缺的情况。因此,“证明困难”无疑是控方无法绕开的一大障碍。在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证明中,相比于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的证明更为困难。在很多案件中,尤其是在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情况下,要证明“明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等要素,在司法实践中不可避免会遭遇“证明困难”的困境。[7]例如,我国刑法中存在目的犯的规定,而“目的犯的设立,对控方的举证增加了一定的难度:控方不仅要证明本罪的客观行为和主观故意,还须额外地证明特定目的之存在”。[8]由此,不难想见在目的犯的证明中,控方面临的巨大挑战。
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和社会整体以合理而有效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为目标而提出的有组织地反犯罪斗争的战略、方针、策略、方法以及行动的艺术、谋略和智慧的系统整体。[9]在推定的设置上,特定的刑事政策是重要的考量。我国刑法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司法解释中频繁使用的“应当知道”的用语均体现了这一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适用前提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出其合法收入,具有贪污、受贿或其他犯罪的嫌疑,但又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上述犯罪的成立,因此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一种最后手段来堵截犯罪。[10]正是由于本罪所具有的堵截犯罪、周延法益保护的功能,基于国家对公务人员廉洁性的重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为我国刑法中设置推定的典型范例。
而司法解释中出现的“应当知道”的用语,也涉及刑事政策的考量。如上文所述,在司法实践中,证明被告人的“明知”往往面临困难,存在着被告人“不知”与“明知”之间的灰色地带。而“应当知道”被“司法解释赋予了证明“明知”心理状态中的“兜底”地位,以覆盖司法机关在难以证明被告人肯定知道的情形下,通过各种间接证据推定出被告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有)知道”的主观心理状态”。[11]74
正因为上述两方面的考量,刑事推定一般出现在既在实践中存在证明困难,又符合国家的刑事政策的犯罪领域。例如,我国刑法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毒品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等。
(三)证明责任转移是刑事推定的法定效力
对于推定的效力问题,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看法。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刑事推定倒置的是证明责任的转移还是倒置,以及如何看待被告人的反驳。[12]以下主要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讨论。
1.推定导致的效果
对于推定导致的效果,主要有两种观点,即“证明责任倒置说”与“证明责任转移说”。[13]872何家弘教授认为,证明责任转移和证明责任倒置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仍然符合“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后者则是对该原则的背叛,即“我主张你举证”。[13]873他以我国刑法第395条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为例,分析推定规则适用时证明责任变化的情况。他认为,在此类案件中,公诉方主张那些财产是非法所得,但是法律规定要由被告方承担其不是非法所得的证明责任。被告方并没有提出一个积极的事实主张进行抗辩,但是法律强制其承担证明公诉方主张不能成立的责任。只要被告人不能用充分证据证明其巨额财产有合法来源,法官就可以推定那些财产是非法所得,就可以判其有罪。[13]874由此,得出结论:适用推定规则所导致的不是证明责任的转移,而是证明责任的倒置。[13]874
而汪建成教授则主张,“在证明责任的转移中,事实的主张方和否定方在证明责任上是一种接力关系;而在证明责任的倒置中,双方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而不是接力关系”,[4]31具体到推定的适用中而言,基础事实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后,由于推定规则的存在,辩方需要承担证明责任以避免推定事实的成立。这种现象符合证明责任转移的全部特质,而与证明责任倒置相距甚远”。[4]32
对这一问题的分歧,产生于对证明责任倒置和证明责任转移两个概念的不同看法。笔者认为,推定导致的是证明责任的转移,而不是证明责任的倒置。首先,证明责任的倒置更偏向于证明责任的非常态分配,详言之,证明责任的倒置是立法者基于特定的价值考量,采取了特殊的证明责任分配方案,即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明责任不是由主张方承担,而是由主张方的相对方来承担。例如,在我国的行政诉讼中,行政相对人主张某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法律基于保障相对人诉权、举证便利性和敦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考虑,由行政机关承担证明责任。[14]证明责任倒置作为一种分配方案,一经确立,就固定下来。而这种确立发生在立法阶段。推定的具体适用发生于司法活动中。其次,证明责任转移可以在控辩双方之间来回移转,是一种动态的转移。[15]这恰恰符合推定适用的逻辑。具体而言,在适用推定的情形中,控方首先就基础事实的成立承担证明责任,在控方完成证明活动之后,推定事实“暂时性”的成立。这时即需要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以避免推定事实成为裁判的依据。这可以说是证明责任的第一次动态转移。而如果被告人提出证据证明推定事实不成立,证明责任再次转移给控方。这是由于无罪推定原则要求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始终在控方,控方此时一般通过证明被告方的反驳、辩解不成立来承担证明责任。[3]281这可以说是证明责任的再次转移。由此可见,推定导致的,是证明责任的动态转移,而不是证明责任倒置。
2.被告人反驳的性质
根据推定的适用规则,在控方证明基础事实成立,从而使得推定事实“暂时性”成立之后,被告人有反驳的机会。对于这种反驳的性质,理论界也有不同的认识。上文所述的观点分歧在于证明责任转移和证明责任倒置的区分,而对被告人的反驳属于承担证明责任是有共识的。另外有一种与上述观点针锋相对的看法,即被告人的反驳不属于承担证明责任,而属于辩护权的行使。例如,有论者认为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被告人提供证据说明其财产来源合法的行为是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行为,而不是履行证明责任的行为”。[16]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至少有两方面的缺陷:第一,逻辑矛盾。论者承认,行使辩护权与承担证明责任的区别在于被告人放弃行使辩护权,司法机关不能因此作出对其不利的裁决;而放弃证明责任,则需承担不利后果。而在推定的适用中,控方证明基础事实成立后,已经使得推定事实 “暂时性”成立,此时,被告人如不反驳或反驳不成立,显然将使得推定事实就此成立,而这是不利于被告人的。这正符合论者所言的承担证明责任的特征,而非辩护权的行使。论者认为,“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里,被告人可以说明巨额财产的来源,也可以不说明”,[16]殊不知,不说明的后果即是巨额财产被认定为非法所得。第二,机械理解无罪推定原则。诚然,无罪推定原则作为现代刑事司法的基石,被认为是对被追诉人人权的最基本保障。无罪推定原则要求控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并且须证明到法定的证明标准。但无罪推定原则并不要求对一切事项被告人均不得承担证明责任,而是特别禁止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由被告人承担。因此,控方承担证明责任也有其例外。[17]论者动辄将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拔高到”违背无罪推定原则的高度,其实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误解。
概言之,被告人的反驳是在证明责任转移到自身后,承担证明责任,以避免推定事实成立的行为,而非行使辩护权的行为。财产来源合法的行为是被告人行为。
三、关于“应当知道”的理论争鸣
我国现行刑法中并未出现 “应当知道”这一用语。而在刑法第219条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定中,出现了“应知”的用语。第219条第2款规定,“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理论界对此有不同看法,陈兴良教授认为,“这里有 ‘明知或者应知’一语,其中‘应知’就是‘应当知道’”。[6]80而张明楷教授则解释道,“刑法第219条第2款中的‘应知’不是指应当知道(即不是指过失可以构成本罪),而是指推定行为人已经知道”。[18]当然,尽管两位学者对“应知”的解读不同,但对本罪的罪过形式均无异议,认为本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18]另外,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本罪的罪过形式既包括故意,也包括过失。其中,在“应知”的情况下,构成本罪的,则是一种过失犯罪。[19]鉴于已有论者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驳,[6]142-143这里不再述及。
而在司法解释中,“应当知道”的用语出现频率颇高。该用语在刑事司法解释中最早出现在1992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在该“解释”的第8条“如何认定窝赃、销赃罪”中,规定,“认定窝赃、销赃罪的‘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的口供,应当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予以分析。只要证明被告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或者代为销售的,就可以认定”。该解释开启了将“知道”和“应当知道”并列地列为“明知”的两种形式之先河。[11]69
张明楷教授在评论上述司法解释时,认为“‘应当知道’是赃物,无论如何不属于 ‘明知’是赃物,“‘应当知道’是赃物本身就表明行为人事实上还不知道是赃物,而‘明知’是赃物表明行为人事实上已经知道是赃物,故‘应当知道’不属于‘明知’”。[20]88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应当知道”的用语,容易与刑法中疏忽大意过失中的“应当预见”相对比,产生“应当知道”属于因过失而不知道的看法。上文所述及的张明楷教授认为“侵犯商业秘密中‘应知’不是指应当知道(即不是指过失可以构成本罪)”,大概就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因此,张明楷教授认为,将对“明知”的解释扩大到包括“应当知道”的程度,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20]89基于“应当知道”是因过失而不知道的立场,对司法解释提出批评意见的还有周光权教授,他认为,“司法解释上将应知确定为明知的一种表现形式,实际上是扩大了故意的范围,属于将过失强行解释为故意”。[21]115
陈兴良教授认为,“不能将应当知道解释为明知的表现形式,应当知道就是不知,不知岂能是明知。实际上,在应当知道这一用语中,人们想要描述的是一种不同于确切地知道的认识状态,这种认识状态我认为应当定义为推定知道”。[22]
纵观上述不同观点,可以有以下发现:其一,上述关于“应当知道”的含义的论述并非在一个层面上进行的。认为“应当知道”属于因过失而不知道的论者是从“应当知道”这一用语的易含混性角度出发,而没有观察司法解释中具体的涉及“应当知道”的情形。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 《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条“关于毒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明知的认定问题”中,涉及了“应当知道”的认定,①该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非法持有毒品主观故意中的“明知”,是指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实施的行为是走私﹑贩卖﹑运输﹑非法持有毒品行为法。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并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其“应当知道”,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一)执法人员在口岸﹑机场﹑车站﹑港口和其他检查站检查时,要求行为人申报为他人携带的物品和其他疑似毒品物,并告知其法律责任,而行为人未如实申报,在其所携带的物品内查获毒品的;(二)以伪报﹑藏匿﹑伪装等蒙蔽手段逃避海关﹑边防等检查,在其携带﹑运输﹑邮寄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三)执法人员检查时,有逃跑﹑丢弃携带物品或逃避﹑抗拒检查等行为,在其携带或丢弃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四)体内藏匿毒品的;(五)为获取不同寻常的高额或不等值的报酬而携带﹑运输毒品的;(六)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携带﹑运输毒品的;(七)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交接毒品,明显违背合法物品惯常交接方式的;(八)其他有证据足以证明行为人应当知道的。从具体的情形来看,司法解释对于“应当知道”的描述,绝非“因过失而不知道”。而认为“应当知道”这一用语实际上用于描述 “一种不同于确切知道的认识状态的观点,则显然是注意到了司法解释中具体的涉及“应当知道”的情形。其二,对于“应当知道”这一用语的易含混性,达成了共识。即由于语言学上的原因和我国刑法中对疏忽大意的过失 “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的界定,“应当知道”极容易(或者事实上)被认为是“应当知道而不知道”。这确实“属于司法解释的用词不当,极易引起刑法学界的误解”。[21]115因此,上述观点的不同,并未形成根本性的分歧,而是在有共识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的阐发。
而实际上,“应当知道”这一问题的真正焦点在于,对于“不同于确切知道的”认识状态,如何看待其与明知的关系,司法解释中的“应当知道”究竟如何认识,是否“应当知道”的用语就意味着刑事推定的设置。
四、司法解释中“应当知道”的定位
周光权教授将“明知”进行了分级,即分为“确知”、“实知”、“或知”、“应知”四级。“确知”,是指根据被告人口供、被害人指认、证人证言或其他各种证据,可以直接判定行为人肯定地、确切地知道。[21]114“实知”是在没有被告人口供可以认定行为人确实知道或者肯定知道的情况下,结合各种证据,在司法上推断其知道。或知,是指行为人可能知道。或知不是“可能知道”和“不可能知道”之间一半对一半的关系,而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判断行为人可能知道的概率很大,可能知道的盖然性远远高于可能不知道,所以,可以认定其存在明知。“应知”则是指“应当知道”。在对涉及“应当知道”的司法解释进行梳理后,他认为,许多使用“应当知道”的司法解释,其描述的是“实知”的状态,而非适用推定的明知,对于极少数不得已需要用推定方法判断明知的司法解释,可以保留“应当知道”的表达方式。[21]117-118笔者认为,无论是否同意其对“明知”的分级,其对于司法解释中的“应当知道”重新梳理,以甄别是否属于推定的适用的思路非常必要。
第一,目前理论界对于推定的认识有“泛化”之嫌。较为典型的是,有论者“通过检索刑事立法、司法解释与相关的法理,总计归纳出44个推定事例”,共分为立法型推定、司法型推定和法理型推定。[23]而实际上,其所罗列的相当部分的所谓“推定”,并不具有推定的特征,不会纳入到证据法学研究当中。例如,该论者认为,刑法第65、66条关于一般累犯和特别累犯的规定,是立法对累犯的人身危险性的推定,性质上属于强制性推定、不可反驳的推定、涉及主体要素的推定和不利于被告人的推定。实际上,该规定属于实体法的一项规则,所谓“不可反驳的推定”与实体法规则并不差异,而在证据法上没有太大意义。就累犯的规定而言,立法对于一般累犯和特别累犯的规定,属于立法的一种价值选择和政策倾向,而非设置一种推定。
第二,推定规则的性质决定了对其认识的 “泛化”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推定是一种特殊的法律机制,其应用总是触及合法性与公民权利这两个敏感问题,因此必须依法确认,不能随机和随意地进行”。[24]由于推定是一种诉讼证明的替代手段,其与诉讼证明应该是例外与原则的关系。过度的设置推定规则必然使得本应是原则的诉讼证明以及一系列规范诉讼证明的原则与规则“边缘化”,形成了本末倒置的局面。因此,正如“泛化”认识刑事推定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刑事领域的推定实际上涉及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关系的处理,推定的背后上演的可能是国家权力悄然扩张的一幕。在推定适用不断扩张的今天有必要认真对待刑事推定”。[23]
笔者认为,正如上文所述,刑事推定的基础与效力是其特征所在,具体而言,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常态联系和证明责任的转移,是判断某一规则是否设置推定的重要标准。以下以一些具体的司法解释为例,对其进行分析。
(一)不属于推定的情形
2004年12月8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二款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明知’:
(一)知道自己销售的商品上的注册商标被涂改、调换或者覆盖的;
(二)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受到过行政处罚或者承担过民事责任、又销售同一种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
(三)伪造、涂改商标注册人授权文件或者知道该文件被伪造、涂改的;
(四)其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情形。”
有观点认为,该司法解释属于推定规则,[25]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妥当。原因在于:其一,上述规定是对刑法第214条中规定的“明知”,提出一些具体化的、提示性的、有助于法官认定的情形,并非基于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而构建的推定规则。例如,司法解释规定的“知道自己销售的商品上的注册商标被涂改、调换或者覆盖的”的情形,在该情形与刑法第214条中的 “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之间并不存在一种逻辑上的跳跃,而是一种常人均可以进行和接受的推断。司法解释上述规定的目的,不在于对于某些不属于明确知道、但又有较大可能知道的情形以推定的方式进行处理,而仅仅是对司法实践当中,“明知”的认定进行一种具体的指导性解释。其二,在该规定下,并不存在适用推定规则时所发生的证明责任转移的问题,在控方对上述规定中的情形证明后,法官即可以对其是否达到证明标准进行判断,而不存在推定事实“暂时性的”成立的空间。
(二)属于推定的情形
2009年11月4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明知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
(一)知道他人从事犯罪活动,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的;
(二)没有正当理由,通过非法途径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的;
(三)没有正当理由,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财物的;
(四)没有正当理由,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收取明显高于市场的“手续费”的;
(五)没有正当理由,协助他人将巨额现金散存于多个银行账户或者在不同银行账户之间频繁划转的;
(六)协助近亲属或者其他关系密切的人转换或者转移与其职业或者财产状况明显不符的财物的;
(七)其他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
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是较为典型的设置推定规则的例子。原因在于:其一,在本条当中,“通过非法途径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的”、“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财物的”等行为,确实表现出行为人具有较大的“明知”嫌疑,即二者之间具有常态联系。但这种联系并非不存在例外。其二,司法解释中的“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和“没有正当理由”实际上涉及被告人在证明责任转移后,所承担证明责任的问题。具体而言,证明被告人有上述规定涉及情形的证明责任在控方,当然这也包括证明被告人在进行相关操作时,“没有正当理由”。待控方完成了证明责任后,被告人属于“明知”这一推定事实“暂时性”地成立,此时证明责任转移到被告人一方。被告人可以选择提出证据证明其“确实不知道”,也可以选择提出证据证明其“有正当理由”,以期阻止推定事实正式被认定。考虑到证明某一事项的“不存在”相比较证明其“存在”更为困难,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是否具有正当理由的证明上,被告人会较控方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结语
由于推定所具有的转移证明责任的效力,使得推定的适用使得被告人处于不利的地位,使得推定的设置较为敏感,也涉及价值判断与选择。对于推定的判断和认识,必须回到推定的本元,厘清推定的基础的效力。推定作为一种替代诉讼证明的手段,其地位决定了其虽然不可或缺,但只能属于例外,而不可成为原则。因而,谨慎对待推定,限定推定适用的合理范围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具体到司法解释设置的“应当知道”,其用语容易使人误解,应当考虑改善。同时,对于司法解释设置推定的权力也应当考虑予以规制。
[1][德]莱奥·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M].庄敬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202.
[2][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M].张凌,于秀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276.
[3]陈瑞华.刑事证据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汪建成,何诗扬.刑事推定若干基本理论之探讨[J].法学,2008,(6).
[5][美]乔恩·R·华尔兹.刑事诉讼法[M.]何家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314.
[6]陈兴良.“应当知道”的刑法界说[J].法学,2005,(7).
[7]徐新励,沈丙友.金融诈骗犯罪主观目的诉讼证明困境与出路论[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5):113.
[8]陈兴良.目的犯的法理探究[J].法学研究,2004,(3):79.
[9]梁根林.解读刑事政策[J].陈兴良.刑事法评论,11:17.
[10]梁根林.持有型犯罪的形势政策分析[J].现代法学,2004,(1):37.
[11]王新.我国刑法中“明知”的含义与认定——基于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分析[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1).
[12]褚福民.刑事推定的基本理论——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理论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50.
[13]何家弘.论推定规则适用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J].中外法学,2008,(6).
[14]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3:523-524.
[15]卞建林.刑事证明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226-227.
[16]李宝岳,吴光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及其证明责任研究[J].政法论坛,1999,(6):69.
[17]陈永生.论刑事诉讼中控方承担举证责任之例外[J].政法论坛,2001,(5):72.
[18]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4:739.
[19]高铭暄.新型经济犯罪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841-842.[
[20]张明楷.如何理解和认定窝赃、销赃罪中的“明知”[J].法学评论,1997,(2).
[21]周光权.明知与刑事推定[J].现代法学,2009,(2).
[22]陈兴良.奸淫幼女构成犯罪应以明知为前提——为一个司法解释辩护[J].法律科学,2003,(6):29.
[23]劳东燕.认真对待刑事推定[J].法学研究,2007,(2).
[24]龙宗智.推定的界限及其适用[J].法学研究,2008,(1):115.
[25]皮勇,黄琰.论刑法中的“应当知道”——兼论刑法边界的扩张[J].法学评论,2012,(1):53.
责任编辑:黄永强
D924.1
:A
:2095-2031(2013)05-0079-06
2013-11-20
白冰(1989-),山西临汾人,北京大学法学院2012级刑事诉讼法方向硕士研究生,从事刑事诉讼法学研究。
——以“被告人会见权”为切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