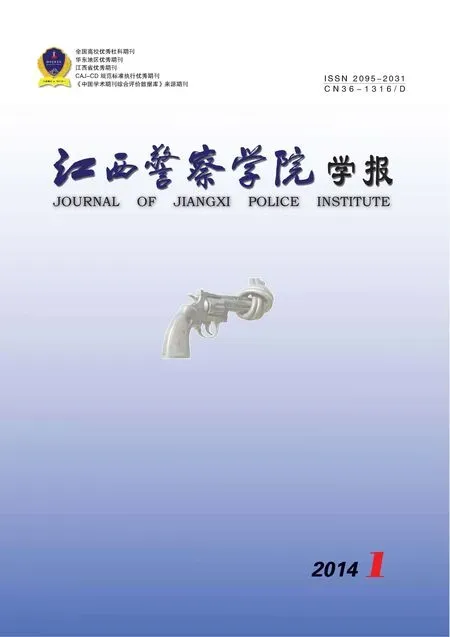刑事证人保护措施的适用条件
潘金贵,李冉毅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刑事证人保护措施的适用条件
潘金贵,李冉毅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证人保护制度的确立对于提高证人作证的积极性、促进证人出庭作证意义重大,然而立法对证人保护的适用条件规定较为简单,缺乏操作性。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应当以证人面临的现实危险为主线,通过综合考察证人受侵害的程度及其迫切性、案件的类型、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及人身受限制程度、证人的个人情况、证人证言的重要性等因素来判断是否应该适用某类保护措施。在此基础上,可以为刑诉法新增的各项保护措施设置合比例的适用条件。证人在长时间内面临被打击报复的危险,或已被采取贴身保护措施却仍持续不断地遭受恐吓、骚扰时适用对证人采取更换姓名、迁居、安排住所和工作等保护措施。
证人保护;考量因素;适用条件;隐名作证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中强调证人的作证义务却疏于对证人的保护,导致实践中打击报复证人的现象时有发生。证人缺乏保护是导致证人出庭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丹宁勋爵所言,“每个法院都必须依靠证人,证人应当自由地、无所顾虑地作证,这对执法机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假如案件一结束,证人就要受到那些不喜欢他作证的人的报复,那么还能指望证人自由地和坦率地提供他们应当提供的证言吗?”[1]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证人保护制度在立法上得到了正式确立,如果在司法实践中能够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必将极大地有利于解决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不敢作证、不愿作证的问题,提高证人出庭率,推动庭审程序的正当化。
然而,从可操作性的角度而言,如何准确判断证人是否存在保护的必要、在何种前提条件下适用相应保护措施,则是执行证人保护时必须考量的要素,也是证人保护实施中最为棘手的问题。虽然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数项证人保护措施,也统一规定了这些保护措施的适用条件,即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其近亲属的人身面临危险的。”但这样的规定存在两项缺陷:其一,条件限定的过于狭窄。新刑事诉讼法对证人的保护单单是从案件的类型出发,并且加以“人身面临危险”进行限制,这样会导致实践中保护机构为推诿责任而机械的执行标准,对其他案件中面临潜在危险的证人置若罔闻。其二,对各项证人保护措施的适用条件没有大致的区分,保护机构可能会因为判断偏误或其他原因而不当适用保护措施。鉴于此,本文将对各项影响证人保护之因素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以“隐名作证”这项最基本的保护措施为例,就保护措施的适用条件进行探讨,同时也对刑诉法新增另外几项保护措施的适用条件作初步设定。
二、证人保护适用中的主要考量因素
司法机关在采取证人保护措施之时,应当以证人面临的现实危险为主线,通过考察一些主要的因素来确定证人面临危险的程度,以此来判断是否应该适用某类保护措施,同时也应兼顾考虑证人所提供证言的重要性。
(一)证人受侵害的程度及其迫切性
证人是否已经受到侵害,以及受侵害的程度是对侵害人实施惩罚的最主要依据,同时也可以据此判断证人是否存在继续被打击报复的危险。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受到的侵害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语言威胁,使证人或其近亲属生活在恐惧之中;其二,蓄意捣乱,打乱证人安宁的生活原状,整日麻烦缠身;其三是骚扰侮辱,使证人身心俱疲;其四是暴力殴击,伤人毁物。[2]这些侵害方式虽然程度各异,但都或多或少对证人的身心造成创伤或财产造成损失。针对证人这种“被害人”化的无辜遭遇,我国刑事立法始终强调严厉打击此类侵害证人的行为。修改前后的刑事诉讼法均明确指出:“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对此,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进一步明确了侵害证人应负的法律责任。①根据刑法第307条的规定,以暴力、威胁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308条规定: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根据侵害证人行为的性质和证人遭受的危害结果,司法、行政机关即可依法对侵害者予以相应的制裁,以此来震慑打击报复证人的不良分子,对证人进行一种 “安抚性的事后保护”。
在追究侵害者责任的同时,证人保护机构可以根据证人受侵害的程度和继续受到侵害的迫切性来决定是否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因为此时证人已经暴露在外,其继续遭受侵害的可能性较大,如果不采取一定强度的保护措施,证人很有可能从之前的被威胁、侮辱等精神侵害转化成被殴打之类的肉体侵害。现实中也不乏从“扬言报复式”的威胁到最后实施打击报复的案例。②其中比较典型的案例:1997年,山东省日照市胡秀娟因在3年前对刘桂安强奸案(未遂)出具了证言,刘桂安在出狱后对其扬言报复:“不是你作证,我怎么会去坐牢!我早晚要收拾了你!”胡秀娟和丈夫因此事分别找过村治保主任、村委会和镇派出所寻求保护,但都未果。1998年7月,胡秀娟和8岁的儿子均被刘桂安杀害。另外,在侵害者不明或在逃时,证人仍旧处于一种比较危险的环境之中,而此时采取专门的保护措施可以防止证人遭受二次侵害。因此,我们可以综合考察证人已经受到侵害的程度以及其他使之可能再次受到侵害的因素来确定是否有必要采取一种补救性的保护措施。
(二)案件的类型
案件的类型无论在立法和理论研究中都被作为判断是否对证人进行保护的主要标准之一。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62条专门强调公、检、法三机关应对在“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中因为作证而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证人采取保护措施。之所以如此,一般认为,这些特定类型的犯罪案件,由于案件关系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犯罪性质恶劣、组织性强,证人遭到打击报复的可能性大,后果也可能更严重,甚至具有生命危险。[3]有学者也指出:“证人恐惧刑事被告报复,于组织犯罪案件,较一般刑事案件更为严重。犯罪组织有延续性及持续性,未必因一成员受刑之执行,而稍减组织对社会或证人之威胁性,此与一般案件不同。犯罪组织为维持组织之继续存在,更有可能对证人恐吓。”[4]相对而言,有组织犯罪案件中对证人的恐吓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和计划性,较易达到阻止证人作证的目的。而且这些犯罪往往带有暴力性质,恐吓证人的破坏性强,证人无论是受到暗示、威胁还是侵害,都会造成极度恐慌的心理,甚至在一个群体、社区造成恐惧,影响潜在证人的作证。[5]178在美国,其“证人保护计划”也正是始于《有组织犯罪控制法》的颁布,充分反映证人在一些性质严重的案件中作证,其所处危境可见一斑。
尽管刑诉法相关规定也同时强调了 “人身安全面临危险”这一条件,但作为适用证人保护措施的基本前提,“证人面临危险”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一眼可见的,而是需要通过其他因素来对之进行判断,此处所强调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便是基于此类案件的性质作出的推断。故此,完全可以根据案件的性质确定一些“使证人受侵害更具可能”的案件种类,以此为作为采取某些特定保护措施的前提条件。
(三)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及人身受限制程度
关于人身危险性的评价因素纷繁复杂,学界至今也未达成统一的标准,③一般认为,犯罪人的人身包括两大方面:犯罪人的个人基本情况和犯罪人的行为表现。犯罪人的个人基本情况具体包括年龄、性别等生物性因素;兴趣、性格能力等心理性因素;家庭、学校教育、婚姻状况、职业等社会环境因素。犯罪人的行为表现包括犯罪前的行为表现、犯罪中的行为表现和犯罪后的行为表现。如果我们将其作为判断犯罪人打击报复证人可能性的一项依据,只需择其部分核心评价因素。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将犯罪人犯罪后的行为表现作为主要考察对象。之所以如此,一来证人保护决策者并非刑事法官,把握太多因素难免会生困惑,反而拿捏不准;二来犯罪后行为表现能集中反映当前犯罪行为人的危险状态,在这里可以此代表错综复杂的人身危险性衡量标准,进一步判断其对于证人形成的危险。如果犯罪人在犯罪后有自首、立功、坦白交代、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或退赃表现,则表明犯罪人具有悔罪心理,我们可以据此认为其人身危险性小;如果犯罪人犯罪后为逃避侦查而畏罪潜逃、嫁祸于人、积极销毁或隐匿犯罪证据,对自己的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么我们可以据此认为其并无悔罪心理,相比而言,其人身危险性较大。[6]在后一种情况下,犯罪行为人对于指证其实施犯罪的证人心怀恨意,容易产生打击报复的动机,在此情形下,证人更可能处于危险之中。
通过考察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判断其侵害证人的内在动力,进而确定保护措施的适用,这固然无可厚非。然而还需要兼顾考虑的是,犯罪人是否还具有侵害证人的能力。如果犯罪人已经被采取最严厉的强制措施或是被判处监禁刑,同时也无法指使他人对证人进行威胁、恐吓和打击报复,那么就可以不采取或解除保护措施,或是降低保护强度。反之,就需要对证人的安全多加注意。
(四)证人的个人情况
在对证人采取保护措施时,除了考虑一系列使证人陷入危险处境的外部因素外,也需从证人自身角度出发考察证人保护的必要性。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从证人的年龄、证人的意愿、自我保护能力、心理状态、证人的可靠性等因素对证人的自身情况进行综合考量。
在证人年龄方面,一些国家特别强调对未成年证人的保护。例如在德国,其对于证人在审判中有正当理由不宜与被告人当面质证的,尤其是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以及性侵害案件受害人,可以通过录音、录像作证,利用有线电视系统在其他密室进行询问等。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条件相对放宽,是考虑到未成年人的身心发育还未成熟,更容易受到刺激和伤害。
在证人的意愿方面,主要强调保护机构不能只考虑如何运用权力开展证人保护工作,也应该关注证人对于被保护的内心需求。尤其是对多次主动寻求保护的证人,保护机构应给予重点关注,可适当放宽保护措施的适用条件。反之,有的证人为了行动上的便利或一些隐私情况而不希望时刻处于被保护之中,保护机构可酌情考虑降低保护强度,当然,此时需要考虑到证人的自我保护能力。相比而言,具有一定防御能力,特别是因为职业需要或个人爱好有过诸如习武、从军经历的证人,其自我保护能力较一般人强。此外,基于自身财力雄厚而雇请保镖保护的证人,也可以归属于自我保护能力较强一类。
在证人心理状态方面,需要考虑的是证人目睹案件情况以及作证给证人正常心理造成的冲击,应该承认“刑事犯罪行为及现场的出现,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证人正常稳定的心理结构”,使证人“形成心理障碍,其心理状态和外在表现出现反常、偏差”。[7]一般情况下,证人心态受到的影响与其目睹案件的严重程度成正比,但是心理素质因人而异,有的时候一起简单的入室盗窃案件也会令其一些目击证人长久心存恐惧。所以,对心理状态不稳定的证人予以额外关注,通过外部的保护措施消除其内心的恐惧,可以使其无顾虑地作证,也体现了证人保护制度人性的一面。值得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心理状态不稳定也包括熟人作证产生的心理矛盾。从人际交往的角度看,中国人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中,一个人一生很难离开特定的工作圈和生活团体。一个与犯罪人同处于一个生活圈或熟识的证人,不会轻易去指控熟人犯罪的,否则将难以生活下去。对于这类证人,保护机构可以根据其主动申请而保密其身份信息,从而化解其心理矛盾,减少因作证对其正常生活造成的影响。[8]
最后,在证人的可靠性方面,主要强调证人作证的动机不能存在恶意。当然,这并不是要求证人必须准确无误地描述所见所闻,而至少不能故意捏造、扭曲事实以陷害被追诉人或是给案件的侦破平添阻碍。在刑事诉讼中,证人可能会为了己方利益而向司法机关提供不实的证言,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案件事实的查清变得扑朔迷离,更严重者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因此,如实作证也被强调为证人作证义务的应然要求。而证人受保护的权利正是来源于其对作证义务的履行,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证人不履行如实作证的义务,就可视为其自行放弃被国家保护的权利。
(五)证人证言的重要性
将证人证言的重要程度纳入证人保护的考量因素,主要基于两点考虑:其一,一般情况下,拒不认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倾向于对知晓自己犯罪事实的关键证人进行威胁、恐吓和打击报复;其二,当证人证言成为定罪不可或缺的证据且被告人对其有异议时,从保障被告人基本的质证权和查明事实真相的双重目的出发,我们需要证人与被告人“面对面交流”,此时,证人的信息、容貌将暴露于被告人的视野之内,其危险系数将大幅提升。
对于前者,保护机构关注的是证人所述内容的价值会给证人带来的潜在危险。其中,一些试图掩饰自己犯罪行为的嫌疑人会尽力毁灭一切不利于己的线索,这时熟知案情的证人就成为他们重点打击的对象。特别是有组织犯罪中的“污点证人”,他们对犯罪组织内部的组织结构、具体行动计划有一定的了解,掌握很多局外人无法知悉的罪证,不仅可以为警方侦查破案提供很多有价值的线索,而且可以成为检察机关强有力的控方证人。[9]利用此类证人证言来破案定罪,犯罪一方可能极力阻挠或泄愤报复,证人受到侵害的风险更大。
对于后者,主要考虑到有的保护措施,如隐名作证、庭下作证和隐蔽作证,都或多或少影响到被告人的知悉权、对质权、保释权等合法权利的有效行使,而其中对质权的缺失可能影响到法官到对证据事实的准确甄别。所以有学者指出,“证人保护不应以‘尽善尽美’为目标,而是应当‘适可而止’,否则会有‘得知桑榆失之东隅之嫌’。”[10]正因如此,对证人的保密性保护不能是无止境的,当证人证言备受争议且与事实发现存在莫大关系时,我们需要被告充分了解指证其犯罪的证人,并且使之在法庭上对不利于己的证言进行有效质证。欧洲人权法院也强调“当隐名证据是唯一的有罪证据或对案件其决定作用时,有罪判决不能成立”,以此将证人隐名保护的适用限制在必要限度内,从而获得被告于证人利益的平衡。但当证人信息因为作证的需要而被暴露时,保护机构须额外考虑证人是否会因此陷入被打击报复的危险之中,必要时需采取强度更大的保护措施。
(六)其他影响因素
除了以上五项影响证人保护适用的主要因素外,还有一些易于掌握的情况值得我们参考。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行为人的到案情况可以作为衡量证人安全系数的一项指标;犯罪行为人对证人的了解程度可以作为具体采取何种保护措施的参考事项;同时应将采取证人保护措施对证人带来的负面影响作为限制保护强度的依据等。
三、刑诉法新增保护措施的适用条件
考量影响证人保护的各项因素,不仅可以在动态中把握证人的即时危险状况以及保护措施的适当性,也可以为各项证人保护措施的启动设定一个静态的标准。也就是说,在具备哪些条件下应该对证人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是可以在规范层面上予以明确的。
(一)“隐名作证”的适用条件
“隐名作证”是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首项保护措施,即“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具体是指办案机关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对有关个人信息予以保密,包括在起诉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上使用化名等以替代真实的个人信息。“隐名作证”是唯一不需要考虑经济成本的保护措施,因而在证人保护实践中要求最低、运用最广。正因为如此,限定“隐名作证”的适用条件是很有必要的,通过严格把关“隐名作证”的启动标准,可以避免其在诉讼中被无限制使用。
在域外一些国家,“隐名作证”的适用受到了严格了限制,例如葡萄牙,作证证人只有同时符合“在一些特定的严重犯罪中或相关犯罪分子所犯八年及以上监禁刑的集团犯罪中提供证言;自身或密切关系人生命、人身、自由、财产面临严重威胁;其可信度不值得怀疑;证言和陈述起到了相应证明作用”[11]的条件时,其身份信息才能在诉讼过程中被保密。然而,这样的要求又过于严苛。将“隐名作证”限制在一些严重的犯罪案件,并且同时要求证人人身、财产等权利面临严重威胁和证言起到证明作用,势必极大限缩隐名保护的范围,无法全面发挥“隐名作证”的保护功效。作为投入最少、操作最易的保护措施,隐名保护理应与专门保护、更名迁居等保护措施的适用条件有所区别,如果条件设置过高,则与这些高强度保护措施的启动标准并无二致,如此不利于保护机构准确抉择。因此,我们认为,在没有与重大利益冲突的情况下,“隐名作证”应当作为适用条件最宽,适用率最高的一项证人保护措施。
任何一项保护措施皆有利弊之处,“隐名作证”之利在于保护证人的安全与隐私,鼓励证人勇敢地作证;其弊在于有损被追诉方的辩护权、质证权等合法权利,有碍实质真实的发现,有违程序公开原则。从“隐名作证”的利弊两个层面出发,我们可以通过肯定要件和否定要件的双向设置确定“隐名作证”的适用条件。肯定要件为“隐名作证”发挥其优势的地方,即证人因为作证而使人身、财产面临危险,正常生活受到重大影响。具体而言,前文论及的一些影响证人保护的因素可以对之细解。例如,证人在有组织犯罪案件中作证,其往往身处危险之中;拒不认罪、毁灭证据的犯罪嫌疑人,对知情证人恐吓、打击报复可能性较大等。否定要件为阻碍“隐名作证”适用之理由,在法庭审理阶段,当证人证言成为定案的关键证据时,需要被告方对证人“面对面”质询,以便法官查明案件事实,至此“隐名作证”不再具有适用的条件。根据肯定与否定的双重标准,以及在所有证人保护措施中的最宽条件标准,我们可以按照如下模式设定“隐名作证”的适用条件:
只要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应当对证人的身份进行保密:
1.证人在危害国家安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毒品犯罪以及其他暴力犯罪等案件中提供证言的;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畏罪潜逃,且有毁灭证据与恐吓证人的初步证据的;
3.同案其他证人已经遭到威胁、侮辱、殴打或打击报复的;
4.证人因为作证产生心理障碍,或是强烈要求身份保密的;
5.未成年人作证的;
6.其他需要不公开个人信息的情形。
但存在下列情况的除外:
1.证人信息已经被披露;
2.证人故意提供虚假证言;
3.证人证言是唯一的直接证据;
4.证人证言与被告人供述的主要犯罪事实存在矛盾之处且无法排除的;
5.不同证人的证言之间存在矛盾且无法排除的;
6.因证人证言为定案的关键证据需要证人出庭当面接受询问的。
(二)其他保护措施的适用条件
1.隔离式“隐蔽作证”
准确地说,“隐名作证”属于“隐蔽作证”的一类保护措施,其内涵远不及“隐蔽作证”所涵盖的范围。“隐蔽作证”包括对证人身份信息保密、对证人容貌遮蔽、对证人声音改变等使证人不直接看见被告人的隔离方式,“隐蔽作证”在被害人做证人的案件中有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未成年被害人和性犯罪案件的被害人,他们因为已经受到伤害而对被告人有畏惧心理,采取隔离措施可以避免他们直视被告人而遭受二次伤害或产生作证顾虑。这种“隔离式”的作证方法也被称作狭义的“隐蔽作证”,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2项保护措施即为此类。而我们只重点讨论“隐名作证”的适用条件,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在被告人不了解证人的前提下,隔离式的“隐蔽作证”是在证人出庭作证时对“隐名作证”的延续,以防止证人的身份信息为被告人所知晓;二是在被告人了解证人的情况下,“隐蔽作证”之适用主要从稳定证人的心理状态出发,尽量为其创造一个平和的作证环境。同样,我们在设置隔离式“隐蔽作证”的适用条件时,只需考虑这两个方面即可。也即是,当“‘隐名作证’的证人需要出庭作证且不是必须要暴露其容貌和声音时,或者证人面对被告人存在心理障碍时”,应当对其采取隔离式“隐蔽作证”。
2.禁止特定人员接触证人
对于新刑事诉讼法第62条规定的第3项保护措施“禁止特定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而言,其并不能对证人起到实质性的保护作用。倘若犯罪行为人真有恐吓、打击报复证人之意,并不是形式上的一声禁令可以阻止的。如果是通过限制或剥夺行为人的人身自由来防止其接触证人,那又是对羁押权力的僭越。所以,我们认为,“禁止接触证人”只能在“特定人员”未被完全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作为其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得以适用。例如,我们可以明令禁止未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极其亲友接触证人;禁止已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友接触证人等。
3.专门性保护措施
“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的保护措施”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重点危险证人的人身或者住宅的贴身保护,这是立法主要的意旨;二是对作证后无法在当地居住的证人进行必要的身份更换、工作安排、居住安排、生活保障等后续工作,这是对法条的扩大化解释。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贴身保护持续时间有限,只是一种暂时性的保护措施,随时会根据案件的进展和诉讼的终结而终止;而更名、迁居等一系列保护措施带来的保护状态是持续存在的,也可以说这些措施的采取会带来一劳永逸的结果,但由于投入成本太大、证人或多或少会有些抵抗情绪等因素,所以在实践中应当谨慎采取,设置相较于贴身保护更高的适用条件。
证人的贴身保护主要适用于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重点证人,而且是有着遭受危险的 “即时的”可能性。例如有组织犯罪案件中或黑社会犯罪等案件中的证人,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中的证人,在诉讼过程中遭受到不明身份人的恐吓和威胁,或者已经受到了一定的侵害。[5]188这个时候证人的身份信息已经暴露在外,采取隐名保护等低强度保护措施已经无济于事,只有及时采取贴身保护措施,才能避免证人遭受第二次侵害。另外,在证人未遭受侵害的情况下,如果其身份信息已经被外界知晓,我们可以参照“隐名作证”适用条件中几项使证人面临“即时”危险的情形设定贴身保护的适用条件,即“证人在危害国家安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毒品犯罪以及其他暴力犯罪等案件中提供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畏罪潜逃,且有毁灭证据与恐吓证人的迹象;同案其他证人已经遭到威胁、侮辱、殴打或打击报复。”贴身保护毕竟只是短暂的,如果犯罪一方在当地势力极大,证人在长时间内面临被打击报复的危险,或是已经被采取贴身保护的证人仍持续不断地遭受恐吓、骚扰,保护机构就应当对证人采取更换姓名、迁居、安排住所和工作等一系列的保护措施了。
四、结语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颁布,而在于有效地实施。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毕竟是较为原则的,研究证人保护措施的适用条件,并无限制证人保护适用之意,而是为了使该项制度在实践中能够更具有可操作性,能够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功能。综合我国刑事司法的种种因素,可以预见,对于证人作证的相关制度能否真正贯彻执行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能盲目乐观。立法所作的努力无疑值得充分肯定,但只有司法对立法的尊崇和贯彻才能使立法具有生命力。
[1][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M].李克强,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0.
[2]欧阳顺乐.证人出庭作证四题[J].法学,1998,(3):23.
[3]郎胜.刑事诉讼法修改与适用 [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136.
[4]王兆鹏.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评析[J].法学论丛,1998,28(1):167-215.
[5]何家弘.证人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6]王奎.论人身危险性的评价因素 [J].政治与法律,2007,(3):154.
[7]马振川,陆志强.证人心理的形成及表现[M]//罗大华.中国法制心理科学研究文萃(下),北京:群众出版社,2006:882.
[8]王刚.论我国“隐蔽作证”制度的建构[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4):78.
[9]胡隽.论我国打击有组织犯罪中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9.
[10]何挺.证人保护与被告人基本权利的冲突与平衡[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3):83.
[11]葡萄牙证人保护法[J].杨家庆,译.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3):114.
责任编辑:张 艳
D925.2
:A
:2095-2031(2014)01-0024-06
2013-08-31
潘金贵(1973-),男,贵州毕节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从事刑事诉讼法学和证据学研究;李冉毅(1989-),男,重庆万州人,西南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从事刑事诉讼法学和证据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