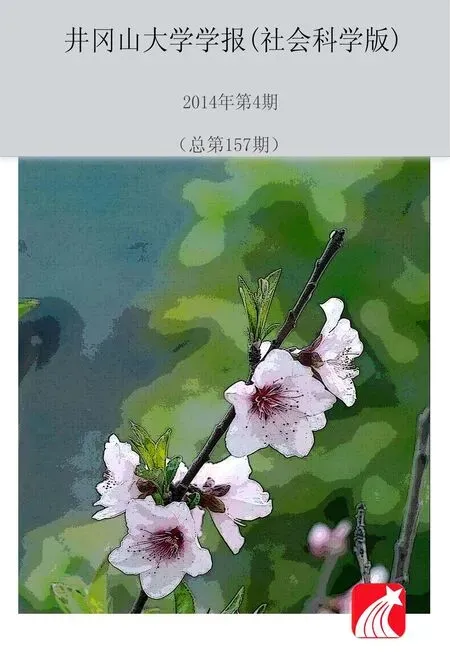宋诗话视野中的庾信诗赋
何世剑
(南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南昌江西 330031)
宋诗话视野中的庾信诗赋
何世剑
(南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南昌江西 330031)
宋人言诗之风大盛,两宋诗话中有逾30种诗话论及庾信及其诗赋,代表了宋人对庾信诗赋的接受程度。宋诗话视野中的庾信诗赋接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探讨庾信诗赋的写作技法、比较论析庾信与其他诗人的写作优劣;二、考察唐以来诗家接受庾信的表现、摘赏庾信诗歌佳句,推溯“徐庾体”的渊源流变及评鸷庾信诗赋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
宋诗话;庾信诗赋;接受;写作技法;审美经验
庾信是六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在南北文化交流、魏晋南北朝文学向隋唐文学演进中起了关键作用,他的诗赋创作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后世对庾信及其诗赋的接受,大致奠基于隋唐,演进于宋金元,兴盛深化于明清,转型于近现代[1]。
宋代作为庾信及其诗赋接受的发展演进时期,有着传承和衍化的意义,在整个庾信诗赋承传接受历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两宋时期,言诗之风大盛,诗话的诞生、崛起,促进了对于前代诗歌写作经验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宋诗话中有逾30种诗话论及庾信及其诗赋,内容涉及:探讨庾信诗赋的写作技法,比较论析庾信与其他诗人的写作优劣,唐以来诗家对庾信的接受表现,摘赏庾信诗歌佳句,记叙庾信诗歌轶事,诠释庾信诗句僻典,推溯“徐庾体”的渊源流变,评鸷庾信诗歌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等诸多方面,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宋人对庾信诗赋的接受概貌、深度和水准,对于了解宋人对待庾信及其诗赋的态度,把握宋代诗家从庾信诗赋中接受了哪些写作养分,认识庾信及其诗赋对于宋诗发展成型的影响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细加论析。
一、探讨庾信诗赋的写作技法
宋人在诗话中对庾信的诗歌艺术创作经验有所体认,发掘了庾信的诗歌构思经验、写作技巧、诗学经验。特别是对庾信在诗歌的用字、遣词、比兴、使事、用典、对仗、声律、结构、风格等方面对诗歌发展所作的开拓性贡献进行了细致论析、阐说,为后人对庾信的创作成就及庾信诗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认识和评价积累了学理经验。
(一)阐精发微,对庾信写作技法的考索
宋诗话在“论诗及辞”时,对庾信用词、用韵、用典、对偶等写作技法有所考察。宋代吴聿《观林诗话》说:“庾信《鸳鸯赋》云:‘昔有一双凤,飞来入魏宫。今成两株树,若个是韩冯?’盖符中切。半山蝶诗云:‘岂能投死为韩冯。’乃皮冰切。”[2](P1094)指出了庾信与王安石用“韩冯”典时“字韵”的不同。胡仔《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五“半山老人”说:“《复斋漫录》云:《西清诗话》:荆公《赏花钓鱼诗》‘披香殿上留珠辇,太液池边送玉杯。’都下人以公用柳耆卿:‘太液波翻,披香帘卷’之句。余读唐上官仪《初春诗》云:‘歩辇出披香,清歌临太液。’乃知荆公取仪诗,岂谓柳词邪!庾信《暮春诗》云:‘宜春苑中春已归,披香殿里作春衣。’长安有宜春宫,此又以宜春对披香矣。”[3](P179)一方面指出了在诗歌对偶、用词、意象上,庾信与上官仪、柳耆卿、王安石的细微区别;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上官仪、王安石、柳永与庾信诗词之间存在的“互文”关系,上官仪、王安石、柳永之词当受到了庾信诗歌的启发,承传了其审美经验。宋代许多诗话在论析“咏妇人多以歌舞为称”写作传统时,也引用庾信《和赵王看妓诗》“绿珠歌扇薄,飞燕舞衫长。”指出要描写妇女、美人,不必直接对其相貌进行白描,而是通过写其歌舞姿态力加烘托,此不失为一种可取的表达方式。
宋代吴幵《优古堂诗话》“石燕泥龙”条说:“周庾信《喜晴诗》:‘已欢无石燕,弥欲弃泥龙。’又《初晴诗》云:‘燕燥还为石,龙残更是泥。’此意凡两用,然前一联不及后一联也。乃知杜子美:‘红饭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斡旋句法所本。”吴幵首次指出杜甫接受了庾信创辟的“斡旋句法”。所谓“斡旋句法”,乃指为了句式对仗、押韵等需要,或作者有意突出所要表达的意象,而将主要意象前置,变换、打破传统诗歌写作结构,转而采用拆分、倒装的手法重新结构,从而产生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应。杜甫“红饭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在写作技法上完全承袭了庾信诗法经验,相比而言,杜甫之诗更具审美意蕴。庾信创新性地开辟了“斡旋句法”,而杜甫则接受并运用成熟。
(二)推源溯流,对庾信审美经验的掘发
在中国诗歌发展进程中,六朝人善于开掘意象,塑造名句,从诗家评谢灵运、谢脁等“六朝人有句无篇”可见一斑。前代诗家努力开掘审美意象,积淀了丰厚的审美写作经验。后起诗家在传承基础上踵事增华,才培植出色彩纷呈、令人炫目的中华诗歌花园。中国诗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正是因为其有着深厚的“接受”传统,后代诗家对前人审美写作经验的自觉接受传承,才推动它一步步前进。
庾信无疑是六朝诗歌中善于创作名句的优秀诗家之一。这一方面缘于他的天赋、学识及写作锻炼所累积的功力,另一方面也在于他善于虚心地接受前代的审美经验,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涵咏承传。宋诗话细致考索、梳理、论析了庾信对前代如阮籍、潘岳、孙兴公、陶渊明等的接受,对后世把握庾信审美经验渊源、诗学生成等有很大的帮助。如宋吴聿《观林诗话》说:“孙兴公《天台山赋》有‘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而界道’之语,为当时所推。后庾信数用其语,作《玮禅师碑》云:‘游极箕张,建标霞起。’又《襄州凤林寺碑》云:‘干霄秀出,建标霞起。’”[4](P134)指出庾信曾句袭、化用孙兴公《天台山赋》名句,客观地把握住了庾信自觉的审美接受意识。的确,庾信之所以能在诗歌上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绩,成为六朝文学“集大成者”,乃在于他善在前人基础上演绎、创变,既传承了前人的审美写作经验,同时又融入了自己的主体实践、个性情趣和美学品味,成为中国诗学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当然,接受还关系到读者自我的审美趣味、鉴赏能力等诸多方面原因。即使对于久负盛名的庾信,在宋诗话视野中也不都是持肯定态度,也有一些批评家将庾信与六朝其他诗家进行比较,认为庾信的写作技艺比一些诗家稍逊一筹。《竹庄诗话》卷二十三说:“露滋寒塘草,月缺清淮柳。夜雨滴空阶,晓灯照离室。幽槛弄晩花,清池映踈竹。疎树翻高叶,寒流聚细纹。《东观余论》云:‘古人论诗但爱逊云云,(前两联)为佳,殊不知逊秀句若此者多,如云云,庾子山辈有所不及。’”何汶在品赏何逊诗时,引黄伯思之语对庾信与何逊加以比较,认为庾信远不及何逊善于创作秀句。从整个诗歌的发展趋势来论,生活于六朝末期的庾信,虽然也注重于雕章琢句,但是他已经不再像何逊等人一样注重于单独炼某一意象、某一句式,而是开始逐渐地过渡到整篇诗文意境的开掘、营构。庾信等人的诗歌在意境等方面有其独到之处,正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前人的创作观念、写作经验,又有所创新,才克服了中国诗歌“有句无篇”的缺陷。到唐代时,在诗歌领域,才确定了整体“意境”上的交融合一为最高目标的写作范式。虽然何汶等人指出庾信在创作方面的不足,但总体来讲,宋人对庾信的创作成就、写作水平还是持肯定态度,他们接受庾信诗学经验甚多。
二、考索唐以来诗家接受庾信诗赋的表现
推溯诗家、诗句的渊源流变是接受诗学的重要表现之一,也是宋代诗话赏诗、论诗、评诗的重要内容之一,渊源批评成为了宋人接受庾信的最有力表现。“以才学为诗”的宋人,胸中储藏了丰富学识,如欧阳修、黄庭坚、刘克庄等人都“学富五车”,他们基于自己的学识才力,经常性地将自己在品诗、谈诗、评诗时对前代诗人诗学来源、学诗得失的考索及体认写入诗话中。考察宋代诗话,可以较为明晰地把握住后代有哪些诗人的诗歌创作出自庾信诗学“知识谱系”,认识处于这一“谱系”中的诗人所处的不同位置、接受庾信的格局大小、承传庾信诗学因子的表现强弱。
从整体文风演变、接受思潮来讲,宋代诗话对唐初以来接受“徐庾体”诗学思潮的概貌、流变、接受者及其表现,多有论析,立言甚著。
宋代诗话论者大多认为,初唐诗人普遍接受了“徐庾体”诗风,徐陵、庾信的诗文作品在唐初直到盛唐都非常流行,成为了这一段时间中创作摹仿的主要对象。在宋人看来,“徐庾体”诗文浮靡俚俗,不值得学习,所应该学习的是“陶谢”之诗、“建安七子”之诗。如宋胡仔《渔隐丛话前集》卷一说:“《诗眼》云:唐诸诗人,高者学陶谢,下者学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韩退之,早年皆学建安,晚乃各自变成一家耳。”宋人,特别是南宋诗评家几乎全盘否定了徐庾诗文及初唐诗歌对中国诗歌发展的贡献和意义。正是杜甫、李白、韩愈等取法甚高,追步“建安”,加以锻炼,最后才自成一家,逐渐扭转了初唐以来学“徐庾体”的文艺风尚,真正确立起唐代的诗歌精神。宋人看重的恰是这种体现了“盛世风流”的诗学精神。南宋人之所以会对“徐庾体”诗风如此反感,在于他们机械地看待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盛唐诗歌之所以美,在于它表现了强盛时代的气势、格调,诗歌中蕴涵着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这种诗歌能激励人的竞争斗志,激发人的创新精神,使社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气势;而“徐庾体”则是亡国之音,梁、陈之所以灭亡,就在于这两个朝代的文人鼓吹绮靡浮艳之音,扰乱了国人的心思,使国人懦弱不振。这种观念受《礼记·乐记》和《荀子·乐记》的深刻影响。
宋人对“徐庾体”大加贬抑,与南宋以来国力衰弱的政治文化语境密切相关。南宋末期诗论家,如张戒、刘克庄等,均倡导追求“建安风骨”,而把“徐庾体”作为批判对象。他们在梳理诗歌源流时,号召时人学诗“入门须正、取法乎上”。为激励士人精神,给文坛注入生机和活力,严羽等强调要保持主体诗性自由,批判了“江西诗派”秉持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创作论。张戒更甚,他在《岁寒堂诗话》中苛责“六朝颜、鲍、徐、庾,唐李义山,国朝黄鲁直,乃邪思之尤者。”其目的亦在发挥诗歌的“言志”、“载道”等诗教功能,以重建诗统、文统、道统。计敏夫等对于经过了陈子昂、李白等人复古变革“徐庾”诗风后所盛行的“雅正”诗风均较为欣赏,如他在《唐诗纪事》卷八“陈子昂条”说:“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子昂始变雅正,为《感遇诗三十八篇》。”反映出计敏夫对“徐庾”诗风也持批评态度。
当然,也有些诗评家能辩正地看待“徐庾体”的得失,客观地认识后人对“徐庾体”的接受。“徐庾体”的生成有其特殊原因。在六朝末期的出现,并流行一时,还波及初唐、盛唐,有着历史的因素,是诗文走向审美自觉的要求。优秀的诗人不仅是摹仿前人的名作,从中寻找养分,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他们能在接受的时候发现前人的弊端,然后加以改进。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说:“唐初尚矜徐庾风气,逮陈子昂始变,若老杜则凛然欲方驾屈宋,而能允蹈之者。”在朱弁看来,只有像杜甫这样的诗家,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大家。他既能够把握徐庾体的不足之处,又能够吸收其中的精华(“允蹈之”)。在当时“江西诗派”普遍模范杜甫,缺乏创新之见时,朱弁等人通过思考前朝诗人接受“徐庾体”的得失而把握到只有接受远远不够,重要的是创新、是新变。计敏夫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肯定了富嘉谟等变易“徐庾体”而创“吴富体”的价值[5](P99)。故在“富嘉谟”条指出:“时天下文章尚徐庾,浮俚不竞,嘉谟、少微本经术,雅厚雄迈,人争慕之,号‘吴富体’。”
从单个诗家对庾信的接受而言,宋诗话对唐以来诗家对庾信的接受表现辨析入微,其中涉言初唐四子、李白、杜甫、李商隐,宋西昆诗家、黄庭坚及“江西诗派”等接受庾信居多,以杜甫为极致。而唐白居易、杜牧、温庭筠,宋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等次之,温庭筠、苏轼相对略胜一筹。以诗赋文本而论,后代接受庾信后期创作多于前期创作,诗赋多于文(包括杂文体的表、碑志、铭、赞等),这与诗话以论诗为主相关。
宋诗话在考索后人对庾信诗赋的接受时,就传统的一些接受观念进行了争辩,加深了我们对于“诗学接受”的认识、理解。自孟子提出“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论说以来,后世对此多直接接受。他们对待诗人与诗作之间的关系非常严格,认为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语境下,有什么样性质气质、人生经历的作家,就必然有与此直接对应的作品产生。也就是说,他们都把作品的生成看成是社会影响和作家主观创作的结果。其实,这种理念是不科学的,它忽视了读者“接受”的特性。宋计敏夫《唐诗纪事》卷十四“宋璟”条说:“皮日休《桃花赋序》曰:余常慕宋广平之为相,正姿劲质、刚态毅状,疑其铁肠石心,不能吐婉媚辞,然观其文而有《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之体。”[6](P522)皮日休首先指出宋广平《梅花赋》有“徐庾体”风,对于“风格即人”论断多有异议,已经开始批评严格将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特性作直接地、机械地联系。也就是说,从作者的角度讲,徐庾等人创建“徐庾体”诗文范式,并不一定是出于他们软弱的个性。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讲,并不一定非得是性格偏软的人才能学习“徐庾体”。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宋代诗话并不满足于仅仅征引辑录皮日休的这一论断,宋人还对此展开了争辩,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态度。有如计敏夫者,仅作辑引不置一评;有如晁无咎者,支持而申论;亦有反对而辩驳者,如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六说:“皮日休尝谓宋广平正资劲质,刚态毅状,宜其铁肠石心,不解吐婉媚辞。然其所为《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殊不类其人……审尔则唯铁肠石心人可以赋梅花,与日休之言异矣。”[7](P158)葛氏显然不同意皮日休之论,他认为惟有“铁肠石心人”才能穷梅花之韵,把握并写出梅花“高格”。从宋诗话中,我们不仅体认到宋广平接受了庾信的写作之风,而且加深了对于“接受”的认识,也即学“徐庾体”者,不必严格地以“读者性格”论。它的意义体现在,不能仅根据后人与庾信相似的、同主题的作品,就判断他们对庾信作了接受,而是应该视他们为审美经验、写作经验的传承者,将他们的创作与庾信的创作,乃至前人的相关创作整合起来。从宋诗话对“宋广平接受徐庾体,为《梅花赋》”一事的辨析中,也可以认识到“读者接受论”理论本身的弊端,因为“读者”本身就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使得大多数的“接受”成为捕风捉影的一种表现,难以证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期的接受美学将“接受”视作为“人类交往对话”中“审美经验”的一种传接的原因。
宋诗话辨析梳理了庾信所开发的一些“意象”的流传接受情况。庾信可称得上是李商隐之前的“意象”写作大师,他凭借高超的写作技艺,开掘了许多意象,如“桑落酒”、“小园”、“枯树”等等,都非常经典,宋人对此把握得非常到位。如宋胡仔《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一“香山居士”条说:“《后史补》云: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时,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酿酒,甚佳。故号‘桑落酒’,旧京人呼为‘桑郎’,盖语讹耳。庾信诗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8](P141)庾信首度在诗歌中写“桑落酒”,上句出自他的《从蒲使君乞酒》诗。他还有不少诗歌用了“桑落酒”这一意象,如《卫王赠桑落酒奉答》说:“愁人坐狭斜,喜得送流霞。跂窓催酒熟,停杯待菊花。霜风乱飘叶,寒水细澄沙。高阳今日晩,应有接离斜。”上两首诗主要表述了诗人穷而借酒消愁,以得其乐的境况。庾信入北后,生活确实非常不幸福,他常常过着一种诗酒生活,通过喝酒、作诗来排解他心中的苦闷。在庾信那里,愁是最深重的愁,酒是坊间酿造的美酒,酒入愁肠,呼出一篇篇悲美诗文,给了后人不少的刺激。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刘敞、晁补之、李彭、王洋、王庭珪、周紫芝、楼钥、洪适、杨万里、韩元吉、施枢、陈着、董嗣杲等人都沿袭、开掘此意象,胡仔在此首先考辨了“桑落酒”典实的来源,并指出白居易诗曾接受了庾信的“桑落酒”意象。后人在接受庾信开掘的意象时,有时一诗二联中的所有意象都取法自庾信,有时又将庾信诗歌意象与其他诗人创作的经典意象相互杂糅。如胡仔《渔隐丛话后集》还载言,“《复斋漫录》云:……子由和云:‘饮食逢鱼蠏,封强入斗牛。’予观其意,上句取杜诗‘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鱼入馔来。’其下句乃取庾兰成‘路已分于湘汉,星犹看于斗牛’也。”[3](P249)指出苏子由诗乃衍化、合用杜甫及庾信诗歌意象。胡仔对于庾信诗文非常熟悉,他对于唐宋以来诸诗人对庾信的接受表现多有发掘,辨析、申论之,有助于后世把握庾信诗学接受“谱系图”。
宋诗话不仅发掘了后人诗文中“意象”与庾信诗文“意象”之间的联系,而且努力梳理后世诗家接受庾信诗学之间的渊源流变,从而将各诗家与庾信之间存在的“知识谱系”关系理清晰。接受就其实质来说,是思想、精神、技艺、知识的传承。探讨与“接受”相关的问题,主要在于把握“知识”传承中,何者为创,何者为继,让我们明白谁对中华文化的建设做了什么样的贡献?从他们身上可以继承什么样的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的确,创新对于文化发展来讲,至关重要。但是假如没有后世读者的传承接受,也就显现不了创作者的价值。对于中国文学来讲,同样如此。假如没有庾信在诗歌句法、意象等方面的开发,没有后人对庾信写作经验的接受,也就很难想象中国诗歌会变化到怎样一种程度。宋诗话在庾信诗学知识谱系的梳理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给后世绘制了一幅清晰的庾信诗赋传承接受图表。举一例来说,宋吴幵《优古堂诗话》中“授图黄石老,学剑白猿翁”条说:“《潘子真诗话》云:杜牧之《题李西平宅》云:‘授图黄石老,学剑白猿翁。’庾信作《宇文盛墓志》,所谓‘授图黄石,不无师表;学剑白猿,遂传风旨。’然余读李太白《赠宋中丞诗》云:‘白猿惭剑术,黄石借兵符。’则太白亦尝用之矣。”吴幵不仅引证了潘子真对杜牧句袭庾信的体认,进而指出李白也有接受庾信的“即旧为新”行为,这让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庾信、李白、杜牧,甚至是潘子真、吴幵之间的联系。刘克庄《后村诗话》卷十二说:“庭筠与商隐同时齐名,时号‘温李’。二人诗记览精博、才思流丽,其浮艳者类徐庾。”[9](P8510)刘氏从诗歌生成、诗风表现方面,指出“温李”浮艳之诗接受庾信颇多。刘氏本人不以庾信南朝诗赋为喜,在诗话及其它诗文中对庾信颇有异词,特别是对“徐庾体”,多大肆鞭笞,《落花怨十首》其八说:“徐庾空浮艳,何曾有一篇。”(《全宋诗》卷3075)《杂咏七言十首》其一说:“宁草两都卿云赋,不作六朝徐庾诗。”[10]但刘克庄受其父的潜移默化,也接受了庾信不小的影响[11]。特别是身处连年战乱,民族矛盾激化的南宋末世,在这种惨淡萧瑟的为诗境域下,矛盾的他也不得不周旋于王褒、庾信诗文中,寻找诗歌共鸣。如其《杂咏七言十首》之一说:“周旋王庾二公际,传授并汾诸子问。”[10]他承认自己也和陶渊明、庾信一样,他们诗歌成就的取得,不仅关乎时代、环境,也关乎是否能“得江山之助”,尤其重要的是靠自己努力写作,把自己的最本真的情感表现出来。其《送叶制参》说:“晋朝陶庾辈,岂必靠江神。”在南宋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刘克庄想的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诗歌创作,一方面安顿自己的心灵,另一方面也激励世人,从现实困境中走出来,少发“满纸烟云”之论,多写有关风化之诗。
宋代诗话作为庾信诗赋接受史中的重要一环,为庾信诗赋及写作经验、艺术特色的爬梳整理、细致体认及承传阐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辩证地讲,宋诗话接受庾信诗赋主要体现在:第一,这些经验认识大半出于偶感随想,充满了诗性智慧和感性精神,它们以轻松灵动、充满趣味的笔调,揭示了庾信在比兴、用事、对仗、声律、结构、句法等方面的创作经验,虽为一得之见,却往往切中肯綮。第二,他们以庾信及其诗赋作为六朝诗学典型,进行了品评赏析,采用了文本细读、心理学、社会学、形式论等多元方式,去发掘庾信诗歌在语言美、形式美、格律美、文化美等方面的独到内涵和潜隐规律,同时指正了庾信创作的讹误和“徐庾体”的缺失,彰显了宋人充满理性思辨的审美心理和重学尚文的文化精神。宋诗话接受庾信诗赋之失主要体现在:第一,这些品评偏重主观,零乱琐碎,不成系统,有的认识缺乏科学性、严肃性,“误读”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也是运用“诗话品诗”方式探索其中偏失、稚嫩的一种表现。第二,不少关于庾信诗赋的品评陈陈相因,缺乏新义,互相抄袭,以讹传讹;搜奇记异,失于考据,流于浅俗,其美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并不突出。
当然,宋代诗话在考索诗学渊源流变之时,对后世接受庾信多有发掘,作为一种诗学知识的钩沉、梳理,奠基了他们的写作才力,考索、体认及批评也有益于加深他们对庾信诗学成就的细部把握。从方法论意义讲,“江西诗派”正是沿着杜甫导始,黄庭坚自觉实践这一接受庾信知识资源以生成诗歌(“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式庾信接受表现之一)线路向前行进,直到吕本中、杨万里等人“活法为诗”时才有所放弃。对庾信作知识谱系考察,也有助于他们的写作,庾信诗赋因此成为他们创作源泉之一,如刘克庄等江西诗人,虽然对庾信颇有微辞,但从江西诗派的作品来看,其写作素材、主题、意旨乃至诗歌整体风格生成,都受到了庾信的影响。
综上可见,宋代诗话视野中对于六朝文学集大成之作家庾信诗赋的写作技法进行了细致探讨,比较论析了庾信与其他诗人的诗赋写作优劣,记载和反映了不少唐以来文人对庾信诗赋的接受态度、审美认知,让后人对庾信诗赋的接受情况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从宋诗话中还可以辑录出不少庾信散佚的诗文,有助于后人更为完整地把握庾信的创作情况。
[1]何世剑.论庾信诗赋在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接受与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8.
[2][清]倪璠.庚子山集注[M].许逸民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0.
[3][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M].廖德明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4]常振国,降云.历代诗话论作家[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5][宋]计敏夫.唐诗纪事:卷十四[M].王仲镛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7.
[6]周勋初.唐人轶事汇编(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M].廖德明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9]吴文治.宋诗话全编[M].南京:凤凰出版社,1998.
[10][宋]刘克左.后村先生大全本:卷三十九[M].四部丛刊本.
[11][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卷八[M].四库全书本.
Yu Xin's Poetry and Parallel Prose in Perspective of Song Poetry-criticism Notes
HE Shi-jian
(School of Arts and Design,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1,China)
Scholars in Song Dynasties took great interests in criticism of poetry.Among the many Poetrycriticism notes written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ies there were more than 30 books discussing Yu Xin and his poems¶llel proses,which signals Song scholars'acceptance of that ancient poet. Discussions of Yu Xin's poetry and parallel proses in the scholars'poetry-criticism notes mainly consist of two aspects:the first is examination of writing skills in Yu Xin's poems and parallel proses and comparison of Yu Xin and other poets in this respect;the second is survey of the acceptance of Yu Xin since Tang Dynasty,digests of Yu Xin's memorable beautiful words,exploration of the stream of Xu-Yu style,as well as the position of Yu Xin's poems and parallel proses in Chinese history of poetry development.
Song poetry-criticism notes;Yu Xin's poems and parallel proses;writing skills;aesthetic experience
I206.2
A
10.3969/j.issn.1674-8107.2014.04.018
1674-8107(2014)04-0112-06
(责任编辑:刘伙根,庄暨军)
2014-03-1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典赋学批评理论的承传接受研究”(项目编号:12CZW015);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青年项目“庾信诗赋承传接受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43)。
何世剑(1979-),男,江西萍乡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论与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