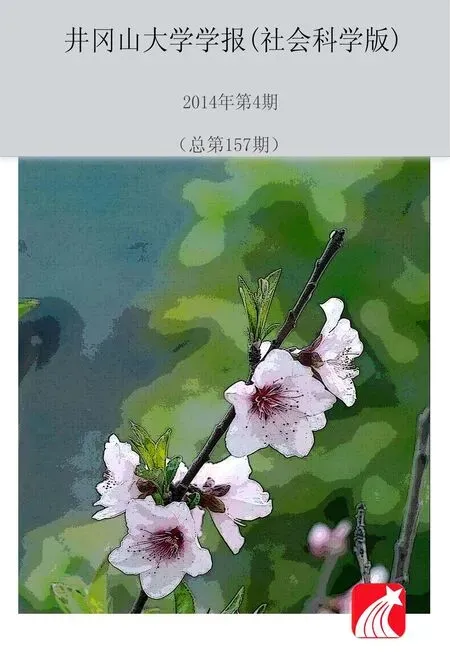中国社会救助制度:从仁慈到正义之路
张浩淼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中国社会救助制度:从仁慈到正义之路
张浩淼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与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内涵在不断拓展变迁,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传统的救灾救济阶段、以城市反贫困为主的改革阶段和城乡统筹、逐步定型规范的阶段。在社会救助制度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制度名称从“救济”转为“救助”,制度内容从单一生活救助向综合救助过渡,获得救助从接受恩惠转为公民权利,提供救助从道义扶助转为政府责任,这些均意味着制度的精神动力和道德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仁慈逐步迈上了正义之路。然而,目前制度的发展完善还任重道远,但可以肯定的是正义作为中国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道德根基和精神动力的终极目标是不会改变的。
社会救助制度;仁慈;正义;救济;救助
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与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内容和体系经历着发展变迁,这一过程是不断与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过程。然而,对社会救助制度不能仅从经济层面或政治层面或社会结构来探讨,还应关注制度的道德伦理层面,这才有助于弄清支撑社会救助制度发展变迁的精神动力。从这个层面看,建国以来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演进是从仁慈走向正义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引人入胜之处不在于其轰轰烈烈,而在于其平淡从容地经历了质的飞跃,使中国在不知不觉中走出了很长一段路程。
本文通过梳理建国以来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历程,以深刻理解社会救助制度内容和体系的变化并考察和解释制度是如何逐步从仁慈迈上正义的道路,进而对制度的未来发展进行初步探索。
一、社会救助制度:发展历程回顾
目前已成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中基础性制度的社会救助,为陷入贫困和其他生活困难的社会成员在基本生活权利方面提供着安全保障。它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穿越了不同的时代,经历着发展变迁。总的来看,建国以来社会救助制度的演变可以大体划分为三大阶段。
(一)传统的救灾救济阶段
建国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开展,逐步形成了由救灾和城乡救济为主的社会救助模式。
建国初期,面对众多遭受贫困、饥饿和灾害的群众,党和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紧急救助工作,拨出了大量资金和物资实施应急性的救灾和救济,促进了新生政权的巩固与城乡生产的恢复。从1953年起,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社会救助也开始从突击、大规模的紧急救助逐步走上了正常化轨道。[1](P53)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城市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均在单位工作,形成了以就业为基础的单位社会保障制;在农村,农民则由生产队负责,形成了以社队集体为单位的集体社会保障制。这样,城乡救济的对象主要是极少数的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和无依无靠的群体以及一部分被排斥在单位或集体保障体制外的特殊群体。此外,农村还针对“三无”群体建立了“五保”供养制度。“文革”期间,城乡救济被看成给社会主义抹黑,成为了批判对象,制度发展受到了影响,但是党和政府仍一定程度地坚持了对灾民的灾害救助工作,对帮助灾民度过荒灾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1](P55)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实施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一直到90年代初,中国的单位保障制仍在延续,主流环境也尚未脱离计划经济,所以社会救助方式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主要是恢复落实原有的城乡救济并开始兴办救济性事业以及农村的扶贫经济实体。此外,随着农村流动人口问题的突出,1982年确立了针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容遣送制度。
尽管这一时期社会救助工作在不断调整中,但总的来看,其构成与内容比较简单,主要由救灾及城乡救济制度构成。救灾主要针对灾民,城乡救济主要针对“三无”人员和贫困户,覆盖范围很窄,其中“三无”人员比较固定,可以获得定期定量救济或“五保”供养,而贫困户则时常变动,获得的主要是临时救济。这种传统的救灾救济制度的救济标准非常低。
(二)以城市反贫困为主的改革阶段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到2006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经济社会的急剧转型,社会救助制度处于以城市反贫困为主的改革阶段。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后,单位保障制逐步瓦解,再加上大规模的下岗失业,城市贫困问题突显出来。面对严峻的城市贫困状况,走在经济转型最前列也最先感受到转型所带来的巨大压力的上海市于1993年最早实施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拉开了中国社会救助改革的序幕,此后不少城市纷纷效仿。中央政府在继续沿用“送温暖活动”、“年节慰问”等临时救济方式帮助城市贫困群体并未产生多大效果后[2](P65),最终把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摆上了议事日程:1997年9月2日,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指出1999年底以前县级市和县政府所在地的建制镇都要建立起低保制度;1999年9月末,在全国城镇提前完成了建制任务的时候,国务院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这标志着城市低保成为全国性的制度安排并步入了法制化管理的轨道;随后,城市低保经过“应保尽保”和“分类施保”,不断发展完善,到2006年保障人数已达到2240万,与1999年比增长了近9倍。①数据参见民政统计年鉴。通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完善,贫困群体的温饱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但贫困家庭医疗难、子女上学难、住房条件差、打官司难等问题仍比较突出,所以2003年后,各地开始了医疗、教育、住房、司法等专项救助制度的探索。此外,2003年国家还废止了已经异化的收容遣送制度,代之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实现了从管制到救助的变化。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社会救助制度的内容和构成出现了重大变革,这种变革主要体现在城市反贫困的救助方式上,即从原来的传统救济转变为最低生活保障和探索中的各类专项救助,新救助方式的覆盖范围大为拓宽、救助标准也有很大提升。虽然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在探索建立的过程中,但由于中央政府既无政策投入也无资金投入,传统救济和扶贫开发仍然在农村的救助方式中居主导地位。
(三)城乡统筹、逐步定型规范的阶段
2007年起,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推进,社会救助制度进入了城乡统筹、逐步定型规范的新阶段。
2007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承诺年内要在农村地区全面建立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中央政府的推动和资金支持下,截至2007年6月底,全国31个省(区、市)已全部初步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②参见“专访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农村贫困人口将怎样纳入低保”,《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08-20,第5版。,随后7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对农村低保进行规范和指导。2007年末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健全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其后,一方面农村低保制度不断完善,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医疗、教育、住房等专项救助也在探索中不断健全,社会救助向着城乡统筹的方向迈进;另一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社会救助作为托底性的社会政策受到了高度重视,《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已经于2013年末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在2014年颁布,这意味着社会救助制度开始逐步定型规范。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社会救助制度的内容和体系逐步定型,主要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和灾害救助制度为基础,以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专项救助和临时救助为辅助,向管理规范、覆盖城乡的方向发展。
二、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进步:从仁慈迈上正义之路
通过对社会救助制度发展历程的回顾,可以发现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内涵在不断拓展,走出了一条稳健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发展道路,这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进而不断满足群众生存需要的过程,也体现出党和政府从为维护社会稳定到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不懈努力,更重要的是,制度发展背后的精神动力和道德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仁慈迈上了正义之路,这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解释:
(一)制度名称从“救济”转为“救助”
建国后,中国政府在制订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时,均将social assistance(社会救助)一词本土化地译为社会“救济”,欲寻求与中国历史上的既存“救济”相统一。[3](P73)在古代中国,“救济”一词意味着对灾民及特殊困难群体进行临时帮助以维护稳定和统治秩序,它强调的是一种消极的救贫济穷措施,基于同情与仁慈的心理,多是临时的及随意性很强的救济行为,所以,不难理解在制度名称为“救济”的时期,支撑制度的道德基础是一种仁慈、恩惠的理念。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学术界开始对西方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理论有了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广泛使用“救助”一词;之后,官方也受到了影响,2002年国务院发表的《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中还把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内容之一称之为社会“救济”,而2004年国务院发表的《中国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白皮书就发生了变化,改称为社会“救助”。另外,主管这方面事务的民政部的相关部门也从“救灾救济司”拆分为“救灾司”和“最低生活保障司”,后者又逐步发展为“社会救助司”。“救助”一词最早是西方社会工作者针对“济贫”这一类代表旧的伦理思想的旧概念而提出的新概念,强调提供制度化的救助措施是政府的责任和受助者应得的权利[4](P207),正义在于应得或权利,实现和维护权利就是实现正义,所以,在制度名称为“救助”的时期,支撑制度的道德基础是正义的理念。制度名称从“救济”转为“救助”,表面看来似乎在玩文字游戏,但实质却是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道德基础和精神动力从仁慈转向正义的真实写照。
(二)制度内容从单一生活救助向综合救助过渡
社会救助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仅提供单一的生活救助,集中关注于满足困难群体最基本的吃穿需要,标准比较低,甚至还曾以“不饿死人”为标准,这其实透露出制度背后仁慈、慈善的理念,因为仁慈是一种源于怜悯之心的道德情感,天然带有恩惠、施舍的色彩,其道德理由只能从施与者那里产生,而非需要帮助的对象那里产生,所以它往往导致受助者利益需要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被忽视。[5](P5)现代社会里,困难群体合理与正当的生存需要其实早已经不再仅仅是吃和穿,而是还有医疗、教育和住房等需要,以保持最基本的“人”的尊严,所以困难群体除了生活救助外,还需要医疗、教育、住房、就业、临时等救助制度的帮助,中国社会救助制度逐步向综合救助方向的努力意味着制度开始关注困难群体的应得和需要,以保证弱势群体能够分享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这其实正体现了制度背后精神动力的变化,即从仁慈向正义的转变。
(三)获得救助从接受恩惠转为公民权利
在传统救灾救济的阶段,劳动是人生的重要价值,有劳动能力的人在当时的全面就业体制之下都有单位或社队集体,可以获得单位保障或集体保障,所以救助对象主要是没有能力自立的“三无”人员等少数人群,这些人在个人归因贫困观的影响下,对社会、对国家更多是一种义务感,把获得救助看成是接受恩惠,当拿到救助时会感激不已,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救助方式背后的潜在的精神动力是天然具有恩赐、怜悯色彩的仁慈;另外,由于仁慈作为一种善心和情操,是不固定、不经常的[6](P9),这也是城乡救济为何在“文革”期间遭受重创、被迫中断的重要原因。当制度进入了以城市反贫困为主的改革阶段后,因下岗失业、贫富差距拉大等各种社会问题,贫困观念由个人归因逐步变为社会归因[2](P51),获得救助逐步成为了一项基本的公民权利。1999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第2条规定: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均有从当地人民政府获得基本生活物质帮助的权利。2003年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给予流浪乞讨者向救助站求助的自由,规定他们的合法权益不能侵犯,体现了对这些人权利的尊重。2013年末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草案)》规定了公民享有申请和获得社会救助的权利。权利和法度是正义的基本语义[5](P6),所以可以说社会救助的道德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从仁慈向正义转变。
(四)提供救助从道义扶助转为政府责任
传统救灾救济的阶段,政府更倾向于提供一次性的救济,这些救济通常在一些重要节日发放,临时救济的范围广、人数众多,被看成是中国社会救济的重要方式。此外,救济工作还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临时救济对象一般没有规定标准,国家拨的救济款多就多发点,国家拨的救济金少就少发点,至于是否能满足维持救济对象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那就很难顾及。[1](P62)这种方式表明提供救助在政府看来仅是一种道义扶助,其背后潜藏着仁慈、怜悯的道德基础,因为仁慈的道德理由源自施与者而非需要救助的对象,所以导致根据既有经费来确定救济人数和标准,而不是根据困难者的需要来提供经费;另外由于仁慈是不经常、不固定的,所以临时救济才会成为救济的重要方式。在不少城市开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试点探索后,中央政府对提供救助是道义扶助的固有观念仍未改变,继续着“送温暖”等救助方式,直到1999年城市低保制度正式确立,提供救助才逐步转变为政府的责任。这种责任既体现在相关法律政策方面:比如1999年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2003年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2007年的《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以及2013年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草案)》等都反映了政府的责任意识;也体现在资金保障方面:比如1999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明确规定最低生活保障所需资金由地方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专项管理、专款专用。同一年,为了帮助财政困难地区更好地满足困难群体的最基本生活需要,中央政府开始对制度进行补助且比例逐年提高,2003年以来一直占总资金投入的60%左右。①相关数据参见民政统计年鉴。提供救助成为政府责任,意味着制度背后的道德基础已经变成了强调法度、约束性和维护权利的正义。
三、结论与展望
社会救助以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基本生活权利为目标,它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概念范畴,不同国家由于社会经济、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各国政府实施的社会救助制度也呈现多样性并存在明显的差异。考察西方国家社会救助制度的变迁历史,可以发现这些国家的社会救助工作大多起源于教会等民间组织的慈善活动,是一种不固定的、非经常化的慈悲之举,进入工业化时代后才逐步发展成为政府的行为和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成为一种固定的、经常化的正义公理,其间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所走的道路恰恰是起于仁慈,止于正义。对中国来说,改革开放后的快速转型与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使中国正在经历着巨大的转变,这期间社会救助制度也顺势而变,其内容、体系均产生了重大变革,从伦理道德的层面看,这种变化与西方类似,是从仁慈到正义的转变,只不过这一过程被浓缩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虽然仁慈和正义两者都充满着人性的光辉,但仁慈只是善心与善行并天然具有恩惠、施舍这样一种不平等的色彩,而正义才是制度化的公理,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制理念。[6](P10)由此,从伦理道德层面考察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变迁是考察中国现代化程度的一个绝佳角度,而支撑社会救助制度的精神动力从仁慈到正义的转变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然而,目前还必须认识到中国的社会救助制度虽然已经从仁慈迈上了正义的道路,但是不少地方仍然通过道德评判等方式设置种种资格限制或附带苛刻条件来限制困难群体的权利,这种做法其实还在把救助当成一种慈善和恩惠,进而无视了受助者的获益权利。所以,在向正义迈进的道路上,制度的发展完善还任重道远。但可以肯定的是,正义作为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道德根基和精神动力的终极目标是不会改变的。由此,我们可以对社会救助制度的未来发展进行初步的展望:在“中国梦”的目标指引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全面发展,公民和受助者要求兑现自己生存权利的意识会逐步增强,而国家会对公民生存权进行更好的维护,会用更人性化的举措取代目前一些苛刻的救助条件与要求;生存权所界定的救助标准是不失尊严的生活并满足受助者的基本生活需要,且这种基本生活需要也是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是相对的。可以期待,随着《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颁布实施,覆盖全国、城乡统筹、健全完善的综合型社会救助制度即将建立起来,以此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
[1]多吉才让.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洪大用.转型期中国社会救助[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3]汪雁,慈勤英.中国传统社会救济与城市居民社会救助理念建设[J].理论与现代化,2001(6).
[4]郑功成,等.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熊君玲.仁慈抑或正义——谈现代社会保障的道德基础[J].社会保障制度,2005(7).
[6]郑功成.从慈悲到正义之路——社会保障的发展[J].社会保障制度,2002(8).
China's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from Charity to Justice
ZHANG Hao-miao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China)
Along with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modernization endeavors,the country's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 is also under expansion.The system has so far undergone three stages of traditional disaster-relief efforts,poverty-alleviation-target urban reforms,and urban-rural coordinated and normalized programs.The system was renamed from"relief"to"assistance",together with the shift from single liferelief to comprehensive assistance.At mean time reception of assistance is no longer an acceptance of charity,but a right of citizen,and the provision of assistance is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instead of humanity help.They indicate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spiritual dynamics and moral basis of the system, that is,a road from charity to justice.Certainly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a perfect system,but it is certain that justice is an unchangeable ultimate goal for the modern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 of China.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charity;justice;relief;assistance
O632
A
10.3969/j.issn.1674-8107.2014.04.013
1674-8107(2014)04-0076-05
(责任编辑:吴凡明)
2014-03-28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发展型社会救助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3CSH107)。
张浩淼(1981-),女,辽宁沈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保障、社会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