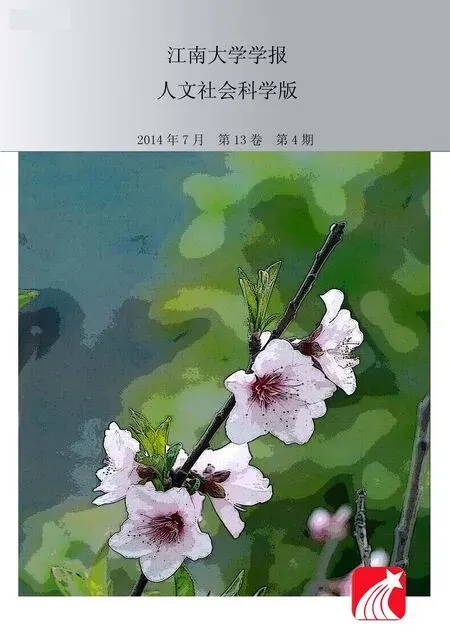论《夜色温柔》中的消费场景
张俊萍,孟 瑜
(江南大学 外语学院,江苏 无锡 214000)
一、小引
被称为“爵士乐时代”的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社会消费主义兴起,消费方式和生活观念急速变化的时代。“与美国的开国元勋富兰克林在其作品《穷查理》中所表现的殖民主义时期节约是一种美德的风尚不同,20年代的美国人认为,节俭可能对社会有害,消费才是一种美德。”[1]“爵士乐时代的代言人”——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1896-1940) 曾这样写道:“我们穷得不能再节俭了,节约是一种浪费”[2]181,这位对社会转型极其敏锐的作家,“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生活气息和社会特征”[3]3,在其作品中描画了大量消费场景,探讨了消费社会初期产生的众多问题。特别是其耗时九年完成的小说《夜色温柔》(1934年),此作以消费场景①“场景”(setting, Scenario或Scene)是戏剧、电影领域常用的术语,在小说中,广义上的“场景”指作品中事件发生的总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狭义上的“场景”与某个场面发生的地点密切相关,表现人物关系和情节的进展。参见波尔蒂克的《牛津文学术语词典》(波尔蒂克:199)和M.H.艾布拉姆斯的《欧美文学术语词典》(艾布拉姆斯:324)。众多著称。“这部小说的背景被安排在作者所熟悉的欧洲大陆,时间跨度为1917至1930年间,但小说展现的仍然是美国“爵士乐时代”的那种奢华消费的社会生活场面。”[3]195本文将从消费文化角度出发,运用鲍德里亚、凡伯伦、布迪厄等人的理论,解读小说中的消费场景,剖析消费场景中人和物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
二、《夜色温柔》中的消费场景
《夜色温柔》描写的是一个出身低微但才华出众的青年迪克·戴弗与出生巨富之家的妻子尼科尔·华伦和女影星罗斯玛丽间的三角恋爱关系以及围绕着这种关系所产生的各种复杂的矛盾冲突。
小说似乎由一幅幅描绘娱乐消费和购物消费场景的画卷组成。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在旅游就是在参加聚会、舞会,不是去购物就是去参与娱乐性的运动,人物的生活似乎就由娱乐消费和购物消费两部分组成。
小说开篇就描写了迪克夫妇的避暑胜地——法国维埃拉风光宜人的海滨地区,“那里坐落着一家高大气派、玫瑰色的旅馆,挺拔的棕榈树给富丽堂皇的旅馆带来一片阴凉,门前延伸出一小块亮晶晶的沙滩。”[4]5迪克夫妇似乎一直在旅游途中,他们“曾有一年游历了许多地方—从伍罗穆娄海湾到比斯克拉”[4]198“此后又游历了戛纳和尼斯,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后又前往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去度圣诞假期。由于夫妇俩的戴安娜别墅已经再次租给别人度夏了。于是,他们决定在这段时间里到德国温泉名胜地区和法国天主教堂林立的小镇去旅游。”[4]212而聚会、舞会也是小说重笔描绘的上层阶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迪克大肆举办舞会,并且完全充满了兴奋和激情”[4]94尼科尔的姐姐巴比不断地参加各种宫廷舞会;迪克夫妇的朋友戈尔丁在他的摩托游艇上举办舞会,并邀请一支乐队在甲板上演奏。 “生气勃勃的绿色溜冰场旁,只听见场上的威尔纳源舞曲震耳欲聋……”[4]223网球、高尔夫球、海滨游泳、水上滑行等高档运动也都成为小说中有闲阶级的重要娱乐活动。而购物,更是小说中人物,特别是女性角色的爱好。菲茨杰拉德甚至在多处刻画了两位女主角的购物细节。
三、消费场景中人与物的关系
“作为消费主体——人和消费对象——物之间的关系极其微妙,在之前生产为主的美国社会,物是作为满足人们需求的商品来呈现出其价值的,而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生产主人公的传奇现在已到处让位于消费主人公。”[5]28菲茨杰拉德小说中消费主人公和物之间的关系表现在,消费者进行消费活动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生活基本需求,而是因为商品可以代表经济力量、标志社会地位;物的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其本身能否满足人的需求或具有使用价值,而是取决于作为交换体系中消费者的身份符号的价值。
首先,人们以对物的 “奢侈消费”、 “套装消费”等“荣誉浪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经济实力。
菲茨杰拉德是这样描绘女主角尼科尔的强劲的消费力的:“尼科尔照着一张长达两页纸的购货单②尼科尔第一次在小说中出场时,读者就可以看到她在海滨沙滩上列购货单。进行购物,并且还买了橱窗里的东西。她所欢喜的这一切东西并不一定都能用得着,而是作为送给朋友的礼物才买下的。她买了彩色的念珠,海滩上用的折叠软垫,人造花,蜂蜜,一张招待客人用的床,提包,围巾,鹦鹉,为一间玩具房买的袖珍家具,以及三码长的对虾色布料。她还买了一打游泳衣,一条橡皮鳄鱼,一副黄金和象牙制成的旅行象棋,送给阿布的大号亚麻纱手绢,两件从赫尔墨斯那里传下来的翠鸟蓝色和有着发亮蓬松的绒毛的羚羊皮夹克。”[4]66显而易见,尼科尔购买的多数是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尼科尔以奢侈和浪费来表明她与社会其他阶层的距离,体现自己的经济实力。这种浪费是一种“荣誉浪费”③社会学家凡伯伦在其名著《有闲阶级论》中提出,“有些物品之所以很受欢迎,使人乐于使用,是由于它们具有明显浪费性,这类物品是浪费的,就其表面的用途说来实在是不适用的”,然而消费者对物品“越是奢华浪费……越能提高其家庭或其家长的荣誉”。(凡勃伦:42、58)。。作为一名上层阶级女性的代表,消费给她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享受,而是虚荣的满足,她所购买的并不仅是物本身,而是物所象征的高人一等的经济力量。
此外,“在丰盛的最基本的而意义最为深刻的形式——堆积之外,物以全套或整套的形式组成。”[5]3小说《夜色温柔》多处表现了上层阶级对物的“套装消费”。小说开始以罗斯玛丽的角度观察迪克夫妇生活中的“套装商品”,“她仔细看了一下他们随身携带的物品——形成一个遮阴天蓬的四把女式太阳伞,一个供更衣用的袖珍海滨更衣室,一只可充气的橡皮马,这些都是罗斯玛丽从来未见过的新鲜玩意儿,属于战后首次迅速问世的奢侈品,也许是最早买主拥有的东西。”[4]22这一整套海滩用品的奢侈程度显而易见,正如作品中所说,它们属于“最早买主”——社会结构中最有经济实力的一部分人。从迪克夫妇的旅行用品清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套装消费”的痕迹:“四只衣箱,一只鞋箱,三只帽箱和二只盛帽子的盒子,还有一只供佣人使用的箱子……一套野餐用具箱,四只装成盒的网球拍,一架留声机,一架打字机。在为家人和随从留下的空间还四下放着二十只作备用的手提箱、小皮包和包裹,每一只都编了号,甚至连藤条箱也挂上了标签……有的送去存放,有的则随身携带。根据‘轻装旅行清单’或‘重装旅行清单’而定。清单上的项目经常变化。单子放在尼科尔的四周有金属板的钱包里。”[4]324由此可见,尼科尔家庭在购物时都是以成套或整套的形式购买。下层阶级可以购买成套商品中的一件,但他们没有经济实力购买一整套奢侈品。全套的奢侈品象征着财富拥有状况,而“不能按照适当的数量和适当的品质来进行消费,意味着屈服和卑贱。”[6]26
第二,人们靠物构建“高雅”生活方式,并以此来表现自己的“有闲”阶级身份。
小说中的尼科尔夫妇几乎不从事生产性的工作。除旅游等休闲活动外,尼科尔最重要的工作便是照看她那片可爱的、没有任何杂草的花园,她老是喋喋不休地念叨着它,生怕它染上病害。养花这一怡情的高雅活动显示了尼科尔属于明显有闲阶层这一特征。这种非生产性的耗时方式可以证明个人的金钱力量足以使其安闲度日、坐食无忧。
小说中的人物还利用服装和饰品表现自己的闲暇。服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符号”。正如社会学家凡伯伦所说,“我们的服装是随时随地显豁呈露的,一切旁观者看到它所提供的标志,对于我们的金钱地位就可以胸中了然。有关服装的各种用品的商业价值所含的绝大部分成分是它的时新性和荣誉性,而不是它对穿衣服的人的身体上的机械效用。服装的需要主要是‘高一层的’或精神上的需要。”[6]55一块淡紫色的头巾,一串奶油色的珍珠项链,总是把尼科尔点缀得恰到好处。“高雅的服装之所以能适应高雅的目的,不只是由于其代价高昂,还由于它是有闲的标志:它不但表明穿的人有力从事于较高度的消费,而且表明他是单管消费、不管生产的。就女子的服装来说,其显然格外突出的一个特征是,证明穿的人并不从事也不宜于从事任何粗鄙的生产工作。”[6]57服饰作为一种象征,将尼科尔等人与普通劳动者区隔开,表现出他们作为有闲阶级的身份和地位。
此外,隆重华贵、耗费高昂的宴会、舞会往往也有助于建构所谓的“高雅”有闲生活,因此它们也经常成为举办聚会的东道主的权威和地位的象征。“对有闲的绅士来说,对贵重物品作明显消费是博取荣誉的一种手段。但单靠他独自努力消费积聚在他手里的财富,是不能充分证明他的富有的。于是有了乞助于朋友和同类竞争者的必要,其方式是馈赠珍贵礼物,举行豪华的宴会和各种招待。”[6]27尼科尔夫妇喜欢在自己建造的豪华别墅举办舞会,宴请同等阶级的名流,在奢侈礼品的馈赠、美酒佳肴的供应中,在觥筹交错、音乐伴舞中,显示出他们坚实的财力后盾和极其闲暇的生活;同时,让宾客目睹由于财力雄厚而无法一人独立消费过剩高贵物品这一事实。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生活水准,也正是此时,我们所熟悉的消费主义特征显而易见地表现出来……”[7]在20年代的代言人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中,消费社会初期消费主义的最初表征已得到充分表现,消费场景中人与物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物受到人的重视不是因为其使用价值而是由于其“符号价值”。①“符号价值”这一说法见博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作为社会分类和区分过程,物和符号在这里不仅作为对不同意义的区分,按顺序排列于密码之中,而且作为法定的价值排列于社会等级。这里,消费可能只是战略分析对象,在法定价值(涉及到其他社会含义:知识、权利、文化等)分配中,决定着其特殊的分量”。( 博德里亚:48)
四、消费场景中人与人的关系
当人与物的关系发生变化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遭到了扭曲。
一方面,社会低阶层成员往往被物化,成为高级阶层消费者购买、甚至浪费的商品。《夜色温柔》中是这样写尼科尔家的某次旅途的:“女家庭教师的女佣和戴弗太太(即尼科尔)的女佣从二等车厢来到卧铺车厢,帮着照看行李和狗。贝洛伊斯小姐只须拿一些手提行李,把西利汉姆斯种狗留给一个女佣,并把一堆哈巴狗留给另一个女佣。”[4]323从这些排场中可见,她家的女佣数量惊人, “这些专业化仆役的作用主要不在于实际服务,而在于外观上的炫耀。”[6]57他们的存在价值并不在于为主人提供服务,而主要在于维护他们的主人在社会上的声望和地位,因此,拥有众仆究其实质是浪费劳力。
尼科尔与迪克虽是夫妻,但其关系本质上也类似于主仆。在尼科尔的姐姐巴比看来,迪克这个出身低微但才华出众的精神病医生就是她家“花钱”为尼科尔这个病人“买来的家庭医生”,是她家消费着的一个特殊的佣人,一个扮演父亲、丈夫和医生角色的优秀劳动力。尽管婚后很长一段时间,迪克总想“保持了一种合乎身份的财政独立”[4]211,但 “他就像是一个靠女人供养的男子一样被人收买了,他的武器也被锁在华伦家的保险柜中了”[4]249。他渐渐地“被淹没在滚滚而来的物品和钱财中”[4]211。即便是他与人合伙经营诊所的资金也是尼科尔家族提供的,尼科尔家的潜台词是:“我们是拥有你的,这点你迟早总会承认。想保持装模作样的独立性是荒唐可笑的。”[4]220可见,“迪克虽然如愿以偿地步入富人圈……富人们始终以尼科尔的‘保姆医生’来定位他,他的礼貌、照顾他人的品性也使得他在富人圈里永远只是个仆人。”[8]
另一方面,社会“高级阶层的选择往往会成为社会的风尚和取向”[9],而社会低一阶层成员则经常需通过效仿性消费获得“晋升符号”,以向高级阶层靠拢。一个人消费什么、以什么方式消费取决于他“拥有的资本的数量和结构”,也即他“手里符号标志的总数”和“这堆符号标志的组成状况”[10]136。“不同的团体购买不同的商品,这种差异巩固了符号价值。人们的普遍特点是,认同高级阶层的价值观”[9]。上层社会通常把物品或商品当做符号来操纵,不惜借助奢侈消费来构建身份,小说中尼科尔和巴比代表着高级阶层的消费行为。巴比出行、用餐、住宿都必须是最奢华的,以成为他人效仿的模板,这对她来说是“原则问题”。尼科尔在尼斯街上买了一种海员穿的游泳短裤和汗衫,很快,“这些衣服后来在巴黎女式丝绸服装行业中流行起来。”[4]353这便是符号价值的直接表现。低级阶层将高级阶层的消费选择作为风向标,努力学习和效仿,无非是想某种程度上摆脱现行的社会阶层,向上攀爬。或者说,“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自身)的符号,或让你(自己)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5]48这在中下阶层出身的主人公迪克和罗斯玛丽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他们企图通过消费找到晋升符号。罗斯玛丽艳羡尼科尔的购物方式和购物品位,她需要用尼科尔上层社会的审美观来帮助她挑选服饰和礼物,以便穿戴这些服饰后获得上层社会青睐和认可,获得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小说中有几次写到罗斯玛丽 “在尼科尔的帮助下”购物。[4]66,117而迪克也努力通过消费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在他举办的一场与众不同的聚会上,“他设法弄来了一辆波斯国王的专用汽车。这辆车是在美国产的一种特殊汽车底盘上制造的。车轮是银的,冷却器也是银的。车厢里镶着无数颗宝石,并有着貂皮车底。”[4]94迪克之所以想方设法搞到这辆特殊的不实用的皇家汽车,无非是想迎合上层阶级的宾客,表现他“趋同”的趣味,提升他个人的社会空间和地位。
五、结论
菲茨杰拉德这位从马克思那里得到“最现实的世界观”[11]的作家,对笔下男女主人公的阶级身份和财产多寡作了细心安排,他把人物安置于一个个消费场景中,表现了当时美国社会刚刚兴起的消费主义文化对不同阶级人物的侵蚀。一方面以尼科尔为代表的富裕的上层有闲阶层在奢华消费中并没有获得幸福快乐、有意义和价值的生活,他们不自觉地接受了消费文化的操纵, 靠机械的消费来弥补内心的空虚,沦为屈从于商品符号的奴隶、商品拜物教的牺牲品。小说中,尼科尔两度精神崩溃,其精神病患者的身份不能不说是对这一阶层的隐喻。另一方面,以迪克和罗斯玛丽为代表的中下阶层企图通过消费来获得晋升资格、赢得上层社会的认可的愿望也没能够实现。中下阶级固有的生活“惯习”并不会因为他们努力向上的消费活动而改变,惯习是“特定的经济条件的产物……属于同一个阶级的许多人的惯习具有结构上的亲和,无需借助任何集体性的‘意图’或是自觉意识,更不用说(相互勾结的)‘图谋’了,便能够产生出客观上步调一致、方向统一的实践活动来。”[10]168-169而不同阶级之间却很难“步调一致、方向同一”。 迪克和罗斯玛丽无论怎样追逐消费档次,他们仍然与上层阶级格格不入。特别是迪克,即便通过与尼科尔的婚姻获得了金钱上的丰盛,但是他本身的惯习还是不属于上流阶层,他与上流阶层成员的观点和生活总是出现分歧,而且更可悲的是,他还被尼科尔家源源不断提供的物品和金钱所束缚,荒芜了自己的工作和研究,丧失了经济独立,成为没有消费资本的消费者。尼科尔的姐姐巴比是这样评价他的:“人一旦被投入一个不属于他的世界,就会像丢了魂似的,不能自制,不论他们如何有模有样。”[4]395因此他的结局可想而知,最后他不仅被尼科尔抛弃,也受到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罗斯玛丽的鄙夷,只得自我放逐,退出那个不属于他的世界。他原本是尼科尔的医生,但这样一个“精神分析者, 治愈别人的人,‘梦幻世界’的矫正者成了梦幻世界本身的牺牲品。”[12]我们不得不说,这也是富有隐喻意义的。
其实,无论是尼克尔,还是罗斯玛丽、迪克,这些消费场景中的主角,都是“拜倒在商品面前,把商品当做自己的灵魂,失去了自主能力,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与操纵的反抗和否定性,丧失了对社会的鉴别和批判的能力”的“单向度的人”。[13]他们全都陷于消费陷阱中,陷入对物的符号价值的永无止境的追求中。而这正是消费社会的主要病理症状。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的重要意义在于其能针砭时弊,较早展现了消费社会的“消费病理”。
[参 考 文 献]
[1] 余志森.美国通史:第四卷.崛起和扩张的时代(1898- 1929)[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471
[2] William E Leuchtenburg.ThePerilofProsperity, 1914-1932[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3] 吴建国.菲茨杰拉德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4] 菲茨杰拉德.夜色温柔[M].王宁,顾明栋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
[5] 博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 凡伯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7] 蒋道超.德莱赛研究[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222.
[8] 王静,石云龙.跨越不去的阶级鸿沟——评《夜色温柔》中人物堕落的阶级根源[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8(8)
[9] 张冰.消费时代的异化美学——论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J].河南大学学报,2013(1).
[10] 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1] William R. Anderson.FitzgeraldAfterTenderisTheNight:ALiteraryStrategyForThe1930s[M]// Eds. Matthew J. Bruccoli , Richard Layman.Fitzgerald/HemingwayAnnual1979. Detroit, Michigan: The Gale Research Company, 1980.
[12] Burton, Mary E.TheCounter—TransferenceofDr.DiverInModernCriticalViews[M].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5:130.
[13]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