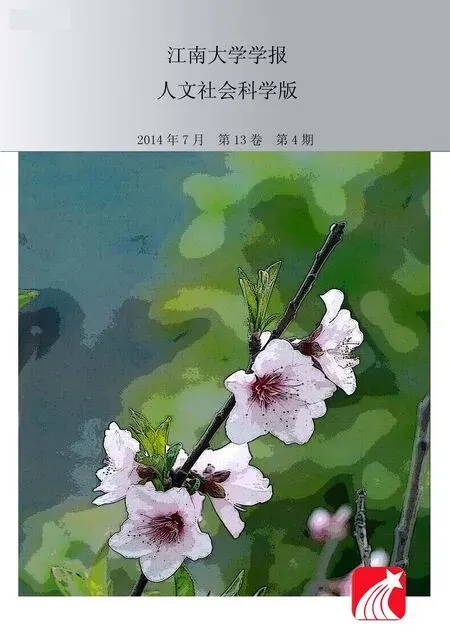明清江南曲坛“松江曲派”质疑
汪 超
(安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明清时期松江地区不仅民间演剧繁盛,如“府城隍庙向极严肃,崇祯末年忽于二门起楼,北向演剧赛神,小民聚观,南向而坐。殿庭皆满”。[1]而且出现一批世人熟知的曲家,如何良俊(《曲论》)、王玉峰(《焚香记》)、范文若(《鸳鸯棒》、《梦花酣》)、徐于室(与吴县钮少雅合作编纂《南曲九宫正始》)等,可以说松江曲坛戏曲活动十分活跃。为此近代学者提出“松江曲派”的观点,“从崇祯己巳(1629)年起,随着刘方等人的聚合,松江府形成了一个以张方伯为首的谈曲中心,这就是张积祥所说的曲社。同社人还有周裕度、止园居士等人,是为松江曲派。”[2]为此,本文欲针对明清戏曲史中这一特殊曲派,通过对曲家、曲社、曲论的具体论析,以期揭示“松江曲派”的形成及其特征。
一、传奇史之“松江曲派”部分人物质疑
松江曲坛的此次活动,主要围绕吴县刘方造访松江望族名公张所望展开,刘方《天马媒》传奇卷首《自题》云:
岁己巳,始获见云间张方伯七泽先生。……客岁春日,先生挈公远及余放舟虎谿,偶翻《情史》,见《玉马坠》一则,甚异之,属余为传奇。余虽雅嗜音律,顾何能为役?然予谬承先生旨,又不敢以不敏辞。扁舟所至,复见烟岚幻出,波縠恣生,山容水色,殊可人意,遂捉笔草成,颜曰《天马媒》。[3]
这也得到同行周裕度的证实,其《天马媒》题辞曰:
晋充,吴下韵士也,读书谭诗,名谊俱馥。……庚午,偕予澄江之役,相与上下千古,偶拈稗史可作院本者,如黄损玉马故事,其一也。归未浃月,而传奇告成。
据陈继儒《张圣清传》记载,张所望、张积源(字圣清)父子皆好放舟林泉,“七泽公有小舟,曰载石,父子常相尾出游”。[4]于是这次庚午春日刘方、周裕度等人追随张所望的放舟之行,被视为他们曲学活动的重要契机,后刘方完成“流脍吴中”的传奇作品《天马媒》,同时周裕度、止园居士、张积祥为之题辞作序,阐发《天马媒》传奇之奇的戏曲观点,构成曲派活动外在形式的基本因素,下文就此曲派相关人物予以考论。
张所望(1556—1635年),字叔翘,号七泽,上海县龙华人。①关于张所望生卒年详见陈子龙:《明中奉大夫山东布政使司右布政使七泽张公神道碑铭》:“公讳所望,字叔翘,世为上海人。……崇祯八年正月卒于家,年八十,葬揭溪之北原,公次子积润,请予为之铭。”(陈子龙:《安雅堂稿》卷一二,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7年版,第353-355页。)祖武,封咸阳侯、潞国公。父大鲁。兄所敬,子张积源、张积润。据康熙《松江府志》卷二四《名臣》载其为万历辛丑(1601)年进士,曾官至山东布政司右布政使。主要著作有《龙华里志》、《归田录》、《宝穑堂杂记》、《梧浔杂佩》、《阅耕录》、《阅耕续录》、《百步桥记》等。②康熙《松江府志》卷五○《艺文》:“《归田录》、《宝穑堂杂记》、《梧浔杂佩》、《阅耕录》、《阅耕续录》,以上布政使七泽张所望叔翘著。”;又嘉庆《松江府志》卷七三《艺文志》:“《百步桥记》,明万历四十五年邑人张所望撰”。张所望与当时吴中、松江文人多有唱和赠答,如丁耀亢、宋懋澄、唐汝询、陈继儒等。
刘方(1602前后-?)字地如,又字晋充,江苏长洲人。刘方一介布衣,生平事迹不见载录,其《天马媒》自题云“余承先世清白之道,贫无负郭,糊口四方者数载”,周裕度《天马媒》题辞亦谓其“杖头不挂一钱,缸底不储半粟”,故而一生糊口四方。所作传奇共有四种:《天马媒》、《女丈夫》、《小桃园》、《罗衫合》。
周裕度,生卒年不详,华亭人,嘉庆《松江府志》七三记载《澄照院塔记》时云:“裕度,思兼子”。周思兼,(1519-1565),字叔夜,号莱峰,南直华亭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除平度知州,擢工部员外郎,进郎中,出为湖广佥事。以母丧归,卒于家。门人私谥为贞靖先生。为官清廉,颇有人望。工书画,少有文名,诗文均受王世贞影响。著有《叔夜集》、《学道纪言》。周裕度以书画名闻松江,“周裕度,号公远,松江人。画花卉,水墨点染,如瑶岛婵娟,离尘绝俗。书学颜真卿。有子名玫。字紫瑶,亦善书画。”[5]
止园居士,蔡毅先生编著《古典戏曲序跋汇编》认为是周天球,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三《公瑕设像》云:“万历乙未九月卒,年八十二。”可见周天球的生卒年为1514年至1595年。[6]同时,周公瑕尝“从文待诏(徵明)游,待诏赏异之。待诏殁,丰碑大碣,皆出公瑕手。隆庆中,游长安,燕集唱酬之作,一时词客皆为让坐,而诗名颇为书法所掩。”[7]由此可见,周天球主要活动于隆庆和万历前期的文人,虽然也别号止园居士,但是显然不是作于1631年的这篇序跋的作者,应当是崇祯时期的另一文人。
从以上考述可以看出,除却刘方有传奇戏曲作品存世外,其他几位虽也“遇物知名,审音必顾”,但毕竟都未能见具体的传奇作品,反而他们的书画成就为时人称道,如张所望为“瑁湖六逸”之一,周裕度存世书法名作《澄照院塔记》等,故而是否能够纳入“松江曲派”之成员,仍需作进一步地斟酌探讨。
二、“吾社”所为何社?
古代文人结社由来已久,《说文解字》释“社”为“地主也,从示土。《周礼》二十五家为社。”《周礼》最初所言之“社”实为祭神的地点,故而有春、秋社之称。由于“君子以文会友”,所以文人“聚徒结会亦谓之社”,[8]“因此一般士子们集合起来习举业,来作团体的运动就是社,他们或十日一会,或月一寻盟。”[9]就松江地区而言文社尤为兴盛,所谓“松郡文社甲天下”,[10]102松江本为文人名家聚集之地,故而文社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闻名一时,如复社、几社等。
但是,围绕松江张叔翘周围的这些文人,他们或所言“同社”、“吾社”,或更以“社弟”相称,这在题辞、引语中皆有提及,周裕度《天马媒》题辞云:
过从莫逆,靡间春秋,每课一目,拈双韵,一时同社面赤未就,而晋充已稿落几上,舒啸自若矣。其武库之敏瞻如此。
同时,张积祥《天马媒》引语亦云:
吾社刘子晋充,仙才侠骨,翩若行空天马,殆不可羁,世无薛翁神鉴,犹然辕下局促耳。家从父方伯公一见惊赏,引缔忘年,虽昌黎之遇长吉未或过之……社弟怡蓭张积祥题。
这里可以看出,聚集在张所望龙华别业黄石园的文人,尤其是张积祥与刘方之间确实存在结社交友的现象,但是他们所称引的“吾社”究竟为何社?是否就是他们谭曲的曲社?似乎还要进行深入之论析。
张家在龙华是世家望族,“龙华张氏,自七泽所望登进士,历官方伯,而其族遂显。”[10] 127这也得到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的证实:“张家浜最近龙华,四姓瞿张沈赵家。子姓聚居年八百,墓碑深刻未麻沙”。同时,张所敬、张所望兄弟“明世以孝友诗礼禅”,如张所敬“浮白延客以娱亲者,丙夜不辍,家门雍睦,和气盎然,海上人以为美谭,曰:安得张氏祖孙、父子之奕如粹如也”。[11]而张所望亦是“归卧林阿,萧然在中。俗皆治产,公常屡空;人多习竞,公独守冲。……乡有秽德,人所共弃。公以长厚,言念旧义。联袂同车,相将游戏”。[12]故而松江乃至其他地区的文人,皆好聚张氏门下交友谭文。
张积祥在《天马媒》引语中称谓张所望为“家从父”,他实则为张所望兄张所敬之子,“今有二子,曰积仁、积祥,皆有声膠痒,而文章行谊,绰有父风。”[11]而其父张所敬,“字长與,人称黄鹤先生,上海之龙华里人。观察史七泽公所望之兄也。”[10]127故而张积祥这里所指的所谓“吾社”,实际为其父张所敬主盟的“雅社”,唐汝询《编蓬后集》卷十五《雅社约》云:
乙卯岁杪,偶憩海上,愁霖晦冥,客居寡欢,日与元常诸君悲歌相答,酒酣耳热,怆然与怀。正以嘉会难长,良俦莫逆,藉非寄情高詠,奚以托好千秋。于是举生平所與,操觚艺林,填箎调合者得十二人为雅社,推长與先生为盟主。后每有一题,在远必告,毋畏难而阁笔,毋托事以废吟,唐代也然。科条不立,无所遵守,谨著社约十四条于右。
乙卯(1615)年冬廿二日,唐汝询与张所敬等十二人相约而立“雅社”,并且规定立课以遵守,“每以一月为率,诵选诗若干,近体若干,须精熟,合社共赋者为公题,人自命篇者为私题。”也即周裕度所言的“课目”、“拈韵”之事。唐汝询《雅社约》所立十四条倡言,“吾党必先精骚选,次及律绝,始可入大乘法门”,并且“以古人为式”,故而“唐汝询所作艺演七子流派,开卷即拟古十九首”,所以说,“雅社”是秉持主张七子的诗歌复古理论,“以文会友”为主要目的的文人社团。
由此可见,吴中刘方已巳(1629)年来访张叔翘方伯先生,其目的虽然今日已不能知,但是确实参加张所敬主盟的“雅社”活动,故而为张积祥、周裕度等人以社友相称,只是张积祥所言之“吾社”并非曲社,而是以谈论诗文为主的“雅社”。
三、传奇史之“松江曲派”能否成立?
对于文学流派的成立,刘扬忠先生《唐宋词流派史》中的界定较为切中肯綮,其概念的形成大致有三个条件和因素:
一、必须有一位创作成就卓特、足为他人典范且个人具有较大凝聚力与号召力的领袖人物作为宗主;
二、在这位领袖人物周围或在他身后曾经聚集过一些由若干创作实践十分活跃并自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追随者组成的作家群;
三、这个作家群的成员们尽管各有自己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采,但从群体形态上看却有着较为一致的审美倾向和相近的艺术风格。①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关于文学流派的界定,如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流派是文人社团的高级形态。文学流派不仅像文人社团一样,必须由一个实体性的作家群体构成,而且还必须具有非实体性的创作风格和理论主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页。);又陈文新《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导论》认为:“流派分为两种:一种是由文学社团发展而成的流派;一种则是在一个或几个代表作家的吸引下,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创作风格的作家群,研究者据以归纳出的文学流派。”(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从以上对于流派形成因素的总结看来,“松江曲派”以何成立的问题亦要具体分析:
首先,具有号召力的领袖人物,显然这里要归之于张方伯叔翘先生。张所望自1601年中进士后一直居官在外,“除刑部主事,奉使荣、襄、靖江三王国,馈遗一无所受,诸王异之。出守衢州,迁广西副使,备兵苍梧,转左江参政。擢广东按察使,不就,起为湖广按察使。积劳疾作解职归,再起山东右布政使”。[13]虽然晚年归乡隐居,“归卧林阿,萧然在中”,“不废丝竹,东山之风”,“纵横剑戟,逍遥词赋。遇物知名,审音必顾。”[12]于音律丝竹心喜乐好,但是并未留有曲作、曲论,反而在当时更多以书画闻名,如胡敬《西清札记》卷四《无名氏云间高会图》载董其昌跋云:
《山阴高会图》凡四人,《香山九老图》九人,《独乐图》七人,《西园雅集图》十六人。此图六人,余与陈眉公、张七泽、朱云莱已足《山阴高会》之数。……又余年七十有七,七泽年七十有六,……晋人云“居为远志,出为小草”。右军誓墓不出,何必捉鼻东山。余虽缪为同社君子推长。湖山不至。林惭涧愧,乃兹趣装赴召,一邱一壑,不能自固。恐稚圭北山之移,非向长损卦之旨。第所与猿鹤盟者,在彭泽八十日闲耳。崇祯四年嘉平八日,晋陵舟次题。董其昌。[14]
从这幅“瑁湖六逸图”可以看出,张所望于1631年与陈继儒、董其昌等“松江画派”著名画家相交甚深,从董其昌自言推为社盟之长可以看出他们之间也有社盟之约,显然这一社盟是以书画为主要因缘聚合一起,遨游湖山,赏景作画。
其次,谭曲中心及其活动是否存在?已巳年(1629)吴中刘晋充“求其好客如王孙,知己如远山,怜才如汉令者”(刘方《天马媒》自题),故而仰慕远道来访松江张所望,但是他来松江后的活动大致有二:一为“每课一目,拈双韵”(周裕度《天马媒》题辞)。刘方与同社文人课目之事,也即“雅社”立约的诵读作诗;二为游处,“先生高卧林泉,萧然物外,性好舟居,所携惟图书数卷,酒铛茶具,从一二胜引,徜徉于名山胜水间,涉三泖、泛五湖,遇词臣与谈诗,遇学士与谈文,遇良将与谈兵,遇僧侣与谈禅,遇侠客与谈剑,遇羽衣与谈黄、老,遇美人与谈歌舞,遇樵夫、牧子、渔父、溪翁,与谈村居烟水之乐”(刘方《天马媒》自题)。至于《天马媒》传奇戏曲的产生,则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素,从刘方自述以及周裕度的言说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及《天马媒》创作的缘由――“偶翻”稗史,张所望只是一时诧异《玉马坠》之情节,故而嘱咐刘方作为传奇戏曲,这或许就是所见的唯一一次谭曲活动。同时,张所望亦只是嘱咐刘方可以改作,而未提出具体明确的曲论宗旨,所以这种随意性和偶然性的特征,导致此次谭曲活动的展开未能形成一定的影响。
最后,戏曲观念的阐发论议。《天马媒》传奇卷首刘方、周裕度等人的序跋、题辞,着重围绕《天马媒》传奇情节,阐发传奇之“奇”的戏曲观点。
此曷以故?大凡姻缘作合,实有天意,夫岂人为?……是以若淑之伦,天必假以奇缘;廻遹之流,天必降以奇祸。则《天马媒》一传可镜也。且从来艳称撮合者,曰押衙、曰昆仑、曰黄衫客,未见有物类而能作人之合者。噫!今人类兽心,无论为人撮合,凡见人稍有遇合,必思百计倾陷,亦有愧于物类实多,此予之作传奇也,非传词也。(刘方:《天马媒》自题)
玉为马,马能蹄啮,人为奇玉,为奇兽。一措大唱名,御殿得两名姝,为奇男子,一在曲中,一在贾人柁楼底,皆善调筝,大江不能沉,天子不能留,为奇女子。有奇女子皆名姝,一节度使不敢夺。真琼琼得假琼琼,却为人绐赠去,又为一奇事。传奇无奇于此者。晋充负奇才,解音律,伤积木之未践,叹绝世之难得,辄借以发其奇。奇于本色,不奇于藻绘。故构造自然,畅俊可咏。(止园居士:题《天马媒》)
尝谬论天下,有愈奇则愈传者,有愈实则愈奇者。奇而传者,不出之事是也。实而奇者,传事之情是也。(周裕度:《天马媒》题辞)
明清曲家多从“奇”之视角诠释传奇戏曲,“奇”甚至可以作为传奇戏曲较为重要的特征存在,如“第曰传奇者,事不奇幻不传,辞不奇艳不传”,[15]并且“奇”的内涵也在不同时期不断演变丰富,从某种程度而言,“奇”也是解读明清文人传奇戏曲的关键词。这里围绕《天马媒》传奇,刘方、周裕度等人也阐发“奇”的主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情节之“奇”,突出“有愈奇则愈传者,有愈实则愈奇者”,肯定《天马媒》之“奇缘”、“奇玉”、“奇兽”、“奇男子”、“奇女子”等,这也正是刘方所自称的传“奇”而非传“词”,目的在于故事情节的奇异;其二为文辞之“奇”,所谓“奇于本色,不奇于藻绘。故构造自然,畅俊可咏。”这里提及“本色”之标准,实则是对何良俊、沈璟等人反驳传奇藻饰奇艳的一种回应,强化于“本色”基础上的出新出奇。可以看出,刘方等人关于“奇”命题的阐释,是随之当时曲坛应运而生的现象,也是明清之际曲家对于传奇文体的共识,未能体现出其独特的戏曲理论。
由此可见,较之万历曲坛“临川派”、“吴江派”而言,领袖人物的核心、流派形式的松散、戏曲理论的普泛等因素的存在,导致“松江曲派”的界定并非严格完整,对其是否成立仍需进一步商榷。
四、散曲史之“松江曲派”能否成立?
松江地区文人曲家的散曲创作,亦在晚明曲坛占据一席之地,其中尤以施绍莘为代表,故而学者提出散曲史之“松江曲派”的观点,如邱明正主编《上海文学通史》论及元代文人杨维祯对于上海文学发展的影响时提出这一概念:
明代以写艳情诗《疑雨集》著称的诗人王次回,生前曾来松江做过华亭训导,以写艳曲《花影集》著称的散曲家施绍莘本身就是华亭人,他们之所以都会热衷于写艳诗或艳曲,成为明代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家,都与杨维帧的铁崖体及其在松江的影响有关。后来明代中后期吴地所盛行的《山歌》、《桂枝儿》、《夹竹桃》等,也以写男女艳情见长,在明代的松江地区十分流行,甚至流传到官府也不以为禁忌,这或许与杨维帧的铁崖体也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微妙关系。此外,他所作的曲对于“松江曲派”也带来一定的影响。[16]
孙琴安先生以杨维桢为该曲派之始祖,施绍莘、王次回等承袭为代表曲家,其创作主要以男女艳情见长,从而形成秾艳的风格特征,是之而为所谓的“松江曲派”。但是,王次回主要以艳诗著称,真正以散曲见长的只有施绍莘。
施绍莘,字子野,号峰泖浪仙,华亭人。康熙《青浦县志》卷七云:“字子野。少补诸生,负隽才,跌宕不羁,隐于西佘,就麓山居。工乐府新词,著《花影集》行世。时辈称其才艳”。[17]其“《花影集》五卷,《文渊阁存目提要》云:‘是集前三卷为乐府,后二卷为诗馀。多作崇祯中,大抵皆红愁绿惨之词。’”[18]主要成就在于散曲创作,陈继儒所作《秋水庵花影集序》中引用沈士麟的评价为:“不雕琢而工,不磨涤而净,不粉泽而艳,不寄凿而奇,不拂拭而新,不揉摛而韵。盖直出其绪余,玩世弄物,彼其胸中宁有纤毫留滞哉!”故而能以独特之风貌屹立于晚明曲坛,这也得到近来学者的高度肯定,如吴梅先生《中国戏曲概论》论议明代散曲时认为“要以施绍莘为一代之殿”,又任半塘先生《花影集提要》中也认为是“明人散曲之大成者”。
虽然施绍莘散曲创作在晚明曲坛成就斐然,具备流派领袖人物的气质,但是却有一枝独秀之憾,其周围并未形成追慕效仿之文人群体,尤其是松江地区文人的集体追随。《青浦诗传》记载“子野少负隽才,作别业于泖上,又营精舍于西佘,极烟波花药之美。时陈眉公居东佘,管弦书画,兼以名童、妙伎,来往嬉游。故自号浪仙。亦慕宋张三影所作乐府,著《花影集》行世。”[19]与晚明另一名隐陈继儒闲游自乐,或许无意功名的隐士旨趣,也使得施绍莘很难成为曲派的领袖人物。所以,施绍莘的奇葩自秀于松江曲坛,个体成就的突出未能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周围未能形成一定创作群体的出现,也即创作风格群体化现象的存在,就使得散曲史“松江曲派”的是否存在,很值得怀疑。
五、结语
虽然无论是传奇史还是散曲史之“松江曲派”是否成立存在诸多悬疑,但并不否认明清之际松江地区的戏曲成就。明清松江地区不仅文人名家辈出,而且受曲坛中心吴越地区的风气熏染,除却当时较为有名的曲家外,还有不少戏曲作品盛演于当时舞台,如《木椎记》(张昉作)、《蚊虎记》(黄伯羽作)、《掷杯记》(许经眉作)、《步烟非》(李宣之作)、《佩印记》(顾谨作)、《倒鸳鸯》(朱寄林作)等。这里尚需一提的就是前文论及张所望方伯公的儿子张积润、张积源,尤其是张积润也是晚明松江曲坛不可忽视的曲家。
张积源,陈继儒《书云间诗隽》云:“瞿弥陆释麟、圣清张积源、子野施绍莘,皆韵士,诗词秀丽异常,翩翩无豪贵习气,享年不若季常希周,而俱伤伯道,人甚念之。”[20]张积源不仅与施绍莘等皆为异常之韵士,而且也是“雅社”的主要成员,可见在当时松江地区皆有诗名。
张积润,字次璧,号思恭,与陈眉公、唐汝询等人友好往来,善音律,崇祯二年作《双真记》传奇以讽刺朱国盛依附魏忠贤:
朱云莱藉魏阉延引,升北太常。阉败家居,声伎自娱,郡中后辈,好讥论之。有张次璧者,作一传奇,名《双真记》,其生名京兆,字敞卿,盖以自寓也;旦名惠玄霜,其净名佟遗万,佟者以朱为乡人也,遗万谓其遗臭万年也,诋斥无所不至。云莱大恨,讼于官,陈眉公为之解纷,致札当事,迫书札当堂销毁,置其事不问。[21]
朱云莱即为松江朱国盛,与董其昌、陈继儒、张所望、秦昌遇、麻衣和尚六人共称为“明代六逸”,[22]都是当时松江文坛的书画名家,这位好友之子填制传奇戏曲作品,来讥讽朱国盛委身魏党,以致诉讼于官府而幸得陈继儒得以调解,可惜的是这部传奇作品未能存世,成为当时松江文坛的一段掌故。此外,谢伯阳《全明散曲》还辑录张积润小令二首:[南双调?公子醉东风]、[南仙吕入双调?姐姐带六么]。[23]
总之,对于明清松江地区文学现象的概论,众多学人都已经注意到云间诗派、云间词派、云间书派、云间画派等的阐述论析,其间并未涉及曲派的论述,可见对于“松江曲派”的提法尚未得到大家的认可,对于相关材料的挖掘和解释,应持审慎的态度。
[参 考 文 献]
[1] 康熙松江府志卷:五四[M]//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 谢柏梁.中华戏曲文化学[M].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1.
[3] 天马媒:卷首[M].古本戏曲丛刊本.
[4] 陈继儒.陈眉公全集:上[M].广益书局,1936:225.
[5] 于安澜编.图绘实鑑续纂[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25.
[6] 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三[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74.
[7]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486.
[8]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二十二[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671.
[9] 谢国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6.
[10] 叶梦珠.阅世编[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02.
[11] 何三畏.张文学长與先生传[M]//云间志略.台北:学生书局,1987:1701-1705.
[12] 陈子龙.祭张叔翘方伯文[M]//安雅堂稿.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7:384-385.
[13] 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397.
[14] 任道斌.董其昌系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272.
[15] 茅暎.题牡丹亭记[M]//汤显祖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575.
[16] 邱明正主编.上海文学通史: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63.
[17] 赵景深,张增元.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7:478.
[18] 嘉庆上海县志卷一八[M]//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9] 王昶.明词综卷五[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79.
[20] 陈继儒.陈眉公全集:上[M].上海:广益书局,1936:10.
[21] 曹家驹.说梦卷二[M]//清代笔记小说.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423.
[22] 马宝山.书画碑帖见闻录[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126.
[23] 谢伯阳.全明散曲[M].济南:齐鲁书社,1994:3940.
——松江二中(集团)初级中学校歌
———王松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