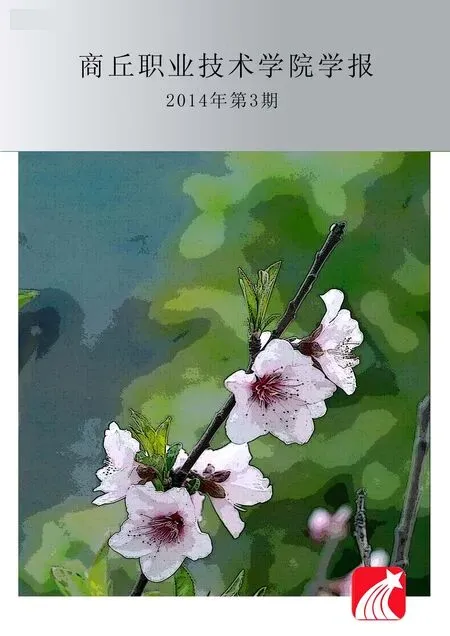马克思异化思想与卢卡奇物化思想比较分析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历史与阶级意识》
平成涛
(河南大学 哲学系,河南 开封 450000)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者的卢卡奇,其思想的敏锐性和深刻性是毋庸置疑和众所周知的,其著作颇丰。但就其对异化(卢卡奇称之为物化)理论的论述,1923年问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可以说是他的大手笔之作。同时,马克思在其早期就完成书写、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32年才公开问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对异化进行了阐释,两部作为马克思哲学史以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著作展现了两位哲学家在思想史上惊人的契合。
一、正本清由:两种“异化”呼喊的历史声源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对异化作出了表述:工人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的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1]52。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里对“异化”与“物化”、“对象化”作出了区分,“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1]52。异化不仅表现为对象化的主客分离,而且这种分离具有明显的敌对性质,客体对象反过来控制主体。马克思反对“把一切的关系和现实的个人都预先宣布为异化的,把这些关系和个人都变成关于异化的完全抽象的词句”[2]316。
“物化”作为贯穿《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一个中心概念,有其独特的卢卡奇式话语。卢卡奇是直接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得出物化概念的:“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2]152“商品结构的本质已被多次强调指出过。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2]149卢卡奇基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的商品形式在批判话语中阐释“物化”。商品作为整个社会的普遍范畴,按其被歪曲的本质被理解,“只有在这一联系中,由于商品关系而产生的物化才对社会的客观发展和人对社会的态度有决定性的意义”[2]152。正如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再版序言中的自我批判所说:“《历史与阶级意识》跟在黑格尔后面,也将异化等同于对象化。”[3]19
对思想本质的不同阐发决定了马克思和卢卡奇走进自己所处时代对异化扬弃作出不同探索。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异化的扬弃道路作出了明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1]78马克思沿着“劳动”的逻辑,把异化的扬弃同生产劳动联系起来。马克思在《手稿》中没明确得出扬弃异化的理论结果,但我们能够挖掘出马克思对异化的扬弃所诉诸的是社会生产实践。随着生产力发展、交往不断扩大、精确社会分工的消灭,随着异化产生的“基础即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以及这种调节所带来的人民对自己产品的异己关系的消灭,供求关系的威力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换、生产及他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4]31与马克思不同,卢卡奇把物化扬弃道路向无产阶级以其阶级意识敞开了,他把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的产生与成熟作为扬弃物化的钥匙。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分析了资产阶级阶级本质对其自身历史功能局限性的决定作用,并从历史性上阐明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并对其进行了反思批判:“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一开始起和由于它的本质的原因——会遭受悲剧性的灾难”[2]123。这就意味在扬弃物化的历史任务上资产阶级历史主动地位的丧失。
马克思和卢卡奇在异化概念和扬弃异化道路上的不同理论分向是由其不同的理论背景以及他们所处历史条件的差异造成的。首先,就其思想来源,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观,主要受到了德国古典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他最早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关于国民经济学唯心主义式的批判,之后在对英法经济学家关于现实利益批判的超越中转向费尔巴哈,受到了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影响。费尔巴哈关于人的宗教异化的唯物主义批判,为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出发提出自己的异化观做了铺垫。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把费尔巴哈对宗教异化的批判发展为对资本主义异化社会的现实批判。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物化概念的提出,直接地从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受到启发。卢卡奇在1967年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历史批判中也说到,当时对马克思的研究“我通过在很大程度上由席美尔和韦伯决定的方法论眼镜去观察他”,并且在再次着手时“主要不是受当时精神科学学者,而是受黑格尔的影响”[2] 2。席美尔作为卢卡奇的老师,在分析劳动分工对“文化悲剧”产生的作用的基础上,深入地分析了由于分工产生的异化状况。卢卡奇在对席美尔理论的批判性反省中认识到物化的商品结构线索。更重要的是卢卡奇实际上是用韦伯的“合理性”思想来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进行解释并试图由此拓展和深化。卢卡奇通过颠倒韦伯的“合理化”思想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集中在可量化和可计算性的过程上,使得自己的物化理论有着双重逻辑,即马克思意义上的商品结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物化与韦伯意义上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物化。也就是说,与马克思在《手稿》中通过异化对资本主义的控诉主要是集中在生产关系上不同,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则重在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当卢卡奇把物化的全部愤怒都宣泄到现代工业文明的可计算性的量化过程上的时候,他的物化理论的逻辑实际上是来自韦伯,而不是马克思。”[5] 5此外,卢卡奇关于物化的思想受到了黑格尔哲学影响,正如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再版序言中关于异化问题讨论时所说:“至于对这一问题的实际讨论方式,那么今天不难看出,它是用纯粹黑格尔的精神进行的。尤其是它的最终哲学基础是在历史过程中自我实现的同一的主体——客体。”[2] 18在黑格尔那里,这一问题是以一种纯粹逻辑的和哲学的方式提出的:通过消除外化,自我意识向自身返回,并由此实现同一的主体——客体。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把这一逻辑表现为一种社会——历史过程,将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放进历史视阈中。
其次,从马克思和卢卡奇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来看。马克思写作《手稿》时,资本主义处于自由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还不是由于科学技术起的作用。同时,阶级矛盾非常突出,无产阶级发生革命是历史的趋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还没有丧失或颓废的信号。这就使得马克思的异化思想是在生产劳动逻辑上进行阐发的,并且在扬弃异化的道路上也诉诸的是社会生产的发展所带来的私有制的消灭。而到卢卡奇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已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生产到文化领域甚至到人的心灵,科学技术得到广泛应用。资本主义商品结构的“幽灵般的存在”吞噬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革命意识被资本主义的一些“虚假”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消磨了。同时加上工人运动在西欧的失败使得卢卡奇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进行了深入地思考。
二、 标异生新:两种“异化”呼喊的隔空共鸣
首先从理论向度上,马克思和卢卡奇都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方式出发,在控诉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都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物”给人所带来的压迫感。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异化的四个规定可以说是从两个维度对异化本质做出的说明:一方面,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是“物的异化”;另一方面,人的劳动、人的类本质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是“人的异化”。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关于物化本质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来阐述:“这种情况既发生在客观方面,也发生在主观方面。在客观方面是产生出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世界(即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的世界),它的规律虽然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作为无法克服的、由自身发生作用的力量同人们相对立。……在主观方面——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异于人的客观性,它正如变为商品的任何消费品一样,必然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自己的活动。”[2] 153在这里,卢卡奇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对物化的阐述同样遵循了物的异化与人的异化两个不同维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与卢卡奇的理论走向了统一。
其次,从价值关怀上。异化与物化的思想都体现了马克思与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下受压迫和奴役状况的同情,以人及其自身的发展为出发点来考察异化现象。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人自身,异化使人的“类本质”丧失。《手稿》中马克思对异化的阐述处处彰显了对人的“类本质”丧失的同情以及愤怒,在马克思的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受到他博大的人文主义胸怀和强烈的对“异化世界”的控诉。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同样有着这种情怀,他在谈论物化时始终没有脱离人的根本是什么这一问题。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卢卡奇对物化的阐述正是沿着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情怀出发的,始终都含有浓郁的马克思话语。
三、结语
在考察异化的理论本质以及扬弃异化的道路上,马克思的《手稿》和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深刻而具历史性的观点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和思考。只不过二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这当然是由于其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以及哲学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但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有着真知灼见的合理之处。马克思所遵循的是一个“生产”的逻辑,卢卡奇遵循则是“观念”逻辑。在我们当代历史条件下,对异化的真正扬弃,需要广阔的理论聚集和不同的思想观点,马克思和卢卡奇从不同的理论维度都给了我们深刻的思考视阈和理论指示。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 周立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及其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回望孙伯鍨教授的《卢卡奇与马克思》
——读《卢卡奇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