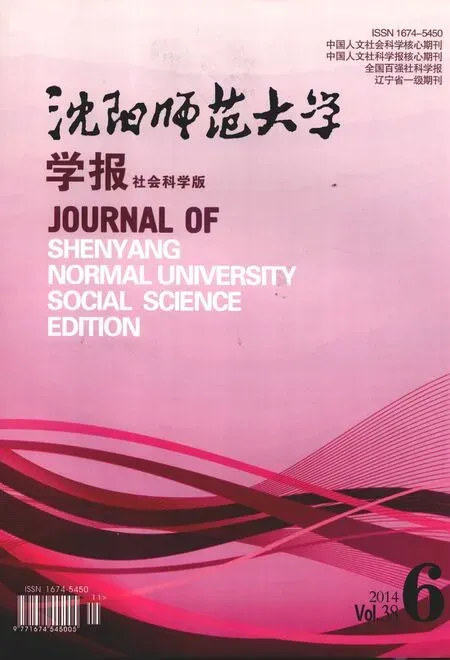语言实践表现符号论的理论基础与思维方式
于全有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语言学与文学】
语言实践表现符号论的理论基础与思维方式
于全有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语言实践表现符号论作为一种新的语言理念,是建立在对传统的相关语言本质理念扬弃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层次语言本质论。而导致这一理论基础形成的原动力与根本因素,是有关语言本质问题认识上的思维方式的转变。传统语言观对语言本质问题认识上的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传统本体论哲学追求抽象同一的本质与抽象同一的原则、将决定一事物为该事物的本质理解为是单一性的这种思维方式上。而语言实践表现符号论则是建立在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认识事物的多层本质的实践思维方式上。这种致思途径,有益于克服传统语言本质观中存在的那种追寻抽象单一、脱离人与社会的语言本质思想,以便从根本上肃清并解决传统语言观中存在的诸多相关问题。
语言实践表现符号论;层次语言本质论;思维方式
语言观问题与对语言的本质认识紧密相连,历来是语言研究的重要核心问题。历史上,人类在有关语言本质问题的相关探索中,曾出现过语言工具论、语言符号论、语言世界观论、语言生物机体论、语言天赋论、语言本体论、语言社会现象论、语言行为论、语言认知能力论等种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理性认识。近年来,笔者曾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语言的本质观重新进行了系统的层次性构建,认为语言本质是一个由底层本质、一般本质、特殊本质构成的层次性系统,语言的底层本质是人类的实践活动,语言的一般本质是表现,语言的特殊本质是符号,并以此为基础,提出“语言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音义结合的表现符号”[1]。这一观点,后来在学界一些相关的文章中被简称为“语言实践表现符号论”。
近来有感于学界部分同道对语言实践表现符号论在理论基础、思维方式的转变上所涉及的一些相对深涩问题之逻辑理路的相关探询及简易化的诉求,始感这一本在笔者前期的系列相关论著中已多有比较详细的论述的问题,有必要对其中所触及到的几个核心问题的逻辑理路再做一相对简明、相对较易于把握的梳理阐释。
一、关于语言实践表现符号论的理论基础问题
语言实践表现符号论得以建立的重要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对传统的相关语言本质理念扬弃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层次语言本质论。而层次语言本质论这一思想的形成,又源于相应的哲学思维方式指导下的对传统语言本质论理性认识上的转变。
传统的语言本质论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不论是语言工具论也好,语言符号论也好,还是语言本体论也好,语言世界观论也好,抑或是语言生物机体论、语言天赋论、语言社会现象论、语言行为论、语言认知能力论等种种其他诸论也好,其对语言本质的理解与认识,往往都是单一性质的。这种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实际上并不符合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上的客观实际,没有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其实是有层次性的,自然也就难以认识到语言的本质其实也是
有层次性的。
事实上,事物的本质本来应该是一个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与内在的逻辑联系的、多层次的结构,它是具有层次性的。事物的本质的这种层次性,指的是某一事物的本质可能在事物的不同层次上表现出来,或者是揭示本质时,可能有不同层次的揭示与深入,可能有不同层次的划分。本质的这种层次性,源于事物的层次关系与属种关系的相对性与多样性及人们对事物本质认识的过程性[2]12-13,合乎认识论的一般原理。关于这一点,无论是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所做的理想层面上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种人的类特性揭示、[3]现实性层面上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这种人的特性的揭示[4],还是从列宁的“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不断深化,以至无穷”的论述中[5],我们都可以从中领悟到其对事物本质的理解上的层次性意识的影子。
从人类历史上已有的有关事物本质的理念上看,揭示与把握事物的本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发掘事物或现象合乎逻辑的属或类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从马克思到列宁,从古典哲学到现代形式逻辑,均大抵有过此类共性意识。[2]8-14
从哲学上看,事物的属性通常又是由系统属性、功能属性、自然属性这样三个基本层次构成的。所谓的系统属性,指的是一种源于系统的关系属性,比如说“狗”属于“动物”等;所谓的功能属性,指的是事物经人类活动作用后的性能上的属性,比如说用狗来看门;所谓的自然属性,指的是事物自然具有的物质结构方面的属性,比如说事物的形状、颜色、味道、组织等。事物的上述种种不同层次的属性,既让我们看到了事物自身属性的相对多样性与层次性,也昭示着我们在思索、挖掘事物的本质时,必须要注意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注意把握本质的层次性。我们对语言本质的思索与发掘,自然也不能从游离于事物本质的这种层次性属性之外去把握。
一般而言,事物本质的层次性可以反映在底层本质、一般本质、特殊本质这样三个基本层面上。底层本质属于事物基础层次上的本质,指的是托起一事物为该事物的底部层面上所蕴含的本质,它是种的最高的属或类,也称之为形式本质,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与多样性等特征。一般本质属于事物核心层次上的本质,指的是潜隐于同类事物背后,既为该事物的每一个现实的个体所不完全地表现、又在不断地趋近的那种性质(类本质)。它是事物未来状态下的本质,规定着该类事物的共性,具有理想性与价值性等特征。特殊本质属于事物表象层次上的本质,指的是作为种的事物或现象最低的属,是一事物自身所特有的、决定一事物之所以为该事物的那些性质、动作、关系等,它是事物在现存状态下的本质[2]14-16。比方说“驴车”,如果我们将其定义为“驴拉的载运车”的话,那么,驴车的最高的属便是“车”,这“车”就是它的底层本质或叫形式本质;“载运”就是驴车的一般本质,具有理想性、价值性等特征;“驴拉”则是驴车的特殊本质,具有现实性等特征。事物本质的上述这种层次性特征,与前文提到的事物属性的一般层次特征之间,具有内在的、大体相应的联通关系。
按照这种本质的层次性理念,语言本质在逻辑上自然也可以有底层本质、一般本质、特殊本质等层次之别。语言的底层本质自然也是属于语言的基础层次上的本质,指的是托起语言之为语言的这种底部层次上所蕴含的本质,也就是跳出语言本身来看支撑语言的底层之本质。它是语言最高的属或类,是语言的形式本质。[2]142语言的一般本质属于语言本身核心层次上的本质,它指的是潜隐于语言现象中、既为语言的每一个现实的个体所不完全地表现、又在不断地趋近的那种性质(类本质)。它规定着语言的共性,使语言万变不离其宗。语言的一般本质是语言未来状态下的本质,具有理想性与价值性等特征。[2]157语言的特殊本质属于语言的表象层次上的本质,指的是最接近语言现存生态的、语言最低的属,也就是语言本身所特有的、决定语言之所以为语言的那些性质、关系等,是语言在现存生态下的本质[2]160。
依照上述这种语言层次本质之原理,根据我们的系统考查[2]142-163,语言的底层本质是人类的实践活动(简称“实践”),这不仅可以在相对宏观的层次上,从语言是人之所以成为人、成为有别于其他动物的社会性意义上存在的人的重要标志上,可以反映出语言的人之属性,而且更可以在相对具体的层次上,从发生于人类自身有别于动物的存在方式——实践——活动中的交往实践的需要对语言的催生上、从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是语言发展的源头活水上、从人类的实践活动是语言习得的基础上、从人类的实践活动是语言应用的基础与准绳上,多角度、多层次地更进一步反映出语言的人类实践活动之属性,即语言的底层本质——实践之属性;语言的一般本质是表现(“表”为“表述”“表达”,“现”为“显现”“呈现”,简称“表现”),这不仅可以从人与人之间交往沟
通的目的、表达与接收的过程、价值、目标上,可以反映出语言的表现之本质,而且还可以从语言“器”的性能上能够成为联通表达与接收的桥梁与纽带的这种工具性上、从语言“道”的性能上能够以其呈现或显现的功能反过来影响与制约人的思想行为的这种反作用性上,反映出语言的表现之本质,还可以从源于语言的底层本质中的交往实践的逻辑运行,必然要求交往实践中的语言之理想性与价值性的选择是能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具有表达与呈现接收这样功能的语言上,反映出语言的一般本质——表现之属性;语言的特殊本质是符号,这不仅可以从现存生态的语言之音义结合状态上,反映出语言具有符号之本质属性,而且也可以从建立在语言底层本质“实践”之基础上的语言一般本质“表现”这一属性得以实现的现实存在载体的必然需求上,反映出语言在现存生态上具有可以承载思想内容的特殊本质——符号之属性。
上述这三大层次的语言本质构成了一个有关语言本质问题的整体,形成了一个与事物的一般属性层次相应的、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的、有层次的语言本质系统。由语言的底层本质、一般本质、特殊本质这三层语言本质所构成的“实践——表现——符号”系统,既是对语言的底层本质、一般本质、特殊本质这三重本质逻辑性的层次反映,又是对语言的底层本质、一般本质、特殊本质这三重本质序列间的逻辑催生关系与实现关系的反映,也是人的生存、实践与语言间的逻辑关系的反映。同时,它还是对语言历史的、未来的、现实的本质状态的反映,也是建立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上的对传统的语言工具论、语言符号论、语言本体论等语言本质观的合理内核的合理吸纳与融通的反映。
这为建立在此理论基础之上的关于“语言”概念的再探讨与重新定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正是在此理论基础上,我们通过对所搜集到的近百余年来中外比较有代表性的关于语言的一百二十余种定义中对语言本质揭示情况的比较分析,依据下定义的基本要求与基本规律,对语言的概念重新进行了定位,认为“语言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音义结合的表现符号”。
二、关于语言实践表现符号论的思维方式问题
尽管语言实践表现符号论赖以形成的理论基础是层次语言本质论,而层次语言本质论这一思想的形成又直接源于对传统语言本质论理性认识上的转变,但尚未触及到本理论更根本的层次上。导致形成语言实践表现符号论更深层次的原动力与根本因素,是语言哲学研究上的思维方式的转变。
在人类几千年来有关语言本质问题的探索历程中,不管是以索绪尔等为代表的语言符号论也好,以列宁、斯大林等为代表的语言工具论也好,还是以洪堡特等为代表的语言世界观论也好,以乔姆斯基等为代表的语言天赋论也好,包括以施莱歇尔等为代表的语言生物机体论也好,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为代表的语言本体论也好,以斯大林等为代表的语言社会现象论也好,以奥斯汀等为代表的语言行为论也好、以帕默尔等为代表的语言声音论也好,直至以莱考夫、约翰逊等为代表的语言认知能力论等,其对语言本质的理解与认识,往往都是单一性质的。这种状况的出现,归根结底,与这些传统语言本质论对语言进行理性思索时的哲学思维方式有着很大的内在联系。这些理论在对语言本质问题理性思索时的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还是或停留在传统本体论哲学追求抽象同一的本质与抽象同一的原则、将决定一事物为该事物的本质理解为是单一性的这种思维方式上。这也是传统语言本质论所存在的若干弱点与不足中,最根本性的、也是最致命的地方。
所谓的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思维方式,通常是一种从预先设定的“本体”出发,去理解存在、把握现实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一般的致思路径是:先是把现实的事物归结为它的初始本原或本真状态、绝对本性,然后再以它为根据去认识、理解现实事物,即是一种看重先定的抽象原则、从第一原理出发去推论现实的方法。这种思维方式把抽象的原则看得比生活更真实、比现实更重要,在原则与生活、真实发生矛盾时,常常以唯一不二的原则去修正生活的情况。而这种思维方式在涉及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理解时,又采取把事物分裂为本体界与现象界、再归结为单一本质的存在的方式(裂二归一方式),追求抽象同一的本质与抽象同一的原则,把丰富多样、复杂矛盾的事物归结为单一性和绝对化的本质,而很难容忍两重化、对立性、矛盾关系的本质存在。即或承认这些情况的存在,也只肯定于现象界而不允许其进入最高的本体界。显然,按着这种传统的本体论哲学思维方式去思考、分析、解决问题,必然会造成理论脱离现实、脱离真实的生活实际、抽象化等弊端[2]133-134。
从前文所及的以语言工具论、语言符号论、语言
本体论等为代表的种种传统语言本质论的基本理论、核心理念上看,这些传统的语言本质论,从哲学思维方式的角度审视,无疑已深深地折射出传统本体论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子。尽管这些理论观点所出现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并不一定相同,其创立者也并不一定对自己的哲学思维方式有过明晰的理性意识或理性自觉。比如说,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符号论之语言本质观为例,该理论不仅在将语言的本质归结为单一性质的“符号”上,尽显其追求抽象同一的本质与抽象同一的原则、将决定一事物为该事物的本质理解为是单一性的这种传统的本体论哲学思维方式,而且在其一系列的语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等二元对立思维后,对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所做的“语言”“共时”等选择中,也可以明显地体味出传统本体论哲学的那种追求抽象同一的本质与抽象同一的原则之思维方式对其理论思维的影响。
语言实践表现符号论的确立,正是建立在对种种传统语言本质观及其思维方式之不足的变革的基础之上的。语言实践表现符号论的哲学思维方式是实践思维方式。
实践思维方式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是其区别于以往旧哲学的根本所在。这种思维方式是从人的活动出发,从人的历史和现实的真实本质出发,去认识、理解世界,把实践作为理解、认识、解决一切哲学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从而彻底地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建立起了新的实践思维方式。在这种实践思维方式下,不仅传统思维方式不能解决的自然世界与属人的世界对立而不能统一问题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得到了统一,而且以往笼罩在哲学世界中的种种诸如思维与存在、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等矛盾分歧问题,都将在实践的基础上得到合理的化解与消弭,达至深层次的统一[2]134。
立足于这种实践思维方式之上的实践语言观认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现实的社会意识,它首先是一种具有物质属性的社会交往实践活动,是社会关系、交往形式的产物。从根植于交往实践基础上的现实的人的语言交往活动出发去理解、认识语言问题,是这种语言观的出发点与立足点。[2]127-136这种特别注重从现实的人的语言交往活动出发去理解、认识语言的思考问题的立场、观点、方式,恰恰是许多传统语言观在理解、认识语言问题时的不尽如人意之处,更具有旺盛的理论活力与思想的穿透力。依据这种实践的思维方式去观照历史上已有的种种传统语言观,我们不难会发现,原来许多问题的症结,恰恰是由于看问题的不同思维方式造成的。比方说,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符号论之语言本质观、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语言天赋论之语言本质观,以及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语言本体论之语言本质观等,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着脱离人的现实的语言交往活动去抽象地论说语言问题。当索绪尔把语言和言语加以分离,只是在就语言而研究语言时,当乔姆斯基宣称人脑先天地存在一种语言能力时,当海德格尔把言说归结为抽象玄奥的大道之言时,当伽达默尔提出“语言向我们诉说”比起“我们讲语言”在字面上更正确时[2]137,这种因看问题的不同思维方式造成的抛开具体的语言实践去抽象地谈论语言或谈论抽象的语言的做法,其看问题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脱离语言实际、脱离语言实践的片面性,便实属难以避免了。现实往往是:理论是一回事,理论能不能和实践相契合细究起来就可能又是一回事了。关键在于审视问题视域的维度与高度。
[1]于全有.语言底蕴的哲学追索 [D].中国博士学位全文数据库,2008;于全有.“语言”定义的重新定位 [J].辽东学院学报,2011(2):58-61;于全有.20世纪以来人类有关语言本质问题的探索历程[J].辽东学院学报,2011(3):42-55;于全有.语言本质理论的哲学重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41-170.
[2]于全有.语言本质理论的哲学重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73.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13.
【责任编辑 杨抱朴】
H0
A
1674-5450(2014)06-0073-04
2014-10-11
于全有,男,辽宁丹东人,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语言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语言学与语言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