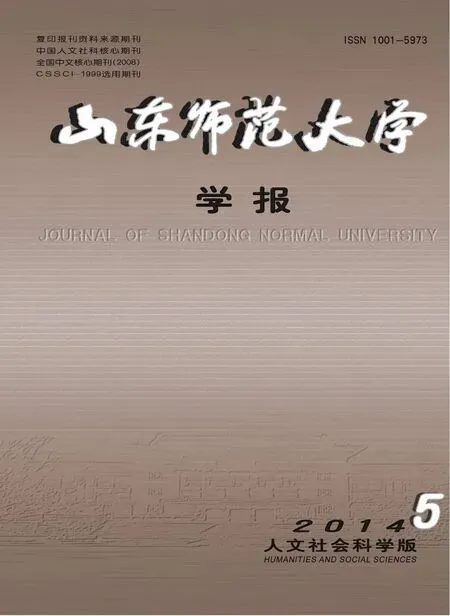平原精神:“内爆”的美学张力与厚重的艺术世界
——李登建散文创作论*
房 伟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250014 )
平原精神:“内爆”的美学张力与厚重的艺术世界
——李登建散文创作论*
房伟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250014 )
李登建的散文艺术,以平原精神作为贯穿散文的内在精神标高和尺度;以内敛深沉而又内郁纠结的情感反思,建立起了“内爆”式的“平原哲学”。他擅长从具象处入手,使用华美丰饶的抒情思语与散发着泥土芬芳的乡言俗语,而“平原”的文化地理意象和“黑色”的色彩意象,构成了李登建散文中的两大核心意象。
李登建;散文艺术;平原精神
散文这一古老文类,从文化深处走来,经受现代欧风美雨洗礼,接受当下大众文化考验,在不断突围和自我完善中,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散文是作者面对读者抒发情怀、感叹人生、诉说忧乐的最真诚、最真挚的艺术,因此,在文学创作的园地里,散文以它可贵的‘真’独树一帜。”①王景科:《中国散文创作艺术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页。尚真,扬善,求美,是散文的核心。李登建,一个齐鲁大地上走出来的“精神之子”,在梁邹平原深深扎下了精神的根,吮吸着民间文化的雨露,找到了灵魂皈依的家园,并建构起了诗化的生命哲学体系。张清华曾盛赞李登建:“他已经停不下来了,这个外表沉默、谦和与矜谨的人,这个内心敏感、细腻和好强的人,他内心的雨雪一直下着,风刮得呼呼作响,一架收不回来的风筝,在岁月和思绪的空间里一直飘呀飘着,那是他寻常看不见的浪漫。”②张清华:《黑火焰在心中燃烧》,《山东文学》2002年第3期。著名作家张炜也曾说:“登建是我喜欢的散文家之一。他的文章像他的人一样敦厚、深沉、质朴。他的文字能够给人格外的温暖和特殊的安慰。他笔下的乡村有别于我所熟悉的胶东乡村,那是另一番情致、另一个天地。可她们又是相同的:同样的淳朴、亲切和安详。”③张炜:《礼花为谁开放·序》,《礼花为谁开放》,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0年,第1页。他们都发现了李登建散文的创作主体的秘密,即敏感心性与宽容善良的品德的结合。
一、李登建散文的三重境界
李登建写乡村,总是放在故乡梁邹平原的背景下,形成了评论家所概括的“大平原系列”。他眼里的梁邹平原古老、年轻,博大、浑厚,喧闹、安详,神圣、庄严,他力图对平原作全方位、立体的展现,塑造一个立体的、丰富多彩的“平原”。他写平原上的树、草、庄稼、牛羊、土路、田埂、老河、古桥、荒坟、瓜棚、水车、泥塘,以及平原上各种各样的色彩和声音。他表现农人的勤劳、善良、朴实、敦厚,也表现他们的愚昧、保守、狭隘、自私。他把一腔激情和热血,都融汇到了对这块土地的思考之中。他歌咏着故乡,回忆着童年,反复咀嚼着那些人和事,他反思社会的不公正,反思天地不仁给人类带来的磨难,反思博大而韧性的平原精神的实质,也常常反省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其真诚,其勇敢,其痛彻,其深刻,其厚重,常常让我读到那些“敲击心灵”,从而“煅烧”出来的文字,不禁击节赞叹。他把对平原精神的感悟,投射到那平原上的人和事上,在厚重博大的平原艺术世界中,显示了几乎是“内爆”式的散文美学张力。
与诗歌和小说相比,散文的“变”不如“常”来得多,很多西方文艺理论,面对散文时,常有难以下嘴的感受。尽管鲁迅曾认为:“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散文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和戏曲之上”*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02页。,然而,正因散文在形式和内容上的“散”,它的理论可阐释性相对比较弱。因此,小说和诗歌的理论经典化过程,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也要相对大于散文。这在每年学术报刊的目录索引中,也会发现端倪。其实,这些流行看法,存在很多“意图谬见”。散文,因其“散”,似乎不足以担当第三世界国家被动现代化过程,“国家民族表征”的“力比多”隐喻(詹姆逊语)的重要功能。更由于“散”,及个体化特征,散文的意识形态性、思想性,似乎也不足,不能像小说和诗歌一样,完美地完成“叙事”和“象征”的任务,只能作为“抒情”的辅助功能出现。长期以来,散文的理论研究,停留在“创作论”的写作学基础上,缺乏深入系统的归纳。但是,由此而轻视散文,无疑是短视的。由于门槛低,散文对普及文学教育,有很大作用。而由于“自由散漫”,散文在培养个性,熏陶文化,丰润国民丰富敏感的心灵,提倡国民的独立思维和独立表达上,也有其他文体难以比拟的优势。老一辈评论家田仲济认为:“散文在个人文学之尖端,是新文学的一个潮头”*田仲济:《序言》,俞元桂等主编:《中国现代散文史》,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页。。对散文的研究,特别需要摆脱简单的创作论的角度,从更为宽广的艺术视野和理论视野,对当代散文作品和作家,进行更为系统和综合的研究。
那么,李登建散文的价值与意义何在呢?散文创作有三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即所谓写实。散文最讲“写真实”,通过对人生和社会的观察,写出自己的理性认识和感悟,虚假的做作,会使得散文的味道全失。而第二个境界,即所谓写情。好的散文,都是真情实感,是抒情的艺术,怀人纪事,感时忧国,都能在情感的自然流露中,有一份特别的感动。然而,散文的抒情不同于诗歌和小说的抒情,这既是一种节制而理性的抒情,又更多是一种“真情实感”,没有了真情实感,散文的抒情,就成了无病呻吟;而没有节制的情感表达,就太浓太烈,容易丧失散文的理性。第三个境界,就是所谓“写思”。也就是说,散文还应该从单纯的写人记事中超越出来,从而表达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层次思考。这种思考,一方面,使得散文拥有了理性平和的气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散文建立“反思”的现代性品格。散文融合了叙事和抒情的双重因素,一方面,给叙事赋予了深沉的情感,另一方面,则给予了抒情以叙事的理性和反思。而散文自由的文体表达,也使得散文善于模仿日常生活,并深入到生活的内在思维中,在真实性中达到对现实的反思。散文的这种特性,也决定了散文,特别是现代散文,也应是一种具有现代品格,特别是现代“反思”品格的文体。
李登建的散文,恰恰具备了这三重境界。李登建的散文,有比较典型化的艺术时空,大多展示的是梁邹平原上惯常的生活场景、自由丰富的生命体验。同时,灿烂的表达与厚重的体验互为表里,凝重的现实与超越性的存在共荣共生。“民间体验”与“平原情结”,构成了李登建生命意识的审美骨架和精神性的统摄。故土与乡情,是他永远也化不开的情结。寻根与乡恋,是他心中永远的歌谣。其实,这又何尝不是我们悠久文化传统无意识繁衍的产物?只是,我们在他的散文中,看到了一条生命的红线,将这“文化的根”,迁到了梁邹平原上,让那乡土情结生根发芽,然后瓜熟蒂落。翻看这些文本,沉郁、古老、悲悯,厚重、雄浑、苍凉,勤劳、朴实、保守,目击、守望、坚守——这些标志性的“精神文化符码”就会扑面而来,接通我们期待视野中业已荒疏的审美经验。于是,平原上的小村、老石桥、打麦场、红高粱、马蹄湾、飘洒的酒香、劳动的场景一并被纳入作家笔下,并沾染上了浓郁的感情汁液,“不管他美还是不美,不管他稻谷飘香还是荒歉年景,也不管他洒满阳光还是被风雨击打、被霜雪掳掠过,我都无法不热爱这块土地。我是他的儿子,他是我的根。”*李登建:《平原,走来了你泣血的歌者》,《散文(海外版)》2005年6期。这就是土地情结的当下言说和作家生命意识生动的反映。《大山深处》中的守庙人,一生兑现他对大山的承诺,对山中文物的承诺。他死后,多病的老伴和瘫儿子继续着他的遗愿,依山而活,生活的贫乏并没有使他们退却,大山给予了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怀,这不是理想的桃花源,却充满着生活的智慧与坚韧。“就这么活着吧!”*李登建:《大山深处》,《文艺报》2014年9月22日。“老伴”这句话里蕴含了生活的艰辛,却始终有一股精神支撑,这是对大山的承诺,对儿子的爱,对生的意志。在光怪陆离的社会中,这种土地情结显得弥足珍贵,这其中也包含着作者对人性的思考。故土和乡情,实际上是他寻根冲动的源泉,在不断与这情结的相互同化中,我们省察到了一个平原歌者的情感逻辑。那些有关梁邹平原的记忆,是历史经过绵长的岁月淘洗后所留下的“根”,也是他目击现实、守望未来的立足点。秃叔杀牛的背后,却难掩瘸大爷的悲伤(《杀牛》);面对美丽的故乡,“我却怎么也快活不起来”*李登建:《裹在雾霭里的村庄》,《平原的时间》,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8年,第69页。;我独自在墓地徘徊,与逝去的亲人对话,也着实令人心惊这生存的苍凉(《西边大道东边小河》)。生命体验,就是这样在和谐与不和谐间摇摆,在现实和未来的基点上徘徊。尤其《齐王之殇》,昔日古朴、温馨的村子,如同李苦禅的水墨画一样好看,却面临着强拆的命运,村人对故土的依恋与坚守,与拆迁队誓死抵抗。但这终究是困兽之斗,城市化的车轮以不可违抗之力,碾碎古老文明为自我开道,古老文明在侵蚀中趋于颓败。老族长自觉愧对先祖,毅然吊死在了千年槐树上,这是预言与前奏。沧桑的故土大地,终究在城市文明中奄奄一息,颤颤巍巍走向没落,留给我们一个巨大而悲伤的背影。同时,对抵抗的村民而言,这也是一场人心的考验。面对金钱的诱惑、权力的威逼,人心的贪婪、妒忌、惧怕与猜忌,都彰显无遗,质朴的人心也被金钱社会侵蚀着,这才是最悲凉之处。李登建立足于此,洞察了故土与乡情在当下社会中的无奈与尴尬,这也是作家精神内涵和意义空间所合成的思想张力和美学意义所在。
李登建以“平原精神”作为贯穿散文的内在精神标高和尺度,以内敛深沉,而又内郁纠结的情感反思,建立起了独特的平原哲学。这是属于乡土梦的哲学,充满了对乡土的依恋,也有着对乡土消失的反思。这又是一个苦难的哲学,在这些有着苦味和涩味的散文中,李登建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写了一个个在人世间饱经沧桑的面孔,一件件令人难忘的事情。勇敢的思想者,总是从自身的批判和剖析中,获得前行的力量和内在的升华。作者既批判社会的不公正,讽刺社会的腐败,又敢于挖掘自己灵魂深处的困境和妥协,卑怯和屈服。《闭上你的眼睛》中,作者在海滨度假,看到的皆是“御道”与“皇宫”,政府官员的特权领地、高墙伫立,平民百姓的简棚陋舍,这鲜明的对比中是社会腐败的表征。高墙深院,阻隔了官民之间的交流与信任。人民的公仆已然端坐于上,百姓只能在仰望中噤若寒蝉,社会公信力的降低,工作效率的低下,都在这俯看与仰视之间决定。在赛若天堂的海滨小城,也只能“闭上你的眼睛”,而这背后尽是无奈与悲凉。李登建的散文是“小”的,他记述梦中记忆中的石桥,小村的风闻逸事,生活中的困惑悲伤,黑伯的酒杯,于老三的鞭技和哥哥壮志未酬的理想;李登建的散文又是“大”的,擅长以小见大,小开口而深挖掘,从小处看国家民族的历史沧桑,从小处为人格和理想树立起别致的审美风范。《众人败给了一条狗》即是典范之作,因为别墅富豪的狗吠吵得小区不宁,这样一件小事却演出了世间百态,生活万象。妇女们的同盟作战与斤斤计较,物业公司的利益至上与偷奸耍滑,富豪的财大气粗、敷衍了事,“甲等着乙出面,乙想借丙的势,丙在探丁的口风”*李登建:《众人败给了一条狗》,《山东文学》2012年第9期。,问题相互推诿,这现代版的“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终究使得解决无果。更有趣的是官员的态度,书记说“任他叫”,局长的“好言相劝”、“苦口婆心”,这些官方的语言艺术看似箴言,实则空洞敷衍。一件小事暗喻了社会的众多现象。这场“战争”最终以狗的“失语”而告终,不战而胜却被大家当做炫耀的资本,这“阿Q式的胜利”延续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思考。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李登建在当下社会中重新对国民劣根性进行反思,在戏谑中建立了独特的审美风范。
二、文体创新:色彩美学意象与诗化语言张力
散文文体的争论,一直连绵不休。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将散文放在了大的诗的艺术之中。散文真正具有独立的艺术品格,是黑格尔所说的史诗之后的事情了。而现代有所谓“小品文”、“美文”等定义,到了当代,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定论。余光中在《缪斯的左右手――诗和散文的比较》中,以散文的功用为分类,将之分为议论文、叙事文、描写文、抒情文,还有身份暧昧的杂文。大陆散文评论家林非却说:“狭义散文以抒情性为侧重,融合形象的叙事与精辟的议论;而广义散文则以议论性和叙事性为侧重,在不同程度上融合抒情性”。林非将抒情散文定义为狭义散文,无疑突出了散文抒情的特质。也有的理论家试图跳出窠臼,如童庆炳在《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中,用“典型、意境和意象”三大模式为分类标准,将散文归于“典型――形象模式――再现类”;*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8页。而刘锡庆则“弃类成体”,他的核心文体概念是“艺术散文”:“它一般采用第一人称手法,以真实、自由的笔墨,主要用来袒示个性、抒发感情、裸露心灵和表现生命体验的艺术性散体之作”。当代学者喻大翔等人则提倡更为宽泛的散文概念:“凡创作主体直接将个性、情怀、观点等以散体文句艺术地表达出来,都可以视为散文”*喻大翔:《用生命拥抱文化——中华20世纪学者散文的文化精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274页。。如果说,小说通过故事来展示我们对世界的认识,那么,散文则更贴近“个人化的真实抒情”。它的抒情,既不同于诗歌多变的形式,也不同于小说的深刻和隐含,而是一种对世俗和身边事情的概括。因此,散文的审美陌生化的难度很大,它看似违背一般的艺术规律,但其实是一种调整后的审美距离,表达人们对自己生活的理解。当然,散文也可以言志,抒发宏大的思想,但散文式的抒发,也绝对不类小说和诗歌,而是更为自由的表达。如果我们对这些概念进行粗疏的整理,就会发现,其实散文文体分类的标准是:表现内容的“真”与表现形式的“深切与自由”。而李登建的散文,在散文文体的创新方面,则很好地体现了这两者的结合。
仅从一个个朴实无华的题目,如《站立的平原》、《平原的时间》、《黑火焰》等,我们似乎可将李登建的散文归于乡土散文一脉。李登建是这样沉迷于平原情结和民间文化。大量方言口语,散见于文本的角角落落,语言的返璞归真,成为了主导性风格。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则构成了文本的底色。那些乡土的传奇,乡野的爱恨情仇,城市生活中的困顿和无奈,都化作了一幕幕沉重的“黑风景”。而作家对于文字形式的敏感,对散文语言表现力的苦心经营和语句锻炼,对散文语言的色彩、弹性、温度和密度、表情的体察,灵活的叙事视角和多变而丰富的语汇,都使得那些土气的乡村故事,具有了最为性感而美丽的形式感。李登建说过:“我认为是否真诚,有无深挚的感情和深刻的思想,是一篇散文成败的关键。一篇好散文要有思想含量,也要有技术含量,二者不可偏废。”可以说,李登建是一个“贪心”的散文家,他追求“完美”的散文艺术,试图用最精美的散文语言和多样化的表现形式,来表现最为宽厚博大的平原精神和意志。这便是李登建的散文。李登建散文的抒情风格,浓厚深沉,而又不乏爆发力,而叙事风格则娓娓道来,如述家常,内蕴而节制,叙事视角和方法则灵活多变,但是他的抒情和叙事,却都有着深刻的哲思。
李登建的散文,有诗化渲染的倾向。作家擅长从具象处入手,细致入微地模拟某种事物的存在,既能调动一切感官感受,从各个角度写出事物细节化的具象形态,能利用拟人、拟物、象征等修辞手段,将之形象化为一些仿佛具有生命灵光的意象,既能有非常感性化的体验,又能将之抽象为某种哲思的概念。例如他在《乡土》一文中写道,“太阳变成一口泉眼,汩突汩突喷涌橙红的彩流,这橙红的彩流泻向无垠的大地,泥土经它的濡染,呈现出一种纯金的颜色”*李登建:《乡土》,《平原的时间》,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8年,第247页。。而李登建的抒情散文,还刻意营造着某些华丽铺陈、对仗工整的骈文色彩,常在意象内部造成富于动感而气势恢宏的“文气”,使得散文气韵生动,原有的生命意识得到了更好的张扬,如他这样写庄稼:“绿头巾、绿衣、绿袍,绿色的旌旗翻卷,长矛密如丛林,威风凛凛,势不可挡。转眼间,平原好像打了一个滚儿,它们又掀起欢庆胜利的热浪……”*李登建:《啊!平原》,《中华散文》2001年8期。。
灵活多变的叙述,则是李登建散文的一大特点。这种对叙事性的重视,体现着李登建散文对小说笔法的吸收和借鉴。“散文正以其内省的倾向和自由的天性侵犯着小说,二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是件好事,既不必保护散文的贞操,也用不着捍卫小说的领土完整,因为放浪的野合和痛苦的被侵犯之后美丽而强健的杂种就要诞生了,这杂种必定胜过他的父亲。*史铁生:《也谈“散文热”》,《好运设计》,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54页。”《老黑》是一篇发人深省的散文。饥饿的年代,“我”和一群少年被饿得头晕眼花,而我养的一条土狗——“老黑”,就成了我们打牙祭的对象。人类的贪欲,让忠心耿耿的老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在我的心灵中留下了沉重的枷锁。该散文在叙事语言上的一大特点,就是第二人称“你”的出现,使作家以非常先锋化的小说笔法,在散文文本内部,形成了老黑的视角和我的视角的双重“对话性”话语,从而表现了作家对自己灵魂的拷问与逼视。老黑,仿佛变成了作家良心的一块试金石和裁判之笔,并进而让作家对人类生存的很多本质性的思维方式,进行深刻的反思。
而华美丰饶的抒情思语,与散发着泥土芬芳的乡言俗语,在李登建的笔下,分别成了两块被精心锻造的语言“精铁”,共同支撑起了李登建散文大厦的语言骨架,并形成内在的、散文文体的对话张力。那些抒情哲思性的语言,充满着令人惊奇的华美动感的意象,丰富感人的形象,理性沉潜的深刻思辨,抒情而不放纵,哲理意味浓却决不晦涩,只从那些常见的事和人出发。例如,作家是这样描述他心目中的梁邹平原的:“说到这块土地,我眼前就站立起一个面色黧黑的北方汉子:他阴郁着脸,身上黑黑的肌块沉默着,显得有点疲惫和苍老,但是他的骨骼却瘦硬而强健,眉宇间透着一股倔劲儿,使你相信他不是那种轻易服输的人”*李登建:《平原,走来了你泣血的歌者》,《散文(海外版)》2005年6期。。以乡民形象入手,将平原精神在拟人化的描述中展开,显得非常别致。而作家的描写状物,也非常鲜活,富于动感和色彩,仿佛一块凝重而精雕细刻的彩塑。例如,他这样描写乡间的水渠:“水渠仿佛一条飞动的青龙,时隐时现,九曲十拐,游至眼前。这是清澈晶莹的一脉,阳光可以照透,使它呈现葡萄酒液的颜色。两壁挂着一嘟噜一嘟噜五彩的水泡,底部的水草如静卧的蓝海星”*李登建:《冬日的旷野》,《文学报》1995年1月5日。。而那些乡野俗语,也经过作家的精心选择和提炼,成为了一首首飞翔在土地上空的农事诗:俗白却不庸俗,机智幽默却不落噱头的下乘,看似随意道来,实际却经过精心琢磨。例如,作家形容村里的一位喜欢吹嘘的老人,语言跳脱押韵,富于民间幽默色彩:“那马大嘴是有名的晕子,有骆驼不说马,见芝麻就是西瓜,嗓门儿又像大喇叭”*李登建:《父亲的华屋情结》,《礼花为谁开放》,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0年,第9页。。而作家在描述农村老年人的凄凉境地的时候,则通过乡民水叔的嘴说出:“你注意到地里的玉米没有?它结了棒槌子,皮就开始焦,梢就开始干,秸子也慢慢地枯了,谁还再去顾它,谁会可惜它?庄稼人一代代都是这样呀!”*李登建:《父亲的晚景和“庄稼人”一词之来历》,《散文百家》2007年10期。语言质朴,却道理深刻,感人至深。同时,我们看到,这两类语言也是水乳交融的,形成了李登建既有神思的超拔,诗意的灵动,又有乡土生活原汁原味的真实与厚重,这种非常独特的“平原气质”的散文语言。
就语言锤炼的追求而言,一方面,李登建追求散文语言的自由性。正如鲁迅先生说:“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鲁迅:《怎么写》,《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4页。另一方面,他也注重散文文气的贯通,如宋代李涂在《文章精义》中所说:“说得通处,尽管说去,说得反复,竭处自然住,所谓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真作文之大也”。李登建的散文语言是主张贵“精”的,他写散文时总是精心构思,反复提炼,在表达方式上也注意变化,舍得在景物描绘、细节刻画上下功夫。他以诗的笔法刻画散文,他精心选择题材,厚积薄发,散文篇章读来乍看平淡,内里却常常内蕴丰厚,发人深省。这在当代散文界,与追求散文数量,即所谓散文就是“随时随地可作”的想法是截然相反的。散文是很自由,但绝不是可以随意为之的,它需要更大程度地对艺术思维的调动和构思,也需要苦心经营的语言锻造。李登建曾说过:“我主张散文不能多写。一篇好的散文里必须有作者对生活、人生独到的发现、感悟和思考,而这种独到的发现、感悟和思考的‘珍珠’是多少日子才能孕育出一粒的,不是唾手可得的,不能批量生产”。*张炜:《礼花为谁开放·序》,《礼花为谁开放》,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0年,第3页。
具体而言,“平原”的文化地理意象和“黑色”的色彩意象,是李登建散文中的两大核心意象。《站立的平原》,《倾听原野》,《啊,平原》都是李登建的平原意象系列散文,以“春夏秋冬”四季的更迭为线索,而以饱含生命意识的细致观察、体验和想象,作为哲思的寄托。四季更迭的平原,以春的盎然,夏的旺盛,秋的沉着与冬的坚忍,成为一种生命意志的象征。这种生命意志,是乡土的魂魄,是田园文化时空的和谐宽容的“自在化”的感受,是几千年来中国延绵不绝的传统精神的火光,也是历史沧桑变幻之中,对平凡人生的生命意志本身的赞颂和歌咏。虽然已步入现代化的洪流之中,但这绵长的平原精神,依然是我们生存赖以依靠的精神家园。绿色,在平原上的延伸,在作家的眼中,简直活了起来:“……刚才那啄破蛋壳的鸟儿的羽毛般的树叶儿,还被柔柔的阳光舔着,黄嫩嫩、湿淋淋的抖不开,一转身的功夫,一切全绿了,绿在到处流,在往远处铺,往高里垛,漫长冬天留下的灰烬、废墟,以及那遍地盐碱屑的残雪,都给这绿轻轻地吞掉了”。在这里,平原被形象化和具象化了,具有了湿度、色泽和动态。而对夏天平原的体察,作者则更注重其整体的温度感,成为一种燃烧的生命意志。“这尽情地燃烧着生命的绿色烈焰依然熊熊不熄,它们永远不会熄灭,你不能想象它们会熄灭,没有了它们,平原就躺倒在地,倒退到那片死寂。”*李登建:《站立的平原》,许评等主编:《新艺术散文精品选》,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376页。
同时,在平原整体拟人化的地理意象中,还有很多支撑的次级意象。比如,树、草和庄稼。这块土地也是多灾多难的,盐碱很重,地下水很苦很涩,好多娇贵的树木在此都无法存活。就在这块苦难的土地上,只有树和草,那些看起来卑贱的植物,才能以顽强的生命力存活下来。而那些卑微的草儿,平凡的树,沉默的土地,乃至那些为生命歌唱的麦子,都在生存的苦难前,挺直了脊梁,默默地承受着苦难,孕育着生命,并包容着所有难以言传的酸楚和尴尬——正如中国大地上那千千万万的农民一样。那些树木,活得如此的艰难,它们把痛苦咀嚼千遍后咽进肚里,即使根“一半以上已经绷断,那剩下的就更加狠命地抓住泥土,像鹰的铁爪,又有点颤抖,甚至不敢喘口气,这样保证着巨大的树冠继续伸向高空,在云里完成它们的绝唱”*李登建:《站立的平原》,许评等主编:《新艺术散文精品选》,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376页。。“昏黄、沉闷、榨不出丁点儿生机的空气重重包围着它,风将息,枝柯的动作迟滞而僵硬……它显得有点老,它像一位额头刻满了皱纹的老人”*李登建:《原野上的树家族》,《黑蝴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2页。。“你剥它的皮,刨它的根,它不曾反抗,好像没有尊严……然而,黑暗如块块磐石,更加凶狠地压过来。树们愤怒了,咆哮着,跳起来,扑上去,同敌人扭打在一起。勇士们筋断骨折,衣裳撕碎,终于把威势丧尽、一败涂地的黑暗赶出了天空!”*李登建:《树姐妹,树兄弟》,《文学报》2006年9月14日。而那些“黄了又绿,绿了又黄”的草儿,当它们刚刚露出脑袋,阴险凶残的霜冻反扑过来,让它们大病一场,气息微弱。好不容易恢复了元气,什么样的蹄、足,甚至爪都可以任意践踏草,蹂躏草。不仅如此,活在世上,草儿还不得不接受种种无礼的鄙视,下流的辱骂,时时胆战心惊地提防着铁铲和锄头。而那些善良的庄稼,也要忍受着生存的折磨,天旱,土地干得冒烟,种子烫得滚来滚去,拱出地面的小苗苗面黄肌瘦,弱不禁风,雨下大了,又积了水,那些害虫,又挡在了它们的前面,这群乌合之众各个都穷凶极恶,如狼似虎,吃肉,吸血,噬骨,“然而,它们都咬着牙挺了过来,一场灾难成熟一分!”*李登建:《啊!平原》,《中华散文》2001年8期。无疑,这平原上的一草一木,都被作者化景语为情语,化物象为心象,寄托了作者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和命运的感受,灌注了一腔同情之泪,一片赞颂之声,一种深沉的反思和清峻挺拔的自省。
另外,李登建也形成了另一类色彩意象,即所谓的“黑色”意象。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李登建偏爱“黑色”。尽管他的笔下,有着如此多的绚烂的色彩,但他独爱黑色。贾祥伦曾在《散文抒情探微》中,以“情感的色谱”来命名散文的抒情色彩,并认为“不同的色调,在散文中,表现为不同的情感发散和聚合模式。”*贾祥伦:《散文抒情探微》,东营:石油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2页。而色彩的象征意义,在比较自由的散文文体中,常常有消极和积极两类。因此,黑色,是深沉而厚重的生命反思,也是无奈而苦涩的黑暗现实。黑火焰,黑阳光,那些跳跃的黑色的意象,或贬或褒,都成了李登建笔下最富于生命力和表现力的象征色。《黑火焰》、《黑风景》、《黑蝴蝶》、《黑阳光》、《黑伯》等篇章,都是其中的代表。《黑阳光》中,黑色,是太阳赋予人类的最健康的肤色,而黑色,也成了大平原上最有活力、最有力量的色彩。《黑蝴蝶》中,黑色则成了权力控制下人性扭曲的证明。一位令人尊重的领导逝世了,看守殡仪馆的老工人,为之真心地流泪伤心。接待处的人们却只专注于如何利用哀悼会,给大小官员排座次,那灯光下粘在B主任脸颊上的“黑蝴蝶”,成了人性中最为黑暗丑恶的部分:“那里钻出一群、两群、无数群黑蝴蝶,纷纷扬扬,遮严了茫茫天宇。”*李登建:《黑蝴蝶》,《散文选刊》1996年4期。散文《黑伯》中,穷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的黑伯,只有死去的时候,黝黑的脸上才露出舒展的笑容。而《黑火焰》中,黑色,却成了“反抗”的色彩。作家对“摽上律师事务所的他”的遭遇,给予深切的同情,并将这种同情,扩大到对社会生活的思考。右派问题,是80年代初期文艺作品的重大题材。然而,对右派现象背后的社会体制问题,对右派们的实际问题和际遇,在社会焦点转移之后,却往往被我们所遗忘。而那些现实生活中朴素而多灾多难的农民,那些生活中被侮辱和损害的普通人,似乎都被我们不断形式进步的文学遗忘在角落,成为无人问津的“冷饭”。似乎现代化的物质丰裕,留给散文的空间,就仅仅是那些非常个人化的伤感、琐碎的生活体验与故弄玄虚式的玄奥。然而,李登建却从这些别人遗忘的“旧题材”中入手,发现散文的价值和生命力。《黑火焰》开端,就从一个意象入手,显得非常别致:“我见过这样一种火焰,黑色的,仿佛遗弃于墙角的墨菊,在夜幕下孤寂地摇曳,花瓣的金丝已被风霜噬断,凋残了。但就是这叫人哀怜,柔弱无力,没了丁点儿烈火的熊熊气势的黑火焰,却把寒夜烧了一个窟窿!”散文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奇怪的“右派”,他当了几十年的右派,然而,当右派平反的时候,他却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右派,他被指定为右派,仅仅因为给院领导提意见后遭到了报复。现在他倒不像真右派那样符合政策,无人受理他的冤案。但他没有绝望,“没法告我也要告!”从他嘴角咧出的苦笑上,“我”看到了这“黑火焰”——不灭的生活的信念。而这黑色的火焰,也曾盛开在铁蛋嫂,一个因丈夫车祸而全家陷入绝境的村妇的脸上。“黑色的火焰”,*李登建:《黑火焰》,《中华散文》2000年7期。不仅成了平凡的人生中的苦难的象征,更成为与苦难抗争的象征。
三、求“真”的艺术:平原时间的深情歌者
平原精神,成了作家观照现实生活的内在的价值尺度和精神标高,也形成了李登建在纪事怀人类题材散文中细致描摹生活细节与抽象思考相结合的特点。抽象而富于哲思的意象,在李登建怀人、纪事类的散文中,又泛化为他对社会和人生更为具体的思考。时代在进步,乡土的社会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高楼大厦和光怪陆离的现代都市,似乎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主流,然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朴实的乡民,在现代化的浪潮的裹挟下,甚至失去了自己赖以存身的土地,被迫漂泊于都市,苦苦地挣扎,而那些留在土地上的人们,则忍受着来自自然和社会的双重苦难。李登建甚至进而将这种悲悯而富于人道主义情结的平原生命意识,贯穿入他对身边所有不幸和苦恼的人们的考察中。《红木“王朝”》中,一群浑身木屑、粗手大脚的木工、雕工工人,与精悍机灵、逸乐尊贵的“大玩家”“杨二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工人们用智慧与勤劳创造着社会的财富,却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本该得到尊敬与仰望的人,却总是被忽视与遗忘,在金钱驱动下,更多精明的人处于社会的顶端,他们在“玩”中收获名利;朴实的劳动人民却在埋头苦干中承受苦难。在巨大的红木“王朝”中,他们无疑是匍匐于地的人,而正是这些人支撑起了庞大的“王朝”上层,这些人才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我们不禁感慨社会的不公,李登建就是将这种普适性的悲悯情怀作为他散文的底色。还有他笔下的众多人物,在孤寂中死去的教师,在冷漠中坚持信仰的文学爱好者,在岁月和苦难中衰老的哥哥,在病魔前皱着眉头、不肯向命运低头的母亲,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知识分子,连同那些在城市里卑微而彷徨的民工,无人问津的乞丐,共同构成了他笔下的“黑风景”,映衬了他富于悲悯与批判的健旺而强烈的平原哲学。
如果说,乡土情怀是李登建一以贯之的生命哲学,那么,建立在这种生命哲学之上的民间文化理想,则是其散文创作的原初动力。我们的民族有悠久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精神矿产。我们的文学工作者还远没有充分挖掘。民间文化资源,是世代劳动人民所赖以生存的精神性依靠,也必然成为作家精神寻根和激发灵感的力量之源。在社会把人的感觉、欲望和心态都狭隘化、单向化的商业文化语境下,在散文创作一味高标独异、趋新求奇的热闹背景下,李登建没有举起什么时髦大旗,而是把敏感的心灵放飞于广袤的梁邹平原,重寻自己的家园。他把灵魂的触角,深深扎根于那片生他养他的大地,接受民间精神资源的滋润。这又是何等的寂寞苦心,何等的勤奋经营!正如周作人有他的苦雨斋,汪曾祺有他的高邮家园,史铁生有他的地坛,贾平凹有他的商州,李登建也有他的梁邹平原,并把这里作为他的“精神原乡”。于是,他尽可以趟过《老河》,跨过《老石桥》,走在《千年乡路》上,嗅着《田野里飘散着缕缕香气》;他不知多少次驻足,《倾听平原》,嗅着《乡间气息》;在《冬夜的书场》里,在自家的《打麦场上》,在《古老的马蹄湾》,他一定不知多少次体验了父亲那一辈的《华屋情结》;也许在和《黑伯》、《于老三》、《郭连贻》、《捡螺女》的攀谈中,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的记忆不知多少次“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因为他是大平原的儿子,他《去看母亲》时,《握住父亲的手》时,又不知多少次地泪水流下;他有时也立在《岁月深处的那个角落》,独自冥想,独自思考《礼花为谁开放》;他多想《打一个电话》,给进城打工的父老乡亲一点叮嘱,给《高楼背后的他们》一点安慰,尽管这样的关照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是的,他沐浴在这种民间文化氛围里,与那些树,那些高粱,那些小生灵,那些底层小人物,一起同生死、共患难,一起在当下现实里寻找生命和心灵栖息的地方。梁邹平原就是李登建的“希腊小神庙”,在这里,他找到了虽不乏辛酸但却是自由、健康、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式。它厚重,雄浑、富于美的蕴含,“是任何悦目的色彩也无法比拟的”《黑阳光》。总之,梁邹平原和李登建进行了一次痛快淋漓地、毫不保留地拥抱。
怀人纪事的散文,写好不太容易。这类篇章容易流于琐细的经验,或个人情感的宣泄,如果写得抽象一点,又容易空疏枯燥。而其间抽象与具象的关系,角度的选择,情感色彩的把握拿捏,情绪的收放,叙事的节奏,都很有难度。李登建却在这里显示出了高超的技能。《老石桥》、《于老三》、《父亲的华屋情结》、《平原的时间》等篇什可说是追述乡土生活的精品。《板石桥》写了哥哥历经苦难的人生经历,为了家庭的生计,哥哥被迫放下了入学通知书,成了一名普通的农民。然而,哥哥却培养出了三个“公家人”,他所有青春美好的记忆,都留在了当年修建石桥的过程中了。《平原的时间》,则从农人们的时间观念入手,记述了这个仿佛缓慢而轮回的世界里,生生死死,喜怒哀乐的体验。作家赞美农人的勤劳,同情他们悲苦的遭遇,叹息他们被践踏的生命,也反思他们的愚钝与麻木。而《父亲的华屋情结》则是一篇令人动容的散文,作家匠心独运地从“房屋情结”这个点入手,实写父亲的人生体验,虚写住房对于农民们的梦想,将新时期《李顺大造屋》的故事,进行了更深的思考和更新的延展。父亲一辈子的梦想,就是住上宽敞的房子,然而,为哥哥盖了房子后,父亲自己动手盖房子的理想,却随着衰老变得遥遥不可期。作家通过父亲的理想和悲剧,概括了中国农民的心理路程和复杂体验。《高楼背后的他们》、《城市的缝纫匠》、《沉默的泥水匠》、《他们得在墙上靠一靠》,则都是描写进城民工的散文,朴实无华,却往往在细致的记述中,展现漂泊在城市里的农民,敏感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农民们与城市人之间的心理隔阂。《沉默的泥水匠》中,那些质朴的乡人,是高楼大厦的建设者,却在这些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自卑。城里人的歧视和冷漠,压抑了他们的生气,他们只能以沉默的方式,保持自己可怜的自尊:“在这个喧闹的世界上,他们已经不习惯使用语言,他们慢慢地哑了,改为用抹子说话,和水泥说话,和沙粒说话,和他们日夜牵挂的庄稼说话,说得非常投机,只有他们和它们才能听得懂”*李登建:《城市的缝补匠》,《大众日报》2000年4月7日。。而散文《他们得在墙上靠一靠》,则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写了几个搞装修的乡下人。散文没有空泛的同情,而是在细致的装修工作的描述中,自然展开他们各自的苦难经历,并以一个象征意味的动作收尾,即他们太累了,“得在墙上靠一靠”*李登建:《他们得在墙上靠一靠》,《散文选刊》2011年6期。。一层意思是,超负荷劳作、筋疲力尽的人们,只有在片刻的安宁中,才能体验到人生的惬意;更深的含义则是,那些无依无靠的弱者,渴望社会的关爱和理解,权势和偏见同样压得他们腰弯背疼。这是多么无奈而酸楚的现实呀!作家从一个细节入手,洞彻了进城民工们内心丰富的情感体验。
《三次流泪的经历》、《小时候我崇拜的一个人》、《朋友之死》、《无处可逃》等文章,都是从自己的回忆出发,写出真实人生感受的文字。如果说,那些抒情的哲思和乡土的告白,都含有浓浓的个人体验,那么,这些文章,作者则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个更为真实的自我。他是如此的坦诚,甚至毫不避讳自己面对困难时的懦弱,避讳自己情感生活的波折,童年最为隐秘的梦想。这些文字,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真实,更在那些滚烫的文字里,感受到了作家拥抱生活的热情,认真生活的虔诚,与反思生活的勇气。卢梭曾经说过,人最难的就是看到自己身上的罪与过错。散文是“真”的艺术,然而,在这个钢筋水泥日益包围我们的世界,谁还能坦然地在白纸黑字上说出自己内心的真实,直面自己内心最为隐秘而创痛的体验?《朋友之死》,记述了《作家报》停刊,这一山东文坛的历史性事件。而《无处可逃》,则记录了作家在北京参加某作家的一次读书签售活动。作家对文学事业的忧虑,对缪斯女神的崇敬,读来让人动容。而《三次流泪的经历》,写了作家自己情感挫折的故事。虽然已事隔多年,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我”对不公正命运的控诉,对庸俗市侩的人们辛辣的讽刺,对自身情感的激愤、伤感:“它不容忍我离经叛道,不容忍我的美好爱情,我的单纯、幼稚。那团浓雾里裹着太多的百年老屋,太多狭窄的小巷,黑森森的门洞。它是花岗岩石头,我是小牛犊的嫩角,我碰得鼻青脸肿!”*李登建:《三次流泪的经历》,《中华散文》2006年8期。然而,作家并没有满足于情感的宣泄,而是将之提高到内在精神强度,最终,在平原的感召下,自尊自强战胜了自卑自怜:“夜间在我眼眶里打转的泪珠没有流下来,又被吸收了回去!我的两眼也被它润泽得明亮无比了……”*李登建:《三次流泪的经历》,《中华散文》2006年8期。
四、对社会的深切关注:纪实文学的新探索
宽泛说来,纪实文学也是散文的一支。而李登建的《最后的乡贤:郭连贻传》*李登建:《最后的乡贤:郭连贻传》,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年。则是一部长篇散文体人物传记,他以散文家的笔触讲述传奇老人郭连贻的一生,下笔深刻,洞察了人物灵魂深处的蜕变与巨大的人格构建。郭连贻老人用他一生书写了一位乡土文化传承者的伟大人格。郭连贻的一生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一生,也展现了我国书法发展的脉络。身处乡野,远离尘嚣,郭连贻老人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清高与儒雅,他不沾流俗,不附权贵,隐于市而显于行。但凡见过郭老的人无不为他巨大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同时他也将自己一生的血泪坎坷融进了他的书法艺术中,延展了邹平的文化脉络。李登建成功地塑造了郭老等“乡贤”的群像,并在后记中写道:“乡贤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扎根于民间世俗的沃野,啄取泥土呢喃成春,培植乡村美好德品,开乡民之眼界胸襟,道德学问为人乐道,可亲可近可遇可师。”*李登建:《最后的乡贤:郭连贻传》,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96页。
李登建对长篇散文体人物传记的书写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和创新。首先,深刻的思想性。如郭连贻一样的文化老人有着深沉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这是医治浮躁滋生的时代病的一剂良药。他以郭连贻老人为代表,将笔触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传达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宣扬知识分子该有的人格力量和精神操守。同时,这是一个典型的乡贤形象,着力表现了“乡贤”这一独特的地区文化阶层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李登建反思那些顶起地区“文化脊梁”的乡贤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沉寂,古老文明在急速的时代变迁中的落寞。这是李登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深切的反思,同时又寄予了对民族文明生生不息的希冀。其次,丰富的文学性。郭连贻扎根于民间文化,延展着邹平地区的文化脉络,这种延展是多方面的,而这其中就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元素。这种文化元素的展示首先得益于李登建对丰富史料的搜集。郭连贻的一生辗转于几处,资料搜集整理不易,李登建在这方面着实是下了功夫的,不仅在人物经历方面叙述周全详细,且配制了大量珍贵的图片。李登建更是到邹平地区深入生活,拜访老人及其亲友,对郭连贻老人的经历、个性、内心及其生存的环境、时代背景、文化土壤进行了解和体验。同时,李登建对郭老的形象塑造不仅有关历史性的人物经历梳理,同时涉猎了邹平文化生活的多方面,书法和文学的创作发展,儒释道思想在邹平这片土壤中的生发,地域的文化气息与底蕴,文化圈层的构建形成……著名作家张守仁评价道:“密集的知识点和成熟的文化分析能力、判断力,为这本书增添了底蕴与阅读的魅力”。*张守仁:《最后的乡贤:郭连贻传》,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年,封底。人物传记不同于散文创作,没有既定的感情基调,而随人物境遇的不同而有所变化。郭连贻的前半生郁郁不得志,作者对他的不幸充满悲悯,行文徐疾得当,疏密有秩。政治乌云散去后,郭连贻的文化事业发展,李登建加入写景状物、抒情议论加以渲染烘托,如对漏月轩竹林的描写,语言风格质朴典雅,真诚而庄重。另外,李登建打破了以往人物传记单薄的单线叙述结构,匠心独运地将郭连贻书法风格的发展演变作为另一条重要线索,融入到人物成长史中,形成了双线结构,丰富了人物的血肉。
李登建近年来一直活跃在中国文坛中,其散文以独特的审美视角、敏锐的题材选择、个性化的美学风格、饱含张力的审美意蕴,在散文创作方面独树一帜,开创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创作净土。李登建以怜悯慈悲的情怀关注农村、关注底层,作品中充满了对生命的体味与感悟,对命运的思考与追问,以人道主义精神展现普适性的关怀。《最后的乡贤:郭连贻传》中,李登建延续了其散文创作的审美风格。首先是现实土壤与精神世界的对比思考。时代的发展总以遗忘为代价。工具理性、商品价值观不断侵蚀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文人风骨。李登建对郭连贻老人以及以他为中心乡贤阶层群像的塑造,展现了乡贤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追求。他展现的是“一个伟大民族沉重的步履和生生不息的活力”,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急缺的。生存的快节奏与浮躁的心理状态导致了当下人的归属感与家园情节的缺失,而对郭连贻老人形象的提倡与推崇也是对故乡自豪感与归属感的心理价值构建。李登建在对郭连贻的塑造中,剖析了当下社会的症候,同时,对其精神世界的塑造,则是诗意的。传记文学是一种线性书写,故事与经历是叙述的主体,这不可避免的将传记文学引向一种崇高化、史诗化的审美倾向。李登建在线性塑造的基础上,同样注重横向的延展,对邹平的历史人物、风土人情,书法艺术的发展、大家名作等,都以散文的形式进行补充,充实了郭连贻人物形象的精神世界,同时晕染了供给其精神空间的文化土壤。其次是关注人的生存境遇,运用了碎片化的艺术手段呈现。郭连贻老人的一生是传奇且坎坷的。李登建以众多的资料调查与自我感知,细致的叙述了郭老的一生,这也代表了那个年代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同时李登建洞察了其一生的屈辱和血泪,沉沦与抗争,性格的裂变与精神价值的重建。这是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敬重与赞扬,同时也是当下知识分子的警醒与引导。这种呈现不是单纯的讲述,而是穿插了书信、杂文、对话等多种艺术形式,这种手法的运用将呈现的整体空间结构打破,碎片化地补充了人物形象。例如传记中呈现了郭连贻的文章《说“西”字》、《〈留别乡人〉是首伪诗》、《杏梅》,组诗《醴泉寺》、《唐李庵》、《老人峰》、《相公山》等,他与友人对书法艺术的深入探讨、在漏月轩的闲情对话、针对邹平文化建设的书信往来,这种碎片性的补充,使整体性的线性结构变得灵活自如。当下传记文学的书写延续了以往宏大叙事、史诗性的审美传统,非虚构性也成为传记文学的特征,严肃性、纪实性都使传记文学走入了枯燥、干瘪的局限中,李登建充分发挥其散文作家优势,将其擅长的写景状物、抒情议论融入其中,行文徐疾有秩,典雅质朴,使严肃传记带有灵动飘逸的审美风格。对郭连贻现实土壤的呈现与精神世界的诗意描写,展现了李登建对乡贤精神、乡土文化在当下社会文明中何种走向的思考,将散文笔法揉进传记文学中,不得不说这是李登建的独特思考与创新实践。
我们经常讲,山东作家大都是厚重的,然而也是保守的。这种看法有一定偏颇。在我们这个喧嚣而功利的时代,似乎总是有一些华丽多变的艺术品,仿佛代表了时代的潮流,它们又总是能赢得廉价的喝彩和关注。然而,真正的艺术,则总能在精粹的艺术创新原则基础上,保持某些一以贯之的价值标准和人格信仰。对此,李登建的文学艺术成就,值得我们赞叹,也在一定意义上推动我们对真正的散文艺术进行深入的思考。
Plain Spirit: Aesthetic Tension of “Implosion” and Profound Art World:On the Prose Writing of Li Dengjian
Fang We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With the so-called plain spirit as the standard and scale, and with a reflection on the introverted and internally intertwined feelings and emotions running through the essays by Li Dengjian, the artistry of these essays sets up a “plain philosophy” of “implosion”. The author, good at starting from the concrete, makes use of a gorgeous rich lyrical language, and a dialect or vernacular emanating the fragrance of his native land. And the cultural geography image,the “plain spirit” and the color image of the “black” constitute the two core images in Li’s prose.
Li Dengjian; prose art; plain spirit
2014-08-15
房伟(1976—),男,山东东营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I267
A
1001-5973(2014)05-0013-12
责任编辑:李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