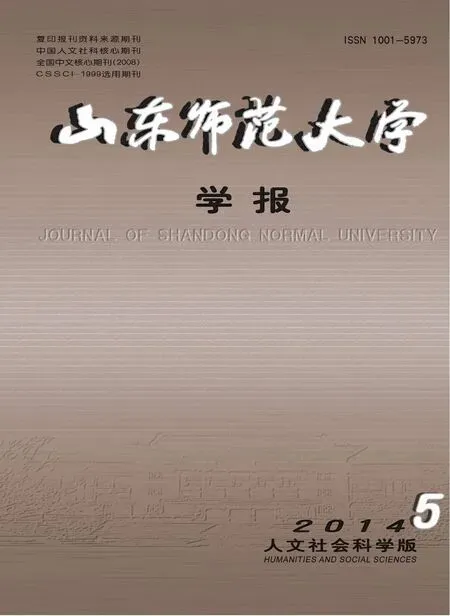历史裂变与跨文化语境的形成
——关于中国20世纪学术思想变迁的反思与探究*
殷国明
(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200062 )
历史裂变与跨文化语境的形成
——关于中国20世纪学术思想变迁的反思与探究*
殷国明
(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200062 )
中国20世纪的人文学术和文学批评之发展,充满着历史、文化、社会及心理的裂变。如果说,跨文化语境的生成,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新的裂变:从旧的肌体中滋生出一种新的文化呈现平台和方式;那么,就不能不顾及到这种裂变的独特性、复杂性和持续性,以及中国本土文化对于这种裂变的接受、理解、应对能力和方式。在这个过程中,20世纪中国学术和文学批评的转型,不仅意味着对于传统文化的不断反思和吐故纳新,而且本身也在不断裂变中求生存、求发展,其不断被卷入新的文化语境,由此不断面对新的命题和挑战,不断转换自己的思路和策略。
裂变;学术史;转型;变与不变
由于中国文化的历史悠久和博杂,更由于近代以来世界境况和局势所发生的重大变化,20世纪中国文学及文学批评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变革,在主体、主题、语言、形式和叙述方式诸方面都不断有所变化和创新,确实给人一种眼花缭乱、变化莫测的感觉。这种感觉来自于社会文化的变化,也缘起于我们的精神和思想状态以及我们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变革。就文学批评来说,近代以来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与作用日益凸显,几乎在每一次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和转换的时刻,都能见到其身影和锋芒;而文学及其文学批评本身的变迁,无疑也成为整个历史变革中的重要部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从一种更广更深的维度去理解这种变革,成为研究这个课题的任务和目标,而对于跨文化语境的理解与把握,则成为跨入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历史时空的文化桥梁。
裂变观念的引入,或许能够为把握和理解这场历史巨变提供一把钥匙。作为现代原子物理学的重要发现,裂变不仅揭示了物质微观世界的奇妙景观和运动规律,而且为人类了解宇宙天体的变化,提供了新的维度和路径,甚至为人类认识自我及其社会的变迁,开启了新的方向。因为如今从天空遥望地球,世界是多么渺小,且处于不断的运动和裂变之中,类似广阔宇宙的一个原子。
一、“世界文学”:跨文化语境生发的历史机遇
说到人类社会,历史及其文学的裂变,不能不关注其发生的文化语境及其变迁。
“语境”(context)这一术语,最初由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1884~1942)提出,后逐渐从人类学扩展到语言学、社会学和文学理论及批评领域。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主要从结构功能角度出发,发现了语言和环境之间的紧密关系,使之聚合成一个新的完整的概念,从而为人类学研究拓展了一个新的方向。而在英语中,“语境”原本就是由“文本”(text)和前缀(con-)组合而成,不仅为文本的意义设置了广泛的、有限定意味的关联项,具有上下文、互文、情景、对话等多种指认;而且为探讨和理解人类在不同地域、不同意向、不同语言条件下的文化行为,提供了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和路径。
跨文化语境由此成为我们进入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的一个路标。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激烈动荡和变革,文化也从相对的封闭状态向开放与改革的方向变迁,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新的格局和特点。其中,西方文论的传入及其引起的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与交流,不仅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事实,也是我们了解和反思历史文学变迁的一个交叉口和基本点。至于这种变革在文学及其文学批评领域带来的显著变化,则是跨文化语境的生成和展开。这不仅是一种价值尺度和思想观念的变化,更是一种语言氛围和话语范式的更新,它以一种渐变的方式解构着古老的、封闭的思维空间,催生了一种与整个世界多向度交流和置换的文学语境。
其实,虽然“跨文化”理念这些年才在中国学界流行,但是其酝酿、发生和拓展,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体现了人类在全球化进程中对于人类发展新的期许和思考。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迅猛发展,不同国度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越来越顺畅、方便和深入,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新的碰撞、争论和交融不断增多,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人文学术空间和氛围。在这种语境中,几乎各行各业都加入了“跨文化”交流的行列,成为身临其境的参与者、研究者和实践者,在共同建构一种新的人类共通的自觉的文化意识。
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预言来说,这种语境就是“世界文学”时代到来的前兆。其前提是科技与工商业的高速发展,已经破坏和摧毁了文化在单一和封闭状态下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取而代之的,不单单是物质产品,而且包括任何文化生产和产品。如果它们还想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获得人们认同的话,都不可能仅仅以本土文化为资源,仅仅以某种单一价值取向为标准,而是要吸取多种文化为基础,极力扩大自己受众的范围,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自己的知音和消费者。对此,我们完全可以继续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表述:
——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4-255页。。
无疑,作为一本文化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的历史魅力不仅在于其深刻的思想性,还在于其对于世界文化走向的前瞻性和预见性,这两者使之至今还具有不容置辩的理论价值。100多年前,继歌德*学术界普遍认为,最先提出“世界文学”这个概念的是歌德。1827年1月31日,他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引出了这个概念:“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诗随时随地由成百上千的人创作出来。这个诗人比那个诗人写得好一点,在水面上浮游得久一点,不过如此罢了。马提森先生不能自视为唯一的诗人,我也不能自视为唯一的诗人。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说,诗的才能并不那样稀罕,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写过一首好诗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过说句实话,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上面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见[德]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16-117页。)不过,我认为,歌德提出这一概念,是基于文学评判和比较而言的,而对这一概念从社会变迁和跨文化视野深入探究的,当属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论述。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把“世界文学”的发生,放在了一个新的语境中加以阐释,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将导致各种文化交流融通的前景,这就蕴含着“跨文化”语境的理论发现,展现了人类文化必然出现的历史格局。
显然,在当今思想学术领域, “跨文化”作为一种历史语境和学术理念,已经获得广泛认同和响应,不仅很多国家和地区设立了“跨文化”学院和相关的专门学科,以不同方式和途径进行跨文化交流和对话,而且“跨文化”已经成为人类思想学术不可或缺的基础和背景。因为“跨文化”不仅是一种新的学术理念,以及由此构建的一种新兴的人文研究学科,而且更是一种新的学术视野和思维方式,其意义在于超越旧有的传统的单一的思维逻辑,突破固有的狭隘的文化价值观,以一种多元化、多向度和跨越文化界限的思考方式和价值观,通过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交流和沟通,建构一种人类共通、共享和共赢的文化平台和历史途径。
这是一个“世界学术”时代到来的契机。这一时代,如同法国学者阿兰·李维比所说,其只有在“封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的跨文化语境中产生,“这就要求我们时刻准备接纳新的模式,那些能够描绘未来世界的新的社会模式、知识模式。我们所要准备的是对世界的再次发现”*乐黛云、[法]李比雄主编:《跨文化对话》(1),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4页。。
“跨文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其实践性,其具有鲜明的动作性。所谓“跨”,意味着一种交流、对话和融通,意味着对某种既定的隔阂、差异和误解的洗涤和消除。它并没有设置特定的对象和内容,却面对着人类以往创造的所有文化遗产和观念形态。没有人会怀疑和否认以往人类文化遗产的巨大价值,因为它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构筑了人类存在的精神家园和依据。失去了它们,人类将不成其人类。但是,谁也无法否定,人类在自身存在和认定方面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人类在享受物质文明的新的满足感之时,在精神和文化方面却经受着缺乏依托的考验:原有的传统的文化家园正在世界化的经济发展冲击下分崩离析,而新的坚实的文化台基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就使得文化之间的冲突显得更加扣人心弦。因为不管人类是否接受文化差异的现实,是否意识到跨文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回避和无法阻挡的趋势,它们所造成的事实和效应已经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不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跨”可能是互相冲撞、矛盾、颠覆、侵占,在人们心灵上形成创伤,留下刀痕,也可能形成一种互相欣赏、交流、融合和丰富自我的良性状态,其关键取决于人们用什么态度来理解和对待,取决于人类自己发展和创造文化的理念和能力。因为文化的核心是人,人创造了过去的文化,人也是处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和对话的主体。当然,在我的理解中,这个主动的“跨”字还包含一种期望,这就是人类能够闯过面对的难关,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度过一段充满文化冲突的历史时期。
无疑,正如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一样,“跨文化”至今还存在着许多障碍和鸿沟,其中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历史形成的巨大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现象,仍然表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和方方面面,很多文化上的偏见和错觉,恰恰就形影不离,依存于这种社会现实中。它们阻断了人与人之间作为本真、自然和平等的人的交流,取而代之的是不同国家、社会阶层和等级的人的观念划分,所谓“文化”也逐渐失去了其人的内核,成为不同利益或阶层“割据”的领地。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精致完备的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并没有减少这种“文化割据”现象,反而加剧了在文化领域的工具化倾向,在不同文化之间制造了新的不信任感。
“跨文化”意义和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一样引人注目,它所面临的课题也是人类必须面对的种种问题。在科技日益发展,人类能够轻易毁灭地球也毁灭自己的情况下,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也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分享人类整体文化,贡献于人类整体文化。由此,我愿意用中国传统的“通”的概念来理解和补充“跨”,“和而不同”,不同有“通”,因为“通”就是要克服万事万物之间的差别和隔阂,通过互相交流和对话,达到物物相通、人人相通的境界。
这种境界是可以实现的。1816年,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还可以说“东方及东方的哲学之不属于哲学史”,而相信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认同这个观念了。人们意识到,人类哲学史应该是不同的哲学体系和价值观的综合和总和,而不能用一种“普遍性”来判断一切。这说明,100多年来世界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已经极大地促进了各种历史传统和文化之间的互相尊重和理解,正在不断破除传统成见和文化壁垒,把人类结成一种多样化的精神整体。因此,在当今世界,人类要共同存在,共同繁荣,首先就要进行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对话和协调,不断探索人类发展中的新命题,完善人类共同发展的文化观念和机制,在“跨文化”中创造人类新的文化。
20世纪的中国,正是在这种历史机缘中跨入世界潮流,走向更广阔的文化时空的。
二、 跨越藩篱:跨文化语境形成的历史视域
也许没有人否认,20世纪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国度,而且是一个文化变革引领社会变革的国度。就前者而言,这个世纪的中国,距离过去的传统中国越来越远,而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社会。尽管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引起不少学者文人的忧虑和恐慌,但是无论如何已经不能再回到原来的文化中国。一种新的来自世界、走向世界和介入世界的理念,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人的一种确定无疑的生存理念和自我意识,同时也构成了指认、理解和阐述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和理论观念的语境和视野。
那么,这种新的语境和视野是如何产生的?它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世界有什么联系?这无疑是探索中国文化变革的基本课题。因为这种语境和视野不是、也不可能单独出现,它是和一系列社会文化变革的事件、人物和作品紧密连在一起的。尤其是中国文学及其文学批评的变革,与西方文论流入中国有直接、密切的关联,并且它是在这种新的语境中得到滋养、获得成长和成熟的生机。而我们如果期望在历史、思想文化和价值观上理解、认同和把握它,就必须在一系列新的文化关系中了解、理清和描述它的来源、基因和流变。
20世纪中国的文化变革无疑脱胎于19世纪中国的历史境况,与其有一种特殊的“父子关系”。关于这一点,王德威在其论著中有过精彩的论述,并且用了一句精炼的话语予以表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美]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页。而从文化角度来说,这种说法似乎更强调所谓中国“现代性”的内源性因素,对于其外源性因素估计不足。其实,就“五四”而言,这个文化“新生儿”颇有些反叛的气息,而传统文化的“父亲”正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由此也为中国人重新认识世界提供了一个契机,把思想变迁推到了一个思想解放、方法变革和价值转换的文化语境之中,开始了对以往的传统文化模式的怀疑、不满和叛逆,进入了一个不断反思、自省和创新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从原来的历史时间的思维隧道中走了出来,走向了一个广阔的横向文化连接和交流的新纪元。
在跨文化语境生成过程中,晚清的文化裂变当然是不可忽视的,而这种裂变是自始至终与接触外部世界、外来文化紧密连在一起的。
自19世纪以来,中国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地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深刻命题。这里所谓深刻至少有三层意思:一是中国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即在世界进入全球化竞争的时代,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面临着重新“洗牌”的挑战,不能不面对可能被淘汰、或者进入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危机;二是就西方和中国的关系而言,它触及到中国人的一种很深亦很敏感的文化心理,牵涉到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世界观念以及在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新变化;三是就中国文化的命运和价值而言,仍然存在着在走向世界过程中,如何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
显然,就第一个问题而言,鲁迅表达得最为峻急和清楚。他说:
但是,无论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而况保古。现状就是铁证,比保古家的万言书有力得多。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鲁迅:《忽然想到(六)》,《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5页。
其实,鲁迅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1925年4月18日,还得面对很多致力于保古的学者文人的质疑和攻击。可见,跨文化语境的形成,原本就是一种充满矛盾冲突的过程,问题在于如何在矛盾冲突中获得文化的新生。
因为文化的碰撞和交汇,已经无法避免,而文化的差异并不见得一下子就冰融雪消,况且文化有其特殊的存在价值和功能,它不仅意味着生活习性和传统的社会规则,而且宣示着某种既定的等级观念和话语权。
就中西方文化来说,两者各自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各自拥有其不同的内涵、规则、话语及价值取向。它们既有相互矛盾的方面,又有相互一致的地方;既有相互联系和兼容的一面,又有差异和相斥的一面;既蕴含着历史意识的沉淀,又熔铸着现实利益的冲突。在相互接触过程中,要想达到某种沟通和认同,首先需要一种相互包容的文化空间,在更宽阔的视域中重新确立文化的意味和价值。
于是,中国与世界,尤其是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成为晚清以来语境转型的纠结之一。 应该说,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并不是游离于世界文化之外,中国人对它并不陌生。但是,在19世纪的中国,这个“世界”却突然变了,不仅变得陌生,充满不可知的神秘和神奇,而且变得异己了,充满了莫名的敌意。因为直到清朝乾隆年间,中国仍以“统驭万国”的“天朝上国”*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0页,第1-3页。自居,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固守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并不觉得中国人会有求于他人。而这种状态却被西方人看作是一种“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1-697页 。。而当国门一旦打开,国人看到了一个远非过去想象的世界,仿佛是一个突然降临的“天外来客”,故意来和“天朝”作对。这意味着过去完整完满的精神世界失去了平衡,被撕破了一个洞,西方异己的文化得以鱼贯而入。
而更不可思议的语境是,中国文化原本的完满和完美状态,是由西方的舰船枪炮打破的,这不仅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极强的破坏力,而且给中国人带来了震撼和侮辱,增强了民族文化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中国人不仅看到了自己在物质上的弱势,更感受到了自己在文化和精神上所面临的挑战。如当代学者朱维铮在《万国公报文选·导言》中就指出:“自鸦片战争起,清帝国被迫同域外侵略者打仗,总是不战也罢,战则必败,败必丧权,已成惯例。每次战败,总在朝野人士中激起反省,引发某种自改革的吁求,也成定势。甚至在鸦片战争前,自改革吁求中便涵泳着对于中世纪式帝国体制合理与否的疑问。但这只是历史思潮的一面。另一面也不可忽视,就是18世纪以来清帝国的文化政策所抉掖的天朝至上论,由天朝迭败于西夷所引出的屈辱感,已硬化成一种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并凝成憎恶西方一切事物的排外情结。”*朱维铮执行主编、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2页。
三、 走向包容:跨文化语境建构的心理突围
在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国度,放下文化优越或优胜感,是一件并不轻松的事。
例如,1876年,作为清政府驻使欧洲的第一人郭嵩焘,就因为在自己日记中如实记录了西方的一些情况,说明西方已先进于中国,竟在国内激起轩然大波。梁启超曾叙述此事: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面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呦,那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清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全事。*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2-183页。
郭嵩焘的见解之所以引起满清士大夫的愤怒,不仅在于这些人当时对于外部世界的无知,还在于由此引发的对于外部世界的恐惧感。究其原因,无疑是和当时这些人对西方的认识与心态有关。第一,不愿承认有一个比中国更先进的世界存在,因为这就意味着所谓“天朝上国”的神话的破灭。第二,不愿放弃旧的体制旧的观念,对不同于自己的世界有敌对情绪。第三,长期隔绝无法接受和理解有这样一个新世界存在的可能性。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确实是太陌生,太难以把握,而且太具有威胁性了。
恐惧不仅会产生排斥,而且会启动心理上的防卫机制,以收缩和固守姿态来维持原来的文化自尊和优越感。在这种心态作用下,对于外部世界和文化的了解和认知也十分浅显和粗糙。据费正清、赖肖尔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中的描绘,即便当时一些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了自强、甚至“师夷之长技”,但是其中很多人甚至不知道美国人也使用英文*[美]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0页。其中写道,咸丰九年,郭嵩焘所在南书房向社会招去通晓英、法、米(美语)等外语人才,仍不知美国人用英文。直到1862年同文馆成立,号称新政,情况才有所改变。。这似乎就是19世纪“中国人眼里的西方”:
郑和下西洋和明代欧洲人首次来到中国所留传下来的民间知识被草率地连同错误、误解以及其他一切抄写出来,并被当成1800年有关欧洲的信息。这是一种经过无数次转抄已经过时的知识,除了这种知识之外,唯一的其他知识来源是那些到广州来的西方人本身,但他们为数很少并且与商人的交往比与学者的多。在缺乏比较准确的资料的情况下,19世纪早期中国的研究者们把千百年来在与亚洲邻近民族打交道中产生的旧框框套在欧洲人和美国人身上,就像亚洲内陆草原上时隐时现、不断变换名称和居住地的游牧民族一样,那些派商人来广州的西方民族,在中国著述的记载中,幽灵般地变换和改变着身份。它们的名称已完全搞混了,1819—1822年阮远主持编选的广东省志中,在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人被说成居住在奎隆(在南印度)和摩鹿加群岛之间,而且只谈到明代的事。葡萄牙的位置被说成在马六甲附近,而英格兰则被作为荷兰的别名,或是荷兰的属国。法国最初是佛教国家,后来变成了天主教国家(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基督教是佛教的旁支),最后,法国被说成与葡萄牙是同一个国家。*[美]费正清、赖肖尔著,陈仲丹等译:《中国:传统与变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8-239页。
当时,中国文化的包容度极其有限。 因此,完全可以说,自19世纪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实际上构成了中国文化意识中最为复杂的一个“情结”,对此我们常常表现出一种极为敏感也极为矛盾的态度。因为“西方”本身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具有双重意味:一方面,它不仅毁灭了中国昔日的光荣感,而且也对今日的中国构成潜在的威胁,弄不好,这个西方会把中国征服,或者把中国“开除球籍”;而另一方面,西方又成了中国的希望所在,中国唯有向西方学习才能得救,西方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世界的代名词,而中国人迫切希望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
由此可见,语境问题不是单纯的文化或语言现象,其首要是心理问题。跨越单一文化藩篱,首先要转换长期形成的心理定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西文化的隔绝与对抗,有其客观存在的基础,更有其“人造”的一面,是心理遮蔽和恐惧的主观幻影。而从隔绝走向交流,从对抗转向融通,则是一种文化不断走向包容的过程。
跨文化语境的生成,就是从文化之间的相互对立,分庭抗礼,转向互为镜像,难解难分的过程,是一种文化格局和心胸敞开的心理嬗变过程。当然,所谓“天朝至上论”心理态势,并非无根之木,而是包含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在世界文化之林中,中国文化以历史悠久著名,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的传统,实现了家国一体、官学合一的高度融合,在意识形态和精神领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与中国以小农经济与家族制度为主体的社会状态水乳交融,高度和谐。再加上中国特殊地理位置,内陆边缘地广人稀,无稳定的、强有力的文明实体交接和竞夺,所以形成自足完美、无所外求的文化心理状态,绝非偶然。而正因为如此,唐宋之后,经清朝数百年的文治天下,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日益受限和缩小,而突破某种文化接受心理阀限的障碍却无处不在。
或许这就是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的文化批判姿态先声夺人的原因。
所以,文化语境的转换,是从突破旧的封闭的文化心理状态开始的。就“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来说,就是如此。当封闭锁国状态被打破之后,它们就不再是原本文化和语言母体中的符号,而是有了新的指认,甚至带上了新的情感色彩,从不同叙述主体和方式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不同的心理体验和价值取向。即便在一些传统文人的笔下,“世界”已经不再是那个来自佛国的、无边无际的时空符号,而是日益成为一个有限的、有疆界的、活生生的地球社会,它可能是神秘和神奇的,能够激发人们新的探求欲望和想象空间,也可能是粉碎传统的自我完满心理世界的介质,是一个与自己不同甚至对立的世界,充满威胁的洪水猛兽。
有道是:“心有多大,眼界有多宽,世界就有多大。”文化心理的嬗变和突围,为语境的多元化预设了前提。正如语言学家索绪尔所关注的,在特定的文化心理驱使下,语言和言语在涵义和功能上都出现了变异,在具体的语言实践和链条中出现了断裂和脱节,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观和感情色彩。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世界”在变化,“中国”也在蜕变,从过去“统驭万国”之“天朝”逐渐回到自己,变化为“世界”的一部分,与“世界”紧密相联又互相矛盾。
语境与心境相连,提醒我们不能忽视跨文化语境生成的内源性因素。“影响中国现代变革的主要因素在于中国的重心深埋于中国内部。”*[美] 费正清、赖肖尔著,陈仲丹等译:《中国:传统与变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8页。换句话说,文化语境的转换并非全然由西方文化进入所引起。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已经酝酿着文化心理的嬗变,尽管它们受到传统体制和文化习俗的抑制和扼杀,但是在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积聚起新的欲望能量,悄然改变着人们的心理状态和话语方式。例如,继《红楼梦》之后,如火如荼的通俗文学创作的兴起,不断瓦解着儒家一统天下的文化语境,扩展了个人生活的精神需求,为之后跨文化语境的形成提供了心理空间。由此不能不说,跨文化语境的生成与挑战,是中国文化及其文学不断获取发展空间和资源的前提和基础。
Formation of Historical Fissions and Cross-cultural Context:Rethinking and Exploring the Changes of China’s Academic Thoughts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Yin Guom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200062)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cademic thoughts in humanities and literary criticism is full of histor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fissions. If we say that the formation of cross-cultural context means a new fiss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namely a new platform and mode given birth to by its former self to present culture; then the uniqueness, complexity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fission, and the capacity and the way to accept, to understand, and to respond to, this fission of China’s native culture will have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Of whic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a’s academic research and literary criticism will not only mean a constant reflection on, and renewal of,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 constant fission for their ow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That is, China’s academic research and literary criticism will continually be involved in new cultural contexts, thus to constantly face new propositions and challenges, and shift the ideas and strategies of their own.
fission;academic history;transformation;changed and unchanged
2014-05-16
殷国明(1956—),男,江苏常州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I206.09
A
1001-5973(2014)05-0005-08
责任编辑:李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