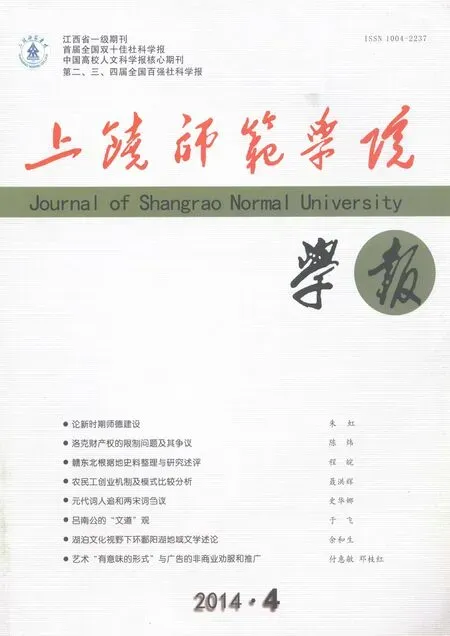从荀子《正名》篇中的“约定俗成”谈“名”与“实”之间的任意性和理据性的辨证关系
(华南师范大学 城市文化学院,广东 南海 528225)
名与实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还是有理据的,自古以来就存在争议。如古希腊的自然派(理据)和惯例派(任意)[1](P7);11、12世纪西方的唯名论(Nominalism)(任意)与唯实论(Realism)(理据)[1](P12);索绪尔(任意)[2](P102)等。
自从索绪尔提出名与实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这个命题,不少语言学家都倾向这一命题,并且经常用荀子《正名》篇中的“约定俗成”作这一命题的证据,说明名与实的任意性,把“约定俗成”与任意性等同起来。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许国璋认为“约定俗成”与“任意性”不是同义词,它们属于两个层次。“任意性”就其严格意义讲,只能指一个人、说一个音、名一件事的条件下才能成立。“约定俗成”完全不是这个意思。“约”意味着一个群体的存在,意味着说话人和受话人的存在。所谓“约”即社会制约,受社会制约的东西是社会公议的结果,绝不是任意地创造。[3]
其实从荀子《正名》篇中可以看出,“约定俗成”是任意性与理据性的辨正统一,本文将从任意性、理据性、任意性与理据性三个方面阐述。
一、任意性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
这段文言的译文是:名称并没有本来就合宜的,而是人们相约命名的,约定俗成了就可以说它是合宜的,和约定的名称不同就叫做不合宜。名称并没有固有的表示对象,而是人们相约给实际事物命名的,约定俗成了就把它称为某一实际事物的名称。
“约定”:事先商量。“约定俗成”:谓事物的名称,初由人相约命定,习用既久,遂为社会公认。[4](P5608)
这里对“约定”及“约定俗成”的解释很显然地表明了名与实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体现了两者之间任意性的一面。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语种,并且每一个语种形成自己的语言体系。在每一语种中都有通用语,在通用语中又有次一层的多种方言,以及更次一层的许许多多的社团语言等。一种语言是由各种各样的事物名称组成的一个大的有机的系统,在这个大的系统中,由于地域、职业等因素的差异,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小的语言系统,也就是各种方言以及各种各样的社团语言等。这样就体现了语言的复杂性、多样性、丰富性,也充分说明了名与实之间联系的任意性。
二、理据性
“约定”不但体现任意性的一面,同时也体现了理据性。“约定”:事先商量,说明不是一个人的单独行为,换句话说是一种集体行为。既然是集体行为,那么要实行“相约”,使各人的想法统一起来,就要有一定的标准,如果没有一个标准,就难以“约定”,如此就无法命名。
一个语言团体对“名”与“实”进行“约定”,要选择什么样的标准、依据呢?又为什么要选定这个标准、依据?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约定”的理据。好的标准、依据能使名称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明白易懂,不好的标准、依据(或者没有标准、依据),就会引起名称和事物之间关系的混乱。荀子的《正名》篇体现了这方面观点。下面分三点说明。
(一) 从“王者”制名方面,看 “名”与“实”的理据性。
“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然则所为有名,与所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也。”
这段话在两个方面体现“名”与“实”的理据性:循于旧名;作于新名。
1.“循于旧名”表现的理据
“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
现代圣王确定名称:刑法的名称依从商朝的,爵位的名称依从周朝的,礼仪制度的名称依从《礼经》,赋予万物的各种具体名称则依从中原地区华夏各诸侯国已经形成的习俗与各方面的共同约定。远方不同习俗的地区,就依靠这些名称来进行交流。
这些名称之所以能被继承,除了体现了它们所表现的事物、现象等继续存在之外,同时也体现它们命名的理据是充足的,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好的名称,应该继承下来,成为“约定俗成”的语词,体现了词语“稳定性”的一面。
2.“作于新名”表现的理据
体现在两个方面:与所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
“然则所为有名,与所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也。”
(1)“与所缘以同异”
“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
“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洒、酸、奇臭,以鼻异;疾、养、ě、热、滑、铍、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
那么,根据什么而要使事物的名称有同有异呢?回答说:根据天生的感官。凡是同一个民族、具有相同情感的人,他们的天生感官对事物的体会是相同的,所以对事物的描摹只要模拟的大体相似就能使别人通晓了,这就是人们能共同使用那些概括的名称来互相交际的原因。
形体、颜色、纹理,因为眼睛的感觉而显得不同;单声与和音、清音与浊音、协调乐器的竽声、奇异的声音,因为耳朵的感觉而显得不同;甜、苦、咸、淡、辣、酸以及奇异的味道,因为嘴巴的感觉而显得不同;香、臭、花的香气、鸟的腐臭、猪腥气、狗臊气、马膻气、牛膻气以及奇异的气味,因为鼻子的感觉而显得不同;痛、痒、冷、热、滑爽、滞涩、轻、重,因为身体的感觉而显得不同;愉快、烦闷、欣喜、愤怒、悲哀、快乐、爱好、厌恶以及各种欲望,因为心灵的感觉而显得不同。心灵能够验知外界事物。既然心灵能够验知外界事物,那么就可以依靠耳朵来了解声音了,就可以依靠眼睛来了解形状了,但是心灵之验知外物,却又一定要等到感官接触事物的性状之后才行。如果五官接触了外界事物而不能认知,心灵验知外物而不能说出来,那么,说他无知,人们是不会不同意的。这些就是事物的名称之所以有同有异的根据。
这段话有两重意思,第一,鼻子与眼睛等不同的器官对事物的不同方面进行感觉。第二,不同的人的相同器官对事物的感觉是相同的。这就为人们能够相互约定事物的名称提供感官依据。
人们给事物命名是为了交际的需要,一方用言辞表达意思,另一方要明白对方所表达的意思。好的名称在一定的程度上能表现事物的被人的感觉器官感受到的一些普遍性,这样交流的双方对所用的词,就能更好地共同地理解,相互交流就能更顺利地进行,就能更好地达到交际的目的。人们对交流中的词,即事物的名称,有共同的认识,这是事物共同性在事物名称中的表现。从感官方面来说,人们对事物的命名是有根据的,即根据感官对事物的共同感觉,然后共同约定给事物一个名称,这样名与实之间的关系就建立了。事物名称建立的这种依据,就是名实之间理据性的表现。
(2)“与制名之枢要”
“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此制名之枢要也。”
事物有形状相同而实体不同的,有形状不同而实体相同的,这是可以区别的。形状相同却是不同的实体的,虽然可以合用一个名称,也应该说它们是两个实物。形状变了,但实质并没有区别而成为异物的,叫做变化;有了变化而实质没有区别的,应该说它是一个实物。这是对事物考察实质确定数目的方法。这些就是制定名称的关键。
要分辨清楚事物的现象和本质。不要把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的东西混同,因为实质不同就应给予不同的名称;而表面不同实质却一样的事物应该只取一个名称。
有一些事物特别容易混淆,在给这些事物命名时,一定要注意他们之间的细微差别,根据这些细微的差别,结合人对细节共性认识,分别给以不同的名称,这就是命名的依据。这些是不可不察,否则引起名与实之间关系的混乱。
(二) 从“名有固善”方面,看名与实的理据。
“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
名称有本来就起得好的,直接平易而不违背事理,就叫做好的名称。
事物的名称有好有坏,直接明白而不引起混乱的名字就是好名字,反之则是不好的名字。简单地说,就是事物的名称有好坏之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名与实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要给事物命名就没有必然的标准。但是没有必然的标准,不等于没有标准,这样反而显示出标准的多样性、复杂性。我们要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给事物命名呢?各语言团体根据自己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选择适合自己的语言标准。
能够使事物的名称在指称该事物时明白易懂、不会与其他的事物名称混淆,让人一看到这个名称,就知道它所指的事物。这样的名称就是好名称,而这种命名的命名标准就是好的标准。既然要求事物的名称指称事物明白不易混淆,那么名称就应尽可能表现事物的普遍的能被大家感觉到的现象或明显的特征。这些现象或特征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如果名称能把该事物的现象或特征充分表现出来,那么这个名称就与该事物相适宜。用该名称指称别的事物或者给该事物别的名称,都不适宜,就不是好名称,那么这种现象或特征就是该事物命名的标准和依据。这说明名称与事物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性,也就是理据性。
“名”与”“实”之间的好名称与坏名称的关系充分体现名与实的理据性。
(三)从“验之名约”方面,看名与实的理据性。
“验之名约,以其所受悖其所辞,则能禁之矣。凡邪说辟言之离正道而擅作者,无不类于三惑者矣。故明君知其分而不与辨也。”
用名称约定的原则去检验它们,用这些人所能接受的观点去反驳他们所拒绝的观点,那就能禁止这些说法了。凡是背离了正确的原则而擅自炮制的邪说谬论,无不与这三种惑乱的说法类似。英明的君主知道它们与正确学说的区别而不和他们争辩。
这句话说明违背“名约”的依据,就会使名实之间关系混乱,交际也无法进行,要禁止这种混乱,就得用“此名”与“此实”相约的依据来验证。
三、任意性与理据性
“实不喻然后命”体现名与实的任意性与理据性的结合。
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故期、命、辨、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
实际事物不能让人明白就给它们命名,命名了还不能使人了解就会合众人来约定,约定了还不能使人明白就解说,解说了还不能使人明白就辩论。所以,约定、命名、辩论、解说,是名称使用方面最重要的修饰,也是帝王大业的起点。名称一被听到,它所表示的实际事物就能被了解,这是名称的使用。
一些事物名称的理据性不是很清楚明白,表现的理据性较弱,就给它命一个任意性强一点的名称,像这种名称让人理解起来不容易,有时要进行解说、辩论。这很好地说明了,给事物命名不是一件随便、任意的事情。
从上面几点可以看出,《正名》篇中的名与实之间“约定俗成”的“约定”除了任意性之外,还具有理据性。事物的名称有好坏之分;王者制名要有依据性;人与人之间感觉的相同相通性;事物特征所表现出的为人所认识的普遍性。这些要素在人对事物的命名中结合成有机的整体,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对制定名称都有其作用。这些都说明了人们对事物的命名可以有理据而且应该有理据。
荀子所处的时代,出现了名与实的对应关系没有依据从而引起混乱,造成了许多没有必要的争论,从而不利于国家的治理。荀子站在治理国家的高度,探询之所以会引起那些不必要的争辩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约定”名与实之间关系的标准不一样、依据不同,因此引起名称指称事物的混乱,造成了诡辩。荀子认为要想治理好国家,条件之一就是去除那些诡辩,要去除那些诡辩,就必须要处理好名与实的关系,要想使名、实关系处理好,就要使名与实之间的对应有一定的标准、依据。这样就不至于引起混乱,有利于人们的交往,有利于国家的治理。
根据语言的最大特点和作用:语言的交际性。依据荀子的名与实之间的“约定”的任意性和理据性,推而广之,任何语言要实现他交际的功能,必须使得交际语言即一切事物的名称在指称事物时都应有一定的标准、依据,否则名称与指称的事物就会混乱,交际无法进行。这也是“约定”的理据性的表现。这里要说明的是,不是所以的语言都要按照荀子的标准来定,因为这不可能,也没必要。但荀子提出的要有标准、依据,这是科学的。到底要什么样的标准、依据,则是各语言团体依据自身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自行选择,只要使自身的语言在交际中不会引起混乱,顺利地实现语言的交际功能,就是好的标准、依据。这是“约定”的任意性的表现。
总之,有了任意性才有各种各样的语言,有了理据性才使得各种语言有系统性,否则一盘散沙,语言将不成其为语言。
因此,荀子《正名》篇中的“约定俗成”,充分说明了名与实之间的任意性与理据性的关系,是任意性与理据性的辨证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 许国璋.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语言哲学探索之一[J].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3):8~9.
[4] 罗竹凤.汉语大词典(缩印本)[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