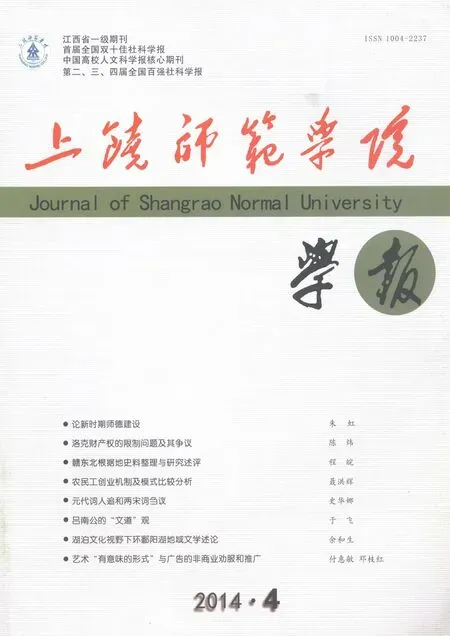论斯坎伦道德契约主义的范围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当代道德理论的运用范围可谓五花八门。最广泛的,其运用范围可以扩展到整个宇宙;最狭窄的,其运用范围可能只包含持有某种道德观点的行动者自身,比如,私人(personal)伦理利己主义。而大多数道德理论的运用范围都介乎二者之间。道德契约主义自罗尔斯伊始复兴以来,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其中一个致命性的批评是由雷切尔斯提出的:道德的社会契约理论在处理现实中的道德实践争论时是无能的,换言之,它无法给我们为何对不能参与契约的那些存在负有道德义务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最为明显地是,它不能合乎逻辑地把智障者、婴儿、非人动物包括在其道德范围之内。[1](P158-160)因此,道德契约主义在其运用范围上就面临着反事实的(conter-factual)批评。由于托马斯·斯坎伦继罗尔斯之后,提出了一种新的道德契约主义,被视为当代最为成熟的版本,所以我打算以斯坎伦的版本为中心来回应这一批评。
一、道德范围概念及其确定
所谓道德范围,就形式而言,顾名思义就是指某伦理学流派、或者某位伦理思想家提出的道德理论所应用的范围。当前一种比较流行的方式是用“道德共同体”这一概念来指涉一种道德理论的运用范围,比如非人类中心主义就已经把道德共同体从人类扩展到了非人动物、植物、生态圈,甚至整个宇宙。如果这里的共同体是指的桑德尔式的构成性共同体(a constitutive conception community)的强观念,那就意味着此共同体中的成员之身份是被其身处其中的社会所规定的。[2](P181)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要认为其他物种、事物和我们构成了一个道德共同体,我们就应该坚持共同体与成员之间是一种归属与被认同的双重关系,成员之间具有在平等基础上的互相性且无贬低他人身份的行动。然而,我们很难确认非人动物、植物对人类主导的共同体有归属感,而平等事实上在面临冲突时很可能被抛弃。因此,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很可能只是在一种非严格意义上使用道德共同体这一概念。鉴于共同体标准的苛刻性,我在后文将不再使用流行的“道德共同体”而是用“道德范围(the scope of morality)概念来指称一个道德理论的应用领域。我相信“道德范围”概念比道德共同体概念在一个道德理论的内部一致性和外部一致性上具有更大的弹性空间和可操作性。
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确定一个道德理论的范围呢?鉴于一个道德行动本身具有一个三元结构——道德行动本身、道德主体和道德受众,我们可以分别从这三个角度来考察,分别称之为道德主体范围论、道德行动范围论和道德受众范围论。我的结论是,道德行动为划定道德范围提供了一个可见的显性标准;道德主体或者道德行动者(moral agent)是一个有理性、有自由意志的、具有道德敏感性,因而具备道德能力的人;道德行动除了具备上述能力还需要事实上付诸实施;而道德受众则是指那些我们应该道德地对待且他们应该被道德地对待的事物。通常情况下,以道德行动来确定范围是最为狭窄的,因为它不仅要求了道德主体的能力,更进一步要求把潜在的能力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其次是依据道德主体确定的范围,它包含了能够实施道德行动的事物,还包括了具备上述道德诸能力但可能无法付诸行动的事物;最为广泛的范围是依据道德受众所确定的范围,因为此范围除了上述两部分,还包含了只享受道德对待却无法主动给予回报的那部分事物。于是,我们看到,道德受众的范围即是一个道德理论能达的最广运用范围。也就是说,一个道德理论的范围即是其道德受众之范围。
现在的问题是,道德受众的范围又该如何确定的呢?目前伦理学中大概可以鉴定出三条标准:第一种是利益原则,即所有能够给人类带来利益对人类有用的事物都应该受到道德关怀;第二种是资格原则,即某事物因为具有某种资格而具有道德地位,因而被纳入道德范围;第三种是能力原则,指回应道德主体之关怀、对待的能力,比如以利益、贡献回报道德主体。能力原则(现实的能力)由于要求过严,可以撇到一边;利益原则在这一点上可能是反事实的,有些事物(包括生物)是存在的,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未能显示出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利益,难道我们可以为所欲为地不择手段地对付它们吗?显然,利益原则在这一点上是不令人满意的。任何把获得道德对待的理由建基于它物之上都是靠不住的。道德资格原则实质上是以某种价值理论为基础的,即某物有一种资格,是因为它具有某种价值,由于这种价值它配享道德的对待。根据生物进化论的观点,人类与非人生物在拥有生命因此渴望活着且希望活得更好这一点上并无多大差异,这种生命来自于自然的恩赐,就此而论,我们因为拥有生命而具有内在价值,由此获得了道德对待的最低资格;在此意义上,珍视生命,包括非人生物的生命和存在,在道德上就具有绝对意义;如无极其充分的理由,故意毁灭破坏一个生命就是绝对禁止的;不伤害生命、保护生命、敬畏生命体现了从否定性禁止到积极追求的贯彻这一道德资格的升华过程;并且,这与人们的深思熟虑的判断相符合:生命是可贵的,我们最低限度应该不去伤害生命。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由于生命特性,我们的存在要以各种营养活动为基础,因为对于生存、生活资源的获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必然以其他非人生物为食物(当然,人本身智识的发展使我们有幸把同类作为食物看成是人间至恶之一),从理论上来说,我们能够以人之下的任何生物为食物,只不过由于生活习惯的差异而有选择不同罢了。所以,根据道德范围的资格论观点,我认为在最低限度上,生物都享有道德对待的资格;同时,由于人与其他物种的差异性,我们又对人自身给予了更高地位,这意味着,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对于其他非人生物的伤害不会是不道德的。
总之,就目前条件下,把道德范围确定在生物范围内,同时由于人类因其独特性而具有较高地位似乎是可取的,在此第一是平等原则,第二是差异原则。这一观点与通常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在于它坚决反对没有极其充分的理由对非人生命进行伤害。这不是出于该物对于人的有用性,而是它们生命本身的内在价值,因此并非从人本身的立场来考虑。
接下来,我将考察斯坎伦的道德契约主义是否能够满足这一范围,如果可以的话,它的理论是否会存在内在的不一致;如果不能,有什么理由可以让其免于批评。
二、斯坎伦契约主义的道德范围
1.契约主义的道德范围问题
所谓道德契约主义,是把契约主义推理作为建构道德的根本方式,认为道德原则规范来自于理性人的契约后果,人们之所以遵守道德,是因为基于先前的同意。虽然所有契约理论都以形成共同的契约原则为旨归,但又因其触发动机的不同分为不同的类型。加拿大著名伦理学家威尔·吉姆利(又译威尔·金里卡——笔者注)在《社会契约传统》一文中把契约主义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霍布斯为经典表述者的自利的契约主义(contractarianism),其动机是缔约者之间的相互利益,当代最著名的阐发者是大卫·高蒂尔,另一类是康德式的契约论,被称为非自利的契约主义(contractualism),动机是缔约者之间的平等对待,当代以罗尔斯为经典表述者。[3](P384)托马斯·斯坎伦被认为是罗尔斯之后的非自利契约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道德契约主义思想最初在1982年发表的《契约主义与功利主义》[4](P135-166)一文中提出,而后在1998年发表的专著《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5]中得到完整阐发。在斯坎伦这里,契约的特征转变为“信息充分的、非强迫的一致协议所导致的道德规则体系”能否被人们“合理拒绝”。对于霍布斯式的自利契约主义,其理论的内在一致性似乎不存在问题,但是对于人类社会中的能力缺乏者无法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所以不能应对反事实批评。对于康德式非自利契约主义的其他理论,比如卢梭、康德、洛克、罗尔斯,他们的范围也限制在人类共同体内,甚至可能局限于一个国家政治共同体内,关于这些观点,我将另行撰文探讨。在此,我将集中讨论斯坎伦非自利契约主义的范围。
2.道德范围确定之一:广义道德与狭义道德划分
托马斯·斯坎伦从来就没有认为他的道德契约主义能够容纳所有生命存在。相反,他认为“道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道德指称一个通常的规范领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见的道德义务领域,这些似乎较少分歧,比如不杀害、不伤害、不撒谎、信守诺言等。这些义务的主要特征是,它们都是指导和调节人与人之间基本关系的道德规范,对于维护社会存在和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是根本性的,换言之,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这些规范的主要目的。这也是斯坎伦《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这本书主要关注的领域,也是他所说的道德正确和道德错误所关注的道德的核心部分。因为这部分道德的边界受到严格的限定,而且在重要性上是根本性、底线性的,所以一般被认为是狭义的道德。我们常常把这个领域称之为道德的公共领域。而广义的道德,不仅涵盖了狭义部分,而且把性取向、性行为的方式、浪费、奢侈、勤奋这些极为个人性的品质都包含在内,一般而言,这些行为不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只与当事人本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有关,从根本上而言,不符合一般认为的道德的公共性、交互性、广泛性、普遍性的特点,所以斯坎伦把这看成是私人道德领域,这包含在广义上的道德内。但斯坎伦不打算把这部分道德纳入契约主义道德所要关注的范围。按照斯坎伦对于道德动机的理解,道德契约主义的动机是向他人证明我们行为的正当性,而这部分道德是不需要向其他人证明的,而且也不可能从对他人的可证明正当性的理想中推导出来。根据这一划分,我们发现,斯坎伦的非自利契约主义的范围狭窄得令人惊讶,因为它甚至没有涵盖人类所有的道德生活,遑论人类中的能力不足者,更不用提非人动物了。当然,由于他自己谦虚地把范围限定在狭义道德中,就此而论,这没有违反其理论的内在一致性。
3.道德范围确定之二:两种模式
(1)自上而下的
我认为我们可以根据斯坎伦对其道德契约主义特征的描述,从内涵上对道德范围提出一个定义。我运用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即通过对道德契约主义根本结构特征的理解推导出一个道德契约主义的理论的道德范围应该是怎么样的。当然,这种方式也是一种形式性的推导。借用一下罗斯的术语:这个自上而下地推导出来的道德范围还仅仅是一个“初始”范围,是否准确需要从具体情形上加以检验。
就决定道德契约主义的范围的条件而言,有如下几个:
首先,它是一个契约理论,作为一个契约理论,缔约各方在某种情境下以一定的方式讨价还价,从而形成一个共同的协议是符合其逻辑结构的。那么,这似乎意味参与制定、创造契约的各方是理性的,是官能健全的。否则,契约过程就无法有效地进行。用集合A表示。
其次,这是一个道德理论,作为一个道德理论,无疑要求它的原则和规范能够得到普遍遵守,人人都能够承认它的权威性。而从道德角度而言,按照康德的观点,我们要尊重人,把人要当作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所以,道德理论的道德属性要求它的范围应该具有尽可能大的普遍性和广泛性。用集合B表示。
再次,由于斯坎伦关注的是道德的“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的部分,所以,这个理论处理的是通常的遮蔽了人的特殊身份和角色的普通的人与人之间(不包括特殊的父子、夫妻、情人、朋友之间的道德)的关系,所以它对上面提到的个体所认肯的价值保持沉默,虽然狭义道德与那些价值应该是相互协调的。用集合C表示。
最后,这个道德理论所设想的道德行动者具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向他人证明自己行动的正当性。换言之,这些行动者之所以愿意通过契约来建构一个契约主义的道德理论,是因为它们被一个相同的动机所推动。这些人甚至构成了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共同体。用集合D表示。
就各个集合所代表的范围而言,A与B相互不能完全包含,它们之间只能是交集,因为可以存在社会契约论、统治契约论,它们并不属于道德理论;而道德理论更是多种多样,其中完全可以不以契约的方式来推理,比如自然主义的道德理论。C所代表的范围只是B的一部分,即人与人之间的道德部分;D所代表的范围最为狭窄,因为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时,很可能有人并不认可那种道德动机,比如他们可能认为,即使道德是人与人之间契约的结果,但也只是人们相互约束自身最大化利益的结果。由于上诉四个条件的限制,我们可以看到,斯坎伦的道德契约主义的范围被限制到一个相当狭窄的范围。这个范围就是:具有理性能力、道德能力且具有寻找共同道德原则之理想而参与契约之缔造的存在。很显然,由这个定义去划定道德范围,它必定是相当狭窄的。引起强烈的批评也就不足为奇了。
(2)自下而上的
斯坎伦的方法与我从内涵上来划定不同,而是从外延上进行。我把他的方法看成是“自下而上的”:通过具体考察各种存在物,看如果他们没有被纳入到契约主义的道德范围之内,是不是可以合理拒绝的。斯坎伦通过对人们常见的存在物的属性的逐步分析,与契约主义的道德动机相印证来确定道德契约主义的范围。在他看来,常常可能被道德(这里显然指广义的道德)地对待的存在物有如下特征[5] (P193):
1)那些拥有善的存在者(beings),也就是说,事情能对其变得更好或更坏的存在者。
2)第一组中那些对感受痛苦有意识、能感知痛苦的存在者。
3)第二组中那些能够判断事情变得更好还是更坏的存在者,以及更一般地说,那些能够持判断敏感态度的存在者。
4)第三组中那些能够作出包括在道德推理之中的特殊种类的判断的存在者。
5)第四组中的那些存在者,与之一起进入一个相互约束合作的系统之中是对我们有利的。
这五个不同的范围每一个都可以鉴定出一个属性,它是属于该范围内的存在的特征,为了能够进入契约,斯坎伦需要考察这个属性是否能够满足他建构契约主义道德的条件:我们有可靠的理由希望我们的行为是可以向这些存在者证明其正当性的。[5](P193)根据这个条件,显然第一组中的存在是范围过宽,因为对于没有意识的生命体比如树木也可以有变得更好或者更坏的状态,但是我们显然无法对它们证明我们的行动是否恰当;对于第四组(具有道德推理能力)和第五组(能够提供合作好处)而言,他们代表着具有典型地和我们类似的能力的人,我们向他们证明我们行动的正当性显然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个范围显然太窄,因为儿童等尚未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就被排除在外了。第三组和第四组的差别在于,有些理性人可能因为道德缺陷或者某种原因不能认识到道德的重要性,他们具有自我自主意识、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我规划生活的能力等,因此也有资格向我们要求行动的正当性证明。
一个直观是,对于非人动物几乎人人都认为我们不应该去不道德地对待它们,不去无故地折磨它们,因为它们能够感受到痛苦,但是道德地对待它们属于广义道德上的事,而不属于契约主义这个狭义范围。因此,对于非人动物,斯坎伦的方式是持一种同情的态度。所以道德地对待非人动物是属于广义道德之事而非狭义道德之事。
在纯粹由人工智能完成创作且数据挖掘也由人工智能完成的情况下,由于数据中体现的独创性表达的价值基础来源于公众体验,因而赋予这种独创性表达的特别知识产权需要以公开发表为权利获得的条件。由于数据挖掘完全可能由不同的人工智能分别独立完成,因此赋予数据挖掘结果的特别知识产权也不能排斥其他人对其独立完成的相同数据挖掘结果享有知识产权。
对于人类这种理性存在而言,我们不仅仅是不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痛苦这种最低限度的消极的道德关怀,由于其内在价值,我们需要进一步用恰当地方式来对待他们,而这种方式就是能够向他们证明正当性的方式。我们对于理性造物的道德关怀具有更为积极的理由。斯坎伦意识到,把道德对错的范围限定在理性存在之内,还是过于狭窄了。在此,他开始面临道德范围问题的真正挑战:“正常的成年人具有这一能力,但是,这样划定范围似乎会排除婴儿,甚至幼年的孩子,以及那些没有发展出正常能力的成年人。”[5](P200)很多理论家都把这个困难看成对契约论有致命威胁,因为任何一个道德理论,如果没有把这部分存在纳入其范围之内都必然是反直觉的。
到此,根据我所提出的“自上而下”的分析模式与斯坎伦自己的“自下而上”模式的结合,这两个范围其实是等值的:即都仅仅指具有现实的理性能力、道德能力且能够以契约的方式表达自身要求的存在。也就是说,其内涵和外延是等值的。然而,虽然其理论内部的一致性没有受到伤害,但是针对道德契约主义的反事实指控即理论的外部一致性没有得到解决:理性能力发展不足者、非人动物等没有纳入到该范围中;而且,就当前而言,人与非人动物的关系也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比如,动物保护主义者与爱好狗肉之间的矛盾冲突就引起了大众的忧虑。
但斯坎伦强调,上述没有正常理性能力的人天然地就应当被纳入到契约主义道德范围内。对于他的契约主义来说:我们要追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某个原则不给上述人群正常人那样的道德关怀,这个原则是不是可以合理拒绝?显然这个原则是可以合理拒绝的。理由在于,一个存在者“生而为人”这个事实就提供了充分的理由给予他们正常人一样的地位,他们拥有这种地位就在于他们与我们同为人类、同胞这种关系,以及属性上的相似性。那些存在是我们所生、或者是我们对他们负有证明义务的其他人所生这一纯粹的“生育”关系就已经确定了他们具有无可争议的道德地位。
对于契约主义的反对者们来说,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直接参与缔约那些人怎么可能允许这些没有能力参与缔约人享有与他们类似的道德权利”。我相信,这些批评者难以理解上述观点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把斯坎伦的道德契约主义与高蒂尔的自利性的契约论相等同。只要出现契约就意味着自利的行动者之间利益的争夺。然而,这种理解对于契约的理解是太狭窄了。我们显然可以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而达成协议,利益分割只是其中的一种。对于斯坎伦来说,契约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相互的良好关系,为了保持自主性的同时也能够提供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环境。斯坎伦的缔约环境也不是罗尔斯式的原初状态那样的理想化环境,相反而是某种确定的环境,那些人对于信息是充分知情的,而不是处于某种信息强制之下,他们提出的理由不是只代表自己提出的,而是任何一个处于他的处境的人都会提出的一般理由。试想,作为一个理性的缔约者,如果他决不会容忍他的孩子因为没有缔约能力而不能享受契约主义道德的关怀,显然与之相似的其他人也不会这样做。那么,自然而然地出现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把那些未成年人、智障者等存在恰当地纳入到契约主义道德范围中呢?斯坎伦提出了“委托”的概念。
4.道德范围的确定之三:委托
“委托”在社会契约论那里一直被当成一个核心概念,它意味着政治权利在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合法转移。在当今社会,它已经被广泛运用于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斯坎伦引入委托的概念,其目的是要保护“那些出于某种原因不能维护自己利益的人的权益。”在道德契约主义中,委托最自然的双方代表是直系亲人间的委托,比如父母与子女等,当子女因为未成年而尚不具备参与契约的正常能力时,父母双亲就可以通过这种亲缘关系成为子女的受托人,子女则是委托人,受托人有义务代表委托人合法地行使委托人的权利,但是该权利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委托人。一般情况下,我们也认为这种情形的委托是最不存在争议的。对于其他的因为各种原因而导致的智障者以及未达到正常契约能力的人类存在,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他们纳入契约的范围之内。我相信,现代法律中的监护人的设立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委托形式的体现。基于亲缘关系而成的委托关系长期以来被看成是一种具有合法效力的惯例,也得到人们广泛认可。至少在我看来,这种道德意义上的委托,比社会契约论中那种假想的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利委托更为真实。因为我们完全能够从我们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找到这种案例,而且为数不少。
这种委托是否只是限于家庭内部或者只具有亲缘关系的人群之间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很多因为意外灾难而成为孤儿、或者本身是智障者而且没有亲人的那些人类存在很可能就不能包括在内。亲缘关系作为委托的基本表现形式只是委托的一种比较典型的方式,它并不是委托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委托的充分条件。对于人类存在来说,仅仅因为作为人类之一员,他们就有资格享有以委托方式被纳入道德契约主义之范围之权利。从这个角度而言,道德的考虑至少不能低于对于人类成员的人道考虑。通过这种人类内部的委托关系,斯坎伦的确可以把人类中的能力不足者纳入到他的道德范围内。
自此,我的分析表明,虽然斯坎伦契约主义的范围非常狭窄,但是由于他的契约主义建构本身建立在道德平等基础上,而且事先划定了一个核心领域,又通过委托的概念解决了能力不足者在现实获得道德对待的实践问题,他的道德范围理论就没有违反内部一致性原则;也没有违反外部一致性原则。然而,我们还是感到些许失落:因为他用“不关注”这个借口封闭了可能的针对道德范围的批评。
三、通过“委托”对契约主义道德范围的扩展?
把人类道德划分为人际道德与个人道德两个部分是当前的通常做法,个人道德留给个体去自由抉择;人际道德则受到严格的限定。有人可能想要通过委托的概念把非人动物、以致于对人类有价值的事物、生态环境都纳入到契约主义道德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纳入到人际道德范围之内。对于动物保护主义者而言,很可能不给予动物与人类同等地位的任何道德理论都会遭到他们的反对。斯坎伦并没有讨论这种情况,但根据他前面对于契约主义道德动机的理解以及对于道德范围的划分,我们可以推论他并不愿意把非人动物纳入道德契约主义的范围内,但是因为它们能够感受痛苦、具有某种好的生活状态(因为我们的不同对待它们的生活能够变得更好或者更糟糕),至少我们对于它们在广义道德上具有义务。但是,如果说我们因此就对它们负有和人类同样的义务似乎有点过。根据契约主义,一方面,我们的行动是应该能够向被影响者证明的;同时被证明者也有可能实施不正当的行动,因此他们也有责任向我们证明其行动的正当性。如果这样,那就预设了对于行动的主体能够进行道德评价,对于一个正常的人类而言,我们可以对他的行动是否道德进行评价,但是,对于非人动物,我们能够要求它承担道德责任吗?一个可能的反驳是,我们似乎对智障者的行动不能进行道德评价。但是,这里有一个区分,对于智障者的行动,如果他做了一个道德上错误的行动,我们会认为这个行动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不会要求他承担这个错误的后果。这个区分就是斯坎伦所说的“归因性责任”和“实质性责任”的区别。对于人类的成员而言,他的能力发展因为某种原因被打断,由此无法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实际上是从一种潜在的能力在向实际的能力转化时发生了断裂,正是因为那种与人的身份和特征相联系的潜在能力,使得我们仍然把他作为一个人来看待。对于非人动物而言,即便正常发展到其成熟状态,我们也不会要求它对其行动在道德上负责,也不会对它的行动进行道德评价。因为我们知道,从根本上来说,那是动物,而不是人(human being)。
那么,有可能利用委托的概念把它们纳入到契约主义道德的范围之中吗?在我看来,由于人类与动物根本特征上的种类差异,我认为我们难以把它们当作与人类相同的存在纳入契约主义的范围。但是,我们或许有可能有一种间接的方式来进行。我的办法是通过把它们作为某个人类的附属物的形式带入契约中,比如那个非人动物作为某人的宠物,作为那个人的私人财产而得到保护;即便不是作为财产,也可能作为一种对那个人有特别价值的事物。
每个人都可能认为某物对他有特别的价值,比如某人A认为某物A’对他有价值,而某人B认为某物B’对他有价值,然而A认为B’完全没什么价值,同样B也认为A’没什么价值,但是他们都想在契约主义的道德内给A’和B’谋得道德关怀的地位。那么,他们可以相互妥协,彼此承认对方所爱之物可以享受到道德的关怀。然而,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本质上履行的不是对于A’和B’的义务,而是对于A和B的间接义务。如此一来,非人事物所享有的道德地位就取决于某个人类的偶然爱好,而非来自于其本身的内在价值,在此意义上,我们很难赋予他们与人类同样的道德地位。因此,总体来说,我对于把非人动物纳入道德契约主义的严格范围内持一种保留态度,但是我同意斯坎伦在广义上认为非人动物享有道德关怀的观点。
参考文献:
[1] James Rachels.TheElementsofMoralPhilosophy(ThirdEdition)[M].Boston: McGraw-Hill College, 1999.
[2] 迈克尔·J·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M].万俊人,等译.南京:江苏译林出版社,2001.
[3] 迈克尔·莱斯诺夫.社会契约论[M].刘训练,李丽红,张红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4] 托马斯·斯坎伦.宽容之难[M].杨伟清,陈代东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 托马斯·斯坎伦.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M]. 陈代东,杨伟清,杨选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