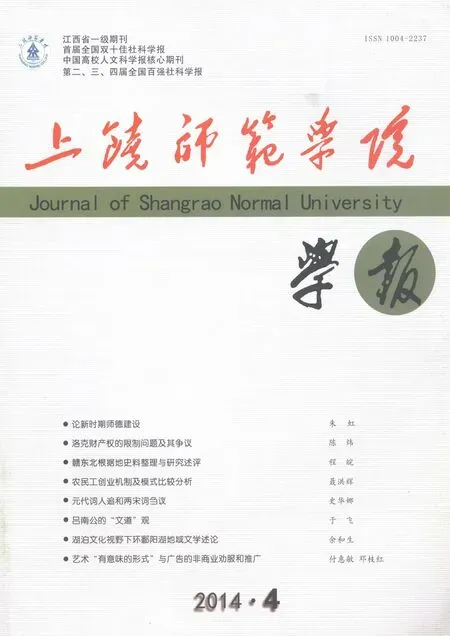洛克财产权的限制问题及其争议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哲学部,江西 南昌 330003)
作为现代自由主义之父,洛克倡导一种区别于古典政治哲学的消极政治观,他的《政府论》洋洋洒洒数万言,却是可以用一句话涵盖其中心议题的:“人们之所以联合成为国家并服从政府的统治,最重大、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保护他们的财产。”[1](II124, P222)如果说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典哲学认可积极政治观,认为政府的目的是追求至善,注重积极的作为,坚持政治应该通过控制、管理和引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倡导个人对于国家的义务优先;那么,以洛克为代表的消极政治观则认为政府的目的是避免大恶,主张消极的设防,坚持好的政府是“守夜人式”的最小政府,它的职责仅仅是保护人民的财产权。财产权甚至是先于政治社会的,“政治权力是人们拥有自己可以处置的财产时才会存在。”[1](II174,P256)既然保护个人的财产是政府的目的,也是人们加入社会的目的,那么必然需要首先论证个人拥有财产权(property)。*“property”概念在洛克的文本中至少包括以下三种不同的内涵:其一,“property”与“possessions”内涵相近,包括土地、生活物资等物质,属于作为主体的所有者占有的客观对象。其二,“property”可以理解为“rights”,即权利本身,例如,“所谓财产底观念乃是指人对于某种事物的权利而言,所谓非义底观念乃是指侵犯或破坏那种权利而言。”(洛克.人类理解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540)所以,洛克把每个人对他自己的身体享有所有权表述为“every Man has a Property in his own Person”(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M].Peter Laslett(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1127,P287);把丧失个人人身自由权利的奴役状态称作是“having no property”,而被奴役地位和财产权互不相容。 因此,Simmons认为洛克赋予“property”这一术语的首要意义是广义上的一种(道德)的权利。其三,“property”可以理解为“property rights”,即关于财产的权利,指人们对第一种意义上的“property”所拥有的权利,属于主体的范畴。这说明当一个东西属于“property”时,它必然指向了一个所有权的主体,所以,财产就意味着财产权的同时存在。另外,洛克的“property”必然是“private property”(私有财产权),洛克从未表述过“common property”(共有财产权),“common”与“property”是自相矛盾的。可见,“property”这一术语在洛克的学说中具有多重维度的内涵。
一、“财产权的限制”问题的提出
财产权学说的提出是洛克通过在《政府论》上篇对菲尔默非自然的财产权理论的批判开始的,他通过对菲尔默关于君主专断的财产权的驳斥希望建立起一种基于自然法约束下的普遍权利理论。洛克认为,人们在进入社会之前的自然状态中就已经拥有了财产,财产权是受到自然法管辖的,此种权利是上帝直接给予我们每个人的,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直接关系的产物,它在性质上不同于社会中其他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因而是“自然的”权利。洛克在《政府论》下篇论财产权这一部分中,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财产权是一种自然权利”这个前提,并承认财产权从起源上讲最初并非私有而是共有。而财产权如何从逻辑上的共有转变为现实中的私有成了洛克不可回避的难题,洛克财产权学说论证的目标就是要阐释财产权从共有到私有拨归私用(appropriate)的正当性所在。
洛克的劳动财产权理论的逻辑基础是个人对其身体具有所有权,即自我所有权(self-ownership)。“虽然自然之物是赐予全人类共有的,但是人(是自己的主人,是自身和自身行为或劳动的所有人)本身就是财产权的一个重大基础。”[1](II44, P173-174)自我所有权认为每个人拥有自己的身体和头脑,因而完全地拥有自己的生命以及由他的身体和头脑创造出来的一切东西。既然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享有所有权,那么就可以推论出个人对自己身体使用的结果(劳动以及劳动成果)拥有所有权,也就是对财产必然具有所有权,洛克由此提出了关于财产权起源的劳动价值学说。劳动是财产权的排他性的根据,从共有到私有的拨归私用的正当性基础就是劳动。然而,洛克对劳动价值论的论证似乎暗含着这样一种推论,即只要财产是个人劳动创造的,而非巧取豪夺的,那么人对自己的财产便拥有绝对的自主支配权。这无疑是一种非常激进的观念,洛克是否真的毫无保留地坚持这一立场?或是洛克认为个人对财产的占有与支配应当具有某种限制?如果具有限制,那么这种限制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与前提条件?这一系列难题正是洛克财产权学说中的关于财产权限制的问题。
二、财产占有与享用的限制
洛克在论证劳动价值论时似乎暗示着人对财产的占有与支配没有限度,但洛克随之笔锋一转,开始强调人对财产占有与享用的限度。为什么人对自己创造的财产并不能拥有绝对的自主支配权?洛克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提及对财产支配的限制来源于自然法。“自然法通过这种方式赋予我们财产权的同时,也对这种财产权进行了一些限制。”[1](II31, P165)霍伟岸从人与上帝的本质属性给出了自己的一种逻辑解释:“只有上帝才能把财产权与绝对支配权合二为一,因为只有上帝的创造才是真正的从无到有的创造;而人的劳动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创造。”[2](P198)也就是说,个人的劳动只是劳动成果形成的形式,而并没有提供劳动成果形成的质料,后者是上帝创造的。由于质料是外来的,所以,人对自己创造的财产并不能拥有绝对的自主支配权。洛克认为,对财产实行支配限度的目的在于“把每个人的私有财产限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使他在占有财产的同时,不会损害别人的利益。”[1](II36, P168)对于个人的财产占有而言,不会损害别人的利益体现在“起码在还有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留给其他人共同享用的情况下”[1](II27, P163),这就是洛克关于财产的足够多和足够好的原则(Principle of leaving enough and as good)。它是对占有财产范围的外在的限制,针对的是某些人的恶意侵占,由人人都平等地享有拨归私用的权利而来。当资源稀缺时,外在的限制才成为一个问题,而自然的匮乏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普遍现状,一个人的过度占有会影响到他人使用和消耗资源的自由。*诺奇克关于持有正义的三原则的第一条占有的正义原则正是继承了洛克的这一精神:我们对无主物的占有来自我们对无主物的劳动改造使其获得价值,并且以不侵犯到他们的权利为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对此无主物占有是否正义还要取决于他人是否与其在未占有时一样好。(参看:诺奇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M].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81,208-213)
对于人类全体而言,“自然法通过这种方式赋予我们财产权的同时,也对这种财产权进行了一些限制。‘上帝把丰富的财物赐给人类’(《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17节),这是已被神灵的启示证实的理性之声,然而上帝到底给了我们多大的财产权呢?以正好满足人类的享有为限。”[1](II31, P165)一个人对财产的占有仅以他的享用为限,全人类的财产也仅以他们的享用为限。禁止浪费在洛克这里是自然匮乏这个假设的推论,如果自然是匮乏的,那么一个人的浪费和贪欲会伤害到其他人的自我保存。对于个人的财产占有而言,这是一条十分苛刻的原则,既然每个人衣食住行基本层面的享用大致相等,那么,依此原则,每个人占有的财产就不应该有太大的差异,这几乎是一种极端平等主义的观点。然而,洛克又强调:“每个人都有能够使用多少就占有多少的权利,对于他的劳动所及的一切东西,他都拥有财产权。凡是他的勤劳所能及并改变了它们原来所处的自然状态的东西都是他的财产。”[1](II46, P175)可见,如果劳动创造了财富,那么对财富占有的限制其实也就是对劳动创造的限制和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这显然不是洛克想要达到的结论。下面,洛克将借由败坏的限制(spoilage limitation)的财产支配限度原则推导出几乎相反的立场,即财富积累与财产占有不均等的合理性。
三、财产积累的限制
在足够多和足够好的原则之后,洛克随之提出了一条更宽松的原则——败坏的限制取而代之,这条原则对洛克关于财产占有不平等的辩护起到了隐秘的推动作用。败坏的原则是指“一个人在一件东西腐坏之前,他能通过劳动利用多少东西就能拥有多少东西的财产权,超过这个范围以外的,就不是他所应得的,而应该归其他人所有。上帝创造的所有东西都不是让人们糟蹋或破坏的。”[1](II31, P165)败坏原则的本意在于表明一个人通过劳动而占有了过多的财产这一行为本身并不是罪恶,而罪恶表现在他让这些东西腐烂掉,此举才违背了自然法。比如,一个人若把生产出来的容易腐烂的大量橘子交换为以便保存的坚果是可取之举。洛克的这条败坏原则是在物产更丰裕的情况下为财产占有提供了一条更宽松的原则,它同样也符合前述提到的在保障自身利益的同时不损害别人利益的财产支配的总目标。那么,关于财产占有与支配的限制和财产创造的劳动应当鼓励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呢?在败坏的限制原则的指导下,洛克认为,是货币的产生彻底改变了所有权法则,使得财产的积累与过多的占有变得无害。“我大胆断言的是,如果不是因为人们发明了货币,并达成默契赋予它一定的价值,从而出现(经过同意)更大的土地占有和土地所有权的话,那么同样的所有权法则——即每个人能利用多少东西就可以占有多少东西——就会在世界上仍然有效……可以肯定,最初超过人们自身需要的占有欲改变了事物的真实价值,而事物的真实价值本来只取决于它对人类生活的用途;或者,人们同意使一小块容易保存、不会耗损、不会腐朽的黄色金属的价值相当于一大块肉或一大堆粮食的价值。”[1](II36-37, P168-169)如果一块金子和一堆谷物同为一个人的劳动所得,那么这块金子就应当同这堆谷物具有同样的财产权性质。然而,洛克却把对金银的占有赋予了对谷物的占有所不同的性质,而理由正是上述提及的“败坏原则”。“对于这些耐用的东西,他想储存多少就可以存多少。一个人的财产是否超过了正当的界限,不在于他占有多少东西,而在于他有没有让任何东西在他手里白白地毁坏掉。”[1](II46, P175)可见,货币的出现解放了对财富占有的禁忌,也就解放了人的劳动创造力。基于不同的人的劳动能力、勤勉程度以及运气的差异,财富占有的不均等成为事实,而洛克认为这并不是骇人听闻的罪恶,基督教道德关于“富人要想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的仇富论断已经过时。但是,毫无疑问,洛克的货币产生论确实为人类贪婪本性的觉醒提供了理论支持:“他是以唯一可以得到辩护的方式来论证释放贪欲的合理性的:他表明那是有利于共同利益、公共幸福或社会的现世繁荣的。”[4](P247)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出洛克对财产占有不平等的立场似乎不那么坚定,论证也颇为暧昧不明,他首先强调财产是一种自然权利,并认为使财产权发生效力的正当手段是劳动,但接着又指出对财产占有、享有和支配的限度,似乎暗示着某种平等主义的主张,不过随后洛克又通过败坏的限制在结论处达成了对财产积累和占有不平等的辩护。洛克在这里体现了一种似乎矛盾的心态,他提出了对财产的诸多限制,但又希望摈弃它。申建林认为洛克的这种立场体现出了洛克在财产权限制方面的特定针对性:“洛克的有限财产权思想主要不是针对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占有制,而是针对封建土地占有制的。如果说劳动财产权理论确立了自耕农的个人所有权,那么有限的财产权理论则谴责了封建贵族,尤其是君主的无限贪欲。”[5](P39)的确,到了资本主义时代,生存需求只是一个低级标准,在保障个体劳动者劳动创造价值的同时,洛克显然也允许为舒适和便利的生活而积累和使用财产实行一个更宽松的标准。可见,洛克并非真正想去为限制享用而辩护,西蒙斯批评麦克弗森过分强调洛克对享用的限制其实是曲解了洛克的真实意图。[6](P288)另外,关于财产权限制的学说体现了洛克隐微主义的(esoteric)*斯特劳斯区分了“俗白的”写作方式和“隐微的”写作方式。(参见:斯特劳斯.迫害与写作的技艺[M].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198)迂回式论证方式,其原因在于洛克必须考虑到当时读者当中流行的旧有观念,那时深受基督教道德影响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毫无限制的获取财富是一种不义之举;但是,在考虑读者情绪的同时,洛克仍会逐渐灌输他的革命性思想。洛克对无限制获取财富的财产权理论鼓励了自由劳动与创造的资本主义精神,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理论辩护。
四、关于洛克让渡权(the right of alienation)的争议
洛克的劳动价值论要阐述的是财产权在起源上是由劳动确立的,而一旦某种财产权建立之后对财产的所有权问题则不是劳动价值论可以回答的。关于最初财产权确立以后财产的是否可以让渡的问题在《政府论》专论财产权的第五章并未系统论证,而是散见于洛克著作的各个部分,也因此引发了研究者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
塔利坚持认为,对洛克财产理论的分析并不能得出如下结论:个人对财产拥有绝对的让渡权。相反,个人对他的财产的处置具有极大的限制。例如,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财产索求具有道德正当性时,后者是不能拒绝其要求的,也就是说他并不具有对其财产让渡的绝对支配权力。洛克在文本中有如下的神学解释:“上帝作为一切人类的主人和父亲,没有把这种支配世界上特定的一部分东西的所有权交给他的任何一个子女;而是赋予他的贫困的兄弟可以享受他的剩余财物的权利,以便当他的兄弟有迫切需要时,不会遭到不正当的拒绝。”[1](I42, P38)并且,洛克把这种见死不救看作是一种罪恶,而上帝的仁慈是不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的。“洛克的自然权利或所有权为穷人从他人的固有财产中获取他们所需之物的做法赋予了道德上的合理性……人的需要产生了对另一个人的财物的权利。”[8](P101-102)并且,“所有人不能趁这个人贫困而强迫他为他的生存而劳作。”[8](P102)塔利认为,这种仁爱理论在继承阿奎那义务论的基础上驳斥了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的否定性理论。所以,在塔利看来,洛克强调对他人的仁爱与义务决定了洛克不可能支持财产权的最初所有者对于自己的财产具有绝对的让渡或处置权。塔利认为,这说明洛克在财产的再分配上并不是标准的古典自由主义抵制福利主义的主张,而是支持经由权威的干预对弱势群体的帮扶,他通过史料分析也找到了现实的证据:“在洛克为济贫法制度制定的计划中,从5岁到55岁劳动人口中的大多数都处于济贫院权威的管辖之下。”[8](P77)学界把洛克语境中贫困人口对富有者的索取或通过政府的征税等再分配形式获得财物的权利称作“慈善权”(charity)。慈善权无疑对财产的最初所有权构成了限制,成为在无限制获取和支配财富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弱者保护的防线。但与今天西方社会过度的福利化相比,洛克在《济贫法》中对福利制度提出了极其严格的限定,他鼓励勤劳致富,并通过立法让懒汉绝无可能成为社会的寄生虫。另外,洛克理论中劳动者不能让渡他对其能力的统辖权与后世资本主义的劳动者可以在工作场中完全让渡他的能力也是不相容的。[9](P182-198)由此可见,洛克在财产让渡权以及相关福利问题上并非坚持一贯所认为的古典自由主义主张。
然而,西蒙斯对塔利的观点提出了质疑,结合洛克对于生命与自由权不可让渡的坚定立场,再根据洛克散见于各部著作的关于让渡权的看法,西蒙斯推论出洛克认为个人有权对除生命、自由之外的狭义财产进行任意的让渡与处置,“我把洛克的观点看作是财产权确实包含着一种自由地(无害地)让渡的要素。”[10](P232)例如,个人拥有对于土地的让渡权,“因为那份土地既然是父亲的财产,他就可以对它进行任意地处置或安排。”[1](II116, P218)的确,对洛克让渡权的争论不已是因为洛克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直接系统地论述,而由于不同的语境和论证需要,洛克对于这个问题的零散看法又存在着表述上的前后矛盾之处。例如,个人对财产破坏的权利在性质上与对财产转让的权利类似,都属于所有者对财产是否具有任意支配的权利。在破坏财产的问题上,洛克一方面强调:“上帝创造的所有东西都不是让人们糟蹋或破坏的”;[1](II31, P165)另一方面又宣称“在必要的时候,财产所有者甚至可以为了使用他拥有所有权的东西而把它毁灭。”[1](I92, P83)因此,西蒙斯认为,在洛克那里,对财产让渡或破坏是基于人类更舒适的生存,“一个人对自己财产的破坏的权利至少经常是财产权的组成要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其愚蠢地破坏。”[6](P233)这种说法就暗含了对于财产的一定程度上的破坏权,可见,在西蒙斯看来,对财产的让渡权存在一个程度和条件的问题:一个人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放弃他的部分自由,但这种放弃不至于使他遭受到他人的奴役;同样,一个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他的部分财产,但这种放弃不至于威胁到他的基本生存。
按照萨姆纳关于权利保护利益和保护选择区分,塔利和西蒙斯关于洛克财产让渡权的分歧折射出两人对于洛克权利模式的不同理解,体现出两种不同立场的权利理论。塔利把洛克的权利理论看作是保护利益的模式,这种权利模式“在对个体有利时把个体视为管理者,在对个体不利时把个体视为他人服务的被动受益者”[11](P88),此时个体的自主和他人的个体利益都将成为衡量标准。在这种模式下,个体对其财产让渡的权利由于必须兼顾他人的个体利益而并不具备完全自主的决定性。而西蒙斯把洛克的权利理论看作是保护个人自主?(选择)?的模式,这种模式“把个体视为积极的自我管理者,甚至在对个体不利?(甚至有害)?的情况下也是这样”[11](P88),在这种模式下,个体对其财产让渡的权利具有完全自主的决定性,个体自由在这种模式下是优先于任何利益的。*诺奇克显然支持这种保护自主的模式,他关于转让的正义原则认为,任何资源不管以什么形式转让、交换抑或赠予,都是基于自愿原则的,都是通过正当的手段来自另一个公正的分配。(参看:诺奇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M].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七章,第一节)
总之,通过对劳动价值的重新确认经由对财产占有限制的分析,再转向对无限制获取财富的辩护,洛克迂回的论证最终得出了财产权具有私有性及神圣不可侵犯的结论,为进一步论述政府的职能与目的奠定了基础。洛克的财产权学说在推动西方政治哲学史从自然义务到自然权利的范式转换,并以此形成了西方自近代以来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主流政治哲学立场。
参考文献:
[1] 洛克.政府论[M].杨思派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 霍伟岸.洛克权利理论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3] 诺奇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M].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 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5] 申建林.洛克经济思想的政治含义[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5):38-41.
[6] John Simmons.TheLockeantheoryofRight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7] 斯特劳斯.迫害与写作的技艺[A].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8] 詹姆斯·塔利.语境中的洛克[M].梅雪芹,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9] Locke.LockePoliticalEssays[M].edited by Mark Goldi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 John Simmons.TheLockeantheoryofRight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11] 萨姆纳.权利的道德基础[M].李茂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2] 洛克.人类理解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3] John Locke.TwoTreatisesofGovernmen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