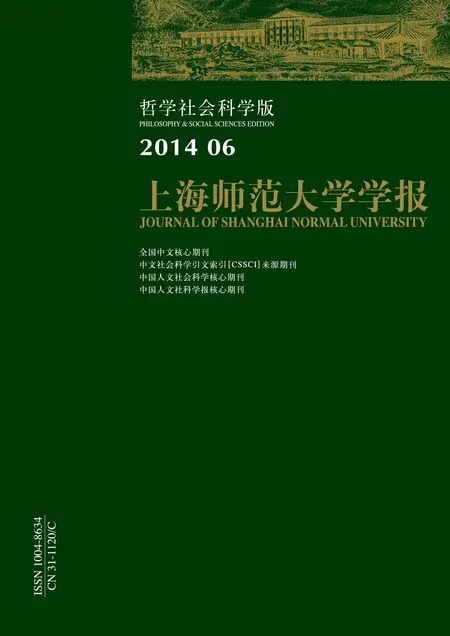数量词的个性及其指代功能的理据解析
陈再阳
(上海师范大学 天华学院,上海 201815)
数词和量词是汉语词类中极有个性的两个范畴类,数量词顾名思义是表示数量的,可数量这个复合词却是单一概念,指一定量的数(真值义或非真值义),可见只与数词相关,那么量词的基本功能是什么?此外,数量词在基本功能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派生功能,即在篇章中的指代功能,学界的考察还很不充分。其实,对于数量词的指代功能学界早已有所关注,朱德熙在《语法讲义》(1982)中就指出:数量词的主要语法功能是修饰名词,由数量词充任的修饰语和中心语之间有同位关系,因此在一定的语言环境里修饰语可以代替整个偏正结构,例如:五张 = 五张纸,两间 = 两间屋子。朱德熙实际上已注意到了数量词在篇章中的指代功能了,只是未展开阐述。明确提出数量词在句子中的指代功能并加以描写、分析的,主要是陆俭明的论文《现代汉语句法里的事物化指代现象》(1991)。在该论文中,陆俭明肯定了数量词的指代功能,并列举了三类现象。第一类是总分式复指结构,第二类是数量宾语结构,第三类是重叠量词主语结构。但陆俭明只考察了部分语言事实,而数量词指代功能的理据也还值得进一步探索。本文立足认知语法,试图重新发现数量词独特的个性,先梳理数词的基本语义及其句法变异,而后探索量词的基本功能及其认知基础,在此基础上解析数量词篇章指代功能产生的理据,运用相关构式(construction)的“强制”(coercion)效应来解释此类现象。
一、数词的基本语义及其句法变异
我们说数词是个很有个性的范畴类,从学界对数词的词类归属处理来看就能初见端倪。在早期汉语词类研究中,学者们对数词的词类归属有三种处理方式:一是将数词归入形容词,如马建忠《马氏文通》(1898)、金兆梓《国文法之研究》(1922)、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1924)、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4)。二是将数词归入广义的代词,如刘复《中国文法通论》(1920)把数词归入代名词,陆志韦《国语单词词汇》(1938)把数词列入指代词,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把数词归入指称词(称代词)。三是将数词归入名词,如陈泽文《国文法草创》(1922)把数词归入名词的次类。后来,高名凯《汉语语法论》(1946)单独讨论了数词,并介绍了数目系统及序数的表示法。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61)在此基础上对数词进行了全面描写,并确立了“数词”独立的词类地位,这无疑是最明智、最科学的处理方式。至于现在通行的做法,即将数词、量词与名词一起归在“体词”名下隶属“实词”,笔者倒以为除了在教学中能有个说法之外,这样处理既没有什么充分依据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1.1 真值义与非真值义
数词的基本语义是表数,这毋庸赘述。然而事实表明,数词所表之数并不简单,这集中体现在数词“一”的表数上,数词“一”有时表示真值义(逻辑义),有时表示非真值义(非逻辑语义)。在通常情况下,表示逻辑量的数词形式属于真值义数,凡表真值义的数词可以用其他数词自由地替换,不影响句子的句法功能,如“语法书他买了三本 / 五本”、“电影他只看了一场 / 三场”;不表示逻辑量的数词,即按照数词逻辑义理解不符合句子语义的数词形式属于非真值义数词,例如:
(1)灰飞烟灭,未建成的庞大厂房、恐龙般的吊车轮廓依稀可见,笼罩在一片水雾弥漫之中。
(2)一楼人都跑光了,扔了一地形形色色的鞋。
(3)阿眉在厨房里忙碌着,把饮料倒进一只只杯子,我不时可以看到她蓝色身影的闪动。
(4)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上颊边,雨水流进她大张的嘴,白色的牙齿一晃一晃,喧嚣的雨声使我听不清她在喊什么。
(5)在这里她一个人都不认识。
(6)山上只有稀稀拉拉的灌木丛,一户人家也没有。
上述例(1)中的“一(片)”、例(2)中的两个“一”都表示“全、满”的意思,属于全量表述(例见袁毓林,2002)。例(3)中“一(只只)”表示“每—”,属于静态多量;例(4)中“一(晃)一(晃)”表示动作的连续性,属于动态多量。例(5)、(6)中的两个“一”与否定词连用,通过对最小量“一”的否定实现全量否定的表述功能。以上用例中的“一”都属于非真值义数词形式,不能用其他数词替换。
真值义和非真值义的区别主要体现为语义上的差异,而语义的差异又是句法变异的结果,即特定的句法分布位置所致。非真值义不是表“数”,那么极有可能表“类”,在特定句法位置上的数词就可能会实现其他功能,而篇章指代功能正是数词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派生功能(详见下文分析)。
1.2 非真值义的语义类型
根据学界的研究,数词“一”表示的非真值义的语义类型比较复杂。据笔者考察,非真值义的语义类型可以分为三类:弱化量义、泛化量义、全量义。
1.2.1 弱化量义
“弱化量义”指在特定的句法构式中,“一量”的表数功能弱化了,凸显的是指代功能。例如:
(7)江浙有两个湖:一个是太湖,一个是西湖。
(8)猴子们很好奇,那圆圆的月亮,天上一个,水中一个。
(9)那个自以为是的家伙,就是傻瓜一个。
(10)我们好歹朋友一场,闹过了也就算了。
(11)不用老往省城跑,这点小事,一趟也就搞定了。
(12)办公室琐事多,一天也看不了多少书,考试怎么过得去?
上述实例中的“一量”,有的表示物量,如例(7)、(8)、(9);有的表示动量如例(10)、(11);有的表示时量,如例(12)。这些实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表数的功能已经弱化,不能用其他数词替换。
1.2.2 泛化量义
“泛化量义”指在特定的句法构式中,“一量”的复叠形式“一量量”、“一量一量”、“一量X一量Y”或“X一量Y一量”,泛指“多量”,或静态多量(量大),或动态多量(连续)。例如:
(13)北风一阵阵,雪花一片片,第一次到北方,感觉倒也奇特。
(14)农民新村一排一排,整齐美观,相当气派。
(15)呆在寺庙里也没啥指望,过一天算一天。
(16)他们一个个溜出教室,到外面捣蛋去了。
(17)他们一本一本仔细翻看,终于发现了线索。
(18)那些先后收集到的先进事迹,一个比一个感人。
上述实例中包括了“一量”的各类复叠形式,量词也包括物量、动量、时量各类量词,但都表示“量增”。有的表示静态多量,如例(13)中“一阵阵”、“一片片”泛指刮风下雪状态,风急雪大;例(14)中“一排一排”泛指新楼多,肯定不止一排;例(15)中“过一天算一天”泛指那段时间,肯定不止一天。有的表示动态多量,如例(16)“一个个”、例(17)“一本一本”、例(18)“一个比一个”都表示事件或状态的连续性,含有时间因素。
1.2.3 全量义
“全量义”指在特定句法构式中,“一量”、“一量量”(充当主语为常)表示“每一”,凸显某个所指集合中的全体成员;或构成“一量 + 都/也 + 不/没VP”构式,通过否定最小量“一”来否定全量。例如:
(19)突击队在村口集合,一个个身强力壮。
(21)一周干5天,一天做8小时。
(22)所有亲朋好友,一个都不理他。
(23)前段时间请吃特多,他在外地出差,一顿都没吃到。
(24)这个春节,我一天也没有休息。
上述例(19)~(21)中的“一量”或“一量量”,在理解时都必须加上“每”,如例(19)中“一个个”指“每一个”;例(20)中“回回都中奖”就是“每一回”都中奖;例(21)讲工作时间,不是指某一周、某一天,而是指“每一周”和“每一天”。例(22)~(24)都是全量否定构式,如例(22)“一个都不理他”就是任何人都不理他;例(23)“一顿都没吃到”就是所有的请吃都错过了;例(24)“一天都没有休息”就是天天都在干事。
上述三类表非真值义的类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由于句式变换或语境隐含,导致数量词与所限定的中心语分裂而单独出现,这正是数量词篇章指代功能实现的句法条件(详见下文分析)。
二、量词的基本功能及其认知基础
我们说量词也是个很有个性的范畴类,这集中反映在对量词基本功能的解释上。具有丰富的量词是汉藏语系的特点,也是汉语的语法特点之一,那么汉语量词的基本功能究竟是什么?汉语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曾经有人认为汉语的量词有其“名”而无其“实”,似乎可有可无,只是一个冗余形式。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至少不明白量词的基本功能。如果量词真的可有可无,那么根据自然语言的“经济原则”,此类形式就会被淘汰。近些年来,在功能学派,尤其是认知语法的推动下,我们对汉语量词的基本功能有了全新的认识。为了厘清相关概念,本文借鉴刘辉(2009)的观点,将传统物量词界定为“实体量词”,传统动量词界定为“事件量词”,传统时量词界定为“时段量词”。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讨论并论证物量、动量、时量三类量词所具有的同一性。
在进一步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热潮下,面对本科办学历史较短、办学经验不足、办学条件也较有限的办学实情,新升格本科院校的艺体类本科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可想而知。但是,只要切实结合自身的办学实情,严格遵循“分类指导、因材施教”、“动态分层”、“课程教学渐进性、持续性和灵活性”等原则,将分类分层教学模式与课程阶段递进式教学模式、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有机结合,勇于实践和创新,新升格本科院校就一定能开辟出一条独特的艺体类本科大学英语教学之路,培养出新时期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艺体类复合型人才。
2.1 实体量词
迪伊杰斯(Doetjes,1996,1997)指出,可数名词指称上的可数性必须在句法上得以标示,而不同语言采用不同的方式来标示可数性,非量词型语言多采用数形态(number morphology),量词型语言往往使用量词(count-classifier)。也就是说,标示名词可数性是否使用量词具有类型学的意义,一个实词类范畴具有“个体”和“非个体”的形式区别,这是自然语言的一个共性。依据国外学者的研究,英语中普通名词(特指可数名词)本身就是个体化(individuate)的范畴,或者说英语中名词的个体化标记是一个“零形式”,一旦这个指称对象不是个体时,就必须通过附加 -s这个复数形态标记来实现,如a student → three students。以此演绎推理,汉语的普通名词都是通指类名,是非个体的“集合”,如果需要对个体进行计量,需要用量词(外部形态)来使其个体化,如“书 → 三本书”。也就是说,普通名词“书”概括了所有的书,是个通指类名,需要计量时需要先选择量词“本”限定,使之成为可计量的个体,然后再由数词实现其标量功能。因此,“三本书”的结构层次究竟是“三本 / 书”还是“三 / 本书”,还颇费思量。
对于汉语量词的此类基本功能,国内外学界早已有所关注。莱昂斯(Lyons,1977)较早讨论了语言中实体量词的个体化功能,他认为实体量词提供或者预设了实体的个体化原则。大河内康宪(1993)借鉴这个论断对汉语的实体量词进行了考察,指出汉语实体量词的作用在于使得表达类名(name of kind)的光杆名词能够指称具体的个体。刘丹青(2008)在讨论定语属性的论文中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观点,专门讨论了实体量词的功能,指出实体量词不能为名词增加数量信息,对名词指称的分类也仅仅是附带功能,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个体化。
2.2 事件量词
既然实体量词(物量词)具有这样的功能,以此类推事件量词(动量词)也必然具有相似的功能。刘辉(2009)指出,事件量词的基本语义功能也是对事件类别进行个体化。他认为在语言表达中存在“类事件”、“次类事件”或“个体事件”的区别。例如:
a.前天中午,张三在家乐福买了海鲜。
b.昨天中午,张三在家乐福买了海鲜。
c.今天中午,张三在沃尔玛买了海鲜。
d.今天中午,李四在沃尔玛买了海鲜。
上述四句话各自指称一个“个体事件”,具有特定的时间、处所信息。虽然这四个事件彼此区别,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抽绎出蕴含的共性特征。比如a、b是“张三在家乐福买海鲜”在不同时段的实现。c的处所和前两句不同,但它们都是“张三买海鲜”的实现。d和前三句区别较大,它们之间不是时段、处所的不同,而是参与者不同;因此,d不能看作是“张三买海鲜”的实现,而是“李四买海鲜”的实现。当然它们背后仍蕴含共性的特征,都是对“买海鲜”这个“类事件”的进一步分类。由此类推,“买N”具有进一步抽象的可能,例如“买海鲜”、“买水果”、“买衣服”……
上面的分析说明,汉语的光杆动词并不指称发生在具体时间的个体事件,而是具有相同性质的个体事件所反映出的类事件。不仅光杆动词可以指称类事件,动词和论元、附加语的组合也可以指称类事件。这些依存成分对动词的意义做出了更明确的限制,将“类事件”进一步划分为“次类事件”,直至“个体事件”,成为事件量词个体化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时间和处所对于个体事件的作用并不相同:同一次类的两个个体事件可以于不同时段发生在同一处所,但不能于同一个时段发生在不同处所,因为一个实体不可能在同一时段身处两地。因此,我们完全赞同刘辉(2009)对事件量词所作的界定:事件量词的个体化作用表现在为事件类别或次类指派不同的个体时段,而数词表达的则是和话语有关的个体事件的数量。
2.3 时段量词
根据上文论述,事件量词的个体化作用表现在为事件类或次类指派不同的个体时段,我们很容易推导出时段量词(时量词)的基本语义功能。很显然,时段量词与某个事件展开过程(以自然终结点为准)的时段有关。客观的时间是没有单位的,对于时间单位的个体化完全是人为规定的后果,我们可以使用“年、天、小时、分钟”等人为制定的时段单位作为依据,对某个事件所持续的时间进行个体化,并用数词表达时段的数量,如“一年、三天、两小时、五分钟”等。
综上所述,实体量词(物量词)、事件量词(动量词)、时段量词(时量词)在实现“个体化”这个基本功能时具有同一性,因为它们属于同一个范畴类。而事实上由于学界长期以来对此的认识并不统一,这影响了我们对量词基本功能的理解。
三、数量词指代功能及其理据解析
阐述数量词的篇章指代功能,必须先说明数量词篇章指代功能实现的句法条件,然后再对此类现象产生的理据加以解释。前者涉及形式描写,后者属于动因解释。下面分而述之。
3.1 指代功能实现的句法条件
数量词篇章指代功能实现的句法条件是唯一的,那就是数量词与所限定的中心语必须在形式上分离,并必然表现出两种特定的属性。
3.1.1 数量词与中心语的分离
在现代汉语中,就数量词本身而言,基本功能是限定性表数,限定某类实体、某类事件、某个时段的“量”,因此它们往往处在修饰语的位置充当定语,限定中心语成分。举些简单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25)他又买了两本语法书。
(26)他只看了一次电影。
(27)他整整读了三天论文。
在上述实例中,数量词“两本”、“一次”、“三天”都处在句中宾语的定语位置,分别用来限定“语法书”的实体量、“看电影”的事件量、“读论文”的时段量。这时,中心语被数量词限定,整个偏正短语共同承担指称功能,数量词不独立承担指代功能。
但是由于句式的变换、成分的移位,数量词可能与所限定的中心语分离,这时,数量词就独立充当某个句法成分,它们就不得不承担起指代功能,指代句中移位的那个中心语。例如:
(25’)语法书他又买了两本。
(26’)电影他只看了一次。
(27’)论文他整整读了三天。
在上述实例中,由于数量词限定的中心语前移做了句子的话题,在原来宾语位置上只留下了数量词,这时它们是独立的宾语,是句子核心动词直接支配的受事论元(参见沈阳,2001)。因此这些留在句末单独充当宾语的数量词自然就承担起指代功能,例(25’)中“两本”直接指代实体“语法书”,例(26’)中“一次”转指事件“(看)电影”,例(27’)中“三天”转指“(读)论文”的时段。
数量词与中心语的分离,有两种现象值得关注:一种现象是句中的数量词有指代对象,但形式上不配套,即该对象同数量词无法一一对应,而数量词之后也不可能出现所指代的中心语。例如:
(28)孩子的父母,一个是私营企业的老板,一个是国有企业的老总。
(29)这个月老出差,一次是北京,还有一次是上海。
例(28)中的两个“一个”的指代对象在形式上无法同“父母”匹配,从语序来看好像“父”在前“母”在后,但在此类总分式复指结构中,“一个”的指代功能很强,后边一般不出现中心语;如果要指明对象,只能用“父亲”、“母亲”来分别替换两个并列分句中的“一个”。例(29)中的两个“一次”的指代对象在形式上也无法同“出差”匹配,而“一次”的指代功能同样很强,后边一般不出现中心语。
另一种现象是句中的数量词指代的对象不在句子中,要从语境中推导出来。例如:
(30)警察们没了主意,跑到大街上,见一个逮一个。
(31)听说解放军快要兵临城下了,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搞得人心惶惶。
上述实例中“一量”都是有所指代的,但指代对象不确定,在句中找不到,只有结合语境才能理解所指代的对象,如例(30)中的“一个”指语境提示的背景下当时当地在大街上的任何一个行人;例(31)中的“一天”指当时语境提示的背景下这一时段中的任何一天。
3.1.2 数量词指代功能的属性
从上述实例分析可以发现,数量词的指代功能有两个明显的属性:
其一,数量词与中心语紧邻出现,构成偏正结构,它们只能体现某种限定功能,表示实体、事件或时段的个体量,一旦数量词与中心语分离,数量词才能在篇章中产生指代功能。应当指出的是,数量词的这种指代功能属于间接的篇章“回指”,不是直接“指称”客观对象,这是数量词本身的属性限制的。只有当句子出现了或语境隐含了某个对象(实体、事件或时段),数量词才有可能指代某个出现的“先行语”或隐含的“对象”。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数量词指代功能属于篇章“回指”现象。
其二,具有指代功能的数量词,可能表示的是真值义,如例(25)~(27);也可能表示的是非真值义,如例(28)~(31)。无论表示的是真值义还是非真值义,数量词在一定条件下都能具有指代功能。但指代的属性有区别:凡表示的是真值义,指代对象都具有“实指 / 确指”的属性,即指代对象是确定的,如例(25)~(27);凡表示的是非真值义,指代对象都具有“虚指 / 任指”的属性,即指代对象是某个“集合”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如例(28)~(31)。
3.2 指代功能实现的理据解析
为什么数量词在独立充当句法成分时就会产生篇章“回指”的指代功能呢?归根结底是内因和外因双向互动的结果,“内因”主要指量词本身保留的实词义所产生的语义效应,“外因”主要指构式框架强制附义所产生的句法效应。
3.2.1 量词保留的潜在语义
数词和量词在指称功能方面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其中数词只落实具体的“量”,而量词才真正解决了指称对象“个体化”的资格。事实上,当“个体化”对象只有“一”的条件下,“一”通常被隐去,如“买本书”、“吃顿饭”等,从中也可窥见数词和量词在指称化过程中的不同作用。
本来汉语量词作为纯粹的个体化标记,应该不再承载具体的语义,而事实上汉语量词大多是实词虚化的结果,如“道、枝、条、根、块、团”等源于名词,“扎、包、捆、堆、把、卷”等源于动词。尤其现代汉语中还有一些被称为“借用量词”的,如“杯、碗、桶、瓶、盆”等(借用为物量词),“拳、脚、刀、棍、声”等(借用为动量词),这更加使得量词本身具备了丰富的词义。汉语量词语义虚化不彻底的现状,使得量词还或多或少带有原实词的语义特征。不少学者如邵敬敏(1993)、石毓智(2001)、郭先珍(2002)、刘街生(2003)、何杰(2008)、宗守云(2010)等,对汉语实词与量词的语义关联,尤其是人们对量词的选择依据,进行了考察、描写和解释,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量词固有的语义特征可以转移到所限定的名词上,从而使该名词临时获得了该量词的某种语义特征。例如量词“滴”本适用于液体,“颗”本适用于固体。可在“一滴翡翠”中,翡翠用了“滴”似乎也具有了液体那种流质感与晶莹感;在“一颗露珠”中,露水也犹如珍珠成了一种固体。事实上,当抽象或无具体外形的实体被加上某个特定量词时,这个量词所固有的语义特征就使这些抽象的东西变为具体的东西,使无形的对象变为有形的对象,从而增加了这个组合本身的表现力,如“一片寂寞、一串笑声、一丝希望、一线阳光”等。
其二,语义相近的量词可以构成近义词群,不同量词表现出来的不同色彩与语义倾向会对限定的名词产生渗透效应。如可与“书”组合的量词有细微差别,用“部”显得厚重,用“册”文言色彩较浓,用“卷”侧重于成套书中的一本,用“本”最能表现通常的本子形态。又如“根”与“条”都是长条形,都适用于“黄瓜、树枝、带子”等,但由于“根”的语义偏重于“直而硬”,而“条”的语义偏重于“曲而软”,因此“一根黄瓜 / 一条黄瓜”、“一根带子 / 一条带子”、“一根树枝 / 一条树枝”给人的感觉是不同的,这就是量词的语义在起作用。
上述两种现象,按照当前认知语言学的解释是“概念整合”(conceptual blending)产生的效应(参见王正元,2009)。汉语量词保留潜在语义,往往使得特定的量词与特定的实词类之间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组合关系。诚如邵敬敏(1993)指出的那样,量词的语义如极其明确,对名词的选择组合是单一的,则名词即使不出现也不会引起误解,这时数量词本身便可替代名词;或从另一角度讲,名词可以省略,尤其是加上动词的语义制约,那时数量词的语义内涵就更加确定无疑了。例如:
a.中间因有事漏看了一幕(戏)。
b.那边空地上已经盖起了好几幢(楼房)。
c.他把走廊里的几盏(灯)都关了。
d.我也来说上几句(话)。
3.2.2 构式赋义的强制效应
上文曾指出数量词的篇章指代功能实现的句法条件是数量词与中心语的分离,而数量词与中心语的分离正是说话人出于某种语用驱动进行的句法形式的再编码。这种句法形式再编码的结果产生了各种表达特定话语功能的“构式”,与中心语分离的数量词的篇章指代功能正是构式赋义产生的强制效应。认知构式语法的创始人戈德堡(Goldberg,1995)曾举例说明了这个原理,例如:
She baked him a cake.(她为他烤了一个蛋糕。)
本来核心动词bake是一个二价动词,只能直接支配两个论元(施事she和受事cake),但在上例中却增加了一个论元(涉事him)。戈德堡对此明确指出:在构式语法的研究中,我们认为关于致使移动、有意转移或致使结果的最终解读可以归结于不同的构式。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框架构式(skeletal construction)本身可以提供论元。例如我们认为双及物构式与施事、受事和接受者角色直接相联,因而制造类动词(如bake)可以在该构式中出现。我们不必因为bake可以出现在双及物构式中而再为它专门设定一个特别的意义。总之,戈德堡认为上例中的直接宾语him是双及物构式“强制性”的语义角色指派而出现的,并非动词的论元结构允准的。
本文讨论的与中心语分离的数量词的篇章指代功能的理据,也是构式赋义产生的强制效应。下面我们选择本文涉及的部分典型构式加以分析,以论证构式赋义的强制效应。
首先,总分式并列复指结构,见本文例(7)、(8)、(28)、(29)。此类构式可以码化为“NP(总说):一量 + VP,一量 + VP”,构式的话语功能是明显的,说话人为了凸显分说部分并列分句的信息。如“哥嫂俩,一个是乒乓冠军,一个是羽毛球冠军”,说话人要凸显的正是两个“一量”都是冠军这个信息。构式中“一量”都是分说部分并列分句的话题主语,后边一般不再也不必出现中心语,因此指代总说NP的功能是显性的。
其次,NP分裂前移话题化结构,见本文例(25)、(26)、(27)。此类构式可以码化为“NP + S + VP + 数量”,语用驱动显而易见,是原来充当宾语的“数量 + NP”分裂而NP前移话题化的结果,如“儿子一口气吃了三块牛排 → 牛排儿子一口气吃了三块”。说话人之所以这么调整句法编码,是为了凸显句末数量成分以体现说话人的主观评价,如上例说话人显然觉得儿子吃多了。此类构式由于中心语NP前移充当了话题,句末只有数量词单独充当宾语,指代句首NP的功能也是显性的。
第三,否定性周遍义主语结构,见本文例(22)、(23)、(24)。此类构式可以码化为“NP,一量 + 都/也 + 不/没VP”,从逻辑上来分析这是通过否定最小量“一”来达到否定全量的目的,与直接否定相比体现了说话人的强调意图。如“说好来参加会议的代表,竟然一个都没来”,在说话人看来这太不可思议了,所以选择了此类构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为了体现这个话语功能,此类构式中句首话题NP需要足够的信息,往往是个复杂形式,而真正的主语“一量”就是个光杆形式,后边没有中心语,但指代话题NP的功能却是显性的。
第四,“一量”同指复现述宾结构,见本文例(15)、(30)。此类构式可以码化为“V + 一量iV + 一量i”,是较为典型的口语表达式,“一量”同指复现(i为同指标记),用来体现说话人对非常态现象的主观评价。如《水浒传》中形容李逵杀人的描述“抡起一双板斧,见一个砍一个”,就选择了此类构式来表达,显然不分青红皂白胡乱杀人是不应该的。此类构式中,同指复现的两个“一量”指代的对象往往隐含在语境中,一般不出现也不需要出现,如上例专指当时当地出现在李逵视野中的任何人。这样两个“一量”构成的述宾复叠显得更精炼,而指代某类对象的功能却是显性的。
最后,状位递进性差比义结构,见本文例(18)、(31)。此类构式可以码化为“一量 比 一量 + VP”,处在状位的两个“一量”之间有递进性差比义,动因是语境中蕴含了时间序列。如“这次的足球比赛,一场比一场精彩”,一场场的足球赛有一个时间先后,“一场比一场精彩”指在这个时间序列上相对在后的“一场”总比相对在前的“一场”更精彩,由此形成递进性差比效应。这也是一个平时常用的口语表达式,其中处在状位的“一量 比 一量”很紧凑,两个“一量”后边一般也不出现中心语,而指代某类对象的功能却是显性的。
综上所述,在考察中,笔者发现由于数量词所处的句法位置不同,指代功能也不同质,一般来说从强到弱呈现如下序列:
主位 / 宾位 > 状位 / 补位 > 述位
究其原因,这与不同句法位置本身的指称性强弱相关。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展开,留待另文集中描写、解释。
[1] 陈承泽.国文法草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1922] .
[2] 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 高名凯. 汉语语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948].
[4] 郭先珍. 现代汉语量词用法词典[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2.
[5] 何杰.汉语量词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6] 金兆梓. 国文法之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922].
[7] 黎锦熙. 新著国语文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924].
[8] 龙景科. 汉语非真值义数词“一”及相关格式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9.
[9] 刘丹青. 汉语名词性短语的句法类型特征[J].中国语文,1999,(1).
[10] 刘复.中国文法通论[M].长沙:岳麓书社,2012.
[11] 刘辉. 现代汉语事件量词的语义和句法[D].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12] 刘街生. 现代汉语动量词的语义特征分析[J].语言研究,2003,(2).
[13] 陆俭明. 现代汉语句法里的事物化指代现象[J].语言研究,1991,(1).
[14] 陆志韦. 北京话单音词词汇[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15]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6] 马建忠. 马氏文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新1版,1999[1898].
[17] 邵敬敏. 量词的语义分析及其与名词的双向选择[J].中国语文,1993,(3).
[18] 沈阳. 名词短语分裂移位与非直接论元句首成分[J].语言研究,2001,(3).
[19] 石毓智. 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
[20]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新1版,2000.
[21] 王正元. 概念整合理论及其应用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2] 袁毓林. 论元角色的层级关系和语义特征[J].世界汉语教学,2002,(3).
[23] 朱德熙. 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4] 大河内, 康宪. 量词的个体化功能[A].靳卫卫,译. 大河内康宪.日本近、现代汉语研究论文选[C].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25] Doetjes Jenny.MassandCount:SyntaxorSemantics?MeaningontheHIL[Z].Occasional Papers in Linguistics. HIL/Leiden University,1996.
[26] Doetjes Jenny.QuantifiersandSelection:Onthedistributionof,quantifyingexpressionsinFrench,DutchandEnglish[D]. PHD dissertation of Leiden University, HAG, The Hague,1997.
[27] Goldberg Adele E.Constructions:AConstructionGrammarApproachtoArgumentStructure[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5.
[28] Lyons J.Semantics:Volume2[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