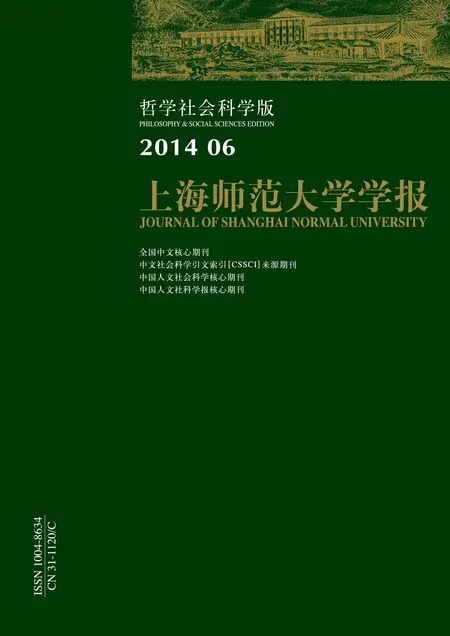“情兼雅怨”的内涵与曹植诗的“集大成”地位
李定广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钟嵘《诗品》对曹植诗评价之崇高,类似于刘勰评价五经。《诗品序》赞曹植是“文章之圣”,而《诗品》卷上更对曹植诗极尽美誉之辞:“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1](P117~118)其中“情兼雅怨”一句,诸家有不同解释,给读者造成一些困惑,本文试图对诸说加以平议,并联系钟嵘对曹植的总体定位以及曹植诗歌的实际成就和特色,提出新解,并进一步探索钟嵘“情兼雅怨”定位对曹植诗“集大成”诗史地位的深远影响。
一、“情兼雅怨”歧说平议
对“情兼雅怨”的理解,最核心的是如何理解“雅怨”。总体上看,学者对“雅怨”一语有偏正、并列两种理解角度。
其一,偏正关系的理解。认为“雅怨”即《小雅》之怨,是“《小雅》怨诽而不乱”的缩略语,意指《小雅》怨而不怒的风格。陈延杰《诗品注》、古直《钟记室诗品笺》、叶长青《诗品集释》、杜天縻《广注诗品》、汪中《诗品注》、赵仲邑《钟嵘诗品译注》、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等皆如是解。杨明先生《文赋诗品译注》有详尽解释:“意谓其诗出于《国风》,又兼有《小雅》怨而不怒的风格。按:班固《离骚序》引刘安《离骚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钟嵘认为曹植诗虽抒发受压抑的怨苦,但表现得温厚和平,仍充满眷恋君上之情。”[2](P47)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对此亦有阐发:“情兼雅怨主要是就思想内容说的……钟嵘于诗歌内容重视表现怨情……他赞美情兼雅怨,就是要求诗的抒情应怨而不失雅正,像《诗经·小雅》那样‘怨悱而不乱’(《史记·屈原列传》),具有儒家所提倡的温柔敦厚之风。”[3](P507)
其二,并列关系的理解。认为“雅”与“怨”是两种美学风格,即雅正与怨诽。权威性辞书《汉语大词典》“雅怨”词条即这样解释:“雅正与怨诽。南朝梁钟嵘《诗品》卷上:‘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向长清《诗品注释》、周伟民、萧华荣《〈文赋〉〈诗品〉注译》、周振甫《诗品译注》等皆如是解。刘跃进《曹植创作“情兼雅怨”说略》一文对此有详尽分析:“‘雅怨’,与‘文质’对举,说明是并列关系。……既然‘雅怨’与‘文质’对举,则这两组术语之间应当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就其显而易见的方面看,‘雅’与‘文’相近,而‘怨’则与‘质’对等。因此,‘情兼雅怨’,实际蕴涵着曹植创作的‘雅’与‘怨’两种相辅相成的风格要素。雅与文,即文雅的风格,而怨与质则表现为质朴、通俗的特色。”[4](P533)
对于以上两解,韩国李徽教《诗品汇注》认为二说皆可通,但以后说较胜:“此‘雅’字之释,诸家之说有二:一为以《小雅》之‘雅’解,如陈注、古笺、叶《集释》、杜注、汪注等说是也;又一为以对‘怨’字之‘雅’解,如张氏标点、许释、车校、立命馆疏等说是也。以上两说,皆未尝不可,后说较胜。”[5](P124)
平心而论,二说确实皆可通,前说实而后说虚,但各执一隅,于义似有未惬,未必符合钟嵘本意。前说的疑点主要在于为了迁就“《小雅》怨诽而不乱”的典故而未能顾及上下文的语境和语言结构,其实钟嵘不喜用典,也反对用典。后说的问题主要在于理解过于虚泛,未落实处,似乎给人感觉钟嵘的审美标准就是“雅”与“怨”两种抽象的风格而毋须坐实,其实《诗品》全书时时贯彻的最高审美标准应该是“骨气”和“词彩”或称“风力”和“丹彩”,且可以落实样板。曹旭似已认识到此一问题,他在认定“雅”与“怨”是两种美学风格的基础上,努力使“雅”与“怨”落到实处。曹先生认为“雅”指“《国风》之雅”,“怨”指“《小雅》之怨”,其说云:
“情兼怨雅”:指曹植诗歌风格既具《国风》之雅,又具《小雅》之怨,得二者之长。……陆机《岁志赋序》曰:“崔、蔡冲虚温敏,‘雅’之属也;(冯)衍抑扬顿挫,‘怨’之徒也。”曹植诗风,既具冲虚温敏之雅,又具抑扬顿挫之怨。可当别解。此处“雅怨”,与下文“文质”,均为并列关系。乃指由《诗经》之《国风》、《小雅》升华出两种对应之美学风格。[1](P124~125)
曹先生的理解能兼取前二说之长,虚实兼顾,并以陆机《岁志赋序》为旁证,较有说服力。然其所落之“实处”,仍有继续讨论的空间。
笔者受到曹旭虚实兼顾理解方向的启发,深入比较二说后,在尊重上下文语境的基础上,再联系《诗品》所标榜的诗学体系和标准,《诗品》对曹植的总体定位,以及曹植诗歌的实际创作成就和特色,提出新解,虽未必探骊得珠,但求自成一说。
二、“情兼雅怨”新解
笔者以为,钟嵘所谓“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两句应当为对仗互文关系。“情”与“体”是同一事物的内外两面,含义相关,故形成对仗互文关系。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的《春秋左传正义》卷一有云:
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正义曰:言其意谓之“情”,指其状谓之“体”。体情一也,故互见之。[6](P16)
《文心雕龙·风骨》亦有“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的互文用法。既然上下句间的“情”与“体”,下句之内的“文”与“质”,都是并列关系的两个概念,那么与“文、质”相对应的“雅、怨”亦应理解为并列关系的两个概念,再加上“兼”与“被”两个对应的动词,上下句才构成真正的对偶互文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明冯惟讷《古诗纪》卷二十三所引《诗品》以及明张溥《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卷二十七所引本句皆作“情兼怨雅”,可见“雅”、“怨”两字互乙,不影响含义的表达。在两句对仗互文理解的前提下,笔者以为,“情兼雅怨”之“雅”,应是指《小雅》及其所代表的风格,“情兼雅怨”之“怨”应是指《楚辞》及其所代表的风格。兹详论之。
钟嵘论全部诗人之源有三:一是《国风》,二是《小雅》,三是《楚辞》。其中标明源于《国风》者14人,源于《小雅》者1人,源于《楚辞》者22人,可见钟嵘认为《楚辞》对后世诗歌影响更大些。而曹植源出于《国风》,是《国风》系的代表诗人,同时钟嵘欲推曹植为笼罩所有诗人的诗人之冠,是无与伦比的“文章之圣”。曹植诗若不能兼该《小雅》与《楚辞》,尤其是影响最大的《楚辞》,则冠其至高无上的“文章之圣”、“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等称号与地位就缺乏说服力。换言之,钟嵘的意图盖为:曹植诗之源虽为《国风》,但又能兼该《小雅》和《楚辞》,这样,既得经(《国风》《小雅》)之正(即宗经),又得辞人(《楚辞》)之长,这样才能称得上真正的诗人之冠。
以“雅”代表三源中的《小雅》比较容易理解,那么以“怨”代表三源中的《楚辞》,又有何根据呢?我们发现,在《诗品》全书中,钟嵘每以“怨”字来代称楚辞或评价受楚辞影响的诗人。《诗品》评《楚辞》系列的诗人,大都强调一个“怨”字。如评《楚辞》第一传承人李陵,谓其“文多凄怆,怨者之流”,“怨者之流”意即《楚辞》一派,而钟嵘将全书其他所有《楚辞》系的诗人皆认定为源出于李陵。又如评《楚辞》系的班婕妤谓“其源出于李陵……怨深文绮”。评《楚辞》系的王粲谓“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评《楚辞》系的刘琨“善为凄戾之词”,评《楚辞》系的卢谌“多感恨之词”,等等。“愀怆”、“凄戾”、“感恨”就是“怨”,只为避免重复而更换词汇。以“怨”代指《楚辞》的特点,是否钟嵘首创?原来以“怨”概括《楚辞》源自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有云:
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7](P2482)
到唐代,李白《古风》(大雅久不作)在描述由《诗经》到《楚辞》的发展历史时说:“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亦以“哀怨”代表《楚辞》。盛唐李林甫等人编的《唐六典》这样概括介绍“集部”《楚辞》一书:
丁部为集,其类有三:一曰《楚辞》,以纪骚人怨刺。[8](卷十,P300)
《唐六典》对《楚辞》的这一定性表述被后来的《旧唐书·经籍志》等目录学作品所沿用。可见,以“怨”或“骚怨”来代表或概括《楚辞》是自汉到唐的基本共识。直到明代吴国伦《七泽吟序》仍云:“予读《楚辞》,而知楚之人善怨,其天性哉?”[9](卷三十九)
当然,具备“怨”的情感和风格的作品并不止于《楚辞》,前述《小雅》就有“怨诽”的特点,甚至《国风》中某些作品也有“怨”。但是只有《楚辞》,“怨”的情感最强烈,“怨”的程度最深,“怨”的特色最突出、最具代表性,“骚人怨刺”或“骚怨”甚至成为《楚辞》的代称,所以汉唐人普遍将《楚辞》一派的诗人称为“怨者之流”,钟嵘以“怨”字来代称《楚辞》或评价受《楚辞》影响的诗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那么,曹植诗歌创作是否有对《小雅》和《楚辞》的学习和继承呢?回答是肯定的。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子建、仲宣……莫不同祖《风》、《骚》。”[10](卷六十七,P1778)沈约所谓“《风》、《骚》”实为《诗经》和《楚辞》的代称。明末清初的毛先舒在《诗辩坻》中就指出:“曹子建言乐而无往非愁,言恩而无往非怨,真《小雅》之再变,《离骚》之绪风。”[11](卷二,P26)清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中认为:“子建之诗,隐括《风》《雅》,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12](卷五,P108)可见,曹植对《诗经》和《楚辞》有学习和继承,是后世学者的一致看法。这在曹植的诗作中有怎样的具体体现呢?这里不妨列举曹植诗歌作品的实例,来观察曹植诗对《小雅》和《楚辞》的学习和继承。
曹植诗中明显学习《小雅》的不在少数。曹植的《赠徐干》诗,毛先舒以为出于《小雅·四月》:“子建《赠徐干》,起四句是比,急接‘志士’、‘小人’,神锋捷露。良田不雨,兼无晚获;膏泽所施,长得丰年。即杨恽‘田彼南山’之意,皆出于《小雅·四月》之四章。”[11](卷二,P27)曹植的名篇《赠白马王彪》,清人何焯认为也是学习《小雅》的“婉转深厚”:“曹子建《赠白马王彪》,《小雅》嗣音……‘霖雨泥我涂’四句不直言有司禁其同途,而托之淫潦改辙,恐伤国家亲亲之恩也。下乃言非我马竟不能进,势固有不克俱者。婉转深厚。”[13](P906)清人宋长白从诗歌句意、技法上认定曹植诗对《小雅》的学习和继承,譬如评及曹植《仙人篇》曰:“陈思王诗‘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知’(笔者按:此曹植《仙人篇》中句)即‘谓天盖高,谓地盖厚,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笔者按:此《小雅·节南山》中句)注脚,想其意味,当是鄄城移东阿时也。”[14](卷二,P31)再譬如宋长白论“隔句对”的源起时说:“隔句对始于曹子建《鳝篇》,即《小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之章法也。”[14](卷十,P206)曹植《鳝篇》开头四句确是精美的隔句对,这一技法是曹植在学习《小雅·采薇》末四句的基础上加以运用发挥的成果。其实更典型的例子如曹植《朔风》篇中的隔句对“昔我初迁,朱华未晞;今我旋止,素雪云飞”,更明显是学习《小雅·采薇》末章“昔我往矣”四句而来。曹植是文人中首个多次运用“隔句对”技法的,所以宋长白说“隔句对”始于曹植也不能算错。有学者统计,“在曹植引用《诗经》的100处之中,出自《国风》28处,《小雅》39处,《大雅》17处,《颂》7处。这些数字与‘小雅怨诽而不乱’的风格恰好相一致。”[15]可见,曹植的确是对《小雅》情有独钟,钟嵘说其诗“情兼雅怨”可谓目光敏锐,即使说其源出于《小雅》也不致离题太远。
曹植诗对《楚辞》的模拟学习,沈约等人早有论述。清人李重华认为六朝真正拟《楚辞》者惟有曹植:“屈、宋《楚辞》而后,不应轻拟《骚》体,必欲拟者,曹植庶得近之。”[16](P927)刘熙载甚至不大认同钟嵘关于曹植诗源出于《国风》的说法,认为曹植诗出于《骚》:“曹子建、王仲宣之诗出于《骚》,阮步兵出于《庄》,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17](P2421)可见,曹植与《楚辞》的渊源关系为历代学者所揭橥。
曹植诗中刻意学习《楚辞》的典型例子很多,最明显表现在曹植对“骚怨”主题的继承和对屈骚“香草美人”表现方式的借鉴两个方面。像《杂诗》六首、《赠丁仪王粲》《野田黄雀行》《赠白马王彪》《美女篇》《情诗》等篇,皆是典型的“骚怨”之作,属于钟嵘所谓的“怨者之流”。清初吴淇认为:“《杂诗》六首,似皆原本于《离骚》。吾不知其有意摹之欤?抑无心偶合欤?第一章‘高台多悲风’即《思美人》。二章‘转蓬离本根’即《悲回风》。三章、四章‘西北有织妇’、‘南国有佳人’,即《经》所谓‘蹇修’,乃《离骚》之正托。五章‘仆夫早严驾’,即《远游》。末章咏烈士,即《九歌》之《国殇》。”[12](卷五,P113)分析切中肯綮。初唐吴兢以为曹植七首游仙诗皆出于《楚辞·远游篇》:“曹植又有《飞龙》、《仙人》、《上仙录》与《神游》、《五游》、《远游》、《龙欲升天》等七篇……皆伤人世不永,俗情险艰,当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其词盖出楚歌《远游篇》也。”[18](卷下,P49)北宋郭茂倩则认为曹植游仙诗《飞龙篇》出于《离骚》:“《楚辞·离骚》曰:‘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曹植《飞龙篇》亦言求仙者乘飞龙而升天,与《楚辞》同意。按:琴曲亦有《飞龙引》。”[19](卷六十四,P926)曹植《飞龙篇》到底学习《楚辞》中哪一篇,吴兢与郭茂倩看法虽异,但源于《楚辞》的认知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本文对于“情兼雅怨”的这一新解,与其他诸解相比,长处是虚实兼顾,既有学理逻辑的依据,也符合文学史事实,在曹植诗歌中得到坚实的验证,而且基本上没有乖碍难通之处,故而可能更符合钟嵘本意。钟嵘本意应是认为,五言诗有《国风》《小雅》和《楚辞》三源,曹植诗源出于《国风》,同时兼具《小雅》和《楚辞》的特点,故能成为诗人之冠。更重要的是,钟嵘的这一看法,不仅概括了曹植诗的特色和成就,实际上也已初步点明了曹植“集大成”的诗史地位。
三、“情兼雅怨”与曹植诗的“集大成”地位
中国诗史上具有“集大成”地位的诗人,当今人们熟知的只有杜甫一人。殊不知,自魏晋六朝以后,曹植也逐渐被推尊为具有“集大成”地位的诗人,而在文学史史实上,曹植也确曾名符其实地拥有“集大成”的诗史成就。只是到赵宋以后,曹植的诗名和诗史地位骤降,而杜甫的“集大成”地位得到公认,从此诗史上的这顶“集大成”桂冠被“气吞曹刘”的杜甫所专有。杜甫一直如同夜空的一轮皓月,掩盖了曹植这颗巨星的光芒。加上赵宋以后,陶渊明、韩愈、苏轼等诗人地位的攀升,使得曹植愈来愈受到冷落。直到明清之际,曹植的“集大成”诗史地位才获得部分学者的重新讨论和确认,但在当今学界,这一定性并未获得响应,更仍未能得到主流学界的认可。个中原因,值得反思。兹详论之。
早在钟嵘《诗品》之前,曹植就被公认是一位兼善、兼美也就是集众家之长的文人,被认为具有“集大成”的创作成就。曹植的诗、赋、颂、铭、杂论等各种文体样样登峰造极而且创作数量大,这在曹植时代以及曹植以前的所有时代无与伦比。若仅就诗歌一体而言,曹植无论在形式上(四言、五言)还是风格上都是一位兼善、兼美的诗人。刘宋初年,颜延之在其《庭诰》中云:“至于五言流靡,则刘桢、张华;四言侧密,则张衡、王粲。若夫陈思王,可谓兼之矣。”[20](卷586,P2640)是认为曹植既擅五言诗的流靡,也擅四言诗的侧密,可以兼该刘桢、张华、张衡、王粲这些一流诗人的长处。这一评价与认定,奠定了后来钟嵘评价曹植的基础。与颜延之同时的谢灵运对曹植亦有类似的评价:“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21](卷中,P586)是谓曹植之才无所不能,曹植之成就无人能及。稍后,沈约在他的著名的史论《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出了“文体三变说”,认为以曹植为代表的建安诗歌“以情纬文,以文被质”,[22](卷六十七,P1778)文质彬彬,尽善尽美。这是在正史中为曹植的地位和成就定性。稍后的刘勰又在文学理论著作中再次确认曹植的“兼善”成就和地位,其《文心雕龙·明诗》云:“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23](P65~66)在前人对曹植的这些评价和定性的基础上,钟嵘《诗品》推举曹植为诗人之冠,认为曹植诗源于《国风》,同时兼具《小雅》和《楚辞》的特点。从此,曹植诗的“偶像”地位和“集大成”特色逐渐深入人心,被后人尤其是唐人所普遍接受。
唐代最重诗、赋两种文体,唐人所树立的唐以前“赋”的偶像是司马相如和扬雄,而“诗”的偶像则是曹植。唐人常以曹植诗作为诗歌的最高代表,认为他是诗界罕有比肩的全才、大才。骆宾王说:“若乃子建之牢笼群彦。”[24](P222)唐玄宗说:“陈思有超代之才。”(《与宁王宪等书》)这些对曹植的评价和定位与钟嵘是一脉相承的。其他如李白说“曹植为建安之雄才”(《上安州李长史书》),并每每以曹植自况。李华认为“曹植丰赡,王粲超逸,嵇康标举”(《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丰赡”亦有“集大成”的意味。杜甫向长官自夸其诗赋水平,如云:“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又云:“文章曹植波澜阔。”(《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晚唐韦庄在他所编的唐诗选集《又玄集》序言中,标举诗歌榜样云:“曹子建诗名冠古。”[25](P579)等等。可见,从初唐到晚唐,曹植在唐人眼中确是具有“偶像”地位和“集大成”成就的诗人。当然,唐人对陆机、谢灵运的评价也很高,如唐太宗对陆机的崇拜、皎然对谢灵运的推崇等。但这只是个别现象,是有特殊原因的,并没有形成唐人的普遍共识,更没有达到曹植那样的高度。
曹植的名声和地位在宋代急遽下滑。可以说,宋代是曹植接受的转折点。宋代最重诗、古文两种文体,宋人所树立的前代诗歌偶像人物不再是曹植,而是杜甫;古文偶像也不再是汉魏古文家,而是韩愈。从宋初王禹偁的“杜甫集开诗世界”,到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杜甫的地位被推向极致。到秦观在他的著名论文《韩愈论》中大力标举杜甫、韩愈两人分别为中国诗、文的“集大成”者之后,杜甫就彻底取代曹植等一切诗人,成为中国诗歌的“代表”。不仅如此,从宋代开始,曹植诗时或受到某些文人的批评,如苏轼曾贬抑曹植诗不及陶渊明。而且对曹植的批评和贬抑越来越重。到明代,大学者王世贞甚至认为曹植不及曹操和曹丕:“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26](卷三,P987)王夫之《姜斋诗话》甚至对曹植极尽诋毁。但总体上看,宋元明清以来,曹植虽时常遭受批评和贬抑,但作为一流诗人的声誉及其诗歌“集大成”的地位也还时不时地得到学者认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偶或有学者将曹植与杜甫相提并论,分别作为不同时期“集大成”的代表。
南北宋之间的张戒,不满苏轼贬抑曹植诗不及陶渊明等人,在其《岁寒堂诗话》中极力为曹植诗辩护:
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自曹刘死至今一千年,惟子美一人能之。……古今诗人推陈王及《古诗》第一,此乃不易之论。[27](卷上,P450~451)
张戒建立在复古观念基础上的辩护,推曹植于一切诗人之上,在当时杜甫、韩愈声名震天,曹植地位每况愈下的背景下,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对于遏制贬抑曹植诗的风气有一定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张戒首次将曹植诗与杜甫诗相提并论,具有深远的文学史意义。宋末的严羽,许多论诗主张受张戒影响很大,在对曹植的评价问题上,虽未如张戒那样推曹植为古今诗人“第一”,但其对以曹植为代表的汉魏诗亦推崇至极,认为与李杜为代表的盛唐诗同为“第一义”(见《沧浪诗话·诗辨》),亦是某种程度上对张戒的呼应。
明末复古派大批评家胡应麟,在张戒和严羽的基础上进一步标举曹植和杜甫分别代表两个时期的“备诸体”和“集大成”者,他说:“陈思而下,诸体必备,门户渐开。”[28](内编卷二,P23)又云:“备诸体于建安者,陈王也;集大成于开元者,工部也。”[28](内编卷二,P35)又云:“建安中,三、四、五、六、七言、乐府、文、赋俱工者,独陈思耳。”[28](外编卷一,P137)胡应麟以“备诸体”与“集大成”对仗互文,含义相近。受胡应麟的影响,明末清初人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中首次鲜明地标举曹植与杜甫分别为两个时期的“集大成”者:
《选》诗有子建,唐诗有子美,各际中集大成之诗人也。盖汉道创于苏、李,盛于曹、刘;唐制始于沈、宋,盛于李、杜耳。世人知尊子美,而不知子建,由于只知唐诗略过《选》诗一际之故。”[12](P108)
吴淇将先秦至明末的诗歌分为前、中、后“三际”,曹植诗,集“中际”(自汉迄梁昭明所选,亦即《选》诗阶段)之大成,杜甫诗,集“后际”(自梁迄吴淇的时代)之大成。这一观点虽遭清代崇杜者的指摘,但论定曹植与杜甫皆为“集大成”者,是很有见地而且非常符合客观事实的。同时他还正确地分析了当时人只知杜甫为“集大成”诗人而不知曹植也是“集大成”诗人的原因在于,时人太重唐诗而忽略《选》诗。其后,吴淇的这一观点不时得到响应和发挥。如清人冯班说:“千古诗人,唯子美可配陈思王。”[29](卷四,P589)清人李重华说:“魏诗以陈思作主,余子辅之。五言自汉迄魏,得思王始称大成。”[16](P926)近人黄节的《曹子建诗注序》对曹植诗的特色做了这样的概括:“陈王本国风之变,发乐府之奇,驱屈宋之辞,析杨马之赋而为诗,六代以前,莫大乎陈王矣。”[30](P1)这实际上也就是“集大成”的内涵。
当代学者钱志熙认为曹植诗融合儒、道、庄、骚而形成的“历史文化因素”在汉魏诗人中最为突出:“将儒家的文学传统和《庄》、《骚》的文学精神融合到五言诗和乐府诗中。曹植诗歌中的历史文化的因素,比起汉末和建安的其他诗人来要突出得多。”[31](P167)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对曹植诗有这么一段论述:“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 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32](P35)当代这些对曹植诗的评价和定性,实际上都是从不同侧面对曹植诗“集大成”特色和地位的一个注脚。当今学界乃至高校教材对曹植诗评价虽然颇高,但远低于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人,更无人明确响应、标举曹植诗的“集大成”成就和地位。这里需要一辨的是,文学史中的“集大成地位”与“文学史地位”(或“文学地位”)是有所不同的。前者在创作成就“高”的前提下更侧重强调创作成就之“全面”,即集众家之长而又有多方面开创;后者在创作成就之“全面”的前提下更侧重强调文学成就之“高”,即文学造诣之登峰造极。曹植诗就其文学成就之“高”而言,也许不及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人,但就其创作成就之“全面”和开创性而言,应当不在诸人之下;而在结合各自时代文体和技法的成熟度上,则更显曹植之可贵。
因此,子建、子美前后呼应,皆为不同时期的“集大成”诗人,这一点既为批评界前贤所揭橥,而子美的“集大成”地位已为自宋以来的学界所共识甚至成为当代常识,那么子建的“集大成”成就和地位也应得到当今学界的明确认可。承认曹植诗“集大成”地位,并不等于承认曹植的“文学史地位”(或“文学地位”)就超过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人。
现在回到前面的话题,钟嵘《诗品》关于曹植诗“其源出于《国风》”,同时又“情兼雅怨”的说法,实质上已初步确立了曹植诗的“集大成”成就和地位,并得到后世批评家的认可和完善,特别是明末清初吴淇鲜明的“集大成”定位。在汉末那个文人诗刚刚兴起的时代,曹植能够“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三国志·陈思王植传》),一生无论顺境逆境,始终勤奋写作,对于诗歌,从题材到技法,从风格到体式,能集众家之长而又有多方面开拓,从而成为我国诗史上第一位融《诗》《骚》风格于一体,集先秦汉魏诗之大成的诗人,为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故钟嵘的评价和吴淇的标举,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曹植和杜甫是中国诗史上仅有的两位具有“集大成”地位的诗人。若从这个意义上看,有人将子建、子美齐名并称是十分合理的。
[1] 曹旭.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 杨明.文赋诗品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3] 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4] 刘跃进.秦汉文学论丛[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5] 李徽教.诗品汇注[A].曹旭.诗品集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6]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杜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7]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8] 李林甫,等.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
[9] 吴国伦.甔甀洞稿[M].明万历十二年刻本.
[10]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1] 毛先舒.诗辩坻[M].郭绍虞.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12]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M].扬州:广陵书社,2009.
[13] 何焯.义门读书记·文选·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4] 宋长白.柳亭诗话[M].上海:上海杂志公司, 1935.
[15] 张振龙,张晓庆.从用典看曹植对《诗经》的接受及其文艺思想[J].求索,2008,(5).
[16] 李重华.贞一斋诗说[M].丁福保.清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7] 刘熙载.诗概[M].郭绍虞.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8] 吴兢.乐府古题要解[M].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9] 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0] 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
[21] 宋无名氏.释常谈[A].陶宗仪,等.说郛三种[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宛山堂藏板,1988.
[22]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3] 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4] 骆宾王.和道士闺情诗启[A].陈熙晋.骆临海集[C].北京:中华书局,1961.
[25] 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26] 王世贞.艺苑卮言[A].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3.
[27] 张戒.岁寒堂诗话[A].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3.
[28] 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9] 吴乔.围炉诗话[M].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0] 黄节.曹子建诗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31] 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2]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