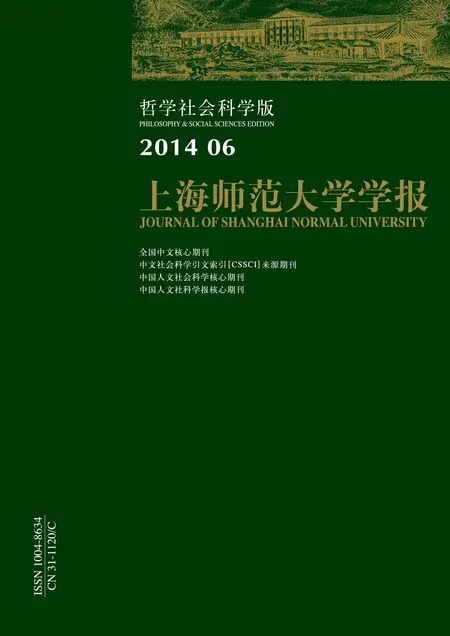20世纪前期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与逻辑内涵
陈 伟,王 展
(1.上海师范大学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234;2.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234)
2.王 展,江苏南通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南通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美学、文艺学研究。
随着“现代性”概念和思想自西方引介入国门,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结合中国20世纪历史进程对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探讨,并在诸多领域掀起了现代性反思热潮。十余年间,中国现代性问题始终是学界广泛关注的焦点之一,美学领域概莫能外。需要指出的是,对中国审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不能停留于纯粹的理论探求,更要结合社会实践分析问题,即如何理解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审美文化所起的作用。如果这一问题不得到解决,对我们准确把握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的本质属性与发展脉络都会产生不良影响。本文抛砖引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梳理与研究,以期推动当代中国美学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
一、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特殊性
科学、准确地把握中国审美现代性内涵,首先需厘清它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坐标轴上的定位。坚持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坚持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客观实际出发,是考察中国美学精神如何告别“古代”迈入“现代”具有现代性必须遵循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早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已经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P103)应用于审美现代性研究,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存在”有别于西方的“特殊性”,必定对中国审美现代性诸方面产生直接、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回顾西方历史不难发现,西方社会从古代至现代的历史进程脉络清晰,各个社会阶段均有与之适应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现代性发展目的单一,审美文化在经济基础变化后随之形成并产生作用。自英国拉开大幕的产业革命发轫,西方社会历经 “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和“科技时代”三大阶段近三百年的迅猛发展,至20世纪已基本完成了物质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从更为严格的历史学意义上说,是完成了“近代化”历程。在物质各个领域充分发展的同时,与之配套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也越来越细致入微地全面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形成了理性占上风的各种法律条文和民风习俗。因此,到20世纪中期德国学者于尔根·哈贝马斯返顾历史,察觉“启蒙现代性”(他把西方重视理性精神的现代化进程统称为“启蒙现代性”)已经严重压抑了人的自由本性,使人在不知不觉中被“理性”所异化。“哈贝马斯继承了韦伯的传统,把审美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主体摆脱社会现代性进程中日益受制于工具理性支配的解放之途。”[2](P19)据此出发,为了恢复人的本性,即恢复人所固有的鲜活本质特征,哈贝马斯提出用“审美现代性”来对冲“启蒙现代性”,即用人所固有的感性本质特征来挣脱社会制定的各种理性桎梏的束缚。马克斯·韦伯在谈到艺术时也说:“不论怎么来解释,艺术都承担了一种世俗救赎功能。它提供了一种从日常生活的千篇一律中解脱出来的救赎,尤其是从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主义那不断增长的压力中解脱出来的救赎。”[2](P19注②)当然,哈贝马斯所谓的“反理性”和韦伯提出的“艺术救赎”,并非真正意欲打碎数百年来西方社会形成的各种规范,而是在西方社会实践理性僵化后,试图用审美感性对其进行反拨,在精神层面上求得人自身的解放。但这种反拨是某种虚拟的完善模态,因而也只局限在审美层面上才具有有效性。这就是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特质。
中国的情况显然与西方不同,两者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历史进程:首先,中国封建社会历史阶段远较西方漫长,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经济生产方式,加上儒家礼治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实践、伦理规范与文化观念等足够强大并且顽固,使中国社会在内在惯性作用下表现出某种抗拒现代性进程的固步自封。据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西方业已迈开现代性进程大步时,中国封建王朝却依旧沉浸在“中央帝国”万世长存的春梦里,以致在东西方现代性进程的出发点之间划出了巨大的时间鸿沟。其次,中国的现代性进程背负着外敌入侵的屈辱,“就像一个被强盗强暴的姑娘,虽然生下的孩子是无辜的并依然可爱,但强盗留下的印记却是姑娘心里永远的痛”。[3](P261)19世纪中期严防死守了数百年的中华帝国大门一朝被强行打开,帝国主义列强蜂拥而至,掀起了掠夺瓜分中国的汹涌浪潮。独立国家的领土、主权在外来敌对势力强力入侵下部分丧失,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又迅速沦落为军阀此起彼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敌入侵使民族、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这也是西方现代性进程罕有的现实背景。再次,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被迫开放的中国沿海通商口岸,随着殖民资本和买办资本联手推进着工商业的发展,民族资本开始在其夹缝中渐渐生成。这在上海、广州、天津等大城市表现得特别显著。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战事无暇东顾,殖民资本经济局部萎缩,中国市场留出的空隙给民族资本经济发展释放了部分生长空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随着民族资本的兴起,一种民族的现代思想文化应运而兴,其结果即为标志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肇始,以启蒙为实质,崇尚科学、民主的新文化,反对愚昧、专制的旧文化,在文艺领域迅速确立了全新的现代美学形态。“这种新兴的美学形态及其延展的审美文化,在立意上高扬科学民主,在政治上推进富国强民,在手法上注重求真写实,在形式上追求通俗明了,在审美上强调平等互动。其深刻之处在于,把美学精神上的破旧立新与社会实践中的破旧立新联系了起来。”[4]中国审美现代性实质上是工商经济的产物,从历史角度观照,“它是以宋代萌发,经过明清两代发展的资本主义因素为基础的”。[5](P2)五四时期后由于殖民资本的推动,以及民族资本的兴起,在中国的经济文化前沿城市,即以上海、广州、天津为核心的工商大都市中,应运而生了以现代美学形态为内核的审美文化,并随即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主流。
此前,部分先觉的中国知识分子已开始对日常的生活进行梳理、批判与反思,渴求一种符合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生活方式,虽不知其究竟为何,但心向往之。随着五四新文化的大旗高举,中国人民蓦然发现自己正走在一条前人所没有走过的“新”路上,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之路。在这条路上,无论是社会物质还是社会精神,都具有不同于以往的内在属性与实践要求,都需要或者面临变革创新。因此,物质与精神两方面携手并进,共同推动着中国社会现代性的进程。这就是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与西方的根本不同之处。在西方,是物质现代性先行发展了,然后用审美现代性对其进行反拨;而在中国,由于是全方位的发展滞后,急需奋起直追,因而物质方面与审美方面同时担负着推进社会现代性的繁重任务。换言之,中国是在物质与审美两方面“共时性”时代要求下,去完成西方社会现代性进程中的“历时性”任务。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化时,不能将物质文化与审美文化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的重要原因。并且,自1840年被“船坚炮利”的帝国主义列强强行打开国门后,由于殖民资本入侵,中国现代性进程带有强制的殖民化色彩。帝国主义列强在殖民过程中所带来的一系列新的经济方式和文化,一定程度上成为整个中国社会从古典向现代转化的基干。古老的东方雄狮就此觉醒。身处内忧外患中的中国人民一方面始终没有停止对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的反抗;另一方面也致力于改造中国旧社会,寻求把中国从封建的农业社会改造成现代的工业社会的多重途径。这个过程反映在审美领域,使20世纪前期中国审美现代性进程拥有了双重含义:第一,在整体社会构架上按照“美的规律”建设中国现代体系;第二,在具体审美文化领域内从“民族独立”、“人的解放”两个维度推动现代社会发展。这就是我们理解的中国审美现代性的本质属性。
目前关于中国审美现代性的思考,有两种观点颇具影响。一种观点强调政党革命的政治权力意志对文艺审美特性的刻意压制或利用,尤其认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批评准则是这种姿态的极致表现。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审美工具主义”与“审美自律主义”在中国现代美学发展历程中始终对峙并存,呈现齐头并进的姿态,演绎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从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分析,无论是“权势统一说”还是“双线并进说”,均有片面之处。前者持抽象的审美自主性观点,无视对其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生产关系、阶级组成状况和时代特定要求,对中国审美现代性进程中基于特定历史时期侧重于民族独立一维的做出了极不恰当的评价,进而形成僵化、错误的思想观点。后者则忽略了矛盾运动中的主要方面,无视虽然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摆在面前,但中国现代美学从未在两条阵线上同时进行大规模推进的客观事实;而且在研究中将具体的个体审美诉求与宏大的民族解放事业等量齐观,也是不甚妥当的。
二、中国审美现代性发展的历史落差与逻辑转折
马克思在阐述人具有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时指出,人在劳动中“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6](P51)“美的规律”何谓?概而述之,“美的规律”就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中能够最大限度地把握客观法则,最大限度地伸张人的主体自由性的方式方法和理想追求。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完成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恰恰是最高准则的“美的规律”的体现。然而,美的规律并不是指某一种僵化机械的原则和标准。人类社会处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个人类社会的特定历史阶段里必定内在地形成与之相应的特定的美的规律。①20世纪前期的历史要求规定了中国现代性进程沿着两个实践维度展开:一个维度是追求独立的民族国家,即把帝国主义列强赶出中国的“反帝”;另一个维度是追求人的解放,即追求自由平等等基本权利的“反封建”。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现实任务有轻重缓急之分,因此按照“美的规律”伸张人的主体自由性在达到特定历史时期审美现代性高度的同时,也形成了这些高度之间的历史落差,导致审美现代性发生“民族独立”、“人的解放”两维度间侧重不同的内在逻辑转折。
中国现代美学起始于20世纪之初的五四时期,就社会性质而言,五四时期不是指一个具体的时点,“而应该指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从量变最后达到质变的一段重要时期”。[7]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反帝反封建”大旗,既要求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入侵,又要与代表封建生产关系的落后的旧文化做彻底的清算。当双重任务被推上历史舞台时,中国早期的美学思想家们清醒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入侵在客观上揭示的不争事实却是:放眼世界,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全方位落后状态。一方面,需要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方法“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技术和物质领域奋发图强改变落后现状;另一方面,思想文化启蒙的反封建任务尤为迫切重要,亟需唤醒“个性精神”、“自由权利”等人的现代意识作为现实活动的指导。由于他们认为个人自由、个性解放层面的启蒙是建立现代国家民族的前提和基础,故此选择以反封建的思想文化启蒙为突破口,以期用“民主”与“科学”两大现代工具来改造国人的思想与精神,解放长期以来在封建文化形态中被严重压抑和束缚的人性。总起来看,这个时期中国审美现代性与思想文化启蒙在本质意义和前进步调上是基本一致的。
随着中国知识分子内在思想素养的提升和国内外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爆发,中国人民在特定历史时期面临的最紧迫的现实任务发生变化,导致审美现代性逐渐发生内在的逻辑转折,从侧重呼唤“人的解放”维度逐步向侧重要求“民族独立”维度倾斜。导致侧重点发生转移的外在诱因是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的失败和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在国内,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鲜血淋漓的现实使因反封建而联合在一起的同盟军发生阵营分化:民族资产阶级和部分右翼小资产阶级投向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怀抱;小资产阶级中的激进派则坚定了革命思想,义无反顾地转向了同无产阶级携手前行的革命方向。在国外,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的困境下为改善本国经济形势、缓和社会矛盾,加紧了在国际市场上的互相争夺,进一步强化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压榨掠夺。在残酷的斗争现实面前,代表先进方向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革命力量自觉审视了以往思想文化启蒙失败的内在原因,牢固树立了在实践中用革命的斗争方式去改变中国社会现状、获得民族独立自强的坚定信念。
文艺思想领域里体现这一时期审美现代性逻辑转折的实例,当属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美学观点从1920年代初期的“分”到末期的“合”。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在1920年代中前期,因各自遵循“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的美学原则,曾在文艺实践和论争中产生过严重的分歧乃至对立。不过从两个文艺社团主要成员的身份和思想来看,其实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大致上都属于具有民主主义意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现状深怀不满,都希望通过自身在审美实践方面的努力来改变黑暗、落后的社会面貌……至少可以说,他们在“反对的对象”上是完全一致的。文学研究会的成员选择了思想文化启蒙的道路,试图通过文艺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社会进行无情的揭露和理性的批判,以此唤起民众现代意识的觉醒,最终达至“社会和人生因之改善,因之进步,而造成新的社会和新的人生”。[8](P75)同样是为了“人的解放”的美学目标,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对社会的不满和抗争比文学研究会更为激烈,更强调对社会的全盘否定,并认为文学研究会所走的思想文化启蒙之路实难成功。在意欲改造现实社会却找不到合适的路径后,他们只能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文艺内在审美特性的研究和个人文艺修养的完善上。但到了1920年代后期,思想理念的革新和国内外严峻的现实让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成员们把“为人生”和“为艺术”的方向都转换到“为革命”的方向上;无论是秉持思想文化启蒙的方式还是高扬艺术审美特性的方式,都转换为“为革命”的方式。他们美学思想的从“分”到“合”,显示出中国审美现代性进程的天平,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渐从追求“人的解放”一端向着谋求“民族独立”的另一端发生倾斜。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内在复杂性还表现在,两个实践维度侧重点之间的逻辑转折不可能一蹴而就。尽管这种转折的态势自1920年代中后期就已初现端倪,谋求民族独立的呐喊声越来越嘹亮,但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半数的时间里,仍有具体美学思想上的不同声音夹杂其间。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同人即为一例。“新月”同人固然也因对现实不满要求改变社会状况,不过他们的美学思想却始终固守于思想文化启蒙的僵化路径;当社会现实斗争方向发生转变,思想文化启蒙的道路事实上已经很难走通时,他们还依旧沉浸在用抽象的“人性论”和偏于形式主义的文艺方法去推行自己的一套美学观点。时间成了评判的最好标尺,“新月”众人最终从内部冰消瓦解、分道扬镳的结局恰好说明他们的美学观点没有贴近当时的社会性质、时代要求并随之转折的根本问题。还有一部分人的美学观点单从美学学科角度来看不乏一定的学理价值或独到之处,代表了美学发展的某一个方面,但可惜他们的纯粹理论探求和社会现实要求相去甚远,难以得到更大程度的赞同或反响。朱光潜和丰子恺就是这样的美学家,他们在自行开辟的美学合规律性研究田地中埋头耕耘,并未投身到为民族独立的美学合目的性斗争的潮头劈波斩浪。
1930年代后中日矛盾凸显,挽救民族国家危亡在此时成为中国社会首要的、最急迫的任务。由于此时中国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力量相对还比较弱小,不足以单独完成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现代性重任,在面对强大外敌侵略时,势必要结成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来共同奋斗。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再次在“反帝”这个共同目标下形成,在规模、范围、力量、影响等多个层面超越了以往任何一次。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是“在中国革命的曲线运动中,又来了一次四个阶级的统一战线,但是范围更放大了,上层阶级包括了很多统治者,中层阶级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层阶级包括了一切无产者,全国各阶层都成了盟员,坚决地反抗了日本帝国主义”。[9](P25)抗战时期革命文艺的主旨是为人民大众服务,即为工农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服务。“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9](P43)然而在中国长期封建统治的现实国情下,占革命阵营大多数的工农兵大众接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不高,他们的审美能力受此限制还停留在传统的古典和谐型美学观念上,无法立即接受高扬个性解放、民主自由等对立崇高型的现代美学观念。针对实际情况,毛泽东辩证地提出了解决文艺“普及”和“提高”的先后关系问题。“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广大的工农兵“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对他们而言是“雪中送炭”,“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普及和提高当然不能截然分开,“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9](P50~51)毛泽东提出的文艺“普及”,实质上就是对当时审美现代性进程中侧重“民族独立”维度的通俗化表述。
中国审美现代性的两个实践维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了最为急迫的革命任务,在两个维度无法兼顾的情况下,依据现实需要,确立了“民族独立”的维度全面优先,大力宣扬呼唤抗战的美学思想及文艺作品,而“人的解放”的维度在思想文化领域不得不被暂时搁置。两个维度侧重点的先后排序,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20世纪40年代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审美现代性似乎看起来比五四时期还要倒退的原因。社会文化中的审美现代性让位于社会斗争中的现实现代性,这不是美学意义上真正的倒退,而是在国家和民族危急存亡之际,用具体的、文化的审美现代性的暂时牺牲,换取了总体的、社会的审美现代性的成功。它正是“美的规律”总体一维性方向在社会实践中的充分体现。
三、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当代定位
纵观20世纪前期中国审美现代性进程,它因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要求不同,大致经历了从1920年代侧重思想文化启蒙的“人的解放”维度,逐渐转移到1940年代侧重呼唤全面抗战的“民族独立”维度的逻辑转折。两个实践维度之间侧重点的转移,宏观层面上始终体现出中国审美现代性总体进程上符合“美的规律”的“一维性”方向,微观层面上又充分表现了具体历史语境的“复杂性”事实。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准确把握这条线索,有助于我们科学地理解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内在规律与本质属性;更重要的是,能够为审美现代性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入发展、不断进步,始终保持先进性,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指明实践的前进方向。
审美现代性在当代中国要获得发展进步,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先进性指导,注重与当代社会阶段的具体要求相结合,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上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遗产,以实际行动反对审美实践中的教条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理论的凝练表述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当代中国坚持唯物史观要认清的是,它是研究人类全部历史的基本原则,是“研究历史的指南”,而绝不是“现成的公式”,[10](P688)离不开与当代中国这一具体历史阶段的有机结合。如果把西方现代性概念、思想运用于中国境地,却不加科学理解而是囫囵吞枣、机械照搬和盲目套用,必定会导致陷入教条主义泥潭的恶果。历史已经证明,当代中国必须坚持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前进之路。此外,审美现代性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也要求我们珍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不能因一味追求“现代性”而对传统文化或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审美实践活动持全盘否定的文化虚无主义立场,人为地割裂中华民族审美文化的历史延续。惟其如此,代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形态的审美现代性,方能在历史的继承中不断汲取养分,以追求创新、积极奋进的姿态迎接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各项机遇和挑战。
审美现代性在当代中国要获得发展进步,必须始终坚持“美的规律”的最高准则,最大限度地把握客观法则,伸张人的主体自由性,着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塑造当代人的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等现代特质不懈努力。中国现代性进程中需要解决的“民族独立”和“人的解放”两大基本问题,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特殊原因先后排序有所侧重,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符合时代制高点的要求,值得肯定。但不能因强调了民族独立的问题并连带在人的解放问题上暂时边缘化,从此可以永远边缘化人的解放问题。换句话说,中国现代性进程的第二个实践维度可以暂时搁置,但不能永远搁置。如果第二个维度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将始终不能被认为已经完成。在既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个维度的前行曾一度经历曲折,走了不少弯路。但令人欣慰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1990年代起,这一问题已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中国要全面实现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必须大力倡扬科学思想与理性精神、主体观念与启蒙意识、真理尺度与价值理想的精神维度。”[11]中国审美现代性进程在当代中国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实践成就的事实亦表明,第二个维度的问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予以解决。这既是当代中国社会对审美现代性的内在规定,也是宏观历史上“美的规律”在当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审美现代性在当代中国要获得发展进步,必须始终坚持审美文化的先进性方向,促进社会生产力的科学发展,推动当代人自身建设的渐趋完善,为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健康向上、积极奋进的动力与能量。在人类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具有时代先进性的审美文化往往不仅创造出了多姿多彩的美的物质世界,而且同时创造出了具有先进审美鉴赏力和创造力的人本身。在当代中国,作为代表了当下社会绝大多数人最根本利益的审美文化,审美现代性的先进性特质无疑也体现在它既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又对人自身的完善充实产生决定性影响。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中物质和审美两方面并行发展、奋起直追的特殊历史境况,决定着社会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应该互相促进、互为支持,形成良性的循环互动,共同稳步推进当代中国社会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西方社会现代性进程中曾走过的弯路已经予以我们警示,如果不能在现代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之间取得和谐互利的发展形态,不能始终致力于人的自身完善,最终将导致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人的精神追求和理想愿望将失去赖以栖身的美好家园。这在本质上正是与审美现代性在当代中国的先进性定位背道而驰的。
注释:
①关于“美的规律”部分的详细阐述,可参看陈伟:《文艺美学的理论与历史》,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1] 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C].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2] 周宪.文化现代性读本[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 陈伟.文艺美学的理论与历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4] 陈伟,桂强.现代性视野中的“红色歌曲”与“黄色歌曲”之审视[J].文艺研究,2011,(3).
[5] 陈伟.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 陈伟.五四时期的新美学精神和新艺术形象[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
[8] 耿济之.《前夜》序[A].贾植芳,等.文学研究会资料(上)[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9] 毛泽东.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邵志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后现代性与价值反思[J].广西社会科学,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