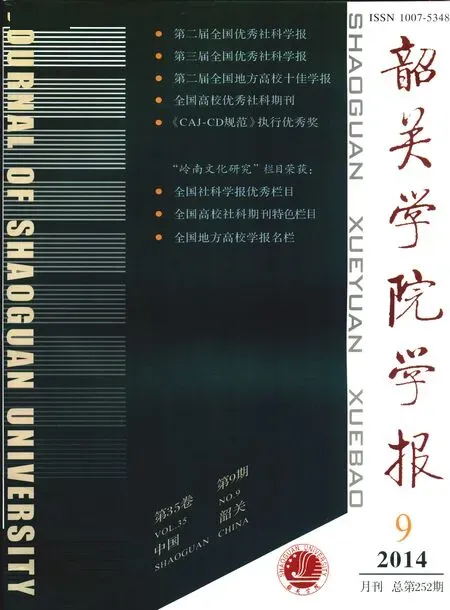慧能与神秀关系探微
朱正国
(云浮市地方志办公室,广东云浮527300)
慧能与神秀关系探微
朱正国
(云浮市地方志办公室,广东云浮527300)
慧能与神秀的关系,从呈心偈与得法偈故事本身来看漏洞颇多,而且不同历史文献的记载也有矛盾。有关神秀与慧能包括“比偈”的故事,是禅宗地位得到提高和内部派别形成以后,内部派系为争夺正统地位而虚构的;或是神会借批神秀来发动一场禅宗革命而编撰的故事。慧能获得六祖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与弘忍的安排无关。
慧能;神秀;六祖;得法偈
在慧能生平中,避不开的一个问题是慧能与神秀的关系,这一千古之谜,关键在于对广为流传的神秀的呈心偈和慧能的得法偈的评判。敦煌本《坛经》神秀偈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慧能的法偈,一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二是“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后来流行的却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本文拟结合前后历史关系,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分析。
一、“呈心偈”-“得法偈”的描写太过细腻反露破绽
《坛经》各版本都记有神秀的呈心偈和慧能的得法偈,而且两人呈偈的过程和心理的细节都刻画得非常生动。如神秀呈偈的情况是:大家都不呈偈,都认为由神秀上座呈偈和得祖位是自然的事;但神秀好多天都处在呈与不呈的矛盾心理中,既怕呈偈被误为谋求祖位,又怕不呈不知学道成就如何,以至“数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拟呈不得。前后经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最后只是偷偷地“书偈于南廊壁间”,之后又是“坐卧不安,直至五更”。
实际上,这种过细的描述反而弄巧成拙,露出了破绽。因为禅之本意,不立文字,不依言语,以心为印,以心传心。《坛经》对此也有说明,如五祖有一句对慧能说的话:“昔达摩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由于禅宗教学这个特点,就产生了如下几点疑问:
第一,五祖要选传人完全不必采取像举办一场科举考试那样让弟子们比偈,更简单也更有效的办法是五祖在日常传法时自然地提出问题,让弟子们回答,再通过问答互动来考察发现可以付法之人。禅宗传统上就是这样做的。《神会语录》提到弘忍传法慧能也是如此:“忍大师于众中寻觅,至确上见,共语,见知真了见性,遂至夜间,密唤来房内,三日三夜共语,了知证如来知见,更无疑滞,既付嘱已。”
第二,呈偈本就是师徒间秘密的事,神秀所呈之偈大不了悟道不深,如果神秀不想公开自己所呈之偈,五祖一定会随其愿。《传法宝纪》说:“及忍、如、大通之世,则法门大启,根机不择,齐速念佛名,令净心。密来自呈,当理与法。犹递为秘重,曾不昌言。”“念佛名”“令净心”是其所传,弟子修持而有所得,就“密来自呈”,如师认为与正理相应,就付“与法”。学者的密呈,师傅的密付,非局外人所知的。所以,神秀完全用不着左右为难“数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拟呈不得。前后经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
第三,即使神秀悄悄地“书偈于南廊壁间”,其他人又怎么对呈偈的过程知道得这么详细?
第四,按故事的描写,一开始,神秀并不想谋求祖位,在呈与不呈的犹豫中“书偈于南廊壁间”。神秀偈之后传开,慧能得知而问,一童子告之“大师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传付衣法,令门人作偈来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为第六祖”后,也请人书一偈于壁,这样反而显得慧能欲谋祖位。如此一来,就真的演变成一场争夺六祖位的竞争了。另外,比偈一事慧能需要童子告之,也说明慧能还不是正式弟子,但慧能却要书偈。这就不是抬高慧能,而是贬低慧能了。实际上,当时,不可能有“第六祖”或“祖位”这样的观念,这只能理解为是后来添加的。
第五,从五祖来讲,竟然按排一场争夺六祖位的比偈赛,这确实比较符合世俗的风格,显得比较公平又有传奇色彩,编出的故事也算精彩,但于禅门却太不合情理。更重要的是,由于最后的结果是弘忍不得不安排年轻而资历浅且尚未正式出家但悟道深的慧能南逃,则显得五祖缺乏谋略和智慧,这决非一代大师所为。
二、《曹溪大师别传》等没有“呈心偈”-“得法偈”的故事
《曹溪大师传》《神会语录》,还有王维的《六祖禅师碑铭》都没有呈心偈-得法偈的故事。从慧能的成长和禅宗发展史的角度看,得法偈确实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故事。长期以来,人们因此而津津乐道。如果说《六祖禅师碑铭》因文字简略的需要,在慧能生平介绍中不讲这个故事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神会语录》《曹溪大师别传》,特别是后者是不可能不讲的。然而,《神会语录》中没有这个故事,反而是说弘忍平时在与慧能的对话和对他的行为观察中发现慧能不寻常,然后与其讨论佛性义,最后认可慧能而付法的,这显得非常合情合理。《曹溪大师传》与此有些相似,是从回顾慧能初见弘忍时“岭南新州人佛性,与和上佛性有何差别”的回答开始,进而讨论“佛性非偏”,“一切众生皆同”的“佛性义”,也显得顺理成章。最后慧能仍表现出谦虚:“能是南人,不堪传授佛性,此间大有龙象。”而忍大师认为慧能是象王:“此虽多龙象,吾深浅皆知,犹兔与马,唯付嘱象王耳。”于是付法与慧能并送其南归。《曹溪大师传》《神会语录》和《六祖禅师碑铭》都是早期可信史料,既然都不讲这个故事,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这个故事是后来虚构出来的。敦煌本《坛经》将这个故事编出来后,后期版本和许多文献都将这个故事继承下来,而且故事越来越完善,由敦煌本的两首得法偈变成一首,最后修改定型为朗朗上口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适应了大众的口味。
三、历史没有留给“呈心偈”-“得法偈”演绎的时间
慧能24岁去黄梅见五祖的矛盾之处甚多,可能性很小。慧能应该是母亲去世以后,在他30岁那年北上黄梅,这样,他就没有机会与神秀相见,也就不存在比偈一事了。其中,主要有这样几点:第一,王维《碑铭》中有“临终,遂密授以祖师袈裟,而谓之曰:‘物忌独贤,人恶出己。吾且死矣,汝其行乎。’”之语。同时,《碑铭》又明言慧能隐居南海“积十六载”,则慧能应于龙朔元年至黄梅,这就产生了矛盾。由于《碑铭》可能是慧能去世后的最早材料,为王维应神会之请而作。故后世诸书皆本于王维《碑铭》,甚至同时说慧能受五祖临终付嘱,又隐居南海“积十六载”等,不觉得时间上有矛盾。多种《坛经》版本就是如此。第二,慧能是个孝子,24岁抛开老母,自己一人北上黄梅的可能性不大,况且从此再无音讯,南归十六载也不回新州(离怀集、四会很近),弃老母不闻不问,不合常理。第三,历代祖师正常情况下都是临终咐法。如果慧能龙朔年间北上黄梅,时五祖60岁左右,主持东山法门也仅10年时间,此时传位与慧能可能性不大。第四,如果慧能24岁时见五祖,五祖看好他,则五祖应该像其他祖师那样,将慧能留在身边继续学习,让他逐步树立权威,再找个适当的时候传授衣钵,而不必秘密传法慧能后,又让其秘密南归和隐居十余年。慧能只有24岁,且学法仅8个月,此时印可慧能没有问题,传位慧能则可能性小。第四,慧能孤儿寡母,老母在家没人照顾,《坛经》有赠银十两安排母亲生活的说法,但却没有下文。如果说慧能是龙朔年间前往黄梅约1年后先回家乡照顾母亲,为何家乡对此没有任何记载或传说?所以,可能性较大的是慧能24岁时并未离家往黄梅,而是一直照顾到母亲去世后才前去黄梅的。此时,慧能已30岁,其母60岁左右,已去世的可能性非常大。综上所述,应该认为,慧能30后离开新州,咸亨年间往东山见五祖的可能性比较大。也就是说,神秀离开东山寺多年后慧能才上东山寺。慧能与神秀在黄梅根本就没有见面的时间,也就不可以发生比偈的故事了。
四、“呈心偈”-“得法偈”文理不顺
陈寅恪先生提出:“古今读此传法偈者众矣,似皆未甚注意二事:一、此偈之譬喻不适当;二、此偈之意义未完备。”“印度禅学,其观身之法,往往比人身于芭蕉等易于解剥之植物,以说明阴蕴俱空,肉体可厌之意。”[1]而此偈中“菩提本无树”的菩提树则是“永久坚牢之宝树,决不能取以比譬变灭无常之肉身”,此偈中之比喻,是“致反乎重心神而轻肉体之教义”之不适当之譬喻,存在着逻辑错误。另外就是“身之一方面,仅言及譬喻,无论其取譬不伦,即使比拟适当,亦缺少继续下文,是仅得文意之一半。”其原因,他认为是六祖慧能大师并北宗神秀“袭用前人之旧文,集合为一偈,而作者艺术未精,空疏不学,遂令传心之语,成为半通之文”[2]。
如果从文理上来讲,不仅呈心偈-得法偈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菩提本无树”和“明镜亦非台”这两句也如此。菩提是一种树,“明镜”与“台”则是一种镜、台的组合,“明镜”当然不是“台”!要否定就应该是“明镜亦非镜”。这说明,“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两句产生的原因就在于要否定所谓神秀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所以,敦煌本《坛经》才出现了另一种否定形式:“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不过,后一种否定形式仍然是着相的。而最终流传下来的是这四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因为这四句否定得最彻底,又更加符合禅的风格——不立文字——尽管它文理更加不通,但否定意义大立其中!这说明,得法偈有一个演变过程,并且作为一个编写出来的“对立故事”,要适应宗派斗争的需要。
五、“呈心偈”-“得法偈”与《坛经》不协调
实际上,呈心偈-得法偈或许不能完全从文理上去分析,要从禅理上分析。如果完全符合文理,也就没有禅了。所以,陈寅恪先生从文上来批评可能意义不大。净慧法师说得好[3],神秀的呈心偈是“根据戒、定、慧的内容而创作的。以戒治身,身得清净,故有‘身是菩提树’一句,诠戒学也;以定治心,心得明净,故有‘心如明镜台’一句,诠定学也;持戒修定,均需以慧观照,才能日新又新,故有‘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二句,诠慧学也”。“神秀偈四个肯定句型,慧能偈反其意而用之,来了四个否定句型,他运用‘翻案法’,坐断有无,一扫当时佛教界‘分别名相’、‘入海算沙’的积习,开一代清新活泼、解脱自在的禅风之先河。”“所谓‘菩提本无树’者,‘无相为体’也;‘明镜亦非台’者,‘无念为宗’也;‘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者,‘无住为本’也。而这三者实际上也就是他对戒、定、慧三学的另一表述形式。”“神秀偈的重点是‘时时勤拂拭’,在一般层次上解决了佛教的理论与实践如何统一的问题,即所谓渐契也;而慧能偈的重点则是‘本来无一物’,有如高屋建瓴,在更高层次上解决了佛教的理论与实践如何统一的问题,即所谓顿悟也。”或许,禅理恰恰不可从文理去分析。
但是,需进一步指出的是,慧能的得法偈在禅理上仍与《坛经》存在诸多的内在矛盾。以“明镜”、“日月”喻佛性、本心是佛教的传统。《楞伽师资记》的《求那跋陀罗传》之中有这样一段话:“大道本来广遍,圆净本有,不从因得。如似浮云底日光,云雾灭尽,日光自现……亦如磨铜镜,镜面上尘落尽,镜自明净。”这里的“大道”、“日光”和“铜镜”就指佛性,借磨镜面上的尘垢来比喻断除妄念烦恼的修行。神秀的呈心偈就是如此。虽然从慧能的得法偈上来看,是否定了神秀的呈心偈,但《坛经》上的一些内容却又肯定了神秀呈心偈的思想。如《坛经》云:“如是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云。”还说:“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于外著境,被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识,闻真正法,自除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现,见性之人,亦复如是,此名清净法身佛。”慧能一方面说“自性”“常明”;一方面又说只为“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能明”,然后要修“无念行”,去掉“盖覆”在“自性”上的“妄念浮云”,那么就“内外明彻”。这里所讲的“自性”和去掉“妄念浮云”的关系,完全符合神秀的禅学见解:“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4]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坛经》没有明言“时时勤拂拭”修行,说来说去,就变成了“自性”拂去自己散发出来而又“盖覆”在自己上面的“浮云”!而且,在不知不觉中引入两个外因,一是“忽遇风吹云散”的外物偶然力,二是“若遇善知识”开真法的师资偶然力。转了一圈,慧能好像在自己批驳自己,自己否定自己!
其一,从禅的实践来讲,呈心偈与得法偈是有内在联系的,慧能得法偈是悟空境界,它表现为一种否定。然而,这种否定却很难一开头就直接否定,因为否定必然是针对某种“有”的否定,所以,慧能要讲清这种空性的时候,一定要借助“自性”“妄念浮云”以及“风吹”“善知识”这种类似“镜”“尘”、类似“勤拂拭”的“有”概念。林有能先生说得好:“慧能偈是在神秀偈的启发下而成的……慧能是站在神秀的肩膀上跃起而最后成佛的。”[5]在《坛经》的有关论述中,如果没有类似神秀偈那样的“有”作为基础,就很难把“悟空”讲清楚。否则,慧能就只好自己否定自己了。这一点,我们还能从诸多后世禅师悟道得法的故事中看出,它反映了禅悟认识发展的阶段性。其二,从深层次上来讲,所谓呈心偈与得法偈的差别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大,这种差别其实本身就是一种“相”。“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除了反映“执有”境界之外,不也从中可以体悟到佛之金刚、佛之真如境界吗?若如此,“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不就成了觉悟之后的保持状态吗?实际上,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第一部重要经典著作《佛说四十二章经》就以“磨镜”比喻修行见性,而且有顿悟义:“净心守志,可会至道。譬如磨镜,垢去明存,当得宿命。”《修心要论》中说:“譬如磨镜,尘尽自然见性。”《楞严经》卷五曰:“又于自心现大圆镜,内放十种微妙宝光,流灌十方。尽虚空际,诸幢王刹,来入镜内,涉入我身,身同虚空,不相妨碍。”这里是以镜喻佛性圆满自足。因此,神秀偈是“磨镜”见性后的保持清静心的状态,即“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是比“悟空”更高的层次,是一种融“有”与融“空”的妙有大智慧。当然,这只能是得道之人才能体味出来的,正所谓“看山还是山”。从禅宗史看,神秀早已是得道高僧,如果真有神秀偈,而慧能如果真悟道,是不会作一个“得法偈”来否定神秀偈的。如果慧能作了这样的偈,只能说明他还处在大多数人的水平,还处在悟空理的阶段。其三,呈心偈-得法偈的故事从历史上来看,应该是虚构的,但从禅理上来看,则可以说它是真实的。因为,任何悟道之人,无非都是在有无中道之中,正如《坛经》三十六对法所教导的那样,著有以空破,著空以有破。凡是悟道之人,都会经历故事中所体现的认识变化。由于偈语体现了常人都可以懂得的从执有到悟空的认识变化,或许正是该故事能为人津津乐道并被广泛传诵的秘密!
六、慧能南逃中的矛盾之处
《坛经》说慧能得弘忍密传后,告之“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于是,慧能南归有逃亡性质。敦煌本《坛经》是:“不知向后有数百人来,欲拟捉慧能,夺衣法。来至半路,尽总却回。唯有一僧,姓陈名惠顺,先是三品将军,性行粗恶,直至岭上,来趁把著,慧能即还法衣,又不肯取:‘我故远来求法,不要其衣。’能于岭上,便传法惠顺。惠顺得闻,言下心开。能使惠顺即却向北化人。”而宗宝本《坛经》与此有很大不同,为首者是惠明,且“为众人先,趁及于能”。惠明是欲夺衣而“提掇不动”而不是“又不肯取”。众人则是“明回至岭下,谓趁众曰:‘向陟崔嵬,竟无踪迹,当别道寻之’。趁众咸以为然”而回的。不是“来至半路,尽总却回”。这里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有几百个和尚来追赶,那么在东山寺占的比例太高,这么一大群人一路追赶恐怕连食宿问题都难解决。再说,在唐时,跨不同州县界都要有通关文书,而几百个和尚要一起过关追赶,也是很难想像。可能《坛经》编者意识到这一问题,于是让追赶者走了二个多月,却同时也让慧能逃了二个多月!然后,敦煌本的说法则是不知为什么追到半路又回去了,并突出一主要人物惠明,此人过去是皇室子弟,曾做过四品将军,大概有些关系,所以算是代表了这次追杀行为了。按《坛经》,慧能北上黄梅时从新州出发是“不经三十余日”,就到了黄梅。南逃时,却是“两月中间”,才至大庾岭。如果粗略计算一下,那么,慧能北上的速度是每天三十多公里,而南逃的速度不到这一半。自然不合情理。如果慧能尊师“汝须速去”的嘱咐,就不该如此慢行,且慧能比追他的人早三天南行,只要“速去”,决不至于在南岭就被后来的和尚追上的。这只有一种解释,慧能南归时是走走停停,一路随缘传法而归,并不存在有人追杀的情况。作者曾与一位《坛经》研究者论及此事,这位研究者说,慧能南归时一路传法,后来南宗在江西大兴,与此有关。
还有另一问题,慧能南归前曾问师:“向甚处去?”祖云:“逢怀则止,遇会则藏。”人们将此看作慧能南逃后隐居四会、怀集一带的理由。但这个说法也成问题。第一,五祖不一定知道有四会、怀集这两个地方。第二,这种说法太神奇,或者说充满神秘迷信色彩,不可信。因此,有人认为这是后人附会上去的“悬记”。第三,这种说法低估了禅师之间的悟道禅机对接的水平,或者说掩盖了师徒之间“道在言外”的教学模式。实际上,五祖与慧能的对话都是充满禅机的,或应作一语双关的理解。正如程东、程辽所说,五祖是借机说禅:“‘怀’者心也,‘止’者是也,‘逢怀则止’,意为悟心即是。‘会’者遇也,‘藏’者归也,‘遇会则藏’,意为对境即归。所以前句指悟心为是,不可更为,如如不动;后句指遇境则归,自返本心,不取于相。因此弘忍的这两句话,是借一句指事落境的俗语,来展示《金刚经》中所说的‘如如不动,不取于相’的境界”;“有人以为弘忍说的这句话是一句‘悬记’……于是就成了预言,故为世人崇拜,以为神秘。”[6]这种说法也有道理。
另外,我们还可考察一下唐时怀会一带的实际情况。当时怀会一带是繁华的南北向重要商道,海运物资经珠江口溯绥江直上怀集,由此可北上江南和中原,西去广西。绥江沿岸一带还发现只有海洋文化才有的妈祖庙,说明古代这一带与海运相通的水运相当发达。如果慧能真是“隐居”在这样发达的商道上,那只能有一种解释,慧能南归后一直在民间传法,这其间,由于他没有正式僧人身份,游离在合法与非法之间,难免有需要躲避官府的管制,而其他派教徒也可能趁机迫害。但迫害来自同门的可能性很小,更不可能是神秀所指使,而可能与历代祖师相似,仍然是禅宗之外的正统教派。因为,唐代真正尊佛(在道教之前),是武则天时代开始的,而她扶持的主要是华严宗,宗禅受到重视要到神秀进京以后。
其实,从《坛经》看,慧能主张在家修行,他说:“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他这种僧俗不二思想非常强烈:“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当有人问在家如何修行时,他还说:“吾与大众,作《无相颂》,但依此修,常与吾同处无别;若不作此修,剃发出家,于道何益?颂曰: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7]我认为,在未获得出家合法资格证度牒前,慧能很可能像维摩诘居士一样,一直在探索和实践一种居士佛教,他在考虑以世俗居士的身份、以入世的方式来弘发佛法,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人间佛教”。或者反过来说,这一段民间弘法时期的经历,对于慧能居士佛教精神、人间佛教精神和僧俗不二思想的形成,进而佛教的平贫化、生活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不过,他可能最终发现,这种没有正式身份的弘法方式仍然难以得到正式制度的认可,到了676年,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正式剃度出家。
七、与禅宗发展的态势不相符合
由于唐高宗特别是武则天时期,佛教的地位已超过道教,但是,佛教主流发展还是华严宗和天台宗等宗派。虽然禅宗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总体来讲,它仍属于较弱势的宗派。在弘忍的时代,东山法门尚未在全国传播开来,东山法门内部争夺正统的斗争更不可能展开,也就不可能出现追杀五祖指定的继承人这种过分激烈的形式。
弘忍作为道信的法嗣,按中国传统的孝道在双峰山为道信守孝三年后,一是因为原道场不够使用,二是可能有些同门师兄弟不服管束,所以,他在附近的东山新建道场。当时,弘忍门下集聚了众多人才,既有失意流浪的知识分子、贵族,也有下层流民。《传法宝纪》说:“及忍、如、大通之世,则法门大启,根机不择,齐速念佛名,令净心。密来自呈,当理与法。犹递为秘重,曾不昌言。”据《楞伽师资记》记载,弘忍曾对弟子玄赜说:“吾一生教人无数,好者并亡;后传吾道者,只可十耳。”这十人是:神秀、智诜、刘主簿、惠藏、玄约、老安、法如、慧能、智德、义方。弘忍认为他们都可“传吾道”,为人师,能将禅法发扬光大,可究竟有没有选谁作为继承人,这就不得而知了。
假如弘忍当初考虑过要选一个接班人,我认为属于慧能的可能性反而较小。弘忍教人是“根机不择”,而且弟子们学习以后是“密来自呈”,如果“当理”就传之以法印可,毕业后就可以离开,结果是“好者并亡”。弘忍为什么会这样做呢?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是他采取的一种传法战略。我们知道,道信之前,有很多禅者,但不可能有禅宗。从达摩开始,禅者多受到正统佛教,特别是律师的排挤,达摩、惠可、僧璨都曾遭受迫害,他们所修之禅甚至被认为是邪教。这些可能正是禅师趋向山林的重要原因,这些禅者想找到合意的弟子都不容易,传人不多,甚至是秘密传授,僧璨和道信都是“不知何许人”,他们之间是否有师承关系也不太可考。但不管怎样,到道信时,禅者的日子应该是相对好过一些了,这主要与道信的创新有关。唐初时流民是一个大问题,道信建立了稳固的道场,而且一改游乞的生活方式而成为农禅并作的自给自足者,这种经济模式的成功奠定了建立禅宗宗派的基础。所以,道信是一个有创新的宗教改革家和寺院管理家,正是他初步创立了中国禅。但道信对弟子的培养不够重视,真正的得法弟子不多,更重要的是,道信对禅宗的战略发展缺乏思考。这些是由弘忍来完成的。
对此,我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以东山为基地向全国传播禅宗,这是弘忍的一个战略布局。正是从这一战略布局出发,一有得法弟子出师,弘忍就会根据情况将之派往一方去经受历练,在因缘成熟时就出山开法。因此,弘忍对每一位得法弟子可能都有密嘱。在弘忍的得法弟子中,智诜出师是最早的,五祖尚未去世就开始在资州开法了。之后,先后有慧能、法如、神秀等在各地开法。弘忍在世时,禅宗十大弟子,以湖北黄梅为基地,形成了向东西南北扩展分布到全国的势态(参见玄赜《楞伽人法志》记弘忍语)。如,慧能、印宗在广东,神秀在湖北、长安、洛阳,玄约、道俊、禅、通、法、显等在湖北,智诜、宣什在四川,惠藏在陕西,老安在河南,法如在山西,法持、智德、昙光、觉等在江苏,义方、僧达在浙江,法照在安徽,慧明在江西,这些著名的弟子,把“东山法门”广播到全国,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是抛弃一代一人的旧传统,采取多头并弘的方式。从历史上看,一人一代,是不可能将一个宗派发扬光大的,弘忍“根机不择”,法门大开招收弟子,说明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由于道信是第一个变游化而隐居并发展到开创丛林、聚徒弘教的禅师,他不仅为禅宗创宗和中国化奠定了基础,而且他也感受到很难采用一代一人的方式来付法。《续僧传》卷20(附编)《道信传》说:“(道信)……临终,语弟子弘忍,可为吾造塔。”“众人曰:和尚可不付嘱耶?曰:生来付嘱不少。”《传法宝纪》载:“永徽二年八月,命弟子山侧造龛。门人知将化毕,遂谈究锋起,争希法嗣。及问将传付;信喟然久之曰:弘忍差可耳!因诫嘱,再明旨赜。”道宣(596-667),是与僧粲同时的著名律僧,道宣所传闻的,凡修持得悟的,都可说有过付嘱,反映的是“分头并弘”。而杜胐所传,大家都争着继承祖位,道信勉强选了弘忍,这是一代一人的付嘱制。历史上就有一宗迷案,即牛头宗认为其祖师法融是四祖道信的付法弟子,而其他人多将之看作禅宗的“旁出法系”。但不可否认的是,牛头禅当年极富思想活力,它主张的“虚心为道本”“无心合道”与“无情有性”“无情成佛”等牛头禅法,已经真正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玄学”带进了禅宗,特别是对石头一系的影响极大。而禅宗的本质便是玄学化了的佛教,所以人们常称法融是“东夏之达摩”。
由于弘忍采取多头并弘的方式,“好者并亡”,有力地促进了东山法门的传播。他在世的时候,其知名弟子就已布局到了全国的主要地方。留在身边造塔弟子有二:一个是跟随他时间最长的法如,一个是晚年从师的玄赜。弘忍去世时(674),他最有名的五大弟子——神秀(605-706)、道安(584-709)、智诜(639-718)、慧能(638-713)和法如(638-689),只有法如还在他的身边。据689年立《唐中岳沙门释法如行状》所载,法如658年投弘忍为师,专心学习“一行三昧”。可见,法如应该与弘忍的关系比较特殊,否则不会一直留在身边十六年之久。从后来看,法如北上佛教重镇,即传说初祖达摩面壁修禅十年的嵩山,并做了少林寺的主持,也说明弘忍对法如是寄予厚望的。法如虽开法仅三年,于689年早逝,又自称没有接法的弟子,但名振一时,被称为“定门之首”。如果真有一代一人的咐嘱制度的话,六祖之位传给法如的可能性最大。《唐中岳沙门释法如行状》提出了中国禅宗史上第一个传承系列表,即禅宗在印度的传承为:如来-阿难-末田地-舍那婆斯……在中国的传承是:菩提达摩-惠可-僧粲-道信-弘忍-法如。当时,弘忍的弟子,包括神秀和慧能都还在世,没有表示反对的。法如弟子杜朏《传法宝记》也沿用此说,并说法如传法给神秀,这样六代就有法如跟神秀两位,或者说兄终弟及,也可以说神秀是七祖了。
严格来讲,这里讲的还是师承关系,还不是后来意义上的第几代祖师的概念。禅师们各讲各的师承关系,弟子们向多个是师兄弟或不是师兄弟的师傅学习,师徒关系是开放的,并无矛盾,但后来要按中国文化宗派思想中的一代一人来争正统,就产生矛盾了,就有了第几代祖师的概念了。
玄赜曾参与玄奘弘福寺成立译场翻译之业,曾师事被后世尊为中国律宗初祖的道宣,咸亨元年(670)至双峰山,入五祖弘忍门下。玄赜撰《楞伽人法志》,虽今不存,但其弟子净觉(先后师事过神秀、玄赜二禅师)在此基础上撰述名著《楞伽师资记》。该书被发现于敦煌,为研究禅宗史极珍贵之资料。很可能,弘忍是将著述和理论传承的责任更多的托付了学有专长的玄赜了。
因此,从禅门传法态势看,一代一祖师的付法制很难成立,即使成立,六祖位传给慧能的可能性也不大。相反,慧能作为一方面人物在南方传法却可能是五祖的密嘱,后来慧能不应诏北上也应与此有关。
八、“呈心偈”-“得法偈”是禅宗地位提高后内部争法统虚构的故事
如果说呈心偈-得法偈是虚构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是如何虚构出来的呢?
由于很多人都认为有一个《坛经》古本,这个古本是法海记录的,法海于730年去世,而南宗的提法至少是745年以后的事,所以,法海的《坛经》古本是不会有南宗的。而现在发现的,被认为最早的版本敦煌本,其书名中有“南宗”二字,故其成书时间也不会早于745年,不是古本《坛经》。
神会语录中,从达摩到慧能一代代都是依《金刚金》传法,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弘忍与慧能师徒讨论佛性义来传法是比较可信的。同时,神会语录中也没有提到呈心偈和得法偈一事,只是说“忍大师于众中寻觅,至确上见,共语,见知真了见性,遂至夜间,密唤来房内,三日三夜共语,了知证如来知见,更无疑滞,既付嘱已,便谓曰:汝缘在岭南,即须急去,众生知见,必是害汝。”而《曹溪大师传》讲的也是弘忍与慧能讨论佛性。据《楞伽师资记》记载,弘忍曾对弟子玄赜说:“吾一生教人无数,好者并亡;后传吾道者,只可十耳。”这十人是:神秀、智诜、刘主簿、惠藏、玄约、老安、法如、慧能、智德、义方。弘忍认为他们都可“传吾道”,为人师,能将禅法发扬光大。
弘忍门下集聚了众多人才,通过法如、神秀等人的努力,特别是久视元年(700)武后派使者迎请神秀入东都洛阳,神秀被尊为“帝师”。神秀后,其师兄弟道安、玄赜又先后被召去补充“两京法主”的地位,后来又有神秀的弟子。由于受到朝廷的崇信,以神秀为代表人物的所谓北宗禅(当时神秀还是自称东山法门,本门都称楞伽师,而不是禅宗,更不可能有北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盛行于以东西两京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一方面,整个禅宗有了较大发展,真正成为佛教宗派,在佛教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东山法门弟子不仅分布全国,所开辟的禅宗法门也都有了各自的发展,差异因此有所显示。于是,谁能代表禅宗,谁是禅宗正统的问题才突现出来,成为禅宗宗派进一步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而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观念,每一代只有一位禅师才是正传,才能继承正统地位的话,就必然出现内部派别之争了。其实,北宗、南宗、渐派、顿派这些概念都是争正统的产物,它们之间虽有一定差异,但仍然属于佛教内部的差异,然而在正统之争中这种差异被放大了。实际上,在弘忍及其弟子们的观念中,禅宗派别之争的意识并不明显。正如慧能所说“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
先看神秀一系,他们突出以《楞伽》传宗为根本旨趣。玄赜和净觉,都自称是楞伽师,而不以禅者自居。净觉《楞伽师资记》,常被人称之为列祖作传,这多少带有后人强加的意识。因为书中并无一祖二祖等称呼,而均称其为大师,并且按传承顺序来介绍这些大师,是代代相承,一代可以有数人。例如,第一,宋朝求那跋陀罗三藏。第二,魏朝三藏法师菩提达摩,承求那跋陀罗三藏后……第六,唐朝蕲州双峰山幽居寺大师,讳弘忍,承信禅师后。第七,唐朝荆州玉泉寺大师,讳秀;安州寿山寺大师讳赜;洛州嵩山会善寺大师,讳安。此三大师,前后为三主国师也,俱承忍禅师后(共有10人)。第八,唐朝洛州嵩高山普寂禅师,嵩山敬贤禅师,长安兰山义福禅师,蓝田玉山惠福禅师,俱承大通和上后。最后说,自宋朝以来,大德禅师,代代相承。起自宋求那跋陀罗三藏,历代传灯。至于唐朝总八代,得道获果,有二十四人。
再看法如一系,则以慧远的《禅经序》为传法根据,强调的是以意密传,所以从来不提有《楞伽》传宗这件事。《唐中岳沙门释法如行状》提出了中国禅宗史上第一个传承系列表,即说印度的传法世系是佛传阿难,阿难传末田地,末田地传舍那婆斯。此后菩提达摩来华传授此法,是“入魏传可,可传粲,粲传信,信传忍,忍传如”。严格地说,法如一系仍是讲述师承关系,而不能简单地说是在讲一代一祖师的正统继承关系。
又过了几十年,慧能一辈都不在世了,慧能一系的弟子神会由于不满足于禅宗的多头并弘的“混乱”局面,特别是不满足于“南宗”不显的地位,才真正挑起了谁是一代一人的正统祖位之争。开元二十年神会在滑台(今河南滑台县)大云寺设无遮大会与北宗崇运法师论辩南北宗邪正是非,大力宣扬慧能南宗为禅宗正统。声称“唯传顿教法,出世破邪宗”。神会认为:“菩提达摩南宗一门,天下更无人解。若有解者,我终不说。今日说者,为天下学道者辨其是非,为天下学道者定其旨见。”所以,他要“弘扬大乘,建立正法,令一切众生知闻,岂惜身命”?远师问:唐国菩提达摩既称其始,菩提达摩西国复承谁后?又经几代?神会根据《禅经序》回答西国传至菩提达摩为第八代。唐国惠可禅师承菩提达摩后,到慧能共传六代。故自如来付西国与唐国,总经有一十三代。远师又问:“西国亦传衣不”?神会说:“西国不传衣”。至于西国为何不传衣,神会的回答是:“西国多是得圣果者,心无狡诈,唯传心契。汉地多是凡夫,苟求名利,是非相杂,所以传衣示其宗旨。”神会还鲜明地指出:“秀禅师在日,指第六代传法袈裟在韶州,口不自称为第六代。今普寂禅师自称第七代,妄竖和尚为第六代,所以不许。”显然,在神会眼里,才真正是一代只传一人,是为正统。但他的一些回答,如西国八代传承,以及西国为何不传衣的解释,都难以让人信服,只能看作是临时应付之辞,并让人感到他真是有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九、正统与宗教革命
如果说抬高慧能只是争法统的话,则仍然有些片面。实际上,神会也是力图通过发动一场佛教或禅法的革命来争法统。从《坛经》看,它所批判的禅法是:迷人著法相,执一行三昧,真心坐不动,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若如是,此法同无情,却是障道因缘……迷人自身不动,开口即说人是非,与道违背。看心、看净,却是障道因缘。《坛经》批判了当时盛行的“一行三昧”以及“看心、看净”、“不动、不起”的禅法。实际上,这是所谓“东山法门”,道信、弘忍一脉相承的传统禅法。不仅神秀自己说他的禅法禀承自“东山法门”,从实际情况看也是如此。《楞伽师资记》说神秀的禅法是:禅灯默照,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神会指出神秀的禅法特色是: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
显然,《坛经》所批判的既是神秀、普寂的禅法,也是弘忍、道信所代表的传统禅法。依照《楞伽经》等如来藏系经论的说法,我人的心性原本与佛一样的清净无染,只因烦恼的覆盖,而无法显现心的本性出来。只要我人透过禅定等工夫的修行,即可去除烦恼,还其本性清净的面目。而“看心”及至“看净”,或“坐禅看心”的禅法,即是此一思想下所发展出来的禅法。然而,《坛经》却反对这种禅法!当然,《坛经》并未指名道姓,后来神会自然也不便针对历代祖师,只好明言那是神秀、普寂的禅法。
神会可能想借《坛经》来发动一场针对传统佛学或禅法的革命,但他没有直接这样做,而是通过为慧能争祖位向已占主导地位的所谓“北宗”来推动这场变革。从《坛经》的起名看,全称是《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就有以“顿”立“新教”的意味,并自称为“经”。但神会掀起的禅学革命并未取得完胜,因为“顿教”难以成立,《坛经》就说:法无顿渐,人有利钝。后来宗密也调和说,神会当年之所以采取激烈的态度提倡“无念”,是因为当时渐教大兴,顿宗沉废,务在对治之说,故唯宗无念,不立诸缘,而现在则应当回到“圆融为一”的立场上来,不应当执着各一宗,不通余宗。而这场佛学革命成功的地方则是《坛经》确实成为中国僧人的唯一称“经”的著作。《坛经》主张“唯论见性”“顿悟成佛”,力图摆脱繁琐的修证过程和名相义学解释,抛弃了已变得外在化、他力化的“佛性论”而转向更加内在的自力的“心性论”,并由思辨推理转入超验直觉,融进了儒、道思想,适应了中国本土文化,慧能一系终于夺取了佛教正宗的法统地位。慧能虽未成为新教教主,但获得了六祖之位。
在这场法统之争中,双方都借助了朝廷的势力。这实际上也是佛教适应中国本土的一个方面。与印度不同,在中国早已形成的传统中,王权是大于教权的。其隐含的意义有二:宗教的正统传承亦如王权的传承,视一代一人为合法,不容篡改。第二,宗教正统要得到认可,就必须得到王权的认可,仅有民间的信奉是危险的。佛教传入中国水土不服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它如何处理与王权的关系,而这又与“孝”内在相关联,因为“忠”不过是“孝”的表现,是更高的“孝”。所以,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中,既表现出一种与王朝的疏离倾向,不合作态度,又表现出一种寻求王权支持的倾向,合作的态度。最终后一种倾向占据主流,佛教终于被编织到王朝认可的政治和文化结构之中。但当某一佛教派别在追求发展中过分依赖王朝时,也难免随王朝权力结构变化而兴衰。即使某教派依靠王朝势力赢得正统地位,变成“国教”或“官禅”,仍然可能成为王朝权力斗争的工具而变得前途难以预料。例如,神秀北上长安充当“帝师”,实际上也是希望得到王权的认可并借王朝之力来发展禅宗,但他发现这样也是有代价的。后来神会北上也是同样的目的,并演变成借助王朝力量来打击占据优势地位的一方,演变成与政局相关的宗派斗争。从后来的发展看,神秀一系和神会一系虽曾红极一时,但传承不长或只传了数代,最终就因后继无人而消亡。
北宗禅秀一系和南宗神会一系的命运说明,过分与王权亲密,并不利于宗教文化和教派的发展。相反,那种既能适应王权又与王权保持独立的宗教派别,会有更充分更健康更长远的发展。在这里,一种能够处理好与王权关系、处理好与本土文化关系的宗教派别被逐步选择出来和发展起来。而从宗教文化发展全局看,它正是通过宗派的兴衰演变,中国禅最终与王权相适应,与中国本土宗教相互融合,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当中国禅真正成为王朝认可的宗教之一时,它就具有了合法正统地位。由于最终成为佛教主流的中国禅宗的各派弟子多出自慧能或者宣称出自慧能,以慧能为六祖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既是历史的选择,也具有“母因子贵”的味道,但与弘忍的安排无关。当然,“一花开五叶”后,自然也就没有一个公认的七祖了。
[1]陈寅恪.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M]//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91.
[2]王清学.陈寅恪论“得法偈”一文之浅析[EB/OL].(2013-04-06)[2014-05-11].http://www.doc88.com/p-9827336928704.htm l.
[3]净慧.关于慧能得法偈的再探[EB/OL].(2012-01-28)[2014-03-20].http://www.foyuan.net/article-516662-1.htm l.
[4]陈金宽.禅宗《坛经》心理学思想研究[EB/OL].(2012-06-05)[2014-03-26].http://www.baidu.com/link?url=_7Tr6a_gGcHkT_oo OApjxxhJ5QeX2FgBVdKgrxdzmhuScnjgfWK3jynpA9aiYom rErgwEkBsd2Q-9_2-xLueq.
[5]林有能.慧能与神秀关系辨析[J].广东社会科学,2007(5):147-152.
[6]程东,程辽.《坛经》究义——惟论见性背后的禅宗变法[EB/OL].(2014-02-27)[2014-0610].http://bbs.tianya.cn/post-647-21620-1.shtm l.
[7]杨惠南.道信与神秀之禅法的比较——兼论惠能所批判之看心、看净的禅法[EB/OL].(2009-04-12)[2014-06-22].http://www. foyuan.net/article-94154-1.htm 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ineng and Shenxiu
ZHU Zheng-guo
(Yunfu Municipal Office of Local Chronicles,Yunfu 527300,Guangdong,Chin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ories of heart stanza and well verse,there were amultitude of omissions as well as contradictions from different period of historical record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ineng and ShenXiu.The stories related to Shenxiu and Huineng,including the verse legend,were fabricated for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status of Zen and internal factions,serving the factional struggle for the orthodox status, or edited for the excuses of Shenhui’s condemnation of Shenxiu,which triggered a religious revolution.The sixth patriarch Huineng’s statuswas the choice of history,which had nothing to do with Wuzu Hong’s arrangements
Huineng;Shenxiu;sixth patriarch;well verse
B946.5
A
1007-5348(2014)09-0005-09
(责任编辑:廖铭德)
2014-06-05
朱正国(1963-),男,湖南长沙人,云浮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主要从事哲学和禅宗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