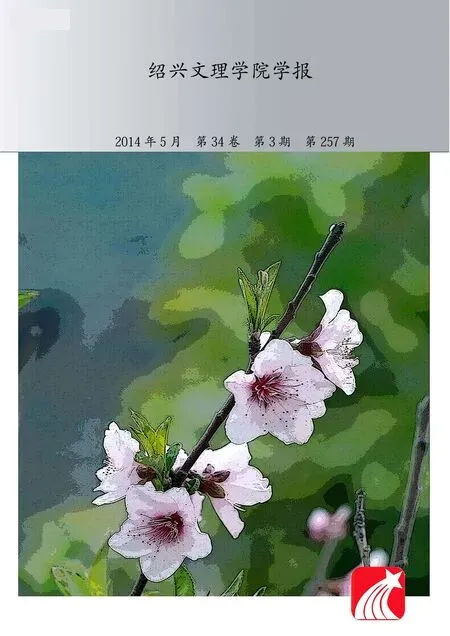当代戏曲中西施形象的身份建构
何金梅
(绍兴文理学院 元培学院,浙江 绍兴312000)
当代戏曲中西施形象的身份建构
何金梅
(绍兴文理学院 元培学院,浙江 绍兴312000)
西施形象的建构经历了从历史典籍中的抽象符号、诗歌作品中的审美对象到戏曲叙事的主体建构的三个基本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以明代梁辰鱼的《浣纱记》为参照蓝本,中国的戏曲舞台上出现了诸多关于西施的戏曲,当代戏曲叙事赋予了西施美女身份、情人身份和母亲身份的多重建构,体现了红颜祸水、红颜痴情、红颜薄命等相似母题,但也有些作品也赋予了西施质疑男性权力、争取个体自主的主体意识,总体上体现了戏曲话语对女性身份的赋权、限制和建构。
戏曲;西施形象;身份建构
一、戏曲、叙事与身份建构
在中国历史和文学典籍中,西施一直是一个被言说的对象。西施是否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其出生地在哪里、命运结局到底如何等史实问题,很多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史料研究和整理工作。西施的真伪问题是历史问题,本文不做探究。但从文学话语的角度看,西施不是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一个传说人物。在文学话语中,有关西施的叙事,叙述的不是历史人物本身,而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传达了人们对这一人物的想象和理解。
从明代梁辰鱼的《浣纱记》之后,西施不断地被搬上舞台。更有意味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根据历史传说和记载,以及以《浣纱记》为蓝本改编的西施主角的戏曲不在少数,这些戏曲演出之后都获得了很大的社会效应。通过不断的叙事和表演,西施也逐渐成为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艺术形象。因为“叙事就是向其社会成员传达生活中一些重要事情的方式,叙事远不止简单的娱乐而已。在这些文本中,社会冲突和信仰被赋予了形式,获得了解决”[1]。在西施形象不断被重塑的故事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和创作者对美貌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思考。按照性别建构的理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那么在中国戏曲的语境中,西施被塑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女性人物,作为中国文化中美女的代表,其女性身份构成的要素有哪些?“人都要形成自我,任何一个自我都具有性别……性别,如同自我的其他侧面一样,是一整套通过叙事、幻想、角色认同而形成的……自我与他人的联系和区分都经过无数的幻觉和想象。”[2]考察西施形象的戏曲叙事,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与美貌、女性与爱情、女性与政治、女性与伦理等关系问题的呈现。因而,对中国戏曲中西施形象的身份建构的分析可以成为一个和性别文化建设有密切关系的典型个案。
本文拟从两个层面来讨论西施身份建构问题,一是梳理西施身份的历史层累阶段,二是通过对当代有关西施的戏曲话语进行分析,揭示其中关于西施身份建构所蕴含的主要内容,考察这些话语如何建构西施作为美女、妻子、母亲、一个具有主体性的人等诸种身份,反思“红颜祸水、红颜痴情、红颜薄命”三个母题对女性身份建构和女性生存的影响。
二、西施身份建构“层累”的几个阶段
对于西施形象的历史建构问题的探析,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和态度。“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简而言之就是:不立一真,惟穷流变”[3]。也就是说,流变的探寻比对真相的探寻可能更有意义。
在中国的文化文学语境中,西施形象的身份建构基本经过了三个的阶段:
(一)第一阶段:历史典籍中的工具符号阶段
先秦、西汉的历史典籍的记载中,西施只是个简单的美女形象,或者只是美女的代称,只有对其外貌之美的简单记录,因而可以看作是一个简单的符号。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以《越绝书》为代表,记述了一则大致清楚而又稍显简略的“西施复国”故事,西施作为一个美女形象开始与男性、政治发生了关系。但是这些记载中的西施还是模糊的,没有具体的人物关系,也不具备丰富的内心世界,虽然“红颜祸水”的事件模型已经基本确立,但这个阶段西施形象基本是历史语境中的政治筹码,即作为男权社会里国家战争里的一个具有价值的“物”,这个阶段的西施形象基本是在历史语境中存在,还没有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主体发出声音,但作为美女的符号代指却已经被确立,其在男权社会中的工具属性也明确无疑。
(二)第二阶段:诗歌语境中的审美客体阶段
西施形象进入文艺语境的时期应该是在唐代以后,唐代有大量咏西施的诗歌作品,在诗歌这一高度抒情的文学样式中,西施形象基本上是诗人用来寄予情感或表达政治态度的一个吟咏对象,是一个审美对象,对西施个体生命体验的形象虚构还基本空白。在众多吟咏西施的唐代诗作中,或认为西施是国家兴亡的关键性人物,或突出西施美人的特质,或将美的含义扩展,代言或借比为其他美好的人或事,“这一方面促使西施形象完成从历史人物向文学人物的过渡,另一方面则使西施传说在历史与文本的共生互动中渐趋完满。”[4]然而,这一完满并非指向西施之一人物形象本身的完满,在诗歌层面,西施的形象还是零碎的、片段的、对象化的,她还有待于叙事文学的文艺空间赋予其主体心理层面的丰富性。
这一时期,虽然西施形象虽然进入了文学话语体系,但创作者们并未进入西施这一人物的心理世界,可以说,这一形象还基本是一个客体状态。
(三)第三阶段:戏曲叙事中的主体身份建构阶段
元明时期,随着话本和戏曲的兴起,西施形象进入了文艺叙事的话语体系。在戏曲中,西施成为了行动的人物,有了具体的社会关系,通过戏曲对白、独白和唱词等方式,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得以展示,情节的发展则显示了人物在具体环境中的处境,同时也显示了创作者对这一人物的认识和态度。因而,可以说,是戏曲叙事使西施形象从简单的符号和抒情的对象走向一个具有行动能力和主体身份的人物。
在古代戏曲中,最有影响和流传最广的是明代梁辰鱼的《浣纱记》。其他的剧本要么只有存目,要么很快就不再搬演,没有太大的影响。在中国当代戏曲的舞台上,西施戏却在很多剧种的舞台上被一再搬演,比较主要的剧目有梅兰芳主演的京剧《西施》(基本根据梁辰鱼的《浣溪沙》改编,情节和台词没有太大改变,本文不作为讨论对象)、越剧《西施归越》(1989编剧,1995年上演,2006年改编为京剧重演)、越剧《西施断缆》(1995)、豫剧《浣纱记》(2005)、歌仔戏《范蠡献西施》(2005)、粤剧《范蠡献西施》(2005)、昆剧《西施》(2006)、锡剧《浣纱谣》(2006)。当代戏剧演出的手段更新、舞台设计、唱腔表演等外部因素固然重要,但都是一种服务于人物塑造的手段,因而,西施在戏曲叙事的“层累”中被赋予了哪些人物身份的文化内涵,是一个需要比较和分辨的重要问题。
三、当代戏曲西施形象身份建构的主要内容
古典戏曲中虽然出现了很多有关西施的戏剧文本,但是流传下来并有广泛影响的只有明代梁辰鱼《浣纱记》。因而,本文以《浣纱记》作为一个参照文本,以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编的西施戏曲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梳理西施形象的主体身份建构的内容。
(一)美色如何:女性的身体之重
后代的西施戏不管如何改编,有个基本的情节都保留了下来,那就是西施入吴,凭着美貌,最终吴王被魅,勾践复国得以成功。“美人计”作为男性战争的一种计谋,总是屡试不爽,不管是在历史典籍还是在文学文本中,西施只不过是一个承前启后用来证明美人力量的人物之一。从情节设置看,西施在吴越之争的历史故事所起的关键作用从未被怀疑。但是,关于西施“美色”身份的建构,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变化。主要表现为对西施美色的闻名程度和美色的力量表现有所不同。
关于西施美色的闻名程度,在梁辰鱼《浣纱记》中,西施的美色并无人知道,“奴家姓施名夷光,祖居苎萝西村,因此唤作西施。……虽貌美而莫知,年及妍而未嫁”,是范蠡路遇西施,发现西施的美貌,并主动献出佳人。而后代很多戏里,西施的美貌美名远扬:
同名豫剧《浣纱记》:“我家大王,最喜美色。听说你们越国有一美女西施,小名夷光,有沉鱼落雁之貌。”
《西施归越》“吴王要美女,越王要复仇,……天下之大,竟找不出第二个西施?西施、西施、唯有西施!”
《西施断缆》:伯嚭“早闻姑娘有绝色,故而来访名花。”
《范蠡献西施》:文种进献美女计策,君夫人训练礼仪,君夫人认为“西施有倾城的美貌,恐怕也是不祥之人,如果她以她的姿色为国建功,也不枉费她天生的美貌。”
在梁本《浣纱记》中,西施入吴是因为范蠡发现其美貌,在当代戏曲中,西施美貌被描绘为众所周知的身体特点。
关于西施美色在吴越之争中的作用,同名《浣纱记》(梁辰鱼《浣纱记》以下简称梁本,姚金成改编豫剧《浣纱记》简称姚本)的表现有所不同,在梁本中,把西施置于吴越之战的历史环境中,作为越国献给吴国的礼物之一,是文种灭国九计中的一计,文种“臣前进九术,缺一不可”,“进美女以惑其心”。但在后代的一些戏里,其他的计谋被有意忽略,西施入吴成了吴国灭亡的最为关键的因素,西施美色的力量在后代的戏剧中不断被夸大和强化。
在梁本“迎施”一出,范蠡劝西施入吴时一段词,表明了对美人救国的希冀:“社稷兴废,全赖此举。……若能飘然一往,则国既可存,我身亦可保。后有会期,未可知也。”这段经典的对白在后代的戏中虽然被基本保存,但还是有些微妙的变化。如姚本:“越国存亡,全赖卿之义举了。然社稷兴废,全赖此举。若能慨然一往,国既可存,身也可保。后有会期,未可知也。……如其不然,国亡家何在?你我同作沟渠之鬼,焉能有百年之欢?”后者把“飘然一往”改为“慨然一往”,“举”前增加了“义”字。改变的部分带上了比较明显的感情和评价色彩,“慨然”带有明显的悲壮和牺牲的意味,而“义”乃是传统儒家文化里要求的一种道德,往往是对抛弃个人之私而服务社会之“公”的行为的肯定。梁本中,勾践和西施并未直接就去吴问题交谈,在姚本中,增加了勾践对西施下跪的情节,对西施发出了:“国家危亡在即,百姓血流成河。望姑娘忍辱负重,救我国家,救我黎民”请求。美色的力量被赋予了道义的力量,连国君都认为救国救民的重任,需要由一个原来和政治毫无关系的美女承担,何尝不是对这一力量的夸大。
后代的戏剧对西施美女身份和美色力量的不断强化,其实是不断强化了女性的身体与身份的关系。身份如何与身体相关?正是身体的某些特征赋予了人物特定的身份,身体特征是自然的或者说是生理的,而身份则是有社会意义的,是被文化赋予和建构的。西施入吴作为政治工具的不可避免的命运正是和她美丽的身体特征有关。“美色”作为女性身体的特征在文化建构中被赋予了超力量,虽然西施赴吴的具体原因在不同的戏中有些差别,有些是吴王点名要西施,有些是范蠡献西施,有些是伯丕进献西施,但所有文本都想象了女色对男性的杀伤力,这种力量不仅摧毁男性的身体和意志,更可以毁灭一个国家。“美人计”得逞这一情节在西施戏中成为一个不变的情节,也就是说,对女性美貌能力的想象和夸大成为后代创作者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但充满悖论的是,西施作为拥有美丽身体的主体,并没有拥有对自身身体的自主权。她原来只是一个远离政治中心的乡村姑娘,卷入政治完全是因为男性,权力之争本来和她并没有关系。而且,一旦政治任务完成,她该何去何从也完全由不得她自己,她的命运只能任人安排。
西施美女身份的叙事中,可以看出,女性的身体受政治和性别双重权力的控制。作为政治斗争中的失败国民,女人和其他财产物品一样,是可以占有的;在性别关系中,占有女性,特别是美貌的女性,是男性胜利者权力的表现。在男权文化中,女性美色被想象出某种力量,但是控制这种力量的却是男性。在西施戏中,作为战胜国的吴王想通过拥有美女证明自己的力量,而作为战败国的勾践想利用美色这种力量完成男性争斗者之间的较量。美色使西施成为工具,美使女人物化。在这一点上,后代的创作者和梁辰鱼一样,并没有赋予西施超越时代和既定社会性别关系的可能性。
(二)女人如何:妻性与母性的建构
作为中国传说中的四大美女之首,西施会成为情人和妻子吗?作为女人,她会成为母亲吗?一个女人的妻子(情人)身份和母亲身份可能具有什么样的内涵?这是西施戏曲叙事建构人物的主要内容。
西施与范蠡的关系是西施戏里很重要的人物关系之一。历史记载中,范蠡原来是楚国人,而西施出生在诸暨一个偏远的山村。从梁辰鱼开始,西施与范蠡这两个原来毫无关系的人物被想象出了的爱情关系,此后这一模式被所有的后代戏继承,西施逐渐被塑造成为一个痴情女的形象。
关于这俩人的关系如何开始有三种不同的演绎。一是偶遇定情,一是日久生(有)情,三是西施主动献情。
梁本第二出“游春”中虚构了一个“路遇”的情节:“奴家……虽貌美而莫知,年及妍而未嫁”。“日复一日,年又一年,不知何时得配姻缘也”,西施是个思春的姑娘,两人相遇,范蠡即为美貌所动:“你是上界神仙,偶谪人世。如此丽质,岂配凡夫。你既无婚,我亦未娶,即图同居丘壑,以结姻盟。”西施当即表示了“不变移”的决心,以所浣之纱为定情之物,约下婚盟。后有姚本《浣纱记》、2005年台湾导演王友辉《范蠡献西施》都演绎了类似情节,西施因为其美貌获得范蠡的爱情,基本呈现出了“才子佳人”的传统模式。
在《西施归越》中,西施和范蠡被虚构为自幼两小无猜的恋人。“我与你两小无猜共长大,一条溪水饮两家,你事越王伴君侧,我奉老母浣纱麻……自幼相邻又相爱。”这个情节完全不顾所谓历史事实,纯粹是出于创作需要而进行的虚构,其实也是符合中国古代男女恋情的空间限制的。比较例外的是2005年的粤剧《范蠡献西施》中,范蠡访艳遇西施,两人并未有婚约。去吴之前,西施向范蠡大胆主动示爱,“能否另选一人代替西施”,“如蒙范大夫不蒙弃,我愿执萁帚长为奴婢,终身服侍范大夫。”这个情节的设置可以说突破了传统男女关系中男性主动、女性被动的关系模式,突出了西施敢于追求和表达爱情的勇气,并且付出了行动,因而也可以说,在这部戏里,西施被赋予了一定的主体性,但所表达的“我愿执萁帚长为奴婢”的愿望,表现的依然是传统文化的性别规约,认同了男尊女卑、男主女次的身份定位。
“家国”与“私情”孰轻孰重,在西施戏曲的叙事中,不同性别身份的主体做出的是不同的选择。在爱情关系中面临选择时,男性往往以国家为重,以感情为次。如范蠡“想国家事体重大,岂宜吝一妇人……但有负淑女,更背旧盟,心甚不安,如何是好”(梁本《浣纱记》)。在粤剧《范蠡献西施》中,范蠡感慨“人非草木岂无情,都只为把山河重整”。范蠡是为了国家而把西施献,西施则是为了范蠡而把自身献。在所有的西施戏中,虽然西施去吴前的矛盾挣扎是很多戏刻画的重点,在解决西施入吴的心理问题时,都体现了感情在其行动中的作用,为了范蠡是西施去吴的主要原因之一。如“范郎,夷光想明白了邦国事大,姻亲可缓。一女身微,万家望重。既入吴宫,必得会承欢之术,您教我吧,夷光再不会让范大夫受鞭责之罚了”(姚本《浣纱记》),越剧《西施断缆》这部戏的故事止于西施断缆去吴,西施的内心矛盾最终也在“为国为民也为心上人,明日去吴意已决”中得到解决。西施被塑造成一个从一而终、以男性利益为重、自我牺牲的女性。
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所有戏中的西施都是一个痴情女子,无论结局有何不同,西施对范蠡的感情都没有变化,哪怕吴王夫差对她如何宠爱与体贴,西施也不会爱上他。在爱情过程中,不管是去吴之前对范蠡三年或三月的痴情等待,还是在吴宫中对范蠡的念念不忘,以及灭吴之后对范蠡的痴心期盼,西施被塑造成一个红颜痴情的典范(有意思的是,在电视剧《西施泪》中,西施最终爱上了吴王夫差)。爱情关系的设置,使西施摆脱了纯粹美色工具的政治性和客体性,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赋予了西施作为一个女人的感情体验。这些叙事话语建构了痴情女性的身份,是一个完全符合符合男性中心的价值观念女性形象,虽然西施并未成为真正的妻子,但是有过婚约或者有过感情,就会按照妻子的要求要求自己,这不能不看作是一种自觉的妻性。
关于西施作为母亲的身份建构是个比较大胆的赋权。只有《西施归越》这部戏是以西施怀孕之后回到越国作为戏的开始。西施明明知道如果生下敌国国君的孩子,一定会为情人范蠡所不容,为越王勾践所不容,也为世人所不容,却决定无论如何也要生下并保护无辜的孩子。母性使西施成为一个勇敢的女人。《西施归越》大胆地虚构了西施作为一个女人成为母亲的可能,实际上是对一个女人完整身份的一种赋予,对观众的传统观念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和挑战。大部分戏剧都避免了对西施母亲身份的可能性叙述,是为了保持西施的痴情女的形象,避免陷入某种尴尬吗?
(三)人之问:红颜为何薄命?
美人、情人或母亲,是西施作为女性被赋予和建构的性别身份。吴越之争的政治历史中,西施作为一个有主体意识的人,被迫去吴经过怎样的心理历程,吴国灭亡之后又可能如何进行自己的人生?这无疑是两个最具有虚构空间的情节,在西施叙事中,人的身份被赋予怎样的话语形态,是我们该考察的另一重要内容。
在梁本《浣纱记》中,西施与范蠡的情感戏并不是很多,西施内心的矛盾冲突也不明显。对于范蠡主动献出自己,西施只是埋怨自己:“好苦楚人也。……何事儿郞忒短情?我真薄命!”,当范蠡劝她“及早登程”,西施虽无奈但也很快“勉强应承”,并未对范蠡、国君的做法提出质疑。最后“泛湖”一出中,范蠡“载去西施岂无意,恐留倾国更迷君”,与西施“聊结湖上之姻盟”,西施感念不尽:“谢君王将前姻再提,谢伊家把初心不移,谢一缕溪纱相系。谐匹配做良媒”。西施完全是一个被动的人物,西施的情人或者说妻子的身份基本是为了衬托范蠡这一英雄形象的。
后代的很多戏都比较细致地展示了西施心理从“抗拒—质问—接受”的变化过程:
梁本《浣纱记》:“好苦楚人也。……何事儿郎忒短情?我真薄命!”
姚本《浣纱记》:“这义举,我不要这义举?为男儿你献妻室情割义断,何颜面立于这天地之间?”
越剧《西施断缆》:“又谁知,风波皆因美貌生,逼我离乡去吴邦。”“悔不该,一见钟情把心许……谁料他,一朝绝情永无期!”
歌仔戏《范蠡献西施》:“你当真要征聘西施?果真要献于吴王?哎呀,可怒啊。竟凭越女去乞怜,屈节事仇谁甘愿,委身媚敌遗臭万年,白璧岂容遭玷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西施归越》:“一身使命难推诿”……“难道是一国男儿尽战死,唯余西施一女娃?”
粤剧《范蠡献西施》“是不是我爱你不够深,所以上苍才会这样责罚我们?”
在这些戏中,创作者让西施发出了质疑的声音,其中有对男性政治暴力进行的批评,也有对男性无能的质问,有对女性保全自身的权力要求,还有对范蠡感情的嘲讽与质疑。这些声音的出现使西施成为一个具有行动主体意识的人,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创作者们对男权社会里女性生活境遇的某种同情。
灭吴成功之后,西施怎样继续自己的生活?活着还是死去?西施结局的可能性设置呈现的是西施作为人的生存的可能性。当代戏曲关于西施最终命运的设置,基本有以下几种类型:
其一,隐退:梁本《浣纱记》的结局。范蠡功成身退,带着西施泛舟隐居,远离政治中心。其中,西施完全是个被动的角色,主要突出了范蠡的政治远见,既实现了政治目的,又忠于和保全了个人爱情。这种结局在中国的戏剧中符合“大团圆”理想模式,才子佳人终成眷属,但也显示了一种较为开放的身体观念,西施没有因为伺吴原因遭到范蠡的厌弃。
其二,自杀:姚本《浣纱记》、歌仔戏《范蠡献西施》都设置了西施自沉的结局。这些剧本自杀结局的设置原因有三,一是西施的身体纯洁性已经不复存在;作为一个女人,已经失去最宝贵的东西;“如此牺牲色相,只怕再无颜面返回家园”(《范蠡献西施》),“今生怕徒是负虚名,来生再证三生石”(姚本《浣纱记》)。二是可能增加范蠡作为一个男性的负担,使范蠡为难,“只恐怕范郎他终生里难展笑颜”(姚本《浣纱记》);三是战争中的敌对双方不能泯灭界限,“越国大夫怎能与敌国之妃婚配”(姚本《浣纱记》)。设置西施主动自杀的结局,无疑是把西施塑造成一个完全听命于男性社会的权利控制和伦理要求的女人,这样的女人,自杀就是不给别人添麻烦,是完成最后一个“义举”。这种结局的设置,剥夺了西施活下去的权利,显示了女性作为人的可能空间的狭隘。
其三,被杀:《西施归越》设置了一个西施怀孕的情节,吴国灭亡之后,西施怀着夫差的骨肉回到越国,范蠡嫌弃,勾践怕西施生下敌国的后代,命令追杀西施。黄梅戏《西施归越》(2007)则集中演绎了西施被杀的几种必然,(1)勾践杀之:因为西施能灭吴也能灭越,吴国的王妃怎能回越国,灭吴怎能被看作是一个女人的功劳,西施回国,必杀之;(2)王后杀之:因为西施太美了,既然能魅惑吴王,也能魅惑勾践,王后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必杀之色,(3)范蠡杀之:西施归来之后,越王勾践想娶西施,范蠡认为“你为越国,已立前功,你嫁大王,必有后罪”,为了越国,必杀之。在这几种被杀的可能性里,不管是男性,还是同性,他们只站在自我利益的一方,美之于女性完全是一种罪恶,所以西施不可能有活的机会。
被杀结局的设置,向我们提出了问题,即女性身体和女性伦理处境的普遍命运,女性身体的工具性功能一旦完成,其文化语境中的贞节观念、权力观念和男性中心意识就会纷纷登场,西施作为人,不可能拥有一个正常女人该有的人生。
其四,没有结局:只有越剧《西施断缆》一剧没有涉及西施最后的命运,这出戏只演到西施毅然断缆去吴就结束了,主要矛盾都集中在西施去吴之前,而西施去吴之后如何,未给结论,留有空间。也可以说,这个剧作对西施之后的生活如何不是最关心,某种程度上说,只关心西施是否能为国献身,政治利益超越了西施个体生存的利益。
当代戏曲都对西施去吴的心理矛盾和抗争作为刻画人物的重点,也对西施可能的命运结局做了种种虚构,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对西施作为个体存在的人而进行的建构。除了梁辰鱼的《浣纱记》,西施自杀或者被杀的死亡结局可以看出,红颜薄命成为一个的基本母题类型。因为美人和女人身份,西施不可能拥有一个人的身份继续生存。这种对传统文化里性别权力和性别观念的批评和反思,不能不说是当代西施戏剧的思想革新之处。
四、结语
经由戏曲叙事,西施从一个简单的名字,到成为一个具有救国力量的美女、痴情的情人、勇敢的母亲、悲剧性的女人等丰富的身份内涵。这些建构的意义如何?按照福柯的观点,“话语通过三种途径发挥作用,分别是赋权、限制和建构”[5]中国当代戏曲话语对西施形象的身份叙事也可以看出有这样的三种功能:
其一是赋权,赋予了西施作为一个女人可能有的妻性、母性,赋予了西施对自己命运提出质疑和进行抗争的权力,使其逐渐趋向于一个完整立体的人。
其二是限制,这些叙事话语也限制了女性身份,作为美女的情色力量和作为忠于男性的痴情女子是西施叙事中的对其身份建构的相似内涵,这些剧作显示出其定型的一面,形成了红颜祸水、红颜多情、红颜薄命这样一些传统性别文化中的基本母题。其中,对西施身体的书写是所有叙事的前提,“让写作指向身体则意味着试图将物质的身体变成指意的身体。”[6]这些戏曲写作使以西施为代表的女性身体逐渐成为一种指意的符号,使女性身体的工具性成为一种不符合逻辑的成规认识,即美丽的女性身体可以成为权力男性渴望的对象,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就是不能成为她自己的所有。
其三是建构,从对西施形象塑造的演变过程看,定型形象和男权中心的话语形态虽然占据主要地位,但我们还是听到了一种声音,那就是对西施反抗悲剧命运的虚构、对西施痛苦心理的揭示,以及在揭示过程中的某种反思。这种声音时断时续,虽然微弱模糊,但也可以看作是对女性身份的重新建构。
[1][美]阿瑟·阿萨·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M].姚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6.
[2][美]波利扬-艾卓森.性别与欲望-不受诅咒的潘多拉[M].杨广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69.
[3]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出版社籍,1982:273.
[4]陈晓虎.唐人笔下的西施形象[J].江淮论坛,2004(1).
[5][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M].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57.
[6][美]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M].朱生坚,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1.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Xi Shi in Modern Operas
He Jinmei
(Yuanpei School,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The construction of Xi Shi’s image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the abstract symbol in classical works, the aesthetic object in poetry, and the subjective construction in operas. Since the 1980s, based onHuanShaJiwritten by Liang Chenyu in the Ming dynasty, many operas regarding Xi Shi have appeared on stage in succession, which endowed Xi Shi with multiple identities like a beauty, a lover and a mother, expressing such motifs as a dangerous beauty, a spoony confidante and a miserable lady. Additionally, there are still other operas endowing Xi Shi with the capacity to query male power and to strive for the individual independence awareness. These works, in general, reflect that the opera discourse can empower, restrict and construct the female identity.
opera; image of Xi Shi; identity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周一农)
2014-03-11
浙江省社科联“中国戏曲中的西施形象的‘层累’建构研究”(2011N15)、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越剧中西施形象的性别文化内涵研究”(125342)、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中国戏曲中的西施形象的‘层累’建构研究”(KYB110612)相关成果。
何金梅(1971-),女,福建莆田人,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副教授。
I207.38
A
1008-293X(2014)03-0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