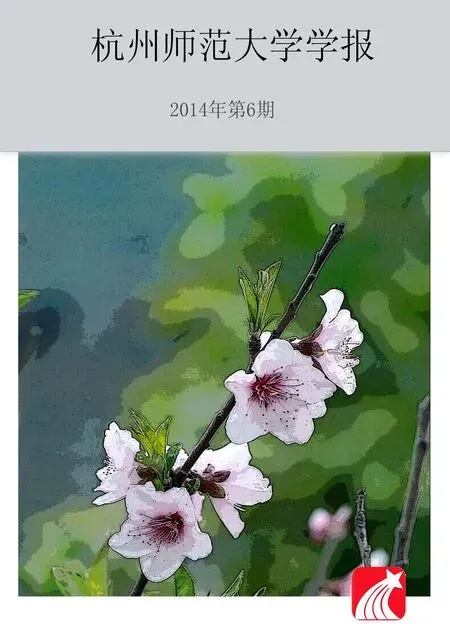《亚细亚狂人》的跨国族同理心
唐 睿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香港浸会大学 语文中心)
《亚细亚狂人》是无名氏首部长篇小说,跟以往的小说相比,《亚细亚狂人》的主题更为集中、明确,脱去了《火烧的都门》的练笔意味。《亚细亚狂人》以韩国的命运为经,以韩国光复军李范奭将军的一生为纬,但当时无名氏的视野,已逐渐超出了对一国一人的关心,而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关怀人类的整体命运。这种肯定国族差异,但同时又能把人类视为一个共同体,强调彼此平等和尊重的观点,实际是世界主义精神的基础观念。无名氏在《亚细亚狂人》的一些章节,如《露西亚之恋》和《狩》中其实已分别借韩人与白俄遗民、金耀东与白俄将军及史上许多名人的命运,表现出“人类普遍命运”的讯息。这些作品,都是把握无名氏艺术思想的重要参照。
《露西亚之恋》①《露西亚之恋》既是短篇小说集的名字,又是该小说集中一篇小说的篇名。本文集中讨论短篇小说的内容,除非特别注明,所言《露西亚之恋》皆指短篇小说,而非小说集。于1942年1月完稿,较写于1943年11月的《北极风情画》完成得早。篇末附有“这是一个未完成长篇的断片”,是《亚细亚狂人》中的一个片段,可衔接《北极风情画》的内容。虽然这篇小说只是一个残篇,但孤立作为一个短篇小说来看,亦有其鲜明集中的主题。《狩》则是《亚细亚狂人》第五部《荒漠里的人》的一个章节。故事发生在1929年至1931年中国东北的外兴安岭,主要讲述主人公金耀东在吉林奉天从事革命失败以后逃亡到黑龙江西北部的故事。《露西亚之恋》讲述韩国光复军在柏林巧遇白俄遗民,因彼此同为亡国人民的身份,而产生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的感情。《狩》则讲述金耀东抗日失败,退居中国东北外兴安岭狩猎为生时的一个片段,当时金耀东想起多年抗日的努力,似乎是命运跟他开的玩笑,最后他想起古今中外许多被命运拣选的巨人,自我开解。《露西亚之恋》和《狩》两篇小说都展现了强烈的跨国族同理心,见证了无名氏作品中,世界主义精神逐渐成熟的过程。
一、《露西亚之恋》的跨国族同理心
《露西亚之恋》的写作日期虽较《北极风情画》早,但故事内容,却是《北极风情画》之后的情节。《北极风情画》以主角离开苏联托木斯克转往欧洲作结,而《露西亚之恋》正好就承接这旅程,讲述韩国独立军转往德国的一个夜晚。《露西亚之恋》的主角虽然也是以李范奭为蓝本,是一位“与马占山李杜一行从苏联托木斯克出发,越过波兰,初踏入这日耳曼的都门”[1](P.134)的韩国军人,却不是《北极风情画》的林军官,而是名字短写为“金”的韩国军人。故事另有一位韩国角色,名字短写为“明”,是金“在柏林大学教书的同乡”,一位哲学讲师。《露西亚之恋》主要讲述金与明在柏林一家白俄咖啡馆——“白熊咖啡馆”遇到一群从苏联逃出来的白俄遗民的故事。当夜双方彼此提及自己亡国的命运,然后产生一种同病相怜的跨国族同理心。《露西亚之恋》共分八节,除韩国军人与白俄遗民外,篇章还提及其他国族。由中韩以及东北少数民族混合编制的马占山军队自不待言,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第一节里,筵席上提到的波兰民族。韩国军人未有直接跟波兰民族交往,但金的演说不断以波兰民族的命运来观照韩国的命运。
我永远忘不了那些在阳光中跑着跳着的波兰孩子。我永远忘不了波兰的自由的原野。我永远忘不了波兰的阳光。我永远忘不了再生的华沙。华沙一切全是崭新的。在华沙,一花一草一本一石全在嘲笑我、讽刺我,在谴责我们那些甘心做东京奴隶的同胞。……华沙是一只刚从灰烬中再生的凤凰,在昂着骄傲的头,在摇着骄傲的尾巴,在向我责问:我们,曾遭三次瓜分悲运的民族,现在是再生了,你们这些“檀君”子孙(指韩人)呢?[1](P.136)
金以波兰和韩国作比较,因为这两个民族都遭遇过亡国的命运。尽管韩国没有跟波兰在政治或军事上有直接瓜葛,但对于韩国民族而言,波兰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他者”,而是一个跟自己拥有相同特质、可以互相理解的“他者”,即一个能够投以跨国族同理心的对象。
波兰与韩国的命运,仅仅是《露西亚之恋》的一段插曲。《露西亚之恋》的主调是韩国光复军与白俄遗民的惺惺相惜之情。在故事起首的欢迎会上,“德国华侨们对这群抗日英雄备致颂词满座响起雷样的掌声”,但金的内心却异常寂寞,“在他听来,每一句话全是最刻薄的讽刺”。[1](P.138)金觉得华侨的颂辞刺耳,因为他虽被尊为英雄,但韩国复国的希望仍然遥遥无期。韩国的亡国和复国问题始终困扰着金,以致他不停地在心里反复自问“为甚么我是韩国人呢?为甚么我是韩国人呢”?[1](P.138)对国族的忧虑无从排解,于是金才在柏林的街上疾走,希望借此挥走这些思绪。可是“这些思想仍紧紧缠着他、不放松他、折磨着他”。[1](P.138)因此,明将金从纷乱思绪中唤醒的一句话便别具象征意味,他问金:“我们究竟往哪里跑呀?”这句话第一层意义是问金要往的方向,而结合故事的叙述后,则产生第二层意义,即韩国独立军的命运将会如何。对此,金回答说:“随便跑吧,直到疲倦为止。”这话落在叙述的语境里,也可以作两个层次的解读:字面义道出金对奔跑目标的茫然,象征义则可理解为金对韩国复国的茫然。如此诠释,并非捕风捉影,从金与明稍后讨论当夜要在哪里歇息的对话,便可继续追索国族讨论的线索。当明问金:“‘今晚你愿意和甚么样的人在一起?’金沉吟了一下,缓缓的道:‘这里有流浪民族吗?——今晚的情绪,是只容许我和流浪人在一起的。’”[1](P.140)由此可见,故事内容始终围绕着国族问题在推进,而金与明稍后走到“柏林的流浪人之街”,步入白俄遗民聚集的“白熊咖啡馆”亦非偶然。
“白熊咖啡馆”并非金与明在柏林的白俄聚居处最先见到的咖啡馆。步入“白熊咖啡馆”之前,“金走过几家咖啡馆”,但都没有跨进去,原因是“从它们的门面装潢看来,这些咖啡馆与他的灵魂之间,似乎尚缺少某种神秘的联系”。这种“神秘的联系”具体所指甚么?这可从金最后步入的“白熊咖啡馆”得到回答。
首先,吸引金注意“白熊咖啡馆”的,是咖啡馆的“烨炜光华”。作为一家“流浪民族”聚集的咖啡馆,“白熊咖啡馆”不见半点破落气息,相反,它华丽得让作者愿意花一段颇长的文字去描绘装潢。除了金碧辉煌的装潢,“白熊咖啡馆”还有一个神龛似的乐坛,容得下二十几个白俄乐师在上面演奏。此外,咖啡馆内还有一张壁画深深吸引住金的视线,这张画便是俄国名画“莫斯科大火”的模拟品。作者对画作了仔细描述,强调了画作的重要性。“莫斯科大火”描述的是1812年拿破仑占领莫斯科的一段历史故事,其时拿破仑以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将会于莫斯科沦陷后迅速投降,岂料莫斯科突然发生大火,法军粮草燃尽,局势迅速扭转。一度濒临亡国的俄罗斯在这场大火之后,乘胜追击,最后更在1814年成功反击法国,直抵巴黎,逼使拿破仑下台。“莫斯科大火”一画,记录了俄国从几近亡国,到复兴的曲折历史,它在《露西亚之恋》中之所以吸引住金,是因为画中的历史呼应着金的家国民族哀思,唤醒了金的跨国族同理心。
金注视“莫斯科大火”一画,是一笔侧写;这段叙述的重点,是金向白俄遗民说着地道的俄语,引起俄人注意,并借由“祖国”二字,令整个咖啡馆变得庄严肃穆的描写。这描写道出韩俄两国的共通民族感情,具点题之效,金和明两个韩国人与“白熊咖啡馆”一众白俄遗民的情感交汇,即由此而起。起初,金道出的“祖国”二字,勾起了白俄遗民许多痛苦的回忆,而金完全理解这种痛苦,俄人“这些阴暗的面孔与微微抖颤的粗壮的白色胳膊,暴风雨样掀起金的感情,一剎那间,一道神秘的热烈的阳光像闪电似地从他身上掠过,他自己一生的坎坷与悲哀完全解了冻,像千万条雪水般从一个高峰上奔流下来,奔流下来”。[1](P.150)
早前金因未能在其他咖啡馆找到“神秘的联系”,所以过门不入,而现在他在“白熊咖啡馆”里却找到了一道“神秘的热烈阳光”,前后互相呼应。这种“神秘”的感觉更在金紧接其后的话里得到阐明:
请不要问我对于沙俄或苏联的意见,请不要向我提出道德问题或社会问题……生命原是痛苦的、不可解的。在我们之间,一切的理论全死了,现在只存在着纯人与纯人之间的深厚的同情。[1](P.151)
这段话可说是《露西亚之恋》的核心话语。首先,它点出了牵引着金在柏林一夜奔走的“神秘”感情,实际就是“纯人与纯人之间的深厚的同情”,而这种“同情”,即是跨国族的同理心。在进入“白熊咖啡馆”之前,金就明确说道:“今晚的情绪,是只容许我和流浪人在一起的。”[1](P.140)而“白熊咖啡馆”的白俄遗民在俄国变成苏联之后,就正是流落异乡,寄居他国,有国归不得的“流浪人”。
此外,“白熊咖啡馆”有别于其他白俄咖啡馆,它华丽的排场,都可说是俄罗斯帝国的辉煌象征。“莫斯科大火”一画,记录了俄罗斯民族浴火重生的历史和精神,至于馆里的乐团、音乐、歌舞、酒食,以及由叙事者或角色提到的风情习俗,在在皆述说着俄罗斯民族的伟大。“白熊咖啡馆”的白俄遗民,对自己的国族文化,充满着十足的自信,而这亦与金对韩国民族文化的看法完全一致。当金在《露西亚之恋》开首忆想故国的时候,他对祖国的描述是“圣洁泉水的祖国,那开遍杜鹃花的故乡原野,那说不尽的美丽的‘槿花之国’,展开在他眼前的是银白色的朴渊瀑布,露梁津的碧柳深深低垂……”。[1](P.134)跟“白熊咖啡馆”的白俄遗民一样,金对祖国怀着无限恋眷,以及十足的自信。“白熊咖啡馆”的相遇,给予金和白俄遗民不少的慰藉,而这种慰藉,即跨国族的同理心。
MTHFR和MTRR基因多态性与陕西地区汉族人群冠心病发生的相关性研究 ……………………………… 白晓丹等(22):3125
《北极风情画》的跨国族同理心,有男女情爱因素掺杂其中,而《露西亚之恋》的跨国族同理心,仅仅是由一夜的一次偶遇所引起,更为纯粹、更为聚焦于国族间的同病相怜情怀,突出国族能够在毫无利害关系下,互相理解,体现出世界主义精神的基础特质。
二、《露西亚之恋》的历史原型
过去,由于学界对《无名书》之前的创作缺少认识,且资料掌握有限,所以难以全面解读无名氏的早期创作。然而,随着无名氏部分佚文的重新发现——特别是1942-1943年发表于《中央日报》(贵阳版)的《荒漠里的人》*关于《荒漠里的人》,有几笔需要补充的数据。无名氏正式在《中央日报》(贵阳版)连载《荒漠里的人》之前,曾在1942年8月19日和24日的《中央日报·前路》(贵阳版)中表示“《荒漠里的人》是我的正在写作的长篇《创世纪》的第五部。这个长篇共分八部”。这部长篇的总题目,在连载之初名为《创世纪》,无名氏晚年却多称之为《亚细亚狂人》,详见汪应果、赵江滨《无名氏传奇》,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341页,以及无名氏著《在生命的光环上跳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所收的《〈无名书〉写作经过记略》。的重新发现,《露西亚之恋》及《龙窟》各个篇章的深层讯息,便得以进一步诠释出来。
1942年8月,无名氏计划撰写《亚细亚狂人》*无名氏早期亦有构想将《亚细亚狂人》这部作品称为“创世纪”,为免令读者混淆,本文仅在引文里保留“创世纪”的篇名称谓,其他的论述部分则一概称之为《亚细亚狂人》。的长篇,而这部长篇的第五部,就是无名氏稍后连载于《中央日报》(贵阳版)的《荒漠里的人》。重新发现并整理《荒漠里的人》连载稿的李存光、金宰旭提出,《亚细亚狂人》第四部应该叙述了有关李范奭在1921-1928年的故事,“写李范奭随军进入苏联,加入苏联红军所属高丽革命军步骑混合兵队,和苏联红军合作攻击斯巴司卡亚的白俄军”,[2](P.11)并认为《露西亚之恋》的《骑士的哀愁》“应该是这一部结尾的断片”。[2](P.118)
诚如无名氏在《关于〈荒漠里的人〉》里的表示,《亚细亚狂人》这个长篇是讲“一个韩国革命者的一生奋斗史”。*无名氏《关于〈荒漠里的人〉》,载《中央日报·前路》(贵阳版) 第609期,1942年8月19、24日。而熟悉无名氏作品的人都知道,这个“韩国革命者”,就是李范奭。根据《李范奭将军回忆录》:1921年6月,李范奭随韩国独立军进入俄国,参加革命武装,希望借助俄国革命党的力量对抗日本,但不久之后俄国革命军与日本达成合作协议,俄单方面解除韩国独立军的武装,李范奭和金佐镇等人逃亡到中国东北。1922年,李范奭得心脏病到俄罗斯治疗,并于1923年“参加高丽革命军,担任高丽革命军的骑兵司令官。高丽革命军与苏联定有密约,帮助红军打仗,苏联则支持武器装备,高丽革命军变成了‘合同民族军队’”。[3](P.320)1925年,苏联与日本签订渔业协议,日本政府承认苏联政府,但同时要求解散西伯利亚的韩国独立军武装。1月,苏联强行解除韩国独立军武装,韩国奋起反抗,李范奭头部中弹,送到安宁县宁古塔治疗。伤愈后,李范奭在满洲军阀队伍中当了四个月雇佣兵,直到7月接到金佐镇电报后,再到宁古塔。8月李范奭在宁古塔结婚,9月起开始组织高丽革命决死团,以种鸦片来赚钱再向俄人购买武器,自此,李范奭一直带领决死团与日军对抗,直到1928年12月,决死团在日军和中国军阀的镇压下,被迫解散,李范奭亡命外蒙古。可以说,1921-1928年是李范奭与苏联武装往来得最紧密的时期,苏韩双方因各自的利益互相利用,又在利益关系消失后瞬即反目。有关内容,在《骑士的忧郁》和《露西亚之恋》中都可以找到线索。
无名氏曾经明确表示,《北极风情画》的内容是从《亚细亚狂人》这篇小说中的第六部改编而来。《北极风情画》写马占山军队离开托木斯克转往欧洲,从内容来看,《露亚西之恋》写马占山军队从托木斯克经东欧抵达柏林的故事,正好在《北极风情画》之后。尽管两篇小说的主角名字不一,但详细分析内容,不难发现,两者皆是以李范奭为原型。换言之,《露西亚之恋》的故事,发生在李范奭和苏联红军联合攻击巴司卡亚的白俄军之后。
梳理清楚《亚细亚狂人》的故事时序,便能深入解读《露西亚之恋》里金为何要对“白熊咖啡馆”的白俄遗民说“‘请不要问我对于沙俄或苏联的意见,请不要向我提出道德问题或社会问题,请不要逼我批评什么或谴责什么’”,“生命原是痛苦的、不可解的。在我们之间,一切的理论全死了”,并特别跟白俄遗民强调,不要在当晚提及政治、社会、道德等问题,因为金的原型——李范奭曾联合苏联红军,攻击白俄部队,而“白熊咖啡馆”的俄人之所以流落他乡,金可谓有一定的责任。金理应最清楚作为亡国奴、异乡客的痛苦,然而他为了自身国族的命运,却让一群跟自己毫无关系的百姓,沦落到跟自己一样的痛苦处境,这对金而言,是一种极大的讽刺,难怪他会说“生命原是痛苦的、不可解的”。
可是,这夜在“白熊咖啡馆”的相遇,金和白俄遗民并未因金曾经追击白俄军队,或者与苏联军队串联而发生龃龉甚至冲突。进入“白熊咖啡馆”,遇到白俄遗民之后,金便被“暴风雨样掀起”一种跨国族的同理心;至于白俄遗民在得悉金来自“俄罗斯母亲”,看到金以哥萨克人的架势喝酒,并喝过金请客的伏特加酒后,他们均对金表示深深的敬爱。一时间,国族忧思、异乡客的感伤更使金希望能够和白俄遗民紧紧相连在一起,表现了一种超越了政治立场、社会问题乃至道德常理 (跟亡国仇敌共饮)的跨国族同理心。这种“纯人与纯人之间的深厚的同情”可以超越国族偏见和政治见解。这正如当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阐述世界主义这一概念时所指出的:“将他者既作为与己相异又作为完全平等的人来看待。”
三、《狩》的跨国族同理心
《狩》是长篇小说《荒漠里的人》*《荒漠里的人》是《亚细亚狂人》的第五部。中的一个篇章(第二章第四节至第九节),现收于《龙窟》并有所删改,剔除了金耀东独自猎鹿茸的一段,但除此之外,《狩》的主要情节未作其他修改,与原载在《中央日报》(贵阳版)的版本大致相同。《狩》共分五节,主要讲述金耀东带着猎犬贝尔特在哈拉苏猎狍子的故事。叙事者除了着力描绘金耀东狩猎时的所见物事,亦对金耀东的心理活动作了细腻的描写。在孤独狩猎的过程里,金耀东想起了自己过去的经历,并联想到“一幕幕生命的大悲剧浮雕”,包括“跋涉在恒河畔的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释迦,苏格拉底的毒药,冰天雪地中的华盛顿的悲惨大溃退,贝多芬的聋瞶与命运交响曲,尼采的疯狂……”。[4](P.26)
其中,作者花了整整一章,叙述一位俄国名将的亡命故事。
故事讲述一位“曾任华沙方面总司令的沙俄名将”,他在罗曼诺夫王朝结束之后,辗转流落到美国洛杉矶,成了一位好莱坞演员。机缘巧合下,他获得了一个演出的机会,所演角色,正是一位帝俄将军。这是一出巨额投资影片,电影公司花了一百万美金来重现帝俄时代的宫廷面貌,而片中最重要的一幕,就是耗费20万美金来制作的阅兵仪式。正当电影拍摄阅兵式的敬礼画面时,这位俄国将军竟突然从马上滚跌下来离奇去世。这部影片最终并未完成,而以“最后的命运”的名字发行欧美。
金耀东对这位俄国将军的故事无从释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歉疚:
过去率领韩籍杂色军在滨海省附近追击白军的一幕,又凸显在他的记忆里。他觉得自己就是促成这白俄将军演悲剧的因素之一。如果不是他们的猛烈攻击,谢米诺夫远东共和国的崩溃不会那样快。[4](P.33)
对于俄国将军的悲惨命运,金耀东自觉难辞其咎,这种自责的心情,就跟《露西亚之恋》里金面对白俄遗民时所萌生的歉疚心情一样。作为军人,战场上各为其主难免需要跟陌生或者与自己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势力发生冲突,金耀东本毋需对俄国将军感到歉疚或者同情,然而有一种高于军人道德的因素让金耀东为对方感到难过,这就是“同理心”。
在叙述完俄国将军的故事后,叙事者叙述道:
他(金耀东)不禁痛苦的想起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血淋淋的一幕——EGCO HOMO*《龙窟》排版为“EGCO HOMO”,应为“ECCE HOMO”之误。(看这个人啊!)
俄罗斯亡命者是“这个人!”他自己也是“这个人!”[4](PP.32-33)
金耀东对白俄将军的悲剧命运感到内疚,一方面是因为白俄将军与金耀东一样,遭遇亡国和流亡的困苦﹐经历十分相似;另外也因为韩国独立军为了换取红军的武器,曾在远东的俄国革命战里,追击跟自己素无嫌隙的白俄军队。金耀东深知,这种基于一己私利,出卖他者利益,将自己深有体会的苦痛加诸白俄军队身上的行为,实在有违道德与正义的立场。
除此之外金耀东心生愧疚,还是基于一种“命运意识”。对金耀东而言,白俄将军的悲剧命运,并非偶然,而是命运特意的拣选。金耀东对自己的命运,也有类似的感悟。当他想起俄国将军的悲剧时,他对自己的命运作了一番提问:“他(金耀东)犯了什么罪?造了什么孽?受生命如此狠毒无情的诅咒与报复?”[4](P.33)基于这种“命运意识”,金耀东想起了耶稣受难的图画,想起“ECCE HOMO”这句话,然后总结道:“俄罗斯亡命者是‘这个人!’他(金耀东)自己也是‘这个人!’”这些联想并非巧合,而是源自一种世界主义精神的觉醒。“ECCE HOMO”是拉丁文,意谓“这个人”,亦有译作“瞧!这个人”,专指圣经故事里,耶稣受难的形象。除了基督教渊源外,尼采亦曾以“ECCE HOMO”作为他自传式思想论著的标题——汉译书名为《瞧!这个人》。尼釆借书名暗示自己也是被时代和历史所拣选,借此展现出一种命运意识。这种命运意识在《狩》还被联系到人类文化历史里,另外几位被命运召唤或拣选的人:
跋涉在恒河畔的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释迦,苏格拉底的毒药,冰天雪地中的华盛顿的悲惨大溃退,贝多芬的聋瞶与命运交响曲,尼采的疯狂……[4](P.26)
耶稣、尼采、释迦、苏格拉底、华盛顿、贝多芬等人的故事,跟俄国将军的悲剧一样,被金耀东归类为“一幕又一幕的生命大悲剧浮雕”。这些人物似乎都蒙命运的召唤,注定遭受极大困苦,嚼透生命的悲苦。至于金耀东对这种苦难,亦深有体会。他为民族吃苦,退居外兴安岭,韩国独立运动似乎已经遥不可及,但金耀东仍无法摆脱困苦,彷佛命运已经将他选定,去演绎这出生命的悲剧。金耀东对这些陌生人表现出一种超越时空国族的同理心,实际是一种世界主义精神的极致体现,就如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的概念一样:
罗马人凭借直觉而实行的普世政策及其倾向也存在于德意志民族之中。法兰西人在革命中所赢得的最好的东西,也是德意志特性的组成部分。[5](P.51)
就文化传承的角度言,日耳曼民族并非罗马文化的嫡系继承者;至于当时的法国,则是德国的入侵者,是日耳曼民族的敌人。然而诺瓦利斯的观点却超然于国族的偏见,站在普世人类的高度指出,国族间的文化实际互相交融影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在国族文化之上,尚有一更高层次的单位,即人类文明的总体。《狩》的金耀东,也就是站在人类文明的总体高度,才在想起白俄将军的同时,联想到耶稣、释迦、华盛顿、贝多芬和尼采等人。在此,无名氏作品的世界主义精神,已得到全面的展现,这是一种超越国族、政见、宗教信仰,乃至时代的同理心,当金耀东想到“俄罗斯亡命者是‘这个人!’他自己也是‘这个人!’”的时候,“你”、“我”、“他”的界线顿时被打破,剩下的就只有“我们”这个集体。
四、结 语
《亚细亚狂人》的世界主义精神,让无名氏作品在主题和写作风格上逐步确立出个人的特点。世界主义精神主张肯定“他者”与“自我”有着同等的价值,并肯定“他者”的文化。从《露西亚之恋》和《狩》等文可以看出,《亚细亚狂人》肯定国族之间的差异,但国族之间仍然可以互相理解、体谅和尊重。国族之间不应互相轻视,而是应该站在对等的地位彼此对话和欣赏。这种平等观念,成为无名氏作品的一大核心思想,从而为无名氏作品的主题和风格奠定出一种独特的基调。沿着《亚细亚狂人》的世界主义精神,无名氏萌生出“写作‘全部人类历史’的计划”,也就是《无名书》的写作计划。1945年无名氏放弃《亚细亚狂人》,并在1946年动笔写《无名书》,转向展望人类未来的存在意义,东西文化的融合,以及人类未来的理想社会形态,这种创作取向,实际是对《亚细亚狂人》世界主义精神的延续探索。
[1]无名氏.露西亚之恋[M].台北:远景出版公司,1976.
[2]李存光,金宰旭.解开无名氏的长篇小说《荒漠里的人》之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7).
[3]李范奭.李范奭将军回忆录[M].龙东林,朴八先编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4]无名氏.龙窟[M].香港:新闻天地杂志社,1976.
[5]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M].孟钟捷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