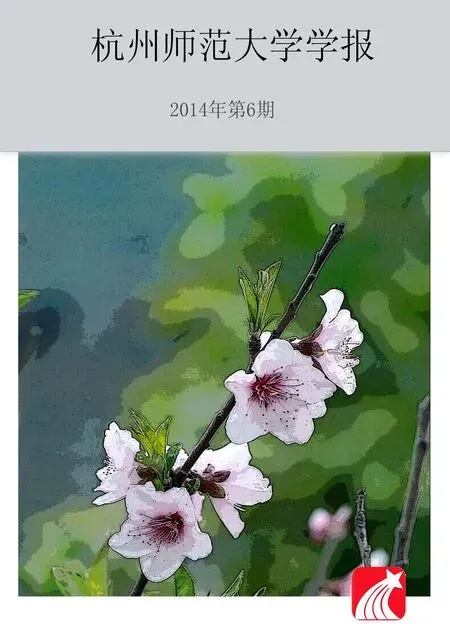叙事的诗意追问
——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史外史观
彭亚非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一、天地间无非史
中国古代的历史叙事之所以是中国叙事文学的发端,是因为从一开始它就具有文学叙事的因素。比如中国上古历史,就可说是历史叙事的文学建构的一个结果。历史消失在时间之中,只有在历史叙事中,它才能重新获得内视性的具象性存在。但是三皇五帝之世,其实已经飘渺难知。要真正进入这样的历史,所能依据的便只能是想象和想象性的内视建构。而这,也就进入历史的文学化和审美化的过程了。
这可能也是历史叙事的宿命。人类历史记忆与想象的滥觞,也正是人类内视世界建构的发轫。记忆与想象是历史建构与历史审美的前提。动物是否已经有记忆与想象能力,因为动物不能通过语言表达,或者说因为人和动物之间还没有能够共享的语言形式,而不能确知。但人类内视世界的出现,肯定是先于语言的。也就是说,在人类拥有完整的语言形式之前,记忆和想象能力就已经开始发育起来了。因此,原始人类的表象思维的发达程度要高于语言形式。但是如果没有语言,原始人类的表象思维内涵也无法交流与共享。因此,在完整的语言形式形成之前,人类应该有过一段通过声音、表情、手势和体态来交流与共享表象思维内容的“立体语言”时期。就此而言,人类内视世界的建构,与人类语言的出现和成型,应该是同步进行的。这是人类语言足以建构、传达和共享内视世界的人类学前提。
但是记忆不同于回忆。记忆只是心理印记,是在条件相类的情况下帮助记忆者作出正确反应的能力;而回忆则是使记忆成为纯粹的心理事件。回忆是对记忆的享受。是在心理上重温曾经的生理性过程。因此,回忆本质上是个将记忆重构化和审美化的过程。因此,动物有“记性”,但动物不会“回忆”。狗会“记得”并“认出”旧主人,但它不会在离开旧主人之后的生存中,经常“回忆”和旧主人在一起的日子或经历过的事件。因此,动物很可能有记无忆,不会通过“忆”来“享受”它所“记”住的东西。
因此,历史的内视性重现是从回忆和追忆开始的,是对记忆的追溯、重构和想象。而且,作为一个完整的内视生存的世界,它必须通过语言或文本建构起来。中国古人似乎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王若虚在《文辨》中说:“凡为文有遥想而言之者,有追忆而言之者,各有所定,不可乱也。《归去来辞》,将归而赋耳。既归之事,当想象而言之。”[2]这无疑是对文学内视审美本质的一种精确描述,不光有追忆的过程,也有想象、虚拟或曰假想性虚构的过程。中国古代的历史叙事,正发端于这样的过程。
《左传》建立在追忆、记忆重构和想象性虚构基础上的历史叙事,可说是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份包含了丰富的内视审美意识的历史文学样本。
首先,《左传》有明确的想象性虚构叙事理念。比如在它所叙述的240多年的历史中,几乎每一次占梦卜筮的结果都应验了。比如庄公二十二年载,懿氏将嫁女与陈敬仲为妻,占卜预言敬仲将在齐国昌大。而陈国灭亡后,敬仲的后代陈成子将在齐国专政,并“代陈有国”。又如闵公元年载,晋赐毕万魏,毕万占卜,结果预言其后代将为公侯。而这两个预言后来都为实际的历史发展所验证了。但这两个堪称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春秋之后,也就是《左传》所记录的历史时期之后。可见这是《左传》作者在知道这两个历史事件的情况下,基于某种历史命定观念,在叙述以前的历史时所预设的一个情节。这样的情节虽然可能有某种传说的蓝本,那也只能证明它更是建立在民间口头文学基础上的一种想象性虚构,显现了某种原始神话思维的文学基因。而且,这一虚构的内视审美意识的自主性和刻意性还表现在,这两个发生在战国时期的历史事件,不光为春秋时的卜筮所预言,而且也为当时一些贤人智士所预言。如晏婴在昭公三年对晋国的叔向预言前者说:“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而孔子在昭公二十八年预言后者道:“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其长有后于晋国乎!”(魏立侯以后亦称晋国。)这显然不是基于历史真实的理念而是基于历史本质的理念所有意强化的内视审美建构。这样的历史文学意识,事实上也成了后世俗文学传统中历史演义的基本理念,并且在历史演义之“义”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十九世纪末,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建筑师路易斯·H·沙利文(Louis H Sullivan,1856~1924)最先提出“形式追随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的口号,是现代主义最有影响力的信条之一。沙利文是19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第一代芝加哥学派的中坚人物和理论家,他的设计观念是从建筑的角度来谈功能和形式之间的关系,但事实上,他倡导的“形式追随功能”设计观念明确了功能与形式的主从关系,符合新时代工业化的精神,成为 20 世纪前半叶工业设计的主流即功能主义的主要依据,甚至对日后许多设计师的设计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还强调“哪里功能不变,形式就不变。”
其次,《左传》有明显的强化内视生存效果的具象性追求,表现出的正是以历史叙事为内视审美活动的某种文学性意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书中虚构性的细节描写看出来:
宣公二年,晋灵公因暴虐无度受到赵盾的一再进谏,便派了刺客鉏麑去刺杀赵盾。鉏麑“晨往,寝门辟矣,(赵盾)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这是一个为学界所熟知的很有名的例子。当时鉏麑身边无人,因此其自杀前的独白细节,显然只是为了增强叙事的内视性在场效果而进行的文学性虚构。不用说,这一虚构大大增加了内视审美的生动性和逼真性。而这一以追求内视审美效果为目的的虚构性历史叙事意识,正是后世俗文学传统中历史演义之“演”的核心理念。
《左传》并不满足于对历史事件的概述,而是通过许多生动的情节与细节,塑造了大量性格各异的历史人物形象,给后人创建了一个具体可感的、提供了丰富的内视生存体验的上古世界。在这个内视世界的营造中,《左传》表现出相当文学化的对传奇性和内视审美效果的强烈兴趣和自觉意识。
历史叙事中这种自觉的内视审美意识,在同样为先秦典籍的《战国策》里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并且最终为司马迁的《史记》所继承和发扬。《太史公自序》云:“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成仁取义、风流倜傥、时势英雄、风云际会、建功立业、显身扬名于天下,由这样的一组组英雄群像构成一幅千年历史画廊,这就是司马迁写作七十列传所要达到的历史叙事目的。这样一个塑形性的历史叙事理念,显然具有明确的、有意的塑造人物形象、创作英雄传奇的文学性追求。鲁迅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感叹它充满了激越的个人情感和丰富的诗性美感;而实际上,《史记》堪称一部散文体的长篇史诗。
《史记》作为中国历史写作中永不可及的最高典范,树立了多方面的高标准。其中有一项最具文学价值的成就就是,《史记》是中国所有的历史著作中最具想象力的一部作品。除了司马迁特立独行的历史写作理念之外,《史记》是中国所有历史著作中唯一一部主要为“遥想而言之”的作品,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史记》前后的其他历史著述,即使不是亲历者、当代者的记忆之作,也大都是人们对刚过去不久的历史“追忆而言之”的作品。这也大大降低了人们基于内视审美建构的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和虚构的可能性。因此,《史记》之后,历史写作的文学化就难以为继了。裴松之注《三国志》,就是使历史具象化的一种努力。也正因为如此,《三国志》才成为了后世俗文学取之不尽的题材渊源之一;而事实是,没有裴注,就没有《三国志演义》。裴注《三国志》,成为《史记》之后最具文学想象性和内视审美魅力的历史杰作。
中国上古虚构文学不发达,所以从一开始就由史传文学担当起了古人内视审美活动的主要责任。历史取代神话,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内视审美建构。司马迁过于历史上所有历史学家之处,就在于他的史传写作更具文学性,充满了人生性、具象性、戏剧性和性格色彩,充满了内视审美的诗意与美感。因此中国由传奇而小说的写作,其实源于司马迁。
不过历史叙事的文学性,并没影响中国古人对历史叙事真实性的判断,反而由于历史叙事是唯一的古典叙事文学形式,使得中国古人认为后起的所有叙事文学写作,也只能是甚至必须是一种历史叙事。至少在文学写作的潜意识里,他们很难摆脱这样的历史叙事情结。
二、正史之未备
但是历史叙事依然具有很大的审美和内视建构的局限性。这不仅是史学家个人写作理念的问题,而且主要是历史文本化自有其要求和标准的问题。它只关注重大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以及整体性的历史过程,因此不能不带有很大的抽象性与概括性。因此:历史无细节,此其一;历史是个舞台,只有角色性演出,没有幕后的生存故事,此其二;历史是事实的罗列,不是生活逻辑、情理逻辑的完整而自洽的呈现,不构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诗意人生、人格、人情,因此,也不构成完整的心理过程和充分内化的心理事件,此其三。它并不是人类具体的生存史。人类具体的生存历史,实际上是由文学勾画出来的。因此只有文学,才是全体人类时间性生存的家园。而这一点,正是文学叙事最早的存在理由,以及其最早的文学本质意识。
因此,历史叙事的文学局限性,导致了中国叙事文学的史外叙事的审美追求。事实上,当裴松之注《三国志》的时候,这样的意识可能就已经开始萌芽了。因此,他引注的更为丰富更为具象的材料,很多都来自野史,实在只是民间传说。但他乐此不疲。这使得他的注充满了俗文学意味和俗文学精神。
因此,在裴注之后,中国古人的内视审美追求就逐渐移出正史,而指向了野史和杂史。李贽《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书发凡》云:“失之于正史,求之于稗官;失之于衣冠,求之于草野。”[3](第3册,P.128)李贽所说的失之于正史的是什么呢?他没有明言,但既然存之于稗官之中,其中显然有深意存焉。而明人熊大木的一段话也许正可看作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或谓小说不可紊之以正史,余深服其论。然而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若使的以事迹显然不泯者得录,则是书竟难以成野史之余意矣。……则史书、小说有不同者,无足怪矣。”[4](P.145)正史失去的,正是历史宏大叙事之外被忽略了的人的具体生存,正是被历史重大事件和角色身份所遮蔽了的、由人的生活内容所构成的内视世界的具象之美和诗意之美,正是被历史的表象真实所排斥的想象的真实和真实的想象。而这一切,正是所谓稗官野史所着意追求的。诚如熊大木所云,野史之所作,不在成史之意,恰在成史外之“余意”。而史外之“余意”,即史之不足以成之“诗意”也。在正史的局限之外,正是野史要开拓和建构的更具审美性的世界。因此,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说:“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其间亦未免一二过与不及,俯而就之,欲观者有所进益焉。” [3](第3册,P.62)历史画卷在内视世界的重新建构,必须有“过与不及”,即超出历史事实的想象性虚构。这是为了观看者“有所进益”,即有超出历史认知的更高的、更丰富的、更具美感的、更深入心灵的、也更本质的收获。事实上,非具象化,非诗意化,非高度内视化,则不足以进入时间性生存。因此,历史的野史化、演义化或曰文学化,使历史转化成了历史性生存的本质化呈现。
耐得翁《都城纪胜》中说:“‘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5](P.1)吴自牧《梦粱录》中说:“又有王六大夫,原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但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5](P.3)前云“提破”者,此处云“捏合”。这两段话突出显示了历史叙事的“短板”。所谓“最畏”者,就在于历史叙事毕竟是限定的真实,即使是作为俗文学活动方式之一的“讲史”,对所讲的历史有所虚构、有所想象、有所发挥,也不离既定的历史事件与角色人物。而小说的讲述者没有这样的限定。对于他来说,他要讲的只是全然虚构的或不为历史所关注的个人生存故事。在他的讲述里,再宏大的历史事件也只是人物生存故事的背景,稍事交待就行。因此,讲史者不免担心,自己准备要“敷演”半天的历史过程,人家讲小说的一句话就交待完了。
而在这样的描述里,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以历史叙事为基本内视审美活动的中国传统俗文学意识,终于在经历了对历史余意的追问之后,将目光和思考投向了真正虚构的内视审美艺术——小说。历史传奇的审美意识,也就走向了世相生存的审美意识。
三、史统散而小说兴
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云:“史统散而小说兴。”[3](第3册,P.226)这一观点认为,小说的兴起,就意味着以史学著作为内视审美活动正宗的终结。但史传传统,是中国俗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强大的前驱。其力量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它依然是通俗小说的素材库与文化惯例,而尤其体现在小说内视审美理念的拓展依然要以历史写作理念为基本参照系,并由此而确定小说美学本质的坐标。因此,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依然云:“小说者,正史之余也。”[3](第3册,P.229)但是此处所说的正史之余,已经不是野史性质的余了。此处之余,已是历史之外的余,是历史之外的历史,是历史之外的个体人生的生存史,是俗世俗众的生活演出与众生相。
宋末元初小说家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云:“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世间多少无穷事,历历从头说细微。”[5](PP.4-6)很明显,中国俗文学中的小说意识,从白话小说产生之初,在这一点上就有着充分的自觉。它自认为是微历史、小历史、具体生存的细节历史,是非正统历史视野的个体生活诗意、人生诗意的内视化审美。历史文本的视野中止之处,正是小说艺术风光无限的敞开之域。历史舞台的聚光灯外,正是俗世人生任意表演的广阔天地。
《娱萲室随笔》中转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王渔洋《香祖笔记》,谓阳谷县有潘、吴二姓,自言是西门嫡室吴氏、妾潘氏之族,且因演《水浒记》戏剧,致成讼事。是耐庵之书,固非尽出于谰言也。……夫汉代丛书,唐人小说,当时亦不过为文人一时之游戏,流传既久,词章家遂为故实……是在好事者之广为传播耳。”[5](P.35)看起来似是无中生有、无理取闹、无聊攀附,但实际上,正可看出古人的俗文学意识。对于庶民俗众来说,甚至对于一般文人来说,小说确实就是他们的《史记》;小说虚构的故事,也就是他们真实的历史。
因此,历史也许从来就是重大事件、宏大主题的记忆与想象,而小说一开始不过是琐碎的、凡俗的记忆与想象。历史是概括的、宏观的记忆与想象,小说是具体的、微观的记忆与想象。历史是结构性的、骨架性的记忆与想象,小说是个体性的、有血有肉的记忆与想象。历史是人类文明、文化、社会演进历程的记忆与想象,小说是人类社会中各种各样的人生、生活、生存的记忆与想象。因此,历史是基于事实的更为客观、更为现象、更为抽象、更为伦理、更重规律、更具形态性的记忆与想象,小说是基于虚构但更为真实、更为本质、更为深入、更为具象、更为诗意、更富美感的记忆与想象。也因此,如果真要进入本质性和本体性的时间性存在,依照王世贞的思路,则不妨更进一步说:天地间无非文学而已。历史不过是人类人文发展的进程与历程,只有文学,才是人类的生存史、生活史、人生史和心灵史。因此,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审美追求,最终便落实到了小说中对俗世生存诗意的追问之上。
四、对俗世生存诗意的追问
《汉书·艺文志》里说小说是街谈巷语,是道听途说者之所造。这个“所造”是有意义的。人们为什么要“造”出这些道听途说的“小说”来呢?因为这是人类基本的心理需求之一。人类需要通过生存共享来确证人的类本质,来确证自己的类的存在性。一个人只有在人类生存的共相中发现自己,他的俗世生存才获得了意义。这不是中国古人的理性自觉,但是他们通过对这种最普通的文学审美方式的追求,显示了这种需要的存在。
前引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写道:“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小说纷纷皆有之,须凭实学是根基。开天辟地通经史,博古明今历传奇;蕴藏满怀风与月,吐谈万卷曲和诗。……世间多少无穷事,历历从头说细微。”这一篇论说对于通俗小说的作者提出了极高的学养及修养要求。他认为,小说本是个无所不包的内视审美世界,一个作者要能完全胜任对这个世界的营构,能使观看者因此而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则必须在知识、思想、文化、阅读资源的积累、生活经验的积累以及文字造诣方面,都能达到无远弗届的境界。其观念的核心,还是如何创构一个包容了“世间”“无穷”生存内容的内视审美世界。所谓“多闻”的写作理念,强调的依然是如何有利于俗世生活场景和生活内容的内视建构,强调的是如何将外视性生存转化为内视性生存、审美性生存的努力。他的观念中所体现出的生存诗意关怀而非人文意义关怀,正是中国古代俗文学创作最根本的理念基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古人对俗世生存诗意的发现是随着俗文学的成熟而明确起来的。因为在俗文学兴起之前,还没有任何一种正统文学活动达到过如小说中“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洞心駴目,而曲终奏雅,归于厚俗”[6](PP.300-301)这样的生存审美效果。
“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这两句话说尽了中国俗文学传统中写实性文学观的美学理想。歧者丰富多样,强调其差异性,就是要求小说类文学作品穷尽世俗社会生存之美的种种状态和可能性。致者诗意也,是对人的生存、生活的普遍性审美价值的深刻认识。同时,它也表达了中国小说美学的一个重要思想:俗世生存叙事。大约自明始,写“世情”、“世相”、“俗人”、“俗事”便成为中国通俗小说的主要传统之一。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中说:“天下之真奇,在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如果说,俗文学传统中的好奇喜异趣味是基于对世俗生存的超越性心理需要而产生的,那么人们对于世俗生存本身的诗意审美追求,则是基于世俗生存意义化、价值化的需要而形成的。宋之后,生活本身的诗意逐渐成为俗文学中写实文学观念关注的核心。
袁宏道在《寿存斋张公七十序》中说:“旷逸不足以出世,是白、苏之风流,不足以谈物外也。大都士之有韵者,理必入微,而理又不可以得韵。故叫跳反掷者,稚子之韵也;嬉笑怒骂者,醉人之韵也。醉者无心,稚子亦无心,无心故理无所托,而自然之韵出焉,由斯以观,理者是非之窟宅,而韵者大解脱之场也。……从者纵也,纵小则理绝而韵始全。”[3](第3册,P.122)韵者余音,此处则指难以言传的俗世生存的审美意味。即现世生存、生活、天然本色之诗意,即所谓真趣,性情由之而已,其审美意义本不在价值是非之理上。不基于理,亦不落实在理上。这是一种全然不同于正统文学理念的文学审美观,所以谓之大解脱。袁宏道意识到出世是真正以另一种方式、以与入世全不相干全不搭界的方式生存,而不是以与入世不合作的、对立的甚至是互补的方式生存,文人的所谓旷逸风流之不足以谈物外,正是因此。这实际上是对另一种生存诗意、即俗世生存诗意的发现。而这一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俗文学的审美成就。这一番议论,也正是非正统的新的审美活动带来的新的审美认识。同时,它也是力图要将俗世生存之审美因素人文理念化的一种理论努力,即将审美的非价值化定性为俗趣之美的人文性意义之所在。
凌濛初《拍案惊奇序》云:“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则所谓必向耳目之外索谲诡幻怪以为奇,赘矣。”[7](P.741)这是对小说理应关注的世俗生存诗意形态的认识,是俗世生存诗意审美的一种自觉。生存的诗意要向日用起居中求,但并非向千篇一律的常态中求,而是要细心揣摩,关于从生活的各种变态中去发现美、体验美、感知和意会其难言的诗意。但这种生活诗意观自然也显示出某种人文局限:它对生存诗意的关注,用心追求的还是表面的、现象性的非常态效果,而缺乏对人性诗意的追问。睡乡居士《二刻拍案惊奇序》也说了类似的话:“今小说之行世者,无虑百种,然而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奇之为奇,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8](P.785)要求在生活的真相中去追求所谓无奇之奇。无奇之奇自然指对世俗生存内容的诗意发现。但这也反映了俗文学活动进入商业性消费阶段后某种双重性趣味之间的张力和冲突:一为追求超常性、他在性生存的审美价值,是之为好奇;一为喜闻乐见对现实生存的诗意性的揭示,是之为真趣。两者虽并重于通俗艺术之中,但是前者更有商业噱头,而后者因更接近对生存本质的诗意追问而更容易获得艺术存在的恒久价值。
究竟什么才是俗文学最重要、最本质的文学性内容——或曰审美内涵?这是古代从事俗文学活动的文人们所普遍关心的问题。王骥德《曲律》“论家数第十四”云:“……夫曲以模写物情,体贴人理。”[9](P.118)陈忱《水浒后传原序》说:“世道之隆替,人心之险易,靡不各极其致……”[3](第3册,P.322)均强调对世人外在的、内在的生存诗意进行全面开掘。所谓极其致者,即要求小说作者远远超出个体经验的可知程度,使拘束个体一跃而为能俯瞰芸芸众生的全知全能者。这固然是一种创作观,同时如果能做到,自然也应该是文学最吸引人之处。小说的可读性,是建立在内容的精彩和难能上的,而前提是作者、故事讲述者要能做到无所不见、无所不感、无所不知,并且足以借助文字有效传达,读者才能同样感同身受,成功建构内视世界,共享内视审美收获。因此,作者首先得是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观审者、感知者。作者的观审、感知的能力与程度,以及传达观审、感知内容的文字功力,往往是作品能否成功的关键。对小说内容及其可读性的关注,正是俗文学活动蔚为大观后的题中之义。
林纾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小说翻译家。他在其所翻译的《孝女耐儿传序》中写道:“天下文章,莫易于叙悲,其次则叙战,又次则宣述男女之情”,“(狄更斯)以至清之灵府,叙至浊之社会”,“……《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其间点染以清客,间杂以村妪,牵缀以小人,收束以败子,亦可谓善于体物。”[3](第3册,P.157)虽然已经可见西学的影响,比如拳头加枕头之类抽象的、非价值论的审美母题,但依然可以看作是中国俗文学传统对小说写作内容的进一步审视。其着力强调的,依然是要善于体物,即要善于发现生存的诗意,善于营构审美的镜像呈现,善于创造并提供色调丰富、细节多样的俗世生存的全幅画卷。
至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理念,通过对历史叙事情结的不断超越,最终在通俗小说的创作实践中达到了自觉——其最根本的理念就是写出世人俗世生存的诗意与意趣。《儒林外史》如此,《红楼梦》亦如此。不用说,这也是人类叙事文学存在的终极目的之一。
[1]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G].北京:中华书局,2006.
[2]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校注:卷34[M].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
[3]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黄霖,罗书华.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序[G].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
[5]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黄霖,罗书华.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今古奇观序[G].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
[7]凌濛初.拍案惊奇[M].石昌渝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8]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M].石昌渝校点.南京:江苏古藉出版社,1990.
[9]王骥德.王骥德曲律[M].陈多,叶长海注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